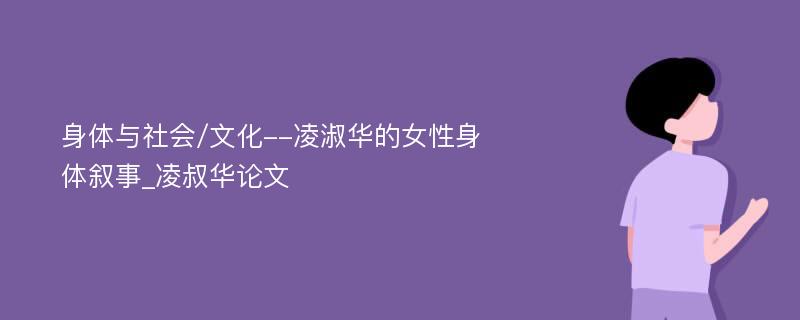
身体与社会/文化——凌叔华的女性身体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凌叔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新闺秀派作家凌叔华
三十年代被称为“新闺秀派作家”的凌叔华(1900-1990)①,与“闺秀派”的冰心及“新女性派”的丁玲、冯沅君等齐名,被称为“新月派作家中的小说圣手”,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②。本文试图评析她的女性身体叙事如何作为一种容器,构成各种社会/文化身体的聚合体,隐含着(特别是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女性身体的隐喻。
身体的社会/文化聚合体的容器论述,可借助特纳(Bryan S.Turner)的观点加以参考。特纳在《身体与社会》导言中指出了身体的悖论:我们的身体即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身体,我们的身体被体现,有如自我的显现。通过身体融入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中,重新思考了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身体与社会构成的辩证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身体视为生物有机体进入社会理论;象征互动主义将身体作为再现的自我而出现;而弗洛伊德主义则将身体体现视为表现欲望的能量场域③。在这些身体悖论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争论中,女性身体往往被赋予神秘的表象;特别在富于张力及矛盾倾向的女性文本中,更能凸显女性身体与社会如何整合、融解的运作。每一种社会的身体理论与管理学说,都有各自的依据;并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进而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④,成为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
女性身体作为话语场域的体现,除了西方的身体与社会观点以外,实际上中国古代儒家身体观的学说论述体系亦久已有之。儒家学说中的社会化身体,富有强大的文化内涵,同样强调身体和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传统儒家理想的文化身体,事实上和社会的身体、形躯的身体及意识的身体等理念相结合⑤。可见不论是中西方的身体理念,自古以来就把身体概念和日常生活、历史、社会思维等联系⑥。由于身体和文化、社会习俗等关系密切,因此可以从有关视角切入女性叙事文本肌理中,以此解读女性与家庭、社会等现象。
在这意义上,身体论述不但存在于社会与文化体系之中,同样存在于文学中的身体书写领域。身体不但是物质有机体,更是一种隐喻:即女性身体是各种公/私场域的聚合体⑦。二、三十年代以降,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书写不只是涉及悲愤与控诉为主调的叙事模式,女性身体亦成为可观的文化符号空间,是实体界与象征界的社会/文化的聚合体,其界线往往无从划分。性别差异与家庭结构,主体身体与客体的联系,在聚合体中展现某种程度的分裂与对立。从哲学理念推而言之,女性身体的书写已从柏拉图的“空间”转变成当代性别论述中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容器”。而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我们亦能找到此类富有西方身体理念和传统宗法文化的身体铭刻。这种女性主义概念中的身体/容器论述,构成强大的文学文本建构,以及社会、文化建构。⑧借助有关视角切入五四女性身体的叙事文体,或可为这时期的女性文本重读,提供新的视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的女性身体书写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酒后》,时年25岁的新时代作家⑨,甫一出手就以富有女性自主意识的情欲主题挑拨家庭伦理。她往后的小说作品,大都含有女性与文化、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所建构的女性闺秀叙事,并不完全只是男性批评下的“次要”作品,其中亦有反映上层社会女性的身体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表现女性在历史变迁中所遭遇的、唯有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作家才能感同身受的身体内在场域。
在1930年代,正是由于凌叔华的作品甚少涉及重大的社会、时代问题,甚至被指为只限于女人和孩子之类的家庭琐屑内容,因此只被当时的文学界视为“次要”作家,特别是男性批评家,将她归属于所谓“新闺秀派”的代表作家⑩。这种被边缘化的女性叙事之言论与评价,其实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早年即提出“父权批评”(Phallic criticism)的术语理念,揭露此类父权/男性批评家的批评偏见。这些父权/男性批评观点倾向于将女性作家的作品本身当作是“女人”加以看待,运用诸如迷人、甜蜜、顺从等狭窄的形容词去评论女性作品,过度地关注女作家的女性气质(11)。凌叔华的文本解读似乎也有类似的困境与瓶颈。
虽然,五四以来的学术界对于凌叔华文本中的女性与身体叙事仍未充分地被解读出来,然而,早年朱自清和鲁迅等人也已经很重视凌叔华整体的创作成就。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已把凌叔华列为五四时期六大女作家之一。沈从文在女作家中也最看重凌叔华,认为凌叔华是女作家中一个不容易被忘却的名字,她的《花之寺》和《女人》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他特别强调凌叔华的女性书写,为女作家中走出一条新路(12)。此类评价无疑为凌叔华作品提出了女性文学论述的新思维。
以往学界对凌叔华的研究通常局限于鲁迅“高门巨族的精魂”来考察她的女性写作,并没有把凌叔华有意面向新时代的女性书写中的女性自觉意识与身体写书结合起来,也没有考察她的作品如何在女性身体叙事中探讨或表露的文化、历史意蕴。实际上,凌叔华早期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叙事隐含着社会化身体和文化身体的话语场域。她的叙事文体之肌理深入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女性闺秀型态与生活内涵,因而变得颇为复杂迂回。她的闺秀叙事笔锋亦深入女性身体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不稳定状态与女性问题,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碎情感,提供了新的观察模式。
这方面的议题讨论,史书美指出“五四”的启蒙话语实际已将性别话题纳入了现代文学中的反对传统体系中。此种新传统话语进一步通过理论范畴的方式把性别和父权问题公开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京派女性作家,特别是凌叔华、林徽因和冰心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将女性问题和现代性定义结合而展开热烈的讨论(13)。史书美相信京派作家中,例如凌叔华等欧美留学生所组成的新月社的文学团体,流行着双重文化主义的世界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虽然挑战了现代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东西二元划分,但却从未挑战过性别的二元划分。为了参与进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肯定传统的事业,女性由于自身与传统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关系而不得不采取了一种相对曲折迂回的现代性写作路线。她们既是传统的遗产,又被拔除在传统之外。正是这种二重性塑造了她们与地区性之间的关系,而从西方传来的女性主体性观念则已然向这种对女性的驱逐行为发起了挑战。(14)
在这种双重文化视野的世界主义观点中,五四时期以降从西方所传进中国文学书写的女性叙事,无疑让凌叔华看到女性处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国际)之间的矛盾情境。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因而充满了矛盾而复杂的文化、心理书写。凌叔华选择了在宗法父权体制内书写女性的身体与文化现象,实乃通过讽刺性的模拟暗中破坏了父权的写作模式。她的作品不难发现此类边缘化女性的声音,并从内部瓦解了父权声音(15)。因此凌叔华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充斥着两种声音冲突的“复调话语”(16),而这种冲突在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模仿中显得尤为明显。
周蕾针对凌叔华的叙事主题,提出以“贤淑的交易”(Virtuous transaction)视角评价她这方面的书写主题,指出这是传统社会中一种特定道德:“自我牺牲”的显现。
这种要求女性作自我牺牲的“贤良淑德”隐含着一种交易:教中国女性放弃她们自己的欲望来换取她们的社会“地位”。我这刻意简单和方程式化的设题是为了要突出女性的哀怨是源出于一种含上的契约,而非出自她私人的自哀自怜。(17)
周蕾明确体察到此一女性身心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契约关系,指出女性言行中此种“最琐碎的感情”、“最琐碎的活动”,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社会意义的交易,涉及了女性身体和心灵在公与私领域中的角色扮演与文化身份的问题。通过含有讽刺性模拟的叙事强调了女性的声音,同时超越文学传统重新定位女性的美学,以及她和文学传统之间的“良性交易”(18);从中不难体察凌叔华的女性/闺秀身体叙事,实则包含了社会、文化的话语场域。
周蕾从“闺秀派”文学视角,特别关注了凌叔华小说中有关封闭、困厄和局限的女性世界;认为此一女性世界一旦被写入文本就有了作者美学观感的介入,而被女性作家用以颠覆父权制度的一种手法。从制度“内部”揭示意识形态上常被认为是“正常”的社会文化运作,其实隐含了女性的重大问题。当女性和社会进行着贤淑的交易达到最完善的阶段的时候,也是女性的自我牺牲到了最不合理的时候。这构成五四女性小说叙述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种表现(19)。这种颇为纯粹的、较少受父系叙事语言污染的女性写作中摆脱父系话语的历史残骸,还原女性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形态与本质。
在两种双重声音冲突的“复调话语”叙事中,凌叔华通过贤淑的交易刻划出女性人物被囚禁于父权制度下的境遇。她的女性叙事既有性别维度,亦有阶级维度;既有身体维度,亦有社会/文化维度。这不只是她对父权制的质询,同时也是对社会、文化阶级的质疑;不只是对女性身体私有领域的探询,同时也是针对宗法父权公有领域的反拨。
未婚女性:闺秀身体的社会/文化聚合体
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叙事及其闺秀身体,乃作为某种社会文化载体的现象与意义。因此,她的女性/闺秀身体书写除了表现女性身心的经验之外,往往亦含有社会/文化的现象。女性个体的身体,转化为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身体,构成她笔下社会/文化聚合体意义的闺秀身体叙事,从而把女性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文化关系的手段加以叙事化使用。
在身体的理论建构中,物质身体形象常被视为自然生理物质与文化产物相结合的现象,是作为指涉中心的再现和实践,其中可能涉及三个语义领域,即个体身体、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身体既是生理意义上的自然产物和文化产物的结合体,有着特定的历史性意蕴,分别包含了物质身体作为指涉中心的再现与实践的三个语义领域。个体的身体含有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身体,社会身体则将身体形象作为一种描绘社会关系的手段加以使用,而政治身体乃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来规范物质性身体(20)。这些不同层次的身体语义领域,或多或少从不同视角体现在凌叔华的闺秀身体叙事中,其中有不少女性个别身体与社会、文化重叠的话语场域。在社会化形态的身体意义视角,揭示女性/闺秀的身体现象和社会、文化互动的关系。
不论未婚或已婚,凌叔华笔下女性的活动场所大都集中于家庭空间之中。在《绣枕》一文中,大小姐即是借助刺绣活动展开她个人的社交空间。虽然这属于隐性的社交活动,却试图通过她过人的刺绣成品的展示,换取美好姻缘的机会。《绣枕》一文中那对精致的绣枕正是大家闺秀陷于家庭与社会空间中,一种不堪情境的体现,揭示出传统家庭中此类大小姐们生命价值的隐喻。那对用了大半年时间精心缝制的靠枕,换来的只不过是男性公众社交场域中的陪衬品。
从《绣枕》中,不难发现大小姐原本期望以过人的女红功夫赢得理想婚姻,通过一系列提示和具体化的表述刻划了大小姐的实际不堪处境。通过绣枕揭示出这些按传统方式生活的“大小姐”们所将面临的命运:她们有如一只被醉酒男人所吐脏、以及被当作脚踏垫子践踏的陪衬品。最后被白总长的少爷叫仆人给捡去:
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印。(21)
此一惨遭糟蹋的绣枕作品,象征了大小姐的闺秀生活的真实价值写照,完全是他者的替身存在,并进一步扩大成为符号的文化空间。凌叔华的笔锋勾勒出中国最后一幅旧时代的女性刺绣图像:一个少女坐在闺房里,下意识地刺绣,时间在她意识中近于停滞,与一切隔绝。她的人生价值在于嫁给一个同属上流社会的男人,但是那个上流社会的男人却已经瞩目更加新式的时代女性,对于传统女红的功夫已然近于完全不在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加以糟蹋。此篇中的旧式女性与其它篇章中的新式女性之间,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隐约的描绘出两种女性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冲突。
在此,绣枕及其制作者本身就是一系列富有女性/阴性的白色符号——这里借用西苏的“白色墨水”的概念——含有自我分崩离析的语境,将女性日常生活及其生命一一进行剪裁、重组和摘录。此中凌叔华选取了深具文化意义的意象,表明这些闺秀的生活几乎就像“绣枕”一样是空白的符号形态。孟悦和戴锦华即指出了此中的意义:
深闺的主人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她的行为和去留取决于闺房外的男性世界。这里只有待他人估的价值,而没有自身的价值,无论是盛年未嫁的大小姐的价值还是她的劳动——刺绣以及她的劳动产品——绣枕的价值,都得待他人来定。(22)
从他者的意义而言,《绣枕》中的大小姐也是旧文化体制中另一种女性亚文化生活的仪式化体现。为了完成一件天衣无缝的手工,她征服了所有困难之后,面对被糟蹋的心血作品后她才了解到:她的生活一如她的手工一样不被社会所重视,甚至体现为一种牺牲者形象出现,在家庭中永远禁锢着她们。周蕾指出,凌叔华手笔过人的地方即表现在她的叙述结构之中:作者对人物困境虽然很了解,但不会为她们创造一条走出禁锢地的出路。
反之,她的了解缩了进去,成为这个被牺牲妇女的强烈自恋感情。这可以从大小姐对刺绣的记忆转而变为对一个梦的记忆而见一斑。(23)
作为女性/身体隐喻的绣枕,最后仍然落入另一个女性的手中被重新使用而有了另一种存在的价值,然而却是更低一层面的剩余价值:从大小姐阶层落入婢仆的阶层。此中绣枕和糟蹋绣枕的父系社会构成对立,显然涉及女性被压抑的身体话语。当大小姐一旦知道精心刺绣的枕当晚就被弄脏后,决定不再刺绣而过其平淡的人生。她和她的超人女红功夫,在传统家庭场域中已然处于更低位的社会文化边缘,不但不受重视,最终更遭受排斥与糟蹋的命运。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绣枕就像女性/闺秀身体一般,隐喻了她们置身于家庭(私人)和社会(公众)领域中的悲哀。凌叔华的世族背景,让她笔下的女性书写有能力展示社交内容的文化场域。这些交际活动,诸如上流社会所盛行的下午茶聚会或各种宴会喜庆等等,其中《吃茶》和《茶会以后》等篇,即有着这方面复杂而细腻的刻划。(24)
《吃茶》一文,有更为复杂的女性/闺秀身体叙事。当芳影开始认识淑芳的表哥时,她的社交活动包括了看电影、喝茶和公园中的音乐会等。她与同学淑贞的表哥王先生一起去看电影,而留学归国的王先生常以西方绅士的态度为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帕,并细心翻译电影中的爱情对白。散场时为她披衣,出戏院时扶她上车接下帽子,有时候还紧紧地望了她好一会儿等等的绅士行为,让芳影陷入单相思之境。她从中国传统两性关系为判断依据,认为王先生对她有意,误认其绅士举止说明他“处处都对她用心”,不禁暗恋起他。这些细节描绘通过芳影回想她们交往的各项言行中表露出来:通过“爱能胜一切,爱是不死的”耳边“喁喁细语”,柔情蜜意地轻轻敲击着芳影“幽闺自怜”的心扉,让她心神摇荡。芳影的心情有些浪漫的想象空间,不时脸红心跳:
午饭后,她在闺房,看着窗上花影因日光忽明忽暗,花枝因微风摇曳,婀娜生姿,只觉得心里满满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25)
此中情境的爱意,而后落在年华如流水的青春伤逝中,让她的眼中蓄满泪水。中西方男女社交礼仪的文化差异的习俗,导致芳影内心爱情和婚姻的憧憬最后遭受到破灭的结局。当王先生来信邀请她参加婚礼,她才大梦初醒。这过程构成芳影认识现实与自我的一种方式,眼泪无声息地在她的一声咳嗽中流了出来:
这请帖好似一大缸冷水,直从她头上倾泼下来。起先昏惘冰冷的,后来又有些发暖,不多会儿仍旧发凉,她一阵一阵的说不出的难受。请帖已经掉在地上,她捡起再看,依旧和方才的一样。随着甩了它,往大椅里很重的坐下,咳了一声,眼泪不禁滴滴点点的流下来。(26)
中西方男女交往的不同心态和方式,误导芳影陷入爱情的迷雾之中而深受其害。芳影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所遭遇的经验,在凌叔华的叙事文体中很自然地流露于日常的看电影和接物待人的社交活动之间,轻描淡写中却带出芳影身心内天翻地覆之转变。芳影显然不能一时从爱情破灭的现实中平静下来,她的自我和尊严丧失在中西文化差异之中:东方女性身体受到西方男性礼仪文化的打击。无疑的,芳影的少女身体演变成为中西文化差异的话语场域,展示了女性在文化与性别结构中私人身体如何在公有/社交领域中的独特经验,不但构成中西方社交习性差异的实验场所和牺牲物,也隐含了女性身体及其内在世界情感的创伤主题。
此外,《吃茶》中还有另一个和大小姐同样遭遇的替身,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女性身体的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聚合体现象。这位黄家的二小姐因为跛脚的关系,走路不方便,淑贞的表哥同样以对待芳影的方式不时地搀扶她过桥、开门、上山下山,还替她拿东西。结果黄家托人叫她表哥去提亲,让她表哥又好气又好笑,解释说西方男子服侍女子是最平常的规矩习俗。芳影听在耳里深感伤痛:
芳影觉得有说不出的一种情绪,她嘴边微微显露一弧冷冷的笑容,她的眼望着窗上的花影,依旧是因风摇曳,日光却一阵阵的浅淡。她迟迟的说:“外国……规矩……”(27)
芳影肉体实质的感知,被叙事者转移到她所身处的外在环境之中被突显出来。此中喻意体现在寻常生活细节中,含有传统文化和女性身心拟仿,被叙事者扣连于无可避免的社会、文化差异。
可见《吃茶》一文的女性身体叙事可体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话语场域,揭示女性理想爱情与现实的缺憾,以及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下的女性经验。现实社交事件转换成社会文化的仪式化行为,重重打击了这一位深闺中的“大小姐”——她亦可视为《绣枕》中大小姐的另一个隐性复写。女性自我和尊严,在她们身上皆遭受创伤的苦痛,体现为女性/闺秀身体的话语场域。在这些女性身/心受创的时刻,凌叔华冷静的为芳影(包括其它大小姐们)留了余地,没有让她(们)出丑:只写芳影知道真相后,倒坐在木椅里流泪(28)。此外她也受到好友淑贞开朗风趣的引导。此中芳影和淑贞的姊妹情谊,在吃茶相聚的生活常态中互相取暖,构成大家闺秀生活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体现。
吃茶的聚会无疑是这些闺秀小姐的生活社交活动。在凌叔华淡雅的叙事语言中讲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生活空间中有关身体、心灵和文化的现象;亦刻划了女性个体身体和社会身体与政治身体的课题,可视为凌叔华小说高门巨族精魂的重心所在。旧时代女性所身处的新旧时代中的惶恐与焦虑,再三被凌叔华再现与模拟。
除旧式和半新不旧的闺秀女性外,新时代中另一群上流社会的新式女性同时出现在凌叔华的作品中。在《茶会以后》中,凌叔华笔下的大家闺秀们现身在诸如周太太的新式社交茶会场合中。众多“文明男女”参加了当时十分“时兴”的茶会活动。此篇的阿珠和阿英姐妹,以及张家姐妹、方小姐、邹太太、玛莉、莱利王、小俊的大姐和李小姐等人都是较为新式的女性人物(29)。这一群与传统闺阁待嫁之传统少女完全相反的年轻女性,充满朝气,步出户外寻找与自身相平等的伴侣。然而此篇中的阿英阿珠姐妹,她们生活中的各种茶会、游艺园和宴会等社交活动依然没有为她们的爱情婚姻打开出路,情境仍然很落寞。从马家的茶会回来后,她们笑谈着人家男女交往趣事,话题最后回到母亲所关注的、自己的终身大事。
凌叔华的叙事在这里由社会、文化场域转入姐妹俩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同样地借助外在环境的刻划道出两人的内心情感。她们在沉默中静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阿珠突然感到冷寂,纸窗为微风所撼动。房中的电灯让她们感到黯淡不明,粉墙上隐约的海棠花影揭示出她们青春易逝的感伤。她们对着惨白的花影和雨声,看到花瓶中的花卉昨天还在阳光中展示醉红欲滴的花蕾,而今天却已是褪红零粉:
黯淡的灯光下,淡红的都是惨白,嫣红的就成灰红。情境很是落寞。阿英闭目休息,只觉得窗外点点小雨拖着凉飔直滴落在她心窝上,不由得使她感到一种空虚冷涩的味儿,同时并起了种种不成形的顾虑和惧怕。这是夜风时时吹开窗纸,露出外面一片黑沉沉冷潇潇的庭院。(30)
在花影零落的青春影像中,姐妹俩试图通过茶会等社交活动开展人生新页的故事,却在爱情和婚姻对象缺席的情节中互相交错、悬搁。她们在公众领域的茶会活动中,展示她们个别身体私领域的内在世界/情感的话语场域。在黯淡灯光、凉飔小雨、夜风涌动的潇冷庭院,以及“种种不成形的顾虑和惧怕”之间,这两位姐妹的身心碰撞到社会文化的困境,在寻找终生伴侣的幽伤中隐含着东方女性的复杂情感。
不论是《绣枕》中大小姐的超级女红功夫,或是《吃茶》、《茶会以后》中的男女交往方式和内容,凌叔华笔下的这些女性群体,往往在结婚以后通常都会面对较为不幸的遭遇;严重者有如后文所将讨论的《中秋晚》的敬仁太太,轻者如《小刘》中小刘的惨淡麻木生活。从中亦可窥探凌叔华在其女性/闺秀身体叙事的实践中,如何勾勒女性婚后的悲惨经验和社会文化现象,十分富有启示与历史意义(31)。
婚后女性:妻子/母亲的身体话语场域
身体的场域化和社会/文化空间的场域化类似,都包含在家庭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领域之内。凌叔华的女性/闺秀叙事,在家庭/私有与社会/公有领域之间,展示出不同的身体话语。这可从家庭/私有的场域加以考察,亦可从社会/公有场域加以理解。
女性婚前婚后生活的失落与自我的丧失,在凌叔华笔下通过家庭内部展开,再延伸到家庭与社会等公/私领域。从大家闺秀、姐妹情谊、到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等,她的叙事文体中都含有女性身体的伤痛印记。在看似不淡、轻松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某种显性或隐性、具体或象征性的女性伤痛与焦虑等体验,凌叔华笔下身体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旨呼之欲出。
在《中秋晚》一文中,作为妻子身份的身体场域及其自我形象,落在在婚姻与习俗、丈夫与男人之间遭受各种传统女性必经的折磨体验:怀孕、生育、受丈夫和婆家冷落与打压、病痛等等,最后更以失婚为收场。本文中有关敬仁太太的身体铭刻,掺揉着迷信的世俗禁忌以及男人在婚姻生活中长期眠花宿柳的不公控诉。话说在敬仁太太婚后的第一年中秋家宴,因为一个病重女人的介入而导致她和丈夫的家宴不欢而散。由于丈夫对妻子的不谅解,敬仁太太遭受连串打击的剧幕逐步展开,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体意象,刻划了女性内在介于情感与性别、心灵与身体的伤害。
第一年中秋节,夫妻俩因为团鸭晚宴的争吵,太太回了娘家,丈夫则流连欢场,丈母娘担心女儿的婚姻而主动送她回去。敬仁最后散尽了家产,婆婆反而责备媳妇笨,未能侍候好丈夫而让他在外鬼混。她只能独自躲到厨房望着炉火擦眼泪,独自面对婚姻破裂中的伤神与恐惧。她第一次怀孕后流产了,而第二次的怀孕又是早产,竟是一个畸形儿:
八月底敬仁太太又小产了一个才六个月的男孩子。因为他没长出正式的鼻子,祗有一只耳朵,手指也不全的。大家都说是精怪,医生看了,说这是受了杨梅毒的流胎罢了。(32)
此段描写至少有两层意义:这“精怪”畸形儿正是敬仁在烟花柳地风流染病后的一个结果,这不但表示敬仁伤害了妻子,同时也表示敬仁太太的肉体在这段期间仍然是丈夫的占有品。丈夫同时在外嫖妓,却也没有放弃和太太行房的权力:前者的嫖妓可视为女性身体在公领域中被消费着,而后者的夫妻行房则是女性身体在私领域中被消费着。通过丈夫的婚外性行为,性病由公领域入侵私领域中,而妻子(同时也是母亲)和孩子都是此一传统宗法父权执行者的受害人。而从孩子的病情也显示敬仁太太也已暗中染上了性病,加深了女性身体话语场域的社会/文化内涵。
在小说结尾处,敬仁太太有点迷信地把这一切后果归咎于“命中注定”。她回想起当初婚后第一年中秋节晚饭,丈夫因赶时间嫌团鸭太油腻,吃了一口就吐出而被敬仁太太视为不祥。她因为丈夫没有吃完她所精心准备的团圆宴,内心充满了委屈和不祥的预感。到了夜半时分丈夫还没回家,惨白的月光射在玻璃窗上,投影出敬仁太太的忧心:她感觉到“恶运的魔神”降临她家。在凄寂的月光中,敬仁太太坐在卧室窗前,满心悚然之感,“好像置身在迷暗的森林中感受恐怖、寒栗和忧愁”(33)。
这情景和故事开始首节文字的月色完全相反:月儿婷婷地升上屋脊,她家的庭院仿似洒上薄薄的白霜,远近的林木亦笼罩在细霰之中。在她所调制的菜肴果饼的香味中,中秋夜的一切显得那样的安详美好。敬仁眼中的这位太太,一身湖色华丝葛的衣裙,满身绣着金碧折枝花色,脸上流露着“可爱的桃花色”:
他觉得她今晚非常的美。他想如果他是欧美人,此时一定就上去搂抱着她热烈地接吻了。(34)
可见在故事开始阶段,敬仁太太的身体呈现出幸福家庭的意象。其中的“欧美”一语,也道出此篇其实也含有一些西方文化的背景,只是没有被突显出来。在这中秋晚饭事件上,妻子坚定地认为中秋夜不吃“团鸭”晚宴将预兆着夫妻分离的不幸,因此她希望敬仁吃完“团鸭”后再去探望他生病的干姐姐。这却导致敬仁因未能和干姐姐见上最后一面,在悲愤交集下怒斥妻子耽误了他的行程,砸碎了供过神灵的花瓶,引发了夫妻关系的不和与破裂。她成为自己恪守妇道、维护家庭礼仪的牺牲品(35)。
到了第四年的中秋节,敬仁夫妻的关系已经完全破灭。这一个束缚于家庭中的少妇无条件地接受了她在家庭内部的价值原则,但这种遵守却反而造成了一场大悲剧。在两次小产过后,这位安分守己的妻子和她的母亲最后坐在周围布满蜘蛛网、蛾子和蝙蝠的小屋中,回首往事,倍感凄凉。她只能在迷信中寻找悲剧的根源,对母亲诉苦:
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他吃了一口团鸭,还吐了出来,我便十分不高兴;后来他又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36)
最终母女两人都感觉是天意弄人,天降灾祸。往日温馨的家居客厅如今已然面目全非,正厅已经“蜒满了蜘蛛网子”,当月亮升上屋脊时,“只见几个黝黑森人的蝙蝠,支起双翅在月下飞来飞去扇弄它们的影子”(37)。敬仁家最终沦落到荒凉凄惨的情境,原本象征“福”的蝙蝠意象,已然被黝黑的不幸色彩所取代。这些刻划深入女性身体内在的私领域,成为凌叔华解构和揭示女性个人身体的手段;而从前文所论及的丈夫嫖宿、及其所导致的畸形儿和病痛等情况来看,凌叔华的叙事实际含有社会身体、文化身体,乃至政治身体的不同层次语义领域,充满女性潜在的伤痛话语。
敬仁太太的委曲求全,试图通过扮演贤妻良母换取社会、文化的地位;没料她的牺牲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落得家破儿亡(儿子夭折)的悲惨命运。在“贤淑的交易”中成为彻底的牺牲品。
除了敬仁太太以外,此篇中敬仁的干姐姐亦是另一个女性身体话语的载体。当年她因为敬仁的病痛而伤心流泪。两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暧昧的关系。这段内在隐性关系或可从以下的描写中看出一二:
他辗转回想前七年他发疟疾时,她(干姊姊)坐在他床前,替他母亲招呼他吃药的情境。他不肯吃那金鸡脑丸,嫌它不干净的样子,她含了一眶泪苦苦哄他吃下去。他从她手里一口一口的喝那杯白糖水送丸药下去。末了一口,他的唇碰到她滑腻带着粉香的手上,心里另有一种说不出甜蜜的感触,不觉狂嗅了一下,她的腮飞红。(38)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敬仁对于不能见到干姐姐最后一面而竟摧毁了自身美好的家庭。而凌叔华对于干姐姐死前的身体叙事,更隐含着敬仁太太日后的现实写照:瘦削惨白的脸,带着阴晦的泪眼,披着稀松的乱发。这些都可视为敬仁太太夫妻关系破裂后,那种“病恹恹”、“枯黄憔悴”的面貌——看在敬仁眼里,不但老了许多年,而且“觉得她非常丑陋”(39),此中叙事语言充满丑怪身体的铭刻。
敬仁太太和干姐姐的女性/身体叙事无疑是此篇值得注意的焦点。女性身体所遭受到的冲击,被表现于外在环境的刻划中,体现出女性亚文化团体落在社会文化边缘的生活体验。可视为凌叔华文本的一种女性私/公领域身体的文化建构,显示女性在家庭内在遭受贬抑的写照。她们的身体不断被父权社会和文化体系所消费,作为妻子、生养孩子、照料孩子和家务等事务。
身为母亲照料孩子和家务而惨遭折磨的女性/闺秀身体叙事,在《小刘》一文中有更佳的刻划。通过小刘的故事,凌叔华试图反思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的命运。少女时期,十四五岁读初二的小刘当年曾被称为“小刘军师”,是位学生领袖人物,常有惊人的言论。那位理科教师因念“蝌蚪”的音不准而为他取名“叩头”先生;又取笑班上一个已婚小同学为“老大一只鸭子”,慷慨激昂地大加讨伐:鸭之为状,前挺后撅,行路时脚尖相对,一摇一摆;一张福福气气的新开鸭蛋脸儿,一双不肥不瘦粽子样的小金莲儿等等。(40)小刘以十分尖酸刻薄的指控,联合其它同学欺负这位新入学的朱姓旁听生,导致她在一片侮辱与嘲笑声中难堪落泪而停学。
本文的叙事者林凤,年少时原本极为欣赏小刘的这种作风言行,然而十二、三年后,当林凤在武昌重见婚后的小刘时,却发现原先伶俐活泼、俏皮风致的小刘已然消失在她的婚姻生活之中。那个曾经有着“小鸟般的轻灵”举止和言辞的小刘,已完全沦落得面容全非。林凤最后在小刘的几个孩子的尿粪臭味、鼻涕影像和极为扰人的吵嚷哭闹中扫兴而归。
重逢那一天,小刘的身体刻划完全是黄脸婆的麻木形象,她穿了一件旧青花丝葛的旗袍,襟前闪着油腻的污垢:
帘子撩起,一个三十上下,脸色黄瘦的女人,穿了一件旧青花丝葛的旗袍,襟前闪着油腻光,下摆似乎扯歪了。这是小刘,我知道,但是我的记忆却不容我相信。(41)
一个身体垮了,没有乳汁的母亲,成为一个她早年所激烈反抗的、嘲弄的愚妇模样。我们可以看到凌叔华从消极的角度描写了小刘的身体畸变。
苹果一般的腮怎会是这蜡黄色的呢?那黑白分明闪着灵活的双眸怎会是这混浊无光的眼儿呢?咳,那笑容,那苗条身材……这样我想着只怔怔的对着目前的人。(42)
少女小刘的军师形象已替换成憔悴不堪的母亲与妻子的现实写照,全然丧失了当年少女时期的自我及其自主性,隐喻了“自主的自我”(Autonomous self)的丧失,如同行尸走肉般麻木不仁。显然的,小刘已然变成当年她所嘲笑攻击的朱姓已婚同学。全文充满了深刻的反讽与哀伤的意味。《小刘》中的女性身体及其精神,在母亲的职责下消耗殆尽,成为非病征意义。
小刘少女时期的自我和自主性形象,和她今日的卑微黄脸婆的写照成了强烈而尖锐的对比。更不幸地,她对本身此一自主的自我之丧失全然一无所察,表现得极为麻木不仁。她亦无能从她丈夫和孩子身上体察自身的丧失和自我的失落。丧失了自我的小刘已无能发现自身的自主意识,成为失去自我意识的空洞能指与符号。可见凌叔华的闺秀叙事,在巨变时代的背景及传统家庭逐渐解体的过程之中展示出女性沉沦的现实语境(43)。这些受新教育的时代新女性,最终仍然落入传统宗法女性的亚文化场域中,在公/私领域之中自我沉沦,表达出女性身体如何受到婚姻和社会的制约。
通过以上几篇凌叔华的文本分析,不难看到凌叔华描绘了日常生活空间中女性身体的话语场域。她的笔锋深入女性身处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公/私领域;一方面讲述他者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刻划女性自我及其自主性的浮现与沉沦。在她的闺秀叙事中,身体与社会、家庭与婚姻、男与女等公/私领域互相结合、对话。女性处在家庭/婚姻中的私有领域身体及其社会化形态的公有领域身体之间,在其叙事文体中同时展开。身体成为叙事文体的一种符号体现,构成外在身体与内在社会文化的话语场域。女性族群的公/私领域身体存在于社会/文化的次文本空隙中,建构成凌叔华笔下的女性符号空间。她的女体书写,展示了女性指涉链中各种语境层面和女性内在/外在、心灵/社会等话语场域。
易言之,通过女性公/私身体在社会/家庭之间的生活形态,凌叔华的女性身体叙事得以展开女性私人(家庭婚姻)与公众(社会文化)领域的叙事修辞。通过种种设计的叙事手法,凌叔华的叙事体引发语言的张力与陌生化的效果,将女性的日常平淡的生活故事从男性文本和男性叙事/父权语言中拯救出来。
从这个视角而言,身为五四新时代作家的凌叔华,所关注的不是叙述政治革命或救世的故事,而是运用散漫、淡雅的所谓闺秀文体与叙事手法,通过接近世俗的语言风格,描绘家庭生活中平庸而无关宏旨的女性生活故事。主题上的琐碎本质占有文本叙事空间,而非只是叙事的时间过程;此类看似近乎“无事忙”的闺秀叙事模式,不论是否涉及“贤淑的交易”活动,都可被视为凌叔华女性书写的特色。
据此,凌叔华笔下的女性/闺秀叙事应被进一步加以重视与重读。在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往往以一种理论原则的面貌出现,其中有关女性身体论述的探讨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不只是一种与现实意义有关的女性话题或文化学、社会学议题而已。凌叔华的女性身体论述,即含有公/私身体领域的建构,并和五四其它有关“现代”的议题同时展开。传统/现代、公/私、男/女、反抗/融合、主流/边缘等现象,也常被凌叔华等五四作家所关注。
凌叔华笔下女性的家庭婚姻生活,无疑常受到社会/文化的规范而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建构;而外在身体的社会/文化影响为她的文本留下女性(内在)身体话语。在私人身体和公众身体之间展示了闺秀/女性在家庭、婚姻等领域的叙事修辞;借助这种女性身体话语场域,凌叔华跻身五四新文学的性别论述之中。她的身体书写,也成为五四过渡时代中一个伤感而郁愤的标征,其叙事体中的女性自我及其命运亦成为凌叔华文本的核心指认。说到底,面对无可逃脱的过渡时代,凌叔华也和石评梅、庐隐、冯沅君、萧红等同时期的女作家一样,她们笔下的女性身体大多隐含着性别、社会、文化等多层面语义的异/同意旨,值得反思。
注释:
①“新闺秀派作家”之称首见于1930年代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一文。毅真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女作家加以归类,冰心为“闺秀派作家”的代表,丁玲为“新女性派作家”的代表,以及凌叔华为“新闺秀派作家”的代表。原载于一九三零年上海《妇女杂志》,十六卷七期。
②凌叔华出身于贵族世家,其父的官职相当于后来河北省总督和北京市长,而其母是其父六个妻子中的第四房,她由于没有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而处在较被忽视和受挫折的婚姻之中。她母亲的祖父谢兰生(1760-1831)因是广东著名的文人画的书画家,因此自小即注重凌叔华的绘画天分。作为父亲最钟爱的女儿,凌叔华很早就被选出来继续其外曾祖父的事业,期盼她成为画家。七岁的时候,她和兄弟姐妹们被送往日本学习了三年,随后又在燕京大学外语系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转引自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2007:242。
③⑦特纳:《身体与社会》,沈阳:春风文艺,2000:54-56、62。
④这个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企图对福柯《性史》里的思想提供一个系统的形式,如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等身体“内驱力”、“需要”和“本能”等观点;在很多方面皆指出,身体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特纳,《身体与社会》,春风文艺,2000:56-59。
⑤详见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1996:8-9。
⑥见何乏笔、杨儒宾:《践形与气氛——儒家的身体观》,收杨儒宾、何乏笔编《身体与社会》,台北:唐山,2004:21。
⑧潘恩(Michael Payne):《阅读理论:拉康、德希达与克丽斯蒂娃导读》,台北:书林,1996:236-40。
⑨凌叔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花之寺》,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女人》,于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个短篇小说集《小哥儿俩》,则于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⑩(13)(14)(15)(18)(35)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2007:250、203、231、251、256、254。
(11)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思考女性》(Thinking about Wome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8:29。
(12)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见《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1983:372-373。
(16)这一术语来自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Caryl Emerson(编译),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181-269。
(17)(23)周蕾:《贤良淑德的交易——阅读凌叔华的三篇小说》,《女性人》,1990.9:113、116。
(19)“闺秀”指传统女性质素的理想规范,但在文学评论中却不是一个褒词。“闺秀”指“大家闺秀”,标志这一种被传统中国社会推许的女性质素。闺秀的质素包括了良好家庭教育、优美的个人外貌和行为,以及善与人相处的品性。到今天,除了喜谈阶级进步的人外,中国人仍喜欢使用这个词语来表示赞可。然而,当“闺秀”,这本来是理想女性的形容词被用于形容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它便带来了某种负面的、含有贬斥的意思。周蕾:《贤良淑德的交易——阅读凌叔华的三篇小说》,《女性人》,1990.9:110。
(20)斯特拉桑(Andrew J.Strathem)指出,在某种象征意义上,由于社会经常有其强制性,因此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乃有部分重叠,具有政治—法律的一面,而其实际影响最终也是指向个体,供个人身体所体验感受。详见斯特拉桑著,王业伟、赵国新译,《身体思想》,春风文艺,1999:4-5。
(21)(25)(26)(27)(32)(33)(34)(36)(37)(38)(39)(40)(41)(42)《凌叔华小说集》,台北:洪范,1984:14、19、23、24、56、51、48、57、53、56、118-119、124、128、130。
(2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台北:时报文化,1993:137。
(24)基本上,由于凌叔华叙事始终与作品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她笔下的身体常常隐藏在她的叙事主题之下,不易看到其中一些女性的社会化与文化身体话语。
(28)叙述者只是设置了一个没有正式出场的另一个芳影——即石坊塘的黄家小姐,闹得黄家“托人示意”王先生正式求婚,出丑下场。
(29)凌叔华试图通过现代的眼光写这些传统或新式的闺秀小姐,例如《茶会以后》的闺秀姐妹不满新式而昂贵的凉鞋的款式,嘲讽为“剜许多窟窿”、“掏皮花”等;而此款鞋子的价钱等于佣人李妈四个月的工资;其它张家姐妹等人的穿着也是以时髦见称。
(30)凌叔华:《茶会以后》,见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四川文艺,1998:79。
(31)凌叔华除了写作外,本身也是专业的绘画高手,一个知名画家。她笔下的女性身体书写,或许也能从艺术视角的图像学(iconography)加以解读——这些女性群体呈现的不只是社会文化层面,同时也富有心理和哲学、女性与权力关系等叙事与主题。女性形象/身体,在她的写作中或可成为视觉的符号加以解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对人类身体与体现(embodiment)早已有了艺术再现的理论,近年亦已被运用在身体社会学著作之中。基于有关背景,这或许也是研究凌叔华文本的另一视角,然而限于篇幅关系,本文没能对此进行更深层的解读。
(43)除了以上论点外,由于时代的巨变,亦有一些女性不再受囿于传统的“妇德”、“妇道”,而失去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气质;但另一方面,她们仍然满足于虚荣的、受供养的生活,并以门当户对和明媒正娶的方式自我欺骗,有如小刘一般过着麻木的生活,值得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