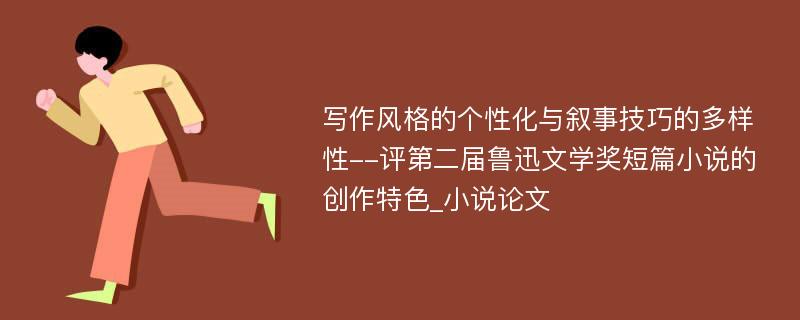
书写方式的个性化与叙事技巧的多元化——简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简评论文,第二届论文,短篇小说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话语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创作在内,受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一时陷于低迷状态。至9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家特别是60年代及其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他们真诚地拥抱现实,体验生活,关注人生,探究艺术,创作出具有较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作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5个短篇小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是:刘庆邦的《鞋》,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吹牛》,徐坤的《厨房》,迟子建的《清水洗尘》。本文拟从短篇小说写作的层面,对其创作特色作一些简略的评析。
取材的多样性和结构的精巧别致,是这些获奖小说的突出特征。《鞋》描写的是农村少女的爱情生活。作品侧重通过主人公守明给未婚夫精心做第一双鞋的过程,揭示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刻画她朴素、单纯、真诚的情感。小说的“后记”也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叙说了作者进城后对“鞋”的态度的变化:先是觉得那双鞋“太土”而退给了那位姑娘,后来又感到十分内疚。意在说明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使不少人物欲膨胀、精神失落,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严重扭曲。其呼唤美好人性的复归和企盼精神家园的重建的主旨,就从小说这种互补式结构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了。
《清水里的刀子》写的是西北地区回族老农马子善祭祀亡妻时对生与死的思索,充满了生命的沉重感。他和儿子虔诚地喂养即将当作祭品的老黄牛和老黄牛自知死之将至而不吃不喝的场面,就成为小说刻画人物个性特征的重点。作者采用交叉式结构方法,将苦难的生存状态与乌托邦式的幻想交织起来,使小说具有了形而上的抽象性与哲理意味。《吹牛》反映的则是西北地区牧民的生活,展现了大草原的广袤、神奇与美丽。作品主人公“他”与好友马杰龙在草原上席地而坐,一边喝着伊犁特曲,一边“吹牛”。从他们海阔天空的“吹牛”之中,使我们认识到劳动创造的价值,品尝到人生的乐趣,体悟到生活的诗意。作者运用了对话式结构方法,来描绘牧民勤劳、豪放的品格及其生活发生的巨变,很有新意。
《厨房》和《清水洗尘》所采用的结构同样别出心裁,各有特点。前者是对比式结构,正面呈现了大都市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主人公枝子是商界的女强人,她讨厌那些“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想回到厨房,回到家”,得到一个男人的真爱;但她看中的艺术家松泽却是一个玩弄女姓的情场高手。一个满腔热情、频频示爱,一个逢场作戏、虚与委蛇,两相对照,既嘲讽了某些人的虚伪卑劣,又抒写了都市人生中精神漂泊者无“家”可归的悲哀。后者则是穿珠式结构,以小主人公天灶要用“一盆真正的清水来洗澡”为线索,将他的家人、同学、邻居的活动片断贯穿起来,从而揭示了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贵这一主题。
鲜明的个人性和独特的叙事视角,是这些短篇的又一显著特征。作者们以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为依托,遵循各自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构建了富有个性化的文学天地。先看两位西北作家的小说。《吹牛》的审视角度比较新颖,它从两个半醉半醒的牧民倾心交谈中,把草原发生的变化如诗如画般地展现出来了。它不是亢奋激昂的赞歌,也不是轻柔悠扬的牧歌,而是一曲幽默诙谐的“祝酒歌”。《清水里的刀子》的审视点更为别致,是对死亡的追问,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那把决定人的命题的“世所罕见的刀子”究竟是什么呢?作为祭品的老黄牛真的能够“携带使命去拯救苦海中因自己的罪行而受难的亡灵”吗?这实在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命题。不过,有一点启示是明确的:人人都将面对死亡,每一个人应该像老黄牛那样“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内里,然后清清洁洁地归去”。
再看两位女性作家的小说。《清水洗尘》从一个少年的眼光和心理,去观察、感受过年的氛围与家人的情绪。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天灶觉得人在年关洗澡跟给猪煺毛一样没有区别。”接着写他觉得人们“焚纸祭祖”“磕头拜年”,使“年仿佛被鬼气笼罩了”,也不喜欢过年穿新衣裳,认为这样“太古板可笑、拘谨做作”。小说最后写他得到清水洗澡的权利时,其感情发生逆转:“天灶觉得这盆清水是好极了,他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畅快。他不再讨厌即将朝他走来的年了……他一定要穿着崭新的衣服,亲手点亮那对红灯笼。”这种叙事角度的选择非常巧妙,有利于人物的刻画和作品题旨的开掘。另外,母亲醋意中的温柔多情,父亲的憨厚善良,奶奶的伤心与唠叨,经过天灶的视觉、听觉和感觉“过滤”之后,别具一番生活的情趣美。《厨房》则以中年知识女性的爱情为切入点,揭示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人性的异化、堕落。作者没有将爱情描写庸俗化,专为刺激读者的感官,却也不回避展示人物性意识、性生理的“身体写作”方式。作品正是在细致入微地描写枝子与松泽的调情、拥抱、接吻的过程中,将前者的失望与后者的卑俗刻画得淋漓尽致。
至于刘庆邦的《鞋》,虽是一篇风格较为传统的小说,但也有新意。那就是将人物的情感全部“移植”到一双布鞋的制作之中,将农村少女纯洁的心灵、美好的情操和专一的爱情写得分外感人,说明要警惕金钱和物欲对人性的腐蚀、扭曲。
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多元化,也是这些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观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不是以所谓消解、悬置、颠覆、断裂为其特征的,尤其是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段上,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以求创新。综观这5篇小说,它们分别书写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如肖像描写、景物描写、细节描写等,同时也采用了其他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举其要者而言,有下列几种:一是张力叙事技法的运用。最突出的是《厨房》,主要表现在女性心理描写上。枝子是怀着希望到她喜欢的男人松泽家里来的,因其特殊的经历、身份、地位,一方面她热情如火,“像只发情的猫”,一方面又竭力维护“矜持和自尊”。正是这种心理张力的起伏消长,作者将人物内心的骚动、狂乱、冷漠的变化过程写得层次分明、惟妙惟肖。二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如《吹牛》中两个牧民的对话,其内容有的是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有的是不合逻辑的,非理性的。这后者由错觉、幻觉、自由联想等构成,将草原菊、太阳、女人、牛等意象交错叠印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有一种独特的美感。三是隐语与象征手法的运用。《清水里的刀子》中的老黄牛就是隐喻性的形象:“牛有着博大而宽容的心灵”,有“不改的忠厚和善良”,“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澈了一切的老人”。马子善心中那把不可明言的“刀子”,“像一种暗藏和秘密那样不断地向你闪悠着银光”。这“刀子”即是有着多层寓意的象征性形象。《鞋》中那双贯串作品始终的“鞋”,既是情节结构的手段,更是纯洁、朴素爱情的象征。隐语和象征能丰富、深化作品的内涵,创造诗意的氛围,增强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