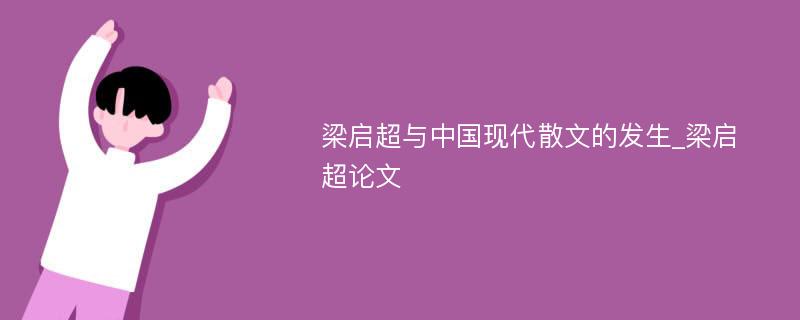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发生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1-0149-10 一、天时与人为:现代散文的开启者 从文学历史的本然看,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无疑是诸多关联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再从文体演进的时间维度上观照,这是一个相关的要素在特殊的场域中累积,由量变而为质变的历史过程。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其中个别的特殊的要素所具有的意义,而是相反。个别的特殊的要素,只有置于具体的史程中,在一个方位明确的坐标中,才能更为清晰地显示它的重要价值。中国散文在“五四”时期,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以此作为一个特殊的端点,我们往溯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进程,回放其中具有史性的人物和事件,相关的场景或影像触目而来。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梁启超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主角之一。 梁启超之有为于中国散文的现代发生,首先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可能性。所谓时势造英雄,于文学也是这样。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如他所说的是一个“过渡时代”:“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寸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而耍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①晚清之际,中国社会亦旧亦新,亦中亦外,酝酿着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除旧维新,革故开远,是一种“不容疑义”的“事势”。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思想和实践事功彰显,得之于他能顺势而为。其次也与其个人才情志趣有关。梁启超是文化史上一个卓尔不凡的“圆形人物”,他在很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创构,其于文学诸体多有关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晚清影响很大的小说文论,他看到了小说对于现代政治建构的想象,并且不仅言说其理,还亲炙其事,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但连梁启超自己也明白他不具有能够写作得体的小说,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②在诗歌方面梁启超张起“诗界革命”的大旗,对此作有具体的设计:“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③并且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但知与行并不能协和,梁启超力不从心,于诗终不能成大气候,他有诗情,但是没有大的诗才,正如他说的“余素不能诗”。 与小说、诗歌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散文这里知与行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他的身体力行使蜕变艰难的散文在“过渡时代”获得了变异开新的重大演进,为现代文学的生成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可以说梁启超对新文学所作出的特别贡献,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在散文方面的历史性作为。一些新文学家确认了这一点。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指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④这里钱玄同列举了梁启超种种“识力过人”之处,但首先标举的是梁启超“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是“现代文学之革新”的重要例证。郑振铎也支持这样的评价,并且更强调了梁启超散文对于现代文体改革的“先导”意义:“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⑤汉语的散文文体命名,体现着命名者对于散文体性的认知。这就是其在形态上是散漫的,在精神上是随心的。但这种体性的呈现或得之于文学史的真实经验,更表示着文人对理想散文的一种想象。在中国文学史的结构中,诗文是文体的正宗,因此散文也被赋予更多的“载道”功能,而且这种“载道”往往体现着体制的种种规定性,这样散文就难以真正地达成其“散”了,尤其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固化为某种“套式与格调”。梁启超基于“文界革命”思想而实验的散文,以“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等的新因素,实现了对传统散文的破体,成为开创“肆笔自如,畅所欲言”体现主体精神自由的现代散文的重要先行者。 二、散文观演进中的“文界革命”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是其有为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主要关键词,这是一个包含了散文变革开新思想和有效实践的复合词。我们先从相关的散文认知表达的梳理中,看取“文界革命”的思想价值。散文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但古代对它的系统研究很少。检索一些文论,可见有的言说虽为感悟片言,但内在的要义是值得重视的。其中在明代就有李贽和袁宏道之说颇得散文真意。李贽“童心说”强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倘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⑥李贽的“真心”、“真人”,以“真”给出文体的精神本质。而散文得“真”,需要作者“独抒性灵”,显示“真我”。在这一点上袁宏道与李贽观点是相通的。他以为好的散文“大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小修诗叙》,《锦帆集》卷二)“独抒性灵”和“自己胸臆”指归于为文的有感而发和自出胸臆、自我写真,而“不拘格套”则意指与写真的内容相应的灵活自然的表达形式。行运至晚清,散文家王韬的表述与李贽、袁宏道的相近,他在自己的重要文集的自序中给出了“佳文”的要素:“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⑦但王韬等所说的只是散文写作的一种可能,而实际上却往往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散文的写作需要受制于一些文统规约,在清代特别是桐城派散文所奉守的“义法”。因此散文要存真显诚,表达出作者完全的个性,就必须破除固有的规约。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晚清散文家冯桂芬言论的勇气和识见:“独不信义法之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⑧我们以后来梁启超的“自评文”对照以上的论说,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点。“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⑨“不喜桐城派古文”,表示了梁启超对“义法”的拒绝;拒绝“义法”需另辟蹊径,走向“自解放”;“纵笔所至不检束”则与“不拘格套”、“称心而言”等相通。由此可见,梁启超也承继了前代散文中有益的思想资源,表示了梁启超对散文文体的精神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但是此前的散文理论没有充分地给出达成“独抒性灵”、“称心而言”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方式,梁启超的意义正体现为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得散文“自解放”的道路,并走出了一片开阔的风景。 “解放”散文需要文界“革命”。革命是特殊时代的一种规定,“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⑩作为散文家的梁启超看到“过渡时代,必有革命”(11)的大势,应时而为地发出“文界革命”时代之声。梁启超并不是从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中设计革命的方法,而是从开放而鲜活的域外体验中获取卓异的思想。这是梁启超既超越前代,又不同于时人的根本所在。近代中国在被动中开放,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却得以自觉地放眼看世界,梁启超是其中一位突出的应时者。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乡人”、“国人”到“世界人”跨越。梁启超自谓“余乡人也”,“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12)这是时代使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性格使然。在走向世界,“为世界人”的过程中,日本的游历和体验对梁启超的影响特别重大。“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13)。“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14)使梁启超“脑质为之改易”的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的日本,而是一个将西方近现代文明成功内化、开启着现代化进程的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西学的“中转站”。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正是由其日本经验触发所提出的重大命题。 梁启超在1899年12月首次明确地推出了“文界革命”的念想,激发这一想法的是读德富苏峰著述的启悟。“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5)德富苏峰的著述不仅成为梁启超“文界革命”直接的思想资源,而且也是他直接借取的写作范式。“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多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时的《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16)比对两人的作品,证之于具体的文例可见这样的论定是信实的,比如德富苏峰有《无名之英雄》,梁启超也有《无名之英雄》;德富苏峰有《社会无无代价之物》,梁启超有《天下无无代价之物》;德富苏峰有《希望》,梁启超有《说希望》;德富苏峰有《新日本之少年》,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等等。梁启超“文界革命”的表述中核心语词是“欧西文思”。“欧西文思”相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义法”自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一种散文革命的要义。“欧西文思”的意义是丰富的,但主要意指的是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 “欧西文思”并不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全部义项,他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起点”。时隔两年,梁启超又重申“文界革命”的主张。但这时梁启超将“文界革命”由表达的意涵拓展到了表达的工具语言。梁启超一方面在《新民从报》上推介严复译著《原富》,认为“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其译著“精善更何待言”,另一方面又直言:“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17)我们再看严复对梁启超批评的回应,就更可以把握梁启超这里强调的“文界革命”的重心所在。严复认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之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若徒为近俗之词,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以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8)很明显梁启超和严复言说的指向是基于写作价值选择的语言问题,所不同的是梁启超意在以“欧西文思”“播文明思想与国民”,意在新民,与此相应文笔就不能“太务渊雅”、“殆难索”,而应求取“流畅锐达”,平易通俗,以使即使“学童”也可“受其益”。而严复译著和述论虽然在内容上也重视对于西学的绍介和阐释,但其目标的读者不是“学僮”等浅学之人,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文人官绅。这样在语言上就拒绝“近俗之词”、“粗犷之词”。由此可见,作者不同的写作价值取向的追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写作具体题材题旨乃至语言方式的选择。 早在“文界革命”正式命名之前,梁启超就声言:“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词达而已,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9)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梁启超选择的是“觉世之文”。这样的选择符合他自身身份设定的逻辑。梁启超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士人,他自画自己的形象:“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惟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0)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政治理想是新民,以为新民是维新的第一要务。他取“中国之新民”、“新民子”为自己的名号;将创办的刊物命名为《新民丛报》,所写的系列论说取名为《新民说》。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是办报立说。梁启超有自述:“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21)确实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报人之一,他主笔《时务报》,又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基于新民的政治理想和“为国人”的责任,梁启超十分看重报馆的特殊作用,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22)极言:“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23)近代报刊具有社会传播的功能,梁启超要借助于报刊传播其思想理念,达成其政治理想,这就需要其文本既要内含“欧西文思”,又要语言表达通俗平易,以实现其价值传播的最大化。因此,梁启超“文界革命”是包含内容和形式要素,并且两者是统一的新散文观。从这里我们可以寻得梁启超推崇德富苏峰并受启发倡议“文界革命”的内在原因。欧西文思、传媒和国民是联结两者的关键词。这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逻辑链。 由晚清“文界革命”推至“五四”文学革命,观察其中表达的逻辑和表达的义项,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首先从话题的设计看,“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文学改良”等关联相通,它们都明确话题指向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其次从话题展开的思路上看,两者具有接近性。在梁启超和陈独秀看来,革命是历史进化的一种基本规律。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篇关于革命的言说,与梁启超的《释革》十分近似,前者有“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24),后者有“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25)。同时基于特殊的时代语境,革命的提出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倡导“文界革命”,是因为不满“义法”疏空、雅驯格套的桐城派古文;“文学革命”虽然对象所指是封建文学,但陈独秀用以说事的文例许多取自散文,陈独秀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26)。陈独秀对于写作价值的估定,主要看取的是作品与特定时代“社会文明进化”的“关系”,这与梁启超所说的“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内在的意思是呼应的。再从革命实现的方式路径看,梁启超明确地指出要取法“欧西文思”,并且在语言表达上要“流畅锐达”,平易通俗。陈独秀没有直接地指说,但在《文学革命论》中间接地表达了借取欧西文学以改造中国文学的含义:“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雨果、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黑格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歌德、霍普特曼之德意志”(27)。稍后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则推出了“日化”、“欧化”、“人化”散文达成现代化路线图:“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他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化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可算得间接接受了欧化了。”(28)所谓“日化”就是日本化了的欧西文明,因为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中国文学更多得便于“日化”的“欧化”,而“人化”则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由此可见,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文学现代化建设者在精神上存在着的呼应。 三、作为“行动”的“文界革命”实践 梁启超“文界革命”取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口头倡导,而且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积极实践。梁启超的知行合致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散文发生具有许多看点的重要作家。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 论说一体是古已有之的文体。作为晚晴“文界革命”标志性成果的“新文体”,或称“时务文体”、“新民体”等是这种文体的近代变体。正是这种变体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重要一脉。关于这一文体的生成背景和特点、价值,学界多有论述。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以“第三只眼睛”观照,论述是信实到位的:“时代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的严谨的论文,而是对以中国的变革为目的的政治课题能发挥作用的文章。西方近现代文明是与中华的传统文明具有不同性质的新的文明,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创立适应这一形式的新的文体。‘新民体’就是应此产生的。它是为了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提炼出来的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文体。梁启超以这一清新的文体写成的文章,正如张君劢所说,是为了‘改造国民脑髓之妙药’而为人民所接受的。”(29)应该说“新民体”诸类不是梁启超一人所为,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的写作是“新文体”的重要前奏,与梁启超同时代作家也多有参与。但是无疑梁启超的贡献最大,他是这一文体主要的集成者。正如狭间直树所指出的,这一文体其价值直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课题”,其内核是“西方近代文明”,而其语体则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语体。可以看出,狭间直树是概括了梁启超“典型新民体”而提炼出这一文体特质的。梁启超的“新民体”其本质为“士人”所作的“启蒙文本”,“改造国民脑髓”的“新民”正是对这一文体本质的注释。 我们取梁启超“新民体”的典型文本加以论述。梁启超在谈及新文体时曾说:“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30)这里梁启超列举了三篇论说,揭示了它们“开新体”、“激民气”的特点。从这些作品的议题设置看,都非关传统文人的私意写作,而是有关国家的宏旨。《过渡时代论》由“各国过渡时代之经验”,观察分析“过渡时代之中国”的情势:“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夕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而耍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31)这里梁启超着意于“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其大意与《少年中国说》(32)相通:“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呵旁观者文》(33)列举“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种种“旁观者”的言行加以批评,其落实点也在“责任”:“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论重心在于旧与新嬗替维新时代国民责任,这是当时中国维新的第一要务,也是“新民”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在论说这样重大的时代主题时,显然无法从中国传统文明中寻找资源,而须得借取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在其文本中导入“欧西文思”。其显著标志是大量使用蕴含新思维的新名词,如“责任”、“人生”、“独立”、“自由”、“进步”、“青年”等等,新名词的熟练运用,使文本新风扑面、新意盎然。另外“欧西文思”也体现为“外国语法”的影响。陈平原曾说:“就对中国文章体式的改造而言,显赫的‘新名词’其实不如隐晦的‘外国语法’更带根本性。前者扩大了文章的表现范围,后者则涉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34)在改造中国传统散文体式中,“新名词”是否不如“外国语法”还可作深入的探讨,因为其实“新名词”背后也涉及新的思维。但是“外国语法”自然也是“欧西文思”的一个部分。体现在梁启超“新民体”文本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逻辑性的增强。这种逻辑性的增强一为长句的增多,表意趋于严密,二是段落层次间意义关联紧密。《呵旁观者文》开篇提出论点“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文章主体部分对六种“旁观者”依次论说,最后收结归纳,典型地体现出由总而分、由分而总逻辑运思的方法。《过渡时代论》有六部分“过渡时代之定义”、“过渡时代之希望”、“过渡时代之危险”、“各国过渡时代之经验”、“过渡时代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这样的结构安排体现了各个部分之间内在的逻辑性,表明作者接受了西方论说体写作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无论“新名词”还是“外国语法”,在传统散文中是没有的。可以说,这是对已有散文范式的一种“断裂”,而正是在这样的断裂处,中国现代散文正在发生。此外,《呵旁观者文》等语言文白相间,如“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等语句已近书面的白话,对古奥雅驯的散文自是一种超拔,易于读者的接受。再者如《少年中国说》表达情势充盈,语势强劲,广比博喻,形象生动,体现了主体才情性情的张扬:“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种张扬也是现代散文个人性的一种表征。 新闻体散文是伴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生成的散文形式。作为报人的梁启超既十分重视作为主笔文体论说的写作,同时又尊重报刊的新闻性,写作新闻叙事类的作品。梁启超认为:“……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赀以求一新事,不惜焉。”(35)“重时事”、“求新事”是报刊作为新闻传播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的“通信”是一种重要的报道文体。不同于消息、简讯,它对具有新闻性的人和事叙写更为具体细致,有的还具有较为充分的文学性。这样的一种写作形态后来独立成为报告文学文体,晚清时期的这种制式可以称为新闻体散文。新闻体是指其题材的特性,而散文则指写作的笔法。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晚清长篇新闻体散文的代表作品。作者以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的身份,以十万字的篇幅对戊戌政变作了较为详细的实录。事件发生于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因为深度参与戊戌变法被清廷通缉,亡命日本。11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次月便在《清议报》发表《戊戌政变记》,体现了新闻体散文写作的快捷性。同时又得叙事散文写作的要义,既叙事又写人,作品包括“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和“殉难六烈士传”5篇,其中的“殉难六烈士传”最为可看。作者写谭嗣同、康广仁等烈士,既注意从他们与时代的特殊关联中展示其精神品格,同时又能同中见异,凸显人物兀自独立的个性。梁启超说过:“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相类似是人类的群性,不雷同是人类的个性。个性惟人类才有,别的物都不能有。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人的个性。”(36)(《作文教学法》)他笔下的戊戌六君子基本达到这样的要求。如康广仁,“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37)而杨锐“君博学,长于诗,尝辑注《晋书》,极闳博,于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君子重之。”(38)作者叙写人物的视点角度不雷同,所以作品呈现的人物面目品格就卓异。六君子中谭嗣同的形象最为鲜明:“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9)这里以富有人物个性特质的语言,写出了谭嗣同敢于任事、勇于牺牲的精神,由此人物大义凛然的形象镌刻在读者的心中。 作为散文家的梁启超具有多副笔墨,除论说、通信体之外,于游记一体也有创建。他先后写作了《汗漫录》(《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和《欧游心影录》等域外记游作品,最具有文体史意义的是《新大陆游记》。游记是中国散文中的重要门类,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体上这类写作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40)到了晚清游记的话语空间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出使或游历外洋官绅,自1866年斌椿起,即产生一个优良习惯,即凡经历国外,多将其见闻观感写入日记,或赋诗吟咏。据约略统计,自1866年至1900年,撰著外国记事之人物有61位,而撰著记述达151种。而此类日记诗稿,往往因其出版而广泛流传,影响官员文士最大。”(41)钟叔河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就36种。这种记游作品的内存与形态与原先的游记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多是写外国题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42)《新大陆游记》在这些新体游记中,由于作者的特异、内容信息的丰富和表达形式的开放,更具价值和影响力。 梁启超1903年游历加拿大和美国,以美国为主,写成将《新大陆游记》,1904年《新大陆游记》在《新民丛报》以“临时增刊”的形式发表。这部游记对风物异景大多“删去”,内容“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43)作品叙写重心的设定与作者的身份有关。“尽管梁启超是一个‘党人’又是‘报人’,但他本质上仍是一个‘士人’……承担天下兴亡、扛起国运民命,他内心所有的就是这种士人的灵魂。”(44)这样的判断符合梁启超的实际,其实也是对晚晴“梁启超们”的一种真实的概括。但在《新大陆游记》中,作者是由“党人”、“报人”和“士人”等多重角色复合而成的。他们的基点是心怀天下兴亡,着意国运民命,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写作的目的是“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亦国民义务之一端也”。复合的角色使《新大陆游记》成为一个复意和复调的“多文本”,这是这部游记的最大的特质。作为“党人”梁启超自然会关注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在他看来“美国百余年来之政治史,实最有力之两大政党权力消长史而已”(45),作品以大量笔墨介绍美国的政体政制和政治结构,还记录了与总统等政治人物会面交流的情况。作为“报人”梁启超有着强烈的新闻意识,基于特定的读者对象,选取他们感兴趣新鲜的话题作详细的叙写,如“美国太平洋海电告成”、“1899年1月以后设立之托辣斯资本表”、各国移民美国的最新数字以及在美华人生活情形等,在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关注。作为“士人”梁启超一方面留心于美国大学和图书馆等与士人相关的存在,另一方面基于“士人”的价值取向对于所见所闻“加以论断”或引申。论断如“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46)。引申如白宫“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羡民主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47)这种见微知著的表达,是一种“士人”式的表达,反映了作者别有意味的政治想象。与特殊的表达内容相适配,《新大陆游记》在语言上大量运用新名词,句式也近口语,文言的比重较少,更多的是通俗流畅的白话,笔调上也更显从容余裕,加之“多文本”的建构,使《新大陆游记》更具可读性。 由上分述可见,梁启超作为“文界革命”的实践者,他在“过渡时代”文学的演进中,对散文的多个门类都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以其为标志的“新民体”实为“五四”杂感文的先期实验,他又以《戊戌政变记》等参与了近现代新闻文学新体式的开创,而《新大陆游记》等则表示了散文在论说之外其他门类存在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的这些创作都为“五四”时期杂文与美文的多样发展作了铺垫。在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关节点上,梁启超留下了开拓者很深的足印。 注释: ①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日本横滨:《清议报》第82册,1901年。 ②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日本横滨:《新小说》第1号,1902年。 ③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④钱玄同:《寄陈独秀》,北京:《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⑤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67页。 ⑥李贽:《焚书·续焚书》,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97页。 ⑦王韬:《园文录外编·自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⑧冯桂芬:《复庄卫生书》,见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99页。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⑩(25)梁启超:《释革》,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1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12)(14)(15)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5、186、191页。 (13)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论学日本文之益》,日本横滨:《清议报》第10册,1899年4月。 (16)冯自由:《冯自由回忆录:革命逸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715页。 (17)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18)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日本横滨:《新民从报》第7号,1902年5月。 (19)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北京:《时务报》第49册,1897年12月。 (20)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21)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2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北京:《时务报》第1期,1896年8月。 (23)(30)(35)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日本横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24)(26)(2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北京:《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 (28)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北京:《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 (29)[日]狭间直树:《梁启超·民治日报·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页。 (31)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日本横滨:《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 (3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日本横滨:《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 (33)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日本横滨:《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 (34)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6)梁启超:《作文教学法》,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715页。 (37)(38)(3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98、103、109页。 (40)(4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欧洲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 (4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4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2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09页。 (44)李书磊:《作为异文化体验的“梁启超游美”——重读〈新大陆游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45)(46)(47)梁启超:《〈欧洲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56、296、324页。标签:梁启超论文; 散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少年中国说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清议报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