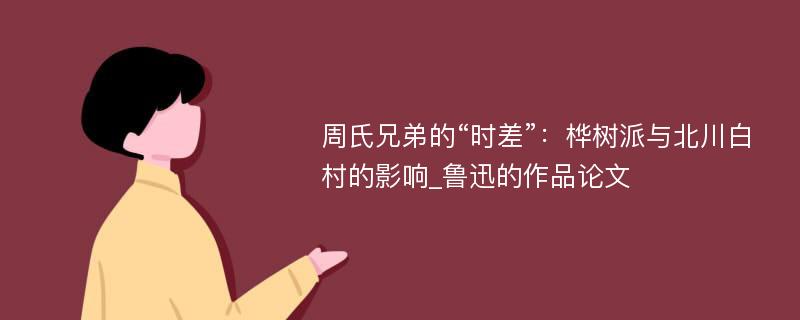
周氏兄弟的“时差”——白桦派与厨川白村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桦论文,时差论文,兄弟论文,厨川白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时差”
毋庸多言,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是亲兄弟,从出生到1923年的兄弟不和为止,他们关系不是一般的深厚。从小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式教育,在青年时代兄弟俩先后到南京学堂学习,同样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了。留学日本期间也比较长,鲁迅则7年(1902-1909年),周作人则5年(1906-1911),他们都在章太炎的私塾里学习文字学,更加深了汉学修养。他们回中国绍兴时,分别是29岁、27岁了。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学问根底几乎是一样。不止日本留学时期,经过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有很多思想上的共同点,直至兄弟不和为止。
兄弟不和的谜团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开,但从此他们的思想渐渐走远了。虽然兄弟分道扬镳并不直接影响到思想共通性,后来还共同主持《语丝》,联合参与女师大事件,但1927年鲁迅经过革命文学论争,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周作人开始摸索传统文化之精粹,到了30年代,二者思想面貌则相异了,那么兄弟之间的分歧从哪儿发生的?
我一直研究周作人。从研究周作人的立场来看,除了天生素质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兄弟回国后的不同步伐所产生的结果。第一步就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的差异。1909年回国的鲁迅积极参与辛亥革命而感到幻灭。1911年刚从日本回国的周作人却对辛亥革命冷漠。[1]第二步则以相反的态度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鲁迅对五四运动迟疑不决,周作人却以热情参加,宣传白桦派的新村运动。后来鲁迅也受到弟弟的影响,翻译武者小路、有岛武郎的作品。第三步在兄弟不和前后,兄弟先后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早在1921年周作人就在他的文学评论里面借用颓废派的概念来拥护郁达夫《沉沦》即此一例。鲁迅则晚了一步,1924年才开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之象征》。
如此看来,可不可以说兄弟之间的“时差”产生了不同思想风貌?我想在此简单地介绍兄弟之间的白桦派的影响及厨川白村的影响,说明“时差”导致思想分歧的可能性。
2.信仰人类主义(1918-1921)
(1)武者小路实笃:新村运动的反响
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读武者小路的理想主义之作一个青年的梦》(第4卷5期)。虽然在前几期发表过几篇翻译,但这才是他自己的文章。就在第一篇文章提到武者小路的文章,可能不是偶然的。周作人对白桦派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据及川智子的考证②,周作人很可能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开始阅读《白桦》,并在回国(1911年秋天)后也继续订阅,还从绍兴邮购补全所有的《白桦》,及至1916年才停止订阅。③这时白桦派主干作家业已在商业性杂志上发表作品,《白桦》渐呈强弩之末了。大致长达六年之久,对白桦派的兴趣持续未减,可见对它独有情种。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前一个月,在北京大学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这里讲述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最后指出自然主义的缺陷,作为超越自然主义的流派,介绍夏目漱石(1916年没),森鸥外(1922年没)等“余裕派”,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后作为当前日本文坛上的主流介绍“新主观主义”。这儿所谓“主观”是与自然主义的“客观”相对而言,但当时在日本文坛上并不普遍,可以说代表周作人个人的看法。他再把它分为“享乐主义”和“理想主义”,分别介绍主要文学家。关于“享乐主义”的特点,指出“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永井荷风为其派代表,并把谷崎润一郎列入此派,认为是比永井荷风“更带点颓废派的气息”。还有一派“理想主义”,就是白桦派了。他介绍道:
明治42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3,4年时,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
按照现在的文学常识来说,大正一年到大正十二年(1912-1923,关东大地震为止)为白桦派最盛行时期。周作人的看法虽然没有错,但仅限大正三年、大正四年的说法并不那么普遍。如说就这两年有特点,自然想到武者小路的作风变化了。武者小路长达五十年的文学生涯可分为五个时期(龟井和本多之说)④,这两年是第一时期(后半)的开头,被认为是“重新回归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代表作就是《一个青年的梦》。这次讲演里面,对白桦派(武者小路)给予高评价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其实写出这篇演讲稿的前几天,周作人读到《一个青年的梦》⑤,读后感激尚在,字行里自然流露出来了。
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里强调,他看了这篇剧本,感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要。他开头先介绍以托尔斯泰为主的反战论,再指出武者小路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但同时他不得不承认武者小路的主张太不现实,“明知说也没用,然而不能不说”的。在这个矛盾的心态底下有强烈的共鸣。他引用《一个青年的梦》,介绍道:如果“真心的觉到战争的恐怖和无意义”,但“世人未达到人类的长成时,战争不能灭”,一定要“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⑥,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里看重民众的觉醒之说完全吻合周氏兄弟的想法。1919年8月,鲁迅翻译这篇剧本,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但因遭到禁止出版而中途而废,后来改在《新青年》上重新发表一次。开始动笔时,他说: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回国后,与周作人同居的时间不算很长,从1912年到南京政府做官僚到1917年周作人应聘当北大教员为止,分开生活的时间居多。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周作人对白桦派的关心。看到《新青年》之后才向弟弟借读,这里所说初次读到也许不是虚假。虽然心里感到翻译这部作品“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但迫使他不得不翻译的不外是武者小路的文章。引用《新村杂感》里的文章,鲁迅说:
“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藤井省三⑦指出这里的比喻非常接近于铁屋里的呐喊。而且不知鲁迅有无此意,把开头的“心里”(うちに)翻译成“家里”。他虽然对革命仍然抱着幻灭的心绪,但又觉得不能响应武者小路的“呐喊”。自然不像周作人那样,对武者小路的评价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肯定。最后说: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虽然具体不说,但书里的过于理想主义的地方,一定不是鲁迅可以接受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章里面找不出对武者小路的批评。可以说全面的肯定。除了“民众的觉醒”之外,当时武者小路的思想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类主义”。剧本里说:
须得用民众的力量,将国的内容改过才好。世界的民众,变了一团,大家握手时,战争便自灭。……假如承认了现在的国家,却反对现在的战争,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⑧
武者小路呼吁民众超越国度团结才能实现世界和平。这个思想于无政府主义相去不远。1918年5月在《白桦》杂志上发表《新しき村に就ての対話》,发动新村运动也是顺理成章的。周作人1918年10月就开始订阅《新しき村》杂志,支持新村运动。第二年发表《日本新村》(《新青年》1919年3月)之后,1919年7月访问九州宫崎县的新村,1920年2月建立北京支部等,可谓全心全意的投入。与此相比,鲁迅对新村运动虽不至于反对,但历来对周作人不惜帮助的,却保持沉默,可以看出他的消极型反对。周作人支持新村运动的同时,1919年3月翻译《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⑨,里面作为社会主义前驱,注重介绍巴枯宁为主的无政府主义。可见超越国家的人类主义的期待。
鲁迅对新村运动保持沉默的理由,这里来不及详论⑩,但他经过辛亥革命的经验,很可能对于新村运动的可行性不敢置信的。与此巧合的是,有岛武郎1918年8月发表《给武者小路兄》(《中央公论》1918年7月号)认为:实行新村运动的意义很大,衷心表示敬意,但“如何周密实行也必定要失败”。作为失败的理由,有岛武郎提到“杜霍波尔教派”(Doukhobor)的移民的故事。
请让我直率地说:我想你的尝试如何周密实行也必定要失败。终归失败才自然的。在您开始尝试之前,就这么一口咬定也似乎非常不吉祥的事,但只好坦白告诉您了。资本主义社会围着你们一群人,不管怎么说也势必逞淫威,你们难免像“杜霍波尔教派”的移民那样,从外界要受到压迫。
这里所谓“杜霍波尔教派”是俄国东正教教派里的一个小教派,否认国家,反对战争,拒绝为国家当兵的教徒。18世纪由于受到俄国政府的压迫,迁居移民到加拿大,独自建立一种公社,经营共产主义式的村子。但在加拿大也屡受迫害,没有成功。他特意在此提到这个故事有背景的。1905年有岛在美国留学之际,读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还主动参加过农村的体力劳动。后来1907年在英国伦敦访问过克鲁泡特金,聆听教诲。“杜霍波尔教派”的尝试和失败是直接从克鲁泡特金本人听到的(11)。“杜霍波尔教派”和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并不尽同,但反对战争,希求建设地上乐园的理想可以说一模一样的。有岛武郎明知美好理想的脆弱,这才所以表示同情的同时,坦白警告武者小路的原因。最后有岛轻轻地加了一句:
说起未来的承诺难免荒唐无稽,不过我也等机会来了,或许以别的方式,想要和您一样尝试,而一败涂地也毫无遗憾。(12)
登载这篇文章的《中央公论》杂志系“白桦派特辑”号,专门登载评论白桦派文学。武者小路也自然看到了。从此有岛武郎与武者小路实笃一直处于绝交状态。直至1921年8月举行第一次“支援新村会”时,由志贺直哉出面调解,两个人才能恢复友谊。这一场风波周氏兄弟也许没有注意到。但此次冲突明确表示在思想上有岛和武者小路已经互不相容了。
诚然,两个人作为白桦派的健将,他们首先都从肯定自我意识出发,建立[自己—艺术家]的立场为特点。这是白桦派的共同点。(13)但此时武者小路通过新村运动,主张人类主义。这个人类主义从肯定自我出发,追求化解自己与他者的界线,合二为一。有岛武郎虽然同样从肯定自我出发,但如《爱是恣意掠夺的》(1917年发表)所言,“爱的表现虽是不惜地给予,但爱本身是不惜夺的”。就是说,把爱情(爱自己为出发点)延伸到对象,努力逼近把对象的内涵夺为己有,这就是有岛武郎的人生观。1918年发表的小说《与生俱来的烦恼》里的年轻画家也为此苦恼。武者小路的人生观极为乐观,气宇之大几乎远离现实,有岛武郎的人生观比较现实,能顾及的对象难免要狭窄。
有意思的是,周氏兄弟竟把这两个人的观点同时接受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武者小路的影响,下面再看有岛武郎的影响吧。
(2)从有岛武郎《与幼小者》引出来的礼教批判
1916年从有岛武郎的身边相继离去了妻子和父亲。夫人安子患了两年结核病而逝世。为了夫人,有岛是放弃农科大学教授的地位到东京来的。同年冬天,从小管教严格的父亲也得了癌症逝世了。此时他才得以解脱家庭的种种约束,开始专心致力于创作了。1917年有岛武郎陆续发表《死和其后》、《该隐的末裔》等小说和上述《爱是恣意掠夺的》(14)等评论而成名了。1918年发表《与幼者》(鲁迅所译)、《与生俱来的烦恼》,1919年发表《一个女人》,从1918年到1920年可谓在思想上、在文艺上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时期。如上所述,有岛武郎的内心世界以[自己—艺术家]为主,但同时面对外界的现实生活。爱情是与现实生活链接起来的关键存在。不只美满的事物,如《阿末之死》那样,他不能对底层生活的悲剧熟视无睹。这种[他者—生活者]的存在逼他的良心承认自己的优越生活环境,承受无法解脱的内疚。他在长野县和父亲过避暑的日记《信浓日记》(1916年的8月所写;《新家庭》第5卷6号,1920年)里写道:
父亲问我今后日本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似乎想这一问可以探出我下一步打算怎么走的。我的回答则是;“劳动者”、“妇女”、“小孩儿”——这三个要成为最根本的问题。
《与幼小者》里讲述的也不只希望孩子的健康成长,还写出对于冒着生命危险生育的女性的敬意,对于忙碌工作而没有钱治疗肺病的邻居的同情,再对于远比邻居富裕的自己的处境感到的内疚,内容相当复杂丰富,正与《信浓日记》所说一样,他在此也关注“劳动者”、“妇女”、“小孩儿”这三个[他者—生活者]。鲁迅虽然翻译过《阿末之死》,表示对底层生活的关心,但这时期在他的思维里“小孩儿”问题主要和儒教道德伦常“孝行”联起来批判,没有和“劳动者”、“妇女”联系。他的关心所在可从《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看出来。他在这里提出三个基本道理:“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然后写道: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略)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鲁迅以科学常识来否定儒教伦常,认为后来者居上。周作人当时也写了《祖先崇拜》(《每周评论》10期,1919年2月)
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略)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
周作人的逻辑与鲁迅几近相同,从生物进化论的常规来否认崇拜祖先的行为。从他们的眼光看来,“崇拜祖先”只不过是一个“野蛮民族的风俗”而已。鲁迅11月还写了《随感录63:与幼小者》(《新青年》第6卷6号),说觉得有岛武郎的小说里“有许多好的话”,摘译《与幼小者》的最后一段:
你们(孩子)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有岛武郎的行文里本来没有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鲁迅则有选择地摘译自己所要的部分。如上文所示,他以进化论的逻辑希望孩子们超越自己,自己宁愿做培育小狮子的营养。用不着说以自己为[劣者],以后来者为[优者],这是进化论的逻辑。但有岛武郎的本意并不在此。他自己视为在优良环境里长大的[优者],从这个前提出发,视“劳动者”、“妇女”、“小孩儿”这三个[他者—生活者]为[劣者]的,才认为社会上有不公平,应该为他们牺牲自己。在《与幼小者》里谈起因贫病交迫而死的劳动者时,一定要加一句“要服的药品都能服,要吃的事物都能吃,我们是从偶然的社会组织的结果,享乐了这并非特权的特权了”(15)。
观点上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不只鲁迅,还有周作人也并不介意(16),采取“拿来主义”接受有岛武郎的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的想法毕竟以进化论为主要轴线,有选择地只接受批判儒教伦常的逻辑,除此外几乎没有接受有岛的思想。如上所述,虽是一个白桦派,但有岛和武者小路之间,当时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如此,鲁迅有选择地接受武者小路的思想,只对反战思想表示赞同,但对新村主义表示消极的态度。周作人则偏袒武者小路的人类主义思想,影响范围远比鲁迅广泛多了。结果,在周作人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缝,招来思想上的突变。
3.人类主义的崩溃——“现代人的悲哀”与“蔷薇色的梦”
(1)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的“现代人的悲哀”
1920年底,忙着宣传新村运动的周作人终于病倒了。经检查判为肋膜炎,3月先在山本医院住院,然后5月起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养病,及至9月病愈,才下山回家。离家住院期间,鲁迅关照他无微不至。这段时间里,在周作人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己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山中杂信》1921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1918),《平民文学》(1918)部分依据托尔斯泰而写的。《平民文学》里特别强调“平民文学”要“内容充实,就是普遍(universality)与真挚(sincerity)两件事”。这两个条件完全依据《艺术是什么?》(托尔斯泰原著),认为将来的艺术不应该是“the exclusiveness of feelings,accessible only to some”(只有部分人能接受的排外感情),而是“is universality”(普遍的感情)。据托尔斯泰,拥有这种感情的艺术才能够让人人体验“feelings as can unite men with God and with another”(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感情)(17)。还在《齿痛》(安特莱夫原著)的译文后记(1919年)里介绍安特莱夫的话,赞扬这是“他文学上的宗旨,也就可以代表俄国人道主义的文学者”。
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安特莱夫是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里也提到过的作家。一般认为是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作家。但再次提出的“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与托尔斯泰的“神人合一,物我无间”这个文学作用几近相同,也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文学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与发动新村运动的武者小路的理想主义相同。周作人病愈下山后,却在《诗的效用》(1922年)引用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开始对托尔斯泰表示怀疑。
托尔斯泰论艺术的价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克鲁泡特金对于他的主张,加以批评道,“各种艺术都有一种特用的表现法,这便是将作者的感情感染与别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须有相当的一番训练。(略)托尔斯泰把这事忽略了,似乎不很妥当,他的普遍理解(universal understanding)的标准也不免有点牵强了。”这一节话很有道理。
在《贵族的与平民的》(1922)认为“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放下“平民文学”的旗帜。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关注颓废派,还写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1921年),介绍弗罗贝尔、陀思妥耶夫斯奇和波特莱尔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源泉”。特别强调波特莱尔的现代性,说道:
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
这里已经找不到赞同新村运动的美满理想了。他面对新文化运动遭到屡次挫折,心里充满悲伤和幻灭感(18)。对周作人来说文学不再是化解自己与他者的界线了。拥护郁达夫的《沉沦》(1922年)时的逻辑也极其相似。
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略)。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在这儿反复提到的《现代人》的《苦闷》即根据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1912)里的《近代的悲哀》这一章。厨川白村解释个人主义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认为积极的个人主义难免带有颓废色彩,认为“自由的个人生活与有拘束的社会生活很难调和,不断在精神上发生挣扎造成苦闷之因”。再关于苦闷的内涵,厨川白村如下解释:
颓废派的敏锐而不知厌倦的感官与强烈的现实感毫无可能让近代人安分过灵的生活,并且在两方面生活上发生冲突矛盾,这就产生苦闷之因。(略)灵和肉两方面的要求之不调和就是近代颓废派(decadantism)的凄惨的一面吧。
这个早期的文艺史书里理论框架很明确,厨川的近代文学论从个人与近代社会之间的矛盾立论,个人面对社会则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感到孤独悲哀,面对灵肉不一致的生活则感到苦闷痛苦,对这个观点周作人非常同感,1922年前后的文艺评论里反复提到《近代人的悲哀》论,显示出文学论的变化。
周作人阅读厨川白村的著作,大概阅读《近代文学十讲》为最早的。查《周作人日记》可以确认1913年9月1日邮购此书。9月6日、10日连日阅读(19),可见阅读兴趣比较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取材方面(作品、作家)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共同的地方。此时可能不是对厨川白村个人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文学历史的兴趣阅读的。后来编写北京大学讲义《欧洲文学史》的时候,也许参考过。但厨川的影响在1921年以后才能看出来的。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对人类主义感到幻灭才有了条件接受的。
尽管如此,这时的周作人的突变还有人际关系的因素。1921年秋天,曾受厨川白村的熏陶的两位学人张定璜(字凤举,1895-?)、徐祖正(字耀辰,1894-1978)陆续回国,认识周作人。(20)通过他们的关系,他很可能因此重新萌发兴趣,受到影响。再加上,虽然还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但周作人通过他们的介绍,可能看到厨川白村的《苦闷之象征》(1921年1月,日本《改造》上发表)初稿而受到它的影响。
厨川白村被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所吞没逝世了。《苦闷之象征》(未定稿)逝世后1924年才出版。如上所述,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近代文学十讲》里展现出来,但到了《苦闷之象征》,才能与精神分析学、性心理学等当时的新兴学科的成果结合起来,隆重提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个观点的。这个观点似乎在周作人的文艺评论里有所反映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周作人1922年开始发表文艺评论,拥护郁达夫《沉沦》的评论非常有名的。他引用莫台耳(Albert.Mordell)《文学上的色情》(The Erotic Motive in Literature,1919.London.),把他的作品定位为“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不道德的性质”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这本书,在厨川白村的初稿里也提到的。这时期,周作人开始大量阅读性心理学者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大著《性心理研究》,莫台耳(A.Mordell)也不是偶然的。厨川的初稿本1921年1月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21)。初稿本里只包括1924年版的部分文字,里面有:
《一,创作论》(全6章):与24年版基本相同
《二,鉴赏论》(全6章):一,二,三章的部分
《三,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全6章):三,莫泊桑(全),四,白日梦的(部分)
《四,文学的起源》(全2章):全无
与1924年版比较起来,毕竟不完全的。但这本书的核心部分可以说都有的。当时《改造》这本杂志属于较有名的杂志,不止日本国内,在中国也许容易看到。周作人的1921年的日记由于当年病卧,没有完整的记录,无法找到阅读《改造》的记录,但完全有可能阅读过这本杂志。就在这期《改造》也有有岛武郎、贺川丰彦、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人的文章。
第二,1921年周作人病愈没多久,就开始翻译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分别在《妇女杂志》《晨报副镌》《民国日报觉悟》上刊登了共八篇散文诗(据说明翻译以英文版为准,并参考了德文版)。当中有一篇《窗》。这就在初稿《鉴赏论》的最后部分“自己发见的欢喜”里,厨川白村特意引用全文的。可见周作人对此启迪很大感受也深。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也翻译过这篇散文诗。他翻译出版《苦闷之象征》以前,1924年10月抢先把散文诗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可见他的感受不比弟弟少。翻译时还特意参考了德文版。当时鲁迅似乎没有注意到弟弟1922年早就翻译过的事实。两篇比较起来,兄弟俩的译文截然不同。
我们再回到厨川的《自己发见的欢喜》的核心思想。这里借用鲁迅的译文。这篇散文诗《窗》主要讲从外面观察关闭在窗户里的人物远比从屋里看窗户外面更有意思。因为仔细观察关在屋里的人物可以想象每个人物的以往生活故事,饶有意思。通过观察还会发现与自己共同之处。厨川白村借此强调“自己发见的欢喜”,解释如下:
倘说作家用象征来表现了自己的生命,则读者就凭了这象征,也在自己的胸中创作着。倘说作家这一面做着产出底创作(productive creation),则读者就将这收纳,而自己又做共鸣底创作(responsive creation)。有了这二重的创作,才成文艺的鉴赏。(译文依据鲁迅《苦闷之象征》)
这种想法现在通行的文艺学里面也比较普遍,并不那么晦涩。但厨川要强调的是,作家和读者的共鸣。就是说作家创作时多少也总要反映出自己现实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生活的记录,而是从实际生活升华为有象征性的文艺作品。这个作品到读者手里时,又要通过读者的实际体验的过滤一次,才能理解文艺作品。通过这一过程,不只作家,读者自己也在作品里面能“发见自己”,感到“欢喜”的。
如上所述,周作人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是无疑的,但这个影响是隐性的。这主要原因在于厨川白村的影响限制在文艺理论上,而不在文艺作品上。因此与有岛武郎的评价自有区别的。与此相反,鲁迅直至1925年才翻译出版《苦闷之象征》。但他还翻译《出了象牙之塔》(1925)、《西班牙剧坛的将星》(1926)、《东西之自然诗观》(1926)等评论。鲁迅眼里厨川是一个文明评论家。与周作人的接受方式比较起来更广泛了。
如此不同时期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而导致兄弟俩走向不同方向。例如周作人从此对厨川白村的“颓废派”有极大共鸣,后来他把这系统理论发展成《新文学的二大潮流》(192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22),走向否定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却相反,充分吸收厨川白村的思想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文艺理论。
(2)有岛武郎《四件事》和“蔷薇色的梦”(23)
周作人的文学观的变化导致他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同时对有岛武郎的评价也有所变化。1921年底周作人翻译了有岛的短篇小说《潮雾》(24),却没收进《现代日本小说集》。这是一篇描写人的命运不可预测的小说。还有重要的是,他在译文后记里译介《四件事》(原著1919年12月),对有岛武郎表示同感。这篇文章里有岛列举自己从事创作的四条理由: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
这里的主张可以说是同年6月发表《爱是恣意掠夺》之后,基于同一个思想发挥出来的。至于四条理由,有岛逐句加以说明。第一条“寂寞”,有岛说:“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偶尔“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能“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感到“惊喜”。第二条“爱着”,因为“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既然爱着“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才进行创作。第三条“欲爱”,因为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得到回应。为了这个“我尽量的高举我的旗帜”,但有回应的次数毕竟不多,“但是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第四条为了“鞭策自己的生活”,而创作的。
这里对周作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第三条。这两段文章,1923年7月,接到有岛武郎自杀的新闻,写了《有岛武郎》,里面又重复一遍的。但句子稍有改变了。
第二条:“爱着”→“欲爱”(日语原文「愛する」)
第三条:“欲爱”→“欲得爱”(日语原文「愛したい」)
按原文的意思来说,原来的翻译才对,改过来反而离本意远了。但有岛的“四件事”里面第二条强调自己的爱情延伸到对象,通过理解努力逼近对象的内涵夺为己有(如在《爱是恣意掠夺的》所说)的。反过来,第三条强调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而且如果被正确理解到的话,达到幸福的决定的。那么这两条是一对儿的,一则是理解而爱,另一则是被理解而爱的。要注重表达这个原意,改成“欲爱”和“欲得爱”是一个合理的翻译。我想周作人改译的理由也就在于此。哀悼有岛的两个星期后,周作人编定了第一本自己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在自序里说:
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如能得到满足,我总是感谢的。
这一段话完全符合有岛的话。通过“理解别人的心情”与第二条的“欲爱”,“得到被理解的愉快”与第三条的“欲得爱”互相对应的。不过周作人也知道已经无法圆他的梦。
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
文艺可以寻求想象的友人,但他已经明白这是虚幻的梦想而已。如他在《日本的小诗》(1923)谈到那样,“在现今除了因袭外别无理解想象的社会上,想建设人己皆协的艺术终是不能实现的幻想”,他已经对当时中国社会不寄希望了。虽然因为是“生人的弱点”,还不完全放弃。就写在这两篇文章的中间,竟发生了兄弟分歧,周作人交哥哥写的信里写下如下句子:
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知道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这里《蔷薇色的梦》是一句非常含蓄的话,很难完全掌握,但主要含义就在于通过文艺作品得到“想象的友人”,得到“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但周作人又在此承认自己的梦已破,心已碎了。
后来周作人编理《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作为《关于作者的说明》,把这篇《四件事》也收进去了。由于《与幼小者》,《阿末之死》系鲁迅所译,“有岛武郎”项目收进《鲁迅全集》里面,认为是鲁迅所作,但恐怕有误需要纠正。
至于后来的鲁迅所接受的有岛武郎的影响,该从《壁下译丛》里的翻译作品。鲁迅翻译作品里有6篇。这些作品的翻译时期很难确定,除了部分译作以外,只能说在1924年到1928年间。但这些翻译的工作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与五四运动时期有关的内容。《生艺术的胎》(原著1917年作)是主张“生艺术的胎是爱”。内容与其说评论,不如说是箴言集。还有专门谈易卜生的就是《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1919年作,1928年译),《伊孛生(25)的工作态度》(1920年作)。这些易卜生论可能应该与有岛武郎的影响分开看的。这里只看《生艺术的胎》。
艺术家以因了爱而成为自己的所有的环境为对象,换了话说,就是以摄取在自己中,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的环境以外的环境为对象,活动着,则不特是不逊,较之什么,倒是绝对地不可能的事。
这段主张从《爱是恣意掠夺》发挥出来,也和《四件事》的思想接近,可以说有岛的中心思想。但这篇文章的翻译日期目前无法确定,只有鲁迅在《小杂感》(1927年9月)里说到“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这一句话,似乎表示留下有岛的影响痕迹。(26)
第二,与革命文学论争直接有关系的。《宣言一篇》(1921年作)是承认将来的世界要属于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同时,宣布自己无法冒称第四阶级,认为不可能也不应该帮助他们。《关于艺术的感想》(原著1921年作)也关于第四阶级和它的艺术问题。与周作人比较的观点看来,第一部分可以说与周作人接受相同的影响。但第二部分则与周作人完全不同的地方,如上所述,周作人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之后,发展“颓废派”的理论,否定革命文学了。至于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宣言一篇》的影响,已由丸山升专门探讨过,我在此不敢多说了。(27)
4.结语——蔷薇色的梦痕
如上所述,周氏兄弟的生活环境几乎相同,接触到的文化思潮也没多大差异。但辛亥革命以来有几次机遇相违,导致他们思想风貌上产生不小差异了。也许连周作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里面讲到白桦派时,他还特意点出永井荷风等人的“颓废派”,认为是“消极的享乐主义”,却到了1922年赞扬“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地求生意志的表现”了。鲁迅同样的接受厨川白村的影响,但受到影响的时候所处的环境不同,“时差”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周作人在《有岛武郎》(1923年7月)最后写道: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且可念的事情。(略)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
这时周作人或许不知道与大哥鲁迅绝交的日子即将到的。不只鲁迅,远在日本的有岛对他来说也是寥寥无几的同行者之一了。他才因此由衷表示哀悼的。借用有岛的话告白自己在寻求“想象的友人”的时候,鲁迅也在《鸭的喜剧》(1922年11月)借用爱罗先珂的话来表达寂寞。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里有一个巧合,都在说“沙漠”里的“寂寞”。但这也许不是巧合。因为周作人和徐祖正、张定璜,再加上废名、江绍原等人创刊了《骆驼》(1926)和《骆驼革》(1930)这两种文艺杂志。《骆驼》附有后记叫做《沙漠之梦》,这正是说明,骆驼就是沙漠里的动物,他们把自己比作骆驼的(28)。
寂寞本来是鲁迅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患的忧郁病。心里的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周作人则经过五四运动的热潮之后,发现新村主义的理想主义竟是一场梦幻,感到幻灭。1922年、1923年这段时期,虽有思想上的“时差”,但兄弟俩的心绪还走得很近。
这句“寂寞与虚空”隔了两年时差,在鲁迅小说《伤逝》里反复出现,我想这也不是巧合的。小说里有一段,子君不辞而别,留下来的史涓生怀着失落感守在家里的情景。鲁迅描写如下:
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
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
周作人用来“寂寞与虚空”对有岛武郎表示哀悼时,在“沙漠”上的寥寥无几的“同行者”的领队本来应该是大哥的(29)。虽然在《伤逝》里的文本里鲁迅有无此意无从知道,但可能因此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认为《伤逝》是写自己兄弟诀别的(30)。
初稿2011年7月13日
修正稿2011年11月12日
初稿发表于《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暨“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绍兴2011年9月25日)。修改过程中参加《现代中国与东亚》国际WorkShop(东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合办),得到了丁帆、王彬彬、吴俊、傅元峰教授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释:
①《九三·辛亥革命(二)——孙德卿》“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知堂回忆录》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②《『白樺』口ダソ号壳却記事について:周作人と武者小路实篤の出会い》(《實踐國文學58号,2000年10月》)结论大致如下:周作人看到武者小路所写的《版画展览会》(《白桦》第2卷11号,1911年11月)的公告,知道有出售《白桦:罗丹特别号》立即邮购,后来还邮购《白桦》过刊。武者小路对此表示感激,在《白桦》(第3卷第4号,1912年4月)《编辑室》写道:“特别高兴的是支那绍兴城的先生说要补全自己没买到的《白桦》”。这可推测为周作人。
③《周作人日记》1916年4月5日项。于耀明在《魯迅訳『ある青年の夢』について》(《武庫川国文》50号,1997年11月)中指出这个事实。
④这里根据龟井胜一郎(经过本多秋五的修正)的定义。第一期(前半)为否认并离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强调自我中心主义时期,到后半则重回人道主义。第二期从人道主义发展到新村运动时期。第三期为离开盛行普罗文学的文坛,埋没于写传记。第四期为赞同大东亚战争的时期,第五期战后文学时期。王向远在《日本白桦派作家对鲁迅、周作人影响关系新辨》(《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1期)中根据本多秋五探讨武者小路的人道主义和后来的突变原因。
⑤《周作人日记》1918年4月8-10日及17日项。
⑥这里按照原文重新翻译,意思应该如下:“我们不要从国家的观点看,要从人类的观点看。”
⑦藤井省三『「希望の論理」の展開』(『魯迅—「故鄉」の風景』,平凡社1986年),藤井省三『魯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
⑧据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的译文。与鲁迅稍不同。
⑨《新青年》第6卷4,5号(后收《艺术与生活》)。
⑩山田敬三对此有详论。「魯迅と『白樺派』の作家たち」(『魯迅の世界』,大修館書店1977年)。
(11)此据有岛武郎著《ク口ポトキソ》(《新潮》1916年7月号、《有島武郎全集》第7卷)。
(12)所谓“和您一样的尝试”是1922年落实了。他发表《一个宣言》之后,放弃在北海道的农园产权,改名为《共生农园》,捐赠给农民。
(13)此处部分参考上牧瀨香著「有島武郎の前期評論」(「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特集有島武郎」,2007年6月号)。
(14)一般译为《爱是不惜抢夺》。
(15)据鲁迅译《与幼小者》(《现代日本小说集》,新星出版社版2006年版)。
(16)鲁迅在《随感录63》(1919年)又引用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说“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也许早注意到两者分歧。
(17)此处依据拙稿《五四時期の周作人の文学観》(《日本中国学会報》第42集,1990年)。托尔斯泰版本参照英译本Leo Tolstoy,“What is Art?”The Scott Library.1899.London.与日译本:有馬祐政訳《藝術論》(博文馆1906年)。此处引用的中文著者自己翻译,部分引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1920年)里译介的部分。
(18)如在《山中杂信三》里面说“但我又舍不得不看(报纸),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
(19)其实当时很多日文书是经过在北京的鲁迅手里买的。这本书也在鲁迅日记1913年8月23日有记载。但可能为了赶紧给弟弟传过去,他没有仔细看。
(20)《鲁迅书信》1921年8月25日“沈尹默绍介张黄,即做《浮世绘》的,此人非常之好,神经分明,听说他要上山来,不只来过否?”据《周作人日记》“8月26日(沈)士远、尹默偕张凤举黄君来访”(此时在香山疗养)。据《鲁迅日记》,徐祖正1922年也回国了。他们都是京都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21)《关于苦闷的象征》(1925年1月)里说及在中国早就有以为明权翻译初稿的事情。
(22)拙稿《周作人と明末文学——〈亡国之音〉をめぐつて》(『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17集,早稲田大学1991年刊)。
(23)此处依据拙稿「中国語訳·有島武郎『四つの事』をめぐつて——『現代日本小説集』所載訳文を中心に」(『大東文化大学紀要』第30号、1992年3月。
(24)这部原著与《与幼小者》都收录于《白桦之森》(白桦派合集,新潮社1918年)。
(25)通常译为易卜生。
(26)丸山升在「魯迅と『宣言一つ』——『壁下訳叢』における武者小路·有島との関係——」(『魯迅·文学·歴史』,汲古書院2004年,初出『中国文学研究』1期,1961年4月)指出在1926年、1927年的《鲁迅日记》里频繁出现购买《有岛武郎著作集》的记录,说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反而对有岛的思想感兴趣的。但这也不能为凭。
(27)鲁迅翻译有岛的文章上述之外有《以生命写成的文章》、《小孩儿的睡相》两篇,但都是短文。
(28)江绍原:《译自骆驼文》,《语丝》第一期1924年11月。
(29)清水贤一郎在「もう—つの『傷逝』——周作人逸文の発見から」(『しにか』1993年5月号)指出,鲁迅写出《伤逝》的九天前,周作人发表散文《伤逝》(《京报副刊》1925年10月12日),当中译介哀悼兄弟之死的罗马古典诗,与兄弟道别“保重”。这篇与鲁迅《伤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0)周作人《知堂回忆录》141《不辩解说(下)》里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白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新青年论文; 沉沦论文; 周作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