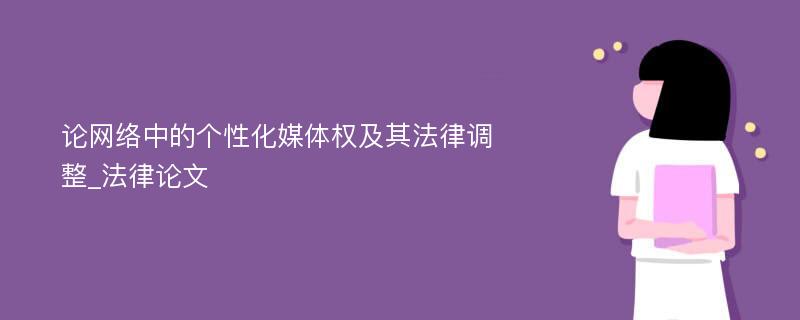
论网络中个体化媒介权及其法律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化论文,媒介论文,法律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1999)03-0035-05
一、对网络法理论和立法的现状分析
随着网络在科技进步、信息传播和商业运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网络的法律调整已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对网络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现状都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网络中的诸多现象进行了探讨,例如对网络案件的国际管辖权、知识产权的保护、ISP (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等等。但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对网络法律调整的宏观认识,特别是缺乏对网络法律关系的基础——权利和义务的深入分析。同时,各国特别是网络发达国家虽都竭力对网络进行法律调整,但至今尚未对网络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达成一致,立法速度远滞后于网络发展进程。以网络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截止目前还未有一部统一的联邦法典或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判例。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网络——这一新兴社会现象中所蕴涵的“权利”还未有充分的认识,而权利在法律上具有“本原”的地位,不仅是法律关系的核心要件,也是立法规定的对象和出发点,同时通过对权利的界定,作为权利界限的义务也就能清晰地把握。因此,对网络中权利的分析是解决网络诸多法律问题的基础。
二、对网络的深层次分析
权利作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的法律概念,对其性质、特点的认识应首先研究其产生的客观社会环境,因此,分析网络中的权利,应首先研究网络。笔者认为,可作以下两方面的阐释:其一,对网络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未有网络之前,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利用受时间、空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工业权威下形成的社会分工,这些因素使得不同的社会主体拥有不同意义上的资源优势,如政府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专业领域的人员拥有专业知识资源。这种分工直接导致了社会成员在履行社会功能或社会角色扮演上的相对固定化。就个体而言,这使得其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影响、利用效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今,信息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社会主体拥有的资源优势可以说是信息资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网络正是以信息为“中介”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数字化的表现”,众多社会关系实现了在网络上的“重新组合和再现”,例如许多传统的商贸活动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整体而言,网络这种对现实社会的“集合功能”使得网络宛如独立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虚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分工”的概念已不像现实社会中那么清晰、易把握,社会主体的角色扮演表现出很强的变化。这使得个体借助网络能够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更富于效率、范围更广泛的认识、利用、影响。“雅虎”(YAHOO!)的创始人通过在网上提供网址搜索服务,并为其他商家登载广告,仅数年间就积累了上亿美元,一跃而成为全美500 家大公司之一。这样的商业发展方式和速度在前网络时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而,网络很大程度上具有现实社会的意义,这也是网络的法律调整应予侧重的地方。伴随着网络概念向人类社会纵深领域的延伸,网络对现实社会的覆盖范围,个体与现实社会的交互性作用会有更高层次的发展,网络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主要生存方式。其二,对网络在技术角度上的分析: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或多或少都带有技术性特征,普通的如收发电子邮件、网址访问,更为深层次的如编写基于网络运用的程序、入侵他人电脑等等,因此,对网络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需借助技术上的帮助:例如下文提及的网络中权利的成本与收益、如何避免裁判人员面对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产生的对案件认识上的偏差、当事人关系的形成和个案的后果等等。笔者认为,对网络中权利的认识应结合网络的社会属性、技术特征加以分析。
三、个体化媒介权的出现及特征
网络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功能之一便是网络能够作为信息的媒介,在这一点上,其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是相同的。而未有网络之前,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的信息交流中居于枢纽的地位,人们所需要的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这些媒介获得的,这些媒介对人们的思想、各种社会活动有着深刻、长远的影响。同时,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均由特定的组织机构所控制,如新闻机构、电视台、电台、以及各种咨询,信息中介机构等等。由于社会分工的作用,这些组织机构天然具有对社会中大多数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控制着各种信息的获取、发布,虽然这些媒介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他社会主体在信息获取和发布能力上难以与之相比,这也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这种格局实际上赋予了这些组织机构一种特殊的权利,笔者将其定义为“组织化媒介权”。对这种权利的调整各国法律均有体现。与这种权利相比较,其他社会主体虽然也有获取、发布各种信息的权利,并得到了来自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保障,但权利行使的条件、范围、途径却受到这种格局的很大限制。然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上文已提及:网络具有对众多社会关系进行集合、重组的功能,通过信息达到了对现实社会抽象化的表现,这使得人们对各种信息利用的自由程度、范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媒介”信息的功能在网络中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媒介权”呈现出由传播媒介集中统一掌握向其他社会主体分散扩展,由组织化向个体化过渡的倾向。换句话说,个体取得了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相似的社会地位,虽然这种地位目前并不十分明显,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后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在获取和发布信息时可能享有的自主权甚至可以全面摆脱传统媒介的限制。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位顾客购买了一台笔记本型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屡屡发生硬件上的故障,该顾客遂与销售商交涉,但后者却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前者将此事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公布,经其他网络用户递送传抄,影响很大,销售商委托律师找到该顾客,声称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商誉,要求立即停止这种“侵权行为”。(1)不难想象, 该顾客如果采取起诉或向消费者组织投诉的方式取得的影响会很有限,而借助网络则获得了与传统媒介相近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实际上赋予了人们一种全新的获取、发布信息的权利,笔者将其定义为“个体化媒介权”,这里的个体泛指除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表现了信息获取、发布上的分散化趋势。
就已有的法律理论对个体化媒介权进行考察,这种权利应属于“私法”的范畴,因为该权利的行使是基于网络用户的自主意愿,这与其他私法上的权利所遵循的“意思自治”原则并无区别。因此,“个体化媒介权”应是一种私权,具备私权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应当看到:私法与公法是人类社会法律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共生共存的法律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在当代,两者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表现在私法上,则是“私法的公法化”,这一趋势将公法的一些理念融入到私法自身的体系之中,从而使私法上的权利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义务,私法权利由“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而不仅仅是“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那么简单。这一趋势表现在诸多法律领域,例如:大规模的环保立法的动因之一就在于限制赢利实体经营权的滥用而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潮流旨在从法律上矫正消费者与销售商、生产商的不平等地位;城市化进程中对租赁权的强化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立法意在抑制不动产所有权的运用,满足社会成员对房屋的需求。有鉴于此,“个体化的媒介权”也应是一种承担了较多社会义务的权利类型。虽然义务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定量”分析,但对这种权利的“定性”是必要的。通过对该权利特点的进一步分析,亦能印证此结论:现实社会中许多权利的行使都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而人们在网络上对信息的各种利用往往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比如在公开网站上公开商业秘密供人免费下载,散播病毒程序等等。可以说,个体化媒介权涉及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使得该权利有被“滥用”的危险,并且,这种滥用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每种权利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从技术角度讲,IT产业的一大特点便是技术、产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这使得构成网络的软、硬件的价格长期处于下降的状况,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网络得以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从这点上讲,个体化的媒介权具有低成本的特点,这种低成本表现在权利的获得和行使上。而高收益则表现在人们通过网络能够突破传统获取信息的方式的限制,达到对各种信息的充分、高效利用。这促使人们会更经常地运用该权利,从而增大了权利被滥用的机率;并且现实社会中的权利人们可以以时间、空间为参照系,凭借语言、行为或其他外部证据认识权利的存在,把握权利运行的轨迹,从而能够建立起一套权利的制约、监控机制,而人们在网络上的各种活动均被数字、图形所抽象化了,个体化的媒介权由于缺乏外部的“支点”而难以清晰把握,权利行使上具有抽象性,难以对该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
综合以上分析,个体化的媒介权不仅是一种承担较多社会义务的权利类型,同时该权利还具有涉及对象的不确定性、低成本,高收益、行使上的抽象性的特点。
四、“个体化媒介权”的法律调整
首先,立法上应承认该权利,无论叫个体化媒介权,还是其他称谓,给出一个确定的法律定义是必要的,以统一人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避免面对纷繁芜杂的网络现象而产生的法律概念上的混乱。由此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对该权利应采取什么样的立法取向。笔者认为,考虑到该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对其的“法律管制”是必然的,但在立法上应避免“精细化,可操作性强”的倾向,这是因为该权利的行使方式非常多样化:(1)从法律角度上讲,既有法律支持和鼓励的, 又有法律明确规定加以惩戒的,前者如个人编写实用、健康的共享软件,热心的网民主动担当公众论坛的编辑,帮助清理不良信息等;后者主要是滥用该权利导致的与其他权利的冲突,特别是网络上的刑事犯罪,例如在网络上进行的色情转播活动、利用网络窃取国家机密,重大商业秘密等。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除此之外,该权利更多的行使方式还有待在法律上进一步认识或急待调整,例如我国目前广为争论的IP(INTERNET PROTOCAL)电话(2)网络广告、连锁电子邮件等等。可以看出,立法上不可能穷尽这些情况,精细化的立法只会导致人为的扩大个体化媒介权的社会义务界限,未能给权利的运用提供合理的法律发展空间,从而在长远上束缚了网络事业在一国的发展,并且,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技术密集的层面,完全由法律条文设定该权利的规矩与方圆,无疑于是由立法者为网络起草“技术守则”。这种立法倾向在我国已有所反映,值得警惕。(3)笔者认为, 个体化的媒介权同其他权利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既在法律调整中的法律解释以及由此产生的裁判中的自由裁量权,结合以上分析,对该权利的立法总体上应“宜粗不宜细”,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制定原则性较强的“弹性条款”,目的在于为个体化媒介权提供合理的法律发展空间,同时为自由裁量权设定界限。其二,立法上应明确裁判机构享有自由裁量权。最后,规定对自由裁量权的“分权制”。第一点实现的是对该权利法律调整的“宏观控制”,第二点则是通过对网络案件的裁判保护实现法律对权利运用的“微调”,同时为分权制奠定明确的权力基础。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第三点:由于技术在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形成需要借助技术分析,个案的后果也要从技术上加以评估,并且技术问题较容易界定,因此分权的含义在于:将案件中的问题区分为“法律问题和其他问题”与“技术问题”,在此基础上,前者由裁判机构负责,而后者则由技术人员组成的审理机构作出裁决,该裁决对当事人、裁判机构有拘束力。这种设计确保了将复杂、抽象的技术问题升华为具体、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在审理方式上保证了裁判的公正和科学。
其次,个体化媒介权不仅行使方式上多样化,并且行使的次数也异常频繁,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网络上每秒钟都发生着具有各种法律意义的现象。因此,完全由现实社会的裁判机构实现对网络案件的管辖将是不可思义的,在经济上也极不合理。笔者认为,虽然该权利行使方式上多样化且次数频繁,但该权利行使的具体后果却可以认识和把握,因此,可以以“效果原则”将网络案件区分为两类:其一是滥用该权利触犯刑律或有重大影响或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案件,其二是除第一种之外的其他案件,前者由现实社会的裁判机构管辖,这有利于从宏观上实现对个体化媒介权有力、正确的法律引导。后者可由在网络中成立的裁判机构管辖,虽然这种裁判机构也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在网络上的表现或许只是一个网址而已,然而其却是网络集合社会关系功能的一个具体反映,职能是现实的。实际上,现实中的审理活动本质上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这与在网络上进行审理并无本质区别,并且目前的网络技术已能够实现多方参与的信息传送,因此,应有“网络审判”、“网络行政”、“网络仲裁”等提法。这些裁判机构也应实行上文提及的分权制,比如可以在网络上成立技术委员会。在对网络案件的处理上,笔者认为,应突出“法律责任承担的技术化”,这种技术化应体现个体化媒介权的社会义务特征,例如,可责令责任人自行承担费用在网络上开辟义务提供咨询和相关服务的网站,责令网络服务商拒绝为责任人提供登录网络的服务等等。这有利于从经济、效率角度达到对该权利的有效调整。
最后,作为一点补充,个体化媒介权行使上的抽象性使得证据原则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这也是各国对网络的法律调整较为薄弱的一个原因,因此,至少在目前,强化该权利的社会义务性,加重法律责任从而抬高法律的威慑力应是立法上的另一可取方向。这可表现在诸多方面:在刑事制裁上除加重运用自由刑和财产刑外,还可更多的运用“资格刑”:比如视具体情况终身或一段时期内禁止责任人从事与网络有关的职业;禁止其以各种方式接触电脑设备;禁止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向他人传授有关知识等等;对于够不上犯罪行为需要进行处罚的,应坚持“重罚”的原则,除传统的货币负担方式,还可责令责任人在一段时期内不计报酬的从事与网络或电脑有关的公益活动。这种倾向在国外已有体现,新加坡国会1993年6月通过了滥用电脑法案, 此后又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对责任人罚款额最高可达10万新元,最长刑期为20年。笔者认为,鉴于网络今后的重要性,坚持这种立法倾向是必要的。
收稿日期:1999-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