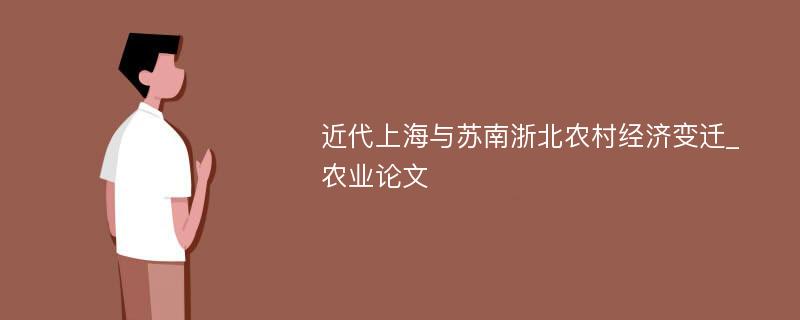
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农村经济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毗邻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与此同时,原先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这些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互动的双向经济关系。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以其地理、经济等综合优势,很快取代广州,跃居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并发展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毗邻上海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并因此保持了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加快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进程,是当今这一地区继续走在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前列的历史底蕴,总结其中的动因、历程和影响,可为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地处上海周边的苏南浙北农村,包容清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与上海之间经由蛛网般的内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欠、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①a]近代上海的崛起,既得力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一、经济作物的扩展
上海开埠后,经由上海港进出的繁盛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直接刺激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一)临江近海的棉花产区
明清以来,长江口两岸的高亢、沙土地带,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种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①b]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8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②b]这一时期经由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的持续增长[③b],无疑也有利于植棉业的扩展。这种扩展,在长江口两岸原先相对荒僻的近海地带尤为显著。地处东海边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已都栽种了棉花,“产数约三十三万包有奇,每包计七十斤,四乡踏户皆挑运至沪,为数甚巨。”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销路畅旺,该县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因此也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近海的大团[④b]。在长江口北岸的通州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地方史料载:“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自昔商旅联樯,南北奔凑,岁售银百数十万。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利,西人又购我华棉,与美棉、印棉掺用,出布甚佳,而吾通之花市日益盛,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传统产区的棉花生产更是有增无减,1863年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出口原棉价格陡涨,“松江、太仓一府一州各县各乡大小花行来申抛盘货三四十万包”,连同其他府县的供货,“统计不下百万包。”这种受出口需求推动呈现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年,且地域特征鲜明,“其地脉东西自浦东起,西北及常熟,更越长江亘通州,其面积之大,实不愧为大国物产领域。”在这一区域里,“到处产出棉花,此等产出棉花地之名,常著闻于当业者之间。”[⑤b]《1902年至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称“目前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截止1912年的统计,“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二十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⑥b]
(二)太湖沿岸等蚕桑产区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一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搬运至广州,行程约三千五百华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统计约增成本35%—40%之多[⑦b]。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⑧b]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①c]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经由上海港的生丝出口通达顺畅,蚕农获利相应增加,“每年蚕忙不过四十天,而亦可抵农田一岁所入之数,”植桑饲蚕者因而更多。江苏吴县,“初仅吴县属香山、光福等处有之,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匮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②c]浙江长兴县,乾嘉之际蚕业不旺,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辟通,蚕业遂盛,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作为生丝出口初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十分兴旺,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丝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如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③c]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木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④c]
1860年代中叶太平天国战事平息,面对残破的农村经济,受上海港生丝大量出口的吸引,蚕桑产区又有新的扩展。湖州府,“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⑤c]在苏南地区,蚕桑产区则由太湖沿岸向西和向北伸展。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这时“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⑥c]无锡、金匮两县,以往“饲蚕之家不多”,此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这些地区的生丝产量,逐渐超过苏南地区原有的蚕桑产区。1880年6月21日《申报》载:“近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故日来苏地丝价虽互有涨落,而价目尚无定准。”常州和宜兴,“过去产丝几乎等于零,而今年(1880)生丝的总产量估计为六十万两,价值九万海关两。”溧阳县,以往最多时年产生丝约260余万两,1880年已增至500万两,约值75万海关两,其中约80%经上海港输出国外[⑦c]。苏南地区蚕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引人注目,1896年张之洞奏称“苏、常蚕桑之利近十年来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次年去实地游历的外国人目击“自上海至苏州有江,江岸多有桑园点缀;自苏州至无锡亦江行,江之两岸一望无际皆桑也。”所到之处附近村落,“每村或三十户至五十户,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⑧c]
苏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在上海郊区也有体现。与棉花相比,上海周围农村蚕桑业受水土条件、耕种习惯等影响,长期发展迟缓,自上海崛起,受丝出口贸易及缫丝加工业设立的推动,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有规模。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而育蚕者更盛”,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即便在稍远的青浦县,1909年也有人创设了蚕桑研究社,并在重固乡间栽种桑树二千余株,以求推广[①d]。
(三)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
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843年约为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跃居全国首位[②d]。适应这种变化,一批蔬菜产地在上海近郊陆续形成。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功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③d]这类纯商业性的生产活动,无论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经营时间的长短,都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其出产较多者,如城市之塌菜、青菜,罗店之瓜茄,杨行、月浦之红白萝卜,刘行、广福之韭菜、韭芽,江湾之马铃薯,真如之洋葱头,彭浦之卷心菜以及洋种菜蔬,均甚著名者。”上海县,“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④d]这方面的发展势头是醒目的,大片土地已用于蔬菜种植业,“蔬菜中的卷心菜、花菜、洋葱之类,过去仅为外国人所食用,现在已大部分由中国人消费,并且还输往香港和中国的其他口岸。”1912年海关报告载:“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求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⑤d]
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3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之后在大场、吴淞、彭浦、真如等地,又相继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创立。上海近郊的畜牧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最早开业者是在1884年,是年“有陈森记者在殷行开设牧场,畜牧牛约二十头,专取牛乳,销售于(吴)淞口各国兵舰,每日出乳二十余磅。四五年后,以兵舰停泊不常,销数渐减,几致歇业。自铁路告成,运输便利,江湾南境多侨居外人,日必需此,销售不仅在兵舰一方,营业渐见发达矣。”[⑥d]
显然,近代上海的崛起,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它有助于改变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和助力。
二、手工业的衍变
受近代上海崛起的冲击,苏南浙北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
(一)手工轧花业
上海开埠后,原棉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轧花业的兴起。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嘉定县,“棉花以车绞去其子,盛以布包,运售他处,昔用土车,自日本车行,今皆改用日车;”“轧棉工作,至为普遍。”与嘉定、上海县接壤的青浦县东北部,“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①e]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造而成。原因是,“棉花出口增加,原来的土法轧花不能胜任,日本轧花机乘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其需求之大,令制造厂应接不暇,“轧花机销售于上海附近农村,松江、莘庄销路最大,常常供不应求,营业非常发达。”以致一些船舶修造厂由兼制转为专门生产,截止1913年形成拥有16家专业厂的轧花机制造行业。是年,上海国产轧花机的年销量达2000余部。除上海郊区,它们还销往崇明、南通、泰兴等棉花产区,义兴盛铁工厂“最多一天的产量达二十台,主要销往苏北一带。”[②e]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同时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逐渐被淘汰。”[③e]一些地区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逵荣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十二匹马力引擎一台,轧花机十五台。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是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④e]
(二)手工缫丝业
自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苏南浙北产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尚可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生丝出口畅旺,南浔、震泽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①f]。江浙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兰西、美利坚各洋行咸来购求,嗣又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称。”加工技术也不断改进,“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前去实地察看的外国商人记载,“南浔的主要生产为一种上等生丝,该地亦为附近所产再缫丝之市场,”这种专为出口的再缫丝,产量年有增加,1878年约产4200公斤。从事该业的手工劳动者“每两工资十文,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②f]
南浔一带这种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很猛。此前当地以出口辑里丝著称,“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乡土调查资料载,“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③f]18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兴起后,无锡等新起蚕桑产区的农户多为专业养蚕收茧出售,不再兼事缫制,南浔、震泽一带传统产区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有相当规模,故《南浔志》曾自诩“无锡、绍兴率皆售茧,我浔则无不售丝者。”缫丝业的发展,还曾带动相关手工业的生产。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于是手工捻制丝线业应运而起,产品“亦销洋庄,每一担值四五十元至八九十元。”湖州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花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000匹,足见周围地区当时手工缫丝业之盛[④f]。
(三)手工棉纺织业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苏南浙北农户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上海开埠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批量涌入,周围农村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困难。在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论述,但应指出以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周围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洋货的冲击下,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的认识是欠妥的。因为国门被打开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廉价洋纱的涌入,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沉重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手工生产,而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那部分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就有所不同。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即由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没落和破产。上海县农村,“机器纱盛行,手纺纱出数渐减,机器纱俗称洋纱,用机器纺成,较土法所纺洁白而细。”该县西南乡用它织成的土布,每年约有百万匹,民国初年仍有四五十万匹,销往东北、华北和山东等地[①g]。经由上海港输入的洋纱大幅度增长,“推销于上海附近及江南一带,最初每年仅数千件,不久就达到二十余万件,”更推进了周边地区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结构的衍变,经上海港集散的土布成份相应发生明显变化。起初,“上海有些土布庄还拒收洋经土纬的土布,门口贴着一张牌纸,上书‘掺和洋纱,概不收买。’但洋纱条杆均匀,织出来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于是洋经土纬的土布越来越多,土布庄也只好收买。”1895年,“门市收进的土布约有60%已是洋经洋纬,40%是洋经土纬。”以后,洋经洋纬的土布所占比重更大。浦东三林塘所产土布,1910年前后已全是洋经洋纬[②g]。
由此可见,苏南浙北农村手工业的上述深刻变化,与近代上海的崛起息息相关,并因此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自有其鲜明的特点。它集中表现为,依托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地位,周边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在面临洋货竞销时,得以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流通渠道和市场取向等重要环节,较快地转向附丽于直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沟通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了在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一旦手工棉纺织业衰败,农家生计便陷于困境的窘况,农村经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荡。这些变化所体现的发展趋向无疑是积极的,应予肯定和总结。
MONDERN SHANGHAI AND CHANGES OF ECONONLC STRUCTURE
IN COURTRYSIOE OF
SOUTHERN JIANSU AND NORTHERN ZHEJIANG
Abstract
The basic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mphasize modern Shanghai as an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countrysideof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Zhejiang include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etc.
注释:
①a 梁章巨:《浪迹丛谈》卷5,均赋;钱泳:《履园丛话》卷4,水学。
①b 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7,第2页。
②b 《申报》1876年9月15日;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
③b 据统计,1869年经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是三万七千余担,至1890年已增至四百七十七万余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详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73页。
④b 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884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
⑤b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97、397、517页。
⑥b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58、204页。
⑦b 何良栋:《论丝厂》,《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535页。
⑧b 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研究所,1939年,第121页。
①c 温丰:《南浔丝市行》,《南浔志》卷31,第2页。
②c 《农学报》1897年5月上;民国《吴县志》卷52,风俗。
③c 同治《长兴县志》卷8《蚕桑》;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
④c 光绪《菱湖镇志》卷11《物产》;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⑤c 同治《湖州府志》卷33《物产》;同治《安吉县志》卷8《物产》;光绪《平湖县志》卷8《物产》。
⑥c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8,物产;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6,物产。
⑦c 《申报》1880年6月21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79页。
⑧c 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43,第15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79页。
①d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民国《青浦县志》卷2《土产》。
②d 〔美〕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③d 民国《真如志》卷3《农业》;民国《江湾里志》卷5《农业》。
④d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
⑤d 《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44、158页。
⑥d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
①e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4《物产》;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
②e 集体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100—102、173—178页。
③e 同上,第175页。
④e 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美〕佑尼:《中国纺织缫丝情形》,《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6页。
①f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81页。
②f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0—82页。
③f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2页。
④f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6、81、82页。
①g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
②g 徐新吾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