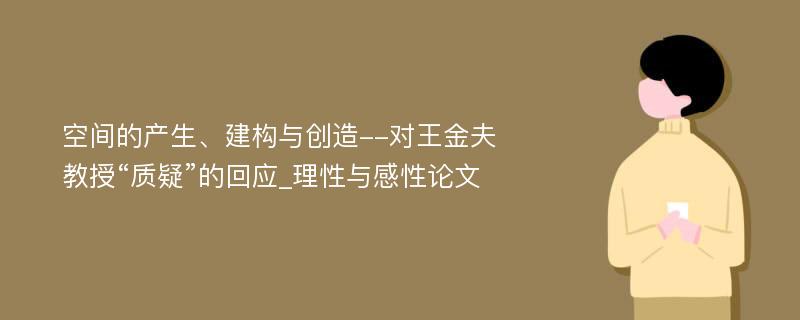
再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回应王金福教授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空间论文,王金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029-07
读了王金福教授针对拙文《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①所写的批评文章《“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②之后,我想与之讨论以下三方面问题:(一)空间是否同时拥有主观性、意识性和精神性?(二)自然空间是否外在于人类实践?我们是否能够创造物质和空间本身?(三)何谓社会空间?不具有社会性的空间能否称为社会空间?
一、论空间的主观性、意识性和精神性
英国哲学家爱德华·摩尔作为一位新实在论者曾明确表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在他来到地球上之前,地球已经存在很久很久,在他死后,地球仍会继续存在很久很久。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常识。正基于这种实在论认识,从二十多年前我开始研究“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时就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反实在论者,至少在承认自身、家人和周围事物存在的日常生活意义上,人们都是唯物论者、实在论者和客观论者。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物的客观性、实在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主观性、虚无性和由此升华出来的概念、观念和理论;我们所面对的空间,是否就像王教授所言:“既然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意识性,它也不可能是精神的存在方式。”
对此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复数。尤其在今天,已经从原初的“宇宙蛋”所开启的单一世界演化出无限复杂的多元世界里,我们更没有理由和根据只坚守一种理论学说、观念或信仰。在这里,我不必过多地陈述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如何超越纯粹的客观性和实在性的牢笼而进达于人与自然、认识与实在相统一的辩证法,仅就我所认可和赞成的马克思与罗素的物质观和时空观而言,也足以表明: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物质世界和时空形式”是如何既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又具有主观性、意识性和精神性,是主客体的辩证与统一。特别是马克思,在物质观和时空观上,从未离开辩证思维来孤立地论述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和实质。在论及物质客体时,他总是将其指谓为“思想客体、感性客体或属人的对象”,且总是站在辩证法的高度批判流行的实证论、经验论和庸俗唯物论,批判旧唯物论所犯的机械论的、非历史的、非辩证的以及抽象地了解人本质的形而上学缺陷。
他当然主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③,并坚持“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的理论”;但与旧唯物论不同,他明确指出,人在生产劳动中既作为感觉论的唯物主义者发挥作用,也作为主体的唯心论者发挥作用。尤其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拥有把唯心论和唯物论相统一的真理。因为,“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物质,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④。所谓的“客观实在”,除了全部经验给定的物质之外,还包含构成它的形式。而这些形式作为观念的东西,只能由纯粹精神的、智力的内省来揭示。
然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论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⑤。而马克思与旧唯物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⑥在费尔巴哈那里,纯粹的自然人,作为空洞的原始主观性,不是能动地、实践地,而是被动地、直观地同自然的死一般的客观性相对立。而马克思则是要把自然消融在主客体辩证法中。他认为物质概念既是人的实践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总体。费尔巴哈由于无反思地单纯强调总体,而陷入“纯粹自然”这种素朴的实在论神话,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把人的直接存在与其本质等而视之。而马克思既没有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同样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来替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去抽象地责难黑格尔的唯心论,而是看到了真理是在不真实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为此,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看世界是以主体为中介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在弄清楚从康德到黑格尔等哲学家之所以会产生独特的激情之后,“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客观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过程这一思想的全部意义”。
至于罗素虽然不是一位辩证法论者,但作为一位哲学家也深入分析论证了有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认识、意识与实在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说:“在每一个哲学问题中,我们的研究都是从可以称之为‘材料’(data)的东西出发的,我所说的‘材料’是指那些常识性的东西……首先是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特殊事物——家具、房屋、城镇、其他人等等的知识。”⑦这些日常事物确实是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在空间问题上才存在两种空间:“一种是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所占据的空间;另一种是物理空间,这种空间容纳有他人的躯体、椅子和桌子、太阳、月亮、星星等等,这些东西不仅为我们个人的感觉所反映,而且我们还假定它们是独自存在的。……至于那种主观的空间,有包含我所有的视觉经验的视觉空间,有触觉空间,有威廉·詹姆斯所指出的那种胃痛感的广延性等等。当把我看作是万物之中的一物时,所有各种主观的空间就皆备于我。我所看见的星空不是天文学上所说的那种遥远的星空,而是星星作用于我的结果;我所看见的东西是在我之内,而不是在我之外。”⑧
我当然不是想只用权威者的话来表达我的认识,只是想说明:我们用眼睛看到、用手触摸、用心领悟、用嘴说出、用文字描述或用数学符号表达的空间,就像物质和运动、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一样,总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体。除非你像一尊石佛,不看,不摸,不想,不说,也不写。然而那样一来,对于一块僵死的石头来说,不仅宇宙万物都是无,连它自身是否存在也无所知晓。因为迄今为止,这块石头所拥有的全部意义都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这个认识和实践主体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所赋予的。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大量“有眼不识泰山”的现实。因此,离开人,就没有我们现实所熟知和理解的一切。尽管你可以大胆地推论:存在一个客观实在的空间。但是,“任何一个愿意假定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经验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人,也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否认这种空间”⑨。
当然,王金福可以坚持一种朴素的、常识性的和经验性的唯物主义空间观。就像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告诉求教者:“太阳就像你家的脸盆那般大”一样,他的回答无疑是唯物的、经验的,也是实在的,但却是错误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再来争论自然、物质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很没有必要。就像今天你再和一位基督徒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得到沉默或讥笑的回应一样。因为这个问题是中世纪神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关于空间,今天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弯曲性、多维性、相对性、虚拟性,以及有关黑洞理论、虫洞假说、超光速旅行、膨胀的宇宙等高深的理论探索。总之,人类要把他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性尽可能多地赋予这个“自在的宇宙”,使其变得千姿万态和丰富多彩。至于我多年来也一再强调空间的主观性、意识性和精神性,当然不是要无知地否定它的自在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主要是想调动人们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积极自觉地参与宇宙自身的不断创生运动。
二、自然空间的实践性和创造性
王金福教授在文中颇为理直气壮地说:“先在的、外在于人类实践的自然空间不可能是人创造的。”对此,从朴素实在论的角度上看,当然无可非议。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论述物质世界的自在性时,的确用过“先在的”这个词,以表明“谁都知道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的朴素道理。然而,一经涉及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一经涉及“外在性和内在性”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据此,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为唯物主义命题的主要源泉之一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就是因为人们对这实在的关系从首要意义上讲,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实践、变革的东西,而且都是由社会规定的。如果没有作为认识主体的社会,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或自然与实体的认识。因为在人的一切认识中,“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⑩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实践主体总是使认识对象、劳动对象或物质对象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这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是最高的存在原则。再者,人在实践过程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抽象;相反,总是仅仅接触和处理有关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各个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的存在形态。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和特殊之中,所谓的本源性物质或存在物的本源根据并不存在。物质的实在性实际上只存在于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现实中的物质世界在处于“为他存在”或“自在存在”时,都与以往朴素的实在论或形而上学唯物论不相容。辩证唯物论不承认有脱离具体规律独立存在的自在实体。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总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经由工业形成的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1)。与唯心论者突出的精神一样,物质也决不是用来解释世界的绝对统一性的根本。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破除了所谓事物的‘终极的’、‘不变的’本质的概念,破除了所谓一切存在物的‘终极’的性质与其现象都可以从中推演出来的绝对的根本实体的概念。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也不存在什么绝对根本的实体”(12)。正是基于这种辩证法,使得马克思把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了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为一体的哲学新体系。当然,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13)。因为这个世界包含的全部能动的意义,无非是人类通过各种行为、实践调节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达到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界也不是“绝对第一的基质”,而是一切都已经同社会实践所产生的认识和事物交织在一起,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具体地说,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类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14)。为此,马克思反对贬低人对自然认识的价值,认为最高的存在不是神而是人。因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从“作为存在物的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正是从这一基本出发点,从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而不是从有关物质的抽象体出发,唯物主义才得出“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实在的和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实在论观点,才得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彼此合乎规律的产生是不证自明的观点。因此,尽管一切自然规律本质上都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但是只有运用“社会”范畴,关于自然和自然规律的陈述才能定型和适用。如果没有人为的支配自然规律的社会实践,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现实中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绝对分离;自然与历史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无论从其范围还是性质来看,总是同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15)
既然人与自然、物质与实践具有如此辩证关系,就不能说“我们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只能改变物质的具体形态,因而,我们也不能创造空间本身,只能创造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16)。因为“物质”绝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它既意味着是万物之和,也意味着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认识的结果。没有离开具体的物质形态的抽象物质,也没有脱离人类所从事的具体认识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物质概念。再抽象的概念都是寓于具体的对象之中。正基于此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和抽象的物质概念的辩证法,我们才说,人类不仅可以生产和创造具体的物质形态和空间形式,也可以生产和创造作为普遍和一般而存在的物质和空间。抽象地讲“不能创造物质和空间”,对于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能力毫无裨益。再者,一切概念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自由的原则和“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在它的绝非空无内容的自身同一性里,总“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17)
也正是基于朴素唯物论宣传的被动的“客观论”和“实在论”的物质概念,葛兰西才批判地说,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接近人民、接近常识的。它和许多信仰与偏见,和几乎所有的人民大众的迷信(巫术、幽灵)紧密联系”(18)。“历史上,许多流行的宗教都是非常地唯物主义的。”因此,要深入把握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必须引进“实践哲学”这一“全新的、独立的和创造性的概念”。为此,他提出“实践一元论”,试图将马克思的“物质”概念直接指向与人的“具体的历史行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认为规定“物质”的内在属性者,实质上“就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19)人类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才将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对于实践哲学来说,人类不应当从自然科学和各种唯物主义的发现中来理解物质,而应当从一种人类关系、历史范畴、经济要素、一种有关物质性质的发现和发明,以及一种同生产力发展的紧密关系上来理解物质。换句话说,决不可以立足物质本身来考察,必须把它作为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所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现实中,除了人类实践变化着的形式之外,一切意义都从实践中来并同实践有关。因此,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唯一绝对的现实。那些自在自为的“客观现实”或物质世界,表面上看存在于历史和人类之外,实际上,所谓“客观的”总是指“人类地客观的”,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地主观的”相符合。“我们只能在同人类的关系中去认识实在,而既然人是历史的生成,那么,它也适用于认识、实在、客观性等等。”(20)因此,即使今天具有最高权威的实验科学,给人类提供的也只是“最客观化的和具体地普遍化了的主观性”。当形而上学唯物论说“客观性”就是指人类意识之外的实在性或自然界的永恒存在时,这实际上是一种神秘主义。因为任何人在论及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时,都只是在与自身及其语言和思想打交道,“都是任意的和约定的,即历史的构造”(21)。
三、何谓社会空间
王金福教授在文章中一方面表明“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说:“‘社会空间’不表示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社会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这段论述实际上就像是说“红花不具有红色一样”令人费解和不合逻辑。因为显而易见,不具有社会性的空间就不能叫做“社会空间”,就好像不具有红色的花就不能叫做“红花”一样。所谓“社会空间”就是因为其具有社会性才被称之为社会空间,因此,社会性就是社会空间的本质属性。就像“善性”是“善人”的本质属性一样。“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摹状词,首先就表明了“该种空间”作为一个专名具有“社会”的属性。再者,当王教授把社会空间界定为“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时,这实际上是说,社会空间本质上就是自然空间,它与自然空间毫无二致。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本身没有空间,它所拥有的空间实质上就是其物质基础拥有的自然空间。对社会空间的如此界定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们还是不能从中理解究竟何谓社会空间,或者究竟有没有社会空间。当然,在王教授为“社会空间”下定义的时候,这本身就等于设定了社会空间的存在,然而一经他的具体界定,就将其划归到自然空间的范畴,而使其化为乌有。没有认识到不同的摹状词使所修饰之专名往往拥有不同的性质,就像“好人”和“坏人”之质的差异。既然王金福否定“社会性”是社会空间的本质属性,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和理解“社会空间”呢?下面,我想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空间开始,对社会空间的本质予以陈述论证。
在海德格尔看来,眼下人们唯有把宇宙万物构成的“世界”置于由原初时空构成的“敞开之境”中加以沉思、领会、解释,“世界”的存在才能自行呈现,人们才能够下意识地“筑居”和保护“世界”。由此,经过他对空间的反思,将其展开为三个层面:
一是在本体论上,“此在”的空间性主要表现为“在世界中”(In-der-Welt-sein)与世界结缘。这种结缘当然不是说先把“此在”当作一个现成物,把世界看作一个三维几何空间,然后再把“此在”放进世界之内。就好像水放在桶里一样。与此“流俗的”空间观相反,“此在”的空间指的是人与世界的缘构成关系,即一种原初的关系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主客体间的传统认识论关系,而是本体论上的相互构成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叫‘此在’的存在者与另一个叫‘世界’的存在者‘并列存在’这回事”(22)。“此在”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世界中”,而世界也永远是与“此在”相互构成的世间境域。因此,从来就没有一个无世界的“此在”,或一个无“此在”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相互构成的本体论空间中,“人”和“世界”的含义从传统的“主客”之间的外在关系转变为相互缘起的构成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从实质上表明了属人的社会空间的本质,表明了社会空间中“社会”与“空间”的不可分割的原初性。
二是在生存论上,“此在”的空间性表现为与“周围世界”结缘,设置各种空间。因为“此在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生存”(23)。为了生存,“此在”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要“操劳寻视着”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此时,为了使生产活动顺利、高效地进行,“此在”必须对用具做到心中有数,按照用具的重要程度,把它们分别摆放在一定位置,即为用具设置空间。“此在”之所以能够为用具设置空间,因为它有两种生来就有的属性:“去远”(de-severance)和“定向”(directionality)。仰仗“定向”和“去远”两种空间特性,“此在”不断地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持续地生活“在世界中”,从而构建了人与世界、社会与空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空间完全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开辟和拓展的空间。
三是日常流俗的空间。在日常生活中,“此在”的空间性丧失其因缘性,异化为“在之内”。此时,“此在”必然要与处于一定的社会空间的他者打交道,并受到社会舆论、法令法规、文化传统、道德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被吞没,沉沦于“世界”之中。在这里,常人终日被“公共意见”所引领,与本真世界断缘,最后像石头一样被装进世界空间。这种空间就“好像是作为一个死板的框架在发生作用,此在对其世界的一切可能行为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却从来不从存在上触动这个‘框架’本身。但是,这样一种想象出来的‘框架’本身也是由此在的存在方式参与所造成。‘在世界中’的一种生存论样式就记录在这种沉沦现象之中”(24)。这沉沦中的常人在断绝与本真世界的缘分之后,便处于一种空虚无根的生存状态,此时,他不可能有正确的“缘关系”空间观,只能对空间作流俗的空间解释,并主观想象出一个无限大的容器:宇宙空间或绝对空间。这样一来,常人在现实中拥有的空间实际上只是社会空间的异化,而本真的空间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在世之人的空间,也即由人之生存决定的社会空间。
与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论相似,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创立了“身体空间论”。在他看来,后资本主义社会对身体的摧残变本加厉。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利用语言符号和政治权力等手段,对人的生命冲动、激情、欲望和生理节奏等进行隐秘的控制和规训,把现代日常生活变成冰冷的、毫无生命激情的“零度空间”。对此,列斐伏尔试图找到一条通往身体解放的大道,进行一次政治、经济和空间“三位一体”的总体性革命,在都市中心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空间”,把日常生活空间塑造成艺术品。特别是随着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迈进了一个以空间的生产、探测、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新纪元之后,以往的空间理论却把时间看作是革命和进步的,否认空间的社会批判意义,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25)而列斐伏尔的身体空间论则试图颠覆传统的空间观,把空间看作三元辩证的、身体化的和革命的;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艺术空间,身体才能完全获得解放。
由此,列斐伏尔的身体空间论既推动了尼采身体观的转向,又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身体空间)不是先在的、既定的,而是身体的产品。他的“空间建筑学”把身体作为本体和出发点,主张“空间的生产从身体生产开始”,而且“整个社会空间也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致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26)这里的“身体”都是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的后现代语境中的身体,也即活生生的人体。当然,动植物也都有“身体”,并用其生产自己的空间。但与动植物的“身体”不同,作为空间生产者的人的身体则是“空间的身体”、“双面的机器”。它由两个方面和向度有机地组成:一面是来自生存空间的物质性能量储存;另一面是“爱欲”,即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欲望和激情,在这里,“性器官是人体巨大能量的汇集处”(27)。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空间、物质资料和人类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生产的空间是农田;武士生产的空间是战场。由此,列斐伏尔作结论道,空间的生产方式是空间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空间就是(社会)的产品”。(28)空间的生产方式有其独立发展的历史,大致说来,它经历了“欲望的生产”、“空间中的生产”、“空间的生产”和“诗意生产”四种形式。由于每种生产方式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且都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所以列斐伏尔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将社会空间按先后顺序划分为五个阶段:绝对空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神圣空间(奴隶社会),历史性空间(封建社会),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社会),差异空间(社会主义社会)。(29)
这种空间演化状态既说明社会空间决定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也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空间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类解放也“产生积极作用”。为此,福柯在题为《差异空间》的演讲中,提出空间“异托邦”(heterotopia)的思想,试图为人们找寻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认为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空间时代,人类通过虚拟技术和电脑网络创造和延异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种空间既不同于自然空间或现实空间,也不同于想象的、无形的或纯粹抽象的空间。它是人造的虚拟空间,是社会空间的转型和延续。它有几何形状,虚拟主体可以在其间旅行,现实主体可以对其观察和利用,然而却无法用现实的尺度测量,因为它具有零距离的性质,以满足与日俱增的拥挤的人类需要和变迁。
上述我对社会空间的理解虽然大多是前人的思想,但我赞同和支持它,也希望别人能够接受之,以增加和推动我们对世界万物和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实践。当然,我也无意要用“空间生产”的概念代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从而否定空间的生产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因为谁都知道,建造房子、修建桥梁、制造汽车、创建工业园等无数与空间生产相关的物质资料的生产都不等于生产粮食、蛋糕和牛奶。我只是旨在强调:在人类文明史上,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具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注释:
①张之沧:《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载《学术月刊》,2011(7)。
②王金福:《“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载《学术月刊》,2012(1)。
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⑥[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98、14页,欧力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B.Russell,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London,1926.pp.65—66.
⑧⑨[英]罗素:《宗教与科学》,第109-110页,徐奕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13)(15)[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24—25、119、120、43页。
(1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
(16)王金福:《“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载《学术月刊》,2012(1)。
(17)[德]黑格尔:《小逻辑》,第327页,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09页,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20)[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87、363页。
(21)[意]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42页,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3。
(22)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Mac quarrie & E.Robinson,SCM Press Ltd.1962,p.81.
(23)(24)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Mac quarrie & E.Robinson,SCM Press Ltd.1962,p.42,p.221.
(25)[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5页,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6)Henri Lefebver,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405.
(27)(28)Henri Lefebver,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196,p.26.
(29)Henri Lefebver,The Urban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xix.
标签:理性与感性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