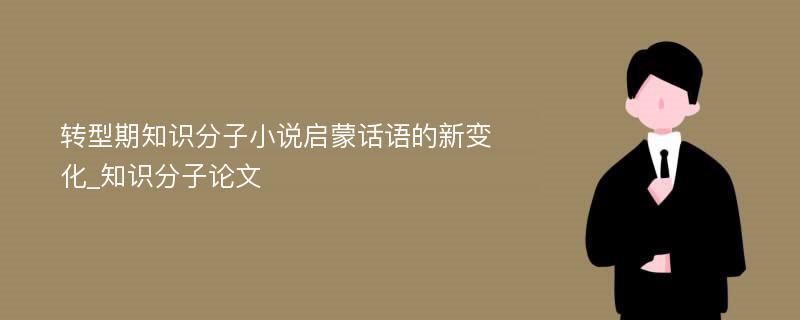
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中启蒙话语的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话语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5)04-0113-06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15.04.026 新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后期遭遇巨大挫折之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更是竞相质疑和抛弃启蒙立场,因此即使西方语境中的“启蒙的辩证法”前提条件——理性充分发达,主体性充分解放,从未在中国真正实现,[1]33否定和解构启蒙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也得到广泛传播。转型期启蒙思想遭到彻底质疑和解构,启蒙知识分子丧失了话语权威性和文化中心地位。虽然启蒙文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依然在批评学界不断得到重申和提倡,文学的启蒙功能依然受到重视,但这恰从相反角度说明文学创作中的启蒙精神实际上已经非常匮乏,众多作家已经抛弃和背离了启蒙立场。而坚持启蒙认同的作家也感受到了世俗身份的强大牵制和自我限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欲望话语取代启蒙话语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话语。综观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小说,主人公的欲望诉求几乎淹没了启蒙诉求,个人对物质、权力和性的欲望严重膨胀,知识分子密集呈现出对各种世俗欲望的强烈认同和执着追求。小说的启蒙话语已经衰退或隐匿,它从文体层面到文化精神都对“启蒙辩证法”作了体认和揭示。与此不同,宗璞、张炜等作家的小说主要书写了具有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求和抗争,为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曲赞歌。相对于对知识分子的嘲讽批判,这类作品的社会反响虽然远不及前者,但是作为文学格局中的一种抗衡力量,代表了对理想知识分子的深情守望,同样值得珍视。转型期不同代际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不同知识分子形象,为我们理解启蒙冷寂阶段的知识分子及其启蒙认同提供了精神图景。 一、右派启蒙身份的剥夺与隐退 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启蒙话语已经明显转变,新时期自觉认同启蒙身份的作家已经陷入对启蒙主体的质疑和失望之中。右派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曾经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得到尊重和礼遇,代表着刚刚恢复了启蒙身份的知识分子反思历史、追求理想的潮流。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古华、鲁彦周等小说中的右派多是忍辱负重、坚贞不屈、善良正直的光辉形象。然而,转型期右派形象已被“反右”运动的亲历者和非亲历者改写了。我们从转型期右派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即可窥见作家情感倾向和叙述姿态的变化,其中,启蒙话语随之延续或产生新变。 张贤亮小说中的“右派”对真理和自由的呼吁已经更迭为对幸福的渴求、对自我的寻找,右派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被他自己改写,小说的启蒙话语已被悄然重构。《习惯死亡》频繁变换的叙述视角,以及急切的近乎自恋和独白的倾诉语调,对他此前惯用的美化苦难、反思政治的叙事套路有所突破。由于故事的重心在展示右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殇,加上主人公与张贤亮身份和经历的许多重合之处,小说实际上成为对右派作家的精神剖析和人性写真,是张贤亮对自己创作及其精神历程的反思和突围。与《唯物论者启示录》相比,其重要突破在于,张贤亮传达出对主人公既批判又辩护的矛盾态度,嘲讽、抛弃了自己昔日迎合政治的笔法,书写了失去政治认同的右派知识分子无法确认幸福、实现自我的心灵悲剧,揭示了他无所皈依的身份尴尬和困惑。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以及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这两部小说重现了右派悲怆而荒谬的生与死,不再掩饰右派知识分子为求生而相互告密、背叛、折磨、迫害的种种劣迹,及其人性中的懦弱贪生、奴性依附、自私自保,毫无抵抗力和凝聚力等弱点。在极端环境中,右派不仅是可怜的受害者,也是可鄙、可恨又可悲的悲剧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类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从维熙和张贤亮对历史及人性的反思深度有较大拓展,实现了对旧作的解构和超越。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对新时期小说中右派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作了更大的颠覆,而且与1980年代右派作家的启蒙话语构成了对话和反诘的关系。如论者所说“它直接处理的是‘新时期’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生活”,对右派和知青两代作家“从现实中逃跑”和“游戏现实”都作了针砭和反思“不仅以其表现形态上的高度复杂化体现了时代的文学变迁,而且以其达到的意识层次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终结”[2]。王安忆延续着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反思路径,不过她没有认同作家“叔叔”的受难者和启蒙者的身份,而是打破了“叔叔”身上“理想主义者”的光环,揭开右派知识分子人性中自私自利以及缺乏理性反思的一面。该小说“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3]343。与自辩自恋色彩不同,王安忆以旁观者的冷静把右派知识分子书写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主体,不但失去了启蒙者的精神权威,而且不再让主人公得到精神慰藉和自我救赎。王安忆彻底否定了主人公获得真正的“新生”及其自救的可能性,突显出他在屈辱历史、现实生活和自我想象中身份认同的断裂和悖论。 右派知识分子的故事在“改写”中于1990年代初期基本定型,之后,创作主体囿于既定的政治身份或者当下意识形态的规训,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下去,叙述上也没有太大的突破。新世纪初,我们相继在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刘继明的《江河湖》等小说中,发现作家作为右派历史的“非亲历者”,讲述出来的右派故事都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情节聚焦在他们的饥饿、疾病、死亡、惩罚和相互残杀上。这批作品虽然在最初发表时也能得到几声喝彩,但却陷入了这样一个接受怪圈: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其讲述历史的真实性,越是纪实性的,引起的社会反响越大。但是,反思右派小说所存在的种种困境,叙述的陈旧掩饰不住作家想象力的匮乏以及思想力的虚弱。作家诚然没有过于急迫的政治使命感,不用在小说中虚饰表态,可政治规训的无形束缚已经让作家习惯于“自我审查”,对历史的反思被限制在既定的轨道和深度上,难以实现更为理想的审美突破。启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现代性,文学和启蒙之间的张力再次显现出来,无论是启蒙理性的残缺不全,还是如王蒙的《季节》和《青狐》中叙述者理性话语的过于膨胀,小说审美形态和启蒙话语之间的和谐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右派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改写和解构,似乎为这代人又增添了一重悲剧性。总体上看,他们的才华浪费在不断检讨忏悔和互相揭发批判中,轻信、怯弱、迂阔,对政治抱有幻想,未能摆脱精神基因中传统士者的依附人格,以至于在被剥夺了政治身份时,其启蒙身份也随之丧失。即使侥幸未成右派,身心同样在如履薄冰中扭曲萎缩。“世事漫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方方曾在《祖父在父亲心中》引用了李煜的这一句词,来强调父辈岁月蹉跎的悲凉和遗恨。方方还在《乌泥湖年谱》中让主人公多次吟诵讨论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诗词,表达他们归隐独善的心态。然而,在没有民主和法制的时代里,迷信、奴性、愚昧和疯狂就有存活的文化土壤。知识分子作为理性和良知的担当者应该率先垂范,在话语和实践中公开地追求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等),如果怯弱退却、不言不争,那么,关于历史和人性的荒诞派戏剧就不会谢幕。如前所述,刻画右派知识分子启蒙身份被剥夺或隐退之后的群像,讲述他们在政治高压、名利诱惑和欲望沉沦中的悲剧命运和精神痼疾,这是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坚持启蒙叙事的常规路径之一。另有一种是高扬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展现知识分子对理想人格和启蒙身份的追求和坚守。 二、启蒙身份的坚守和延续 与右派小说中创作主体的理想情怀越来越淡漠不同,宗璞、张炜、马瑞芳在小说中常常蕴含着对知识分子主人公的暖暖爱意,对坚守理想人格和启蒙追求的知识分子唱了许多颂歌。这是创作主体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把心中葆有的浪漫主义情愫,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化为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守望,在如今呈现出“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4]的文坛,体现出价值重建的思想意义。 宗璞的这种批评和守望姿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主人公美好精神世界的倾心塑造。《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自传性作品中,以隽永的语言和节制的情感着重描摹了知识分子精英在漂泊中对正义、良知、理想的坚守和追求。宗璞专注于刻画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尽伦尽职”和“爱国主义”情怀,但由于其主人公高洁伟岸的精神世界与今天有较大差距,宗璞的颂歌在文坛争相讽喻知识分子的潮流中是个异数,以致显得曲高和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拔高和自恋,缺乏对知识分子的理性反思。这显然误读了宗璞以老弱病残之躯至今笔耕不辍的真诚执著及良苦用心。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名利追求中日益世俗化、庸俗化,丧失了对正义、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而宗璞在失望和痛心中追忆、诉说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试图为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建输入理想精神,为民族品德的重建提供精神资源。质言之,宗璞小说文本内外都彰显出启蒙知识分子的“本色”,作家的启蒙身份与小说中的启蒙话语高度融合在一起。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需要不断地去抵抗投降、拒绝诱惑,在动摇、孤独和困惑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1990年代初期以降,张炜格外关注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不断探索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之路。多卷本《你在高原》的中心人物宁伽、《外省书》中的史珂、《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以及《刺猬歌》中的廖麦,无一例外都是在孤独、流浪中寻找身心安歇之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理想、诗意、质朴的生活充满向往,基本上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扩张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为人性恶的释放、道德的败坏、社会的不公感到厌恶和忧虑。张炜的小说常常洋溢着散文诗和流浪汉式的浪漫主义气息,对风光旖旎、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更是描绘得令人神往倾心,他用饱含激情和诗意的笔墨谱写了知识分子在世俗生活中坚守理想、屡败屡寻的自我救赎历程。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张炜在廖麦和宁伽身上,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目击与疾呼、呐喊与反抗、苦寻和游荡,投射了自己对田园乌托邦浓得化不开的爱恋与隐痛,寄托了他对知识分子能够洁身自好、坚守理想、自我启蒙诸多愿望。有学者认为,张炜“一度对贫穷、落后、愚昧充满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意味的批判热情”在世纪之交被对现代文明的愤怒淹没了,这标志着他小说中启蒙/道德精神的衰落。[1]376如今看来,启蒙既然包括对启蒙自身等一切权威的反思和质疑,那么张炜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人公对科技理性、工商业文明批判立场的坚持也是一种启蒙立场,而不是纯粹的道德立场。张炜对权贵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进程中种种丑行恶果的愤怒和批判,意味着对社会正义和价值理性的呼吁,突显的仍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也许我们应该超越启蒙/反启蒙、现代/反现代这些二元对立的模式去解读张炜的《你在高原》,其实作家诉说的一直是具有启蒙认同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对理想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寻找和守望。 马瑞芳在1990年代接连创作了描写高校教师的《天眼》和《感受四季》,撕下高校知识分子神秘而高尚的面纱,揭露了学界黑幕以及知识分子的虚伪、嫉妒、势利、卑劣等人格缺陷,对他们作了理性的剖析和审视。虽然“借助于知识分子精神沉沦的整体景象生动、立体地展现了整座‘象牙塔’崩毁的悲剧过程”,但是,“在马瑞芳的小说中对于人格和精神的执著与吁求却似乎仍然是其主题的最重要方面”[5]。这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中的“小丑”对面还矗立着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正面形象,如铁磊、诸葛白帆、葛菀葭和穆瑶等,是作者以欣赏和敬重的姿态着力塑造的知识分子“英雄谱系”。他们真诚、清高、爱岗敬业、正直磊落,以追求良知、正义、公平等为真善美,自觉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岗位以抵抗人世的庸俗势利,身上充溢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气息和人格魅力,呈现出马瑞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启蒙知识分子的心仪和吁求。同时,她还充分运用写实和寓言等手法对高校和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批评讽喻,对有才有德的人遭遇坎坷满怀同情,表现出作家冷静的理性意识与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众多高校题材小说中,马瑞芳作品中所具有的古典文学修养和诗性情怀让人印象深刻,如《感受四季》中铁磊退休返京之夜众人洒泪相送的情景,以及铁磊和诸葛白帆去世后的葬礼场面,为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谱写了颂挽之歌。对马瑞芳来讲,《感受四季》实际上完成了她在世纪末启蒙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的文化语境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守望。 宗璞和马瑞芳分别对民国和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的讴歌,张炜对童年和田园生活的频频回顾和寻找,这无疑蕴含着创作主体的理想精神和怀旧情结。怀旧主要产生在社会文化大转变时期,这种转变使个体感到自身的连续性受到断裂性的威胁。以此来看,这些作家对理想知识分子的怀恋和守望正是转型期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产物,正如张旭东说:“九十年代最为显著的潮流之一就是文化怀旧,它可以视为这种意识形态剧变的一个感伤的注脚。”[6]我认为,宗璞、马瑞芳、张炜的怀旧是一种“反思性怀旧”,试图运用知识分子在连续性上的心理资源,重建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在世纪之交繁盛的知识分子小说中,作家群体仿佛对“知识分子已死”达成了默契,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对知识界存在的问题作了触目惊心的揭示,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知识分子的种种恶德丑行,尽情地嘲讽、谴责了腐化堕落和精神迷失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这样一致“唱衰”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中,宗璞、张炜和马瑞芳小说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当然,其他作家也书写了知识分子主人公对正义、真理、公平和理想的追求,体现出对知识分子认同启蒙身份的信心,比如张承志《心灵史》中的叙述者“我”,王安忆《乌托邦诗篇》中的“这个人”,王小波《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以及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盛霖等形象,显然寄托了创作主体的理想和情怀。这些作家为坚守启蒙身份认同的知识分子所作的颂歌不但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而且还有为知识分子“招魂”、重建理想和价值体系的作用。 三、启蒙身份的溃败与困境 如前所说,文坛上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歌颂已经式微,相反,解构和批判之类的知识分子小说在数量和社会影响上却占据着极大的比重。作家们在这类小说中集体讲述了知识分子启蒙身份遭遇到的窘境和失败,揭示了启蒙在转型期面临的严峻问题。小说中曾经具有启蒙认同的知识分子或者纷纷在半推半就中脱去了启蒙衣衫,加入了追逐欲望的狂欢者队伍,或者变得茫然失措、心无所依,陷入了失去方向感和意义感的身份危机之中。1990年代以来,刘心武、方方、汤吉夫、张梅、贾平凹、格非、阎真、张者、阎连科等作家的小说,在表现当下知识分子启蒙身份遭遇挫败和困境方面颇有代表性。 刘心武于1992年发表的《风过耳》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率先为历史变迁中的当代知识分子描绘出一幅“群丑图”,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大都专注于个人得失,是一群庸俗势利、投机钻营、欺世盗名的无德无行之徒。令人尊敬或喜爱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在刘心武小说中的醒目“缺席”是耐人寻味的,他曾经热衷于讲述知识分子拯救他者的故事,至此转变为集中揭露知识分子自身的丑行恶德。刘心武说,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社会发展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的深渊,其恶的东西和难以言传的东西同样是非常深邃的”[7]。社会变迁导致了人们对知识分子启蒙地位的质疑,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对启蒙精神的怀疑和抛弃,刘心武所描摹的“群丑图”不但为知识分子启蒙形象解体的年代“立此存照”,而且充分流露出作家对曾经担当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的整体失望和无情嘲讽。 方方《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都讲述了知识分子在物质困窘中的尴尬和挣扎。值得注意的是,方方这几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虽然对经济贫困耿耿于怀,但是还没有完全认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如方方所说:“理想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是完满的,但又不能不向现实妥协。内心和外表处于分裂状态。”[8]与方方齐名的“新写实”作家池莉同样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存在,在《不谈爱情》、《你以为你是谁》等作品中,知识分子要么物质生活窘迫却自命清高,要么一厢情愿地进行精神宣导却无人倾听。知识分子陷入物质困窘和精神困惑中的类似故事,我们还可以在叶兆言的《挽歌》、《别人的爱情》中看到。 汤吉夫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悲剧境遇作了深刻的描写,呈现出他对当代启蒙者的同情和反思《龚公之死》中的龚公与《漩涡》中的靳先生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但在高校这个名利场中,他们却成为异类和失败者,最后龚公死去,靳先生走向了同流合污,成为转型期仍具有启蒙认同的知识分子的一幅缩影。《大学纪事》中的副校长盛霖、校办主任卢放飞、古典文学教授阿满,这些具有启蒙认同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排挤打击,他们的抗争如同在“铁屋子”中呐喊,只能引起众人的反感和厌恶而无助于事情的改变或者人心的好转。由于启蒙身份所坚持的价值理念与这个急功近利的世道格格不入,对人们已经适应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破坏和危险,因此它被怀疑、嘲弄和摒弃。与此相似,李锐在《银城故事》中书写了20世纪初启蒙者的革命斗争与民众日常生活的隔膜和冲突,以及启蒙者的动摇和困惑。继续坚守启蒙身份进行抗争世俗的,如同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自然被当作守旧落伍的愚者或多余人,迎接他们的是出局或者失败的共同命运。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曹征路《大学诗》中的主人公马同吾在抗争失败后挥刀自宫,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宣告启蒙身份的彻底“去势”。 刘心武、方方、汤吉夫、李锐、曹征路等书写了知识分子坚守启蒙身份的孤独、贫困和悲哀,揭示出启蒙主体抗争的悲壮性和无效性。与此有所不同,张梅、贾平凹、格非、李洱等主要书写了启蒙者失败之后的种种变化和困境。张梅在《破碎的激情》中以超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社会角色的转换。理想主义在1990年代销声匿迹,这让张梅流露出对激情年代的留恋,但是她在小说中不无嘲讽地揭示了当年启蒙理想的空疏和知识分子自恋自大、趋时逐新的人性弱点,思想启蒙者已经从梦游中醒来,殊途同归地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物质主义者,没有守住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反观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理想弱于实践,信仰变动不居没有形成独立而坚定的启蒙价值理念,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理想在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根本无法持久坚韧地为知识分子提供精神动力,内心的溃败、萎缩和颓唐是其必然的结局。 19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让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产生了裂变和分化,激情不再、精神分裂、颓废虚无等症状表明“新启蒙运动”失败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正在承受精神无所皈依的孤独和痛苦。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为写不出东西而焦躁烦闷,企图通过征用性资源来寻找灵感和安慰,摆脱话语权失落之后的身份危机。庄之蝶在诗酒酬唱、寻香猎艳、结交达官、访僧问人等许多具有古典气息的活动中,都不能确认自己“作家”身份的价值,无法证明自己生存的意义,终于在孤独和虚无中走向死亡。庄之蝶身上突显出具有传统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溃败和死亡,他亦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产物。贾平凹的《高老庄》可以看作是《废都》的续篇,小说中子路返乡寻找精神皈依以失败告终,再次证明失去启蒙认同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失魂落魄、无枝可依的精神窘境。 知识分子的溃败和困境,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讲述了这个令他感受尤深的问题。主人公曾山试图运用哲学理性确证自我摆脱生存困境,并为现实世界建立价值秩序,却为此感到沮丧和绝望。格非点破了理性的虚弱和不可靠性。我们看到,当理性和智慧受到他者和自我的双重否定之后,从事哲学追求真理的人在欲望和理智之间动摇妥协,感到思想的贫困与存在意义的匮乏。理性的力量失去,启蒙的认同已经在内心瓦解,精神分裂、灵肉分离正在成为内心仍旧残存启蒙精神位置的知识分子的集体镜像。实际上,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理想崩溃和信仰荒凉。哲学不能救治知识分子,诗歌同样败北。张者《桃李》中的邵景文、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以及北村《玻璃》中的李文,都曾把诗歌当作精神依靠,后来遇到无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震荡之后弃诗、焚诗,另寻出路,对启蒙精神的抛弃成为他们改变身份的首要前提。与此相似,徐坤《游行》中的黑戊、李洱《午后的诗学》和《饶舌的哑巴》中的主人公都是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却在脱口秀式的表演中迷失了方向,崩溃的启蒙身份再也掩盖不住补救不了其灵魂的苍白和碎裂。 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对知识分子启蒙身份的溃败和困境作了形象的揭示,他们已经从物质困窘转变为精神分裂,在自我和他者的双重否定中,在无边欲望的包围中,知识分子拥有的启蒙身份被不断地修正和摒弃。精英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形成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记忆和想象,对科学、理性、正义、自由等启蒙价值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物质、权力、金钱和异性的追逐,其启蒙认同随着激情的退却和理想的匮乏而动摇直至分崩离析。小说中那些不能调适自己身份认同的知识分子,走入了无所适从、茫然失措的精神处境中,迎接他们的是出局、死亡和疯癫等悲剧性结局。更为普遍的是,知识分子背离了1980年代的启蒙身份,在物质化和欲望化的世界中以世俗身份随波逐流。作家在审视、批判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实现着对启蒙以及启蒙主体的反思,这已成为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启蒙话语的主要形态。 四、作家的启蒙认同、启蒙话语之新与旧 启蒙话语是新文学近乎神圣的主流话语,在“五四”和新时期兴起的两次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圭臬,启蒙主体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晚清至“五四”时期,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的“新民”、“立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等思想,莫不认为文学具有教育民众、革新精神、改造社会的功用。新文学自一开始就与启蒙思想紧密关联,它是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物,也是启蒙思想的载体。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西方现代思想都在新文学中得以传达和提倡,其中人道主义和以实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启蒙文学中的精髓部分。新文学成为启蒙思想的文化实践,启蒙成为新文学的主要传统。 启蒙文学在传输启蒙理念时通过揭示民众精神疾苦,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描述社会黑暗腐朽的过程中,确立了知识分子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以及启蒙本身的合法性。“现代”与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所讲述的启蒙者的失败、孤独和堕落,体现了作家对启蒙者以及启蒙效果的反思,但这并没有质疑启蒙自身的合法性,因为讲述启蒙遭遇的尴尬和障碍反而论证了自我启蒙和继续启蒙的必要性,可以视为作家唤醒民众、启迪读者的一种策略。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阐释,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小说把启蒙者塑造成了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作家所坚持的启蒙立场影响和引导了读者的阅读效果,更重要的是,其时启蒙话语是文学创作的主导性话语,启蒙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在文学知识分子心中并未发生根本动摇。 1980年代“伤痕”、“反思”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纷纷操持科学、民主和人道主义等现代启蒙话语”展开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政治”的批判,并在这些批判之中,“实现着自己的启蒙认同,初步建构了启蒙者的身份形象”[9]113。启蒙话语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然而,到了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1990年代,坚持还是告别启蒙已经成了一个争鸣问题。[10]转型期的文学知识分子与1980年代相比,已经由启蒙者变为边缘者,在大众面前失去了话语威信,不但不是受人瞩目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文化英雄,而且在大众文化崛起时成为精神上的孤独者和失败者。例如,张承志、张炜、格非等作家在世俗意义上是功成名就的,但无不感慨孤独和失败。格非甚至认为他自己代表失败者,反复说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11]究其原因,一方面,1980年代作家们操持的现代启蒙话语俨然过时和失效,由于旧的启蒙话语对人的尊严、主体性的强调缺乏对人性复杂的辩证认识,因而启蒙者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异化,丧失了解释的能力和底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专制、奴性作为批判对象已经被社会淡忘和搁置,大众已经不再有耐心阅读和聆听,理想和信仰、道德和责任遭到嘲笑和颠覆,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挣钱运动”。作家们的启蒙地位岌岌可危,与启蒙传统赖以共生的知识分子身份在质疑和自嘲中逐步瓦解。 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中的种种启蒙话语与作家的启蒙认同以及启蒙语境密切相关。总体来说,作家的启蒙能量和启蒙热情都已经大大衰退,然而,启蒙传统还是在守持和变异中得以存活,质疑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主义,揭示、批判人性和自由的异化等,成为一些作家新的启蒙理路。与1980年代作家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批判来实现启蒙不同,转型期作家的政治激情已经消失殆尽,他们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张承志、张炜等作家高扬道德、理想的旗帜,以浓烈的批判激情不无悲壮地固守着作家的启蒙身份。但是,他们的启蒙方式和启蒙话语都与1980年代有所不同。1980年代作家操持的科学、理性、民主和自由等现代启蒙话语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已经让位,启蒙反思、公正、平等、和谐、节制成为新的启蒙话语的核心部分;作家已经不再通过非文学的方式来干预社会、启蒙大众。转型期的作家依然珍藏着19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辉煌的历史记忆,更难以忘记中国革命对平等和公正的允诺和追求。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阶层分化和固化、生态失衡、伦理失范和精神危机等问题,作家们主动肩负起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在言谈和作品中揭露了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困境,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化发展的失望、忧虑、愤怒和批判,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践行了启蒙认同。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张炜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人性论文; 马瑞芳论文; 作家论文; 右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