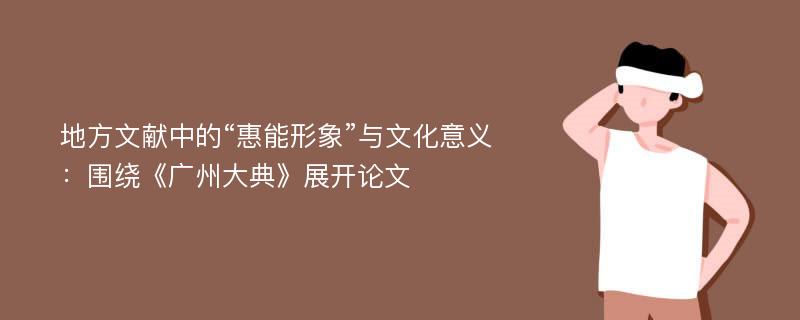
地方文献中的“惠能形象”与文化意义:围绕《广州大典》展开*
谭苑芳 林 玮
[摘 要] “惠能形象”在禅宗史上具有科学主义和民间信仰的双重性张力。这种张力可以在地方文献中加以反思和确证。《广州大典》是典型的地方文献,其中的“惠能形象”可以从思想史和信仰史两个层面展开讨论。思想史的“惠能形象”又可以分为趋向主流与趋向民间两个层面,而信仰史的“惠能形象”则可分为精神性和物质性两个层面。《广州大典》中的“惠能形象”带有突出的生活美学特征与张力。
[关键词] 惠能形象 广州大典 地方文献 民间信仰 生活美学
无论从严格的史学意义,还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惠能形象”都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话题。前者自顾颉刚、胡适等疑古学派开始,就在史学领域对惠能形成了某种负面的刻板印象;① 参见白光、洪修平:《大陆地区慧能与〈坛经〉研究述评》,《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 而这种印象(或称“形象”)在岭南文化的民间信仰中,是不被认可的。② 相关现象在本文将要展开的广东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而其当代表现可参见区锦联:《慧能信仰与地域祭祀共同体建构的人类学考察——广东新兴县“六祖轮斋”的个案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因此,至少在胡适所认定的文献支撑层面与民间信仰的人文想象层面,“惠能形象”存在着明显的二重性问题。③ 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带有典型的科学主义倾向,其史料要求便是“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参见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二重性问题无法通过学术的反思得到解决。一方面,禅宗文献的信史部分确实有所不足;而另一方面,与六祖相关的民间信仰实践也不会因为学者的研究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科学主义与人文想象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恰是推动人类文化演进的重要力量。但是,从“惠能形象”的上述矛盾中,却可以启发出一个新的问题意识,即在某一限定语境中的“惠能形象”究竟如何。这一限定可以是某个历史断代,也可以是某个相对明晰的地域。只有从不同限定语境中挖掘出富有新意的“惠能形象”,才能使学界和社会对六祖的认知得到更新。这既可以让传承至今的习俗有所依据,也可以为讨论由胡适开出的“信史中的惠能形象”这一话题提供一些新材料。
在埃里斯塔的郊区耸立着一座1996年为纪念1943—1957年卡尔梅克族被举族流放西伯利亚而建的被巨型纪念碑。熟悉卡尔梅克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纪念发生在二战期间对卡尔梅克人一次极不公正的、可以称之为政治迫害事件。
一、《广州大典》与“惠能形象”源流
《广州大典》于2005年开始组织编撰,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为基础、海内外公藏机构和个人藏书为补充,至2015年完成出版工作。这套丛书珍本众多,其文献上溯秦汉,下至1922年,个别门类文献适当延至民国,较为完整而系统地反映了广州的变迁和发展。而这恰为综罗历史上与六祖相关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契机,也为重新考察“惠能形象”提供了可能。
六祖在广东传法长达37年,广州地方文献对他及其弟子的传教创教活动,以及其后广州地区对六祖的相关事迹、遗址,多有记载。这些资料分散各处,有的还残缺不全,但对于禅宗及惠能形象的研究来说,却是直观而可靠的文献史料。经检索,《广州大典》收录文献中与惠能直接相关者多达46条,具体来说,包括经部2条(总类、群经总义类各1条),史部33条(纪事本末类1条、地理类6条、专志1条、方志类25条),子部7条(释家类5条、儒家类1条、杂家类1条),集部3条(总集1条,别集类2条),从部1条。这些史料已经能够显现出“惠能形象”的一些侧面,丰富了学界对六祖的已有认识,尤其是六祖在民间信仰中的特殊性,可以较好地回应本文开篇提出的二重性问题。
肉鸡生长过程中常见的病害都是通过病毒、细菌、真菌等病原体进行繁殖和传播,这些病原体大多喜欢温度和湿度较高的环境,若养殖场中保持高温、高湿度、通风不畅,病原体会大量滋生,对肉鸡进行传播,导致肉鸡患病;且肉鸡养殖场内的肉鸡数量多以万计数,每天排泄出的粪便重量上吨,若不能及时清理和消毒,粪便中存在的病菌也容易在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中大面积繁殖,对周围肉鸡进行传染,或污染饲料,导致肉鸡患病。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与六祖自身身世直接相关的史料不足,其主要依据者仍为《坛经》,所以《广州大典》中收录“惠能形象”的一手资料(即“源”者)有限。基于地方史料的收集原则,《广州大典》收录了《坛经》两个最为通行的本子,即唐敦煌写本和明成化四年刻本,分别署名“唐释惠能撰”和“唐释法海等辑,元释宗宝编,明释真一纂”,均收入在“子部释家类(第52辑)”(第1册,总第409册)之中。《坛经》流传较广,这两个本子也最为常见,故于“惠能形象”的“源”来说,《广州大典》可增补者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六祖行踪部分。如史部总目第10方志类收录的《康熙三水县志》卷4记载,“旧华岩寺,大潭册麓,六祖惠能尝住锡”;卷14又载,“亦尝在西南和光寺”等。① [清]郑玟:《康熙三水县志》,清康熙五十年刻本,《广州大典·方志类》,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59、360页。 而于《广州大典》中所见多为丰富者,乃是“惠能形象”之“流”,即后世关于六祖及南禅的各种评价、认知,以及传说、史迹等,这是本文所试图讨论的主要对象。
三是禅宗趋下。这是中国传统儒家主流意识反对佛教思想的地方呈现。反对佛教流行,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其下沉于地方文献之中,则可以《广州大典》收录的若干文字为例。《广州大典》对禅宗“惠能形象”的解构,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罪状论”,这是自韩愈《论佛骨表》以来的常见手法,颇有耸人听闻之效。如《万历广东通志》序中就说:“达磨驻广,以楞伽印心,卢能居韶,以坛经传法,非无言语文字也。宋人黄安石、苏辙辈靡然归之,喜其顿悟超脱自见本性,出乎六籍之外,吾人染焉,自是尧舜周孔之道,驯而不纯矣。其流至于束书不观,浮谈无根,政治弗疆,祸且逮国。厓山之败,盖可睹也。元品南人真儒于娼丐之间,而尊西僧为帝师,演媟慆淫典礼尽灭。”② [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46-47页。
当然,论及“惠能形象”之“流”,《广州大典》中亦有偏重科学主义范式者,如其史部总目第10方志类收录《嘉靖广东通志初稿》第36卷中提出,禅宗“自六祖分为二派,曰青原思,曰南岳让”,进而生五门,“而临济派为最盛”。在广东,“其相住云门者,曰宝、曰照、曰爽,皆有名于韶,为得法眼者云。”③ [明]戴璟、张岳:《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明嘉靖刻本,《广州大典·方志类》,第1171页。 这种对“惠能形象”之“流”的论述多载于灯史等禅宗文献,在《广州大典》中者虽有裨补之效,但并不多见,也不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
二、《广州大典》中的“惠能”:形象分层与主流思想史意义
“惠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这不仅表现在史料与信仰之间存在的二重性上,而且深刻地表现在不同群体对六祖认识的立场差异上。地方文献是一个庞杂的汇编集合,《广州大典》虽有经、史、子、集、丛的区分,但其囊括史料的时间跨度大、作者多,相互之间也必然有群体的不同。这直观表现在部分史、集部汇编多收入地方文人的方志、艺文,而子、丛部汇编则又多见上流士大夫的笔记、著述。两部分文献的作者虽都属文人群体,但其阶层高下却很明显,而在对“惠能形象”的书写中,这两个群体的立场、表述差异也比较突出:前者更多来源于民间,将六祖个人予以神话的倾向比较突出;而后者虽然也尊重六祖在禅宗谱系与宗教“神谱”中的地位,但更倾向于将六祖思想作为一种独立讨论的对象,而非仅将其视为“佛”或“祖”。因此,在对《广州大典》中的“惠能形象”进行大而化之的讨论中,有必要对其进行分层。可以把六祖思想作为讨论对象的,是趋于抽象、归纳的思想史形象;而将其个人身世、神迹作为著述内容的,则是趋于具象、演绎的信仰史形象,这样大致可绘出“惠能形象”上下层面交叉、勾连的复杂状况,从而便于对文献进行归纳、分析。
30%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情况下SVM分类器对测试集的识别准确性分析,表5展示的是以80%:20%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情况下SVM分类器对测试集的识别准确性分析。
一是儒禅会通。这是一个思想史的老题目,在《广州大典》所收录的若干理学家文献和方志中的士大夫碑刻中有所显现。其典型者,如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收录《广州大典》经部总目的群经总义类)第9卷就记载苏辙的话,“六祖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盖中也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名也”,而陈澧加案语说:“此自古以来所未有”,并对苏季明答程颐的相关思想史上的著名论述加以分析,其重视可见一斑。①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清光绪刻本,《广州大典·群经总义》,第156-158页。
经过反复优化,最终确定以报废磅台为基础,焊接6寸钢管为立柱,其上安设10m皮带架,最上面安装滚筒。通过机电维修车间近十天的焊接,滚筒筛装置最终在车间厂房内预制成型。然后整体转运至煤场进行安装调试。
不过,这种纯粹的禅宗与儒家思想比较、辨析在《广州大典》中也不常见。部分儒者论及六祖,或仅列举其行迹做比照。如湛若水在《复王端溪书》(收录集部总目第一别集类明代之属《湛甘泉先生文集》第7卷)中就叹曰:“每忧我之不能归而归之不能,速是相爱无己也,浮屠异教也。六祖将殁,其徒皆泣。六祖曰:‘尔辈忧我去不知路耶’。是诸贤忧我不知路也。何相知之浅耶?”②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清康熙二十黄楷刻本,《广州大典·子部·第一别集》,第124-125页。 或仅以一般敬仰者语气论及,而不涉思想史意义,如蔡沈游曹溪六祖寺,写下“智药曾过此溪,源掬水香……六代长千年。法珠在持,得照迷方”等话。③ [宋]区仕衡:《九峰先生集》,清道光二十年伍氏诗雪轩刻粤十三家集本,《广州大典·子部·第一别集》,第31页。
而《广州大典》中以主流意识对“惠能形象”予以认定的,当是收入史部总目第10方志类《万历广东通志》第67卷的《柳宗元碑记》和同为第10方志类的《乾隆番禺县志》方外篇。前者将六祖放置在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逻辑中予以反思,提出了六祖的底层倾向是其获得历史认可的重要原因这一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六传至大鉴,始以劳苦服役,听其言言,希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④ [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933页。 碑刻本是面向社会大众进行宣教的工具,因此不同于一般士大夫文集的写作。而如果说柳宗元的上述说法仍不脱士大夫的主流意识背景的话,方志中对“惠能形象”的论述就更带有从儒禅会通的主流意识趋向民俗教化的意识了。
此规则下的密码可以不是一条连续的折线,可以是多条线段或折线。本文设计的限制规则如下:折线或线段至少经过两个点,所有线经过的点均不能重复,且必须经过所有背景图形的点。图6中左图由于一个点未被经过,故为不合法情况。图6中中图由于一个点被经过了两次,故为不合法情况。图6中右图为合法情况。
《乾隆番禺县志》方外篇首先突出广东的地理意义,提出“翻故苑遂为粤刹,所剏始五代时,求那罗跋陀与智药三藏、达摩初祖、波罗末佗接踵继至。笔授之经,南中渐多,而梵字亦渐崇矣。初达摩自西而来,始于粤,由是而金陵,而嵩少,终返葱岭之西。今释家所谓一祖也。至惠能得法一祖衣钵,仍归粤中,所谓以此始者,亦以此终乎。”这种认定岭南佛教地理意义的记载虽无奇殊,但其故意营造由巧合而必然之论,是符合方志作者地方文人意识的。而其后还从“梵教沿今,视道纪为胜者,殆以累世崇奉之”,以及“托而外者,多依以自隐,其中不无忠孝廉节之士”等说法,⑤ [清]任果、檀萃:《乾隆番禺县志》,清内府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132、1133页。 把“惠能形象”士大夫化,使佛教(禅宗)与儒家在社会意识上基本实现无差。这种将思想层面的两宗对话,寻其相通之处的学术研究转化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社会认识,是需要相当智慧的,也是以《广州大典》为代表的地方文献中的“惠能形象”这一话题最值得讨论之处。
尾水渠开挖设计总量649万m3(自然方),2016年汛前已完成尾水渠有效开挖50万方,剩余599万m3。由于现场钻孔勘察尚未完成,土石比暂按主合同尾水渠土石比计算1:5考虑,石方为499.17万方。
二是儒禅有别。这其实是思想史常识。如《广州大典》史部总目第九地理类中杂志之属收录的《广东新语》第19卷中提到“六祖发塔”时说,“佛以肤发为垢浊,委而去之,顾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见而瞻礼”,这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未敢损伤,孝之始也”的观点大不相同。而由于地方文献主要由儒家知识分子充当把关人,这种“儒禅有别”的论述往往就会被其转述为禅宗自相矛盾的思想辨析入手处。如“佛以肤发为垢浊”之论,屈大均随后添加:“是犹有我相在也,失其旨矣”,三言两语就实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清康熙水天阁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九地理》,第533页。
事实上,即使胡适本人基于所谓“信史”而展开涉及六祖的禅宗史研究,其结论也不过是“惠能形象”之“流”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于地方文献中寻找六祖研究的思路,是“科学化的历史”范式向心态(mentalite)史范式转型的一种表征。在这种表征之中,历史甚至可以是计量式的科学,而不再是客观的。在这种表征中,叙事及“人们脑中的各种念头和想法”显得尤为重要。② [美]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古伟瀛译,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综上所述,当前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健康意识的强化,开始以健康体检的方式及时了解自身身体状态,而采血是体检中的主要项目,但是采血期间皮下血肿问题明显,影响体检人员情绪、身体情况。通过综合护理干预可以帮助体检采血人员提高采血认知,更好的配合采血工作,降低皮下血肿形成率,并提高体检人员的护理满意度,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三、《广州大典》中的“惠能”:思想史形象的民间层面
思想史本身除了精英的主流意识之外,还需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而其“首先要做的也许是重新检讨传统的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范围”。④ 葛兆光:《思想的世界: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地方文献是讨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要材料。在《广州大典》中,六祖的思想史形象同样也有趋于民间信仰的层面。这一层面虽然就“思想”本身的精妙而言,或许无足轻重,但却构成了讨论“惠能形象”第二层的基础。纯粹物质的信仰世界,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法脉”作为支撑。
《广州大典》中对“惠能形象”在思想层面的民间性讨论,同样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者是续佛法脉。这一层面的论述即是援引历代祖师对六祖理论的阐释,如《万历广东通志》第66卷中收录了惠越、智隍、方辩、晓了、石头、聪公等和尚对六祖思想的阐述,《光孝寺志》中也有天然等和尚的相关语录。总的来说,这类“惠能形象”的延续在《广州大典》中不多见,也常是灯史照录而已。⑤ 清《光孝寺志》的“凡例”中即言:“语录乃佛氏之微言奥义,各山志内有载有不载,以其另有专书故也。然光孝自六祖后,继起寥寥,今兹所存,本亦无多,吉光片羽,犹见一斑,故为补入。”可参见《广州大典》史部总目专志之属收录的《光孝寺志》12卷。 但值得一提的有两条史料,一是《康熙新会县志》第16卷中关于荷泽神会的部分记载,为考察神会行踪提供了线索:“子年十三即参六祖,师问还将得本来否?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生。及师欲离世间,众悉涕泣,神会不动,师曰:神会小师却得。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尝过慧龙山,奇其山水,结庐于此。”⑥ [清]薛起蛟:《康熙新会县志》,清康煕二十九年刻本,《广州大典·第十方志》,第741-742页。 二是刘禹锡的《佛衣铭》,收录《万历广东通志》第67卷。
首先,绩效评价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想要保证各个阶段的经营任务都可以保质保量的完成,就必须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现状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动向来稳固经营理念,在逐步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同时发现自身问题和不足,逐一加以改正。绩效评价的过程是寻找差距的过程,既是对前面工作的总结,也是对后续工作的展望,有利于企业各部门和个人明确下一步的目标和方向。
而另一种则是“以内化论”,就是用禅宗自身流变,引出其思想的荒谬性。而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层次。常见者,举佛教自身例证而论,如收入《广州大典》经部总目总类《皇清经解》的《揅经室集》1集第9卷就把中国佛教演化史看作是印度佛教的等而下之。“至于梁达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兴禅宗,则是西域人来中土,不耐经卷,不如全扫一切,更为直捷。此又远不及慧远翻经之时,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达磨入中土,言语难通,亦慧能等傅会而成也。”③ [清]阮元:《揅经室集》,《皇清经解》第6册,《广州大典·经部总目总类》,第220-221页。 这些说法,多就现象而论,虽然也有一定说服力,但对“惠能形象”的负面效果并不彰显,言辞中还隐隐透出遗憾。
国外巨型被补偿水电站分别指的是加拿大的拉格朗徳Ⅱ级水电站、巴西与巴拉圭共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和美国大古力水电站。其径流调节特性参数见表1。这3座水电站除大古力扩建工程是采取按保证出力作调峰水电站设计外,其余两座均按轻流式水电站设计。3座水电站均规划为分期建设,其中大古力水电站二期扩建工程至今已近30 a尚未付诸实施。
二是禅道会通。“佛老并称”自佛经汉译以来,就是一种极有生命力的思想论述,其在宋代的直观表现是尊道抑佛:“寺院已改为宫观,诸陵佛寺改为明真宫……初祖达摩封元一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经文合改佛称金仙,菩萨称仙人,罗汉称无漏,金刚称力士,僧伽称修善。”① [宋]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127卷,清抄本,《广州大典·史部·第三纪事本末类》,第2005-2006页。 而在《广州大典》所记载的民间,这一官方行为已演化为传说显现。在史部总目第十方志类收录的《乾隆番禺县志》方外篇中,有取材于《杜阳杂编》的“卢眉娘”故事。② [清]任果、檀萃:《乾隆番禺县志》方外篇,清内府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152页。 比之原书,收录于地方文献中的这个故事多了一处细节,即交代了卢眉娘的身世,乃“北祖帝师之裔”,并随后给出按语,表示其即六祖惠能之后裔。这显然是以其同姓而进行的附会演绎。而这种演绎恰说明禅宗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密切。直至清代郑观应写《盛世危言新编》(收入《广州大典》子部总目第一儒家类礼教之属),仍脱离不开“仙佛同源”的说辞。郑观应认为,“佛法详言性而略言命,然《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则已微露其端;道经详言命而略言性,然《关尹子》及《清净经》《心印经》《悟真外编》亦颇略阐其妙”。③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第14卷,清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广州大典·子部·第一儒家》,第586页。
三是禅趋于俗。在《广州大典》中,把“惠能形象”用俗化比拟的方式呈现的,莫过于对宾公佛的描述。宾公佛是增城特有的地方信仰,迄今在博罗、从化、南海、番禺、东莞、广州等地仍多有流传。宾公以放牛娃身份,显种种神迹,基本是地方性民间信仰的表达;况且宾公16岁即坐化,并无任何与禅宗思想相关的论述传世。但在《广州大典》的部分文献中,宾公与“惠能形象”关系密切,许多地方文人都以六祖比拟宾公,如《康熙增城县志》第14卷中有沈受祉的《万寿寺菩提树记》一文,即说:“宾公即无殊六祖,六祖究无殊我佛矣”。这是将“惠能形象”通俗化的典型,亦可视为一种表征。
就其思想史形象来说,《广州大典》中的“六祖”同样可以分为趋向主流(儒家知识分子)与趋向信仰(民间)两个层面。第一层以与儒家主流意识的亲疏关系可分为儒禅会通论、儒禅有别论和禅宗趋下论三个层面,以下分而论之。
还值得注意,《广州大典》中对宾公佛的描述带有儒化色彩。宋代虽然佛道流行,但民间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家。因此,地方文人对宾公的认识自然也无法脱离儒教思想。如《康熙增城县志》中说,“湛元明曰:惠能逢仲尼,吾国有颜子。余谓:宾佛亦然。”这就是把宾公比作颜子的例证。此外,《广州大典》中还有几处描写地方神迹传说的细节,明确提到了六祖。如《康熙新会县志》第9卷、第16卷都提到行宣和尚从六祖故宅到吴村月华寺发现海怪飞龙,后坐化而成肉身菩萨。其中,第9卷还特意将行宣与六祖、神会进行比照,认为其“同得佛祖之妙道”,并赞誉行宣是“知尊吾儒之道者”,④ [清]薛起蛟:《康熙新会县志》第16卷,清康煕二十九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428页。 都可与《广州大典》中宾公的故事相比照。
《佛衣铭》“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是对六祖思想的形象辨析。虽然作者是儒家士大夫,但其论者却与前引《柳宗元碑记》类似,都是出于对民众认知立场的引导,才提出“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同。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等论述。⑦ [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广州大典·第十方志》,第2934页。 且“铭”这一文体朗朗上口,易于传播,非常有助于民间从脱离物质层面信仰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惠能形象”。但是,诚如清《光孝寺志》的“凡例”所言,“光孝自六祖后,继起寥寥”,后世广州于禅宗和儒家都缺乏足够数量的重要人物以启民智,这造成了“惠能形象”的等而下之,其愈发与道教以及同道教关系密切的民间信仰相联系,日益彰显其民间性。
四、《广州大典》中的“惠能”:信仰史形象的分层
在《广州大典》中,“惠能形象”的信仰史意义也大体可以分为两层。一是精神性的信仰,也就是通过种种非物质性的神话、传说,来赋予六祖超自然的“神迹”,使其具有被信仰、被祷告的可能。事实上,早在六祖在世时,已极有威名。“天下知有禅者,必来参能,以至禅人肩踵相摩,佛法盛行于广。”⑤ [清]郑藀、桂坫:《宣统南海县志》第12卷,清宣统二年刊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549-550页。 因此,在其入灭之后而被加以神化,也在情理之中。而六祖的这种神通形象还可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对六祖本生故事的神化,如《万历广东通志》第66卷记载,“唐惠能姓卢,初范阳人,父行韬,武德三年,左官新州,母李氏感异梦,怀妊六年,生能时,有二僧来谒,因定名惠能,言惠众生能佛事也。”⑥ [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第66卷,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898页。 这显然是后编的传说,尤其对“惠能”法号的解释极为牵强,但其却显现出民间对六祖神通的充分信赖和充满善意的想象。而晚出的《道光南海县志》,还依据《坛经》“添油加醋”,说其“孕六年乃生,生时不饮母乳,神人灌以甘露。”⑦ [清]潘尚楫、邓士宪:《道光南海县志》第42卷,清同治八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445页。
其次是对六祖神通现象的描述。由于缺乏信史支撑,这种描述只能发生在其成为信仰对象之后。如《光绪香山县志》第9卷载平山村飞来寺六祖金身曾“三迁而后飞至”,“附近有旱患凶饥必现神火”① [清]陈澧:《光绪香山县志》第9卷,清光绪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331页。 等神迹,都颇合民间信仰需求。
最后是对六祖神通的想象,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常见的“托梦”一说。这也是《广州大典》中“惠能形象”神通属性的重要意涵。《万历广东通志》载:“聪公者,新州人,姓谭,南汉时,往南叶参礼六祖,遂为沙弥,持戒律甚肃。忽一日,梦祖师曰:‘今夜午吾当有难,惟汝能救。’其夜火焚塔殿,乃祖师圆寂处。寺僧弗动,惟聪升出山门,众大惊异。尝欲航海往普陀落伽山,复夜梦祖师云:‘我昔有难,荷汝护持,汝今南行’当为汝说:‘逢东则住,逢林则止’。”② [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第66卷,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912-2913页。 与前文所述宾公、宣公类似,这一传说也把“惠能形象”投射在聪公身上,尤其“逢东则住,逢林则止”一说显然出自《坛经》。但有意思的是,此处传说中六祖亲自“现身”,以“托梦”的“惠能形象”对聪公加以引导。《广州大典》中方志多有“仙释”并称,“记述纯阳了悟于点金,惠能僡灯于米熟,岂不彰明显着哉”。③ [清]黄培彝、严而舒:《康熙顺德县志》第9卷,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613页。 这是“惠能形象”在民间信仰史中的精神层。
“惠能形象”民间信仰的第二层意义在于其物质层,即以物质性的遗存作为形象的显现。信仰本是精神层面的“思之事”,但其运行却多需要借助具体的物质基础(如庙宇、遗迹、文物等)而展开,这在民间信仰中尤其明显。作为六祖祖庭的光孝寺史料在《广州大典》中收录极多,韶州六祖寺也有收录史部总目第九地理类杂志之属的王临亨《粤剑编》“余闻六祖曹溪剎宇甚盛,余驻韶一月,而以病困,不能一往,念之怃然”一语提及;《道光南海县志》第30卷中《修复戒坛碑记》一文还记载了“是戒坛以六祖,而重六祖”,以及“悠然而兴,倏然废,而又兴”的整个过程。④ [清]潘尚楫、邓士宪:《道光南海县志》第30卷,清同治八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060-1062页。 凡此种种,都足见“惠能形象”在正统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具有扭转苏轼“岭南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见《粤剑编》)名言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的民间田野中自然生发出“仙释同源”式的六祖信仰,这是“惠能形象”在民间物质文化层面的重要表征。
如《道光新宁县志》第8卷载东郊观音堂“中为大士像,左伽蓝右地藏,东建六祖堂,西为禅室”;⑤ [清]张深、温训:《道光新宁县志》第8卷,清道光十九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63页。 《咸丰顺德县志》第16卷载三丈庙“并祀六祖、后、华光”;⑥ [清]郭汝诚、冯奉初:《咸丰顺德县志》第16卷,清咸丰刊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772页。 第15卷载锦岩三庙“北帝、泰山之神、六祖、普庵诸菩萨分列于左右”⑦ [民国]周之贞、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第3卷,民国十八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385-386页。 等类,在《广州大典》中极多。而六祖经行场所都有建庙,《康熙广东舆图》第4卷就载“六祖卢惠能传黄梅衣钵后,于此(象岭)建寺”;第7卷载“昔六祖尝隐此山(扶卢山),上有六祖庵”⑧ [清]蒋伊、韩作栋:《康熙广东舆图》,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58、330、337页。 等,都说明“惠能形象”在民间信仰中具有重要的神祇(地方神)意义。
正因为此,各地以“六祖”命名的寺院庙宇也为数众多,且有神迹。如康熙、咸丰年间两部《顺德县志》均记载有德钦和尚肉身“不臭不腐,其徒将其真身安坐奉祀六祖殿中”;⑨ [清]黄培彝、严而舒:《康熙顺德县志》第9卷,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613-614页;[清]郭汝诚、冯奉初:《咸丰顺德县志》第30卷,清咸丰刊本,第1353页。 《康熙新会县志》载,“大云山在城西里许有龙兴寺,建自隋唐,又有文昌宫、天妃宫、六祖堂”;⑩ [清]薛起蛟:《康熙新会县志》第5卷,清康煕二十九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78页。 《道光新宁县志》载,“六祖庙在海晏横冈村”① [清]张深、温训:《道光新宁县志》第8卷,清道光十九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24页。 等等。这些庙宇的神迹显现,如有前引《光绪香山县志》第9卷载平山村飞来寺六祖金身“飞迁”。② [清]陈澧:《光绪香山县志》第4卷,清光绪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63页。 在正统佛教中被目之为“外道”的抽签,在《广州大典》的“惠能形象”中也有所显现。《道光南海县志》第44卷指出,在抽“六祖签”时,“傍塑灵通使者,必先拜告,而后敢祈。光孝寺前有辩签人。”③ [清]潘尚楫、邓士宪:《道光南海县志》第44卷,清同治八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1513页。 此类种种,生活气息极浓郁。
此外,以“六祖”命名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在《广州大典》中记载也极多,如“六祖泉”(《万历广东通志》第27卷)、“六祖井”(《万历广东通志》第67卷)、“六祖偃息石”(《广东文选》载《西岩石室记》)、六祖洗钵处(《道光南海县志》第7卷)等。④ 这些古迹的真伪问题,在当时已有学人提出,如《广州大典》史部总目第十方志类收录的清代学者周广等人辑撰的《广东考古辑要》就有对南华六祖坠腰石刻字的讨论,论者提出“既称师坠腰石,而又云卢居士志,文法不相连,属字画亦不佳”,以及六祖的生卒年等论据,可供参考。 而这些遗存的显著特点也是与生活密切相关。
五、“惠能形象”的生活色彩:一种美学反思
地方文献有别于庙堂高典之处,正在于其“乡土色”与“接地气”。如果上文梳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可以认为《广州大典》中的“惠能形象”呈现出逐渐脱离思想史开宗大师的学术形象,转而成为维护地方文化、凝聚地方认同,形成地方性生活方式的民间地方神祇形象的谱系。这种形象充满了岭南文化偏重神秘的同时,又保持对儒家主流意识尊崇心态的特色,这从上文的辨析中不难看出。当然,这一脉络并非历史形成的,而是站在后设立场上对地方文献加以研究的结果。但地方文人一方面以儒家“尊经”传统贬低“惠能形象”,认为其“游谈无根”;另一方面又用儒家“崇孝”传统包装“惠能形象”,对宾公等六祖的“衍生形象”予以认可,却是事实。这种微妙的心态,其实都在重塑着岭南文化的生活色彩,从而使“惠能形象”从高高在上的庙堂中走入色彩斑斓的民间,并以种种奇思妙想和传说故事,构成了“惠能形象”的美学特征。
这种生活美学集中体现在“惠能形象”的物质文化层面。虽然这些史料还可以从空间文化或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无论如何,其美化生活、使生活拥有抽离开现实苦难的美学特征,都是极为明显的。《南海县志》记载光孝寺中的智药三藏手植菩提,“庭前双树尚依然,何处犹参无树禅,一自老卢(即指六祖)归去后,年年长结万灯缘”。这棵古树“不花不实,经冬不凋,叶之根脉细致如纱绢,广人每用此为灯、为花、为蝉虫之翼”;“其枝其叶似柔桑,而大本圆末锐,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于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尽,惟余细筋如丝,霏细荡漾,以作灯帷、笠帽轻柔可爱,持赠远人,比于绢縠。其萎者,以之人爨矣。”⑤ [清]潘尚楫、邓士宪:《道光南海县志》第8卷,清同治八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296页。 而《新宁县志》所载的古树,“在广海卫城东门外,灵湖寺六祖堂前”。而其物之姿态,也是“风摇其叶,若骤雨至其叶坠土,青绿脱尽而筋络独存,夹以笼灯若纱縠可。”⑥ [清]王暠重、陈份:《乾隆新宁县志》第4卷,清嘉庆九年补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404-405页。 这恰是一种生活美学的象征,进可为品味之美物(为灯、为花、为蝉虫之翼),退可为生活之日需(为灯笼纱縠、为薪柴),而其间恰暗示了“惠能形象”的美学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超越的可能。
“惠能形象”的复杂性,在地方文献中以一种亲近生活的面貌显现出来,而这种面貌同样含有趋向思想史与趋向信仰史、趋向禅宗与趋向道教、趋向精神与趋向物质、趋向想象与趋向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一如康熙年间修编的《增城县志》中收录有宋学士苏轼的《同程正辅表兄游白水山》诗云:“首参虞舜款韶石,次谒六祖登南华。 仙山一见五色羽,雪树两摘南枝花。”⑦ [清]蔡淑、陈辉璧:《康熙增城县志》第13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广州大典·史部·第十方志》,第499-500页。
〔中图分类号〕 B9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10-0040-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东南沿海地区宗教新态势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16BKS1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405);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浙江 杭州,310028)。
责任编辑:罗 苹
标签:惠能形象论文; 广州大典论文; 地方文献论文; 民间信仰论文; 生活美学论文;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论文;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