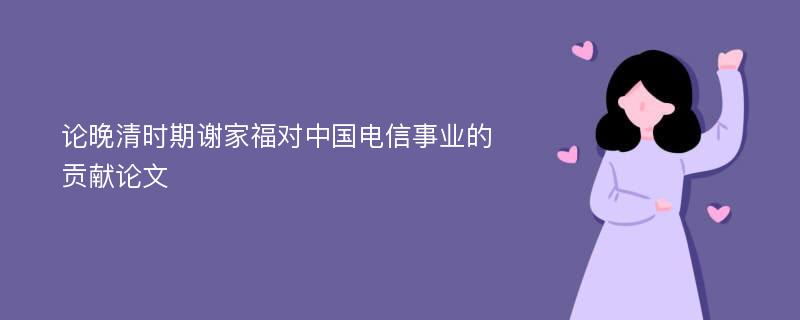
论晚清时期谢家福对中国电信事业的贡献
刚 苗 苗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摘 要 :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科技成果电报的引进,开启了中国电信事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在中国电信事业草创阶段,谢家福在电报线路的筹建与扩展、电报价格的调整与规范、电报器材自制与电报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开拓中国电信事业的先行者之一。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谢家福奠定了中国电信事业发展基础,促进了中国电信事业走向近代化。谢家福作为先行实践者,在创建中国电信事业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 :谢家福;晚清;电报;电信事业
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拍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正式宣告电报诞生。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方科技成果,电报在向中国东延的过程中经历了中与外、新与旧的较量,国人对电报的态度也经历了从抵制到主张自建的转变。电报诞生30年后,清朝疆臣才开始试办电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大规模创建电报的呼声愈来愈高。1880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的津沪电报线路,晚清由此掀起大规模自建电报活动,开启了中国电信事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谢家福(1847年~1896年),字绥之,号望炊,江苏吴县人,早年曾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首倡晚清义赈,后因义赈进身洋务。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谢家福参与筹办上海电报分局工作,同年十月调苏州电报分局,担任苏州电报分局总办。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又调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上海电报分局改称上海电报总局,谢家福任上海电报总局提调。谢家福在参办电报事务时,深受盛宣怀器重,盛宣怀曾多次向李鸿章推荐谢家福。现存的李鸿章奏文对谢家福也是褒奖有加:“帮同盛宣怀办理电报电线事宜,实心实力,井井有条,凡有所见,地无论远近,事无论巨细,皆竭诚筹助,其议论亦多可采用,在电局五年,甚劳损。”[1]194这充分说明谢家福对中国电信事业尽心尽力,不惧劳苦。史学界对谢家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谢家福义赈方面,强调谢家福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贡献。而关于谢家福对中国早期电信事业的贡献则少有研究。目前仅有柯继承的《中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对谢家福的电报建设活动做了介绍[2]。作为开拓中国电信事业的先行者之一,谢家福积极投身实践,并“始终其事”[3]458。在电报线路的筹建与扩展、电报收费的调整与完善、电报器材自制与电报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电信事业的近代化。
一、 推进晚清电报线路的筹建与扩展
从1874年清廷批准沈葆桢奏请(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奏设电报)拟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台湾地区架设电报线路,至1880年李鸿章获准创建天津至上海的津沪线路,此期是晚清电报的试办阶段。这一阶段架设的电报线路有马尾线、津衙线、台南线和津沽线。这些电报线路多属试办性质,且线路短,影响小。相对于电报试办阶段而言,1880年~1884年是晚清电报的大规模创建阶段。在这段时期,先后建成津沪线、长江线和沪粤线等三大晚清电报主干线。这三大干线绵延千里,在中国沿海、沿江铺展开来,构建成中国电报线路发展的基本框架,之后晚清电报网的形成,大多是在这三大干线的基础上延展扩建[4]94。谢家福积极参与了这三大干线的建设,为中国早期电信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推进津沪线官督商办
1880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陆路电报线路,强调引入电报的国防意义,旋即被朝廷批准妥速筹办。津沪线的筹办,经费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考虑到电报线路建成后,绵延千里,常年经营用费甚繁,且电报线路一旦建成,不仅为清廷传递军务所用,更可以充作商线为民所用,所以,李鸿章本意是“先于军饷内垫办”[5]206,以解决筹办津沪线路的资金问题。早在津沪线请设之前,中国已开办官督商办性质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官督商办企业经验,因此,李鸿章在奏请设置津沪线时便指出,“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6]159,指明了未来该线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随后,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在紫竹林、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6处设立电报分局。
为深入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培养优秀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人才,提高基层经济发展管理质量,11月10日-16日,十二师二二二团首批28名由连队、社区“两委”和致富带头人、合作社社长组成的考察团赴对口援疆省市,山西长治市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观摩学习。
因办理义赈而得到盛宣怀、李鸿章赏识的谢家福,成为经办津沪线事务的重要人选。谢家福也非常清楚电报事业对中国,尤其是对军事、国防方面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参与津沪线的创设,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投入到上海电报分局的筹办工作中,同年十月调至苏州电报分局,担任苏州电报分局总办。身为苏州电报分局总办的谢家福连同盛宣怀、郑观应等一起禀请李鸿章,请准由他们招集商股,将津沪线买归商办。谢家福等人认为,“电线兴造之资有限,而常年之费糜穷”,中国初创电报,风气未开,“此等有益富强之举,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非商为经办,无以持久”[5]206。在肯定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后,谢家福等人进一步提出,“凡沿途文武官员、弁兵人等,仍应官饬认真巡守;如有疏误,准由职局详请,照章赏罚”[5]206,进一步明确了官督的职能。对于谢家福等人对津沪线官督商办的规划,李鸿章表示认同,这加快了津沪线实现官督商办的进程。
筹谋建造电料场之事,在当时虽无法实现,但却为之后邮传部意识到电报器材国有化对中国电报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拟设立电品制造所埋下伏笔。
这些那些明增暗减、简约中隐含丰富的做法,未必已经成熟,可能仍是创作途中的探索,但至少说明创作团队不仅是在表演陈仲子,更以一种致敬的姿态贯穿艺术创作本身。
由于中国电报事业处于草创阶段,风气未开,因此,此次的津沪线招股并未得到大量商人的响应,基本上由盛宣怀派认,谢家福积极响应,参与入股[8]530。谢家福作为中国电报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不仅担任苏州、上海电报局的公职,还成为上海电报局四大商董之一[9]234。
(二)参与筹划长江线、沪粤线的请设
长江线作为晚清三大电报干线之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早在谢家福等人禀请津沪线由他们招集商股,买归商办之时即指出津沪线“原为军务、洋务缓急备用,自北至南,所经之地,绝少商贾码头,其他丝茶荟萃之区,尚无枝线可通,线短报稀,取资断不敷用”[5]206。由此可知,津沪线的创设,主要是出于海防而非商务考虑。津沪线架设之后,其示范作用使时人注意到电报带来的良好效益。又因津沪线所经之地“绝少商贾码头”,需要进一步在商业兴盛之地架设电报,以通商业信息,促进商业发展。因此,请设长江线的呼声应运而起。
1883年7月6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左宗棠终于改变态度,奏请朝廷架设长江线路,并提出准由盛宣怀等人承办。至此,历时一年多的请设长江线事宜尘埃落定,谢家福与电报同仁的努力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882年初,谢家福、郑观应等即向李鸿章提议架设长江线路,而相对于津沪线,长江线的创设可谓一波三折。由于长江线所经地区多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所辖范围,所以,李鸿章对谢家福等人的提议并无具体回复。谢家福意识到,想要架设长江线路绝非易事,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道:“江线事鄙知所断不容已,阆帅(涂宗瀛)不即到任,芍师必因地方绅士决不尽以为然,诿诸正任。”[8]524谢家福认为左宗棠必定借地方士绅之由,阻挠长江线的架设。但谢家福并没有放弃创设长江线的计划,他积极谋划解决方案,并提出应对方法:“亲往酌看情形,万一以舆论却我,即答以改用水线。”[8]524谢家福提出若左宗棠以舆论为由拒绝请设陆线,则改设水线,其认为水线虽然昂贵,但是陆线“每年延守计须五千金,已占五万金股息地步”[8]524,况且“江线即成,津沪一线每月多售之数总在五百金外,亦暗贴五万金,股息尚合算得来”[8]524。谢家福在综合分析水线、陆线利弊的基础上,提出改设水线的方案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谢家福还与郑观应、经元善等人针对架设长江线路议定具体办法,在其给盛宣怀的信中写道:“添线一节,顷与毂(沈善登)、松(李培松)、陶(郑观应)、莲(经元善)诸君议定办法,先求太翁老伯大人(盛康)在浙抚处疏通,松翁亦于今日赴杭,敷衍绅士一边,毂翁见过侯相,亦即赴杭,投递浙商请办电线禀件。莲翁与弟今夜乘轮船赴鄂,一面疏通上游,一面约同茶商,具禀添设电线。”[8]526-527谢家福尽心竭力为设长江线路奔走呼告,与郑观应、经元善等人商定计划,分头行动,足见其设长江线之决心与毅力。
评判性思维是个体在复杂情景中,能灵活应用已有的经验、知识,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最后做出合理的判断和正确取舍[1].评判性思维是培养护理本科学生(以下简称护生)核心胜任力的内容之一.《成人护理学》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在实践教学中培养护生评判性思维,使护生面对临床情景时,能结合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反思、分析,综合做出符合个案的判断和决定,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黄金周”旅游存在的问题是因为休假政策引起的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反映了旅游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依靠市场自身无法有效调解。仅调整休假制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要建立规范、合理、有序的市场运作体制,不仅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要合理分配,还要协调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
在谢家福等人请设长江线时,即提出申请承办苏浙线(后拓展为沪粤线),只是受长江线事情的影响,苏浙线的承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正当诸事陷于困顿之时,一次外患危机使申办苏浙线出现转机。1882年10月24日,英、美、法、德等四国公使认为既有的上海至香港的海线为单线,一旦有所损坏,容易造成信息传递不畅,为此,他们提出设立万国电报公司,铺设新的沪港海线等意见。面对列强对中国电报权利的觊觎,李鸿章考虑到丹麦属小国,容易控制,不至对中国电报权利造成巨大影响,本意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合作建线,盛宣怀、谢家福等人知道此事后,会同经元善、王荣和等禀请自建,提出在原来的苏浙线计划上加以拓展,从苏州经浙江、福建各通商口岸架设与广东相接的陆线,即三大干线之一的沪粤线[4]108,此提议得到李鸿章认可。1883年1月16日,李鸿章奏请“招商接办由沪至浙、闽、粤各省沿海陆线”[10]131,很快得到清廷批准开始搭建。至此,晚清电报三大干线(津沪线、长江线和沪粤线)在谢家福等人的努力下相继建成,构成晚清电报网络的基干。
电报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其后续发展成为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谢家福的关注点集中在电报器材自制与电报人才培养两方面。谢家福深知这两方面对后期电报事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力倡导电报器材自制与电报人才培养,并积极付诸实践,为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推动晚清电报价格的调整与规范
电报收费制度关乎电报主客体双方的利益,向来在电报的各项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收费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电报局的经营状况。谢家福身为电报创建之人,在电报局的收费管理制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
(一)调整电报定价
自1881年12月津沪线开通,电报定价体制极不完善,且变化幅度较大,谢家福作为苏州电报局总办,曾在早期电报定价方面有所建言,并得到采纳。
在津沪线官督商办之前,各电报局电报收费价格较低,随后,盛宣怀与各电报局负责人商议在原来的报价基础上平均加价,上调电报收费价格。谢家福考虑到中国电报业处于初创时期,且国人风气未开,甚至对电报怀有畏惧、抵抗之心,如果此时不加区分,平均加价,这对初创的各电报局的发展将会十分不利。因此,谢家福针对各电报局电报收费价格平均加价问题向盛宣怀提出建议,其认为“华报加价一节却宜斟酌”,“苏沪二百四十里,每字七分半,沪镇五百五十里,每字八分,试以差分法分之,沪苏贱乎?贵也。沪镇贱乎?贱也。苏市淡于镇而电价贵于镇,若再一体加价,报稀无疑”[8]530。身为苏州电报局总办的谢家福,通过对比苏州电报局和镇江电报局迥异的实际经营状况,认为如果统一平均加价,不加分别,则对像苏州电报局等经营惨淡的电报局危害极大,不仅会打击人们利用电报的热情、影响苏州电报业的未来发展,还极有可能导致“报稀无疑”的后果,这对草创时期的电报业发展极为不利。同时,谢家福进一步指出“清扬济亦然也”[8]530。谢家福站在清江电报局、扬州电报局和济宁电报局的角度,指出平均加价对这些电报局的危害。因此,谢家福提出依据各电报局生意旺淡的标准确定电报收费价格。此建议因符合当时各电报局的实际情况而被采纳,报价于是上调为:“沪苏一角,沪镇一角一分,沪清八分五厘,沪济九分,沪津一角五分。”[4]223直至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后才又重新调整。
(二)促使头等官报收费
早在1884年,谢家福、经元善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因思日本电线材料各种均自能制造,吾局无不仰给他邦”,应“共筹另设制造电料场”[9]244-245,意图降低电报建设成本,推动电报建设发展。考虑到电料场初创时期必然入不敷出,谢家福、经元善决定求助于官府,“欲求中堂贴助万金”[9]245,谢家福与经元善共同进谒李鸿章,提出创办电料场事宜,不料却被李鸿章以“电归商办,官不能帮”为由拒绝,但谢家福没有放弃,力陈创办电料场的必要性,更是以日本电报事业发展经验为例极力劝办。遗憾的是,由于清廷财力有限及对自主制造电报器材的意义认识不足,自制电报器材的建议仍没有得到认可。谢家福十分痛心,感叹:“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无涯际,此后之杞忧未艾也。”[9]245谢家福认为电报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途径,而当政者却看不到自主制造电报器材对中国电报事业乃至中国富强大计的重要性,这使他万分悲痛。
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之际,谢家福认为上海电报局“官报必多”,于是前往上海电报局监察发报,发现“商报中如道署寄总署,立候回音以复巴使止住孤拔开战之报,均为官报压迟”[8]568,此类事关开战与否的关键电报,只因其为商报而为官报所积压,这令谢家福非常紧张,谢家福又细查官报,发现其中竟有“绝无紧要”之事。谢家福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头等官报可以免费,故大多愿用官报。于是,谢家福向盛宣怀指出,“如此决不相干之报列诸一等,限以时刻,不发不可,而四等中极为紧要之报反致延搁,此大害于军国也”“大害于商也”[8]568。谢家福发现电报等次和官报免费寄发的弊端,对此,其提出改进办法:“一等报不能以有钱无钱计,无钱则人人欲列一等也。应照西例,参以奏案,反系紫花印衙门发出之报,与夫有印有关防之官员电复,紫花印衙门报费解还户部。”[8]569这样减少了无关紧要的头等官报的数量。接着谢家福又提出:“一等报中再分别轻重,加一码号,如和、战定于此报者加一某字码,调兵发饷加一某字码,探报军情加一某字码,凡此皆提前速发,庶官报之中不致轻重颠倒。”[8]569谢家福认为这是“非等闲寻常可以通融”之事,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对电报局不利的局面,“如果一等电报不能变通章程,必致大误军国要报,并使商报裹足不前”[8]568-569。谢家福向李鸿章提出头等官报照收报费的要求,但被李鸿章以中法即将开战为由,未予批准[1]55。等到中法战事既定,头等官报收费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887年8月19日,李鸿章奏知清政府,正式确定头等官报收取半费,进而使电报局增加了收益,维护了电报局的利益,为电报局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房屋检测的精度分析可见,对于高出地面的地物使用GoodyGIS卫星影像进行矢量化测图精度损失较大,主要原因是GoodyGIS卫星影像的分辨率不高,容易造成作业员视觉误差从而导致对地物投影差改正不准确。
三、倡导自制电报器材与培养电报人才
谢家福积极推进晚清电报线的筹建与扩展,坚决抵制列强对中国电报权利的侵犯,为维护我国电报领域的自主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倡导自制电报器材
中国电报创设时期,所需电报器材长期不能自制,大多需从国外购买。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电报建设的“权自我操”,更增加了电报建设成本。晚清电报总体收费较高,也有这个因素的影响。
津沪线官督商办后,就各电报局电报收费情况来看,主要有头等官报收费和普通电报收费两部分。对于等待寄发的电报,电报局将其分为四个等次,按等次顺序寄发,避免混淆,以提高效率。第一等为头等官报,首先寄发;第二等为各电报局间公务报,次发;第三等为加费电报,再次发;第四等为普通电报,最后寄发,同一等电报按送局时间先后寄发。就头等官报而言,早在津沪线架设时期,盛宣怀所拟《电报局招商章程》即明确指出对官报实行头等官报免费的优待政策。盛宣怀这样规定,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偿还当初架设津沪线时政府所垫之款。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电报事业尚属草创阶段,风气未开,仍需晚清政府的垫款、巡护等扶持,因此,便定下以头等官报应收资费划抵官府垫款的制度。虽然第三、第四等报寄发越多,电报局盈利越多,但这种电报等次制度明显给予寄发官报以极大便利。随着头等官报界定范围的不断扩大,尤其在战争时期,头等官报数量激增,甚至造成电报局发报生整日寄发官报,而其他等次的电报堆积几天不能寄发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电报局的收益,致使电报局难以维持,这对电报局的发展极为不利。
津沪线在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上,官商意见一致。但就津沪线官督商办的具体实施办法,官商之间仍存在诸多分歧,这体现在制定津沪线招商章程的问题上。1881年12月,津沪线以官款筹建完工,招商事务提上日程,盛宣怀在之前所拟章程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电报局招商章程》。《电报局招商章程》强调官督之权而削弱了商人在企业中的经营管理权。对于《电报局招商章程》中对商人权利的轻视,谢家福与郑观应等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津沪电线二千八百余里,已由官垫经费二十万两,拟集商股十万两,归还官款之半,嗣后成本,官乃居半,官本十年之内不提官利,庶商本余利于充足,即线路易于推广。十年之后,与商本一律起息,仍不提官本,永远存局,加添官股成本等语,似未稳妥”[7]1003。谢家福等认为,此《电报局招商章程》太过强调官对商的体恤,担心日后被官府利用,借机控制勒索电报局,危害商利,影响电报局的发展。在谢家福等人的努力下,盛宣怀随后拟定了《电报局变通章程》,强调以头等官报免费的形式还清官款,弱化官对商的体恤之意,以免将来官府借机控制勒索电报局,这有利于使津沪线若干年后不存官本,只留商本,实现名副其实的官督商办。津沪线在运营一段时间后,从1882年4月18日起,正式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4]180。
(二)培养电报人才
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电报人才的培养,早在沈葆桢第一次吁请中国自办电报时就曾提及电报人才培养问题。电报作为中国的新生事物,急需专业的电报人才。在谢家福参与电报学堂事务之前,清政府已经创设了福州电报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但随着电报事业的发展,这些电报学堂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1882年,清政府在上海增设电报学堂,该学堂的主要负责人便是谢家福。谢家福认为培养电报人才是促进电信事业长足发展的根本,因此,所有上海电报学堂及商线各电报局调派报生等事宜,他都竭力调度、安排,对电报学堂事务极为用心。谢家福指出上海电报学堂在培养电报人才方面存在的弊端,其认为“沪堂难出优生之根”有两点:一为“无所取才”,一为“调动各局学生难如登天”[8]557-558。谢家福对比上海电报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的发展情况,认为天津电报学堂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其生源多选自香港书院和上海广方言馆中精通中西方文化的优秀学生。因此,谢家福主张上海电报学堂“向广方言馆调取十、廿人,以裕其本”[8]557-558,多收学贯中西的高质量学生。同时,谢家福指出各电报学堂在调派学生时往往只调派初出茅庐的新生,而对经验老道的学生则自留而不派遣,这不仅不利于电报学生自身技术的长进,更不利于各电报学堂的发展。为此,谢家福常常在调派电报学生等事务中多方疏通,甚至到“笔枯舌干”的地步[8]558。谢家福任职于上海电报学堂时,极力促进上海电报学堂的发展,对学堂各项事务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当盛宣怀对电报学堂建设提出不恰当建议时,谢家福也直接以“公于堂事,实多隔膜”进行回复,并毫不避讳地提出反对意见,由此可知,谢家福对上海电报学堂建设和电报人才培养的重视。
1892年,谢家福呈准盛宣怀,又于苏州城内五亩园创设苏州电报学堂,也称苏州电报传习所,简称苏堂,与天津、上海电报学堂同列为中国早期培养电报人才的三大学校[2]26-27。学堂内设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学生主要学习电报收发技术,高级班学生则学习中英文电报通报、收发等技术。苏州电报学堂在3年间培养了电报值机生800余人[11]131,民国时期形成了苏籍电报学生遍布中国的盛况。谢家福为培养电报人才不遗余力,尽心筹划,由于操劳过度,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不幸病世。
四、结 语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谢家福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意图挽救颓废的晚清社会。为了打开近代电信事业在中国发展的局面,避免西方列强侵犯中国电报利权,谢家福主动提出自主筹建、扩展电报线路。在电报建设初期,针对电报局的实际经营情况,谢家福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推动电报局收费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了实现中国电信事业的长足发展,谢家福在电报器材自制和电报人才培养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中国电信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成为开拓中国电信事业的先行者之一。
依据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拟建场区地处淮河右岸,江淮丘陵北缘,属丘陵地貌,总体地形南高北低。场区主要位于采煤塌陷区内的垃圾填埋堆及其周边,受人工活动影响,地势高低不平,其中场地内的垃圾堆长度约600 m,宽50~150 m,呈不规则长条形,垃圾堆高度10~20 m,顶高40~48 m,垃圾堆四周地势较为平坦,多为麦田,总体地势略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高程34~38m。
谢家福作为创建中国电信事业的先行实践者,其电信建设思想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表现在谢家福创建电报实践活动中的非主导性。一方面,其实践活动多同其他电报局同仁联合开展,如郑观应、经元善等,且具有一定的派系色彩。另一方面,作为具体实践者,谢家福终究不能左右晚清上层当权者,主导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从其与经元善共同提出电报器材自制建议不被肯定中可看出。但也正是由于谢家福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晚清当权者的思想认识转变,促进了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
招标需求设置上,主动明确招标需求应包含的服务、商务要求等关键要素,“一举打破了以往招标由对方提供服务参数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11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 柯继承.我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J].苏州杂志,2002(3):26-27.
[3]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4]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王尔敏,吴伦霓霞.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6]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9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 王尔敏,吴伦霓霞.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9] 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 戴逸,顾廷龙.李鸿章全集:第10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1]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6辑[Z].1986.
Discussion on XIE Jiafu′s Contributions to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ANG Miaomiao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of telegram, the achievement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rted the difficult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the pioneer stage of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XIE Jiafu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pa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elegraph lines, to the adjustment and regulation of telegraph prices, and to the self-made telegraph equipment and the training of telegraph personnel. In view of the complicated background of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extremely rare for XIE Jiafu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However, as a pioneer practitioner, XIE Jiafu had a certain historical limita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Telecom.
Key words: Xie Jiafu; late Qing Dynasty; telegram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19.02.015
中图分类号 :K8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19)02-0081-06
收稿日期 :2018-10-16
作者简介 :刚苗苗(1991-),女,河南安阳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 闫丽环 )
标签:谢家福论文; 晚清论文; 电报论文; 电信事业论文;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