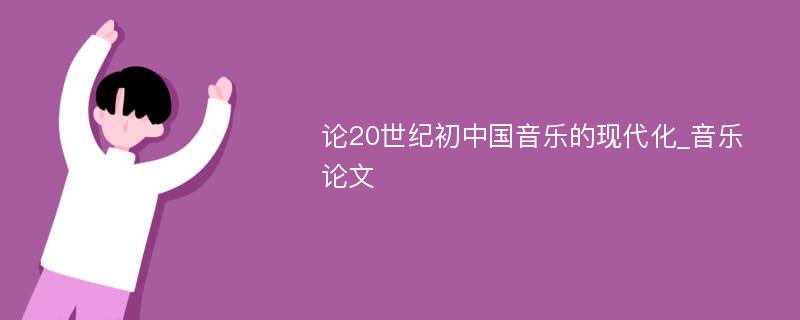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有关中国音乐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Modernity)发端于欧洲19世纪初,其后一百多年来它不断发展、变异、扩张, 并且影响全球,在各个领域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相伴而生的 对现代性的思考与反思也从没终止过,西方重要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对现 代性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作为第三世界的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可追溯到晚清,而20 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开始热烈讨论现代性问题并反思中国的现代性,有关“ 现代性”话题可说是贯穿整个90年代文化讨论的基本线索之一。讨论的话题包括:直接 以“现代性”概念为标志对中国当代现状或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整体的、断代的、综 论的、专题的)进行反观;直接介绍、评价、反省西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但是, 遗憾的是在近千篇这方面的论文里我们几乎听不到音乐界的声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 音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扯不断的联系,更确切地说,中国音 乐的发展深置于中国的现代性之中,中国音乐思想、音乐性质、形式等被深深地制约、 框定在这个历史情境之内。笔者以为,从现代性理论视域入手探讨中国音乐历史、思想 、美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学术天地,正如有论者所言:“现代性条件 下的问题是存在的,就看我们对此理解和关心的程度,它是逃不过去的一道‘槛’。我 深信,从这个理论角度去思考、研究中国音乐学的前路和进向,是大有益处的,许多没 有解开的理论‘死结’和现实争论,可能会有新的结果。(注:罗艺峰《现代性条件下 的中国音乐学》,《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这是笔者所能检索到的 惟一一篇有关的文章,它的不足是大而化之地谈论中国音乐学的现状,并且作者对现代 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这里所谓‘现代性’,是指后传统的世界所建立的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行为制度和模式,它基于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对人和社会的全面监控、媒体资 本主义对人类思想和艺术所行使的话语霸权。”)笔者以为,探讨中国音乐现代性问题 必须首先回到原点,追索中国音乐现代性的起源。
概而言之,“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 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它包括三个 方面的含义:第一,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是一个整体性的、却 又具有内在冲突和矛盾的概念,其核心是时间框架中的历史观;第二,这一概念有其历 史的形成过程,是在特定时期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产生的;通过词义由贬 义向褒义的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历史、未来及自身的关系,最终所导致的都 是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第三,这一概念通过对具体历史内含的遗忘而被启蒙时代 用于总体历史的描述,从而它本身不过是该时代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目的论的 命名(注: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第2页、第7页。)。现代性是个矛盾的概念。它是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未来社会的一 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 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 理论。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课题。从诞生起,现代性就不断向世界发布 变革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境界。现代性也将古老的中 国裹挟其中。现代性问题可大致区分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等。依据 马克思的辩证眼光,资本主义变革仍在进行,现代性正四处蔓延,走向全球。无论喜欢 与否,我们已经生活在现代性后果之中。(注: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200 3年第2期。)
中国现代音乐从晚清到现在已走过百年历程,但追根溯源,中国现代音乐是如何形成 的?笔者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有如下显著特征:
一、历史窘境中萌发的中国音乐现代性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工业化、城市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兴起等现 代化过程密不可分,现代性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 动关系。
如上所述,现代性首先是指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这一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 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 未来的目标之中。这又成了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巨变进程的体验,是 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现代性把我们卷入这样 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现代性的 观点在中国传播大致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算起,1898年,严复翻译发表了《天演 论》,从此进化的观念、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观念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注:参阅汪 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中国近代以来,多次遭遇现代性 ,反反复复的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 望、理想与现实。
中国现代音乐的诞生,中国现代音乐思想的兴起必须置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浪潮之 中,必须置于中国特定的现代性之中才能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新的界定和见解 ,思想文化界(当然也包括音乐界)争论不休的古/今,中国/西方,落后/先进、保守/进 步的二元对立最好纳入现代性的阐释构架之中。中国音乐现代性首先在20世纪初音乐人 的思想、心理、情感层面上产生,然后才化作行动,介绍外国歌曲和音乐教育体制,推 广乐歌,呼吁音乐进入学堂,在制度层面上确立音乐现代性。当时的音乐人普遍以历史 性的进化、进步作为取舍标准,不按线性时间规律而进步的现实社会图景就显得格外黑 暗和令人绝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正面价值则被放到了“未来”。落后挨打,赶上 西方的心理使中国人普遍产生了现代性焦虑,作为内忧外患、新旧交替时代的音乐人产 生音乐救国、音乐万能思想,批判中国传统音乐,呼吁推广新音乐都是现代性焦虑的集 中反映、体现,下面从中国新音乐发展方向、中国新音乐的特质方面论述一下中国音乐 现代性。
晚清通晓音乐之人对学堂开设唱歌科的必要性逐渐统一了认识,“今中国办理学堂, 尚在萌芽时代。唱歌一科,多付阙如,实因古乐之既亡,而俗乐尤万非可用于学校也。 然若听其无唱歌一科,又乌何?”(注:竹庄《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第8期,1 904年,见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版第24页、第25页。)但对于中国新音乐的性质、构成、表现形式分歧很大,王国维认 为:“而就歌词之美言之,则今日作者之自制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审矣。或谓古人之 名作不必合于小学教育之目的与程度,然古诗中之咏自然之美及古迹者,亦不乏此等材 料。”(注:王国维《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世界》第148号,1907年10月, 见上书第100页。)王国维在“歌词之美”,即歌词的意蕴、美感、典雅上无疑是推崇古 人名作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也是崇古的:“吾国古诗今诗,可以入谱者正自不少;如 岳鄂王《满江红》之类,最可谱也……推此以谱古诗,何忧国歌之乏绝耶?”但他也认 识到谱写适合儿童学习的新歌必须雅俗兼顾,而做到这一点很难。(注:梁启超《饮冰 室诗话》,见上书第9页。)
20世纪初开始启动的音乐现代性历程呈现出朝野互动,向前推进的格局,清政府《奏 定学堂章程》中写道:“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 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依照”,这说明官府对西方中小学开设音乐课持肯定、认同态度 ,并有仿效之意,并且该章程中出现的“养其性情”、“舒其肺气”、“唱歌作乐”、 “和性忘劳”等词语表明官府对开设音乐课的目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雅乐 久微”无从学起,在情感上又不愿模仿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歌曲内容、形式,只好采 用变通的、替代性的、暂时性的方式:从中国古诗词中选取“雅正而音节谐和者”、“ 雅正铿锵者”、“有益风化者”、“词义兼美者”供学生吟唱。由此看出在古今中西的 对应中,在时局变动中,中国音乐现代性诞生的艰难、中国新音乐蜕变的艰难,选择出 路的困窘、尴尬。(注:见《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第25页。)
中国音乐现代性一开始就存在着崇古与西化的对峙,曾志忞有言:“知音乐之为物, 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欲改良中国社会者,盍特造一种二十世纪之 新中国歌”,他尖锐批评了音乐改良中的“泥古”、“自恃”倾向。(注:曾志忞《< 乐典教科书>自序》,曾志忞译,1904年,见上书第90页。)匪石更是表达了热烈拥抱 西方音乐之意:“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 西乐哉!”(注: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浙江潮》第6期,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 ,日本东京出版,1903年6月,见上书第5页;第3—6页。)
当然也有人意识到中国新音乐必走借鉴西方而创新之路,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音乐,竹 庄认为音乐关系到国民的精神、情感,“故我国学堂之设唱歌,必宜斟酌,非可借用英 、美等国之歌,亦非可用日本歌也”;“近日有志教育之士,乃能假经彼国之音调与学 器,而编成祖国之歌,此至善之法也。”(注:竹庄《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 第8期,1904年,见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0年版第24页、第25页。)其实这还只是停留在用外国的曲谱填中国歌词的阶段, 对曲式、和声、对位、旋律等音乐本体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国音乐现代性由于具备强烈的启蒙意识、功利主义意识,因此是一种国家的、民族 的、民众的、集体的音乐,而不是抒发生命个体一己的悲喜情感的音乐,这类音乐也往 往被指斥为淫词艳曲、靡靡之音而遭到批判,中国新音乐是体现精英意识的音乐,而不 是通俗的、市井的音乐,此中存在着雅俗的对立。如曾志忞认为:“社会腐败,以音 乐感动之,当今之急务也。然当杜绝从前哀艳淫荡之音调”。(注:曾志忞《<乐典教 科书>自序》,曾志忞译,1904年,见上书第90页。)当时的音乐人为填补中国音乐的 空白,筚路蓝褛,怀着急切的心情从西方“拿来”乐曲,无暇辨别、取舍,使中国现代 音乐思潮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痕迹,正如黄子绳等所言:“今就一得之长,择其所学曲谱 ,缀以汉文歌词,付诸梓人,意欲为吾国社会上作风气之先导,歌词工拙,不及计也。 ”(注:黄子绳、权国垣等《<教育唱歌>序言》,日本东京,1905年7月,见《中国近现 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第93—94页。)李宝巽也坦言:“特于音乐学极力研究,并拔其 曲谱之粹而无汉文歌词者,缀而补之……工拙不暇计也。”因为当时的音乐人介绍西方 音乐,都抱着“以谋整理中国国民之惰,定精神教育之基础,将来涵育人才,改良社会 ”的宗旨。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性体验是他们无暇明思细察的主要原因。
二、西方音乐文化参照系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批判
从音乐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界人士往往有留学国外的经 历,他们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有着切身的体验、感受和一定的理性认识,他们回 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多了一个比较的眼光,从而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产生批判意识,发现它的缺点、落后并进而探究它衰落的种种原因,提出开创新音乐的 一些主张。
李宝巽写道:“余居东日久,时与诸生参观各师范学校及小学、幼稚园,聆其歌声乐 声,自成节奏”;“日本维新之初,颁大、中、小各学校制度,随即补入唱歌一科,并 设立音乐专门学校”。(注:李宝巽《<教育唱歌>序言》,黄子绳等编,日本东京出版 ,1905年7月,见上书第91页。)黄子绳、权国垣等也指出:“读希腊文明史,音乐实为 教育界、学术界之要点,且以此定国民之等级……今日欧西文明,多渊源于希腊罗马, 所谓精神教育莫不竞竞于音乐一科。”(注:黄子绳、权国垣等《<教育唱歌>序言》, 日本东京,1905年7月,见《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第93—94页。)他们还把日 本学习西方音乐教育体制成功与中国传统的衰落作了比较。曾志忞也持同调:“远自 欧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视音乐。而其余小学校之唱歌一科,更与国语并 重。”(注:曾志忞《<乐理大意>前言》,《江苏》第6期,日本东京出版,1903年, 见上书第22页。)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音乐发达的原因:“考西洋音乐发达时,凡国 乐之勃兴,有二大原因:一由君主或贵族提倡,故力大而速;一由学者相继研求,固本 固而厚。”(注:曾志忞《音乐教育论》,《新民丛报》第三年第14、20号,梁启超主 编,日本出版,1904年,见上书第10—21页。)至于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大都有 一个共通的心理认知基础,那就是中国上古的音乐是好的,可惜已经失传。曾志忞指 出:“吾国音乐发达之早甲于地球,且盛于三代,为六艺之一,自古言教育者无不重之 。汉以来,雅乐沦亡,俗乐淫陋,降至近世,几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注:曾 志忞《<乐理大意>前言》,《江苏》第6期,日本东京出版,1903年,见上书第22页。 )李宝巽指出:“雅乐久亡,靡音艳曲,贻害风俗”。(注:李宝巽《<新编唱歌集>序言 》,1907年,见上书第97页。)剑虹对这一现象的表述充满了激愤之情:“古乐沦亡已 非一日,至于今,则音沈响绝久矣,我国民之心中尚复有音乐观念者乎!”(注:剑虹《 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云南》第2号,日本东京出版,1906年,见上书第28—30页 。)在这一点上,官府与民众的认识是一致的,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中也提到中国 “雅乐久微”。
那么,古乐失传的原因何在?竹庄认为:“盖亦有天演淘汰适宜者存亡之理焉”,他从 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弹琴指法名目繁多,不好掌握,而世上万物“无有不日趋 简便之理”,因此,古乐消亡的原因是“亡于乐器之繁重”。(注:竹庄《论音乐之关 系》,《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见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 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第25页。)他指出古乐不传的第二个原因是古 琴适合独奏,夜深人静,明月窗前,拂琴悠然,这种情调是超乎尘世的私人享受,而不 适合大庭广众之下共同弹唱。竹庄对雅乐不传的看法还停留在“器物”即乐器的层面上 。而留日学生匪石对传统音乐的批判则要深入、全面、严厉得多,他认为中国音乐无论 古乐今乐,“皆无所取焉”,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缺陷,他概括了四条:“一、其性质为 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二、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三、不能利用器械之 力也”,匪石对中国乐器的作用的看法与竹庄正相反,他认为中国丝竹乐器结构很简单 却不好学,他的意思,中西音乐优劣不在于乐器结构简繁上,而在于西方音乐乐理完备 ,乐律科学;四、他认为中国乐皆存在着“师匠秘传之痼习”,“鄙夫略得毫末,诩然 自夸,不以人告,又不欲笔之于书,故旧乐日益消灭,而新作亦复绝响”。匪石从中国 音乐的性质、精神、学理、传播机制、渠道等方面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弊端。他更从中西 文化差异的宏观角度指出中国音乐衰亡的原因,中国以“理”立国,数千年来以道学理 学控制社会,到了穷途末路,而西方以情立国,所以能兴盛,因此,他主张必须推行感 情教育。(注: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浙江潮》第6期,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 日本东京出版,1903年6月,见上书第5页;第3—6页。)黄子绳等也认为,“三代后, 义理之说日盛,乐歌之学日微,音乐之道盖几乎息矣……究其所谓音乐者,亦不过供个 人之玩好,于社会上无丝毫裨益也。”(注:黄子绳、权国垣等《<教育唱歌>序言》, 日本东京,1905年7月,见《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第93—94页。)从以上论述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现代中国第一代音乐人的价值取向、音乐态度、情感立场。尽管他 们以为中国上古时期音乐地位至高无上,尽管他们念念不忘,但他们为形势所迫,只能 鼓吹、推崇西乐。当时的音乐人士的思维方式深深受制于现代性之中:即中国/西方、 传统/现代、革新/守旧、进步/落伍的二元对立模式,形成了只能在中国传统与现代西 方中弃一取一的选择。西方的、新的就是好的,中国的、古老的就是得抛弃的,这种变 革的、与传统断裂的、向前进步的意识深入人心,这种现代性观念的获得是以主体性的 丧失为代价的。
另外,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里产生了一种音乐救国论:音乐在改造国民性,铸造民族 灵魂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这正是体现了现代性的矛盾复杂之处,就是说中国的后发现代 性状况使之具备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潜能、质素和吁求,它也必然在音乐上表现出来。在 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澜中,国人由此产生了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它又对现代中 国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一批精通音乐的文化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具有 浓重的“音乐救国”色彩的民族功利主义音乐观,它构成了现代音乐观念的一个重要基 础,他们将音乐与民族道德、风俗、人心、人格的改造与更新联系起来,高度重视与强 调音乐的思想启蒙作用,要求音乐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新性格的有力武器,突 出强调音乐与民族盛衰兴废的关系,希望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影响来达到振兴民族的功利目的。推而广之,当时人又产生了音乐功用的普适性、扩 大化认识。20世纪初的音乐界、教育界人士除了对音乐有利身心健康、陶冶情操产生了 明确认识之外,还赋予音乐各式各样的功能,使之承担了不堪承担的重负,这是一种音 乐万能论,音乐似乎在功用上适用于一切方面,这种夸张的、扩大化的对音乐作用的认 识一方面源自音乐人士对世道时局的忧患意识和心理焦虑,一方面源自他们对作为新事 物出现的新音乐的价值、作用、意义寄予了深厚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治疗社会痼疾的 一副良药,这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音乐观对音乐教育、音乐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但从历史的眼光看,也有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从以上几方面论述可看出20世纪初中国人对中国音乐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理论是当 今跨越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种学术领域的影响广泛的 理论,它本身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它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张力,20世纪初期中国人在追 求中国音乐现代性方面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而看不到它的复杂性,中国传统音乐如何创 造性地转化为现代音乐不在时人的思考范围之内,对音乐本体缺乏深入的认识,一旦特 定的历史语境不复存在,我们发现20世纪初的音乐思想很难称得上是深刻的思想,是对 音乐本体的思想。但由此开创的中国音乐现代性的进程和现代性品格却历经风雨沧桑不 可阻挡,也许,由此出发探讨中国音乐的种种复杂问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立场、视野和 方法,也许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能够由此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