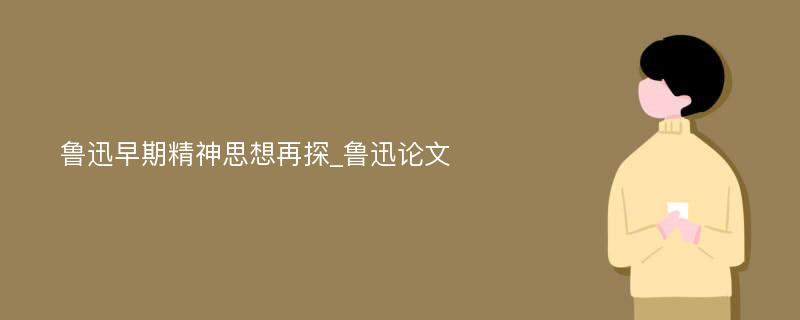
鲁迅早期重精神思想之再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与本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仍面临着物质与精神错位的难题。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弃医从文,并继而形成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文化观念,是他研究了十九世纪的西方文明及受西方文化冲激的中国社会的现状后作出的文化选择,实行了由热衷科学到重精神革命的思想转换。鲁迅当年为什么实现这一思想转换,曾经是鲁迅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只是近几年冷落了下来,但是对这个命题的认识其实远没有终结。面临着本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越来越令人焦虑的物质与精神错位的难题,重行研究鲁迅当年重精神的思想,比之于其他热门话题或许更有意义,故曰“再剖析”。
上篇 文明史的启示:“致人性于全”
当科学的“巨魔”闯进人类的生活,改写着人类的历史,把人类在宗教世界里向往的“天国幸福”带进了现实世界时,这个“巨魔”很自然地在人类心目中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当人类从“上帝”的手中要回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科学的“巨魔”,不再向往那彼岸世界,立足于此岸世界创造着现代文明时,又痛感那曾经遥寄于彼岸世界的精神的缺失;在“上帝已死”之后,人类又发现了“圣杯”的丢失。于是我们看到由科学“巨魔”所写的历史,显露着愈演愈烈的文明与道德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错位。我们发现在地上建起天堂的人们精神上其实是躁动不宁的。但是现代理性告知人们历史不可能回到“上帝”的时代,需要寻求新的精神出路。罗丹曾设想完成包括二百多人物的大型组雕《地狱之门》,提出“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可惜他毕其一生都没有完成。但他所留下的那尊坐在“地狱之门”顶上的《思想者》的雕像却启示人们面临现代社会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思考人类的精神出路。这个科学的“巨魔”在上世纪末也走进了东方,东方文化的魅力抵不住西方现代文化的魔力,几经冲撞,古国的历史打了几个回旋后也发生了转折,二十世纪之于中国,也成为动荡的巨变的世纪。本世纪初,在古老中国开始现代化历程时,也出现了一个思虑着民族精神出路的“思想者”鲁迅。
鲁迅的文化活动起步于科学,他是由科学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本世纪初,他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表现出对科学的热衷。早年写有《中国地质略论》《说鈤》《人之历史》等纯自然科学论文。但随着他对西方文明社会的深入体察,也沉入了对科学与文明之关系的深深思索。
1906年6月,鲁迅弃医从文, 他自叙弃医从文的原因是看到救治民族灵魂是当务之急,但原因不止于此。从他以后对上世纪末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偏颇的分析看,他的弃医从文还隐含着对科学难于救治现代社会精神沉沦之现状的思索。1908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表《科学史教篇》一文,这虽然说明他对科学的热情不减,但目的显然不止于介绍科学史知识。他将科学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总体构架中考察,赞扬科学推动了人类文明化进程,但又指明科学史不等于文明史,科学不是判定人类文明化程度的唯一准绳,判断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必须是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与人文彼此不能取代。
人类从科学获得理性,并以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克服对自然、对人认识的盲目,产生了人之为人,民族之为民族的自觉意识。鲁迅所描述的西方科学史,乃是人类的理性不断照彻历史的过程,“科学者神圣之光”,神圣的上帝必须让位给科学。但是当人们把科学推上神圣的地位后,也不能因此而陷入拜科学为造物主似的盲目;同样当宗教被推下神坛后,也不能因此而无视宗教在文明史上曾经有过的精神建树。
当希腊人告别了神话时代,把宇宙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进行研究时,兴起了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如数学方面的几何三角;物理方面的原子论,力学,流体力学,静体力学,机械学;天文方面的气象学;生物方面的解剖学等等。其后罗马把希腊科学的成果转化为技术,又化为实利,创造了人类最初的物质文明,罗马一举而成强大的帝国,统一了欧洲,但是与这种强大跟着出现的是“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败”。在鲁迅看来,这种道德颓败却也为兴起于希伯来的基督教的传入并统治欧洲创造了条件。作为对继科学技术的实利化而出现的道德颓败之救正,则是基督教的“宣福音于人”,把宗教信仰与道德义务作为人的根本精神追求。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为人们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信仰与道德为本,知识为次,并从属于信仰与道德。这就形成了宗教道德对科学也即是对人的智慧的压抑,于是“科学之光黯淡下去”,也即是人们所说的中世纪的黑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鲁迅又看到,中世纪的宗教道德精神固然压抑了科学,使社会停滞,但“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薰染陶冶亦胎嘉葩”,即产生了路德,克灵威尔,弥尔顿,华盛顿,嘉来勒等宗教改革家,革命家,艺术家,思想家。这种观点,固然是受章太炎先生“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注: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说明鲁迅没有用科学理性裁决一切。甚至在他看来,即使将宗教置于科学理性法庭内裁决,也应承认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上精神建树的成果。
宗教的确如列宁所说是“精神的鸦片”,它以上帝为信仰、为人的精神追求的终极,以神本取代人本,人异化为神的附庸,但是对真诚的信仰者来说,“上帝”与“道德至善”是等义的,信仰使人相信,人不单是为积累财富而生活,还应该有道德向善的理想,他们相信上帝是反对“为富不仁”的,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也使真诚的信仰者相信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人与人应彼此相爱,同情。这种观念也曾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所吸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洗涤。为鲁迅所称道的宗教改革家,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从他们反宗教的思想统制及僧侣与贵族的专制看,是宗教与宗法制的反叛者,从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受胎于宗教教义看,他们又是宗教思想的继承者。古典宗教人道主义的博爱,平等观念经科学理性的证明与重新解说而成近代人道主义,成为克伦威尔,弥尔顿,华盛顿等反宗教贵族专制的强有力的武器,历史终于走出了中世纪,又是一番天地。所以鲁迅说:“此其成果,以偿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对基督教精神的吸收与借鉴影响及于中国,如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鲁迅对于宗教之信仰精神,并没有纯然用科学理性来裁决。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可能会“反本心而获恶果”,宗教也可能会反本心而致善果,各有利弊而又互相救治。科学反宗教对人性的压抑而使人发展探寻知识的理性,宗教因科学的实利化对道德的冲击而矫俗。如果我们去掉宗教的神学因素,剩下的就是它的道德精神。从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文明史所显示的是知识与道德难于同步,“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如希腊罗马之科学,以极盛称,迨亚拉伯学者兴,则一归于学古;景教诸国,则建至严之教,为德育本根,知识之不绝者如线。”知识与道德彼此消长的关系在鲁迅看来其实是人类文明史的一般规律:“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人类文明化的进程的确深含着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当人类走出了中世纪的神学之圈,回归于人的本体,人神关系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取代。科学的理性使人日胜一日地发现了自然对人的价值,知识的获得意味着对物的占有,知识的富有使人性日趋物化,人不再苛求自己而放纵自己成“自由人”。但这种“自由”不过是不再役于神而役于物。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以前为上帝所做的事,现在成了为金钱所做的事”(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91页。)。面对着人性发展的又一次片面, 鲁迅在称誉科学现代的神圣地位时,又说:“盖使举世为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唯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不唯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德苛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所谓“致人性于全”,对人类文明而言,应是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当科学在近代被推上神圣地位后,就应防止人性向物的偏倚。要“致人性于全”,应是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给人以“知”,给人以认识改造物质世界的巨大力量,而人的人文素养又将“知”转化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从鲁迅所列举的与科学相对应的一些人物看,在人文领域中他尤重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似乎与科学最不相涉,鲁迅有意将一些文艺巨匠如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与一些科学巨人并提,说明了文学艺术对于人的精神的启迪与洗涤不是科学所能代替的。
而且在鲁迅看来,科学的价值不仅仅是使人占有物的世界,而且科学的发现也是人类精神建树的成果。科学的发现有时也如文艺创作一样,并不纯然是智力的表现,也需要理想的精神,灵感的激励,去名誉功建之心:“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现真理:“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是以真理的发现实现人的思想的飞跃,犹如哥白尼以宇宙太阳中心说破除地球中心说,从而破除了对上帝的迷信,动摇了宗教神权统治的根基,伽俐略对天体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太阳中心说,为反宗教神学提供了更充足的论据;而康德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最终完成了用人的理性取代上帝信仰的思想革命。人类产生了全新的宇宙意识。科学以对真理的发现不断更新人的观念与情感,使人走出蒙昧,由必然向自由提升,这才是科学之本,而科学的实用化是末,本末不能倒置,因为真理对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往往意味着扬弃科学实利化对人的物欲的刺激。
显然,鲁迅对西方科学史的解读融入了自己希望“致人性于全”的文化思辨,但这毕竟是一个历史的难题,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缺憾。古老的中国在西学东渐时,传统的道德精神也在失落,必须面对“致人性于全”的难题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困扰着现代的西方,又困扰着在生存竞争中追逐着西方的古老中国的难题面前,鲁迅最终作出的抉择是重精神,非物质。
下篇二十世纪:“恃意力以辟生路”
继《科学史教篇》之后,鲁迅又写了《文化偏至论》,这是鲁迅思考本世纪文化建设的重要论文。西方的物质文明使素来自尊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并成为一些人心目中本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成为本世初的时尚,一种人皆以为应当如此的文化趋势。而鲁迅则深察这种时尚的浮浅与盲目,“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所谓“中国之情”则指中国之贫弱,既表现为物质文明的滞后,又表现为精神的贫困,“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所谓“欧美之实”,是指近代西方文明只重物质的偏颇,以及与片面的物质文明发展相伴的是日益深化的精神危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鲁迅正是从对“中国之情”的洞彻,对“欧美之实”的深察,舍弃了世纪初一般人追逐西方近代文明以建设本世纪中国文化的思路,确定了“非物质”,重精神的文化建设思路。
鲁迅以分明的近乎决绝的态度表明要“掊物质而张灵明”,是出于在洋务运动,改良运动中一些人干禄之色、攫利之心的暴露,出于对近代文明使人的道德良知为物欲所蔽的反思,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救治民族精神的病弱是当务之急,应建设更新民族精神的新文化。所以鲁迅之“张灵明”与国粹主义力主“中学为体”不同,他不“求古源”而“求新源”,注目于欧洲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崇奉主观”的哲学与叔本华、尼采的“张皇意力”的哲学,他认为在崇尚物质的十九世纪,“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是对物质文明之弊的救正。鲁迅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神思”的概念译述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唯心论哲学,而称之为“神思宗”,显然是将他们的哲学视为富有浪漫诗意的哲学,与自己重精神的思维不谋而合。他认为“神思宗”的哲学尤其是“神思宗之至新者”即叔本华、尼采的“意力主义”反映了人类自省意识的苏醒,将由重物质转而重主观内在之精神,“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意力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将是“二十世纪文化始基”,二十世纪将是一个重“意力”的新世纪。
鲁迅对他称为“神思宗”哲学的推崇,显然隐含着对黑格尔、叔本华,特别是对尼采的误读。黑格尔的哲学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所张扬的人的理性精神的最高概括,并把这种理性精神引向绝对,以“绝对理念”作为他的所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并外化为宇宙的本源,因而他的哲学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黑格尔所崇奉的理性即是欧洲的近代精神:人类以理性面对客观物质世界,获得知识,产生科学,一步一步占有客观物质世界,所以他把这种理性精神视为绝对精神,并外化为宇宙的本源。这种理性精神虽然属于人的主观精神,但其价值取向是占有物质世界,与鲁迅所说的摆脱物的限制,回归于“本有心灵之域”的人格精神不能同一。《文化偏至论》处处闪现着近代理性的光辉,如力主启人智而开发性灵,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区分文明与野蛮,张扬“自我”,肯定“个人”人格独立等。但鲁迅没有把理性绝对化,他看到了人在近代获得理性后又为理性所伤害,成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他的重精神的文化观恰巧是要救正人为理性所伤害的一面。所以鲁迅把黑格尔之“崇奉主观”视为自己重精神,非物质思想的哲学根据,不能不说是对黑格尔的误读。
鲁迅尤为推崇“神思宗之至新者”叔本华,尼采,把他们的唯意志主义归入自己重精神的文化观念中,视为人类精神革命的新成果,并因此而预见二十世纪文明的新精神:“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这显然也是对叔本华,特别是对尼采的误读。
叔本华与尼采视意志为世界的本体,与黑格尔视“绝对理念”为宇宙本源一样,都是唯心主义,所以鲁迅将他们都归为“神思宗”,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改变了欧洲哲学的方向,使欧洲哲学发生了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研究外部世界向研究人的神秘的内部直觉世界的转折,这种转折表现了西方文明世界精神的危机。
理性是人的本质,这是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观念,叔本华一反传统,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盲目的欲望的冲动,这欲望冲动是生存意志,是人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体,这种哲学观念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导。尼采继承改造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创立权力意志说。他去掉了意志主义的悲观成份,把创造法则、支配世界的权力意志视为人的本质,生命的冲动即表现为要支配他人、占有一切的意志,这是真理,是善,普遍存在于一切人之上,“即使在奴仆身上,我也发现了欲成为主人的意志”。(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97页。)经过尼采的改造, 叔本华的悲观的意志主义成为行动主义的意志哲学。而不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所说的意志主要指情感欲望,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往往也是非道德主义,否定义务,否定道德。尼采说:“生命本质上就是占有,伤害,征服异己和弱者,压制,历难,按人自己的方式进行欺诈,吞并,而最起码也是利用。”(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303页。 )这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自有他的原因,人在推倒了上帝之神以后,又在制造理性之神,后者正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要做的工作。于是又有反理性的意志主义,即如尼采既反基督教,又反理性。但是非理性的意志主义思潮的出现,不是昭示人的意识的再次苏醒,也不能由此而预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新生,所以鲁迅的误读是不言自明。
唯其是误读,所以我们很容易找到鲁迅早期思想与尼采相近甚至逼似的地方,但也唯其是误读,鲁迅与尼采总是貌合神离,鲁迅不过是借尼采的思想资料表述了自己重精神的文化追求。尼采说:“对人来说,没有比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地理解一件事情更困难的了。”(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1页。)这是一个思想家的最深层的经验的表述,对鲁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要作的工作是将鲁迅表述尼采思想时所带的“个人感情色彩”剥离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鲁迅仍是鲁迅。
作为哲学概念的唯意志主义源出于拉丁文Voluntas,指人的情感欲望凌驾于理智之上。鲁迅将“意志”译为“意力”,并非在中国文化典籍中没有“意志”一词。《商君书·定分》“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这里的“意志”指思想志向,如用“意志”相译,则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志”相混;译为“意力”,则淡化了原概念中生命本能冲动之义,而强调了“力”。这显然是鲁迅理解中的个人感情色彩。这样唯意志主义经鲁迅的理解与翻译,而成“意力主义”,他对尼采哲学的叙述,处处着眼于一个“力”字。他把尼采所说的超人概括为“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人,这种“意力”即是“排斥万难,黾勉上征”;而现代的理想人格则是“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总之,鲁迅对“意力主义”的种种译述概括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思想。
鲁迅以“意力主义”来解读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吸收了其从人的本能冲动体验生命意义的哲学观,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在张扬“力”,后者则崇拜“欲”。因此鲁迅是带着救治民族精神的病弱,避免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病的思想革命要求来解读尼采、叔本华的,并最终形成了他对二十世纪新文化建设的构想:“恃意力以辟生路”。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只有引进敢于反抗,勇于进取的“力”的成份,方能实现改变民族精神积习的精神革命。
这种“意力”鲁迅概括说明为“反抗为本”“勇猛奋斗”。鲁迅所希冀的“意力轶众”之人,“勇猛奋斗之才”在我国历史上自然可以找到例子,但总体而言,那种足能改革社会的“意力”,那种不甘沉沦,想有所作为的精神,在大多数人身上,往往沉潜很深,压抑在宗法道德意识的限阈之下,难于表现出来,没有转化为激荡于文化表层的显在的思想行为。这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道德本位,人生的最高境地是“内圣外王”,“内圣”是指道德修养,“外王”是指建立功业。但两者的价值取向是矛盾的,“内圣”的实际内容是畏天知命,忠恕,“外王”则是自强刚健,不畏天命,打破现状,竞争进取;两者的矛盾往往是以“内圣”的道德修养消弭“外王”向外求发展之心而达于统一。因此,在封建宗法制下,每当国家危难之时,不乏以身殉国的忠勇之士,但少有秉改革之志,“反抗为本”之人。这也就是在儒家伦理精神下中国社会难以实现近代化革命的原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线不能富国强兵的原因。鲁迅所要张扬的“意力”正是在宗法制下没有得到发展的“外王”精神。
所谓“恃意力以辟生路”对于一个病弱的民族来说,就是要敢于冲决一切使人难于有所作为的观念,更新民族精神。在这里,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意欲路向的分析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认为“意欲”是文化产生的根本,不同的“意欲路向”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如果我们把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意欲向前”理解为“意力”,那么西方近代文化正是以这种“意力”产生了科学与民主精神,而“意欲自为调和”则是对“意力”的消融。因为所谓“自为调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譬如屋小而漏,假使照本来的路向一定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持第二种路向的遇到这种问题,他并不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就在此种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梁漱溟先生写这段话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鲁迅在本世纪初所说的“恃意力以辟生路”,也可理解为变中国文化之“意欲调和”为“意欲向前”,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路向。因为鲁迅对中国文化也作过近似的分析,他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儒家的中和主义,道家的自然无为,使人只求保位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注:鲁迅《摩罗诗力说》。)这即是“意欲自为调和”的精神路向。为改变这种精神路向,鲁迅欲借文艺之力,于是他介绍欧洲摩罗派诗人,“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注:鲁迅《摩罗诗力说》。),为的是破中国之平和。他把拜伦、雪莱等摩罗派诗人称为“神思之人”,即“意力轶众”之人,这样他把在哲学上所推崇的“神思宗”与诗歌创作上的“摩罗派”相融为一,形成了他早期以表现“意力”为内容的浪漫主义诗学观。他的文化哲学观,艺术观全都着眼于一个“力”字,“力”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美之本体”(注:鲁迅《摩罗诗力说》。)。他对拜伦,雪莱等诗人的评述,字字皆是“力”的颂歌,如评述拜伦:“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注:鲁迅《摩罗诗力说》。)而这种精神在一个遵循“思无邪”诗教传统的国度里,是难于读到的,即使伟大如屈原之诗也“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注:鲁迅《摩罗诗力说》。)出于对中国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的这种认识,鲁迅日后成为了文化革命的旗手,文学革命的主将。
更深一层来看鲁迅所张扬的“意力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而且与形而上的信仰精神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尼采也以“精神界之战士”自居,但他那种异常猛烈地反形而上学,反信仰的思想在鲁迅早期重精神革命的思想中是找不到的。尼采讥笑了所有形而上知识之无用,“其无用性比之海难中的水手对于了解水的化学成份更甚。”(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56页。)他嘲笑良心因信仰获救是“欺骗”(注:见《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16页。),尼采宣布“上帝已死”, 自称是为上帝掘墓的狂人,是对基督教神权的彻底反叛,但他因此而否定人类一切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舍弃一切道德义务,不能不成为一个非理性,非道德主义的精神狂人。与此相反,鲁迅倡导的精神革命固然表现为对束缚人自由的封建伦理的反叛,但是他一直致力于向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信仰精神。他一直痛感中国国民性“无确固之崇信”(注:《文化偏至论》。)的精神缺失,他所评述的摩罗派诗人,其力量皆来之于献身于社会与民族的理想。他认为人的社会与人生理想必须是超越了现实利益的形而上的纯精神追求。所以他在《破恶声论》中对人们视为迷信的宗教作了独具一格的分析,人们崇拜那并不存在的上帝,固然是迷信,但不能因此而将信仰与迷信等同。而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往往是将理性与信仰对立,信仰与迷信等同。人类在丢掉信仰后让理性片面发展,结局是反受理性之伤害,这是近代文明史的事实。鲁迅认为中世纪的信仰精神是“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注:《破恶声论》。)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使人超越人生利益的有限价值,而达于无限永恒的精神之域。这正是鲁迅所希求的主观精神的内曜,是使人的“意力”得以爆发出巨大能量的精神源泉。伟大的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俄罗斯人民恃信仰真理的力量开辟新世纪的精神闪光:“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五十九“圣武”》)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舍身求法,为信仰而牺牲的人,“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注:《热风·五十九“圣武”》),近代也有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但毕竟是少数,不代表“中国历史的整数”。中国伦理本位的文化也崇圣,“圣”即是道德价值高于一切,但是对于道德的本质没有抽象为形而上的信念,在现实世界里,道德的修养与人生享乐并行不悖,道德修养而达于“圣”,仍不脱求名取利的功利主义目的。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的伦理文化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虽然都是重精神,但两者哲学内涵不同。后者“不安物质之生活”“有形而上之需求”;前者“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天,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因而“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注:《破恶声论》。)。为物所役,就难于有超越人生实利的纯精神追求,人的肉体的存在理所当然地视为第一义。所以在封建社会里,人生的理想是: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见了;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之!”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注:《热风·五十九“圣武”》)。
这是儒家的人生理想。道家呢?则是成仙,“仙”即是长生不老,肉体不灭,无限地活下去。求仙不成,“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注:《热风·五十九“圣武”》)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士阶层带着这种传统心理接纳西方近代文化时,往往只见“物质的闪光”,而对于欧洲文化中精神的闪光则视而不见。
所以鲁迅犹如普罗米修斯从别国窃得火来,输入新世纪的信仰精神,点燃文化革命的火种:“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注:《热风·五十九“圣武”》)他举着追踪新世纪真理之信仰的圣火,踏上改造国民性的艰难思想革命之途,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标签:鲁迅论文; 叔本华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读书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人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