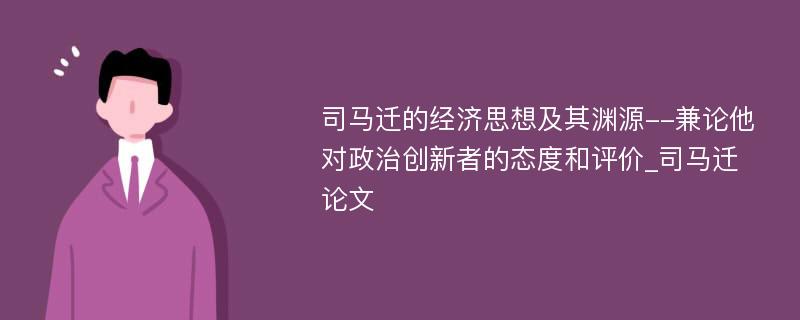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其对论文,司马迁论文,态度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K2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62(2004)01-0001-07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礅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是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因之”政策的实施,《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
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入《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变法的措施有多种,而要在“农”、“战”二字之上,《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变法的这种农战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农业提供战争的兵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便于运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从而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国君得到最高的尊崇。这里面,自然包括历来最被人们所称道的“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讲农战,但他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他的政治谋略,目的是为了“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因此他并非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商鞅则不然,他几乎把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经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围绕着战争服务。由此,笔者不得不对长时间以来盛行于史学界的一种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看法就是:商鞅变法是为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与一切阻碍和反对变法力量的斗争,都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商鞅变法使一部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旨在使国君一人独尊的极端专制的国家(这一点,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与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启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车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却是旧奴隶主贵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当作何解释?“后世遵其法”不独是司马迁一个人的看法。《韩非子·定法篇》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贾谊《过秦论》也说:“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实,那么车裂商鞅就应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当另外做出解释。
这里顺便谈一下商鞅之死的问题。
关于商鞅之死,《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君列传》的这段记载,情节有点像小说家言,很有传奇色彩;然而却未必不是实情。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吕氏春秋·无义篇》:
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
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家不积粟”,这明显地是一种“国富民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仅如此,商鞅还主张通过“刑”、“赏”来控制人们的贫富。《商君书·去强篇》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实际上,这里说的“贫者使以刑则富”是假;因为对于贫者来说,能够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他们很难达到用粟来买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赏则贫”却是真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强迫的手段来使他们买爵捐官,从而让他们“家不积粟”。商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标签:司马迁论文; 商鞅论文; 商君列传论文; 韩非论文; 管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货殖列传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荀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法家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西汉论文; 离骚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