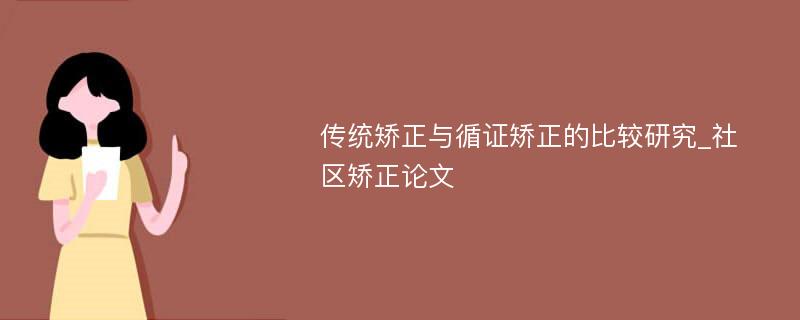
传统矫正与循证矫正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矫正理念之比较:建构主义VS实用主义
(一)传统矫正理念: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制度变迁
我国历来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这突出表现于政治、法律对罪犯改造的定性分析上。其实质内容可以归结为探索如何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一些措施,其方法是对罪犯已然犯罪事实与人身危险性的定性分析,以罪犯的现实表现为基础,以主观估量的方法判断罪犯的改造情况。定性分析矫正理念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对罪犯矫正要求还是对矫正方法的制定,都是以语言描述的方式呈现的;第二,矫正改造方法以三段论逻辑推演方式进行。如在劳动矫正理念中,劳动改造人的理论成为大前提,监狱行刑成为小前提,结论是罪犯接受劳动改造从而能够洗心革面转为守法的人。定性分析的矫正理念带有不可忽视的缺陷。理论的抽象与一般化难以应对犯罪人的复杂与多变性。基于此,定性分析的矫正理念有必要另寻他路,以突破行刑发展瓶颈,提高矫正效果。
2003年司法部提出了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具体目标任务。其中“科学化”建设监狱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行刑领域内矫正理念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重大转变。定量分析的矫正理念突破了传统从一般到个别的矫正思路,适当降低了抽象哲学在矫正中的地位,提升了个人因素与数据统计在矫正中的地位。
(二)循证矫正理念:客观证据的基础性地位
循证矫正是指在矫正领域内,实践者在所研究的证据中,遵循最佳证据原则,结合实践者个体矫正经验,在矫正对象的配合下,针对矫正对象犯因性特点,开展高效矫正的一系列矫正活动。
与传统矫正理念不同,循证矫正以确定实践存在的问题为前提,全面收集和使用有关专业文献,利用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手段从中找出最好的证据,以支持决策者作出最有力的决定。循证实践的证据具有动态性特征。在矫正过程中,实践者所采取或者寻找的项目措施并不以追求统一性的或者一致性的结果为目的。证据会随着循证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之中、之后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证据。这意味着,曾经的最好的证据并不总是最好的证据。①
循证矫正体现出较强的专业槽理念。罪犯的特殊群体特征决定了矫正工作带有明显“专业槽”痕迹。而专业优势重要策略就是将专业实践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并将研究结果作为专业性的判断依据。循证矫正理念接受了循证临床实践概念,认为实践人员应将实验的研究方法导入临床实践,并致力于评估与测试实践效果。②它倡导矫正工作人员采用个体受试的设计方案去评估工作成效,测量案主的风险与能力,以此为基础,采用具有信度与效度的科学标准测试工具,根据已有的实验证据选择最佳的矫治(治疗)方案。③由上观之,在循证矫正工作中,以证据为根基的矫治工作包括3个基本要素:最佳的证据、实践专长和案主的价值。这意味着循证矫正实践不仅仅包含“使用”证据,还包括矫正专长与使用证据之间的平衡,否则很容易走上纯粹的工具主义,不利于罪犯矫正工作。循证矫正本质上是采用“数量化方法”或定量分析的方式对犯罪人进行以客观证据为基础的矫治。这种哲学基本上是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它要求工作人员知晓什么样的治疗项目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然后把这种经验和自己的治疗专长以及罪犯的个人情况整合起来,以便提出可能最有利于罪犯的行动过程。
(三)简要评析:建构主义VS实用主义
按照建构主义的主流思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其认识方法也存在质的差别。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是主观存在,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知识、反思知识并运用知识,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而理解形式则是诠释。④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经反思后形成的认识是人们认知了解世界的主要工具。建构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强调主观意志在征服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社会理论的指导性作用。我国传统矫正理念体现出明显的建构主义特色。
与传统矫正所持建构主义理念不同的是,循证矫正从传统的强调矫治要以权威理论、意见为基础,转向证据为本、实际研究为基础,它依赖于当下可用的最佳科学证据。以证据为本的矫正理念认为,矫正项目与手段都来源于科学实验,工作人员所能掌握的也只能限于经验,至于项目经验背后的矫正结果是不可知的,去探知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循证矫正理念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他们看来,传统矫正以他人的意见、权威的指示、未经反思的直觉及前辈的经验为根据,尽管这些根据对于矫正都很重要,但都是没有经过科学实验证实,传统的矫正工作是否有效尚需通过科学的手段进一步证实。传统矫正工作人员遵循权威为本的实践使得矫正工作难以形成“专业槽”,从而有效地应对犯罪人这一特殊群体。总之,循证矫正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重视实验结果,以“量化”的方式选取最佳矫治项目。
论者认为,无论是建构主义模式的矫正还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循证矫正模式都有其优缺点。矫正的建构主义理念重视反思的重要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罪犯矫治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我们需要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行动来帮助人们突破既有的矫治惯性,提供工作人员解放和矫正转型的方向和动力。实际上,我们对循证矫正方法的引进与对传统矫正方式的反思正是利用了建构主义理念。实用主义模式下循证矫正的最大优势在于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选择最佳矫正方案,其决策过程更为客观有效,避免了传统矫正根据的盲目性。循证矫正认识论采取主观抽离的立场,对罪犯矫正采取客观化的分析,其直接目的是获得一种机械的逻辑关系,以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但是这种认识立场和旨趣可能会物化罪犯矫正的作用,过于强化专业知识的等级关系,不利于产生反思与解放的作用。循证矫正最令人担心的是会出现以证据为本的实践过度遵循实用主义下的科学“决定论”。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是建立在误差最小化的经验研究所提供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取向,而不是建立在生理学、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倾向。这意味着“证据”比其他形式的知识对于罪犯矫治更为可信和更为重要。罪犯是生理、心理与社会的融合体,循证矫正可能因过于重视客观因素而忽略了生理、心理的主观要素。实际上自19世纪后期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就已经认识到并明确指出进行理论中立的、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
传统建构主义式的矫正理念与实用主义下的循证矫正理念是一种相互补充与相互借鉴的关系。建构矫正理念重视权威理性,但轻视了客观证据,实用主义矫正理念强调科学实验下的证据,但可能忽略了主观理性在矫正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传统矫正理念的发展思路也印证了这一点。立法与司法对矫正的态度从过去的以定性分析为主到现在对定量分析的重视足以证明,实用与建构两种理念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绝不是中庸的选择,而是以证据为本主观反思的结果。
二、矫正主体之比较:管理型VS学员型
(一)传统矫正主体:单一性
我国传统矫正主体以监狱人民警察为主,他们主要负责监狱管理事务与监狱日常管理工作。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通过,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矫正主体有所拓宽,增加了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由专业的非狱警人员组成。但无论是监狱矫正主体还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矫正主体的来源方式单一。目前,我国对矫正工作人员选录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军转干部通过招录考试的方式进入;二是普通高等院校或社会人员通过公务员考试招录。上述两种方式本质上都属于考试招录。无论是军转干的考试还是公务人员考试,其试题内容大致相同,主要以考察公务人员的应变、反应与普通管理能力为主。通过历年公务人员考试试题内容可以看出,公务人员所需要的能力是一种先天能力而不是后天培养的能力。这意味着,公务人员的选拔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人才选拔,不具有专业性与行业性。现代化矫正至少需要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管理、职业技术、精神病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现行的矫正主体结构远远不能满足矫正主体系统复杂庞大的需求。
其次,矫正主体的知识结构单一。受选拔方式单一的影响,传统矫正主体的专业知识结构单一,他们多限制于法律专业。军转干人员的作用主要发挥在监狱管理方面,但因受军队管理的影响,其管理作风中难免带有服从命令式的管教,这与矫正改造罪犯的理念是相违背的。招录的普遍化,造就了矫正主体知识的单一化。而矫正主体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罪犯这一简单对象,而是矫正对象背后的心理、生理、社会等复杂的因素。这需要具备严格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的矫正工作人员,而这既需要先天的素质更需要后天的培养学习,但传统矫正领域缺乏知识结构整合的环境与条件。
最后,矫正主体的矫正方式单一。表现在矫正实践中,矫正工作人员组织罪犯实行统一的劳动、统一的学习与统一的思想反馈。随着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虽然现在的矫正措施形式趋于多样化,如增加社会与家庭系统的支持,引进心理学家咨询制度等,但因受人事制度限制与“安全为本位”的社会政策影响,矫正方式的多样化极其有限,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并没有成为制度化的选择。距离遵循“犯因性需求”而制定的个别化矫正措施还相差甚远。
(二)循证矫正主体:复合性
与传统矫正主体相比,循证矫正主体无论是在人员配备结构方面还是在知识构成与矫正方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复合性特征。
首先,矫正主体的配备结构上呈多元化发展趋向。需要原则或者因人施教原则是循证矫正原则中目标干预原则的子原则。⑤该原则要求矫正人员在给犯罪人提供矫正服务时,充分考虑他的个人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犯罪人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性别、犯罪动机、学习方式、事业发展情况等。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到罪犯对不同矫正措施的反应。上述因素反映到矫正人员方面则要求其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否则很难从中提取有关数据,作为量化的依据。但因专业知识的分工限制,“万金油”式的工作人员无法应对这一庞大的矫正任务,只能吸收不同行业专业的人员参与。从实行循证矫正的域外国家实践来看,矫正主体配备已基本实现行业的多元化。如从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墨西哥、菲律宾、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哥伦比亚、意大利、韩国、瑞士、智利等15个国家的矫正工作人员的分类和比例配置来看,矫正工作人员有明显的科学分类,专业化分工明显,凸显矫正功能。⑥
其次,矫正主体的知识构成上呈交叉发展趋向。传统上矫正人员单一的知识结构难以满足循证实践模式下的矫正工作。循证矫正模式下的矫正人员知识构成呈交叉发展状。对矫正工作人员而言,交叉知识的储备有利于他们应对罪犯的复杂情况,提高迅速做出矫正措施决定的能力。矫正员工的交叉知识技能的培养是循证矫正干预原则的要求,它不仅有利于罪犯本身的矫正改造,还有利于减少罪犯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可以减少员工因伤病及情绪等导致的缺勤率,提升管理中的整体关系。⑦
最后,矫正主体的矫正方式呈复杂化发展趋向。强化内在改正动机原则是循证矫正基本原则之一。根据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矫正工作人员应以特有的交际方式与罪犯交往,强化罪犯改造的内在动机。实践证明,罪犯改造的可能性受到人际交往的强烈影响。人际交往大体包括语言交往与行为交往两种方式。传统矫正主体一般偏重于行为交往,如组织、管理活动等,这种交往是以一般性的群体与管理事件为媒介的,缺乏交往的针对性与直接性。即使存在语言交往也是以劝说的方式,要求罪犯服从管理。循证矫正中的交往偏重于个体交往,且重视语言与行为上的双重交往。如矫正主体与罪犯的语言交往与行为交往大都带有“劝说”策略因素,这是造成矫正主体与罪犯情感纠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循证实践模式下的矫正要求矫正主体除进行前述交往行为外,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励志性的交往谈话。⑧研究结果表明,励志性谈话技巧,能够有效地促成和维持行为更改的动机。矫正方式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矫正主体选择项目措施的复杂与应用项目的复杂性上。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在熟悉大量的案件库基础上,采集罪犯的个人数据,通过数据库比对选择最佳的矫治方案,这与传统带有普遍性的矫正方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矫正方式发展的复杂化趋向明显。
(三)简要评析:管理型VS学员型
我国传统矫正模式将矫正主体定位为管理人员,与罪犯形成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上位与下位的关系。这一偏差性定位对矫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首先,管理地位容易给矫正人员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优势,罪犯处于“无知”或“弱知”的劣势地位。矫正工作人员的管教先验地成为指导理论或者是正确的规则,罪犯没有怀疑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矫正工作人员管理地位的确定将矫治的双向行为异化为单向行动。其次,矫正人员管理地位的确立容易强化司法行政本位思想。在以管理为指向的矫正环境中,矫正人员的地位被制度化地层级化。矫正措施的选取以管理者指令高低为标准,而不是矫正实践的需求。最后,管理地位的确定,不利于实现矫正人员的个人价值,阻碍了矫正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矫正人员管理定位的环境下,矫正人员成为命令的执行者,而不是矫正的实施主体,其工作业绩的衡量标准是对命令执行的好坏而非矫正的有效性,这会压抑矫正人员的创造性,不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
相较于传统矫正主体的管理型定位,循证实践下的矫正要求充分发挥矫正主体的创造性,其矫正措施或项目必须来源于罪犯个体,来源于科学实践。矫正人员配备和知识结构上的交叉与复杂化要求至为明显。这决定了循证矫正主体属于专业式的学员型而非“万金油”式的管理型。循证矫正主体的学员型特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学习科学的矫正方案。循证实践视野下的矫正措施带有极强的科学性、专业性特点,可以说矫正人员的后天学习能力成为循证矫正成功与否的关键。如对于认知行为治疗方案,必须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操作。为了成功地向罪犯提供这种治疗方案,工作人员必须了解反向思维能力、社会习得能力,学习适当的沟通技巧。矫正工作人员通过运用这些技能能够正面强化罪犯所产生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⑨其次,矫正组织的培训与评估促使他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学习。在循证组织看来,循证矫正员工成为非常关键的资源,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左右项目的成功与失败。员工具备的沟通能力对矫正项目的持续力与效果性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有关治疗的矫正项目中,1/3的罪犯“变化”与员工和罪犯之间的关系有关。(11)矫正员工的培训内容涉及科学的矫正方法、数据库的管理与使用、人际沟通技巧及其他专业知识的培训等。此外,为提高循证矫正的效果,矫正组织会定期评估矫治工作人员的态度、知识和技能,从侧面督促矫正员工的学习。其评估内容包括以宏观与个人的不同层面的评估标准,分别评估其文化信仰、识别错误观点的能力、交际官的交际能力、认知行为治疗小组的执行情况,对案例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能力等等。(12)
管理型与学员型两种矫正主体相比,学员型的矫正人员制度更为可取。学员型矫正人员制度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我国传统管理型矫正人员造成的矫正缺陷。首先,有利于拓宽矫正人员的来源渠道。其次,有利于专业化整合,提高矫正人员整体素质。我国传统矫正主体的管理型地位来源于建构主义理念,并受制于当前的人事制度安排,很难突破体制性围城。循证实践很好地满足了矫正刚性内在需求,能够深度推进专业化建设,从技术层面上助推当前监狱民警专业化建设。最后,有利于实现矫正工作人员的个体价值,间接推动监狱人事体制的改革发展。循证实践下的矫正工作都是建立在真实案例、科学实践基础之上的,只有对它们进行系统学习、熟练掌握才能进行准确的分析,得出权威的结论,提出高水平的矫治方案。在循证矫正模式的技术性需求催逼下,知识成为矫正的主宰,同时成为量化矫正主体工作成效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发力于内部的技术、知识的协调与充盈能够瓦解传统矫正厚重的组织层级观念,将矫正人员从简单执行命令的“大锅饭”式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不单能体现真正的工作价值平等观,还为狱警的专业化队伍建设注入了活力,成为监狱人事体制改革的间接推动力量。
三、矫正模式之比较:阶段性VS一体化
(一)传统矫正模式:分段与流水
在监狱或社区矫正机构中接受矫正的罪犯大都经历了如下刑事司法过程或阶段: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审判与执行。上述阶段对犯罪个体而言是一种连续的过程;对刑事司法主体而言则是一个分段过程,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法官及行刑人员分别负责各个阶段的刑事司法活动;对刑事诉讼程序设计而言则是一个流水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的接力过程。但从设置刑事诉讼与刑事执行的最终目的来看,刑事司法流程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为所有的诉讼活动最终目的都在于能够改造罪犯,而不是单纯地实现某个阶段的任务。这里的“连续”有着特定的含义,将其看成是一种“衔接”可能更为贴切。刑事司法各环节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环节的增多,这种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形成的合力越来越大,矫正环节将是合力爆发点,所有前续环节积蓄的有利于改造罪犯的因素与力量都集中于此,这是刑事司法制度都应该具备的一种体系。但从我国的刑事司法整体体系来看,远未达到上述程序标准要求,诉讼阶段分化有余,过渡衔接不足。这突出表现于传统分段化的矫正模式中。
首先,矫正阶段与行刑前阶段分化严重。对罪犯的改造矫正并不限于纯粹的行刑阶段。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就有义务教育改造罪犯。特别是随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建立与施行,对罪犯教育改造的关注比例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对惩罚犯罪的关注比例。但司法实践对行刑前程序的教育改造精神的贯彻并不彻底。这表现在司法人员在诉讼阶段上的脱节。这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司法实践中的原因。如,一般情况下,侦查机关是首先接触罪犯的刑事司法主体,他们掌握着罪犯的第一手事实资料,熟悉罪犯的家庭及生活、工作情况,但后续的审查起诉及公诉阶段由检察机关接手。与国外检警一体化的刑事司法体系相比,我国的检警关系过于松散,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控制度过低,这导致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掌握基本上来源于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囿于案件事实与程序法规定的限制,侦查机关掌握的一大部分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事实材料并不会上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与侦查机关的做法类似又将省去一部分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事实材料。呈现于法院面前的只有与案件事实紧密相关的事实材料。这些事实材料作为定罪的材料一并移交给行刑机关。上述事实材料对定罪量刑已经足够,但不能满足改造罪犯的需求。公安司法机关不移交的有关罪犯的其他事实材料可能更有利于改造罪犯。这种情况受我国特有的“侦查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影响,形成司法实践中的“侦查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司法机关是吃饭的”流水作业情况,导致后续程序对前续程序的制约乏力,程序衔接不力,影响罪犯矫正效果。
其次,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衔接不畅。社区矫正的对象很多来自监狱机关。从相互影响上看,监狱的矫正效果会对社区矫正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社区矫正效果亦会间接辐射到监狱中的行刑。如作为社区矫正载体之一的阳光中途之家进监教育基地建设是前延式帮教的重要方式。它不但有利于缓冲服刑人员监狱化与出狱后社会化之间的冲突,还有利于对监狱管理者产生间接性的甚至直接性的教育改造手段的影响。从监狱方面看,监狱对服刑人员的了解是比较深刻的,特别是在对其犯罪悔改态度上,有很大的发言权。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方式与改造效果都将会对社区矫正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为此,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材料的转交与说明对社区矫正机关深刻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至为重要,但两机关之间的衔接存在很多困难。监狱机关对阳光中途之家进驻监狱机关的行为持排斥态度,社区矫正的理念有别于监狱矫正,两者的矫正契合度不高。从矫正工作人员方面看,监狱矫正人员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基本脱节,他们虽同属于司法矫正机构,但人事财政安排相对独立。这导致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之间泾渭分明,其物理界限是监狱机关的看守大门,罪犯出狱之后完全交由社区矫正机构。这种阶段式的任务完成制度直接影响到对罪犯的矫正效果。
最后,矫正完毕标准代替了回归社会标准。一个事物或者一项制度都有一个终结的标准。或者出于工作的简单性考虑,或者出于理念上的误差认识,以往对制度或者工作都有一个结束性的标志认识。如监狱矫正制度,其改造好的标准是罪犯正常服完刑期。对于社区矫正改造完毕的标准稍高一些,一般情况下,“特殊群体”在心理恢复正常,特别是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或者服刑人员和一些机关签订的一些合同、约定已经终止,行为人不需要再去遵守特殊的义务时,就认为改造完毕。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真的可以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特殊群体”在回归社会之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社会。传统矫正中把“回归社会”这一终极改造标准替换为“阶段工作任务完成”标准,是对矫正改造这一神圣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工作阶段式的完成极不利于巩固改造的效果。换言之,对特殊群体的改造、关怀不应划分出清晰的界限,哪里有需要,哪里就应有阳光。特殊的回访、走访及善后服务制度的构建是罪犯矫正制度的当然组成部分,将行刑的“改造功能”向后延伸至“特殊群体”的回归生活,才能真正实现理想中的罪犯回归,以解后顾之忧。
(二)循证矫正模式:过渡与衔接
循证矫正以最佳证据为基础寻求改造罪犯的最佳矫正措施,证据与矫正项目的目的最终性与一致性能够有效链接矫正的前延与后伸阶段。目标干预原则是循证矫正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干预度是其子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提供适量的矫正服务、亲社会结构和监督是刑罚资源的一种战略性应用。实践证明,对于在释放后最初的3到9个月期间,矫正服务和监督应该更为深入。某些特殊的罪犯,如严重的精神病或者慢性综合病患者通常需要计划性的、广泛的和延伸性的矫正服务。证据证明,不完整或者不协调的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往往浪费司法资源。(13)可见,循证矫正措施的过渡性或者连接性特征是由证据要求的矫正项目措施这一内在需求决定的。从国外的循证矫正实践来看,矫正衔接对象趋向于向后延伸,即注重社区矫正、社区回归等方面。
循证矫正理念将监狱矫正定位为罪犯回归社会的过渡或者准备阶段,而非矫正的终点。这意味着矫正的任务不仅仅是监狱安全、有序、稳定等程序的运行,更为重要的是为罪犯真正回归社会做更好的过渡准备,从而真正提高公共安全。将监狱定位为罪犯回归的过渡阶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在美国每年约有60万罪犯从监狱中被释放,其中有42%的人又重新回到了监狱。(14)但当监狱服刑的罪犯被释放到社区进行监管时,监狱矫正项目和社区重返计划之间有连接时,重新犯罪率将大大降低。(15)另外,有实验证明,监狱中减少违法项目措施适用于社区中对于减少罪犯也非常有效。(16)社区矫正机构作为罪犯回归社会的进一步的准备程序,特别重视与社区及监狱之间的合作与沟通。社区矫正机构可以为监狱提供罪犯在社区停留的参考时间,这有利于监狱内部的分类矫正制度,为进一步细化操作假释制度提供了条件。当对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时,监狱机关可以参与社区矫正,并向社区矫正机构提供罪犯服刑情况及其风险情况,以提升大众安全的系数。
循证矫正的有效性根源于对罪犯的动态矫正符合罪犯回归社会的自然路径。循证矫正在重视后续延伸监督矫正服务时,并没有忘记矫正改造的前续延伸,且其前续延伸的触角已经远远超越了整个刑事司法流程,将一切与罪犯矫正有关的机构与治疗项目措施连接在一起。如对于某些患有吸毒或属于长期的职业犯罪者,他们在被纳入刑事司法程序前,就已经与心理健康及戒毒机构有着重复的联系。循证实践下的矫正要求这些机构之间的整合与协调,特别是针对标准化的评估和项目规划与各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能够显著提高矫正改造他们的效率和效果。循证矫正技术的刚性需求与最佳证据或项目的内在需要推动了各机构、人员之间的自然衔接。技术推动下自然产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各个部门之间的员工可以相互分享他们的最佳做法以帮助其他的员工和合作机构,有效提高了矫正改造的整体性效果。
(三)简要评析:阶段性VS一体化
我国传统阶段性的矫正模式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行刑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难免受到刑事司法制度整体性设计的影响。崇尚权威、信任权力的历史传统造就了刑事司法体系内部权力分工有余、制衡不足的局面。《刑事诉讼法》先后经过两次修改,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方向亦可看出,传统刑事司法对国家权力的重视与信任。此法历经两次修改后,权力制衡不足的现象有所改善,诉讼程序的阶段性特征有所减弱,但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典型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相比还相去甚远,加之司法惯性作祟,权力相对独立的现象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程序的阶段性特征依然会成为削弱刑事司法体系整体性效应的重要因素。
现行的“审前社会调查”、“人格调查”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刑事程序之间的距离,但因受“定罪量刑”目的的限制,其对罪犯的矫正改造影响并不大。随着社区矫正、阳光中途之家等与罪犯矫正改造休戚相关的制度设立,罪犯矫正改造的后续延伸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但距离弥合彼此之间的缝隙还有一定差距。这不仅仅是因为矫正理念不同造成的冲突障碍,还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人事制度安排有着重要的关系。因缺乏实质利益导向,矫正工作人员的价值与利益无法从矫正衔接中体现出来。况且,所有上述制度安排对矫正罪犯来说“打的都是外围战”,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作用有限。传统的罪犯矫正制度若想获得实质性的变革,必须寻求一内在的突破力量,产生“化蝶”式的转变。
循证矫正虽不能说是万能的矫正改造方式,但对于我国传统阶段性的矫正模式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该矫正模式的根本性力量来源于内在的连续性矫正规划方案。以监狱矫正和社区干预为例,在监狱中启动的项目会延伸或者扩展到罪犯释放期间。在某些案例中,社区矫正项目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但必须借助监狱矫正项目中的精确评估。同样,如果对监狱和社区矫正进行完整的评估,就必须使用一个共同的规划模型或者相似的模型。监狱和社区矫正项目的结合,可以保证互相分享最佳实践并共同面对为提高矫正效果所面临的挑战。循证矫正方案的连续性还体现在项目建设的一体化方面。罪犯评估是循证矫正中的基础性内容,而项目中的评估种类与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评估,只有两种评估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时,才可以将评估结果作为矫正的证据。
上述寻求证据的严格性是由评估结果的体系性作用决定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评估结果的结合,不仅仅是作为矫正的根据,还具有强化案件裁定正确性、加强矫正工作人员与罪犯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工作关系的作用。(17)“最佳证据”或“优势矫正项目”成为矫正罪犯的根本性指导方针,它内在地需要整合所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以提高矫正的效果。对于罪犯回归社区之前,循证矫正项目的监管人员必须事前了解社区的情况,掌握所有可能诱发犯罪的情形。研究表明,针对诸如综合症患者、滥用药物等高危人群,获得他们的家庭支持或者其他直接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参加者的支持,都有利于正面地巩固矫正改造的革新行为。(18)总之,循证矫正实践有效地将所有的社会资源整合在一起,使他们在自我协调的限度内形成合作团队共同为矫正罪犯、提高公众安全而承担责任。这种整合以“证据”为主线,以共同的基本原则为链条把缓刑、假释、监狱、社区及回归社会连接在一起,将定罪、量刑与行刑连接在一起。循证矫正自觉运用系统论理论,在有效整合系统各要素的基础上,利用并提升系统的功能,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服务。
四、结语:矫治范式转换对现代矫治模式的挑战与应对
(一)循证矫正的启示意义:矫治范式的变革与转换
传统的矫正模式与中国的刑罚模式如出一辙,遵循着相同的范式即单线推理模式,其主体由国家与犯罪人构成。传统矫正遵循演绎单线推理模式,其表现形式是以既定的原理与规则适用于案件进而得出结论。上文述及的传统矫正建构主义理念正是演绎式思维的具体载体或表现方式。
单线式矫正推理的缺陷在于该范式的简约化,换言之,“在单线式推理下,人们的认知来源于不证自明的原则,这些原则具有不可再分性,其推理的结果则来源于演绎,具有不可置疑性”。(19)传统矫正遵循既定的理论将复杂的矫正事实进行极大地简化,抽掉了复杂的犯罪心理、犯罪事实、行为动机等细节,只关注其中的某个部分。但事实上,被演绎推理扔掉的东西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至为重要。罪犯矫正改造兼具事实性或描述性与规范性特征,单线思维模式偏重于规范性特征,忽略了事实性特征。单线式推理矫正模式不可避免地把犯罪解释为单一的原子式的原因,而实际上犯罪的原因非常多,既有复杂的个体因素,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传统矫治的单线推理范式的具体表现是矫治的角色以主客观两分法的方式确定为国家与犯罪人,国家扮演主角,罪犯扮演配角,且处于被动地位。此矫治体制强调国家权威,并赋予国家抽象利益以优先地位。该推理当然地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的侵犯,对犯罪的治理同样是国家的事情,忽略了其他对矫治罪犯的有利因素。
循证矫正与传统矫正相反,它从个体出发,不放过任何致罪因素,寻求所有有利于矫治罪犯的良方。循证矫正一改传统演绎式思路采用归纳式推理,从个体中累积矫正证据,并形成案例库,以指导矫正工作。循证矫正与传统矫正最大的区别在于矫正的起点不同,偏重于罪犯矫正中的事实要素。循证实践模式下的矫正赋予国家与犯罪人平等的主体地位。为增加数据库案例,实现其最佳证据、最佳方案的选择,循证矫正会力所能及地关注所有有利于矫正罪犯的因素,突破了传统演绎式的矫正惯性思维。但需要指出的是,循证实践矫正思路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该模式就是完美的罪犯改造制度。从其研究的思路来看,也没有超出单线推理范式范畴,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角度的改变。正如Erik Luna教授所言:“归纳和演绎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单线式推理,不管是从法律总体演绎推理出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还是从个别观察实验归纳出法律总体,其推理方式都是单线的,要么是从总体到个别,要么是从个别到总体”。(20)为此,不宜夸大循证矫正的作用,其单线式的推理思路仍然会受到主客观二分法的根源性缺陷限制。但循证矫正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意义不容忽视。
论者认为,循证矫正从个体到全部及体系化的研究与矫正思路拓宽了我们传统的矫正视野,让我们认识到,对于罪犯的矫正改造,不但可以定性分析还可以定量分析,不但要重视国家权威,更要重视罪犯及社会力量,不但要重视阶段内的改造还要重视阶段内的准备与衔接,不但关注私人领域还强调公共领域,不但关心生活世界还重视社会系统。循证矫正的归纳式推理与传统矫正的演绎式推理的糅合将带动矫正制度质的飞跃,带来研究与实践范式的转换:整全式的逻辑推理。整全式的推理在重视规范价值时不否认事实价值,它以求同存异的方式生存。无论是国家抑或是个人、社会都可以就矫正改造这一问题发表言论,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理论与实践。在整全式的逻辑范式下,没有权威的理论,其理论的有效性是通过“共识”的方式产生,认可在具体情境下的各种价值。(21)由传统单线推理的矫治范式转向整全式矫治推理并不是论者的片面结论或主观意愿,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是矫治改造事业循序渐进的结果。它的出现必将带动我国矫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升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水平。
(二)循证矫正的生成根源:矫治环境的反思与完善
循证矫正的宗旨在于寻求更好的矫治方案,这种思想来源于传统矫正领域中的变异思维。自犯罪与刑罚开始之时,就有对罪犯矫治改造之说。但千百年来的矫治结果却是罪犯越改造越多,这自然与社会、刑法的变迁有关,亦与矫治模式的效果有着莫大的联系。人们开始探求新的或者更加有效的矫正方法,为了防止进入主观主义的泥潭,人们设置了“证据”这一门槛,以证据证明矫正效果是否有效。可见,循证矫正起源于人们对传统矫正的一种变异思考。遵循这一变异思路,我们对传统的矫治制度的反思已经足以成熟到需要引进新的矫正方法吗?
现有的矫治制度框架是建立在行刑司法行政体制之下的,几乎所有的罪犯矫正都是以行政运作的方式存在。行政运作的典型特征是从上而下,权力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循证矫正则是从下而上,从个体到国家到社会的思路,这意味着若根本性地引进循证矫正制度有必要从下到上地瓦解现有的矫正运作机制,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论者认为,有必要将矫正改造的行政运行方式转变为司法运作模式,这不但有利于减轻行政领导的负担,还有利于形成矫正平等主体的环境,为开展循证矫正打下良好的基础。
无论是教育刑理论还是劳动刑理论与实际的矫正改造之间的关系脱离太大,不论是何种矫正理论,其矫正效果大都一样,表现较差。面对这种现实,人们将矫正失败的罪魁祸首推向理论的不可靠及与实践的脱节。以证据为本的矫正适当缩小了矫正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循证矫正模式下,所有的理论都需要“证据”来检验,而所有的“理论”又来源于“证据”的积累。我们传统的矫治理论来源丰富,有领导人的口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专家学者的独创,还有域外的各种混杂理论。但矫正实践与这些理论的关系并不太紧密,没有呈现出如国外式的矫正实践随理论的改变而左右摇摆现象。我国的矫正实践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同时提醒我们,循证矫正理论的引进并不能一定在实质上影响传统的矫正制度,必须将循证矫正的具体做法糅合到传统矫正中,才真正有可能引进这种理论。这不单单需要实践的努力,更需要改变现行的理论教学现状:以国外理论的教授为形式,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否则注定会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甚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的现象。
循证矫正根源于一种道德诉求。(22)传统矫正建立在道德权威与规范权威上,这种矫正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帮助还多。从矫正对象角度来看,他们有权利知晓自己被矫正的方式、矫正的效果及与其他矫正效果相比产生的优劣情形。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更多地关注服刑人员的利益,相应地增加了矫正人员的道德义务,他们必须寻求对罪犯的更加有效的方法,否则可能会违反自己的伦理职业道德。道德虽然不是一项规范,但它是衡量人性价值的重要筹码。道德价值与体现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有个体因素、群体因素,也有国家因素、制度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制度性的指引,道德虽然是个体范围内的事情,但更与集体与国家相连,道德就如信用一样需要制度的维护与指引。在矫正领域更是如此,将矫正人员的工作神圣化与道德化,利于避免出现矫正人员将矫正仅仅看做是一种工作的现象。
(三)循证矫正的可能担忧:矫治模式的继往与开来
自有循证实践以来,理论界对它的批评之声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论者认为,循证矫正本身也存在一些值得令人担忧之处:首先,以证据为本的矫正对证据的定义过于狭隘,可能排除了某些重要的信息。循证矫正对证据进行分级,如它赋予随机试验的证据最高的证据等级。但问题是,随机控制实验和元分析并没有显示出比其他研究方法更为可信。以证据为本的矫正对可以回答的问题是有限的,它排除了一些其他形式的、非统计学意义上的但重要的矫正信息。其次,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本质上并不是以证据为本的。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是循证矫正的假设起点,但这样的假设起点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循证矫正工作人员虽然致力于将矫正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但实际上没有发现有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所界定的那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再次,循证矫正对个别矫正对象的作用是无效的。循证矫正以统计学为分析工具,以案例库为基础,试图在多样本的基础上寻找一个矫正群体的平均行为或者某种趋势。但问题是,矫正人员经常缺乏具体的对应的罪犯介入有关研究。罪犯是个人,并不是群体,对于单个的罪犯而言,没有所谓的“平均趋势”。甚至有学者坦言:“循证矫正是实践一条不完整的途径,他的基础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对真实的世界存在着片面的或者潜在的误读。”(23)最后,循证矫正忽视了个体价值,削弱了个体的自主性,将科学价值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在循证矫正制度下,一切矫治方案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据基础之上的,降低了罪犯与矫正工作人员自主作出决定的数量。当循证矫正越来越被科学所驾驭时,很可能会超出人的控制,演变成为奴役人类的异化力量。人的自主性与人文价值可能会丧失在对实践技术化的追求中,最终使得科学价值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
由上观之,以循证矫正代替传统矫正的替代主义做法是不可取的。论者认为,循证矫正给予我们的启示意义远远大于其给予我们的具体做法。以单线式推理范式向整全式推理范式发展为基础,在吸收循证矫正有益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矫正的定性分析优势,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矫正制度进行体系性整合。首先是信息的体系整合。这需要做到在矫正机构内所有的罪犯矫正信息能够实现实时共享。在矫正工作人员层面,应该建立起矫正信息系统平台,完善信息搜索引擎系统;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制度化地疏通矫正信息流入和流出通道,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共享、共用;在专家层面,构建矫正专家信息库,对矫正行业进行信息化管理。其次是机构体系的整合。整全式的矫正范式需要各机构、各部门的自然流畅衔接。对于监狱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公安司法机关及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除应以外部力量的方式推动各自的互动与衔接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在内部建立常态联系机制,制度化地引导各机构之间的对接。最后是专业人员的体系整合。传统上,机构之间的专业人员流动性不强,影响了工作效率,不利于矫正效益的提高。整全式推理范式要求建立专业人员交流的常态化机制,以实现不同专业人员之间有益信息的共享,并推动各专业人员的创新意识,同时通过改变工作环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实现其人生与工作价值。
注释:
①Roger K.Warren,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Reduce Recidivism,Implication for State Judiciaries,Washington,DC,U.S.Dept.of Justice,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p.59,2008.
②Jayaratne,S.,& Levy,R.,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58,1977.
③Witkin,Stanley,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A Critical Analysis,Social Work,vol.36,2(1991):158-163.
④Hayward A.Alker,Rediscoveries and Reformulations:Humanistic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96,1996.
⑤循证矫正的8个基本原则分别是:Highest Risk Offenders.Correctional agencies should provid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programming to their highest risk to reoffend prisoners and parolees first.Provide other types of programs to low risk to reoffend prisoners or parolees.(使用精算工具对犯罪人进行危险评估原则);Assess Offenders Needs.(强化犯罪人动机原则,该原则又包括罪犯内在动机的程度与动机和机构内违法行为和再犯之间的关系等内容);Design Responsivity into Programming.目标干预原则,该原则内容又具体细化为风险原则、需要原则、回应原则、剂量原则及处遇原则等;Develop Behavior Management Plans.技能培训原则;Deliver Treatment Programs using Cognitive-Based Strategies.正面强化原则;Engender the Community a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Recidivism and Use the Community to Support Offender Reentry and Reintegration.自然社区持续支持原则;Identify Outcomes and Measure Progress.过程考核原则,考核反馈原则。See Evidence Based Correctional Practices,Prepared by Colorado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Office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Based in part on material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www.nicic.org),August,pp.1-69,2007.
⑥田越光:《德国监狱的安全秩序保障措施》,载《中国监狱学刊》1997年第5期;李豫黔、赵洪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第9届年会》,载《中国监狱学刊》2008年第2期;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代表团:《哥伦比亚、智利监狱管理情况》,载《中国监狱学刊》2008年第3期;张金桑、白焕然、石少刚:《瑞士监狱制度简介》,载《中国监狱学刊》2006年第1期;李静:《日本矫正制度概况》,载《中国监狱学刊》2007年第3期;王恒勤:《澳美监狱制度概况与借鉴》,载《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王戌生:《墨西哥、菲律宾监狱制度概况》,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4期;李豫黔、张高平、赵洪奎:《西班牙、加拿大监狱管理体制及刑罚执行制度概况(一)》,《中国监狱学刊》2005年第6期。
⑦Rice,M.E.,Hams,G.T.,Varney,G.W.,& Quinsey,V.I.,Violence in institutions:Understanding,prevention,and control,Toronto:Hans Huber,p.230,1989.
⑧R.Harper and S.Hardy,An evaluation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s a method of intervention with clients in a probation setting,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30(2000):393-400.
⑨M.W.Lipsey and D.B.Wilson,The Efficacy of Psychological,Educational,and Behavioral Treat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vol.40,(1993):1181-1209; J.McGuire,What works in correctional intervention? Evid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Offender rehabilitation in practice: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effective program,pp.25-43,2001.
⑩Serin,R.C.,Expanding the "What Works" agenda for effective corrections:The role of correctional staff,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rrection Monograph,No.8,(2003):2.
(11)Lambert,Psychotherapy outcome research: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ve and electrical therapists,In J.C.Norcross,& M.R.Goldfried(ed),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New York,NY,US:Basic Books,Inc,pp.94-129,1992.
(12)Andrews,D.A,Personality and Crime:Knowledge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Criminology,Justice Quarterly,No.6,(1989):291-309.
(13)P.Gendreau and C.Goggin,Principles of effective correctional programming with offenders,Center for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New Brunswick,p.59,1995.
(14)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1,August 28,Probation and Pa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Release(NCJ 188208).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Justice,p.98,2000.
(15)Broome,K.M.,Simpson,D.D.,& Joe,G.W.,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following short-term inpatient treatment,The American Journal on Additions,p.156,2002.
(16)French,S.& Gendreau,Safe and Humane Corrections Through Effective Treatment,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Research Report RR-139,pp.126-129,2003.
(17)D.A.Andrews,J.Bonta,and R.Hoge,Classification for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Rediscovering psychology,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Vol.17(1990):19-52(1990).
(18)J.Bonta,S.Wallace-Capretta,J.Rooney and K.McAnoy,An outcome evaluation of a restorative justic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Justice Review,No.5(2002):319-338.
(19)Erik Luna,Punishment Theory,Holism,and the Procedural Concep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Utah L.Rev.205(2003):261.
(20)Erik Luna,Punishment Theory,Holism,and the Procedural Concep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Utah L.Rev.205(2003):261.
(21)同上注,第272页。
(22)Macwilliam,S.,Maggs,P.,Caldwell,A.,& Tierney,S..Accesing Social Care Research:An Introductory Guide.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Social Services,University of Exeter,p.89,2003.
(23)见前注(2) Liz Trinder,Shirley Reynolds,p.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