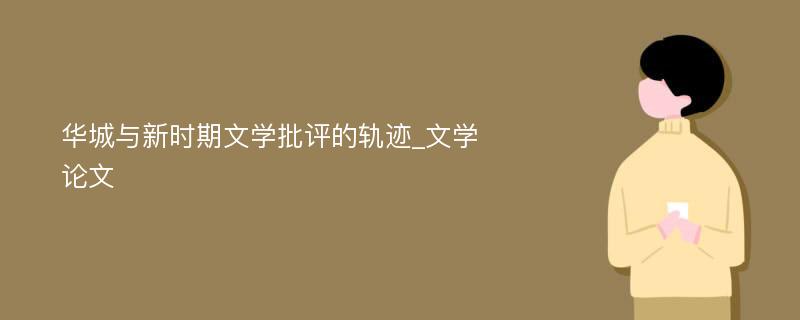
《花城》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踪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城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踪迹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当下的热点到《花城》的文学批评
《花城》历来作品与批评并重(据笔者统计,从1979年创刊到2010年,《花城》共发表理论批评文章527篇),为当代批评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对先锋文学的转型、后现代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研究、第三种批评、新生代作家论、先锋作家论,等等,这些都是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具体而精准的把脉。其实,《花城》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纯文学刊物所能做到的。国外小说评介、作品争鸣、当代作家论、当代作家访谈录、笔会笔谈研讨会,等等,成为《花城》长期以来的重头戏,刻下了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鲜活而真实的轨迹。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评论家的文章,成为考察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比如陈晓明、程光炜、赵毅衡、欧阳江河、谢有顺、张柠、朱大可、王一川、陶东风、南帆、汪民安、王岳川等人的批评文章,尤见笔力。开创性、先锋性、统摄性、前瞻性、精确性,构成了《花城》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品质。
《花城》70年代末推出高行健的作品及其系列批评文章,而且推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影响是无需多言的。1979年4月曾敏之在《花城》创刊号上发表《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最早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而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成显学。推举很多有潜力的作家,如周梅森、残雪、陈染、林白、毕飞宇、海男,等等,不仅发表他们的作品,而且跟踪评论,举办研讨会。《花城》多年来一直推出年度小说综述文章(新世纪以来,这个栏目消失,颇为可惜),以及国内小说述评,作者多为国内知名评论家。年度作品述评,对促成自身的编辑导向与文学潮流的推进,加强创作的理论研究,都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对当代作家进行综合性研究,先后发表的作家论有:乔雪竹论、赵大年论、周梅森论、赵本夫论、刘绍棠论、蒋子龙论、李杭育论、路遥论、苏童论、史铁生论、王朔论,等等。《花城》与作家联系密切,除多次举办有重大影响的笔会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还开辟作家访谈专栏,以促进作家、创作、批评、理论的多方互动,访谈对象先后有:苏童、格非、韩东、朱文、陈染、林白、北村、史铁生、叶兆言、莫言、刘恒、邱华栋、刁斗、李冯、迟子建、海男、徐小斌、李大卫、东西、李洱、荆歌、行者、潘军、残雪、毕飞宇、墨白、吕新,从名单足见其分量。2000年以来,还发表不少外国作家的访谈录,其中以俄罗斯重要作家为主。此外,2007年开辟“作家书信”栏目,2008年开辟“作家讲堂”栏目。新世纪以来,又设海外汉学家访谈栏目,以推进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互动。《花城》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极有担当的,可谓时刻保持着关注的力度。1996年第1—3期,连载《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一)、(二)、(三)》,参与者有:王蒙、史铁生、耿占春、墨哲兰、余虹、刘康、张闳、萌萌、蔡翔、陈家琪、赵毅衡、陈晓明、南帆、张颐武、李小山、曲春景、汪政、晓华、王干、吴炫、李陀、王鸿生、戴锦华、程文超、王安忆、鲁枢元、葛红兵、李陀、张柠、艾云、王光明、李森等数十位批评家,这对认识、反思与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花城》的文学批评几成范式。可以肯定的是,《花城》结合了学术与批评的各自优长,结合了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历史和传统,结合了当下的现状和潮流走向,从而使批评的有效性与力量得以生成。下面通过考察《花城》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以期打开一个窗口,来追寻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踪迹,并对当下批评的反思与重建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渐行渐远
建国后数十年来批评的沉疴,惯性地影响到新时期初期的表现。《花城》自创刊至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性依然浓厚,素以先锋性著称的《花城》,也概莫能外。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面目?它又是如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的?《花城》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证。
(一)意识形态化批评的余音和批评新质的初显
《花城》创刊阶段的批评是之前余音和新质混生的。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及其过渡时期的语境。
“我们知道,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培育香花、铲除毒草,而除草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繁花的开放。……”(于鸿舒:《胸怀·题材·批评》),这仍然是“文革”时期的语气。黄药眠在《科学技术发达对文艺的影响》开篇写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要于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强国。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这一时期的批评仍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后的狂喜之中,处在继续的政治批判之中,基本上沿用了惯用的毛语体,属当头一棒式的口号式批评。不过,《花城》一边沿用之前的政治话语模式,一边开辟新的批评领域。“外国文学”译介、“香港通讯”一类栏目的异质性就相当明显。二者并存并交错的情形,实际上存在于《花城》试刊阶段的前七期当中。
总第2期苏晨的《有边的遐想》道出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弊端。胡德培的《悬念与艺术的活力》,已不再浮于文本之外,可谓得风气之先。第3期楼肇明《盖棺犹难论定》的阶级论却又十分明显。1980年总第5期艾彤的《文学作品的知识描写》,意识形态基本消失。
1980年元旦前后,《花城》编辑部在北京搞了一次座谈会。沈从文指出:“一个作家,下去生活一个短时间,回来就搞大题目,这未必妥”。陈荒煤提出:“要多团结港澳作家,发表他们的作品。”刘绍棠说:“文学作品写得不美不行。如眼泪、血,不是不可以写,而是要写得美。”李陀希望《花城》办得洋一点,文艺界不应该有排外情绪,“《花城》要开成一朵洋绣球。”谌容也认为“《花城》还不够洋”。洪子诚更主张“《花城》再洋些,再开阔、深刻些。”刘心武希望“《花城》用适当篇幅发表一些试验性作品”。这些评论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极具远见的,犹如灯塔,直接引导了《花城》对海外及港台文学的关注,以及对实验性作品的重视,《花城》的先锋性也正是由此开始打下了导向性的基础。①
总第6期阎纲的《长篇小说印象》,高屋建瓴地对新时期以来几年的长篇小说进行综述,提出“落后了”、“把人当人”、“有了起色”等核心问题,并辩证地分析了“写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以及探索性的作品的可贵品质。总第7期王若望的《说假话大观》:“过去若干年中我党为了维持这面骗人的红旗,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浪费了多少笔墨纸张,真是难以统计”,这已是完全反对意识形态性的批评话语了。
(二)意识形态化批评的反复和疏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花城》走过了试刊阶段,也基本上从以往意识形态性模式中走了出来。但是《花城》几篇带有自我批判性质的文章,使之出现回潮反复之势。
同年第1期杨越在《论当前的文艺口号之争》一文中质疑过去三十年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期发表洪子诚的《论徐志摩的诗》,对于一个曾经“对着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学发出恶毒的啼叫”的现代诗人,作者站在新诗发展史的高度上,肯定了徐志摩在诗歌艺术上的贡献。同期还发表了署名“本刊评论员”(苏晨)的《不断自问——〈花城〉两年》,其“核心观点是我们个人我们政府我们党都要不断自问”②,文章引起很大争议。第2期上发表“本刊评论员”(黄安思)文章《再一次自问》,表态承认《不断自问》“说了一些错话”,要“认真接受这一教训”,“我们搞的文艺,必须首先保证在政治上同党的基本主张完全合拍”。从这两次“自问”,可以看出当时的批评仍是噤若寒蝉而小心翼翼的。1982年第1期遇罗锦的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引起了大风波,“上面意见很大,要求收回,以收回的版权页为准计算退款,刊物在当地封存③。第3期发表蔡运桂的《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评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以进行及时的批判;同期署名“本刊编辑部”(黄安思)文章《我们的失误》指出:“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意识形态性阴魂不散,批评生态相对恶劣。
《花城》的其他举动却又令人欣慰。1981年第2期刊登了《1945—1979有关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欧美博士论文》的篇目,体现了《花城》对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密切关注与历史意识。第6期舒大沅的《关于中篇小说〈你在想什么?〉》,其中提到的人的价值观问题,这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1983年第1期,开辟“作品争鸣”栏目,开栏即为贾平凹的《鬼城》,同期另一个重要栏目为“流派鉴赏”,介绍了魔幻现实主义。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即以魔幻现实主义见长。1982年《花城》在北京召开文学评论家、编辑关于小说创作的座谈会。次年第1期上以12个页码刊登座谈会成果,显出《花城》与意识形态性文学批评的疏离倾向。之后,《花城》也发表相关文章④,指出当代文学及其批评的三个倾向:趋炎附势、机械配合、片面求新。
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发出了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花城》及时表态:“发表过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生产商品化等等倾向的影响”⑤。如此表态可折射出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控制的新苗头。之后《花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极少发表有个性的与有争鸣性质的评论。极有意味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第5、6期,干脆中断了“花城论坛”一类的批评,直到1990年第3期才恢复,但之后也是多次中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92年。
由上观之,如从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之关系来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批评经历了几起几落。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从新时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渐行渐远的,再也不是密不可分。
三、文学“边缘化”之后批评的艰难建构
进入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性日趋淡弱,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批评最多只是作为一元而存在。同时,文学“边缘化”的命运也已不可逆转。文学批评一旦疏离与不再依附于意识形态,则显现出其本应具有的个性和丰富性。学院批评的介入,使理性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批评建构的欲望。其与建国以来的文学批评是大为不同的。概而观之,这种不同表现在:对文学史进行理性的反思,在之前重写文学史的基础上,及时跟进到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现象及其走向的把脉;利用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形成中国式后现代批评,并将之作为一种新方法来评析90年代先锋小说的转型、新写实小说、晚生代作家的创作等文学现象;文化批评的兴起,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视野;如果说90年代是疏离意识形态的,甚至在批评话语体系上是去中国化的,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批评则是再政治化与再中国化的,只是这种“政治化”是以一种介入现实生活为姿态(并非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化”则是以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彰显、“中国经验”作为一种理论被提出为基础的。从90年代试图利用西方话语体系来建构中国式的批评,到新世纪尝试进一步将批评话语本土化的努力,无不是艰难而曲折的,至今我们虽然仍难以对其作出价值判断式的定论,但是我们却无法忽略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样,《花城》的批评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鲜活而浓缩的个案,它清晰而有效地见证了这个发展历程。
(一)先锋小说的转型与90年代文学走向的考察
先锋文学以小说为主,在80年代文学潮流的更迭推进中,具有现代性与启蒙的意味。尽管它披着文学性试验的面纱,但实质上起着终结之前及80年代文学意识形态的作用。90年代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文学的转型,先锋文学的启蒙与现代性迅即涣散甚至是瓦解,从而呈现出后现代性意义上的异质蔓延。文学批评及时而精确地掐住了这一走向,并作出了合理的评析。
《无望的救赎——论先锋派从形式向“历史”的转化》(陈晓明,1992.2)、《先锋派在中国的必要性》(赵毅衡,1993.5)、《边缘:先锋小说的位置》(南帆,1998.1)、《先锋:自由的迷津——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洪治纲,2002.5),等等,《花城》刊出了系列关于“先锋小说”的批评。陈晓明认为“先锋派”小说是“写作不再是去建构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神话”之后的一种“文化救赎”的形式,它在90年代的转型本是不攻自破的,因为“它既不能被上层建筑的权力系统所认可,也不为大众化的日常需要所认同”。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先锋作家们进入90年代后,大多数“在历史的边缘”讲述着“寓言”,并谋求着“复古的共同记忆”,然而,“对虚假性的揭示与对神性的精神乌托邦的祈求,使他们无法与‘真实的生活’相融合”,所以即使是先锋文学转型了,那也只是一种“无望的求赎”。陈晓明及时看到了先锋小说的转型,并预言了这种转型之后的有限性前景。鉴于先锋派在90年代已备受质疑的现实,赵毅衡认为“中国先锋派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文字游戏”,“其目的是保持语言的生命力,保存文化价值”,并能与俗文化相抗衡。赵的文章从另一层面全面而深刻阐述了先锋文学的在中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还指出,先锋派在某种程度上催长了学院式批评,它还能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推出新的文化,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先锋文学作品的解读基础之上的,具有相当的理论建构高度。南帆认为先锋小说是“孤独”的,但是因为“先锋小说的孤独不可避免,孤独时常是自由的重要补充;孤独暗示了边缘文化享有的待遇”。洪治纲的文章,无疑带有总结与前瞻性的意味。他深刻剖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虚浮的思想根基、孱弱的独立意识、匮乏的想象能力、形式功能的退化、市场化的物质屏障、先锋批评的滞后,这些观点的提出极具反思性与建设性,其本身也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艰难建构的努力。
对90年代以来文学、文化、批评走向的考察,《花城》刊出的文章可谓十分丰富。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欲望化叙事、私人化写作、后新时期、晚生代新生代作家批评、第三种批评、中产阶级化、消费娱乐化,等等,都是具体的表现。众多活跃在当代的知名学者、批评家,在《花城》上都发表过很出彩的言论。比如:《“戈多”究竟什么时候来?——从后朦胧诗看八十年来的新诗发展》(王晓明等,1994.6)、《超越情感: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九十年代文学流向之一》(陈晓明,1995.1)、《“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王宁,1995.3)、《碎片中的世界——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散论》(陈思和,1996.6)、《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王蒙,1996.3)、《私人性和相关的社会想象》(蔡翔,1996.4)、《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陶东风,1997.1)、《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吴炫,1997.2),等等。
其中,欧阳江河在长达二万多字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994.5)中要努力阐明的观点之一就是要把“1989年”作为90年代诗歌的起点。此文成为研究90年代诗歌的重要文献,它还成为世纪末“盘峰论争”理论源头与导火索之一。欧阳江河还发表了《文本的变迁》(2009.5),从语言的角度上回顾了中国文学近30年来的变迁,对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历程所做出的高屋建瓴式的宏观考察,这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二)后现代主义批评与文化批评
早在1985年,美国学者詹姆逊在北京大学做了有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系列讲座。有意思的是,当西方正在叹息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时(哈桑,1991),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却正在兴起。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个接受、消化和具体应用的迂回过程,然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却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有着更为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从《花城》90年代以来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文章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摸清中国这一批评路向及其实绩。
《花城》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某些领域的最高成就。比如:《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王宁,1993.1)、《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陈晓明,1993.2)、《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蔡翔,1993.6)、《从单语独白到杂语喧哗——90年代审美文化新趋势》(王一川,1995.4)、《“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赵毅衡,1995.5),等等。王宁把后现代主义理论具体化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变体上来,比如对先锋小说、元小说、先锋诗歌、新写实小说、消费性的“拼凑”文学等都做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论述。在后现代主义批评领域,陈晓明或许是最有分量的一个批评家。他设论的核心围绕着:“当代中国出现‘后现代主义’种种征兆并非是对西方当代文化的简单模仿和挪用,当代中国正处于非常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它汇聚了各种矛盾,隐含了多种危机,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构成的奇特的多边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及其显著的中国本土特征”。针对知识分子的日益平民化与社会的日益商业化,知识分子主体性失落,日常生活的诗性渐然消解,蔡翔都做了细致分析,指出了这种文化现象向传统观念生发出的“挑战性”。王一川则对90年代杂语喧哗的后现代主义审美文化的趋势做出了描述。赵毅衡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出发,提出建立中国文化批判的主体性问题,并拒绝媚俗之路。
90年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中国批评界是自觉的,同时也是有担当的。在混乱与多元格局之中,仍然不失重建中国当代批评的信心,并取得了诸多的成就。
(三)再政治化与再中国化
上文提到,中国文学在进入90年代以后已被边缘化,在文学批评层面,也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既体现了自身主体性的自觉,同时也是追求自身价值和独立性的努力。从宏观上来看,80年代是一个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阶段,90年代是一个多元混杂的理性重建阶段,而新世纪以来,则是一个再次回归政治化与再中国化的新时期,是90年代批评的延伸和发展,同时,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又密不可分。再“政治化”与80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以往的意识形态性是自上而下的裹胁式的结果,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再政治化则是自下而上的诉求式的主动介入和干预。2004年开始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以及近年来由《人民文学》所倡导与推动的非虚构写作,都是文学批评再政治化的具体表现。最近几年所掀起的重建当代文学批评的浪潮,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的实践运动。文学和批评再次干预生活,现实主义的再次推进,文学和批评必须有所担当和责任感,文学的写作伦理追求,等等,都是文学再政治化的新变体。再中国化与“中国经验”作为一种理论的兴起密切相关。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本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范畴,这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性,是与西方道路相对而言的。2007年《芳草》第2期发起“中国经验”的讨论,才正式将这个概念引入到批评话语体系中来。从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现代、当代、当下等诸多因素都抹上一层中国的光晕,显示出将中国的文化迅速融入世界文化并与之对话的迫切心态,这当然也与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而需要相匹配的文化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新世纪以来,中国批评界就一直在为之努力。再政治化与再中国化遂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批评的新气象。
《花城》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批评文章,尤具特色,虽然体系多元、风格各异,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再政治化”与“再中国化”来展开的。
吴炫指出:“在中国即便讲多元,也不太可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元”(《当代现实问题及其美学期待》,1999.4)。程光炜所提到的“文学性”的丧失,拒绝的是“写作日益变成一种超规则的游戏”,反对作家与文化市场的“密谋”(《反对文学性的年代》,2001.2)。张柠把消化、娱乐、商业、肉体经验等概括为“卡通一代”的精神背景,否定了“盲目追逐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消费时尚的狂热”(《中国“卡通一代”的精神背景》,2001.4)。邵建认为“人民”本身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常“给批评家提供居高临下的说话背景”,在这个“后人民”时代,他希望公民(法律概念)社会早日到来(《“后人民时代”》,2002.1)。陶东风、李松岳认为艺术家“在摆脱了工具论的文艺学的统治地位以后,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以后,以自主性为基础与依据的政治参与才成为可能”(《从社会理论视角看文学的自主性——兼谈“纯文学问题”》,2002.1)。朱大可、张闳严厉指责了学院批评,认为它们“制造了大量与公众无法交流的自闭性文本”(《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2002.3)。从不同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现实、文化现实与批评现实的再政治化的批评文章还有:《中国思想的欠缺与无神论世界感情的建构》(葛红兵,2002.4)、《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程光炜,2002.6)、《穿越当代经典——反思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吴炫,2003.1)、《智慧偏至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分裂》(郜元宝,2003.5)、《消费时代的红色经典》(唐小林,2005.1)、《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朱大可,2005.2)、《大话文学·犬儒主义》(陶东风,2005.5)、《平民话语的权力修辞——论博客》(洪治纲,2006.3)、《“后严肃性”与新世纪文学》(张颐武,2008.3)、《“造反文艺”与暴力美学》(张闳,2010.1),等等。
2009年第2期《花城》发表王岳川的《文化走向: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这篇文章带有普遍性意义和总结的意味。出于西方固有的中国只是物质生产大国而不是精神文化生产大国观念的焦虑,中国开始提出软实力输出的构想,这是该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同时也是新世纪以来倡导“中国经验”和再中国化的一个整体趋势。同期发表的另一篇则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批评“再政治化”和“再中国化”的总结性文章,即孟繁华的《文学与批评的镜中之像》。虽然其主体是探讨今天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但其恰恰又构成了再中国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公共论域、公共性问题。
总而言之,近年来所热议的重建当代批评的话题,实质上都是本着“再政治化”和“再中国化”的初衷,显示了中国当代批评界再次回归现实和关注现实的热情,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这种努力前行与重新建构的热情之下,难免出现“灯下黑”的情形。从我的考察范围来看,《花城》的文学批评清晰显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批评的踪迹,虽然其中也难免存在一些因时代语境因素而造成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它却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中国批评界多年来弊端,实现了批评的良性发展,保持了批评的真诚和品位。我们在热切呼唤重建当代文学批评的同时,是否可以认真地回顾、重视和借鉴《花城》的文学批评模式呢?
注释:
①参见《花城》1980年总第5期文章《〈花城〉,愿你增色!》。
②③参见《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范汉生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花城》2009年第2期。
④刘建军:《时代精神——文学当代性的灵魂》,《花城》1983年第6期。
⑤参见“本刊评论员”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办好〈花城〉》,《花城》1984年第1期。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花城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陈晓明论文; 赵毅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