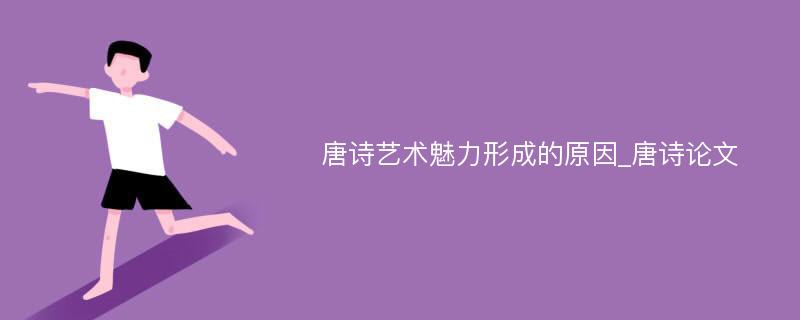
唐诗艺术魅力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原因论文,魅力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诗国”之称,而唐代又是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唐诗数量之多,名家之众,质量之高,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都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并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作为一代文学的标志,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
唐诗一出现,就以其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社会上的各阶层人士,读诗、赏诗、写诗,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不少诗人的诗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衒卖于市井之中”,书写在观、亭、寺、驿的墙壁上,有的还流传至西域与海外,受到少数民族与国际友人的青睐。“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概括。
一千多年来,唐诗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并输注给后代诗人最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今天新诗的创作与繁荣仍然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唐诗的艺术魅力及其产生原因等问题,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唐诗的艺术魅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些古今学者对唐诗艺术特征的阐述中找到答案。
南宋严羽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他又指出唐诗的妙处在于“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
明人胡应麟说:“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诗薮外编》卷六)
清人沈德潜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清诗别裁集·凡例》)
今人钱钟书先生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见胜。”(《谈艺录》)
今人缪越先生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论宋诗》)
将上面种种把唐宋诗进行比较的看法加以归纳、综合,可以看出,形象鲜明,意境浑成,情韵盎然,语言清新,就是唐诗的主要艺术特征,也是唐诗艺术魅力之所在。
唐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于唐诗的作者,而唐代诗人之所以能创作出大量富具魅力的诗篇,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关心现实,热爱生活,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动力,也是唐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纵览唐诗的发展过程,凡是那些有成就的诗人,无不面向现实,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观察、分析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自己最擅长的手法,在诗篇中加以再现。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有为而发,有感而发,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初盛唐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中晚唐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感伤情绪,都是那个时代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由于作者爱憎鲜明,感情真实,手法高超,因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感染人的巨大艺术魅力。现略举数例为证。
李白创作的旺盛时期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前夕,因此,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较多地带上盛唐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富于幻想,勇于进取,渴望建功立业,向往过一种不同凡响而又可以自由享乐的生活。当他在政治上碰壁以后,他对压制人才,扼杀个性的黑暗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时,对实现个人抱负并未完全绝望,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笑傲五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直面人生,追求自由,纵情欢乐等思想感情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作品的风格与基调时而现实,时而超脱,时而农烈,时而谈远,时而恬静,时而雄健,但始终以“飘逸豪放”作为它的主调。我们读《将进酒》、《梁甫吟》、《行路难》等作品时,就会深刻地感触到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追求与痛苦在其中的交织与斗争,就能听到李白那些发自内心的呼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个性色彩与抒情味极浓的诗句,深深地叩击着每个读者的心弦。
杜甫创作的旺盛时期在安史之乱以后,即唐代社会由盛变衰的转折阶段。经过这场大浩劫的中唐时代,各种矛盾更为尖锐,统治阶级更为腐败,人民生活更为痛苦不堪,因而杜甫的人生观中更多地具有转折时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特点:关心国家命运,渴望王朝中兴,又缺乏足够的信心;饱经沧桑,稍有迟暮之感,但政治热情仍未衰退。加上他坎坷不幸的遭遇,与下层群众较为广泛的接触,以及儒家思想中进步因素的指导,使他写出了《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岁晏行》等“诗史”式的作品,写出了《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登高》等描写苦难现实和咏叹身世相结合的作品,使他的诗歌显得沈郁顿挫、严整流动、雄浑浩荡、浑厚精深,从而登上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可以说,古代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人,像杜甫那样提出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反映如此多的愿望和理想,时代与个人心灵的脉搏在诗中跳动得如此强烈有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安得如鸟有翅膀,托身白云还故乡”(《大麦行》),“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遗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诗句有力地突出了诗人的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极大差距和深刻矛盾,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加强了诗的思想性和感染力。
中唐诗人刘禹锡因参加过“永贞革新”而受到守旧派的迫害,一贬再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沉论,仍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他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扫古代诗词中的悲秋情绪,身处逆境而心胸坦荡,胸襟开阔。在《扬州逢乐天席上见赠》一诗中,他又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情、哲理来鞭策自己,鼓励友人。他任夔州刺史时,饶有兴趣地学习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仿写了十多首同名作品。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充满了山村的芳香气息。这些都说明丰富的情感,达观的生活态度,对诗歌贴近现实,打动读者起着较大的作用。
孟浩然是位终身不仕的隐士,他没有李白、杜甫、刘禹锡那样饱满的政治热情,但他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农村生活极为向往,因此他的山水田园诗写得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气息。《过故人庄》一诗,通过清幽的环境,盛情的款待,融洽的叙谈,赏菊的邀约等富有田园风味的场面,表现了诗人对农家纯朴情谊的赞美,从平谈的语言中渗透出醇厚的诗意。
二、善于继承,敢于创新,是唐代诗人极为可贵的创作态度,也是唐诗具有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古人创作非常重视借鉴与创造。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以及他人所谈到的“因革”等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继承与创新。唐代诗人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直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五》),“未及前贤更铁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其具体表现为:
向古人学。纵览唐诗,我们可以感到,《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辞”的浪漫主义手法,建安诗歌的“风骨”,齐梁“新体诗”的声律,乐府民歌的清新色彩,六朝文人诗的修辞技巧等,无不为唐代诗人所吸取。特别是他们善于将南朝文学声调激扬、高亮,语言清新、华丽的优点,与北朝文学内容严正、注重气势,风格质朴,说理深刻等优点结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从而创造出唐诗——这一中国诗歌最健美,最具艺术魅力的典型。
向今人学。唐代诗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之风颇为流行。杜甫对李白可说是尊崇备加,钦佩之至。“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梦李白二首》其二)等诗句就是对李白诗歌准确而高度的评价。还有“元白”、“刘白”、“韩孟”、“皮陆”等人,他们都是诗友,经常唱和,相互谈诗,论诗,共同提高诗艺,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向少数民族和国外学,向其他文艺形式学。唐帝国的空前强大与统一,促使中外文化得以广泛交流,国内各民族文化得以密切融合。吐蕃、印度、西域等地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传入中原,给唐诗提供了题材和艺术借鉴。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欣《听董大弹胡笳》,李贺《李凭箜篌引》等诗篇描摹中外各种乐器的演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同饮旗亭听唱的传说,说明当时的绝句多能谱成乐曲,广为传唱。白居易《胡旋女》、李端《胡腾儿》等诗,风格也宛如雄武健美,矫捷奔放的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李白从张旭的草书中体会到凌厉放纵的气势;杜甫从公孙大娘的剑舞中领略到变化莫测的奥妙;王维从绘画中得到灵感,提高了捕捉形象,创造意境的能力。这些都与加强唐诗的艺术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诗人不仅重视继承,而且更强调创新。他们不是机械地模仿前人,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做到了学而能变,变而能新,常学常变,常变常新。
就拿杜甫来说吧,他在创新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变汉魏文人用乐府旧题写时事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为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他精通格律,严守格律,但又能打破格律,作拗体诗,他在律诗中发议论,写时事,并用连章体的组诗反映复杂的事件,描叙众多的人物;他把不少口语、方言写进诗中,以致招来“村夫子”的讥诮。正是由于这种创新精神,使杜诗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高度。
中晚唐诗人在盛唐诗歌成就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敢于独辟蹊径,闯出新路。白居易向平易通俗方面发展;韩愈、孟郊则向奇崛险瘦方面进军;李益用七绝写的边塞诗,与高、岑相比,意境更为动人;李贺的浪漫主义诗篇,与李白相比,多了一层冷艳的色彩;李商隐善于运用典故与象征手法,开了古代朦胧诗的先河;杜牧的七绝情致俊赏,风格轻利,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切都说明唐代诗人具有一种锲而不舍,苦苦追求的执着态度,和不固步自封,敢于突破前人的解放精神,固而他们的诗歌就具有一种永不消失的艺术魅力。
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他又在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唐人懂得形象思维,李贺的诗值得一读等问题。从目前新诗的创作现状来看,从近几年所掀起的传统诗词热来看,从新诗的发展前景来看,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诗两条出路的论述,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古典,主要指的是唐诗、宋词。如果今天的诗人能够认真学习唐代诗人的一些宝贵经验,吸取唐诗中的丰富营养,创作出有内容、有感情、有意境、有韵味、有审美价值、有艺术魅力的新诗来,就一定能扭转目前新诗不景气的局面,使当代中国诗坛上出现一个百花吐艳的春天。这就是我们从探讨唐诗的艺术魅力中所得到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