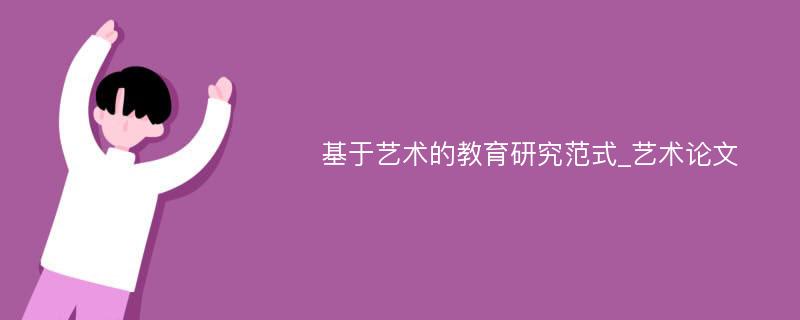
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art-b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ABER)目前在西方教育研究中的数量越来越多,价值也越来越凸显,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后现代转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方法逐渐兴起。这种研究方法的最早创立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艺术教育家、课程研究专家艾斯纳教授(Elliot Eisner),其艺术和教育的双重学术背景使其反思以往科学主义范式下的教育研究,创立了一门艺术批评的学科,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方法。 尽管由艾斯纳开创的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质疑,但他点燃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动了它的发展。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成立的第一个“基于艺术的研究”机构成为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成员。如今,这种研究范式方兴未艾,分化出了许多新的类型,诞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这种研究范式在目前我国教育学术界还很陌生,关于它的译介、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的成果几乎为空白。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一个包含基本的认识论假设、理论观点以及方法论、具体方法的体系,所以本文着重就这几方面来阐释何谓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以期引起我国教育研究者对此的关注和借鉴。 一、认识论假设 认识论的假设构成了一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前提,它关涉到这种研究范式如何看待认识方式、知识、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并且直接影响了研究者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模糊的认识论(an epistemology of ambiguity)[1] 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和方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成为教育研究的主导。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站在主客二分的立场上,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的唯一确定性;强调研究是去发现已经存在的客观真理;强调人的理性是把握世界的唯一方式。然而随着这种研究范式弊端的逐渐显现,它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可以说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其基本的认识立场就是建立在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之上。它持有一种不精确的认识论,即认为人们所认识的宇宙世界不是确定不变的,其因果关系也不是固定的、线性的、单一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联系的、复杂的,对于人类社会和教育现象来说更是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人们所获得的认识或知识也不是永恒的,放置四海皆准的唯一真理,而是从不同视角获得的局部的、暂时的、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认识。同时它不认为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确定不变的真理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而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通过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不断交往对话所建构出来的。艾斯纳说:“人类的知识无论是对精神的反思还是对自然的认识都是经验的建构形式,因此,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简单的发现。”[2]他认为在传统的认识论中,人们低估了这一知识的建构过程。“知识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物体或产品。思想更像是一条流动的小溪而不是一块固定不动的岩石。思想也总是产生在工作的过程之中。”[3]因此,基于艺术的研究范式认为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谦卑的认识论态度(epistemologically humble),而不是霸王式的认识论态度(epistemological bully),[4]不应该强加给读者他们自己对世界的单一观念,而是激发一种令人受到启发的对话。 (二)艺术具有照亮教育情境,呈现教育体验,增强教育理解的独特价值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除了具有质性研究共同的一些认识论取向之外,它更加强调认识世界方式的多元化,不仅艺术和科学都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且艺术能够提供独特的看待教育的视角并且增强对教育的理解。在艾斯纳看来,“存在多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艺术家、作家、舞蹈家以及科学家都可以在认知世界中作出重要的贡献。”“而且人们所选择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不仅影响了他们能够阐释什么,而且也影响了他们能够体验到什么。”[5]“艺术能够让人们进入到通过其他呈现方式所不能获得或很难达到的体验”。[6] 艾斯纳借鉴杜威(John Dewey)在《艺术即经验》中对“表达”和“陈述”的区分,即杜威认为科学是陈述知识,而艺术是表达意义,以及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 Langer)所提出的“陈述性符号”(representation symbols)和“描述性符号”(presentation symbols)的区别,指出科学符号或语言陈述了一个状态或事实或事物,这种陈述是透明的,它直接指向了指示物。而艺术符号或语言是不透明的,它的具体、形象、情感、情境性使其不是简单的指向所指之物,而是能够传递体验,能够唤起人们的想象,使读者直接被其呈现的意义所吸引,从而激发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其实,这是一个关乎艺术是否能够和科学一样揭示真理和意义的问题。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大发展,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日益显著,文学、艺术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只关乎情感,唯有科学是理性的,是实证的,它不仅是世界的主宰,而且是真正知识的唯一来源。这种对立,使得艺术长期以来被看作与真理无关,艺术不可能揭示真理。其实,马克思(Marx)早就论述过人类有四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一是哲学,二是实践,三是宗教,四是艺术。世界不仅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信仰的对象,改造的对象,而且还是人类体验、审美的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世界的丰富意义,而且确认了人的本质力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中指出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创造了一个由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符号构成的文化世界。其中艺术与其他符号一样,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其独特性在于艺术是一种直觉符号的语言,艺术品不仅通过形式去唤起读者的感官享受,更是通过可观可感的符号去表达生命形式,使读者在对形式的关照中,整个生命都产生共鸣和震动,从而实现自身生命的再创。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诗”乃是“存在之真理”显现的最本源、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他批判了传统真理观,认为符合客观现实的知识就是真理的传统真理观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的,真理应该和人的存在紧密相连,所以他指出存在的显现即真理之所在。诗的语言保持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保持了抽象意义与感性意义的统一,因此表达的是活的存在。然后海德格尔由“诗”推演到“艺术”,认为一切艺术品都是按“诗”的原则创造的,“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7]由此海德格尔提出了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 这些哲学家的深刻论述不仅重新思考了何谓真理,而且颠覆了艺术与真理无关的传统论断,将艺术放置到与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认为它比科学更能触动人的情感、生命,表达人的体验、存在,揭示价值和意义。这些观点构成了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的重要认识论假设,即艺术具有认识和理解教育的独特价值。 二、基本观点 认识论假设决定了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在研究的目的、方法以及研究者、研究对象、读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呈现了与其他教育研究的不同之处。 (一)丰富看待教育的视角,唤起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教育观念和现象的关注、思考与变革 在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看来,教育研究的目的不是去讨论和揭示一个正确的、令人信服的教育答案,使读者获得一种确定性的舒适感。而是在于扩大人们看待教育的视角,将那些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惯常的教育情境、现象以独特的艺术化方式呈现出来,将读者引入到研究者所创造的反映现实的虚拟世界,与文本进行认知与情感的交流,从而唤起他们的教育敏感和思考。艾斯纳说:“通过我们的工作,要丰富对话,将我们的敏感性指向那些教育情境中细微的但又是重要的方面。”[8]艾斯纳并不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把我们引向同一个目的地或结果,而是不同的方法引向不同的目的地。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要做的是引发新的问题,而不是回答。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教育的“启示不是仅仅来自于分享一些事实的结论,而更在于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世界的视角。”[9]通过改变和丰富看待教育的视角,通过多元的阐释,不是为了促进教育共识的达成,而是要成为一种新的介入和干扰,甚至有时是制造一种不平衡,使得教育者能够更深入地思考那些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和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 (二)艺术元素和形式融入教育研究,研究文本体现情境性(contextual)、地方话语性(vernacular)和唤起性(evocative)[10] 除了采用如访谈、观察等一些质性研究方法之外,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还将艺术创作实践、艺术品融入到探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之中,使艺术成为教育探索和表达的重要方式,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教育研究的最根本特性。以往的教育研究通常以逻辑的论证和阐释,以抽象的学术语言提出概念和命题。而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则让艺术元素和形式成为教育表达和呈现的中心话语。在研究者看来,教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无生命的、确定不变的机械物体,而是在具体的场景中,有着情感思想和能动性的人,而且教育研究也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和情感无涉,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从自身的视角,伴随自己的经历、情感和思想而完成的。所以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就是要将传统科学主义范式下所揭示的单一、普遍、抽象的教育世界,还原到它的复杂性、具体性和意义性,将其所观察、体验、思考的教育场景、现象和问题通过小说、诗歌、绘画、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多视角的、细致的描述、描绘和演绎出来。比如一位研究者通过被命名为“破碎的身体”的一幅幅视觉艺术作品,[11]向观众诉说了她作为艺术家、研究者和艺术教师三重身份在教育情境中所经历的艺术创作、研究和教学三者之间的冲突、妥协等,展现了一名艺术教师的现实生活状态。 艺术符号和形式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象直观。所以当我们面对任何艺术化呈现的教育研究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可观可感的教育世界,它有鲜活的人和物,有情节的展开、细节的描绘、场景的呈现,这让读者或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艺术的语言不是抽象的教育概念、命题,而是形象、具体、日常和地方话语的,所以它不排除教育学术之外的读者,能够邀请更多的所谓学术的门外汉进入到这个由研究者所创造的生动教育世界之中。它的情境性、地方话语性为读者或观者创造了一个既虚拟又真实,既陌生又熟悉,既无关又有关的教育世界。他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暂时地与自己的世界隔绝,但又很快通过移情、想象在虚拟世界找到与自身世界的联系,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与对话,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习以为常的教育,反思自己的教育经历,质疑那些平时对此毫无问题的教育现象。所以在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中,艺术“不仅仅是纪录、分析和展示,而且也是创造数据和资料的工具。这可以使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平台。所以艺术具有创生性。”[12] (三)移情性理解构建研究者、研究对象和读者之间的“我与你”关系 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过程也犹如艺术家的创作过程,研究者要经历体验、构思和表达的阶段。体验呈现的是研究者与教育世界的密切关系,它需要研究者对教育的深入感悟,这是研究者积累研究素材的阶段。构思阶段则是研究者发挥自己的思维、想象、情感对素材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形成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审美意象”的阶段。表达阶段则是选取特定的艺术语言、媒材将审美意象物态化,呈现出艺术形象的过程。其实这每个阶段都蕴含着研究者整个身心的参与,不仅是理性的思考,更是对研究对象的移情性理解。移情性理解是认知和情感的共同作用,研究者不是把研究对象仅仅作为一个客体去做理性的分析,而是能够设身处地,进入研究对象,感同身受,这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就从“我与它”的分离、对立转变成了奥地利宗教哲学家布伯尔(Buber)所提出的“我与你”的彼此敞开,真诚对话的共在关系。关系的改变使得研究对象不断展现出的它的丰富性,研究者对教育的思考和理解也就更加深入。这个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犹如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所说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同样是竹,但每一阶段的竹因为画家与竹的关系的不断融合,从而有了新意,成为新的竹。反过来,逐渐敞开的研究对象也在改变着研究者自身,使得研究者能够在不断更新的对象中反观自身,实现自我的不断变革和超越。 移情性理解不仅始终存在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研究者所创造的艺术化文本与观者或读者之间。艺术化文本所具有的情境性和唤起性能够激发读者或观者暂时忘掉现实世界,作为一个局内人对其中所描述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产生移情性理解,这种移情使他们减少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幻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研究对读者或观者心灵深处的触动和共鸣。 (四)发挥教育想象,寻找和呈现教育的复杂联系和多种可能 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想象是在直观中表现一个本身并未出场的对象的能力”。[13]现当代哲学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是从传统哲学的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追求唯一真理的纵向理性思维方式,转向强调寻求事物的普遍联系。超越在场的东西,想象那些尚未出场的,但与在场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也是现实的事物,从而达到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这是现当代哲学的“横向超越”:唯有想象能够成为沟通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格林(Maxine Greene)教授积极倡导教育想象的价值和意义,她说:“当我们能够从主客的、内外的分离中走出来时,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想象在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14]“想象可以揭示事物的不同状态,可以打开我们对于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认识窗口。想象关注对他人的移情,关注我们和世界新的互动关系的开始。”[15]所以教育想象不是要给人以确定的方向、明确的知识,而是要唤醒,要揭开未见、未闻和未预期的事物。 艾斯纳在他的《教育想象——学校课程设计与评价》("The Educational Imagination:On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School Programs")一书中对科学主义的课程开发范式进行了批判,认为无论是课程的设计和开发,还是教学都不只是一种预先设定的过程,而更应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想象,不断发现,不断生成、不断创造的过程。同样,对于他所开创的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者需要具备教育想象的能力,即有不断探索可能性的热情和勇气,能够从有限空间进入到无限空间,由在场联想到不在场,在对各种可能性的积极探寻过程中,创造一个个新的联系和新的惊喜。教育想象改变了研究者与认识对象、与世界的线性、单一关系,呈现出了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复杂联系和多元性,丰富了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三、主要类型 当今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艺术融入,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研究态势。不仅采用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而且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等多种艺术媒介形式与教育研究融合;不仅有教育研究者单枪匹马式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艺术家、教师等组成研究共同体,发挥各自的特长,开展合作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类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式和丰富的研究案例。 (一)教育鉴赏与教育批评模式 这是由艾斯纳首创的基于艺术的教育评价。他明确指出“教育鉴赏(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和教育批评(educational criticism)是两种植根于艺术的教育评价过程。教育鉴赏属于艺术欣赏”。[16]任何一个教育情境或教育事件,在艾斯纳看来就像一件艺术品,研究者若想深入理解并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也必须像艺术欣赏者一样仔细地去观察、品味。所以教育鉴赏是指对教育情境中微妙却又重要的地方,对一系列逐渐展现的事物特征的意义的辨识和洞察。这个过程需要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知觉能力,不仅用各种感官仔细地观察,而且用直觉、情感去体察;不仅是整体地把握,更是对细节的觉察;不仅是解码的过程,也是编码的过程。教育鉴赏强调的是研究者需要以丰富、形象、完整的审美知觉去代替以往单一、抽象、破碎的日常知觉,从匆忙、功利的状态中走出来,慢慢地、细细地品味教育,发现它的独特,从而为教育评价提供丰富的教育印象和资料。 教育鉴赏是个人的一种教育体察,将这种体察用适当的语言形式描述展现出来的过程就是艾斯纳所说的教育批评。在此,艾斯纳不是在否定意义上来使用批评这一个概念,而是借用艺术批评的内涵,即一种扩大对艺术作品欣赏和理解的过程。所以教育批评是进一步阐释、理解和评价教育并且对他人有所启发的过程。教育评价包括描述(description)、解释(interpretation)、评价(evaluation)和主题(thematics)四个方面。[17]描述是对教育情境、事件等的具体呈现。描述不只是单纯的说“是什么”,更是要呈现出这些情境、事件的色调、感觉,融入其中的情感等。在此,艾斯纳强调了艺术元素和形式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的重要价值。相比以往人们所常用的学术语言,他认为散文、诗歌、照片、视频等艺术形式更能表达出研究者对教育的细微体察,比如影像能够捕捉到那些稍纵即逝的教育瞬间,能够向我们展示单纯以语言文字所无法呈现的教育的情境性特征;比如散文中的节奏和韵律使其比抽象的学术语言更加深刻和精确地传达人的情感和体验。教育批评不止于描述,研究者需要对所体察的教育情境、事件、关系等作出意义的解释。艾斯纳举例说,当研究者向我们描述了学校环境中教师与学生所建立的各种盟约之后,他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盟约的出现,它们在教室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等。这就是教育批评中的解释。评价则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作出价值判断。艾斯纳在教育批评中提出的“主题”其实是指研究者用一定的概念或命题对研究内容的提炼,是教育研究普遍化的过程。比如上面的例子,研究者就用“盟约”这个词作为了研究的主题。这里艾斯纳针对传统量化研究认为从个别现象无法做作普遍结论的观点,指出艺术不仅将我们对教育关系、意义的体察用特定的形象、场景描述出来,而且它为读者或观者提供了可参考的图景(schema),[18]使读者或观者能够对教育中相类似的情境、现象等作出反应和思考。尽管这不是通过随机抽样的量化统计所作出的普遍结论,但它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这也是艾斯纳所坚持的,即基于艺术的教育探究形式和过程,需要创造看待教育的新视角,需要为教育理论、实践、决策提供重要的思考和观点,从而真正改善教育。 (二)艺术与科学相融合的研究模式 这是将艺术形式,诸如文学、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作为一种工具和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共同运用于教育学术研究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艾斯纳的学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巴若内(Tom Barone)和艾斯纳共同开创的。他们于1997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出版的《教育研究中的其他方法》("Complementary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一词,并且阐述了基于文学的教育研究的一些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文本的特征,“比如创造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虚拟世界的文本;用表达性、情境性、日常性的语言进行陈述;能够激发读者对文本人物的移情;通过研究者独特的、个人化的表述性呈现出一个审美的文本。”[19]另外,一些人类学者进行了艺术方法与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探索,比如自传式人种志研究(autoethnography),这是文学自传与人种志方法的结合;比如利用视觉影像呈现的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等。这种研究方式也被一些教育学者所采用,通过自传式文学呈现自身的生活体验和教育反思。 在这类模式,巴若内2001年出版的著作《触及永恒:教学的持久性成果》("Touching Eternity:The Enduring Outcomes of Teaching")是一个代表性的研究,他用故事叙述的方法讲述了一位高中艺术教师和他教过的学生之间的故事,呈现了这位优秀的高中艺术教师的教育生活史。通过唤起性的语言和审美化的文本引发读者对教学的本质是什么,学习究竟学什么,教育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和价值是什么等这些基本的教育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 如今,这类研究不只是采用自传、叙述、诗歌等文学形式,越来越多的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戏剧、舞蹈等作为收集数据,呈现研究的手段。比如教师通过视觉日记的方式,即集文字、绘画、粘贴等表达方式为一体的日记,记录自己的教育故事和教育反思。比如将田野调查的资料改编成剧本,通过角色的扮演、情节的展开,使每一位参与者具有亲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教育体验,同时在扮演、分享和讨论中不断生发新的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悟。总之,这一类研究的目的在于:[20]探寻一种新的言说和表达教育研究的方式,努力实现艺术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合法地位。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提出新视角和新问题的兴趣要大于寻找对教育的绝对答案;使研究者清晰地认识到自我和研究对象、研究情境的一体性或共在性;通过艺术语言而非抽象的学术话语,试图使教育研究不仅成为学术群体内部的讨论和认识,而且能够吸引更多学术圈之外的读者,真正达成关于教育未来可能性的广泛对话和交流。 (三)艺术家、研究者和教育者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欧文(Rita L.Irwin)教授在20世纪90年初首先提出了a/r/tography的概念,这种模式最初由艺术家驻校的合作研究发展起来,并逐渐运用到艺术教师的专业发展之中。"a"指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r"指研究者及研究活动,"t"指教师及其教育教学活动。所以a/r/tography是一种将三种身份、三种活动整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它强调艺术家、研究者以及教师这些角色之间的不停转换,通过艺术创作、反思、教学实践的整合活动,通过视觉化的描绘和文学化的阐释对教育、对自我做情境性、持续性、创造性的探究。[21]这种研究方法力图打破二元对立、线性、确定的思维方式,借鉴当代哲学、经验美学、关系美学的思想,实现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三种思考方式:认识(knowing)、实践(doing)和艺术创作(making)之间的不断转化,重筑心与身、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艺术、自我与他人、时间与空间等的整合。 因此,a/r/tography显示出这些特性:第一,强调不同角色、不同活动、不同知识之间(in between)的对话和交流,由此产生的边界地带(borderlands)就成为新的感受、思想和创造出现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当艺术教师能够不断游走于作为教师、艺术家和研究者三种角色之间,能够将教学、艺术创作与教育反思结合在一起,他或她就成为集艺术家、研究者和教师为一体的人,即a/r/tographer。第二,强调研究者身心整体参与的,不断探寻的行动研究。它认为“以往研究感兴趣的是去发现既存的或者需要被发现的知识,而行动研究和a/r/tography关注的是创造一个具体的、联系的、体验的环境,这个环境能够使人通过丰富的探究过程去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理解。”[22]所以这是一个认知、实践、再认知、再实践相互转化、动态的生成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不只是认知地参与,更是在体验、创作中不断地阐释和理解。第三,强调合作的社群关系。a/r/tography认为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教师还是研究者,个人的探究活动都需要纳入到一个群体的关系中,因为通过群体的多视角对话,能够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以a/r/tography不仅是指艺术教师本身集教师、艺术家和研究者为一体的研究方法,而且越来越强调构建一个由艺术家、教师和研究者共同组成的研究群体。通过彼此学习、交流、理解、阐释的社群关系,实现持续而又具有创造性的探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a/r/tography已经不只是停留在运用艺术形式去收集资料和展现研究成果,而是将研究过程和教学、艺术创作过程融为一体。比如在《在关系性艺术实践中与教育学相遇》("Encountering Pedagogy through Relational Art Practices")一文中,[23]作者详细阐释基于关系美学的理念所开展的一个a/r/tography的案例,即一群艺术师范生、指导教师与两位艺术家共同度过一段集体的艺术创作生活,在关系性的艺术创作实践环境中,通过彼此的对话、分享和讨论,不仅激发了师范生、指导教师对艺术创作、艺术学习本质的思考,而且还唤起了它们对艺术教育和教学的不断反思。 随着教育领域对“课程作为一种美学文本”的观念的不断深入,a/r/tography已经从艺术教师、艺术教育的领域拓展到了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等领域,比如我国台湾已经有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发展出了以艺术为基础的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即“教师利用创造性的艺术经验或艺术创作,理解、诠释和批判在实际中自己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发现自我、并自我赋权增能。游移在艺术家/研究者/教师的角色,以第三空间上的模棱两可(ambivalence)作为生成的场域,从混沌中创造意义,寻求更多的可能性。”[24] 四、评价标准 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范式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的科学主义的教育研究范式的质疑,比如以传统的衡量教育研究的信度、效度、适用性等概念去质疑这类研究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对于这些质疑,巴若内和艾斯纳提出了衡量好的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的四个标准:[25](1)阐明性,能否揭示一个尚未被关注的教育现象和问题;(2)问题性,能否引发更多问题;(3)深刻和敏锐性,能否对教育话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4)普遍性,所揭示的问题和现象是否具有普遍存在性。后来艾斯纳又在《基于艺术的研究中的张力》一文中进一步做了些回应,他详细论述了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中所面对和需要思考的几对张力或矛盾,比如特殊与普遍、艺术化的表达与教育事实、提出问题和给予实践的指导等。在艾斯纳看来,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遵循的是文学的普遍化概念,而不是统计学中的普遍推论。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通过典型化的呈现将读者和观众引向对普遍意义的思考和追求。他认为好的“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是能够提出值得人们去思考的问题和值得追求的理想”[26]。尽管重点在于引发问题,但艾斯纳认为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必须最终指向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不是要去取代或对立原有传统研究,而是要模糊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去拓展研究者的洞察和创造能力,展示另一种研究探索和分析呈现的方式。正如艾斯纳所说:“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但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又都有他没有看到的东西。”[27]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就是要通过艺术作品、艺术创作的介入,让我们从新的视角去感受细节、激发体验,关注被我们所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教育现象,从而实现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反思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