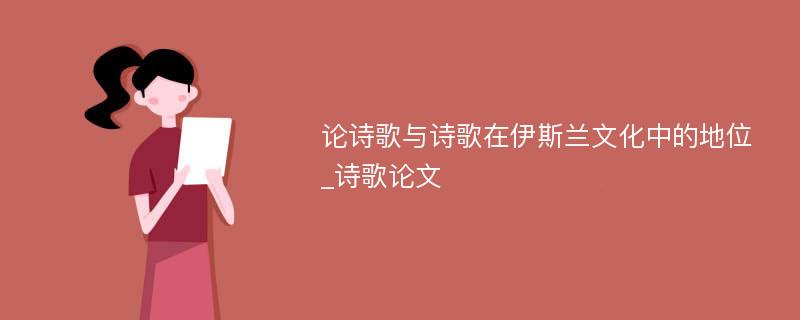
伊斯兰文化中关于诗歌和诗人地位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诗人论文,诗歌论文,地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0)01-0126-06
一、指控诗歌和诗人
欧菲创作于1221年的《诗苑精华》是波斯古典诗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第一章《论诗和诗人的优越性》中记述了这么一场有关诗歌的争论:一天晚上,在伊本·阿巴德(阿巴德家族1023-1091年统治阿什比利叶地区)老爷家的聚会上,有群才子(afāzel,一般指诗人)对诗歌的益处与害处展开争论。一拨人认同诗歌的益处,另一拨人持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诗歌是一种应被谴责的东西,而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状况都应被谴责。因为大多数诗歌不论其是赞颂还是抒情,二者的基础都是公开的虚假之言(akāzib),都是直言不讳的谎话(dorugh),这使得时下大多数诗人将自己的表达(bayān)之技艺用于贪婪的目的。书中没有提及正方是如何辩驳的,只是说争论陷入僵持之中,可见争论还是相当激烈的,双方相持不下。这时,阿布·穆罕默德·哈赞(生平不详,估计是一位德高望重者)一锤定音地说:诗歌乃万物中最妙者。如果虚假掺入诗歌,则诗歌之美自能战胜虚假之丑。因而有言曰:最好之诗乃最诚实之诗,最甜之诗乃最虚假之诗。他说,诗歌比所有的东西都好。因为谎言与任何东西混在一起,谎言的丑陋就会把那东西的意义之脸孔弄得没有光泽。然而,如果谎言之黄铜镀上诗歌之金,并在机智者才华的熔炉里获得光泽,黄铜也会变成金的颜色。诗歌的益处超过了谎言的龌龊。那么,这炼金术把谎言之黄铜转变成美好的纯金,我们能对它进行什么责难呢?于是,所有的在场者都给出了公断,都慎重地承认这个道理。因此,基于真理之道,芸芸众生中没有人否定诗歌[1]。
这场论争的焦点似乎是在指控诗歌是谎言,这不诚实的东西使诗人变得贪婪,以不实之词去博取各种赏赐,因此诗人应受谴责。欧菲还在对论争的记述中援引了一首讽刺诗,说诗人“把自己称作奴隶”(bande,该词也是反指“自己”的谦称代词即“鄙人”),把柏树称为自由民,有时给乌黑的桑给人(坦桑尼亚一黑人部落)起绰号为天仙,有时把下流坯称为豪爽之人,这似乎更加说明了诗歌的不实之词是“诗歌是谎言、诗人应受谴责”这一指控的原因,与柏拉图谴责诗歌的理由大致相同,说明在波斯也发生过曾在古希腊发生过的论争,只不过柏拉图是自己与自己论争,他一方面谴责诗歌是谎言、诗人说谎,要把诗人礼送出“理想国”,另一方面又处处为诗歌辩护。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成为西方后代诗学研究讨论的重点。其实,这一论争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争辩诗歌的利弊,而是在为诗歌的地位而争论。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心中,诗歌与哲学孰轻孰重。然而,波斯欧菲记载中的争论似乎仅仅是在争辩诗歌的利弊。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为诗歌的辩驳(见下一节)中发现论争的目的并非如此单纯,论争的起因也不是在阿巴德老爷家聚会的才子们闲来无事,一时兴起而争。欧菲的记载是有关诗歌之争的最早波斯史料,尽管不够详细,但我们从中可以隐约窥见,阿巴德老爷家发生的争论不会是这种有关诗歌之争的肇始,一定还有着相关的前因。
其实,欧菲在第一章之前的“分章”中已经触及这场论争的最早源头。他说:可以将水灵的诗歌比作海洋(bahr),没有格律(bahr,欧菲在这里充分利用该词的双重意思阐述了格律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就不是诗歌(nazm)。无声的宝藏和幽玄的珠宝蕴藏在这海洋中。尽管在海洋(bahr,同时也指“格律”)中航行会收益颇丰,但其危险性的打击比获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智者们对收益颇丰的海洋之行应谨慎为之。因此,圣使——最具有理智的完美造物——并不渴望这海洋之行,至上之言:“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2](《古兰经》36:69)然而,在《古兰经》降示之前,阿拉伯的才子(诗人)们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中,炫耀自己的诗歌,常用金汁书写并悬挂起来显摆(欧菲这里说的是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悬诗”),其实这些诗歌都是一些粗野货,这些所谓的诗人并不懂得格律。因此,海洋中的巨鲸使“诗人们被迷误者所跟随”(《古兰经》26:224),导航之书(《古兰经》)打败了他们。从《古兰经》之宝库中获得源泉的那群人,由于有了护甲,他们的诗歌便获成功[1](P57-58)。欧菲的记述有些语焉不详,蒙昧时期的诗人不懂格律,诗歌大都粗野,但伊斯兰之后的诗人们从《古兰经》汲取营养,获得成功。这与对诗歌是谎言、诗人应受谴责的指控并不相干。尽管如此,我们从欧菲的记述中多少还是能窥见,这场论争与《古兰经》的降示、伊斯兰教的产生密切相关。
像夏姆士·盖斯的《波斯诗歌规则宝典》(创作于1232年)、阿罗梅·阿莫里的《技艺集萃》(创作于1343-1352年)、贾米(1414-1492年)的《春园》等波斯古典诗学著作都提到这场论争,但对论争本身的记述都语焉不详,他们更多的是在为诗歌辩护,我们将在下一节谈到有关内容。至于这场论争因何而起,笔者不知道阿拉伯史料是否有详实的记载,就笔者阅读所及,波斯史料中只有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创作于1486年)的相关记述可以让我们分析出一些真实原因。
都拉特沙赫在《诗人传记》“阐述在善于辞令一族中诗人的专门化”一章中说:“书籍记载和佚闻传说都一致认为,从纯洁的阿丹(亚当)被贬谪到大地之时起,在伟大而尊贵的人类中间时刻都有一门学问被发现,那群人中的聪明者,那些人中的智识者都致力于这门学问,不断将先知使命的方式遮蔽,正如在努哈(挪亚)时期是咒语之术,在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时期是耍火术,在穆萨(摩西)时期是巫术魔法,在尔撒(耶稣)时期是医学。他们将这些双眼瞎般的技艺妄称为先知使命的学问,并将这些学问视为奇迹。……随着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显世,雄辩之学和动人之学获得荣耀。阿拉伯的才子们将这门学问妄称为先知使命。倭玛亚·本·阿比萨尔特是多神崇拜诗人的先驱。当神圣的经文‘诗人们被迷误者所跟随’为那迷路者降示,这种妄称便自行作废。”[3]这段记述告诉我们,每位先知显世的时期,都有一种学问被发现,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智者从事这门学问,并自称先知,将自己所擅长的技艺称为只有先知才可能创造的奇迹,以此蒙蔽人们,使人们不听从真正先知的召唤和指引。在穆圣显世时期,是语言之学流行,擅长语言技艺的诗人们妄称先知。随着《古兰经》的降示,这种妄称便破灭。也就是说,诗人妄称先知是“诗歌是谎言、诗人应受谴责”这一指控的根本原因。
的确,在蒙昧时期,诗人往往受到本部落人的尊崇。黎巴嫩学者汉纳·法胡里在其《阿拉伯文学史》中说:“诗才在一切古代民族中都受到尊崇。从前,阿拉伯人认为每个诗人都有一个精灵在向他启示诗句。那时,诗人的地位十分显赫。……一旦某个部落涌现出一位诗人,全部落都为他大举庆贺、大摆宴席,其他部落也都前来为它出现一位能言善辩、维护尊严、记载光荣历史的诗人而祝贺。”[4]看来诗人妄称先知,或被本部落人视为先知是当时阿拉伯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实在远古时期,或在现今尚未开化的土著部落中,能吟出诗句的人普遍被视为通灵者),这对穆圣传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妨碍。之所以说这种妄称随着《古兰经》的降示而破灭,是因为《古兰经》中有多条经文否定诗歌和诗人:第26章“众诗人”第224—226节:“诗人们被迷误者所跟随。你不知道吗?他们在各山谷中彷徨。他们只尚空谈,不重实践。”第36章第69节:“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是两条被后人用来否定诗歌、指控诗人时最常引用的经文。另外,第21章“众先知”第4—5节:“他说:‘我的主知道在天上和地上所说的话,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但他们说:‘这是痴人说梦呢?还是他捏造谎言呢?还是他是一个诗人呢?教他像古代的众使者那样昭示我们一种迹象吧。’”这里的“他”指穆圣,“他们”指违逆者。经文通过违逆者们之口,将“诗人”与“痴人说梦”、“捏造谎言”并列,后人从中推论出“诗歌是谎言、诗人应受谴责”这一指控,又加之诗歌本多为幻想和夸张,使得这一指控更加确凿。
这些经文引发了伊斯兰教初期有关诗歌是否应当被提倡的争论,并且从后人的辩驳中可以看出,这场争论应当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断有人以上述《古兰经》经文为依据,对诗歌和诗人的宗教合法性提出质疑或进行否定。究其实质,这其实也是一场关于诗歌和诗人地位的论争。
二、为诗歌和诗人辩驳
上一节所提到的阿巴德老爷家发生的论争,哈赞的辩驳是说,诗歌如同炼金术,具有炼铜成金的优越性。别的东西被谎言笼罩,就只能是耻辱,而当诗歌遭遇谎言,诗歌之炼金术就将谎言之铜锻炼成了黄金,从而变得美好。结合上下文来看,其辩驳的出发点是形而下的生存之道,认为从诗歌这门学问所获得的利益,比从句法学、《古兰经》注释学、《圣训》诠释学等别的学问所获利益更多,能够得到君主们更多的奖赏。因此,即使诗歌是谎言,也是一种美好的谎言,有何不可呢。这可以说是一种诡辩,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仅仅是针对“诗歌是谎言、诗人应受谴责”这一指控本身,并没有涉及到论争的真正实质。
针对不断有人以《古兰经》有关经文为依据,提出诗歌不被许可,不具有宗教合法性,不应当被提倡,欧菲在《诗苑精华》中说道,“圣使口吐吉祥之言:我不是诗人,他没有将它赐予我,那扇门没有向我开启,高贵的圣门弟子、迁士、辅士们做过很多诗歌,哲理的珍珠经由表达之手串连在诗歌之线上”[1](P63)。圣门弟子,指穆圣早年的伙伴,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迁士,指跟随穆圣从麦加迁徙麦地那的穆斯林。辅士,指穆圣迁徙麦地那之后,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并辅助穆圣开拓伊斯兰教事业的麦地那人。也就是说,尽管圣使说自己没有作过诗歌,但其弟子们是会作诗歌的,并且圣使对之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欧菲没有进一步的辩驳。
阿罗梅·阿莫里在其《技艺集萃》中有较为严密的辩驳。他说:“乌来玛(宗教学者)界都认为,其间蕴含赞颂、膜拜至高无上的真主的诗歌,或者是描绘圣使的诗歌,或者是不涉及羞耻之事的诗歌,只要它正直、劝诫、哲理、讽刺都是许可的。”也就是说,首先宗教界并没有完全否定诗歌,而是认为对待诗歌应该一分为二,歌颂真主和圣使的诗歌,或者其他内容健康向上的诗歌都是被许可且应被提倡的,只有那些诲盗诲淫的诗歌(当时在阿拉伯地区,情色诗和纵酒诗都是比较泛滥的)应当被禁止。因此,诗歌是否应当被提倡或被许可,关键在于诗歌的内容,而不在于诗歌形式本身。
阿罗梅·阿莫里还援引了多条圣训和典故来为诗歌辩驳,其中一条圣训说:“真主要降示我们的已经降示在诗歌中。”笔者的理解,这里是指诗歌的功用在于揭示幽玄的奥秘。阿罗梅·阿莫里在书中还说不少圣门弟子是会作诗歌的,还引用了他们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都得到了穆圣的肯定和赞扬。据传说,在伽迪尔日(伊斯兰教什叶派庆祝阿里被宣布为先知继承人的日子)赫桑·伊本·萨贝特(圣门弟子)将圣使旨意撰成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传到圣使那里,圣使便召赫桑前来为自己吟诵,然后训言:“赫桑啊,只要你的舌头声援我们,你就会得到玄灵的佑助。”还训曰:“至上的真主的宝座下藏有宝藏,这宝藏先知不能探及,却能在诗人的舌尖体现。”这些圣训成为后人为诗歌辩护的主要依据,说明圣使对诗歌是持肯定态度的。另外,阿罗梅·阿莫里还说到,在《圣训》中圣使的训言很多都被记载为具有律动(mowzune)和对称(gharine)的语言,具有诗歌的特征。因此,阿罗梅·阿莫里下结论说,作诗是被许可的。“被许可”只是解决了诗歌的世俗合法性,并没有涉及宗教合法性,因为诗歌和诗人是被《古兰经》否定的。因此,“被许可”并不意味着“合教法”。
这样的辩驳虽然很有分量,但还没有解决诗歌的宗教合法性问题,因为《古兰经》中否定诗歌和诗人的经文摆在那里,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阿罗梅·阿莫里又进一步辩驳说:经文26:224节说:“诗人们被迷误者所跟随。”这里的“诗人”是指作无聊的诗歌和虚假的赞颂之人。也就是说,经文中的“诗人们”并非泛指所有的诗人,而是一部分所作诗歌品质低劣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些狂妄的不信道的诗人。
最难作出诠释的是《古兰经》36:69节经文:“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条经文的一般诠释是:真主没有教授先知穆罕默德诗歌,因为诗歌对他是不相宜的。由于圣使具有不谬性,普通人不具备不谬性,那么,按照教法推理,对圣使不宜的东西,对普通人更不宜。大多数人在为诗歌辩驳时,针对此条经文,采用的都是“尽管……但是”的解释,即尽管经文这么说,但是诗歌依然是被允许的,云云,并引用有关圣训为证。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并没有解决诗歌的宗教合法性问题。对此,阿罗梅·阿莫里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阐释。他认为,此条经文中的“他”这个反身代词不是指圣使穆罕默德,而是指《古兰经》,这句经文的意思应当是:“我没有教授也没有降示《古兰经》以诗歌。”因为紧接着36:69—70节经文说:“这个只是教诲和明白的《古兰经》,以便他警告活人,以便不信道的人们当受刑罚的判决。”阿罗梅·阿莫里因此认为:“根据经文旨意推测是合理的,因为圣使不是诗人,因此做诗或吟诗都是对他不相宜的。”[5](P170-173)笔者认为,阿罗梅·阿莫里的辩驳很有分量,也很有道理,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与他的推理在逻辑上有点拧着,因为否定诗歌者正是依据经文推论说,对圣使不相宜的东西,对普通人更不相宜。因此,按照阿罗梅·阿莫里的推理,结合《古兰经》36:69节与36:70节经文,其逻辑推理与结论应当是:真主没有降示《古兰经》以诗歌,因为这个只是教诲和明白的《古兰经》,是用来警告世人的,要人们皈依正道,因此经文需要晓畅明白,因此诗歌这种体裁对于《古兰经》的教诲作用来说是不相宜的。这样的辩驳解决了诗歌的宗教合法性问题,但这只是波斯学者的辩驳,笔者不知阿拉伯的学者诗人们是如何辩驳的,寄希望于未来能看到阿拉伯方面的相关史料。
三、《古兰经》使诗歌之学立于不败之地
针对诗歌的宗教合法性,大多数诗人学者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辩驳的:《古兰经》否定的是蒙昧时期的诗人和诗歌,而伊斯兰之后,以《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为源泉的诗歌具有毋庸置疑的宗教合法性。上文讲到,欧菲在《诗苑精华》中说,阿拉伯蒙昧时期的诗歌都是粗野货,尽管语言雄辩(fasāhat),但当“《古兰经》的表达(bayān)一展示,在较量时那帮人在《古兰经》典范的质疑面前的软弱无能就被证实。‘表达’这门学问的导师(《古兰经》)将阿拉伯才子们教育成语言动人(balāghat)的一族,他们从它效益的筵席上摘取有用的光芒,使他们拥有了完全的仰仗依靠。辞令雄辩(fasāhat)界的商人们从这无可质疑的宝库中获得指引”[1](P57)。
从宗教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说,作为宗教经典的神圣的《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击败蒙昧时期的诗歌,乃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然而,作为学者,我们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需要从纯粹的学术角度、学理的角度来探讨,蒙昧时期的诗歌为什么会被《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所击败?蒙昧时期的诗歌有着怎样的特征?被视为语言典范的《古兰经》其语言表达方式又是怎样的?
阿拉伯蒙昧时期的诗歌都是口头文学,在各个部落之间流传,在伊斯兰初期才开始进行收集和整理。现存的蒙昧时期的诗歌始于公元5世纪末期,更早期的诗歌已经失传。蒙昧时期的诗歌大多数都是即兴之作,在语言上“诗句雄浑有力、语言铿锵豪放,有时也很粗糙”。总的说来,它是朗朗上口、富有感情的诗歌。因此,欧菲用“语言雄辩(fasāhat)”一词来形容。由于是即兴之作,一般不讲究音律,因而蒙昧时期诗歌的音律“存在某些紊乱……就像用‘麦法尔伦’来代替‘麦法伊伦’,硬凑长诗律一样;又像在一首诗中多处使用不同音符的韵脚字母一样”[4](P29)。“麦法尔伦”和“麦法伊伦”都是格律单元名称。也就是说,蒙昧时期的诗歌在音律方面是紊乱的,欧菲因此说它们是粗野货。结合阿拉伯半岛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蒙昧时期的诗歌属于游牧部落中产生的口头文学,是一种朴实浑然的初民诗歌,没有什么音律规则,即没有格律。
《古兰经》被视为真主传授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天启,圣使口述出来,最初记录于树皮、木块、皮革、布片、石块等物品之上,或圣门弟子们将之记在心中。632年穆圣归真之后,由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命人将记录天启的碎片收集,又让圣门弟子们将心中记忆的天启书写出来。645年,在奥斯曼哈里发执政时期,《古兰经》所有章节汇集成书。至于《古兰经》的语言特征,按照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尔顿的分析,“散文,或为骈文(mosajja'),这种文体由若干不同的段落构成,其每两个词都押一个韵(ghāfiye),人们称之为骈文(saj′)。或为自由体(āzād),这种文体完全自由,不划分为若干部分,并且也不要求押韵,也没有别的羁绊,是一种完全放开的文体。这种散文多用于宣教、祈祷,或者是鼓舞和恫吓民众。然而,《古兰经》尽管被列入散文体(mansur),但却超越于上述两种特征,既不是绝对的自由体也不是骈体,而是各节经文彼此分开,(每节)以停顿(moghta')结束,在那停顿处呈现出语言结尾处的美感(zough),然后语言转入紧跟的下一节,不必须再次出现骈体或押韵的词。……《古兰经》中每节经文的结尾被叫做间隔(favāsel),因为它不是骈体,那在骈体中必须遵循的东西在《古兰经》中没有必要采用,它也不是押韵(ghāfiye),并且我们所提到的所有因素适用于《古兰经》全部各节经文,尤其是第一章(masāni)”[6]。现代黎巴嫩学者汉纳·法胡里在其著作《阿拉伯文学史》中引用了伊本·赫尔顿的观点,并且说:“《古兰经》具有独特的风格,它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总而言之,其比喻和表达都很细腻,雄浑流畅,明白而又优美和谐。此外,它的修辞艺术达到了极高水平。”[4](P100)
上述引文中“骈体”一词,指在散文句子(不具有格律的句子)中,上句和下句的结尾词,或韵律一致,比如:本质(zāt)和生命(hayāt),两词韵律相同,但格律不同;或格律一致,比如:佳话(tarāyef)和奇谈(ajāyeb),两词格律相同,韵律不同;或韵律和格律都一致,比如:“说”的祈使形式(beguyad)和“洗”的祈使形式(beshuyad),两词格律和韵律都相同。这种修辞方式也用在诗歌中,笔者将之译为“内称法”,指在诗歌上下句的相同位置(可以是句首、句中、句尾任何位置)使用对称词,这种对称可以是韵律一致,也可以是格律一致,也可以二者兼备。这是阿拉伯—波斯诗歌的修辞手法之一,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对偶”。也就是说,《古兰经》的句子既不是自由体散文,也不是具有“对偶”形式的骈体散文。然而,《古兰经》的语言是规则有序(nazm-o-tartib)的[7],这一点是公认的,其中(nazm)一词是指句子具有规律性和整齐性,在一定义域中与“诗歌”同义。的确,《古兰经》的语言风格十分独特,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但是句子具有极其特殊的旋律,音律优美和谐,尤其适合吟诵,“古兰”一词的本义即为吟诵。就笔者亲耳聆听之感性体验来说,《古兰经》被吟诵时的优美旋律,犹如空谷传响,神圣撼人,让人心灵沉静。也就是说,《古兰经》的句子具有和谐优美的律动(mowzune),并且很多经文句子的音律具有同律动性(格律的范式),但这种同律动性又不呈现为一定的规则(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之为格律),而且经文长短有致,吟诵起来极其有旋律感。另外,《古兰经》虽不是骈文,但是韵文。尽管上述引文中阿拉伯学者称每一节经文的末尾为“停顿”和“间隔”,而不称之为“韵脚”,但笔者仔细翻阅阿拉伯语《古兰经》,并求证于国内阿拉伯语界的师友,皆认为《古兰经》是韵文,每章都有数个韵脚。《古兰经》中译本除了马坚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之外,还有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就以“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一经文所在的第36章“雅辛”章为例,该章共计83节经文,用了un、in、im三个韵脚。但是,与其音律特征一样,虽然有韵脚,但又不呈现为一定的规则,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之为韵律。也就是说,《古兰经》的语言具有一定同一性的律动和韵脚,具有和谐优美的音律,并且“修辞艺术达到了极高水平”,但又不是诗歌。就笔者的感性体会,笔者认为从某种技术角度来说,大致与中国古代的辞赋相似。“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中国《艺文志》对“赋”所下的定义,此定义正好与《古兰经》语言的吟诵特征不期而合。
朱光潜先生在其著作《诗论》中指出,楚辞与汉赋对中国古典诗歌从古体诗发展到格律诗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六朝的骈俪文加剧了这种促进作用。就笔者的初浅认识来说,从不讲究音律的初民诗歌到音律成熟的文人格律诗歌,是古典诗歌发展的普遍规律(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第152页说,律诗是中国诗歌的特别体裁,“它是外国诗体中所没有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阿拉伯—波斯诗歌格律极其严谨,并且也十分讲究对仗、对称等修辞手法。当然,朱先生的话主要是针对西方诗歌而言,笔者对西方诗歌无知,不敢置喙);从音律讲究的格律诗再到完全抛弃音律的自由诗,是现代诗歌发展的普遍规律。《古兰经》被视为天启神授,其美妙语言特征的形成原因乃是神创,不可探讨。上文讲到,阿罗梅·阿莫里说在《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的训言很多是具有律动(mowzune)和对称(gharine)的句子,具有诗歌的特征,尽管穆圣不被视为诗人,因为诗人的身份是对穆圣先知使者身份的一种亵渎。《古兰经》降示之后,阿拉伯诗人们以《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为典范,以《古兰经》语言的律动、押韵、修辞为源泉,使阿拉伯语诗歌迅速发展为格律、韵律、修辞都齐备的严谨成熟的格律诗(而波斯语诗歌又以阿拉伯语诗歌的规范为规范),并且还促成了骈文的产生(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散文很少,尚无严格意义的骈文,只有一些具有“对偶”性的成语或俗语。伊本·赫尔顿以骈文与自由体散文去分析《古兰经》的语言特点,其实在时间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是以后产生者去分析前产生者。不过,这样的分析也的确对人们认识《古兰经》的语言特点起到了帮助作用)。也就是说,阿拉伯—波斯格律诗和骈文皆是以《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为源泉而形成的。《古兰经》降示之后,阿拉伯诗歌的格律日趋严谨,走向规范化,哈利勒·本·阿赫玛德·巴士里(718-786年)是阿拉伯诗歌阿鲁兹格律规范的第一个制定者,他制定了15种阿拉伯诗歌格律。也就是说,在《古兰经》降示一个世纪之后,阿拉伯诗歌发展为成熟的格律诗。因而,从古典诗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说,具有和谐音律和高妙修辞的《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击败蒙昧时期不讲究音律的初民诗歌,乃是必然。
由于成熟的阿拉伯—波斯语诗歌格律源自《古兰经》,因此诗歌之学被认作是一门崇高的神智之学。夏姆士·盖斯在《波斯诗歌规则宝典》中说,诗歌律动(格律)是一门神圣的必备学问,这门学问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教人如何作诗,而是在于“整齐有序的诗歌和受欢迎的律动这门神智学问对于高贵的气质和懂得阐释至高无上的真主的话语以及圣使训言的含义来说是必要的”[8]。因为,当圣门弟子和宗教学者们在注释《古兰经》和诠释《圣训》时,遇到疑难之处或在记录抄写时的笔误和脱落之处,往往可以根据格律构成的原则,找到恰当的解释和补充。也就是说,通过学习诗歌技艺,可以使人走向更崇高的目标,探索幽玄的奥秘。因此,夏姆士·盖斯将诗歌称为“神智学问(ma'refat)”。夏姆士·盖斯的这段话其本意在于阐释诗歌格律之功用的实质,但同时也为诗歌的宗教合法性进行了辩护。
都拉特沙赫在《诗人传记》中为诗歌的宗教合法性的辩护很有意思。他说:“当《古兰经》迈步抵达苍穹顶端,阿拉伯的才子们就钻进了沉默污秽的席子。……可以推想,伟大的《古兰经》使之作废的那门学问其基点不会缺少知识和实践性。传说,伽兹尼的玛赫穆德国王亲手打过的那个人,别的任何被造物都不能再打他。都说,当玛赫姆德国王要打某人时,那是作为奴仆的被造物的荣耀。因此,任何一门学问,若击败它者是敬爱的《古兰经》,其他任何学问也不能将它打败。”[3](P7)被《古兰经》击败的诗歌,获得了宗教上的豁免权,其他任何学问都不能将它打败。这样的逻辑推理完全出自宗教意识形态,但也真可谓高妙,既指出了蒙昧时期的诗歌语言在《古兰经》的语言典范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又肯定了诗歌的宗教合法性,更把诗歌推向了一个崇高的地位。
贾米在《春园》中也为诗歌辩驳,他说:“那至高无上的荣耀的真主用否定之汁(用诗人的话是这么说的)将装饰《古兰经》的神奇言辞从对诗歌中伤诋毁的玷污中澄清,将关于它的语言动人之学从最低贱的境地(甚至把诗人本身)抬举到圣洁的顶点(我们所认识到和我们所知道的诗歌的地位),并非是要证明这个意思:诗歌就其实质是一桩受谴责的事,诗人因发表整齐有序的(manzum)言辞而受谴责和非议。而是基于如此之上:无能之辈无法以诗歌的鉴赏力去解《古兰经》的规则句子(nazm)。固执者一味较量不属于诗人之列。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要以诗歌和诗人的崇高地位和魔法创造者的崇高身份来装饰诗歌。赞短诗一首:
请看诗歌的基础,出自天经
被人用作对先知使命的否定
为修正与《古兰经》的关系
就把对它的中伤指向诗艺。”[7](P90)
由于贾米的《春园》辞藻华丽(有点汉赋的味道),严格按原文直译成中文后,句子有些绕口费解。贾米首先指出,真主在《古兰经》中降示了几条否定诗歌和诗人的经文(诗人们将这些经文称为“否定之汁”),其目的并非是要谴责诗歌和非议诗人,而是因“无能之辈无法以诗歌的鉴赏力去解《古兰经》的规则句子(nazm)”。nazm一词是指句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整齐性,往往与“诗歌”同义。也就是说,不懂得格律之学的人是无法理解《古兰经》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这样的经文是要使《古兰经》的神圣言辞具有不谬性,免于遭受无能之辈对诗歌的中伤和诋毁。(从这一辩驳看,贾米是赞同阿罗梅·阿莫里对《古兰经》36:69节“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一经文所作的诠释,尽管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因此,这样的经文其实是把“语言动人之学”(使诗歌格律流畅易懂之学)也就是诗歌、甚至诗人本身“从最低贱的境地”(指蒙昧时期的诗歌不讲究音律、粗野)“抬举到圣洁的顶点”(指使诗歌成为一门“神智学问”)。因此,真主降示有关经文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要赐予诗歌和诗人魔法创造者这样的最崇高的地位。(鉴于伊斯兰教是反对巫术魔法的,但承认先知的奇迹,故此笔者认为,贾米这里所说的魔法实际上是指奇迹,但由于不能把诗人与先知等同,因而贾米只能这么说)因此,针对长期有人据《古兰经》经文否定诗歌,贾米作诗说:诗歌的基础出自《古兰经》,不信道的人们无法非议《古兰经》,就转而指控诗歌。贾米作为一位伟大的苏非思想家,其辩驳比其他人的辩驳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
上述各种辩驳的根本基点都在于认同诗歌的“神智学问”性质,将诗歌之学视为理解《古兰经》《圣训》及圣门弟子、迁士、辅士们著作的学问,是探索幽玄奥秘的学问。这与苏非神秘主义的兴盛、形而上的认主之道被苏非诗人们视为诗歌的根本功用密切相关,也与“诗歌神授”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其实,比上述各位学者诗人更早的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9年)作为重要的苏非诗人,虽然在自己的诗歌中没有明确的针对指控诗歌的辩驳,但有著名的一联诗歌,说在幽玄奥秘阐释者的队伍中、在真主的排班中“其前后都排列有伟大的队伍/后面是众诗人前面是众先知”。二者都是真主奥秘的阐释者,他们都是“国王(真主)的近亲眷属”。内扎米·甘贾维的话旨在阐述“诗歌神授”,诗人如同先知一样是接受神的天启的人,具有崇高的品阶,但在真主的排班中位列先知之后。这样既否定了诗人的先知属性,但同时又把诗人确定在一个仅次于先知的崇高地位。这联诗歌被后人不断引用,作为替诗歌和诗人地位辩护的重要依据。
标签:诗歌论文; 古兰经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阿拉伯文化论文; 诗人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读书论文; 波斯论文; 散文论文; 阿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