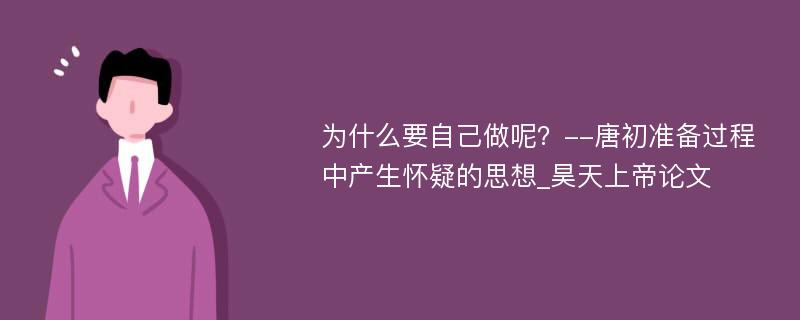
自我而作,何必師古——論唐前期制禮過程中的懷疑經傳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作论文,自我论文,思想论文,制禮過程中论文,懷疑經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朝前期,統治者復興儒學的重點在經籍整理和重建禮樂兩個方面。《舊唐書·禮儀志》開篇回顧了儒家禮儀制度的發展歷程:早在五帝之時,禮儀便是治國之本,後來周公輔佐成王,制禮作樂,形成制度。但春秋以後,諸侯争霸,禮儀日漸衰微,“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到漢朝建立,意圖恢復,通過收集經典來揣测三代的禮儀,“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說,五禮無著定之文”。①剛有進展,遇漢末動亂,魏晋南北朝佛學流行,儒家禮制又趨于停滯。隋唐制禮作樂就是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進行的,可依據的也只有儒學經典和前人注疏。要將書本中語焉不詳的理論變爲現實產物,必然要經歷一個質疑、辨別、取捨、創新的過程。唐代最早的懷疑經傳思想便在這一過程中萌芽。 一、對《五經正義》中禮學內容的懷疑和批判 唐代禮儀中最重要的內容莫過于祭祀,祭天、祭神、祭祖先等都是歷代君王彰顯其統治合理性的方式。新的王朝建立,這些祭祀的具體對象、內容、方式等各個方面都要重新予以確定,中間便產生了很多懷疑和争論,一大批杰出的儒者(以禮官們爲主)都因此而精研禮學,考證古今,爲皇帝建言獻策。他們的基本思路是:以儒家經典爲依據,參考諸家注解,辨別正誤,然後廢除前朝錯誤禮法,重建符合上古禮制的唐代禮樂。 唐太宗時,爲了規範科舉考試,統一思想,規定了儒學各經典的標準注疏,並撰《五經正義》加以推廣。禮學方面孔穎達以鄭玄注本爲權威,十二部經典中《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禮學典籍全部采用鄭玄注。而在現實使用中,儒生們引經據典發現很多問題,指出鄭玄注解的諸多謬誤,開啓了懷疑傳注之風。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②,太尉長孫無忌等人上奏討論“祖宗共同配祭天地”問題,認爲鄭玄注解錯誤,而依鄭注將唐高祖與唐太宗同祭于明堂的做法是違背《禮記》經文的,請求更正。奏章指出:《祭法》中說周人合祭祖宗時以帝嚳配天而郊祀時以後稷配天,以文王爲祖,以武王爲宗,並没有說祖宗合祭。而鄭玄注解說祭天帝祖宗,意思是以祭祀時配食,禘是祭昊天于圓丘,郊是祭上帝于南郊,祖宗是指祭五帝、五神于明堂。③禮官們認爲“尋此鄭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④經過分析論證,建議奉祀高祖于圓丘,以配祭昊天上帝,祭太宗于明堂,以配上帝。 第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上奏議,認爲鄭玄關于昊天上帝、圓丘、郊祭等問題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應遵從。該奏議云: 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圜丘祭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意,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後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謂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 按《周易》云:“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⑤ 唐代將祭祀的天神稱作昊天上帝,昊天上帝之下又有五帝,鄭玄根據緯書,認爲昊天上帝即爲北辰星,名叫“曜魄寶”,五帝則是天上太微垣中的五顆星。這意味著昊天上帝與五帝均爲星辰,可以相提並論。而禮官們則依《周易》、《毛詩》,認爲昊天上帝並非星辰,而是昊大元氣,是太微五帝之體,若視爲星辰,則與五帝地位等同,不是至高之神了。他們還根據史官和天象的記録來提出對鄭玄的質疑:“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⑥由此,昊天上帝不同于北辰星。古代祭祀中,昊天上帝是在祭壇之上的至高神,北辰與北斗則在第二等,能稱爲天的也只有昊天上帝,即可以爲體的昊大元氣。這一觀點後來被武則天所采納,于永昌元年專門下詔明確昊天上帝的至高地位:“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⑦ 另外,許敬宗還提出,鄭玄分圓丘與郊祭爲二也是錯誤的:“《孝經》惟云‘郊祀後稷’,無別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异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弃正經,理深未允。”⑧許敬宗以《孝經》等經典爲依據,推斷上古圓丘與郊祭是同一祭祀,只是名稱不同,因而贊成王肅的看法,反對鄭玄的注解,他還考察並糾正了關于祭祀中篷、豆之數的錯誤認識,這些意見都被武則天所采納。 從這些議奏中可以看出,在禮學領域,當時的學者並非盲從傳注,而是善于考辨經典,提出自己的觀點。關于祖宗合祭問題,鄭玄引《孝經》以解《祭法》,禮官們則反對牽强附會,要求對《祭法》本身進行分析,以回歸周公仲尼之本意。關于昊天上帝等問題,鄭玄觀點的來源在于緯書和星象,禮官們卻根據《周易》和《毛詩》將至高神昊天上帝歸爲昊大元氣而高于星象。關于圓丘與郊祭分立的問題,許敬宗又以“正經”爲依據取王肅而駁鄭玄。這些都表現出他們以經駁傳、捨傳求經、回歸經典本旨的態度。武則天的詔書則表明即使在經傳各有記載並可以互相印證的情况下,也應該根據事件本身進行分析判斷,糾正從前的謬誤,具有抛開經典,實事求是的創新精神。禮官們之所以將矛頭對準鄭玄,因爲鄭注是《五經正義》所采用的標準注解,對鄭玄的反駁就是對官方所定《五經正義》的批判。辨别傳注正誤雖然來源于政治實踐,但卻是一個對傳統經學理論的懷疑和論證過程,推動了經學的發展。 二、黎幹“十詰十難”狀 随著唐王朝禮樂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學者考證和懷疑的內容更加深入,態度也更爲激烈。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大臣們因是否仍要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天地而發生争論。禮部官員薛頎、歸崇敬等根據鄭玄的注解提出:神堯皇帝(唐高祖李淵)是受命之主,不是始封之君,不能作爲太祖以配祭天地。太祖景皇帝⑨最初受封于唐,相當于殷的契和周的後稷,應該以景皇帝郊祭配天地,宗廟之中也應該以景皇帝爲始祖。諫議大夫黎幹則認爲太祖景皇帝不是受命之君,不能以之配祭天地。黎幹因此上“十詰十難”的議狀,以經典爲依據,充分表達了他的質疑和反對。該議狀中涉及諸多對禮學傳注的懷疑和詰難,摘録如下: 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髮》,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攬典籍,更無异同……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髮》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髮》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 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所自出”,謂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鄭玄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一也;注《大傳》稱“郊祭天,以後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于四時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 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晋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 ……⑩ 黎幹此奏摺名爲“十詰十難”,從十個方面提出質疑,現選取有代表性的前三難進行分析。這三難討論的問題都是關于“禘祭”,第一難中講禘祭的性質,黎幹首先指出鄭玄的自相矛盾之處,鄭玄在注《周頌》時認爲:禘祭是祭祀太祖文王的大祭,在注《商頌》時又說:大禘祭是祭天的。而黎幹認爲,《商頌》與《周頌》本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說明,經過對經典的考證可以發現,“禘太祖”與“大禘”祭都是五年一次的宗廟大祭,没有什麼不同。只有鄭玄注《商頌》說大禘是“郊祭天”的,如果說《商頌》中“禘”前面多了“大”字,就成爲祭天了,那麼在《祭法》、《大傳》中的“禘”前面均没有“大”字,鄭玄爲什麼也說是祭天呢?由此看來,鄭玄對禘祭的解釋前後不一,没有根據,也不符合經典。相信鄭玄注解便是違背經典和聖人之義,壞亂祭祀,是大錯特錯的。 第二難中說:《禮記·大傳》講得清楚,不稱王不能進行禘祭,而禘祭是稱王者祭祀其遠祖所由來,由近祖配祭。例如虞、夏出自黄帝,殷、周出自帝嚳,所以他們分別禘祭黄帝和帝嚳,以各自的近祖作爲配祭。鄭玄對這一問題理解錯亂,對禘祭竟有三種不同說法:一說禘祭是祭昊天上帝于圓丘,又說禘祭是郊祭天,還說禘祭是祭太祖文王,大于四時之祭小于祫祭的祭祀。考察其各種說法,都没有確實根據,混亂而矛盾,完全是憑空猜想,不足爲信! 第三難從總體上回顧歷史,認爲三代之前,禘祭之禮的宗旨內容都很明白,而到了漢代鄭玄給予錯解,歷代先儒都不采納他的觀點,因而其理論一直没有變爲現實。黎幹稱鄭玄之言爲“錯亂之義,廢弃之注”,不能用來指導唐代祭祀之典。 在《十詰十難》狀中,黎幹的態度可謂激烈,論證也有理有據。他從經文出發,指出鄭玄的謬誤,稱周公、孔子所撰之經爲“法言”,而鄭玄之書則爲“小注”,鄭玄觀點爲自我臆說,全無典籍依據,從鄭注解經便是“違經非聖”,結果必會“誣亂祀典”。除了與經文相符,黎幹還提出一個理論取捨的重要標準,即看其是否曾在歷史中被成功推行,如果從來没有實際應用,只是憑空解經,那便是“廢弃之注”,必須被抛弃。黎幹上奏之後没有立即得到批復,朝廷又令衆臣就此事討論了一年多,最後考慮到尊敬祖先的因素,還是采用了歸崇敬等人的看法,以太祖景皇帝配祭天地。儘管没有聽從黎幹的建議,大家對他所指出的鄭注的謬誤並没有多少异議,由此引發了更多辯論和思考。此後,在制禮上對傳注的批評和質疑不斷,到修建明堂之時,衆說紛紜,皆認爲注解不可相信,要靠自己的判斷結合實際而行。 三、修建明堂的百年論争 修建明堂的計劃早在隋文帝時就已經確定,但因儒生們對實施方案争論不定而没有動工。到唐太宗平定了天下,重提這一計劃。貞觀五年(631),時任太子中允的孔穎達上奏,建議令群臣就明堂修建的規制、層數、結構等問題展開詳細討論。但由于三代以後明堂之制失傳,典籍又記載不詳,所以討論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侍中魏徵議論道: 夫孝由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盍,故飾宮以廣其敬……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顧所爲,則又傷于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幾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11) 東漢學者蔡邕對禮樂多有研究,曾遍考經典而作《明堂論》,至爲繁複。魏晋裴頒認爲衆說紛紜,雞以决斷,不如從簡,只建一殿用于祭祀就可以。魏徵認爲這兩種觀點都不足采納,前代學者的討論也都没有確實根據,無法選擇,建議根據實際情况,修建五室二層建築,上層用于祭天,下層用于皇帝處理政務,實用又符合禮制,至于具體規格尺寸,根據修建情况來自己决定,抛開歷代經傳之言,以我爲準,不必非去效法古代。這樣,明堂不久便可建成,廓清千年疑慮,成爲後代的樣版。 出于慎重,魏徵的意見没有被采納,修建明堂的各種議論仍在進行而無法付諸實施。到貞觀十七年(643),秘書監顏師古上奏說:明堂制度來自古代,而典籍中没有完整的記載,從黄帝、有虞氏,經夏、商,到周代,各立名號,分別創立規格。歷代學者“衆說舛駁,各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雖然文字注疏繁多、詞采華麗,卻不知裁斷。其實,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朝的焚書坑儒,“典籍廢弃”,“經禮湮亡”,今天所流傳下來的,只是“傳記雜說”而已,用作標準,實在是不合道理。根據《尚書·周書》的記載,明堂有四面,有應門、雉門的規制,那麽明堂應該是帝王的居所。再考察《文王居明堂》、《月令》、《周官》、《尸子》等當時可見的經典,都證實明堂是“路寢”,即帝王的正殿,可以處理政務的地方。 根據這些經典,顏師古對《大戴禮記》提出質疑:“《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又列舉了漢儒孔牢、金褒、蔡邕、鄭玄、淳于登、穎容等人的觀點,認爲他們是“苟立同异,競爲巧說”,都出自主觀臆測,並没有可靠的流傳依據。顏師古的意見是:自古天子平定天下,功成之後制禮作樂,起初創造階段比較簡單,後來逐漸完善修訂。所以,“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随時之義,斷可知矣”。對于前代的經傳注疏,顏師古主張:“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异守株,何殊膠柱?”(12)所以建議皇帝不考慮經籍傳注所言,按照自己的想法修建大唐的明堂,使其傳于萬代。 在這篇奏議中,顏師古懷疑傳注的態度是鮮明的,在他眼中,傳注很多都是注家憑藉想象而來的主觀臆斷,那些篤守鄭玄、淳于登之言而不敢有所突破的人,無异于拘泥固執,不知變通的守株待兔者。他甚至提出,有些經典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對周公的言論也要辨別是否可行來進行選擇,對孔子所定的原則,也還可以補充其不足。這意味著對聖人的經典也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和發揮,而不是一味盲從。魏徵與顏師古都是唐代杰出的儒者,也是著名的經學家,顏師古還曾經受命編撰過《五經正義》,他們以經駁傳,勇于懷疑甚至抛弃經傳的思想說明唐代經學並非只有“疏不破注”的呆板模式,優秀的儒學人纔能够根據實際需要對經典和注疏進行批判性選擇。 當然,不可否認,對禮學傳注的辨別和懷疑很大程度源于政治上建設禮樂制度的需要。昊天上帝、禘祭、明堂等現實問題引發了經學上的討論和争辯,而當這種辯論和質疑產生之後,勢必會啓迪人們思考傳統經學的解讀方式,對經學的發展產生直接影響。“自我而作,何必師古”是儒者們對于明堂修建給出的答案,這一觀點卻來自于對經典的充分討論和取捨,何嘗不意味著他們對于典籍傳注的潜在態度呢?這一思想趨向在中唐以後至宋代發展成經學的疑古思潮,開啓了儒學復興的序幕。 唐太宗之後的四代皇帝都曾决心建造明堂,唐高宗甚至爲此大赦天下,改年號爲總章,並從萬年縣分設出明堂縣以示紀念,而最終還是因學者意見不一而擱淺。直至武則天當政,踐行了當年魏徵“自我而作”的原則,不聽衆議,只按自己的想法,纔完成了明堂建造。從隋文帝開皇三年(583),隋朝大臣牛弘建議修建明堂(13),到武則天垂拱四年(688),明堂建成(14),中間歷代皇帝都有這一計劃,卻終都因學者争論不休而作罷,一百餘年的争論主要根據禮學經典展開,可以想象,其間儒者們對于經傳和各家觀點提出的疑問應該數不勝數,這也是後來造成儒家禮學衰落的原因之一。政治上,安史之亂使以禮樂制度治國的方針遭到失敗,經學上,禮學內容本身代有變异、記載不詳、多有臆斷,又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討論還没有任何成果,再多的研究看起來也終將無濟于事。既没有政治需求,又缺乏學術意義,學者們自然對其失去了興趣。與此同時,《論語》、《孟子》等經典因爲具有更大的心性詮釋空間而符合了社會需要,《大學》、《中庸》從《禮記》中分化而出,經典的重新選擇和儒學話題的轉向成爲必然趨勢。 綜上所述,學界通常認爲宋初胡瑗、孫復、歐陽修、劉敞等“以己意解經”、“疑經改經”的經學懷疑思潮是宋明理學興起的重要條件,並將這一思潮的萌芽追溯至唐代劉知幾《疑古》、《惑經》篇和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學”,本文則認爲,唐代懷疑經傳的思想最早興起于唐前期的禮學實踐領域。唐代自太宗即位(627)後便開始恢復儒學,重建禮樂,樹立以禮樂治天下的政治構想,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代表唐代制禮最高成果的《大唐開元禮》頒行使用。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儒者們針對各種禮學問題,圍繞歷代注疏進行了全面的考證和辯論,對禮學經傳提出諸多質疑。開元十四年(726),通書舍人王嵒甚至曾經上奏,請求改編《禮記》,將舊文删削,用當世禮儀重新編訂(15),足見當時學者的開拓意識。在政治實踐中產生對經學理論的懷疑和甄別,然後修正創新理論再將其應用于實踐,這是經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註釋: ①《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禮儀一》。 ②即《五經正義》頒行後第三年。《五經正義》于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編成,後經校定和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 ③鄭玄觀點可參閱《禮記正義·祭法》,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92頁。 ④《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禮儀一》。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武則天:《五帝皆稱帝敕》,《全唐文》卷九十六《高宗武皇后二》。 ⑧《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禮儀一》。 ⑨“太祖景皇帝”是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因戰功卓越被列爲北周開國第一功臣,北周皇帝追封其爲唐國公。唐朝建立後追尊爲“太祖景皇帝”。 ⑩《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禮儀一》。 (11)魏徵:《明堂議》,《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12)《舊唐書》卷二十二《志第二·禮儀二》。 (13)《隋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四·牛弘》。 (14)《舊唐書》卷二十二《志第二·禮儀二》。 (15)《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禮儀一》。王嵒上奏後,唐玄宗命集賢院學士詳細討論此事。右丞相張說上奏說:“《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雞改易。”他建議考察古今,將當時的禮儀合併統一,重新編撰一套完整的禮儀之書。玄宗聽從這一建議,六年之後,制成《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頒行使用,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