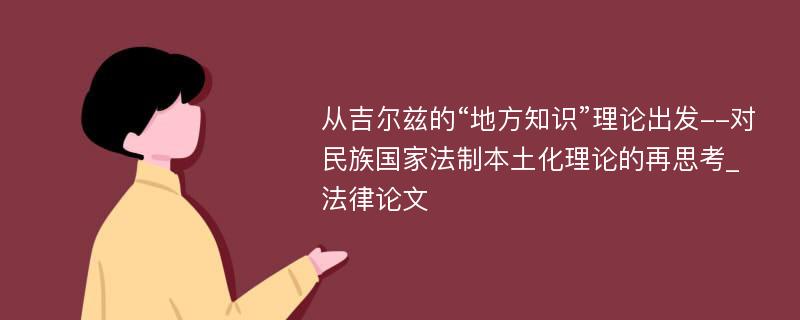
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理论说起——关于民族国家法制本土化理论的几点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尔论文,理论论文,本土化论文,几点论文,性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1—0041—06
笔者曾在《民间法》第二卷撰文提出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宜择取“规制的多元主义”之路径,而不应偏重于“本土化”(即强调以本土资源为主进行现代化,且现代化应顺应甚至迁就本土资源的观点)或“化本土”(即强调与国际化接轨并且废弃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本土资源进行法制现代化的观点)① 在那篇文章中,限于文章篇幅及文章中心的考量,笔者主要是证立了“规制的多元主义”观,而在对本土化与化本土观点的评析上则不很充分。在下文中,笔者将对与本土化论点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再关注(关于化本土论的进一步分析,笔者将另撰专文),以一方面对本土化论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析评,从而弥补笔者前一文章的遗憾;另一方面,也达到进一步证立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择取“规制的多元主义”路径必要性的目的。
一、“地方性知识”理论与本土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吉尔兹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1](第73页) 可谓早已被法学界所熟知。然而,颇有意思的是, 吉尔兹的这个论断却被部分论者用来维护自己关于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应走本土化之路径的观点——并且显然是作为一种较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些论者认为,该论断正是自己观点的有力论据,因为它亦强调法律的“地方性”。然而,吉尔兹关于“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法文化理论真的能够内在地支持本土化理论吗?
欲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简要地剖析一下地方性知识理论的主要内容。该理论是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一文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在该文中,吉尔兹主要是在一种方法论意义上——作为沟通法学与人类学之方法意义上——阐述他的相关法文化理论,仅从这一出发点看,我们就大体可以认为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很难作为本土化论的理论论据,因为很显然本土化理论主要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地方性知识理论中与本土化理论相关的一些论断。吉尔兹确实指出了“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并且他同时还解释了地方性,即“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吉尔兹的这种观点很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年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法律之“民族精神”属性不正是这种“地方性”么?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吉尔兹的观点与历史法学派的关于法律是民族精神之体现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不同:它们都强调法律的“地方性”。
而以吉尔兹该论断作为论据的本土化理论的主要逻辑大致是:既然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此,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知识,也因此,彼地方的知识到此地方就未必会具有适应性(反之亦然),所以,搞法制现代化建设不应走法律移植的路线,而应注重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演绎,也即应走本土化的路子。从表面观之,这种理论由于建基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论断之上,因而从逻辑上看好像是成立的,但一则这种理论割裂了吉尔兹的法文化理论——如下文将要提及的,吉尔兹不但强调法律的地方性,同时还强调法律对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和建构作用;二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倡导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时)吉尔兹承认差异性,并设法去理解它;而本土化论者则肯定差异性,并坚守和赞美这种差异性。这或许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异”[2]。也就是说,一方面,吉尔兹该论断可能仅仅是他的一种实证性结论,也即这里并不包涵他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可能仅仅是他作为一个文化学学者所必须持有之“价值中立”学术态度的具体体现而已,因为——正如韦伯所倡导的——惟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进入到他的研究对象并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吉尔兹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时,虽然我们可以像本土化论者那样理解,但我们亦可认为这个论断其实只是证立了法律移植的前提而已:试想,如果法律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一种必然普适的知识——这意味着法律在各个独立的地方都应大体相当,若真是这样——那么,还有移植法律的必要么?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这么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论断并不必然能作为本土化观点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当年历史法学派的鼻祖萨维尼所持的一个论断也许最能说明为什么“地方性知识”理论(或“民族精神”理论)并不必然支持本土化,他说,“一如古代民族的发展,一个国族的独立发展,通常并非绝对循沿大自然所已然昭示于现代人的那种既定轨程亦步亦趋。各国族的宗教并不一定是她们自身所独具的,其文学亦甚少決然摆脱最为弱势的外部影响——基于同一原理,她们拥有一个外来的、一般的法律体系,亦未非不自然”[3](第29页)。
如果说,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法文化理论的第一个基本论点仅是不必然支持本土化观点的话,那么,该理论的第二个观点即“法律是一种建设性知识”(遗憾且有意思的是,本土化论者总是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吉尔兹法文化理论的这后一要点)则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其并不能作为本土化理论的论据。正如前述,吉尔兹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论断与历史法学派观点本质上并无不同,然而,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学者,吉尔兹肯定不应只是炒前人理论现饭之辈——事实正是这样,在该文中,他接着指出,“法律,即使高度技术化如我们社会中的法律,仍然是,一言以蔽之,建设性的;换言之,它是构造性的;再换句话说,它是组织性的”。那么何谓建设性?所谓建设性,用吉尔兹的话来讲,即“法律具有着将所发生的特定事情置于某种框架之中的力量”,“法律不仅反映地方性知识……法律还是一种赋予特定地方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在吉尔兹看来,地方性知识与法律之间其实主要应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地方性知识可以导生法律,但法律亦可反作用于地方性知识。换句话说,即:虽然法律源自地方知识,但法律并不只是消极地随地方性知识的演变而演变,相反,它能构造、型塑地方性知识从而达到一种两者积极共融的态势——笔者认为,正是在这里,吉尔兹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历史法学派之理论的法文化观点;也正是在这里,吉尔兹超越了历史法学派并创建了自己的法文化理论。而若一旦承认法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法律是可移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既然法律可以影响、建构地方性知识从而达到一种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合的状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移植过来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本土法律)就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由上观之,笔者以为,吉尔兹的观点即使不能用来反对法制本土化的论点,至少也不能用来支持这种论调。
二、孟德斯鸠的法理论与法律移植否定论
本土化论与规制的多元主义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重视法律移植或者说反对法律移植,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在类似的争论中,本土化论者(包括几乎所有的法律移植否定论者)一般喜好将孟德斯鸠相应的法理论搬出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因为孟德斯鸠曾明确宣称,“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4](第6页)。
应该说,从表面观之,作为经典方家的一种话语,孟德斯鸠的这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但若深入而较全面地考察孟德斯鸠的全部法理论及相应的一些情况的话,就可以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在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他自始至终就只出现了这一句与法律移植有关的表述。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创作该书时,其并没有去刻意关注法律移植——甚至法律的问题,因为他明确地指出,“我讨论的(主要)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精神”[4](第7页)。当然,孟德斯鸠并非不关注法律的移植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对征服者提出过自己对法律移植的看法,即“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在各种形式的统治之下,人们都是能够服从的”[5](第41页)。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对法律移植的态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各种强加的法律移植;二是对一个征服者来说,并没有必要去进行法律移植,因为被征服地的统治形式就足以维持地方的稳定——所谓“在各种统治下,人们都是能够服从的”。第二,从孟德斯鸠的法理论本身来看,由于其坚持主张一种自然法理论,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一切事物都有它们的法”[4](第1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孟德斯鸠实际上是承认或说强调法律的共通性的,即虽然各国法律在表现形式上会受地方性气候、风水及习俗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应是相通的——相通于“事物的性质”。如果说事物的本质方面才是事物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有何理由认为孟德斯鸠会否定本质相通的法具有可移植性?第三,本文认为,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可能仅仅是他根据自己的考察所得出的一种实证性结论,也就是说其并没有反映孟德斯鸠的价值判断:因为这句话与孟德斯鸠在论述一个地方的习惯、法律之改变时的一个实证性判断很是吻合,即“人类对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是不可思议地依依不舍的;每个民族都因自己的法律和习惯而感到幸福快乐。我们从各国的历史看到,如果没有大动乱和大流血,人们是很少改变自己的法律和习惯的”[6](第196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又怎么能以之作为孟德斯鸠反对法律移植的论据?进而言之,我们又怎么能用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作为反对移植的适格论据?
当然,如果我们跳出孟德斯鸠的理论,不以一种迷信的眼光而以批判的眼光对之进行分析的话,则我们可以发现他说的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具有合理性,或说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诘。具体说来包括:其一,孟德斯鸠所处的时期决定了其观点(如果说这句话真的反映了他的关于法律移植的观点而不仅仅是他的一种实证性表述的话)的狭隘性。相对于现时期的国际交往和全球化进程而言,显然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更加封闭的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得出这个实证性意味很强的观点确实情有可原——然而,如果孟德斯鸠身处今世,以他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他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答案当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孟德斯鸠的观点即使符合前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法制发展的大致情况,也未必符合现状。其二,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批判孟德斯鸠关于法律最终源于由气候等地理因素决定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因为正是这个观点实际上导生了后来的历史法学派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即使从原生意义上讲,法律确实决定于地方性气候和地方性生活方式,这也决不代表法律就只能从地方性因素中产生——而孟德斯鸠和后来的历史法学派及本文所讨论的本土化论者正是认为由于法律源于地方性所以其只能一直保持地方性。关于这种历史经验主义理论和逻辑,当年潘恩就曾予以了尖锐的批判,他不无辛辣地指出:“你(指历史经验主义者——笔者注)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应该吃肉,或者说,我们一生的开头二十年应该成为第二个二十年的先例”[7](第21页)。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讲,孟德斯鸠等人总是习惯于往后(历史)看,而从来不学着往前(将来)看,如果说这种做法在理论的建构和展开中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关于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就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采取向后看的做法:毕竟——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说——法律永远属于生者。换言之,法律的实践应该永远往前看,而非其他。最后,正如前述,孟德斯鸠只是在此一处涉及到了法律移植问题,因此,这句辄被引述的话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孟德斯鸠的详细证立。既如此,则我们仅凭前人的一句断语就作出一种关于某问题的判断是否是一种明智且严谨的做法?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那些以孟德斯鸠的前述断语作为本土化论据的理论,要么不能算是一种较为严谨的理论——因为其并没有对孟德斯鸠的理论进行一个全局性把握,而仅仅是断章取义地割裂了它;要么则可能仅仅是作为一种论证策略在肢解孟德斯鸠的理论,即明知本文上述所分析之内容,但仍然将孟德斯鸠的话作为论据使用:毕竟孟德斯鸠是一个大家,而部分人又总是习惯于对某些经典理论或论断抱有一种迷信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两种可能的情况都不可取。
三、本土化论的逻辑前提及其批判
如所周知,本土化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在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本土资源应处于一种优先的和主要的地位,反对任何可能消解——特别是用外来法制资源消解本土资源优先地位和主要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和实践。从逻辑上看,这种理论应建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法律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文化,即法律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的现象。换句话说,即法律是不可以被创造的或被创造出来的法律总是会因“水土不服”而失效;也因为这样,所以第二,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在过去是封闭自足的并且在将来也可以/应该是封闭自足的,相对应地,外来法律不会也不可能与本土法律或法制资源相互融合。为什么说本土化论建基于这两个前提之上呢?原因在于,就前者而言,如果本土化论不坚持认为法律的自生自发性,不否定法律的可被创造性,则本土化理论必将成为一种空中楼阁:若法律从来或可以主要不是自生自发的,则本土化怎么成立?同样地,就后者而言,如果本土化论不坚持主张本土法律的自足性,不否认移植法律的可能性,则本土化论必将灰飞烟灭:若移植来的法律可以在本土融合生根,则有何必要坚持本土化?那么,本土化论的这两个逻辑前提能够成立吗?为了下文行文的方便,我们不妨将本土化论的这些前提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是一种自足的文化体系;第二,法律不应被创造;第三,本土之外的法律并不足取,因为它们不能与本土资源融合。很显然,只有这三个前提都基本能够成立,本土化论方可能成立。然而,这三个前提真的成立吗?
首先,关于“法律是一种自足的文化体系”的看法。让我们先看看作为一个文明体系的文化(如中华文化、米索不达美亚文化),也就是比法律文化范围更大的文化之发展是否真是呈现这种特点。从实证的角度看,一种完全封闭且自足的文化确实存在过,然而,这些封闭自足的文化之历史命运却大体逃不出如下两种:其一是走向了衰微甚至消逝。从一定意义上讲,那些曾经辉煌但终究被历史所遗忘的文化,如玛雅文化等,都或多或少地与其过于自闭有关,否则,即使该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自然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毁灭,其文化容貌也应大体能在他处寻见,而不应在地球上几近湮灭;其二是落后于并且是远远落后于他种文化,这方面的例子多见于现存的各种原始的部落文化。相对于封闭自足的文化之衰微、消逝命运而言,那些乐于开放并善于开放的文化则每每取得了本身的一次次地发展,并始终能保持与世界文化水平大体相当的层次。因此,可以说,作为一个文明体系的文化,其较为理想的发展方式不应是自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这一点其实早就被文化学界所意识到,有文化学学者曾对之进行了如下评述,“从文化的本质上看,世界上绝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群体指导自己行为和行为选择的一套标准体系,表现了人们适应和利用自己周围环境的能力。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力求扩展自己的行为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他不能完全拒绝一种先进和进步的外部文化。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东挪西借而凑成的一个文化百衲衣”[8](第165页)。以上的简单论述表明,作为比法律文化范围更大的文化体系,并不是一种封闭自足的文化,既如此,那么作为某一文化组成部分的法律又凭何独独具有封闭自足的特点?事实上,只要我们对现存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华法系、伊斯兰法系及非洲、美洲法系进行考察,就可发现它们大体都是一种“文化百衲衣”:英美法系至少吸收了古日耳曼法、基督教义等外来法文化;大陆法系至少吸收了古罗马法——而古罗马法又是一种以希腊文化为底蕴并糅合其他法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法系至少吸收了印度法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法文化;伊斯兰世界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融合的产物[9](第161页) ……总之,可以这么认为,一个现存且较发达的法律文化,其不仅不是封闭自足的,反而是一种过去事实上开放、将来仍应继续开放的文化体系。
其次,关于法律不应被创造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又可内分为两个子观点:即,一方面法律在过去并不是被创造的——若法律过去就一直是被创造的产物,则本土化论的第二个前提显然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为了使法律不致与地方脱节,所以在将来也不应被创造。那么法律真的纯粹或主要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产物?本文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以下三点:其一,应注意区分人类的需要和这些需要的满足措施之间的区别——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一些持法律不能/应被创造观点者的诸如以下的说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怎么可能产生经济法’、‘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哪有各种公民权法律产生的可能’……既如此,则法律怎么可能是被创造的?”应该说,类似这种说法的前半部分是成立的:没有某种需求决不会产生满足该需求的产物;但因之得出的结论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需求(如商品经济对经济法的需求,又如公民意识对公民权的需求)固然不能创造②,而主要是一种内生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这些需求的措施不能/应被创造。其二,应注意区分法律的创造和法律秩序的创造。本文认为法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创造,而并不认为法律秩序也是被创造之物(相反,笔者认为法律秩序主要是一种自生自发之物)。可以说,本土化论者在论述法之创造性问题时对这两者多有混淆。笔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区分法律与法律秩序的不同,则法律的被创造性属性可能早就会成为一种共识。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许从哈耶克的如下一个论断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说,“……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重构”[10](第201页) ——连最强调人类社会之自生自发属性的哈耶克氏尚且承认法律的被创作性,持其他论点之学者如果对法律与法律秩序进行了区分的话, 承认法律的被创造性就当属必有逻辑了。其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有赖于我们怎么看待“创造”一词:若所谓创造仅指一种纯粹的从无到有,那么毫无疑问,法律主要不是创造之物,而是发现之物。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却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创造一词,即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创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创造,显然主要地是指一种利用自然规律制作各种工具的活动。那么,为什么我们对自然科学家利用自然规律进行工作称为“创造”,却独独不承认人们利用社会规律、自然规律进行法律创制工作为“创造”呢?是这些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自己会以人类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我们对社会领域内的“创造”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标准?总之,关于法律的创造性与自生自发性(也可视为经验性)之间的关系,笔者对庞德的一句相应论断颇为赞同,即“法律是被理性发展了的经验,同时是被经验检验过的理性”[11](第91页),也就是说,法律既不主要是理性创造之物,也不主要是经验自生自发之物,而是两者的共同产物:此时可能理性创造占主要地位;彼时则可能恰恰相反。既然法律一直以来就或多或少地是人类创造之物,那么当然地,在人类社会的未来,法律也一定意义上应该/必定是创造之物。
另外,有些本土化论者还经常提及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中国史上各种“人定胜天”式法律变革的惨败教训,以证立法律在将来不应被创造的观点——可以说,除此之外,本土化论者并没有提出多少关于法律在将来不应被创造的有力论据。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因噎废食心理,对于这种心理,较为中肯的评价应是:谨慎当然是必要的,但因谨慎就放弃做某事则显然是不可取的,可取的态度应是正视可能的困难并想法去克服它,因此可以说,本土化论的这个论据并不具有多大说服力。当然,欲反驳这个论据,我们还可举出一些正面例子,如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日本的1868年明治变法,又如俄国1861年改革,再如中国近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及相应法律制度的改革等,很显然,这些例子均是一种当时社会的创造性活动。至此,可以认为,本土化论的第二个前提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了。
第三,关于移植法律的命运问题。如前述,本土化论者一般认为其很难真正与本土资源融合从而也不能真正生效。这种观点若放在前现代社会是基本符合现实的,但放在全球化潮流已基本不可逆的今天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今各国几乎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移植本土之外的法(包括国际法和别国法),并且实践已经表明各民族国家也是愿意这么做的——因为这是国家强盛的有效途径。当然,笔者支持法律移植原因并不仅限于此,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某些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如市场经济领域、互联网领域等),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最为经济的做法应是移植本土之外已有的法制,而不是等待本土资源对相应法律的生发;第二,我们移植本土之外的法律,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要破坏、取代相应的本土资源,很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国际交往中的便利性考虑,而对于那种纯内国性的交往我们完全可以继续适用原有的法制——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不少基本法律,如民法、民事诉讼法等最后都附有同时与纯内国性条款并行的涉外条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移植的法律与本土资源的关系是一种重叠而不是取代关系,既如此,也就谈不上融合问题了;第三,对于某些失败的法律移植例子,可能不是移植之“错”,而仅仅是移植方式之“错”,因此,只要我们注意移植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其实许多原本移植失败的法律是可以被重新移植并获得成功的。
收稿日期:2005—10—20
注释:
① “规制的多元主义”这个术语是法国学者马蒂在论述世界法(即全球化的法律)的形成模式时提出的,她认为,“规制的多元主义”是指围绕共同的指导原则将具有多样性的各国传统组成一个合成体系。笔者所谓的“规制的多元主义”是受马蒂教授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但又略有不同:它是指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处理本土资源时应以坚持自决原则为前提,以国际化为价值取向,并在对本土资源进行认真识别的基础上对之分别进行保存、倡扬或革除、重构。相关论述,可参阅周赟、黄金兰:《在本土化与化本土之外:规制的多元主义》,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当然,在现代商品社会,有时候需求也是被制造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都市年轻人对诸如“麦当劳”等产品的需求——很显然,这种需求是一种被商家制造出来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