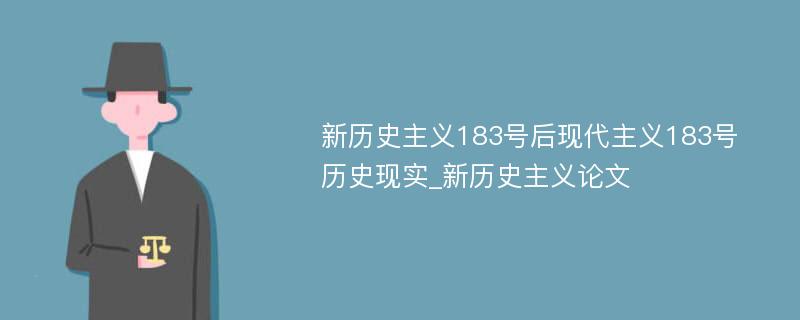
新历史主义#183;后现代主义#183;历史真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真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提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于历史的又一种阐释。[1]限于当时的材料和文章的篇幅,这一论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过去几年中,新历史主义可算是我国文学理论界比较关注的一种西方理论思潮,然而对其理论的局限似乎讨论得还不太多。本文拟在这方面再作一点探索,并请教于同行。
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起点
正如新历史主义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及后来许多提倡或反对该学派的文论家所指出的,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thick description)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厚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论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术语。在后者看来,独立于文化的人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里的“文化”不是指习俗传统一类具体的行为模式,而是指主宰和控制行为的一整套制约机制——如计划、程序、规则、指令等。因此,我们迄今获得的有关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把人置于他所处环境之中、对他与所处文化机制的关系反复加以描述而逐渐形成的。格林布拉特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也是这样。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他把这样一种阅读和阐释的策略称为“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2]
但是,这样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新”,很大程度则表现在它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上。后来确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他们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正如解构主义批评的最主要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近来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被一些人描述为文学批评思潮发展中的“一个突变”,一种“大规模的转移”;是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是从过去“关注语言本体”,转向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3]但是公允地说,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甚至还有不少的新历史主义者并不断然否认他们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处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例如,格林布拉特在论文《莎士比亚与驱魔师》(Shakespeare and the Exorcists,1985)中就曾这样承认:
我相信,当代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当然包括我本人实践——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颠覆了过去那种将审美再现视为与文化语境隔绝的看法,不再把审美看成是自足独立、与产生和消费一切艺术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物质母体根本脱离的领域。这一颠覆,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甚至也得到极其封闭和抽象的解构理论的认可。因为解构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也受到了质疑。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这种不断的超越(它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甚或可以说,它将逼着阐释承认:任何一种观点总要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所以我们说,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4]
这里,格林布拉特不仅追溯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哲学对英美文学批评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影响,而且说得很到位,颇令人信服。文本的不确定性,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混淆,能指将超越意图、并颠覆意图,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宕,同一文本存在着相互取消、而又相互影响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解构批评的基本立场都得到了他的肯定。然而,当这篇论文被收入作者的《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一书时,这一段引文却耐人寻味地被删去了。作者不希望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有什么瓜葛是可以肯定的,但出于什么更具体的动机则令人费解。看来,回答也许要在讨论了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关系之后才能找到。
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到格林布拉特最初确定其新历史主义立场时所做的思考上。格林布拉特在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要点的一篇论文中,曾分析了他为什么不能投靠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而必须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原因。他发现,人们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一个既无天堂式起源,又无千年至福式企盼的世界上”。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描述,例如詹明信和利奥塔这两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就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詹明信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公共”与“私人”、“政治”与“诗学”、“历史”与“个人”等“功能性的区分”都是虚伪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让人类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奥塔从他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则认为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林布拉特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中,所谓的“历史”只是“外加在一种理论结构上顺手捎带一样的装饰”。于是格林布拉特问道:那么,真正的“历史”,那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存在在哪里呢?他发人深思地回答说: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此话怎讲?格林布拉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已是社会现实上升到话语层面后形成的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的表述,这个“资本主义”,已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为此,这才有了下文进一步的界定:它(资本主义)既不存在于审美领域,也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在审美与政治、虚构与真实等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不断地“周转”(circulation)、“交流”(exchange);一种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的“商讨”(negotiation)等等。[5]
格林布拉特这篇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宣言的论文,其实已经用了再明确不过的语言承认,新历史主义的认识起点是建立在利奥塔、詹明信等人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基础之上,它已经在认识前提上否定了此前既定的人文观念的分类,也放弃了对于某一最终真实的追求。这样,把新历史主义看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表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质疑
虽然“新历史主义”的命名系格林布拉特所为,但他不久却放弃了它,觉得还是最初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1980)中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更符合他的原意。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文化诗学”进一步作了具体的界定: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不同的文化实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在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更明确的理论界定和建构方面,恐怕还是应该说是加州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路易·A·孟酬士(Louis A.Montrose)的贡献更大。他自80年代以来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A Poetics Renaissance Crltre,198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1986)和《文化诗学与政治》(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1989)等一系列的论文,深入探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和来龙去脉。
与格林布拉特稍显不同的是,孟酬士明确肯定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他认为,米勒将语言与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是偏颇的。[6]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从来都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被认为是由话语构建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又是所谓的“对话式的”,要受到社会物质方面的决定和制约。孟酬士指出,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共同的信仰、观念、价值观系统,而近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术语越来越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被塑造、再塑造,以致成为该社会一个自觉的公民这一过程联系在一起。这样,任何一种专业活动,连同其内容,就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从事此活动的专家学者本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它同时又在积极地使这些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具体化。而从这一角度看,米勒所谓的“纯粹的语言方向”中的“语言”,实际上就仍然应该是站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立场上的产物。[7]
孟酬士对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承认这一研究构想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史性文本”,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取向的历史观”,一种“既是历史主义、又是形式主义”、“两者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孟酬士说,过去以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区别是勿庸置疑的,而新历史主义之“新”,则在于它摒弃了这样的看法,它再也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了。除上述这些理论阐述,孟酬士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准确描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一种颇为醒目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则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8]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多半是由于这一表述自身结构的工整和均称,于是很快就被看作是对新历史主义特征的最好归纳之一。也许是为了衬托新历史主义的“新”,传统的历史主义便愈来愈被描述成了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一成不变的记录。好像只是到了新历史主义者,才发现历史是处于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之中。殊不知,这实在是对传统与现状的一种双向的误解。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教授在他的专论《新历史主义及其他一些老话题》(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1991)中指出,西方文明进入所谓的“现代”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再也不像古代或中世纪时那样相信一个封闭的宇宙,而是设定下一个开放的境地,始终着眼于未来,尽管这未来很可能包含着将先前的连贯性摧毁、并使过去认为的“现实”变得不真实的各种成分。而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一个个“事件”就不是孤立地发生在历史之中,而是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于是我们看到“顺时性”(temporality)成了“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现实”是有时间意义、时间内容的,也就是说,“现实”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由于这一缘故,历史的不断重写就成了一种必须和必然。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歌德当年就有言,历史必须不断改写应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根据这一切,托马斯教授认为,产生于现代想象的“历史主义”,其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求新、不断更新的历史。[9]如果说传统的历史主义本来就包含了对于自身的不断改写,那么,新历史主义的自封之“新”,则又从何说起呢?
说完“文本的历史性”,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新历史主义者提及“历史的文本性”,想必其中已经包含德里达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意思,但是为稳妥起见,他们多半会更加同意F·詹明信关于“历史”的看法。后者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一书中指出:
依照阿尔都塞“不在场的缘由”的说法也好,拉康的“真相”的说法也好,历史都不是一个文本(text),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我们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10]
詹明信的这一说法带有某种看似折中主义、其实是机会主义的色彩。他一方面承认“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即历史从根本上说是非文本性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做出一番承认的姿态之后,翻手就把历史的这种本质意义上的非文本性搁置了起来。他说这种非文本性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都只能是具体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这样看来,他对历史的看法与新历史主义者所谓历史的文本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诚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的确都是文本化了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者于是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人们也同样有理由追问一句:当我们得到了由叙述人讲述的无数个版本的故事以后,我们还该不该对那个所谓无法企及的真正的“历史”保留着向往和追求的意向?对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然而却是真正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从此就弃之不顾了呢?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历史教授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一针见血地指出,“除某些突出的例子以外,它(新历史主义)其实并不太注重历史”(not very historical)。[11]她这里所说的“历史”,可以有多种理解。从原文的语境看,它并不是指新历史主义不关心客观发生的“事件”,作者似乎在强调新历史主义看不到自身从事的批评和阐释所具有的历史性,认识不到自己所作的阐释,所发掘出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我们不妨对此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径直批评新历史主义不重视“历史”,不重视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真正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等同于文本,这从表面上看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历史”的确不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的记述,不是无序的文物陈列,不是简单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现在很多人趋向于称它为“话语”,就是赋予了“历史”以某种思想的地位。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对孤立的以往事件的记录,而成了所记录的事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反映了某种理解方式的一种文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或许会为自己过去的幼稚而感到羞愧。可是,我们是不是又得反过来想一想,在认识到“历史”是“文本”之后,我们其实仍不该忘记:这“历史文本”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nothing)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一个对于曾经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所以,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的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在用“历史”来指代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
如果要说新历史主义者有什么差别,这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历史文本中性化,把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放逐了。西方学界由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洗礼,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习惯于意识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穿行,在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旗号下,文本与文本似乎可以不受约束地拼接在一起,从而产生种种无须受最终所指检验的意义。说这些意义无须受最终所指的检验,是因为对于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的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搁置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1980)中对于托马斯·莫尔形象的重塑即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他的一生不啻是文艺复兴时期动荡不定、充满危险的政治的一个缩影。15世纪90年代的初期,莫尔还只是摩尔腾大法官家中的一个听差,可是,近40年法律、外交、议会政治等朝政事物的风风雨雨,竟使他于1529年成了沃尔西枢机主教的接班人,继而又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然而,仿佛是应验了他自己对于权贵的一种莫名的恐惧,由于他拒绝支持亨利八世国王的离婚,他于1532年5月不得不辞去了大法官的职务,而后来又由于他拒绝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则使他身陷囹圄,并于1535年的7月6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则希望我们接受另一个莫尔的形象:身居高位时的莫尔怀有一种特别的心情,他野心勃勃,带着某种自嘲自娱,充满了好奇心,又有几分厌恶;他仿佛在观看一场虚构大戏的演出,自己也为它的非真实性、为它凌驾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力量所倾倒。格林布拉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是生活在幻念之中,一个幻念接着一个幻念,从他的《安逸与困苦的对话》到《乌托邦》,幻念不断。人为什么会受制于幻念?莫尔自己的解释是受了权力的驱使,而权利的基本标志,就是以虚构凌驾于世界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已经洞悉政治生活的真谛,然而这所谓的真实其实又是无理可言的荒诞,所有身居高位的人都是受制于幻念的疯人。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切莫小觑了托马斯·莫尔将世界视为一片疯狂的看法,莫尔的这一看法并不仅仅是他的一种修辞技巧,这同时也是他对于人的存在的一种持久根本的反应,他总是以一种充满睿智的人生态度面对险境,格林布拉特称此为莫尔所特有的“超脱”(estrangement)。
格林布拉特试图重新勾画一个他所理解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这里十分有趣的是他所作的一套论证:为了论述他所理解的托马斯·莫尔的可信性,他的别具匠心真是令人叹服。首先,他对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英王亨利八世的御前画师小霍尔拜因的一幅题为“外交家”的名画——进行了一番分析。这幅画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画面上是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派出的驻英大使和大使一位朋友的正面像,两人之间摆着一张桌几,上面的陈设和各种杂物,都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在并排站着的两个画中人的前下方,有一片模糊不清的光影。行家指出,这是画家以另一个透视角度和另一种比例尺寸画上了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若想看清楚这骷髅,你必须将画面调换一个角度,而且要看得十分的仔细。这样,在这同一幅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而且相互抵消的画面,你若想看清画中的另一层面,就必须放弃那个被认为是“正常的”视象,把画像置于我们所习惯的透视角度以外。就绘画语言而论,这种“顾此失彼”的设计,似可看作是一种“悖论”(paradox),而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悖论所取得的画面效果,就在于它能抵制对于真实的明确无误的确定,能够对我们通常用以把握世界的关于真实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对我们十分信赖的符号系统提出怀疑。
那么,格林布拉特绕了这么一大圈所作的这番分析,与托马斯·莫尔的研究有何关系呢?他认为,我们从霍尔拜因画中得到的启发,有助于我们认识莫尔“超脱”的人生态度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文字艺术的丰富内涵。与“外交家”的画一样,在莫尔《乌托邦》的同一文字层面上,也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乌托邦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乌托邦》全书分成上下两部,这种人为的割裂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可以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格林布拉特指出,在语言叙述上,《乌托邦》也多采用与上述总的结构相对应的方式,例如比比皆是的以反面之否定代替肯定的“曲言修辞法”(litotes),其目的旨在使读者能看到问题的多个侧面;又例如文本本身就存在众多忽隐忽现的断裂,在地貌标识、经济交换、行使权力、犯罪概念以及使用武力等许多问题上,都暴露出一些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乌托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乌托邦必须消除上述种种矛盾才能成其为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中存在着这些用以克服上述种种矛盾的社会政治力量,乌托邦又不成其为乌托邦。格林布拉特说,这些断裂,这些东鳞西爪、互不连贯的叙述“飞地”,不仅破坏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统一,而更重要的是,莫尔的这一叙述特点与霍尔拜因采用的畸变画法一样,起着对文本表现的世界的地位不时提出质疑的作用。[12]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更详尽地转述格林布拉特对于托马斯·莫尔以及他的《乌托邦》的分析。但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已经足以看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目的显然不是回归到历史,而只是提供又一种对于历史的阐释。包括格林布拉特在内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家们,其实也都明白无误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它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所留下的印象,人们总以为它所提供的阐释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这样一种新的神话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要说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文本化”。
在以上有关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的论述中,格林布拉特本人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实。他心目中莫尔的形象,出自威廉·罗帕(William Roper)的《托马斯·莫尔爵士传》,此书经过理查德·S·西尔维斯特(Richard S.Sylvester)和戴维斯·P·哈定(Davis P.Harding)的编辑加工后再版;西尔维斯特曾撰文讨论莫尔在其早期著作中的形象问题,对格林布拉特影响至深;著名心理批评家戴维·布莱奇(David Bleich)曾对莫尔的著作与其幼年状况的关系进行过精神分析学研究,这也对格林布拉特产生直接的影响。格林布拉特对《乌托邦》中“曲言修辞法”的分析,借鉴于伊丽莎白·麦卡琴(Elizabeth McCutcheon);他对《乌托邦》中叙述断裂的分析,又得益于路易·马林(Louis Marin);甚至于他对霍尔拜因的名画“外交家”的分析,也是在玛丽·F·S·赫维(Mary F.S.Hervey)关于霍尔拜因的“外交家”的专著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样看来,格林布拉特的独创性又在哪里呢?他的独创性就在于他出人意外地把以上所有的文本巧妙地缝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全新的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丰富了我们对于托马斯·莫尔的认识。格林布拉特的聪明实在令人赞叹不已,但我们不可忘记:他所勾画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只不过是用文本拼贴而成的又一个文本。
历史纪实还是文学虚构:对于海登·怀特的反思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对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上来。她这篇论文,集中反映了西方学界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激烈争论,而这一争论现已远远超出史学的范畴。正如她所说,横跨历史和文学两个领域的一些学科,例如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现在也正受到严厉的攻击。这场争论的焦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文学理论是否应当介入历史写作的问题。对此,福克斯—杰诺韦塞曾有这样的归纳:“即使再不确切,我们仍然用历史来指代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些曾经实实在在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以及具体作家在撰写它们时所采用的方法。而当代的批评家们却不适当地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描述过去的方式,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13]福克斯—杰诺韦塞在论文中作了一条注,明确点出了她所批评的是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及他的《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中提出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
从70年代起,海登·怀特就从历史史实的研究中抽出身来,上升到“元历史”(metahistory)、即讨论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什么是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如何相互转换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继《元历史》之后,他又撰写了《话语转喻论》(Tropics of Discourse,1978)等论著和论文,跻身于史学界的大讨论。由于他从“文本”的写作和阐释的角度看待“历史”,他的著述在史学界引起极大的争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这套后结构主义的史学理论,不想竟成了文学批评理论界、尤其是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的必读经典。
怀特的历史观首先包括对于所谓“历史”的重新定义。他认为一般人们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的事情”是偏颇的,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是某种“能够有意义地加以讨论”的“过去”;“过去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属性,或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因为任何人文学科其实都要考察和研究过去,甚至许多的自然科学也可以把过去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所说的“历史”应该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关于过去的资料本身并不是历史的知识,它只是所谓“档案性”的资料,只有使它化为历史话语的题材,将它纳入某种意义的结构,这些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才能变成“历史”。而“被写下来”和“供人阅读”这两大特点,则决定了“历史”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的文本特性。怀特说,当把历史话语描述为阐释,把历史阐释描述为叙述化(narrativization)的时候,这已意味着在关于“历史”性质的争论中选定了一种立场。什么立场呢?简单地说就是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于是,按照怀特的看法,每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它包括一定数量的“素材”和对这些素材作出结实的理论概念,它还必须具备表现这一切的一个叙述结构,也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上去像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但是怀特强调指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paradigm)。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在《元历史》中,怀特对黑格尔、米什莱、马克思等八位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进行考察,旨在展示迄今未被历史哲学家发现的历史话语的一些认识层面。众所周知,历史文本具有认识、审美和道德的层面,再往深处进一步,历史又包含了一个旨在自我解释的理论运作的层面,这也是历史哲学家们早有认识的。而怀特则希望更进一步,对于历史话语在进行自我解释时所采用的具体策略作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历史话语是通过“形式论证”、“情节设置”以及“意识形态的暗示”这三种策略进行自我解释的,在每一种策略中,历史修撰者又各有四种方法可供选择:供“形式论证”选择的是“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决定论(contextualism)”;供“情节设置”选择的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等原型;而供“意识形态暗示”选择的,则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叙述态度[14]。通过对历史话语运作策略的多层面的考察,怀特提出了他对历史话语的本质的认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论点就是:历史修撰的可能形式,无非就是历史在哲学思辨意义上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说,“历史”只能是写下来的“历史”,说什么与如何说,两者必须合二为一,不能分家。而在实际撰写历史时,我们则首先要为历史表述形成之前在我们头脑中已然存在的诗性灼见赋予某种形式,以使撰写出的历史表述呈现出某种合理性。怀特认为,从逻辑上说,我们并不能证明从某一种理论出发就比从另一种理论出发写出的历史更“符合真实”,我们撰写历史,必须在诸多相互冲突的阐释策略中作出选择,这种选择与其说是出于认识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出于审美或道德上的考虑。而具体地说,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即是说,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也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
如果说怀特在《元历史》中所强调的仅仅是历史修撰离不开想象,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包括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成分,那么,他在《话语转喻论》中则又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断然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他认为,史学家与文学家所感兴趣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他们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则往往一样,他们用以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也往往大体相同。因此,怀特语出惊人地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因为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15]
怀特这套建立在“话语转喻论”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有其自身的认识前提和运思的逻辑,在西方当今对一切本源、对任何与所谓“宏大叙述”沾边的话语都产生怀疑的后现代氛围之中,这种理论一时颇有得风气之先的势头。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形式论思潮的式微,怀特的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诘难,而争论的焦点则仍然是集中在历史所必须具备的真实性这一问题上:怀特认为“历史”是和其他文本一样“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文本,因此认定“历史”的真实性只能是转喻性的,历史话语的论证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第二级的虚构物;而对立面的意见则认为,“历史”首先是对于所发现的事实的一种“报告”——其中包含了历史学家对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的信念,包含了他对这些事实的理解,也包含了他所能设想的关于这些真实情况的种种原因和意义的论证等等。批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怀特所持的立场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决定论”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他就只能看见他的语言所允许他加以概念化的东西。批评意见认为,怀特还不仅仅是混淆了语言的本义用法和语言的比喻用法,而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the"reality")的存在,把实实在在的“现实”,幻化为曾受到罗兰·巴特严厉讥讽的一种“现实-效应”(the"reality-effect")。难怪有人要诘问,既然怀特把一切都视为虚构,那么他的话语转喻论本身是否也成了一个虚构。[16]
怀特对批评意见进行了全力反驳,反驳的意见在理论上似乎也站得住,就其自身的逻辑推论而言,甚至可以说无懈可击。对“历史”这个本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认识竟如此大相径庭,其症结和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以怀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史学理论家把历史仅仅归结为文本,他们把那个实实在在发生、并产生影响的事件彻底地放逐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历史”是文本,他们一直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而我们则认为,“历史”首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其真实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而不是文本。以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例,问题就再清楚不过了。大战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大战所造成的影响,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文本、仅仅局限于文本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应该诉诸我们起码的良知而坚定自己的信念。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纳粹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犹太人,然而纳粹罪犯福利森在战犯审判时却对这一大屠杀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使30万无辜生灵涂炭,然而这一惨案至今却仍被日本的正史排斥。邪恶势力企图改写历史文本的事实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把历史仅仅等同于文本那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人们也许还都记得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大火。那场暴乱的起因是三名白人警察殴打一名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黑人。受害者向法庭投诉,法庭审判时重新播放了目击者录下的当时警察施暴场面的录象。被告的辩护律师以审查事件的全过程为由要求将录象定格后逐一回放,于是警察施暴打人的连续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一个互不连接的单一镜头。律师辩解说,从这些单一的镜头,人们根本无法判定被打黑人在那一个即刻是否已经放弃了反抗,警察既然无法判定对方是否还要还手,于是他们的拳打脚踢便成了制服罪犯的需要。于是施暴反被说成了自卫,施暴者被宣判无罪释放。不公的审判激起极大的民愤,终于酿成洛杉矶的大火和暴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审判结果竟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认识意义。有学者指出,这一黑白颠倒的审判结果,恰好揭示了将最终所指放逐的解构主义阐释学的要害。解构主义的阐释理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承认语言有最终的所指,它把语言文本的意义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能指符号的置换链,而文本的即刻意义(一如那录象的定格镜头)便成了没有确定意义的一种意义的可能。[17]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建立在纯语言层面的构想,然而语言的实际运用则总有其最终的所指。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说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否有最终的所指。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这就是我们唯物主义者对于怀特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
注释:
[1]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3年第5期
[2]参见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3-4;p.179.
[3]J.Hillis Miller,"Presidential Address(1986):The Triumph of Theory,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terial Base,"PMLA 102(1987),281-291;283.Also in his"The Function of the Litaerary Theory at the Present Time,"in Ralph Cohen,ed.,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Routledge,1989,pp.102-111.
[4]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 and the exorcists,"in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eds,.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89,P,429.
[5]Stephen Greenblatt,"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PP.1-13.
[6]这一点显然又是对米勒的误解。其实米勒文中提及的语言和社会、历史的对立,是对学界一种流行意见的转述,而并非他本人的看法。他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一再强调解构主义并不是脱离历史、脱离政治的纯语言修辞性的批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详尽的阐发。
[7]Louis A.Montros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Routledge,1989,p.15;pp.16-17,pp.19-20.
[8]Louis A.Montros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Routledge,1989,p.15;pp.16-17,pp.19-20.
[9]参见Brook Thomas,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32.
[10]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82.
[11]Elizabeth Fox-Genovese,"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Historicism,"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P.214.
[12]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18-25.
[13]同注(11),p.216.此文的中译本译为:“当代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则不管……”。经与原文对照,译文中遗漏了"disproportionately"(不成比例地)这一表明作者对新历史主义持批评态度的重要字眼。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14]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p.ix-x.
[15]Hayden White,Tropics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122;pp.123-125.
[16]怀特本人对话语转喻论所受到的批评有一个很好的归纳,可参见Hayden White,"Figuring the nature of the times deceased":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sec.III,in Ralph Cohen,ed.,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New Rork:Routledge,1989,pp.31-34.
[17]《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主编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教授1995年来华讲学,在一次饭后闲聊时他曾以此为例批评解构主义,我认为甚有说服力,转述在此以飨读者。
标签:新历史主义论文; 后结构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乌托邦论文; 文学论文; 格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