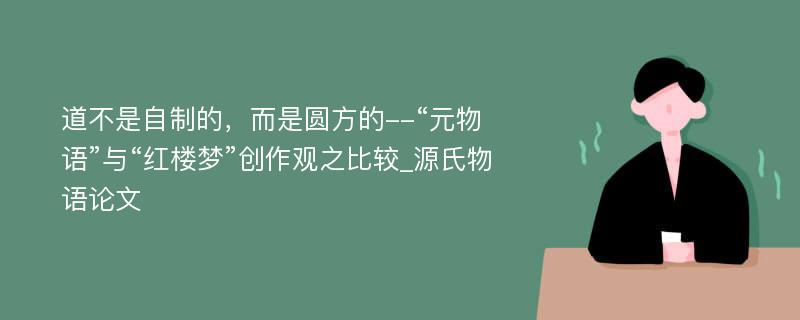
道不自器,与之圆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创作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红楼梦论文,与之论文,观之论文,圆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2)05-0005-08
一、“真”的层面:“真情真事”与“真情实感”对比
艺术真实指的是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来显示社会生活和人性层面的某些本质与规律。[1]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讲,“艺术真实”指的就是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抽象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是在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方面。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本文所探讨的两部名著,可分别用“真情真事”与“真情实感”来进行概括,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艺术真实方面的异同。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妙玉在听到黛玉和湘云的五言排律对至“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时,从栏外山石后现身,劝她们就此收结,并说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2]1094这其实也应视作曹雪芹借妙玉之言来表达自己的创作观。曹雪芹在小说开头的那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说明这部小说是用他的真情灌注而成,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也是有其亲身经历作为支撑的。除了利用正史和野史中的记载和传闻进行考证外,从小说本身也可以看出作者记录现实的痕迹:
《红楼梦》第一回即提到“甄士隐”,即“真事隐”的谐音,后来虽然在他家身上着墨不多,但并未真的将其故事隐去,只不过比较隐蔽: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与贾雨村之口提到甄府与贾府“是老亲,又系世交”,甄家“那等富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2]31;第五十六回写江南甄府里家眷进宫朝贺,也是盛极一时;到第七十五回,就有“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2]1067,贾府在显出颓势的时候,甄家已经完全没落了。在“甄”与“贾”——也即“真”与“假”之间,曹雪芹用曲折的手法来表现出自己的真实寓意,他自己的身世际遇,正可如是观。《红楼梦》所蕴含的“真情真事”,即是从以上归纳出来的,相比较而言,《源氏物语》中所包含的则是“真情实感”。
紫式部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佛经等均有很深的造诣,后来家道中落,就给一个官吏做小妾,丈夫去世后又寡居十年,然后就进宫做当时彰子皇后的侍读女官,写完《源氏物语》后不久,她就离开人世了,这时她还不到四十岁。所以在《源氏物语》第十回《杨桐》中,在简要地介绍完桐壶院的遗言后,便有了这样几句:“作者乃一女流,不宜高谈国事。记此一端,亦不免越俎之罪。”[3]226这与其说是为其避谈国事找理由,毋宁说是因为自身的处境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文化积累和成长经历,让她对当时的时代和身边的生活产生了流转不居的印象,如樱花一样灿然盛放,但又迅速凋零,那种怅惘难遣的心绪正契合平安时代的物哀审美观念。对于紫式部来说,“真情”就是在当时盛极而衰的时代去感悟社会与人生易逝的情怀,“实感”则是她用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生经历去切实体察时代、人生和自然的表现,其中尤以物哀精神为特色。
曹雪芹的“真情真事”与紫式部的“真情实感”,虽然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以及人生经历的相似,而表现出某些相似性——比如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但因为思想文化渊源的不同以及儒道释在两国发展的情况互异,所以同样是“真”,但内涵是有别的。叶渭渠曾指出,宝玉和源氏“虽然都是在尘世生活和遁世理想之间徘徊,但贾宝玉的出家是立足于来世,而源氏是立足于现世的,他的企图遁世完全是停留在观念上。”[4]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而道教在初期的时候,对来世并未予以关注。汤一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中即指出:“道教之所以没有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主要是由于它作为一种宗教其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缺陷……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追求的目标是‘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5]107,这显然没有那些世界性宗教的“来世”观念更具安抚作用。东汉后,佛教曾一度成为国教,但中国人的心性结构更多的是倾向于现实的,所以才有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论述的:公元八到九世纪的时候,禅宗在中国已经正式崛起并取得了和其他派别抗争中的胜利[6]。直指心源、简捷适意的禅宗盛传下来,至宋朝又与儒家合成理学,而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华严宗等,影响渐至式微。汤一介认为,道教后来不得不吸收佛教关于‘形尽神灭’、‘三世轮回’等思想,“这样道教的流传就大大受到限制,而佛教则可以在道教流传所到之处取而代之。”[5]107事实上,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又顽强的,其包容、“无为”的特点是其他任何宗教——甚至世界性的宗教所不及的,到了清朝,更是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鼎盛期。清朝的闭关锁国,这是其统治者视野与格局的狭小所致,不能因为这个朝代受尽欺凌,便否定当时的文化成果。在清朝的时候,道教的发展情况与汉朝早期利用黄老学说来休养生息,与李唐王朝的崇尚道教以给予自身合法性地位都不同。清朝时,道教已经发展完备,包容性、协调性,使其能够在民间得到极为广泛的接受和流传。而紫式部所处的平安王朝,她所接触的道教,还远未达到那种成熟的地步,所以在遇到磨折时,源氏是立足于现世的,而宝玉则寄托于来世。这是可以从道教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这是事物萌芽期与成熟期的分别,不能以此做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造成这种差别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需要注意的:
《源氏物语》成书的年代一般被认为在1001至1008年间,正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中期。这个时期日本政治有两大特征:摄关政治达到全盛和武士集团的崛起。“摄关政治”简称“摄政”,是代替年幼的天皇或女帝来执政的一种官职,刚开始的时候是由圣德太子这样的皇族来担任,公元855年藤原良房成为清和天皇的监护人,第一次以非皇族的身份摄政,藤原家族此后又与皇室结为姻亲,从此外戚便开始干预朝政,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贵族阶级间不惜近亲联婚,甚至不同辈分之间也可通婚——《源氏物语》中,源氏追求桐壶帝续娶的女御藤壶以及自己的婶母六条妃子,即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投影。
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以及自身因素的局限,外戚摄政不久便暴露出种种问题,集中表现在政治腐朽和生活堕落方面,这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贪官污吏得以横行,社会矛盾很快变得尖锐起来,公元十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大叛乱事件,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此时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于是武士集团趁机而起,逐渐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源氏物语》中各大势力之间的斗争正是以上述历史作为依据。与此相较,《红楼梦》写作的时代则是另一番情景,这个时期的中国一方面被笼罩在康雍乾盛世的光环下,另一方面危机四伏:清政府通过设置军机处来进一步集权;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又布置了军事镇压网;大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剥削的加重使底层人民几乎破产,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等因素,整个社会处于很不协调的状态。《红楼梦》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谈那钟鸣鼎食之家的败落,就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2]27,这正是对当时清政府危局的一个隐喻。
既然关注的重心不在国事方面,那就只有用心于人情。这里的人情主要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人受自然风物影响所体会到的情愫。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与争斗,在紫式部的笔下化作了共同为追求美而携手,一起为美的消殒而叹惋。葵姬的死和桐壶院的去世,均令源氏倍感心痛,这还是人之常情,而第九回《葵姬》中,源氏与头中将忆及往昔偷香窃玉之事,“结果往往是慨叹人世之无常,相与泣下”[3]205,就让其他时代和地域的人们有所费解了,其实这里包含的正是“物哀”的精神。那些有违人们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的事情,在《源氏物语》中并没有受到强烈的谴责,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都将其视作可以理解的“本能”之一,这种“本能”与“忠孝”等“人生重大事物”是并行不悖的。面对美的消殒,紫式部秉持的是“物哀”的美学理念,所以小说中出现大量细腻、优美的场景,作者和其中的人物会一起抒发对于生命易逝的叹惋之情。当处理“本能”的种种事情时,作者同样以温和、沉静的态度加以面对,这种理念来自她的时代和自己的生活,但又有自己的发挥。紫式部在这部小说中持有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皇权观念相契合,她的写作因此具有一种消遣的性质,虽然含有悲感,但并未试图对当时的社会与人生加以批判,而是将其升华为对于美的皈依。
这种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观,体现的正是“道不自器,与之圆方”的含义。《二十四诗品》第十七条《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7]145婉转变化要应节合度,“道”指抽象的原理,是在对“器”的分析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但又不拘泥于“器”,还要赋予“器”以“圆方”——即方圆适当,在小说中即指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也即是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能反作用于实践,从而产生更先进的事物。
“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在《红楼梦》中同样有生动的展示。《红楼梦》中的“道”,表面看起来,似乎与当时的实际生活并不相涉,第一回中,空空道人向石头谈到其上刻的故事:“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2]4但读者自可从大观园里人物与外界的应酬以及园内人物的日用方面探得时代的印记。
《红楼梦》中的“器”,主要是指贾宝玉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们之间的相知相惜的故事。贾宝玉认为女子是水做的骨肉,清净自在,而男子则是须眉浊物,不堪映照。对于天地自然的风景,也无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女子而倍添光彩。而一旦她们遭遇不公,作者则为之深感惋惜。源氏对于其所喜爱的女子,则是有着占有欲的,不像贾宝玉是怀着敬慕的心情去看顾。相对于《源氏物语》中女子们的那种沉静和直观,《红楼梦》中更多的是不屈和遮蔽。无论是像林黛玉那样有所依傍的,还是像晴雯、鸳鸯那样势单力薄的,都会竭力抗争不公的命运,这种抗争精神在《源氏物语》中是很少见的。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道”,是因为曹雪芹当时已经处在社会的边缘了。他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过的是举家食粥的日子,这和紫式部在宫廷里享受的生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红楼梦》遮蔽了许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的事情,这主要是因当时文字狱的严酷,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又通过那些女子们不屈的抗争来表达他对社会的不满,这是更深层次的揭露。紫式部对当时的时代则没有多少深入的反映。鲁迅评价《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8]242这“本真”正是他在早年所遇到的那些美丽而自由的女孩子们,他描写了这些女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讲述了她们所受到的不公,他是在蓬蒿之间为这些人间的精灵抒发浩叹,这与紫式部以御用文人的身份为天皇写书做消遣又是不同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源氏物语》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和《红楼梦》所体现出的悲剧意蕴同样是深挚的。
二、“善”的层面:伦理的疏离与礼法的规约相较
对于平安时代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国来说,“道德”与“礼法”是形成其时代风气和文化氛围至为关键的要素。鲁思·本尼迪克特曾这样分析日本人的道德观:“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9]137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源氏物语》体现了日本人的“人情”,这种人情表现为“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9]123而“中国人忌谈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的享乐,由此免去人际间许多纠纷,家庭生活也相当平稳和谐。”[9]127这种观点需要辩证地看待。从《诗经》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爱情和性的态度并不忌讳,这在后来的文学艺术和风俗传统中亦可屡屡见到,只不过由于宗法制的形成,人们受礼法的约束越来越严,心中自然的性情也就被遮蔽了。
而日本人——尤其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他们并没有将道德与“忠义”等“人生重大事物”相联结,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论述的,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9]137如此一来,日本人便将道德和所有能导致其陷入矛盾状态的事物隔离开来,《源氏物语》中那些在我们看来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一旦行为主体表示忏悔,很快就会得到大家的谅解,正是因为道德的这种疏离状态,使人们没有将其作为判断一个人内在品质的准则。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其所提出的礼法观念则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规则。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善与恶即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首先对道德的缺失表示深切的忧虑,《论语·卫灵公》:“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0]154孔子将“德”归结为对于“礼”的遵循,“礼”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表现是《论语·颜渊》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129,在伦理道德层面则指“孝、慈、恭、敬、仁、义”等,孔子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努力达到《论语·颜渊》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0]125的状态。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对于“礼”又有自己的阐发,在伦理道德层面,《孟子·离娄上》讲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10]265孔子和孟子从制度层面对人们的道德进行了规约,而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则进一步从人性的层面来提出自己对道德的认知。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1]455所以要“以义制利”,即用法制、礼义来节制人的利欲;要“礼以养情”,即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人的性情。及至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之中善与恶的斗争已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随着古代社会的不断演进,礼法对中国人心性的规约也愈加严苛,这在《红楼梦》中有非常明显的展露。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即是,大观园里的那些丫鬟等身份低微的人,对于非直系的长辈——如赵姨娘,时常是有顶撞的,但对于老太太、太太等直系长辈——甚至是同辈,是敬畏有加的,曹雪芹这样安排,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出当时礼法的森严,那是很难逾越的屏障。这种屏障对人性的遮蔽,是更潜在,也是更有力的。
相比较而言,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9]137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在日本,“古代故事并未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近代则成为一个主要题材。”[9]143这里的“义务”指“忠、孝、仁”等范畴,作为日本古代小说代表作的《源氏物语》,确实没有将这种冲突作为故事的中心,而《红楼梦》则相反。大观园里的那些血泪与这种冲突是息息相关的:《红楼梦》第七十七回,晴雯在“四五日水米不曾粘牙,恹恹弱息”[2]1102的情况下,被王夫人硬是赶了出去,贾宝玉目睹此景,虽然心中极不愿意,但也不敢多发一言,只能回来后“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及至晴雯撒手而去,宝玉才和着血泪写成一篇《芙蓉女儿诔》,既是悼念,更是于沉痛之中表达出的最有力的抗争。
《源氏物语》中很少出现以上抗争的局面,这部书里的嫌隙与不平,虽然与“忠、孝、仁、义”等有关联,但总能在美的陶冶和宿命的观念中得到化解。紫式部在第八回《花宴》中写源氏应皇太子之邀表演舞蹈,那舞姿美妙无比,连对他有怨恨的左大臣看了,也“浑忘旧恨,感动流泪。”[3]117第九回《葵姬》中讲到,源氏明知自己的妻子葵姬是被六条妃子的生魂蛊惑致死的,但终于想到:“死者已矣,无非前世宿命制定”,后来还是“回心转意,对六条妃子的爱情终于不忍断绝。”[3]204《源氏物语》中道德的疏离与《红楼梦》中礼法的规约,是各自的作者对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经历分析归纳后形成的认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认识在小说中生硬地加以传达,而是进一步将其升华为独特的创作观,最后将这种创作观转化为多姿多彩的人物。
具体说来,紫式部通过对平安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经历的分析,形成了“物哀”的审美理念,《源氏物语》即以这种精神统领全篇。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本居宣长在注解《源氏物语》时,对“物哀”这个理念有深入的阐发,在他看来,“物”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物哀”就是两者相互协调一致时产生的和谐的美感,这种美感表现为优美、细腻、沉静和直观。根据本居宣长的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到:这种理念不重在解决矛盾和纷争,而是将视野集中在主、客观相互交融时产生的适度的、玄静的情感方面,《源氏物语》里虽然也有许多生离死别和其他令人伤心欲绝之事,但紫式部总能让小说中的人物“哀而不伤”,让他们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来应对人生。曹雪芹则通过审视康雍乾盛世,使用了“悲凉”的审美理念,《红楼梦》正是以此结构全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谈到大观园就像当时表面繁华的清政府一样:“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8]239,秦可卿、金钏、晴雯等人的相继消殒,让他顿感生命之易逝,在鲁迅看来,这“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8]239这“悲凉”又不仅仅是作者对亲历生活的感知,更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透视,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同样被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而曹雪芹正是在悲凉之中树立起自己的风骨,用满含血泪的文字为我们展示没落贵族傲然不屈的气质。
三、“美”的层面: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各美其美
《源氏物语》里的“悲”,是“无常”之“悲”,是对生命终归要凋零的怅惘之情;《红楼梦》里的“悲”,是为蕴含天地灵秀之气的女孩子们所受到的不公而发出的控诉之声。虽然这两部书中均有一些喜剧性的人物,但总体看来,仍是悲剧人物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这些悲剧人物又是令人思索不已的圆形人物。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讲道:“在成效方面,扁平人物是不如圆形人物的。但要取得喜剧性效果时,扁平人物就大有用场了。”[12]63而对于圆形人物来说,“即使情节的发展要求他们发挥更大作用,也能当之无愧。”[12]66所谓圆形人物即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他们的性格有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而且其性格的各个层面又有相互对立、相互生成的特点,当这些层面之间显得均衡时,就与“物哀”有了共通之处,当出现失衡甚至难解的局面时,就有可能达到更为深沉有力的美学意境,“道”与“器”之间的辩证也因此显出别样的光彩。
费孝通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做主题演讲时总结出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准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让各种文化共生共赢的一种努力。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亦曾提到:“通常一本构思复杂的小说不仅需要有扁平人物,也要有圆形人物”[12]62,这两种人物在小说中是应该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源氏身边那些只追求声色的人物即可理解为扁平人物,《红楼梦》里的薛蟠也是这样的人物,正是有了这些丑角的映衬和充实,名著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比这两部名著中的圆形人物的不同,也可以从中发现《源氏物语》中的圆形人物,其性格的各侧面之间是互不干涉、协调一致的,而《红楼梦》中的圆形人物,其性格的各个层面是在矛盾中体现对立统一的。
紫式部是将作品呈现给皇帝,这种写作所具有的消遣性决定了其创作所遴选的题材与风格,均与当时的贵族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的是他们优渥而感伤的心绪,而曹雪芹虽然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即写道,那块未曾补天的顽石笑称这些“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但正如其自题绝句中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2]7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撰写此书的一片深心。因为是呈现给皇帝看,所以紫式部尽量少地在小说中表现当时社会中已经出现或隐伏着的种种矛盾,她将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均推向“物哀”的层次,让人在细腻、沉静的氛围之中体会那种无常、易逝的美,这种美虽然让人感伤,但却是温和的,是人在面对事情和景物时主观与客观合而为一、协调融洽的一种状态。而《红楼梦》中虽然也有许多情景交融的描写,但曹雪芹意在抒发心中的悲凉抑郁之气,他让贾宝玉、林黛玉和晴雯等具有顽强的反抗性格,从而使其言行均具有一种特有的“风骨”。
这里的“风骨”不仅是指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更是用来形容作品中人物以及作者本人顽强气概的一种风格。与《源氏物语》中主人公们在沉静中消解彼此的矛盾不同,《红楼梦》中的人物,除了那些醉生梦死,对身外世界漠不关心的人外,都会敏感地意识到大观园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只不过暂时还能维持住场面。即使像金钏这样地位并不高的丫鬟,在面对不公正时也会竭力反抗,甚至以死抗争,更不用说贾宝玉、林黛玉等直接体现曹雪芹意志的人了。紫式部和曹雪芹站在各自的立场展开故事,他们早年的生活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出身于贵族之家,但他们的成长之路是很不同的。曹雪芹经历的波折要比紫式部大得多,对于社会与生活的体察也深广得多,也即在“器”的层面要更宏阔。“道不自器”,作者的“道”,虽然来自社会生活之“器”,但又会因为自身禀赋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不同。紫式部是用女性的笔触来书写宫廷和贵族的故事,她尽量让文字和情节显得圆融,这样既符合日本文化中“物哀”的美学精神,又能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纤细而又敏感的体会表达出来;曹雪芹则运用了沉痛而又流丽的笔法描述了荣宁二府的兴衰荣辱,他的文字融典雅与通俗于一体,诗词歌赋和俚语杂谈交织成一片生动的图景,而其凛然的风骨又通过小说主人公们的言行呈现出来,让人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为切近的体察。
作者的写作理念同样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之中。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两部小说均表现得跌宕起伏,但又各具风姿。这两部小说虽然都是描写几个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消长,但在《源氏物语》中,源氏是身居高位,而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做的是“富贵闲人”;源氏的一举一动,要顾及到朝廷的颜面以及自身的地位,他和许多女子的来往,因此总是小心翼翼,况且他也不仅仅是想和对方在精神上有共鸣,而是希望更进一步发生关系,紫式部正是以源氏的得势与失势以及他和女子们关系的亲疏来谋篇布局。曹雪芹同样也以荣宁二府的“得势”与“失势”来掌控全篇,但作为男主人公的贾宝玉,和源氏比起来就纯粹多了:他钟爱这些充盈着灵秀之气的女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非分之求,只要能在大观园里看着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就已经很开心了,曹雪芹通过设置一系列连环曲折的情节,来让贾宝玉不断地看到香消玉殒,他和这些女孩子们的相知与分离都在草蛇灰线似的结构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衡量一部小说成败优劣的标准,是看其能否成功地塑造出生动、完整的人物形象,也即“圆形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又是通过作者在思想观念和写作理念熔铸成的创作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道德”取向与清代的“礼法”规则造成了两位作者在创作观方面的差异。紫式部秉持着自己的创作观,又充分吸收和转化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精神,从而创作出日本——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曹雪芹则在自己的创作观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士宁折勿弯的“风骨”气概,在艰辛的环境下辛勤锤炼,终于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了最高峰!
在小说艺术中,“道”指创作观,“器”指现实生活,“圆方”指作者在特殊的创作观指导下,将亲历的生活升华凝聚为生动而完整的人物形象。面对着各自的社会生活经验铸就的“器”,两位作者在不同的创作观的指导下,从其中提炼出与自身禀赋相契合的“道”,然后在小说中规划“圆方”——即创造出具有时代典型性和自身独特性的生动、完整的圆形人物,从而使《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并立于世界伟大小说之林,“道不自器,与之圆方”,正是他们用辛勤的努力亲证的道理!
真正的圆形人物,体现出的正是性格中多层面的对立统一。《红楼梦》里的贾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第十七回中,可以看出贾政对宝玉虽有不满,但仍是非常器重的,望子成龙,这是那个时代普遍的观念,他也没有超出这个藩篱;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中,我们就可见作为封建秩序维护者的家长,贾政严苛地施行了自己的治家理念,而到第七十一回,他“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宴然复聚于庭室,自觉喜幸不尽”[2]1001,这又是一个羁旅中怀念亲人的形象了,再看他回家后,“一应大小事务,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共叙天伦之庭闱乐”[2]1001,传统士大夫的清闲与自适,在在可见。到第七十五回时,这位一直以严肃的面貌示人的家长,竟当着大家的面讲起了笑话,至此,贾政的性格的丰富与深刻,已被作者描画得生动无比。贾政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从这个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他也有寻常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只不过比较隐蔽,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曹雪芹这样的作家来加以展示。这样具有内在对立统一特征的性格,在《源氏物语》中的人物身上是很难找到的,他们秉持的“物哀”审美理念,大大消解了性格中矛盾的生成。
曹雪芹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等级尊卑分明,但带着的是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紫式部是以一个女性的纤细和敏锐,在比较优渥的环境中,来抒发物哀的心绪;他们作品中的圆形人物因此有了很大的不同,而那些扁平人物,则显得非常相似。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圆形人物,都必须与书中的扁平人物搭配得当,这样才能让小说的悲剧色彩和喜剧色彩交织得更加完美动人。在《源氏物语》中,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经常能够在同一屋檐下诉说着相似的衷肠,即使和源氏有嫌隙的人,也会被他那优美的风姿所吸引,从而化解以前的怨怼——物哀正是形成这种情形的最重要原因。而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对那些他认为“无趣”、“污浊”的人,基本上采取无视或蔑视的态度,而这些不被宝玉“待见”的人,对待宝玉和他欣赏的人,也只是仅仅保持着恭敬的态度,内心也不见有多少钦慕流连——这也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另一种体现吧。但曹雪芹的内心又是十分炙热的,这悲凉之雾不能遮蔽他那带有同情之理解的目光,想反,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去寻找寒冷中的些许温暖。从这点来看,曹雪芹和紫式部一样,都是在内心深处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能够“美美与共”的。
四、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关联之探讨
曹顺庆对“媒介学”曾作出允当的界定,在他看来,媒介学是与渊源学相对的一个与影响研究有关的术语,是影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是外国作品进入本国的方式、途径、手段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13]。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是有着更加切实的意义的,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影响研究中的另外两种研究方法——流传学与渊源学,均是基于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红楼梦》的成书受到《源氏物语》的影响。媒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这两部名著的关系时,我们就可以将《源氏物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受《源氏物语》的影响,视作一种催化剂在其中起作用。催化剂在参与化学反应的时候,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在反应前后均没有变化,但它却可以加快或降低该化学反应的进程。
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两部名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催化剂的存在。中国自先秦、汉魏至唐朝时的文化是紫式部借鉴吸收的文学经验,但这部分文学经验只是一种参照,《源氏物语》的整体意境以及包含的思想,是“物哀”和“神道”,这都是日本特有的文化范畴,《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凉意境以及儒道释——尤其是道教思想的成熟,亦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征。两部名著各自秉持着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创作,虽然对外来的“催化剂”有借鉴,但无论是小说思想还是艺术等各方面,均按照各自的路径发展。
汉唐文化作为一种媒介来催化当时平安时期的日本文学——尤其是小说体裁的形成,反过来,日本文化也催化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唐朝后,大致分为两支:一支是在中国本土发展,一直递嬗至清朝;另一支流传至日本,经过作家和学者的吸收,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思想和物哀观念融合,共同形成新的作品,如《源氏物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源氏物语》首先受到影响,然后经过七百多年的发展,小说这种体裁突破国家和文化的限制,按照自身特有的规律演进,最终在中国结成《红楼梦》这枚硕果。对这两朵“花”的评价不能用高低优劣的方式,而应根据各自成长的环境来做出相应的判断。
饶道庆曾谈到,国内学者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两部名著的比较,基本上是循着“惊人的相似——本质的不同——深刻的文化根源”[14]这样的思维模式来进行。如果我们将这种模式翻转过来,可能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开拓一片新的疆域:从文化根源上来看,中日两国文化均具有一种强大的吸收整合能力,外邦的文化一旦进入本土,会很快被纳入到本国的文化体系、氛围之中,然后生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成果。
叶渭渠在论述这两部名著的共同思想文化渊源时,亦指出:“由于两国的风土、政治经济条件、宗教文化形态各异,尤其是各自以自己的本土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汲取和消化,其影响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4]这种影响更多是以“媒介”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的儒释道——更具体说是儒、禅、道——作为外来的文化更多起的是一种催化、一种媒介的作用,紫式部在这种“催化剂”的影响下,以日本本土的宗教和审美观念为基础,创造出了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曹雪芹所在的时代,不仅仅是传统社会的末期,又是道教发展到顶点的时代,同时小说艺术经过不同国家间的流传和发展,也到了成熟的阶段,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红楼梦》应运而生。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这两部名著的比较中关联起来,正是基于以上事实的存在。
“媒介学”与“主题学”的关联,主要在爱情主题与悲剧主题方面。无论是先秦的诗歌还是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都直接影响到日本小说的生成和发展,对此,严绍璗在《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15]中即有详细的论述。悲剧主题更是两个多灾多难国家永恒的主题,日本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学经验时,对此亦是十分看重。
“媒介学”与“题材学”的关联,更多体现在盛极而衰的家庭和时代,以及缤纷错落的情感纠葛方面。紫式部所在的平安朝与曹雪芹所在的乾隆盛世,均是在繁华的表面下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盛极而衰,在作家眼中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宿命,两位作者对此均是不胜感慨的。
“媒介学”与“文类学”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小说文体自身的嬗变方面。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作家很有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发展的痕迹,从而自觉地加以遵循。一种文体的演变,有时是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寻绎出线索和规律,对于文学理论、文化递嬗的研究都将是极有益的。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结合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影响中的平行,平行中的影响,对这些考辨得越清晰,梳理得越细致,越有利于将两种研究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越可以在更加深广的层面激活两种研究内在的潜能与联结的可能,这样就可以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路径。
标签:源氏物语论文; 红楼梦论文; 贾宝玉论文; 曹雪芹论文; 紫式部论文; 圆方论文; 日本源氏论文; 文学论文; 源氏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