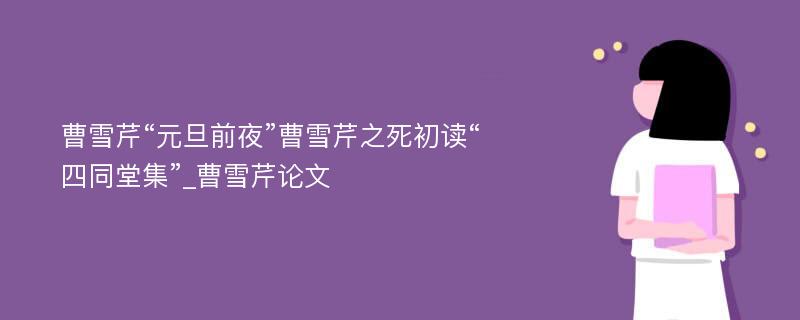
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本论文,除夕论文,卒于论文,初读论文,四松堂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与刻本的关系
《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是胡适在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买到的。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我在国图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在善本室仔细看了这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胡适在书前有一段长题,可以借此了解此书的情况,兹摘录于下:
我访求此书已近一年,竟不能得。去年夏间在上海,我曾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借此书,他回信说辛亥乱后失落了。今年四月十九日,松筠阁书店在一个旗人延某家寻着这一部稿本,我仔细翻看,见集中凡已刻的诗文,题上都有“刻”字的戳子,凡未收入刻本的,题上都帖(贴)小红笺。我就知道此本虽(确)为当日付刻的底本,但此本的内容都有为刻本所未收的,故更可宝贵。
即如第一册《赠曹芹圃》一首,不但《熙朝雅颂集》《雪桥诗话》都不曾收,我可以推测《四松堂集》刻本也不曾收。
又如同册《挽曹雪芹》一首,不但题上帖(贴)有红笺而无“刻”字,可证其为刻本所不曾收,并且题下注“甲申”二字,帖(贴)有白笺,明是编者所删。此诗即使收入刻本而删此“甲申”二字,便减少多少考证的价值了。
我的狂喜还不曾歇,忽然四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先生向晚晴簃选诗社里借来《四松堂集》的刻本五卷(下略所列卷数),卷首止刻纪昀一序和敦敏的小传,凡此本不曾打“刻”字戳子的,果然都不曾收入。
三日之中,刻本与稿本一齐到我手里,岂非大奇!况且世间只有此一个底本,居然到我手里,这也是我近年表章(彰)曹雪芹的一点苦心的很大酬报了。(下略)
十一、四、二五,胡适。
胡适的这段题记,基本上为我们说清楚了《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与《四松堂集》刻本之间的关系,胡适说:“集中凡已刻的诗文,题上都有‘刻’字的戳子,凡未收入刻本的,题上都贴小红笺。”我手头恰好有《四松堂集》的刻本。这本书说来也巧,一九五四年我刚到北京不久,在灯市东口一家旧书店里,在书架的最底层的面上,放着一部《四松堂集》,书上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心想可能是同名的书罢,我随手拿起来一看,卷首居然署“宗室敦诚敬亭”,开卷就是“嘉庆丙辰长至后五日河间纪昀”序,这是千真万确的宗室敦诚的《四松堂集》,当年胡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有买到,还是蔡元培给他借来的,我却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部书,实际上书店老板根本不知道这书的价值,所以任其尘封,以后我在各书店一直留意,五十年来竟未能再遇,这次我就拿这部《四松堂集》的原刻本,与胡适的这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对照,验证了胡适的话是大致可信的,刻本比底本少了很多诗,连悼念曹雪芹的那首诗刻本都未收。不过,胡适对于《挽曹雪芹》诗题下的“甲申”两字,却仍有未经深思之处,此事待下文再论。
特别是胡适只注意到“付刻底本”删去的诗,却没有注意还有比“付刻底本”增出的诗。据我的统计,“付刻底本”共删去诗43首。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在“付刻底本”结束后,刻本又增出15题31首,为“付刻底本”所无。这是以前谁也没有注意到的,甚至胡适认为有了“付刻底本”,刻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完全不是如此。所以刻本和“付刻底本”对研究来说都是有用的资料,并不是有了“付刻底本”敦诚的诗就尽在于此了。
二、关于《四松堂集》的编年问题
关于《四松堂集》和《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的编年问题,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第二册(胡适题《四松堂集》下)内有一首诗,题为《三月十四夜与佩斋、松溪、瑞庵、雨亭至黑山饮西廊看月》,诗云:“吾诗聊记编年事,四十八年三月游。五客四童一瓮酒,黄昏白月黑山头。”按乾隆四十八年岁在癸卯,在此诗前正是《癸卯正月初十日,乾清宫预宴恭纪二首》,前后紧接,因此吴恩裕先生文中特别强调“敦诚的《诗钞》① 是比较严格地编年的。再看他的自白:‘吾诗聊记编年事’一语,更可证明。”② 但我认真查核《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书中关于纪年有多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诗题下有明确的纪年,如“付刻底本”第一页第一首《农家乐》题下有“丙子”的纪年,如同集后边《雨中泛舟》题下有“癸巳”的纪年,如后边《北寺腊梅嵩山日使人探之,今春稍迟,至仲春下浣始放,因相约入寺,上人万钟置茗饮共赏其下,且拈春字韵索诗,即书以寄谢》,题下有“辛丑”的纪年等等。第二种是诗题本身即含纪年,如《癸卯正月初十日,乾清宫预宴恭纪二首》,诗题开头即含纪年,又如《辛亥早春与鲍琴舫饮北楼,其友王悔生、恽简堂、张皋文为不速之客,琴舫有作,次韵二首》,这也是诗题一开头就含纪年的(此诗“付刻底本”上无,是刻本所增)。上举前一首诗,在“付刻底本”上未加删除,在刻本上也仍保留诗题的纪年。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到上述第一种情况的纪年时,即诗题下的小字纪年,在刻本上都已加删除,尽管底本上未加删除符号,但付刻时也作删除处理。只有诗题本身即含纪年的一首付刻时未加删除。第三种情况是题下原有小字纪年,编定时在纪年上贴小白纸片盖住,表示删去纪年,如《南村清明》题下原有小字“癸未”,编定时“癸未”两字被小纸条贴盖,经揭去纸条,才能看到下面被覆盖的字,又如《挽曹雪芹》一首,题下原有“甲申”两字纪年,付刻前又用小纸片将“甲申”两字贴盖掉,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干脆在题上加了“×”,表示删去此诗。细看原稿,诗题上已有o(这个o因墨重已变成一个圆墨点),表示入选。后来又加“×”表示删去。如果一开始就决定删去此诗的话,题下覆盖纪年的白纸条就无须多此一举,故此诗的删去估计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特别是此诗的下面一首是《遣小婢病归永平山庄,未数月,闻已溘然淹逝,感而有作》,诗说:“……一路关河归病骨,满山风雪葬孤魂。遥怜新土生春草,记剪残灯侍夜樽。未免有情一堕泪,嗒然兀坐掩重门。”死者是敦诚的侍婢。给她写的挽诗倒入选,为至友曹雪芹写的挽诗,反倒被删掉,其间什么原因,值得深思,包括贴去“甲申”两字的纪年,是否还有纪年不确等情节也可思考。又社科院图书馆也藏有《四松堂诗钞》抄本一册,确是乾隆抄本,内有这首《挽曹雪芹》诗,题下“甲申”两字未删,但此集未抄完,最后一首是《上巳后一日,同佩斋、瑞庵、雨亭饮钓鱼台,台在都城西》。以下还有约五分之一的诗未抄。所以此本是未定本,故“甲申”两字未删。又如《送李随轩廷扬编修之任粤东二首》,题下原有“壬辰”纪年,题上已加盖“刻”字印戳,但题下的纪年仍用白纸贴掉。第四种情况是题下纪年用墨笔圈去,如《清明前嵩山庭中梅花盛开相招,因事不果往,记去春主人置酒,蒋银台螺峰,朱阁学石君,王员外礼亭,方水部仰斋,暨予兄弟俱在座,颇为一时之盛,倏忽一载矣。即次荇庄看梅原韵却寄二首,且冀补嘉会云》,题下原有“丁未”纪年,编定时用墨笔圈去。又如《南溪感旧,记乙未初夏同墨翁、嵩山于此射凫叉鱼,倏尔十三年矣》,题下有“戊申”纪年,被编者用墨笔点去。
尤其是吴恩裕先生特别强调的“吾诗聊记编年事”一诗,证明敦诚的诗是“严格地编年”的,但此诗在敦敏编定时,也一并删去。这只能说明“吾诗聊记编年事”这句话已不是十分确切了。所以综上几种情况,再看刻本《四松堂集》,除上述诗题上含纪年的二首外,其他所有的纪年概被删去,所以单看刻本《四松堂集》,要寻找各诗的明确纪年是已无法见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要的变化呢?我认为《四松堂集》并不是真正“严格”编年的,大体编年还可以这样说,但并不“严格”。所以敦敏在编定此集时,感到并非“严格”编年,因此把有关纪年的文字全部去掉,以符合实际情况。由此,我们对《挽曹雪芹》诗下的“甲申”两字被贴条删去,也不能不审慎思考。事实也确是如此,《四松堂集》的编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特别是“付刻底本”以外增出的31首,除其中《辛亥早春,……》一首诗题有纪年外,其余都无原稿可查,更难一一考明写作年份,所以说它为“严格编年”确是不尽合事实。因此我们对底本上各诗的纪年也不能不审慎对待。
三、重议曹雪芹的卒年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了,最主要的仍然是“壬午说”和“癸未说”。这次,趁重见《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的机会,再来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再认识,我觉得是十分必要的。
一、壬午说的根据有三条:
甲、“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乙、《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录脂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赖(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愿造化主再出一脂一芹,是书有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原矣。甲申八月泪笔。”
丙、一九六八年北京通县张家湾平整坟地(曹家大坟)时出土一块“曹雪芹墓石”,墓石高98公分,宽36公分,正中刻“曹公讳霑墓”五字,字体分书,左下端刻“壬午”二字。墓石现藏通州区博物馆,据文物专家鉴定,此墓石为原物,故墓石刻“壬午”二字于考证曹雪芹卒年至为重要。
二、癸未说的证据是敦敏的《懋斋诗钞》有《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首诗:“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此诗无纪年,但在此诗前三首《古刹小憩》下有“癸未”两字纪年。同时编者又认为《懋斋诗钞》是严格编年的,《小诗代柬》既在癸未纪年后第四首,应是癸未年的诗。这就是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乾隆28年)除夕的唯一根据。我们现在就先从《懋斋诗钞》的编年说起。
《懋斋诗钞》基本上是一部编年诗集,但并不是“严格编年”。卷首“懋斋诗钞,蕴辉阁藏,自乾隆二十九年戊寅起至三十一年庚辰止”这就是完全错的。二十九年是甲申,三十一年是丙戌,连干支都错了,更错误的是诗的起讫年都不对,这一点吴恩裕先生已说过了,不必多说,何况这是“燕野顽民”题的,错不在诗集的作者。但就诗集本身来说,编年上也是有问题的,例如诗集第一页的一段题记说“癸未夏,长日如年,偶检箧衍,数年得诗若干首……遂以东皋名之”。这段文字里的“癸未”两字是后贴上去的。原文是庚辰。但无论是“癸未”抑或“庚辰”都是不对的。这段文意是说庚辰年的夏天,整理庚辰以前数年的诗,那么就是说庚辰是诗集的最后一年,所收的诗都是庚辰以前的诗(含庚辰),就算后来发现不是止于庚辰(乾隆二十五年),而是止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因此改为“癸未”,这也仍然不对。细按各诗的序次,实际上是止于“乙酉”(乾隆三十年)。吴恩裕先生说“抄到甲申为止”,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细按。从《懋斋诗钞》的第九题《清明东郊》开始,题下即有明确的“己卯”(乾隆二十四年)纪年。从此起直到《丁丑榆关除夕,同易堂、敬亭和东坡粲字韵诗回首已三年矣……》,自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下数三年,正是己卯(乾隆二十四年),但诗题表明已是己卯除夕,诗的第一句就是“一岁馀一宵”。所以从下一首《春柳十咏》起,便是庚辰(乾隆二十五年),顺次下数,季节很清楚,《午睡梦游潞河……》是夏天,《立秋前三日雨中……》是庚辰秋天,《访卢素亭……》诗说“秋冷寒毡自著书”则已是秋末冬初,下一首《过贻谋东轩……》末句说“满天明月凉于水”则已入冬季,以下诗集是空白,当是删去数诗。到下一首没有题目,首句是“入春已十日”,则已是辛巳(乾隆二十六年)春天,《寄松溪》说“无端樱笋又逢时”则是春末夏初,《和敬亭夜宿……》说“联床小话早秋天”,是早秋,下面《雪中月》说“乾坤一望白茫茫”则是冬天,以下《送二弟之羊房》首句说“帝京重新岁”,即又是壬午(乾隆二十七年)的新春,《雨后漫成》说“疏烟寒食候,小雨暮春天”则是壬午暮春,《秋海棠限韵》说“西风秋老雁声苍”则是晚秋,《九日和敬亭韵》首句说“不把茱萸兴自豪”则是重阳登高节,《雪后访易堂不值……》说“门掩一庭雪”则又是冬天。下面《古刹小憩》题下有“癸未”纪年,正是癸未(乾隆二十八年)的春天,下面《小诗代柬寄曹雪芹》确是癸未春天。再下面《集饮敬亭松堂……》应该就是《小诗代柬》的邀宴,此诗值得注意,但其中七人却无雪芹,可见雪芹未能赴宴,此事下文当再论。下面《刈麦行》当是夏初麦收季节,以下《秋事》说“秋事无端剩暮蝉”,则又是秋暮季节,《九日冒雨过敬亭……》首句说“登高愁负东园约”则是癸未的重九节,《十月二十日谒先慈墓感赋》《腊梅次敬亭韵……》则是癸未冬天。下面《闲居八首用紫琼道人春日园居杂韵原韵》说“花竹自成园”“插柳迂疏径,移花傍小亭”则又入甲申(乾隆二十九年)春天。以下有数处删去留空,直到《九日同敬亭子谦登道院斗母阁》则又是甲申的秋天。下面《虚花十咏》当不是纪年之作,接下去就是《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开头即说“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则已是乙酉(乾隆三十年)的春天。因为前诗已经到了秋天,现在又写“春欲归”,则当然是又过了一年,下面还有几首诗当都属乙酉年的。如此排比,可见此集终于乙酉而不是甲申。
从以上的排比,可见《懋斋诗钞》基本上是编年且依季节编排的。但其中也有误差,如《上元夜同人集子谦潇洒轩征歌,回忆丙子上元同秋园徐先生、妹倩以宁饮潇洒轩,迄今已五阅岁矣,因感志事兼怀秋园,以宁》。按丙子是乾隆二十一年,自丙子下数五年,当是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但事实上根据上面的排比,此诗已入辛巳(乾隆二十六年),可见作者自己把年份搞错了。其次是此集的起讫年份也是错误的,吴恩裕先生已指出此集应起于戊寅(乾隆二十三年),这是对的,但此集的终止年份应是乙酉,而不是甲申,此点连吴恩裕先生也搞错了。所以说《懋斋诗钞》基本编年而不能算“严格”编年。
辨明了《懋斋诗钞》的编年情况,我们就可以讨论《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的问题了。
《小诗代柬寄曹雪芹》,吴恩裕先生等坚持是癸未年的诗,根据以上排比,确是“癸未”,这一点没有错。但问题是《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没有回音,毫无消息,到此诗下第三首《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余得蓬字》,诗题中就提到了六人,连敦敏自己共七人。全诗说:“人生忽旦暮,聚散如飘蓬。谁能联同气,常此杯酒通。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分盏量酒户,即席传诗筒。墨公讲丰韵,咏物格调工。大川重义侠,擊筑悲歌雄。敬亭妙挥洒,肆应才不穷。汝贻排酒阵,豪饮如长虹。顾我徒老大,小技惭雕虫。最后易堂至,谐谑生春风。会者此七人,恰与竹林同。中和连上巳,花柳烟溟濛。三春百年内,几消此颜红。卜昼更卜夜,拟宿松堂中。”此诗的时节是“上巳”,“中和”是二月初一,也是节令,但此处是用来陪衬的,实意是在“上巳”,正应《小诗代柬寄曹雪芹》诗中所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的诗句。当时敦敏邀客,当不止一人,也可能是敦敏、敦诚分头邀约,聚会饮酒赋诗的,但此会却无雪芹。按说所会都是雪芹的友人,雪芹不应不来,但竟然未来,这就更应注意。如果雪芹是因事未来,按理雪芹会有答诗,但竟然一无回音,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他是否已不在人世了,何况还有“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记载,这就更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了。此诗是任晓辉同志悟出后提醒我的,我认真琢磨,觉得颇有道理。
主张雪芹卒于癸未除夕说的只注意《小诗代柬》一诗作于癸未春,因而认定雪芹不能死于壬午除夕。但从考证的角度来说,这只是推理、推测而并非实证。因为雪芹未应约,有可能是人在因故未赴约,也可能是人已不在,这两种可能是都可能存在的,不能单执其一,所以考证讲究“孤证不信”,何况这还不是“实证”而只是推测。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从《懋斋诗钞》里,自癸未春天的《小诗代柬》以后,经过整整癸未、甲申两年,迄无一点雪芹的信息。不仅敦敏的诗中两年未提及,就是敦诚、张宜泉等其他友人的诗集里再也找不到一首癸未年或以后与雪芹唱和的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雪芹还健在,他能不参加那上巳前三日的宴集吗?他能与所有的友人完全不通音信吗?《懋斋诗钞》从《小诗代柬》以后,隔了整整两年,一直到乙酉(乾隆三十年),才又出现雪芹的名字,这就是《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这首诗,可惜已经是悼念雪芹了,而且从诗意看,雪芹已非新丧,现将全诗引在下面: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诗题说的“河干”当然就是东郊的潞河,敦敏、敦诚的诗里屡屡提到潞河,《懋斋诗钞》第一首诗就是《水南庄》,水南庄就在潞河边上,现今还在,故诗里说“水南庄外钓竿斜”,另一首《水南庄即事》说:“柳丝拂拂柳花飞。晴雪河干鱼正肥。”还有一首《庆丰闸酒楼和壁间韵》说“古渡明斜照,渔人争集先,土堤崩积雨,石壩响飞泉……”。二十多年前我曾到过庆丰闸,当时水势依旧,闸旁有一家卖酒楼,据乡人说,当年雪芹等人常到庆丰闸酒楼饮酒,我还到过潞河边上英亲王阿济格的陵墓,也即是敦敏、敦诚先祖的陵墓,至今这些地名和遗迹都还在。特别是诗题不仅标明“河干”,还标明“题壁兼吊雪芹”。这就非常明确的说明雪芹已故,其埋葬之地就在“河干”。要不是雪芹的墓就在河干,怎么诗题可说“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呢?后来一九六八年通县张家湾平整坟地,从曹家大坟挖出一块“曹雪芹墓石”,墓石的出土地“曹家大坟”即在潞河边上,这为《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这首诗无异是作了最好的证实。细味诗意,雪芹已非新丧,诗意只是惆怅伤感而不是剧哀深痛,不是悲不可止。由此可以细思,从癸未《小诗代柬》到《河干集饮》,中间整整二年有余,杳无雪芹信息,到乙酉则已是伤悼故去已久的雪芹,那么我们能不想想,癸未春天《小诗代柬》之时,雪芹之所以杳无音信,是不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呢?有人说,雪芹与二敦如此深交,二敦怎么会毫无消息呢?其实这不难理解。雪芹死时仅仅只剩一个飘零的“新妇”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传递信息呢?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就经历过三起这样的情景,最短的是隔了一年多才知道,最长的隔了五年才知道,说来伤痛,不再具体细说。
总之,癸未说的《小诗代柬》一是“理证”不是“直证”“实证”。二是“孤证”,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全凭推测,这就难以成为可信的结论了。何况更有与它对立的实证、直证在,癸未说就更无立足之地了。
说清楚了“癸未说”的根本不足成立的道理,那么再来看“壬午说”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壬午说”现有三条证据,都可称为“实证”和“直证”。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初讨论曹雪芹卒年时,还只有甲戌本上的脂批一条,1964年发现“夕葵书屋石头记”残页脂批,俞平伯先生作了题记并写了文章,但文章到1979年才发表。曹雪芹墓石则是1968年发现,但未公布,直到1992年才公布和鉴定,所以现在讨论“壬午说”比起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要有利得多,因为可靠的证据增加了两件,其情况当然就不同了。
先说甲戌本脂批(已见前引)。甲戌本脂批是可信的,但甲戌本脂批一是抄时被分割成两处,二是有抄错。即使这样,当年讨论时也未被否定。只是在“壬午”的纪年上有癸未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才发生了争论,二是甲午八日泪笔的“甲午”认为从“癸未”到甲午已相隔十二年,故“壬午”肯定是记错了。但是“夕葵书屋”抄件出来后,可以说这些疑问已涣然冰释。首先此批是批在“满纸荒唐言”一诗诗下的,今甲戌本在“谁解其中味”句下,还有“此是第一首标题诗”一句批语,而“夕葵书屋”本此句是整个批语的第一句,整个批语是完整的一篇,不似甲戌本上分成二处三段。这样可知“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一句,是针对“谁解其中味”这句诗来的。特别是末句甲戌本的“甲午八日”,“夕葵书屋”本却是“甲申八月”,所以俞平伯先生说“文甚简单,却把上文所列各项问题都给解决了”③。从“壬午除夕”到“甲申八月”中间只隔一年半时间,还可以说雪芹逝后不久。所以这条批语的出现,确是把以往讨论的主要疑点都解决了,因此脂批就更为可信无疑了。至于通县潞河畔张家湾曹家大坟出土的曹雪芹墓石,石上不仅有“曹公讳霑墓”的题字,更有“壬午”的纪年,且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大卣和史树青先生鉴定,还有红学家邓绍基、刘世德、陈毓罴、王利器等专家的鉴定,一致认为可靠无疑,其后上海的大画家唐云、谢稚柳、上图碑刻研究专家潘景郑诸先生不仅一致肯定,还都作了题记。潘景郑、徐定戡两先生还填了词作题。当然坚持癸未说的人仍然说墓石是假的云云,但这已是不足为辩的问题了,特别是墓石不合碑刻的规制云云,更是不值一驳。因为墓碑的规制,是对封建朝廷的官员来说的,普通老百姓死后的墓志墓石,有谁来管?我曾买到过一块高20公分,宽12.5公分,厚3公分的明万历丁巳年(45年)的青花瓷墓志,还曾买到过一件直径21公分的陶制盖盘墓志,盖上写“安陆黄公墓志”,时间是乾隆丙子(乾隆21年,志文长不录),正好是曹雪芹的时代,我还买到一件94公分×94公分的唐代特大墓志,是狄仁杰族孙的墓志。所以曹雪芹的墓石不合规制,正好说明他穷困潦倒,且是家破人亡后的一个破落户,死后朋友们为他凿一块墓石为记,刻上“壬午”的纪年,以志他的逝年,这是完全合乎情理,无可怀疑的事实。所以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既有脂砚斋的记载,更有墓石实物上的纪年,这是任何强辩都无济于事的。所以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完全可以定论。
四、有关曹雪芹的几首挽诗的解读
有关曹雪芹的卒年、葬地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所以对曹雪芹的几首挽诗的写作时间,内容的解释自然也会不同。这本来是属于共同探讨的问题,学术也正因此而能得到前进。假定说我的解释是错误的,别人的解释是正确的,读者自然应该选择正确的解释,连同我自己也应该抛弃错误的观点,接受正确的观点,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当然,当我现在写出我的意见来时,自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写出来了。我的这种想法和对待学术是非的态度,我想易人而处,也应该是同样的态度。所以当我对某一种学术意见不同意时,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学术意见的作者的不尊重,反之也应该一样。例如我上面分析的对曹雪芹的卒年,主张壬午说,虽然我认为这是定论,但这是我个人反复斟酌后得出的定论,是属于我个人的见解,并不是说别人都应以此为“定论”。别人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看法,并且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我想是应该郑重说明的。
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共三首,两首在《鹪鹩庵杂志》抄本里,此书原是张次溪先生所藏,后由吴恩裕先生借出,我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获交吴先生的,而且交往甚深,并一起合写文章,但一直未顾得上讯问此抄本的下落,还有周绍良先生,我交往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交往了,他至迟到60年代就应该看到此抄本了,但当时我未研究《红楼梦》,所以也未向他讯问此抄本的情况。现在更不清楚《鹪鹩庵杂志》抄本的下落,好在周绍良先生、吴恩裕先生都已将这两首诗辑录下来,所以我现在只能据这个辑录本加以分析。
首先要强调,据上面我的分析,我认为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是证据充足的,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是在不知道雪芹已于壬午除夕去世的情况下发出的。这是我分析这几首挽诗的立足点。
现在我先将《鹪鹩庵杂志》抄本里的两首挽诗抄在下面:
挽曹雪芹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迴故垅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
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付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对于这些诗的通读性的解释,我觉得蔡义江同志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已做得很好,所以我就不必重复他的解释,我只把我自己不同的见解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其余都请读蔡著,以省篇幅。
首先我认为这两首挽诗,是作于癸未上巳节以后,因为这之前敦诚、敦敏还不知道雪芹已死,所以还写诗去邀他来聚会,等到不见雪芹回音,也不见他到来,才开始得知雪芹已去世,究竟是癸未的什么时候知道的,现在很难确切地考出,但总在上巳聚会雪芹不到以后一段时间里。因此这两首诗,不是雪芹刚死时写的,并且敦诚当时还不清楚雪芹病故丧葬等具体情况,我们从诗里可以看得出来。
“四十萧然太瘦生”这一句一直有争论,我同意沈治钧同志的意见,不能死指“四十岁”,这个看法,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理解的,何况明摆着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在那里,同是雪芹的好友,都为雪芹写过挽诗,而张宜泉还与雪芹同住西郊,为什么只认一说为可信而不考虑另一说呢?读了沈治钧同志的文章,更加相信“四十年华”不是实指四十整数。第二句“晓风昨日拂铭旌”,这里的“昨日”两字也不能死解,不能认为就是今天的上一天的“昨日”,而是泛指已经过去的时间。这说明敦诚没有能参与雪芹的丧葬。第三句的“故垅”,我认为是指“旧坟”,也即是曹家在东郊张家湾的祖坟。因为他的儿子死了,不能去葬在别人的坟地里,所以只能葬到自己的祖坟里来。据文献,曹家在通县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虽未说及祖坟,但“曹雪芹墓石”是从老百姓俗呼的“曹家大坟”挖出来的,这一点应该予以重视。至于注文所说的“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当然是说雪芹死前数月。“遗文”应该是指他的《红楼梦》文稿,可能还有部分诗稿。“鹿车荷锸”句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说明他像刘伶一样“死便埋我”。因此雪芹是死后不久即被埋葬的,埋葬的地点应该是张家湾的祖坟,与他的孤儿在一起,特别是曹家大坟挖出来的墓石,下面就是尸骨,没有棺木,真正是“死便埋我”。所以这句诗是实写。同样的道理,他死后,不能去埋葬在别人家的坟地里,必须归自家的坟地,《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特别提到“目今祖茔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这是曹雪芹对祖坟的观念,当然他死后只能归葬祖坟,才是他的安身之地,何况张家湾正有他家的典地六百亩等等,前文已提到,不再重复。末两句,特别是“何处招魂”说明他对雪芹的丧葬情况还不清楚,要招魂还不知向何处去招,这正是他初得雪芹死信时的情景。
第二首第一句,当然是指他的《红楼梦》文稿,第二句可参看敦诚的《哭复斋文》和《寄大兄》两文,确实在雪芹去世前后,不少位友人都相继去世了。第四句“一病无医竟负君”,更是关键的诗句,说明雪芹从病到死,敦诚都不知道,也说明雪芹从得病到死时间很快,说明敦诚感到十分歉疚,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还写诗邀雪芹来赏春。这些诗句都可以贯通起来理解。下面四句无须特别讲解。
第三首收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里,我曾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看到原件。诗题下署年“甲申”,而又被用白纸贴去。前二首应该是听到雪芹去世的消息后就写的,属初稿。虽未署纪年,我认为当是癸未上巳以后所写。第三首当是后来的改稿,因诗中句子都有相同。改稿的时间相隔已较久。但诗意变化不大。第二句“哀旌一片阿谁铭”比前首第二句更明确说明他对雪芹的丧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第三句上诗是说埋在祖坟里的孤儿知道父亲也死了,因而迴肠九转地哭泣,改句改为雪芹地下的魂魄去寻找他在冥冥中的孤儿。五、六两句未改,第七句抄本是“青衫泪”,《红楼梦卷》误作“青山泪”,应纠正(吴恩裕《四松堂集外诗辑》不误)。末句“絮酒生刍上旧坰”是重要改动,前诗只说“何处招魂”,要招魂还不知向何处去招,说明葬地不明,改诗却明确说“上旧坰”。这就是说郊外的老坟,也就是指祖坟,则可见雪芹逝后,由朋友匆促间将他归葬到祖坟上,因贫穷,买不起棺材,是裸葬,正符合“鹿车荷锸”之典。人们常以为雪芹死后一定葬在西山一带,昔年我与吴恩裕同志还曾多次到香山、白家疃一带调查,杳无所得,但根本不曾想到东郊的通县,直到1992年墓石的重现,并经过鉴定,实地调查,再细读有关文献及诗文,才确信雪芹是最后归葬到东郊的祖坟,再细读以上诸诗,更可贯通无碍。
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和《河干题壁兼吊雪芹》两诗,前面已分析过了,不再重复,但这里要补充一点,即《四松堂集》里记到雪芹的朋友寅圃、贻谋的墓也在潞河边上,与雪芹的坟离得不远,我二十多年前,曾多次出东城沿潞河(现在叫通惠河,此名乾隆间也用过,从敦诚、敦敏的诗里可以查到)一直走到张家湾曹家大坟,故确知其地理。现在再读敦诚的《哭复斋文》: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
为什么说“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呢?过去未加深思,包括《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总以为他们生前常在此游览宴饮,因此想起往事题壁感怀,现在确知贻谋、寅圃的墓就在潞河边上,与雪芹墓地较近,所以无怪敦诚要有这样的想法了。
还有一首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也是一首悼诗,也应该一谈。
伤芹溪居士
(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鋩鋩。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这首诗的写作,也应是雪芹逝后一段时间,不像是雪芹刚去世时的悼诗,诗意伤感而沉痛深稳,第一句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典,称赞雪芹是一位诗人;第二句说明雪芹已逝,再也见不到了;第三句用典说明雪芹还工画,第四句说他的《红楼梦》未写完。五、六两句说雪芹的才华未得抒展,最后两句说再到雪芹原来藏修(隐居读书)的地方,已经是“翠叠空山”晚照苍凉了。这末两句意义深长,不仅说明雪芹已逝,人去山空,连他的坟墓也不在西山了。如果说雪芹的墓地是在西山,就不能说是“空山”,这“空山”一词,正说明雪芹已归葬东郊祖坟,此地只有空山晚照了。
所以将以上各诗作一整体的疏解,则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归葬东郊潞河边的通县祖坟,与当年的多位诗友同葬在潞河之滨,而与张家湾出土的曹雪芹墓石,也完全是天然吻合,成为一体。
★★★
以上是我重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的一点新的体会,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待以后长时间的考验。我希望看到正负不同的验证,使学术有所前进。
2006年6月16日于瓜饭楼
注释:
①敦诚的《四松堂诗钞》藏社科院图书馆,我曾用《四松堂集》刻本去核对两次,编次与刻本完全一样,但只抄到《上巳后一日同佩斋、瑞庵、雨亭饮钓鱼台,台在都城西》一诗为止,比刻本少七十首诗。
②见吴恩裕《曹雪芹丛考》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三月版。
③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俞平伯先生文:《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一文,197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