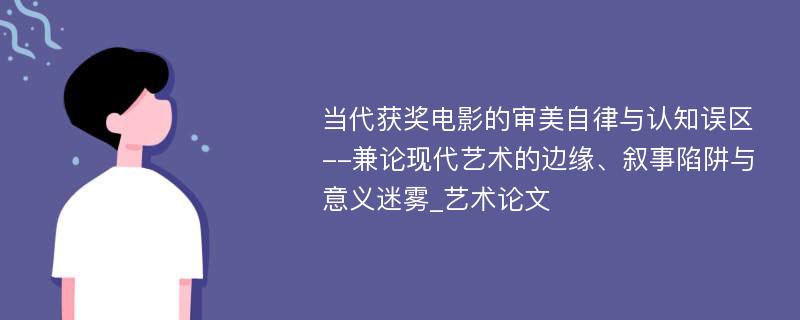
审美自律与当下获奖电影的认知误区——兼论现代艺术的边缘性、叙述圈套与意义迷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圈套论文,迷雾论文,认知论文,误区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的电影种类中,艺术片已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一员,尤其成为了大大小小电影节理所当然的选择。相应的,获奖意图也成为了众多艺术片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如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说:“只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实验性和思想性……恐怕难以排除一个动机,那就是:迎合国际影展评委们的口味。”(注:孙慰川:《论蔡明亮的写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与追求票房的商业片不同,艺术片趋向精英的认同;与阐析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片不同,它坚守一种个性立场。但是,许多电影人并不承认艺术片因获奖就雄踞在艺术的制高点。某些艺术片,尤其是抱有明确获奖意向的参赛影片,遵照电影节的规则而制作,出现了日渐萎缩、狭隘的艺术体验与情感世界。这很难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我们必须正视,以获奖为目的、排斥商业价值的艺术片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远离了影视艺术的工业性、技术性,而且在再生产上陷入了自我重复的困境。
这种现象的出现颇令人尴尬。获奖电影偏执于现代主义的艺术立场,与当下的接受语境产生了明显的错位,而各种电影节的评价机制更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导向作用。事实上,当获奖艺术片成为一种类型模式时,也标志着目前评价机制的僵化与呆板。这突出地表现在艺术观念上,甚至出现了几种偏见与误解:题材越边缘,越具有艺术性;影调越阴暗,便越是艺术的;叙事越复杂,意义越含混,艺术色彩就越浓厚。本文主要从近来艺术片《紫蝴蝶》、《任逍遥》等切入,兼及近年来在许多电影节获奖的作品,探究艺术片体验的偏执病症,并希冀其早日走出强大且顽固的现代艺术的审美禁锢。
一、边缘与自律
《紫蝴蝶》之所以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参加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角逐。然而,当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仅获得“有保留的认可”(娄烨语)而在大陆上演时,却让许多观众大失所望。阴沉的影调,模糊的人群,支离破碎的情节以及毫无来由的情节突变和激情戏,不仅远离了希求轻松消费的观众,而且与知识者之间也画上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而在去年的相同时间里,被誉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一面旗帜的贾樟柯,携带着新作《任逍遥》闯进了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影片所呈奉的世界以及在我们记忆深处唤醒的时代感,与《小武》、《站台》等似曾相识。宏大的时代情氛、社会心理,在个体的情性命运的激烈撞击下,幻化成飞舞不定的记忆碎片。尽管它与《紫蝴蝶》的叙事策略差异甚大,然而对边缘人群、边缘状态的极端关注,却成为两者共同之处。
这两种创作原则在当下电影人中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如果说王家卫、章明、李欣、张元等导演更贴近娄烨的思路的话,那么蔡明亮、侯孝贤等则与贾樟柯的艺术理念相似。而强调的边缘状态,在众导演颇具想象的演绎下,已经嬗变成一道亘古陈旧的篱墙。笔者随机选取了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25部华语影片,刻画边缘状态中的边缘人的16部,占了64%;国外25部获奖影片,书写边缘题材的影片更有18部之多,占了72%。(注:25部国内获奖电影分别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你那边几点》*、《青少年哪吒》*、《河流》*、《香港有个好莱坞》*、《洞》、《悲情城市》、《活着》*、《爱你爱我》*、《鬼子来了》*、《我的父亲母亲》、《恋恋风尘》、《海上花》、《那山那人那狗》*、《菊豆》*、《麻将》*、《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阳光灿烂的日子》、《蓝宇》*、《蓝风筝》*、《过年回家》*、《十七岁单车》;国外25部电影分别是:《黑暗中的舞者》*、《迷墙》*、《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给我一个爸》、《小奥德赛》*、《我的性生活》*、《钢琴教师》*、《无记名投票》、《赤裸》*、《我母亲的一切》*、《堕落花》*、《深色胭脂红》*、《芝加哥》*、《天生杀人狂》*、《唇语惊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生何求》、《钢琴师》、《罪孽天使》*、《红色》、《蓝色》、《白色》、《无主地带》*、《花火》*、《地下》*。*号为边缘题材电影,不仅包括边缘人群、情感,而且也包括边缘政治、异域风情等后殖民话语。)两组惊人的数据清楚地表明边缘题材在获奖影片中的盛行,更反衬出电影节评价机制中艺术观念的单薄。边缘题材实际上从浪漫主义开始便得到极大的重视。不同寻常往往被认为是艺术的,因为它“否定了现实的统治原则,即一切事物都可以和其他东西交换”。(注:Adorno,T,W,Aesthetic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122)与中心形成严重对峙的边缘世界,具备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自足空间,传达了一种坚定的自律信念。齐美尔在上世纪初就预言,为了远离日益丰繁的物质文化,保持精神和心灵的独立和自由,现代主义艺术必然会走上一条自律的乌托邦之路。因此,现代主义艺术在“陌生化”创作原则与“自律”精神的双重支持下,更将边缘推崇为唯一的合法源泉。艺术的自律实则承当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正如韦伯所说:“无论怎样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这一世俗的拯救功能,即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刻板,尤其是从理论的和时间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的救助。”(注: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第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种宏大的拯救使命从根本上奠定了艺术家从事艺术的勇气。在《小武》中,尽管褪色的生存状态占据了中心,作为一种边缘的存在,小武彷徨于充满“严打”之声的街道而无路可走,甚至被铐在电线杆上成为窥视者津津乐道的注视品;但是,小偷身份未能遮蔽半点善良、羞涩与忠厚的闪亮人性;人文精神的丰富内质在情感无限流失且日益苍白的庸常生活中难能可贵,他更在与小勇(突出地位与朋友之情的决断)、梅梅(突出金钱与两性爱情的选择)、父母(突出物质与天伦之情的两难)等世态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情感救赎的角色。
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现代主义艺术肯定没有拯救世界,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不可救药的近视……在愤世嫉俗日益成为时尚时,也许我们能从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相信观念能拯救世界见识中得到一点安慰”。愤世嫉俗仅仅是一种批判思维的认识态度,能充分表明对旧有的制度、规则的愤懑,但是却不能在建构新秩序上有任何的建树。即是说,态度偏激的认知方式可能在批判观念桎梏时充满力量,但当涉及构建一个未知世界时,激进偏执的思维方式只能于事无补。因此,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所囊括的种种艺术手段、实验方式,在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马尔克姆·布莱德伯里看来并未给文学、艺术带来任何的复兴。“如果愤世嫉俗的哲学压倒优势,那是我们的损失,而且这种消极影响将持续下去”。汤因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人从世俗大众中异化出去,“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疾病。”(注:参见申慧辉:《世界文坛潮汐录》第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现代主义的弱点正是严格区别了精英与大众、天才与庸众,竟然不顾很少有人可以理性地面对真实,哪怕是自身生命的真实,而全然否认把丑陋掩饰起来的传统艺术可能的优点。因此,当蔡明亮一再地将小康一家搬演到银幕上,昏天黑地的大雨浸泡着“存在的家园”,用小康与父亲的同性恋行为暴露大都市中的零落与孤独(《河流》);以小康与父亲之间的巨大隔阂确证城市中难以弥合的父子裂痕(《青少年哪吒》);把现实追求抽空为时空距离甚远的虚幻思念(《你那边几点》)等种种边缘的生存状态(甚至包括一些难堪的生理痛苦)淋漓尽致地充斥于观众的眼球时,即便是身受其苦的观众恐怕也难以(也不愿)接受这种可怖的真实。人们不禁追问:人类的生存果真这样,现实只能如此绝望吗?蔡明亮的系列电影形成了固定的风格,在反复的书写过程中,将生活经验逐渐磨平,甚至阉割了丰富复杂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是一种“萎缩了的”体验。“萎缩的体验意思是说,专家在其特定领域里所获得的体验不再被转回到生活实践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经验,审美体验以其纯粹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体验的萎缩在艺术中表现出来。体验萎缩的另一种表述是:审美体验是这个过程积极的一面,由此艺术的社会亚系统作为一个独特领域界定了自身;其消极方面乃是艺术家失去了任何社会功能”。(注:周宪:《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这种萎缩的审美体验在蔡明亮电影系列中不仅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悲观理解,故事情节狭窄雷同,演员、道具及其后期制作等表演、技术方面均显得墨守成规,而且影片固执地割裂与大众的关系,其文化救赎的功能显然难以实现。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主义成为了先锋艺术的主流其实是19世纪末的事情。艺术的本质伴随现代主义进驻体系中心而发生了历史性裂变。显而易见,现代艺术包孕的自律概念也仅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艺术在自律的包裹下说出了某种真相,亦即艺术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道德伦理以及生活实践的纠缠而变得纯粹起来。同时,它也包含了某种谎言,自律似乎不是艺术发展的结果,而是永恒不变的本质。(注:周宪:《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于是,当下的艺术电影将现代主义特征发挥出来,并以此为标准,运用个性化的叙事策略来组建艺术天堂,正落入了历史的陷阱。因为极端化的原则、边缘的状态,尽管在艺术潮流重要一环的现代主义中定型,但并非艺术本质及其必然的要求。
二、叙述与故事
尽管蓝灰的冷色调、近乎木讷的天然表情、大光比的光线造型给故事蒙上了一层掺杂尘埃的古旧与沧桑,《紫蝴蝶》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就叙述而言,情况就显得很不相同了。娄烨说:“我在情节安排和叙事推进中,处处都强调事件推进的可能性的动态和主人公的不确定的选择。”(注:娄烨、倪震:《在追寻中感受创作》,《当代电影》,2003年第5期。)他更强调充满动态的叙述可能,甚至质变为提示叙述的犹豫和故事的虚构。“编导总是不甘寂寞,时时在叙事过程中显露出有意加工的痕迹,让观众意识到有一个故事讲述者一直在伴随着他的观影过程”。(注:胡克:《探索在实验与市场之间》,《当代电影》,2003年第5期。)因此,《紫蝴蝶》与《苏州河》一样,实际上体现了叙述与故事的相互争斗,不仅虚构的叙述颠覆了故事的拟真性(如结尾时死去的顾明与辛夏的激情戏,之所以遭到非议,便在于叙述的虚构性力图突破线形时间的链条,但这种颠覆往往引起观赏的反感),而且故事也形成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反过来对叙述人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叙述人自身也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如《苏州河》的叙述人“我”的生活被虚构的马达搅乱)。故事变成了一种辨证的叙事运动来摧毁故事或自我摧毁。
叙述与故事的这种争斗实际上是现代主义以来的事。故事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已经不复存在。“生活是无情节的,戏剧性对于现代人越来越不真实”。(注:贾平凹:《使短篇小说短起来——自我告诫之一》,《贾平凹自选集》第567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不真实的故事被现代主义艺术唾弃,叙述却一跃成为人们兴趣盎然的话题。从讲什么到怎么讲、谁来讲,标志着整个叙事艺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伯格曼、雷诺阿、费里尼、特吕弗等诸多电影大师的出现,直接提升了电影的艺术品质,银幕成为了呈现人物性格的空间、意识的纸张。故事的全线告退导致了叙述出尽风头。但是,叙述的缺点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得异常醒目。如同《紫蝴蝶》遭到的非议一样,故事被叙述割裂成情节碎片,碎片之间的叙述关联却模糊了碎片本身的意义。在故事主体缺席的状态下,叙述往往演变成一种故弄玄虚的陷阱。事实上,叙述圈套、策略、语态等只有在具有拟真性的故事支撑下,才更显个性才情。因此,当以现代主义理念为艺术准则的影视作品叙述全然压过了故事的分量时,叙述往往出现了不能承受之重,自我颠覆的危险在推崇叙述的极端态度中越来越大。这种危险集中体现在叙述已经不再是对一个故事的叙述,“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藏的符号”。(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在这种观念下,叙述不仅颠覆了故事,而且解构了自身。当彬彬骑着摩托车向着镜头驶来成为《任逍遥》的开头时,它促使我们开始反思开头在叙述中的庸常性。他不远不近地在街头行驶,街道的各种声响清晰地传出,在俱乐部里见到唱着歌剧的疯子,他转身坐在旁边的长椅上。这一切都仅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段落。《小武》的开始同样如此。小武上车后偷临座人的钱,与他的生活完全契合。开头的“猝然”(从生活状态中任意地提取一个开始)成为了此类影视作品的典型。这与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开头明显不符:“开头是指该事物与其他事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会自然引起其他事物的发生。”(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他看来,开头如同一颗种子,其他事物的发展正是从种子的萌芽开始。但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天才般的表达了“开头”之不可能。因为叙述的开始总是涉及到一种悖论:既然是开头,就必须有当时在场和事先存在的事件,以此构成故事的生成源泉或发展动力。但是,这一事先存在的基础本身也需要先前事件作为基础,这样一来叙述就会没完没了地回退。开头并不真实,与他事物间的承接、因果、转折等等关系更非真实,于是,叙述的虚假性就暴露出来。叙述的开始并不是故事的开始,因为故事的开始是不可能的,叙述只能采取从中间开始这一权宜之计,给读者一种虚假的前记忆。“它(指虚拟的永恒困境)导致哲学与叙事均永远无法开始,也无法发展。倘若哲学与叙事违背逻辑,依然开始发展,那么,这个自我构建出来的永远悬置的困境就再也不会让它们停下来”。(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即是说,叙述一旦虚假地开始,中间尽管可能出现真实的幻觉,但也必然会虚假地结束。
结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与开头“恰恰相反,是指该事物在必然规律或常规作用下,自然承接某事但却无他事相继”。(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然而,这种“无他事相继”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更显虚妄。《紫蝴蝶》的激情戏结尾似乎在所有人物、情节完结后,纯属于画蛇添足;《小武》、《站台》以及《任逍遥》等影片结尾与开头同样显得非常“仓促”。小武被铐在电线杆上被旁人围观,最后的命运不得而知;抱着小孩的尹瑞娟与崔明亮的结局被漠然地表述,似乎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平淡开始;《任逍遥》在彬彬被抓后唱着任逍遥而突然黑幕结束。这种结尾体现出的开放性恰恰消解了结尾的传统功能。希利斯·米勒精辟地认为:“真正具有结束功能的结尾必须同时具有两种面目:一方面,它看起来是一个齐整的结,将所有的线条都收拢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交代,同时,它看起来又是解结,将缠结在一起的叙事线条梳理整齐,使它们清晰可辨,根根闪亮,一切神秘难解之事均真相大白。”(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究竟是打结还是解结,现代主义艺术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需要而且是同时需要这两个比喻,不断在两种功能间来回摆动。因此,上述影片的确有结尾的收束感,(如《紫蝴蝶》的死亡,《小武》的被捕,《站台》家庭的建立,以及《任逍遥》抢劫的失败),但这种收束感仅仅造成结尾的幻觉,它又是朝着无限敞开的,随时可能从结尾的地方开始。
中间的主体部分则应“既承接前事又有后事相继”(亚里士多德语),一种因果的逻辑关系将前后事贯串起来。电影的播放形式、被动的接受状态使寻找因果逻辑的接受心理潜藏起来。因此,电影实质上最容易产生离心力而不被人们察觉。《任逍遥》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彻底,追求原生态的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直接削弱了因果关系的串接。影片中的异质既包括了街头响起的福利彩票的宣传,关于“法轮功”制造的惨剧的新闻报道,电视里申奥成功的新闻直播以及本地的重大刑事案件;也包括了借用流行歌曲来指称的具体时间,片名的产生得益于一首流行歌曲,《花样年华》的音乐尽管在背景中出现,但给影片也打上了特定时间的烙印;更包括情节自身的种种空白与矛盾,如小济的父亲到工商银行兑换美元,被小济看到后,一句“你怎么好意思”无逻辑性的质问使得父子关系出现了混乱,观众与小济的父亲一样产生本能的回应“怎么就不好意思”,小济声称“回家再跟你说”的父子冲突在后来的叙述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再如赵巧巧把小济叫到车上后,语气恶劣地说“我找过她了,看你怎么泡我”,小济听了有点垂头丧气,但“她”到底指谁,为什么巧巧能找到她,找过她就不能“泡”赵巧巧了?这一连串疑问始终没有获得解答。事实上,整部影片的叙述视点在小济、彬彬之间平行移动,虽有交叉,但并不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甚至有些随意为之。然而,事情又非如此简单。“罗兰·巴尔特告诉我们,只要下点工夫,看上去最不相关的细节也能显得相关。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某个事件肯定是无法收入主线条的插曲性事件或所谓‘毫不相关的细节’呢”?(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这个角度上看,《任逍遥》的情节碎片又很难说与影片的内容主旨毫无关系。福利彩票的宣传正切中了当下希求暴富的社会心态,也与彬彬此时“英雄不怕出身单薄”的自我安慰相呼应;流行歌曲的反复指称,正实践了贾樟柯的“艺术就是记忆”的理念;而巧巧的质问以及后文的疏漏表明了影片拍摄追求的真实性与原状态。细节出现的意义、功能的多变,使得砍削素材的逻辑原则也变得面目模糊。因此,确定一个使得作为现代主义影片连贯衔接,是一个难题。中间的叙述始终贯穿着两个叙述声调,这也就出现了相互抵消的不稳定性和无意义。
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电影媒介有着它的特殊性。如果说,文学消解了故事,而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地放在人物内宇宙的情感心灵,绘画消解了宗教故事的宣传,而增加了自身的主观性与创造性,那么影视艺术在故事缺席的状态下,实则难以完成明确清晰的意义传达。它缺少话剧中人物大段内心独白的权利,也没有文学拥有的灵动细腻的笔触来抚慰敏感脆弱的心灵的自由,更不具备绘画丰富复杂的个性化手段。影视艺术尽管就构成元素而言具有艺术的综合性,如色、音、形的完整统一,但也正因如此而比其他艺术更贴近现实。媒介这种强大的拟真性,甚至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叙述征服了故事,意味着对拟真性的强行拆解,主观力量获得了极端的释放。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有违电影媒介的本性。
三、抽象与意义
伟大的托尔斯泰提出了著名的决定艺术感染力大小的“三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3)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注:转引自曹苇舫:《论艺术传达的构成与发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事实上这也是意义产生的前提,因为任何情感的传达总是依附在一定的意义之上。如果说现实主义着意传达的清晰性,那么现代主义则极端地强调独特性,甚至导致了意义表征的危机。“到现代主义阶段,再现或表征出现了深刻的危机……现代主义表意实践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对新奇的崇拜导致了传统的表征方式失效”。(注:周宪:《审美话语的现代表意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与古典艺术不同的是,现代主义深刻质疑符号再现在世界的可能,并不断地探索表达的极限。杰姆逊认为,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往往存在着双声部(甚至多声部)的复调表达,“传达出在他们使用的语言后面,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总之,表达问题是现代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表达出现了一种危机……维特根斯坦早期著作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到此结束,不能说的,就应该缄默”。(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在这种沉默中,现代艺术便成为了一个难以猜测的谜,接受者加入了众多的个性理解试图完成一种诠释,但这种诠释由于“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的出现,又显得言之无据。现代艺术“追求的就是某种‘谜样的事物’,它表现为对我们熟悉的日常事物的粉碎和变形……艺术作品具有‘谜一样的’特征,它不像日常生活那样一目了然,也不像科学推论话语那样清晰明了”。正因这样,现代主义理论大师阿多诺非常推崇卡夫卡的现代小说,认为那种非现实的、片段的和变形的艺术内容,实际上把日常生活的假象所掩盖的深层现实昭示了出来。(注: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第128—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但是,与小说、绘画等传统艺术不同的是影视艺术接受方式的差异。具有充足的时间并带着宽裕的心境,人们能在一幅画前流连忘返,或者对小说掩卷玩味。而当欣赏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缺乏一种欣赏艺术的庄重感,而且由于接受环境、接受心理以及“一次过”的接受方式,导致我们取消了审美距离,完全沉浸在影视世界中。现代主义艺术所要求的“猜谜”式的审美主体在这里是缺乏的。利用视听刺激愉悦感官,是观赏影视艺术最普通的审美心理。因此,以现代主义艺术为核心理念的获奖影片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往往遭致观众的拒绝。横隔着一团意义的迷雾,他们既难以辨识流动的情感,也难以享受到纯美的意境。如《苏州河》不仅用现实中苏州河的破落陈旧,戏弄了观众期待视野的古典美,而且更以暴露虚构本质的“元叙事”策略组建整个影片的世界,有意地将真实与虚构缠绕在一起。观众即便被牡丹对爱情偏执的向往所打动,但也一再被提醒:“这样的爱情故事我也能编。”《苏州河》的故事意义遭到叙述者的一再解构,但事件仍然是依据因果逻辑来安排:事件没有连缀成线,但就点而言,意义无疑是清晰的。因此,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解构意义,体现摇滚歌手混乱意识的英国影片《迷墙》在这方面显然彻底得多。
意义的解构,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压制人物的对白。这是因为人物的双向对白使得意义具有明晰的方向感与语言的所指,增强了语言的现实感。张艺谋早期作品显著的特点便是对白奇少。《苏州河》的意义消解之所以不够彻底,也正因为具有意义的人物对白固执地对抗画外音的干预。《迷墙》则利用了摇滚歌手的身份,以歌曲代替旁白,严重地钳制了人物之间的对白。即便是对白,也因缺乏对象质变为独白。如面对老师在课堂上的嘲讽咆哮,孩子低头沉默;伙伴看到了火车奔驰而来,对铁轨上摆放子弹的小洛伊德叫嚷,他却不理不睬。歌曲不仅起到了串联影片内容的作用,而且成为解剖人物内心的秘密武器。在歌曲的吟唱中,出现了战争、暴力、性等影像,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性表达。这种批判性因表达超越人物的特征,直接进入了抽象的话语层面。解构意义的策略在《黄土地》中有了明显地扩张,如不仅有民歌对人物对话的淹没(如憨憨爹、翠巧等所唱的信天游),而且有对话反复的无意义(在婚宴上,顾青与村民之间的对话);不仅用沉默直接取消人物间的对白(如顾青初到翠巧家的一场戏,人物的沉默偶尔被拉动风箱的声音打破,却更显可怕的沉默),而且也有对白之间的人物错位(顾青教憨憨唱歌,但憨憨固执地沉默,当顾青失望地走开,憨憨却突然放声高唱)。
意义的缺失与影片剪辑有着密切的关系。剪辑实质上代表了编导对影片故事自然意义的干预。《迷墙》的剪辑贯彻着感觉主义原则,用相同的声音(如推门的声音、电话铃声,等等)、动作(吸烟、喝酒等),把宾馆里洛伊德的孤独迷茫和成长记忆中的种种痛苦联系起来。因此,人物的幻觉,甚至错觉导致了一种夸张的戏剧化处理(如小洛伊德在隧道惊恐地看到火车奔驰而来,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看到了戴着面具的老师凶残地挥舞教鞭,于是火车上的人也戴上了面具不停地叫喊)。这两者的衔接缺乏明确的意义,而是用人物的幻觉简单地缝合在一起,这种缝合尽管有惊慌的心理依据,但在影像上缺乏必然的意义流程。因此,以幻觉(甚至错觉)为核心的剪辑原则将影像活动产生的意义做了非理性处理,也就很难清晰起来。
互文性在《迷墙》的集中出现也导致了意义模糊。如果说歌曲以旁白的方式自由地出入影片的意义世界,那么动画则使用了隐喻的修辞策略,与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但是,影片的间离性元素越多,意义的表达也就越中立含混。再加之隐喻这种修辞格颇具含蓄性,需要解谜式的参悟。如影片中,以动画形式出现的两朵鲜花相互缠绕的状态,隐喻了男女两性的交媾。而画面上彼此紧张类似战争般的冲突变化意味深长,鲜花突变成老鹰的动画隐喻了对女性的畏惧以及害怕被吞噬的心理。由于具有游戏性的动画的加入,意义含混起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观赏时的沉重感。而互文性在其他作品中也有相似的运用。如《天生杀人狂》把父亲对女儿充满暴力的性侵犯,通过肥皂剧的方式播映出来,将现实(电影中所谓的现实)媒介化了(质变成电视肥皂剧),而观众成为了双重意义上的观众,进而远离了乱伦的沉重与罪恶;《黑暗中的舞者》则是将塞尔玛的暴力、磨难、痛苦,用歌舞的形式扭转成喜剧,邻居被杀死之后却复活并谅解塞尔玛的所为,更从视听效果上证实她的无辜。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互文性将作品的元素视为平等甚至混杂的关系时,文本之间的冲突与质变、曲解与扭转同时模糊不清了影片传达的意义。正负不同的文本纠缠在一起,可能将整个作品的意义抵消为零:这一切均可能被一笑了之。
“谜”一般的现代主义作品在意义传达上否认了清晰的可能,也基于对读者解读能力的信任,将意义传达、阐释、选择、组合等诸多权力移交给了读者。“由于人们对连贯性有着极为强烈的需求,因此,无论先后出现的东西多么杂乱无章,人们都会在其中找到某种秩序”。(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14、6、56、57、51、60、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存在不能解读的艺术作品,也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但是,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艺术片极大地消解了作品自身的意义,而寄希望于接受者。或者煞有其事、看似深沉地堂皇地归置于非理性与感觉主义(如高小松导演的青春时尚片《那时花开》);或者在大众文化作品中不加分辨而强行编织精英文化的意义系统(如《紫蝴蝶》);或者将镜头对准生存的边缘状态而一味地纪录写实(如《站台》)等等诸多策略中,编导从先前的解释者转换为展示者,从侧面透露出缺乏一种突破极限的穿透力。对艺术家来说,影片的晦暗化也许意味着主题的丰富、扑朔迷离的玄思。然而,艺术世界是艺术家用自己的影像话语传达出独到的个性理解与体悟。当他们不能表达,或者将表达不出的个性经验存放于无意识领域,是否也表现出自己的无奈甚至传达的软弱呢?
标签:艺术论文; 任逍遥论文; 获奖电影论文; 现代艺术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电影节论文; 苏州河论文; 小武论文; 迷墙论文; 站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