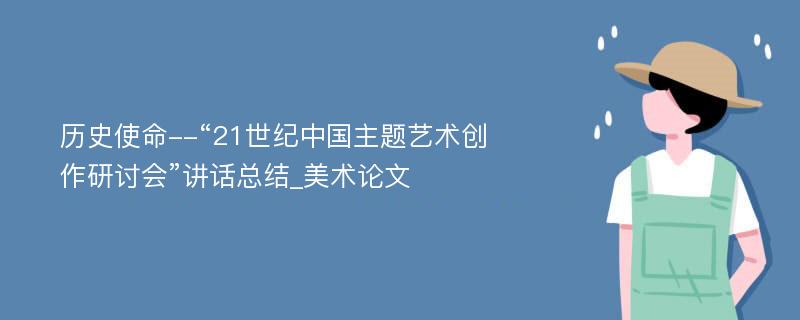
历史的使命——“21世纪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研讨会”发言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使命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化画报社于1999年9月2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21世纪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对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发展方向、目前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靳尚谊、钟涵、王宏建、邵大箴、詹建俊、冯远、王仲、刘曦林、刘龙庭、翟墨、陈醉、赵力忠、陈瑞林、罗世平、田黎明、杭间等十六位在京美术家、美术理论家参加了讨论。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司副司长张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白国庆、党委副书记王泽洲出席了会议。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曲润海同志到会并致辞。中华文化画报社主编、美术学博士郭晓川主持了这次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解放军画报》、《美术》等新闻单位的记者20多人。
这次研讨会的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 现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现状、成就及问题;2、 主题性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3、 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繁荣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中的作用;4、中、 西方主题性美术创作比较研究以及在当前如何借鉴外来经验丰富我们的美术创作;5、 主题性美术创作个案研究与美术家创作体会。与会代表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这次研讨会的发言纪要。
靳尚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最近,第九届全国美展作品评选活动刚刚结束,我看了其中的油画作品。这次全国美展与往届不同,具有特别的含义:它既是五年一次的全国性美术展览,又有庆祝建国50周年的纪念意义。因此今年的参展作品中,主题性美术作品就比较多一些。由于90年代以来美术的发展变化,形成风格多种多样,所以这次油画展区表现为风格繁多,主题性美术作品的风格相应增多。
主题性美术绘画是建国以来一直倡导的,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主题性绘画”、“情节性绘画”等等名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很多博物馆建起来了,象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等,需要一批这类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绘画,去表现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变革。因此,在50到60年代,这种绘画发展得比较快,也比较好。“文革”前,产生过一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的《地道战》等等。现在看这些作品在创作上能反映时代,包括一些新的风格形式的出现,都是很不错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技术、表达的手段和油画语言,还不是很完善,与西方同类绘画相比,它显得简单、粗糙一些。这种情况不是由谁来决定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油画引进的时间不长,发展也较慢。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油画有很大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题性绘画在样式上有所拓宽,反映的角度、表现的观念、形式的处理都有很大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现象: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一直提倡反映现实和变革的主题性绘画;另一方面是从事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人越来越少。象我们这一代年龄较大的画家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创作的,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有一定的经验,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画家面临着多种风格、多种样式,从入学就不是以这种创作为主,因此他们在主题性美术创作方面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从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油画作品可以看到这一点,其中有好的东西,也有很多不足。
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里,绘画在整个美术门类中已经不是唯一的表现手段了。我们新一代的画家是在信息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接触着大量的图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画家对主题性绘画的形式处理就与过去不一样。那么,我们又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
钟 涵(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探讨一个问题应该对其中的关键概念作相应的界定。原则上我对“主题性绘画”一词持保留态度。这是一个“误构词”。该词首创于20年代的苏联。它要求绘画内容为人民所喜爱,倾向于表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具有重大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世界氛围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美术的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该词的要求与其内涵的关系来看,二者不是非常相适应的。尤其是在今天,时代发展了,现在的中国对主流美术创作的指导应有相适的观念。目前看来,“主题性”与“主旋律”容易混淆。而“主旋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词,它很明确。
王宏建(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我认为主题性绘画创作与提倡主旋律还是有区别的。正如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主旋律作品要积极、正面地关注社会主义建设及伟大的历史变革,带有歌颂的性质。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要要求就是关注现实,其表现有时是消极的,关注对象有时是负面的,因此它还包括了揭露、批判的性质。
历史上属于主题性绘画的有历史画、宗教画等等。中国在六朝时就有明确主题要求的绘画,后来的敦煌壁画中如《张仪潮出行图》等也具有主题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向来很重视主题性美术创作,重视历史画。
中国近现代主题性绘画的出现和创作始于30年代的徐悲鸿。他的《奚我后》、《愚公移山》等作品体现了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国的主题。但是中国的主题性绘画之所以能确立其地位,原因在于社会的需要。“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本身就要求关注社会现实。当时的西方则不同。那时的西方正经历着工业革命以后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的美术创作在内容上更倾向于表现人的内部心理。当时中国的时势也呼唤爱国主义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建国后的十多年是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要发展时期,产生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扛鼎之作,为中国美术史画上了辉煌的一笔。
“文革”时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为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趋于简单化、公式化,实质上有悖于关注现实的根本要求。“文革”以后,出现了变化。70到80年代初期,反映反思“文革”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大量出现,也产生了不少好作品。80年代后期以来,美术创作对现实的关注渐次深入,而且面貌也渐趋多样。同时,各地大型博物馆,如抗战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也都出现了很好的主题性雕塑、绘画作品。但是,二十多年来美术创作的格局是渐趋多元化,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主题性美术创作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作为一元也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不是主观规定,而是发展着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中国美术史上有一句话:“难成而易好”。现在的画家进行主题性美术创作是“难成而难好”。一个画家要表现一个重大的题材,就要研究这段历史,找到其中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最后,这种理性的研究还要化成感性的东西,激发出自己的创作激情,还要有丰富的积累、丰富的经验、纯熟的艺术语言,才能完成好作品。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艺术家具备多种素质,有高度的修养。
现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好作品出来后去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该怎样接受,评论界该怎样对待。我想,如果国家和社会需要这样的作品,就存在两种吸收途径:一是通过市场,二是通过展览,展览完后应该由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的美术馆、博物馆来收藏。50、60年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繁荣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政府支持,博物馆收藏,作品有去处。这样虽然收入不很多,但艺术家还有热情。现在也应该在这方面给艺术家以物质和精神的保证,保护艺术家创作主题性美术作品的热情。另外,对主题性美术的评论应加以引导。我国的主题性美术虽不再象过去那样占主导地位,但是仍占一席之地,对优秀作品应从其思想性、艺术性上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国家应提倡和鼓励主题性美术创作,优秀的作品应该作为国家的精神财富而保留。目前,这些环节对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该逐渐找到解决的办法。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主编):英文没有“主题性”一词,俄文有该词,含义为“主题的”,有重大题材的意思。广义上看,一切绘画,无论人物、静物、风景,都有主题。因为它们都表现一种观念或思想。因此“主题性绘画”这个词严格说不太确切。但是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它有自身的特定涵义,主要就是包括了重大题材、重要主题和重大意义等几个方面。
20世纪中国由于经历了重大社会变革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特别重视主题性美术创作,而且主题性美术创作也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民族特色了。1998年,美国人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也选择了中国的主题性绘画,不论他们选择的角度与意图为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也认为这些作品是很有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题性绘画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不应该贬低自己。应该将这类作品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艺术的重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主题性美术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少,质量也不低。但是正象前面靳尚谊同志所提到的,它为什么会衰弱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组织得不够。50、60年代一批画家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组织和经济支持就无法创作出那些力作来。象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另外,当时作者的稿费虽然不多,但是政治待遇很高。这些因素都是主题性美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还有关于集体创作的问题,它需要有力的组织才能得以解决。象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的大型作品不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行吗?没有有力的组织和经济支持行吗?这次九届美展油画作品中,主题性绘画约占十分之一,其中大部分作者是总政的,原因就在于总政组织得好。
总之,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对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育,我们就应该组织主题性的绘画,不但要组织其创作,还要组织收藏。国家要倡导主题性绘画,就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保障,挖掘潜力。
詹建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今天与会的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主题性”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觉得,它首先应包含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和突出的社会意义。这种鲜明的思想性与一般的审美性、精神性不同。主题性首先不是题材的界定。人物、风景、静物都有主题性作品,但它们又区别于一般的人物、风景和静物作品,如王式廓的《血衣》、罗中立的《父亲》、艾中信的《过雪山》,以及这次九届美展湖北送展的静物作品《五角星》等等,都是主题性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次,主题性还不等同于某种“主义”。过去我们把50年代从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绘画看作主题性绘画,但从学术意义上看,二者并不相同。“主题性”一词,不等同于某种主义。历史上,象伦勃朗的《夜巡》、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属于不同的主义,可都是重要的主题性绘画。另外,主题性也不能等同于“主旋律”。主旋律作品确切地界定为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社会的一切向上、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艺术。但是主题性作品则不全是积极向上的作品,我认为有许多作品,其主题思想非常明确,但它们不是歌颂,有时批判、有时甚至表现消极的思想情绪。
50、60年代主题性绘画繁荣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文艺政策的狭隘,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创作领域拓展了,绘画的风格、题材、样式多了,作者探索的方面多了,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与过去不同了,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艺术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的重大题材为主题的创作缩小了,但主题性绘画本身的探索也拓展了,不再局限于某一种主义,而是引入了各种主义和流派,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去表现主题鲜明的题材。象有些波普作品的主题性就很强。
王 仲(《美术》杂志副主编、副社长):在美术界、文化界,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语汇概念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经不起逻辑形式诘难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概念上都对其含义的精确性求全要求的话,我们就很难使用语言了,因为有很多概念都是不合逻辑、不合语法而约定俗成的。“主题性美术”一语也是如此。它约定俗成地指向那一块反映重大思想、重大社会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也就是说,是“重大主题”,而非“小主题”、“中主题”。其实,“主题”没有“题材”更贴切,“主题性美术”实质指的是“重大题材美术”。我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觉得在探讨这个概念时应把几个层次区别开来,题材、主题、倾向性和艺术的优劣等方面都穿插在里面,使主题性与主旋律等概念难解难分。我认为,我们在探讨“主题性”美术或“重大题材美术”的时候,应该把倾向性和艺术上的优劣等方面问题先放在一边,只要一件作品的主题反映的是重大的思想或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它就是主题性美术创作。至于它画得好不好,人们如何评价它的倾向性,那是另一回事。
用“主题性”代替“主旋律”,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主旋律”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象一张神经网似地渗透在大小作品里面。它在一幅大的历史主题绘画里可能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在一件非常清淡的山水画和花鸟画里可能体现得比较含蓄,强弱显隐,但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主旋律”。所以,我不赞成纯粹使用“主旋律作品”这个词。探讨“主题性美术”有必要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把它分成几个层次来进行探讨。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美术领域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一个有乔木、有灌木、有花草的“生物群落”。而借用音乐来说,美术创作的不同层次应表现为“交响”的效果。艺术领域也是一个“生物群落”,其中的每一个品种都应得到发展和重视,而不是只提倡某一部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较为平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同气质的艺术家适合搞不同规模的作品。大主题与小品式的美术创作都受到重视和鼓励,艺术的生态系统才会健康发展。
当然,艺术史上能立得住脚的作品还是那些思想含量大、艺术质量高的大主题、大题材的大作品,这是艺术史上一条“残酷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这类作品相对而言确实少了,艺术家们普遍的心态是随遇而安,缺乏进取精神,这也是大型力作不易出现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艺术上的那条真理。因此,我呼吁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高水平的交响乐似的大型主题性作品的产生,但要注意生态平衡。
翟 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形象设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同样,统治阶级的艺术也应该是统治艺术。古今中外的美术史表明,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希望思想和艺术有利于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从古代的“成教化,助人伦”,到今天提倡“主旋律”,以及外国历史上的宗教艺术历来都是官方提倡的,也是重要艺术家积极投入的美术史上的“重头戏”。它是美术史上的一条主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主题性美术作品无论提倡与否、繁荣与否,它在美术史上都占据着主流和主导地位,是一条主线。
针对艺术图解政治的倾向,马克思曾经强调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这观点表明,优秀的主题性美术作品首先一定是艺术品,否则它也就不能进入美术史。我认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它一定要有“贴近的距离美”。意思就是,它既要贴近政治,贴近现实,但又不能直接图解政治、显现现实,而应保留一定的距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叫“中边”。《尺牍新钞》说:作文如打鼓,呆者下下捶中,高者下下打边:以打鼓边左右时,其下下意都送到鼓心里去也。王朝闻先生的理论处女作题目是《再艺术些!》,如今出版的《王朝闻集》22卷,亦可一言以蔽之:“再艺术些!”从这个角度辩证地理解,也可反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表述:“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即:艺术性是主题性美术作品的生命,否则你直接去写政论文好了。
我理解的主题性绘画是具有历史性、叙事性、政治性、歌颂性、纪念性、社会性、伦理性、积极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作品。创作这种绘画需要文化、思想、形象和感情的积累。如果缺乏这种积累,只凭好的政治愿望去创作,往往导致失败。所以,政府提倡主题性绘画,但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家都来创作主题性绘画。艺术家也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特长大胆发挥艺术创造力,实现自己的多彩追求。我赞成用“生态平衡”或“立交桥”的态度来对待美术创作。主题性或非主题性美术都可以有杰作出现,都应该受到鼓励。
冯 远(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如果说艺术史的任务相对侧重关注和研究艺术作品的创作观念、风格和形式语言的话,那么美术史的功能则不仅包括了前者的诸要素,同时还要关注作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当时社会哲学观念的、审美趣味的、民俗特色的等众多背景因素——美术史家在演绎史实时,将某个时代的某件作品或一批作品从发生到演变置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情景之中加以评判。因此,记录、反映、状写、表现特定时代的人和人的生存环境,人和人的精神状态的作品应该成为一个时代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社会在发展,时代在更替,艺术在变异。但是艺术中的某些核心部分是不能变、也不应该任意或轻易改变的。我们在关注某些东西的时候,也往往忽视了某些东西。只是在我们突然醒悟过来之时,才意识到失去的可能是弥足珍贵的。
主题性不等于思想性,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倾向性、立足点问题:主题性也不同于主旋律,因为几乎任何时代都应当涌现一些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具有丰富思想内含(深度)新颖的形式、风格(新度)以及精湛独特的技术语言(精度)三者兼具的经典作品。当然,经典作品不会很多。然而,唯其少、才经典。
前不久,我参加了九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区的作品评选。应该说风格、形式千姿百态,但评到后几轮,忽然觉得虽新则新尔,精则精矣,却缺少有份量和深度的题材与作品。国家级五年一届的大型展事留不下几件“大作”,是个遗憾。虽然个中原因很多,但多少年后若令后人觉得乏善可陈却是我等责任。我觉得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扶持一批“大作”(此“大”当不以尺幅大为“大”)。这当然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大家想想办法,争取政府投一点,社会赞助一点,画家贡献一点,是完全有可能把事情做起来的。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在中外美术史上,一直存在着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语言来创作主题性美术作品的现象。象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俊里与赤松俊子的《原爆图》、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都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战争暴行的揭露这样的主题。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适应了不同的审美习惯和艺术思潮,虽然形式、语言、思维不同,却都获得了人类的共鸣。
在新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语言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使我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技巧和思维方式,都可以完成同样的主题性作品,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变化或突破。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天艺术家的心态已经与50、60年代的老艺术家们不太一样了。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上没有那么心齐,缺乏创作的真诚,不是有感而发,有的往往是为了拿奖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影响艺术的发挥和质量。另外,一些青年画家在时代脉搏的把握上,我认为是值得商量和研究的。比如以《世纪末》为题,却描绘了人吃人的血肉横飞的图景,其目的在于揭露社会的弊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但这样表现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主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里就存在一个分寸感问题。过去我们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只许歌颂,不许批判,也有干预过多,以致违背历史真实、违背艺术规律的教训。而现在允许批判了,但是该怎样进行批判?什么是假、恶、丑?对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应该怎样认识?应该怎样体现时代精神?这些都值得探讨。
现在我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在题材上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但表现现实生活不够。这种缺憾反映了画家的一种思想顾虑:担心成为“政治画家”。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艺术家的真诚和是否有持续地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信念。另外,国家在这方面的支持和提倡也应该言行一致。
还有一个主题性泛化的问题,需要注意。如果山水、花鸟画中主题性泛化过度,可能以牺牲艺术规律为代价。
陈 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借用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甚至最后数典忘祖。所以要谈概念,但也不必太局限于概念上来谈问题。我所理解的主题性美术是:以一个事件或故事的背景为依托创作,情节可有可无,但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却不一定是重大题材,更不一定是现在具有特定内涵的“主旋律”。
主题性美术作品有自身的特点。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同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国家的意志,换句话说就是具有针对性和导向性。所以,建国以后几乎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创作样式存在。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单一样式的创作也成了艺术家成功的唯一途径。当年的名画家虽然不能卖画,但他们得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的绝对价值要比今天的经济价值高得多。
近期以来,社会对主题性美术的重视程度客观上确实不如以前了。这里有各种原因,首先就是我们的体制改革造成的冲击。当时出现的“淡化主题”以及后来创作中的主题消亡,实际上是过去政治化造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因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相对而言难以带来经济效益。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主题性美术以其突出的教育功能和内容的厚重感依旧自立于艺术之林。当前受“冷落”,也恰恰是一个最好的机遇。时下的艺术掺杂了太多的低俗;社会仍然需要高雅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去引导人们审美素质的提高。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很多具有很强的写实和造型能力并曾创作过成功主题性绘画的作者不再画此类“大画”而改画“小品”了,我觉得十分可惜。在大家都不搞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低谷时期,如果有一批人执着地追求主题性绘画,把握住它的时代性和发展趋势,经过历史的淘洗,肯定会有一批很好的作品出现,放射出历史的光辉。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副教授):关于主题性绘画,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主题性绘画既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旨范围,又是一个有较鲜明的时代选择性、传递时代主流信息的表现类别。我们有可能说清楚的,一个是作品的主题切入方式,比如有正面歌颂的,有非歌颂的,还有实写的。另一方面是表现手法,比如有写实的、超现实的、象征的、波普的,这类实例作品可以举出很多。尤其是在本世纪由战争、市场垄断和高科技竞争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分分合合,引发的是艺术家对人类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心,如果跳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应该是主题性绘画出现和仍将有其生命力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鼓励主题性美术作品的创作。
第二,应该看到主题性绘画创作在传递时代主流信息中存在着与社会风尚不完全合拍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矛盾有可能还是深刻的。因此,艺术家在创作主题性绘画所承受的矛盾压力是应该得到理解的。消解这种矛盾压力,一方面是要对主题性绘画作观念上的延展,另一方面还需要得到政策的切实支持。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当今中国处于多元化的大变革时期,人们在思想上和美术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模糊和混乱。今天这个关于21世纪主题性美术创作研讨会的目的主要在于给学术界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
我理解的主题性美术主要指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重大社会题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的人物画。
中国美术史上历来都有表现各种主题的主题性佳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其画幅规模都不属于“大型”,却不影响其优秀的主题性,艺术表现上也极其出色。古代绘画理论中,如张彦远所说的“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既强调了绘画社会功能的主题性要求,也强调了高度的艺术性。可见,要求主题性与艺术性的协调统一是中国美术史的传统,今天也仍然需要这个传统。未来主题性美术的发展难以预测,但是主题性美术创作还是有一个主题先行的问题。不过,优秀的创作其关键还在于艺术家的素质和修养。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编审):今天这个研讨会具有前瞻性质,但我不敢预言什么,希望这次会议能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繁荣。“主题性”一词的产生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客观的需要。这不是一个较模糊、覆盖性较强的概念。我认为它是可以使用的。
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战时期,正需要主题性美术去表现它。但我们的这类作品还要更重视艺术语言的创造和运用。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艺术手段、艺术语言去对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主题。
过去我们对“重大题材”的认识较窄,除了领导人和重大事件就别无他物了。这种狭窄的认识导致了艺术创作上的狭隘。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了。
田黎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副教授):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一个深远的课题,它让我们考虑如何来探索属于时代的艺术创作规律。时代呼唤力作的出现,作为一个画家更想画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但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是属于时代的严肃课题,在这里,形式与内容更需要赋予时代的精神内涵,画家仅凭热情还不够,它的内涵就是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并包容着有关绘画所有的因素。因此,主题性绘画向画家提出了社会、历史、人生的经历和阅历等方面的要求,也同时询问画家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西方文化体验到的是什么。这里需要有生命的真诚和人类精神的协调、艺术规律与艺术观念的协调、造型文化与笔墨文化的协调,它们都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前提。所以,我觉得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一个深远而重大的课题。
陈瑞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主题性”美术创作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是不明确的,“主题性”与题材有关,又不等于“重大题材”,“主题”也不可能分成“大主题”和“小主题”,更不能将“主题性”与“情节性”、“文学性”混同起来。我们所认为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往往是指那些社会现实题材或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具有精神力度和黄钟大吕式审美品格的美术创作,这样的作品在艺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反映出时代的艺术风貌。在没有更加明确的概念替代以前,恐怕还只能先沿袭以往“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说法。
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留下了不少历史的经验教训。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主题性”美术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能够真正符合人民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长期以来我们提倡“深入生活”,往往走入被动地“反映生活”、甚至只是反映生活的表象和假象的误区。我以为,大胆地、积极地“干预生活”,使“主题性”美术创作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才有可能有一个大的进步。其实“干预生活”这个概念也是很不准确的,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反映出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滞后,在这里只能姑且用之。我所理解的“干预生活”是在描述现实生活的同时,更要把握住现实生活的本质,大胆地揭露矛盾,表现出前进与后退、守成与变革、新与旧的斗争。假如我们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只是去赶任务、迎合时尚和潮流,甚至去粉饰现实、歪曲现实,也许作品会显赫一时,但历史的“最后审判”却将是无情的。
90年代以来,“疏离生活”已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在美术创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呼唤积极“干预生活”,深化“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为了促使”主题性“美术创作达到新的高度,出现真正优秀的、足以流芳百世的美术作品,对于改变当前美术创作重大一些不良风气、扭转美术创作中的某种颓势,我想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杭 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杂志主编):几乎每一个画家都曾面临过“怎么画?”和“画什么?”之类的问题。这个问题,传统风格的画家遇到过,革命的红色画家也有过,就是那些所谓最前卫、最先锋的画家,也无法避免回答。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包含着“主题”和“主题性”问题。我想说的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专利,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文艺对社会、对政治的回应,它往往滋生于艺术内部。
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评价关键在于对“主题”的判断,绘画对象所要反映的主题,是否真正经得起时间、思想和实践的检验,这样看,一些历史上的主题性创作就比较清楚了,例如齐白石的《祖国万岁》、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壮士》、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常书鸿的《攀登珠峰》、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以及石鲁等人的作品。对“主题”的判断是思想的结果,一个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如果它对社会、历史、人生、伦理等的判断是错误,那么反映错误观点的美术作品,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作品。毛泽东1951年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说:“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这样的作者,当然是不应该的,一个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会自然作出自己的判断。有人会说,西方的“自由艺术体制”产生了许多大师和优秀作品,这话也对也不对。不错,西方的确产生了许多大师,但他们的作品仍然是有“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贾克梅蒂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画家,萨特专门为贾克梅蒂的作品阐释都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年,中国的前卫艺术作品展《中国!》在德国大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前卫艺术中那种反映中国现实的方式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很符合当年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他们不管这个判断是否客观,现在已人人都知道那时一种东方主义的产物了)。西方前卫艺术没有主题吗?我想是有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对文化的反思,这些都是他们的主题,在这些主题下,你可以搞行为、做装置,但是思想的判断是必须的。
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误解我在盲目说“主题性”的好话,我想澄清的是,“主题性”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问题,重要的是看你的主题性如何与艺术表现的妥善结合。
浩然在一篇文章中仍然对《艳阳天》等作品持肯定态度。我十分感动他对过去理想的坚持。《艳阳天》所反映的当时中国农村在“革命理想”下的改革和变化,我们今天不能用真实性否定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当年的农民思想这一事实和处境。文学如此,绘画亦然,那些恰当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总要进入艺术史。
郭晓川(中华文化画报社主编、美术学博士、本次研讨会主持人):从广义来说,任何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都有主题思想,这是“主题性”的广义概念。我们此处所谓“主题性”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这里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是指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或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和创作活动。主题性美术作品对人的社会现实活动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主题性美术创作有别于纯审美的美术创作,区别就在于后者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前者不仅具有审美作用,它还有明确的社会涵义。
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历史。“主题性”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硬的概念,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本质上的变化。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看,“五四”前后是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分水岭,社会的变革赋予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现代意义的内涵。此后的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溶进了中国现代变革的洪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题性美术创作更成为美术发展史主流,阶级性和时代性是此时主题性美术创作概念的新内涵,与此前的任何历史阶段相比,它都显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化的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被推向另一个极端,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同时,简单化、概念化和雷同化成为该时期的最大弊病。新中国成立后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阶级性”此时则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文革”结束后,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长期受到压抑的人性的呼唤、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赞颂,成为该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潮。目前活跃在中国美术领域的优秀美术家,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八十年代中后时期至今,可以视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阶段。这期间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大。其中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更有美术家自身的原因。就目前来看,尚无人对此做出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面对现在创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弊病,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究竟应该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鉴于这些认识,我社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一课题的重视,进而开展更加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使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新的世纪中取得新的成就。
最后,我代表中华文化画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来参加讨论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先生和各位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谢!对给予这次会议大力支持的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山东省菏泽地区行署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