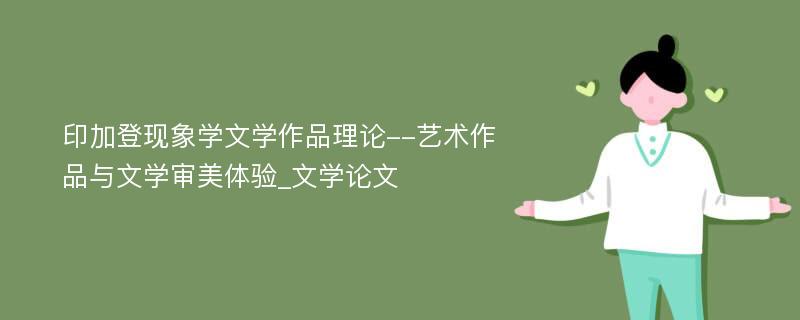
英伽登的现象学文学作品论——文学的艺术作品与审美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文学作品论文,艺术作品论文,经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3-0014-06 在区分了三种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以后,当然英伽登就要集中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态度的进一步阐述,这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在审美经验中得到现实化的文学作品的具体化的各种情况。于是,英伽登主要分析了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问题。 一、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 英伽登严格按照现象学的思想来看待文学的艺术作品。他指出:“文学的艺术作品不是作为物理的、心理的或心理物理的客体而存在的。作为物理事物的只有书,即一系列装订成册的带有有色符号(印刷油墨)的纸张。但是一本书并不是一部文学的艺术作品;它只是为文学的艺术作品提供一个稳定的、相对不变的现实基础的物质工具(手段),并以这种方式使读者可以接近作品。在心理状态和经验中只有已经描述过的阅读活动,或各种心理行为和心理意向,它们同一部特定的文学的艺术作品相联系并以之为它们的对象,但并不是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然而,尽管如此,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具体化可以是审美经验的对象,或者至少是在它的基础上,伴随着真正的审美经验,可以构成特殊的审美对象,只要这种构成是在经验中完成的。”换句话说,在英伽登看来,审美对象是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经过了审美经验的意向性构成才形成的,从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的客体到审美对象有一个意向性构成的审美经验过程:作品的物质存在——阅读活动(心理行为和心理意向)——审美态度——文学的艺术作品——审美具体化——审美经验——审美对象。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是在作品的物质存在的基础上以审美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将文学的艺术作品审美具体化的审美经验的意向性构成的结果。 英伽登以维纳斯雕像为例来说明这个过程。我们欣赏米罗的维纳斯,却并不感知那块构成维纳斯的大理石及其物质性质,而是以审美态度把大理石所构成的形体构成感受为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女人,从而形成一个审美对象——维纳斯雕像。他说:“任何到过巴黎并且就近观察过我们叫做米罗的维纳斯的那块大理石的人都知道,这座石像有许多实在的性质,我们在审美经验(它向我们提供米罗的维纳斯)中不仅不考虑这些性质,而且如果考虑它们的话,还会给审美经验造成明显的干扰。我们仿佛不自觉地忽略了它们。例如,维纳斯的‘鼻子’上有一个斑点妨碍和损害了它统一的外观。这块石头也显得有点粗糙,有一些压痕,甚至在‘乳房’上有一些小洞,似乎是被水侵蚀了,在左边‘乳头’上也有一块‘损伤’等等。我们在审美态度中(对维纳斯的理解是在这种态度中发生)忽略了所有这一切。我们仿佛没有注意到石像的这些细节,仿佛看到‘鼻子’统一色彩的形式,仿佛‘乳房’的表面没有任何损伤。有人也许会说,尽管我们实际上看到大理石像平滑的、微微闪烁的、白里泛黄的表面,但我们仿佛没有看到它,我们仿佛忘记了维纳斯的‘身体’毕竟不会像大理石那样炫目的‘白’,它不可能有这样微微闪烁的外观,等等。我们忽略了那同我们关于‘女人活的身体’的概念和‘完满’的概念不适合的东西;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补充了那些保持‘女人活的身体’的形式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思想(尽管人们会说它们正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而是生动的显现并且和其他因素和谐地结合起来构成女人身体的形式。在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正是这些附加的因素在保持审美‘印象’可能的‘最适条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构成作用,它们造成(或至少有助于造成)审美对象的形式的显现,这个审美对象在特定环境中的审美相关性质和审美价值达到了相对说来最高的程度。”英伽登还强调了在审美对象构成过程中直观的作用和重要。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审美经验中看到的还要多;我们以直观的方式理解‘维纳斯’,但现在这不仅指我们理解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在一个特殊的地点和物理位置上,在一种心理状态中——这清楚地表现在面部表情,在目光和非常特殊的微笑中,等等。然而同时,它不是一个实在的女性形体,也不是一个实在的女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实在的断臂女人(我们假设说,她的伤已经好了),我们肯定会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到强烈的反感、厌恶或者同情。另一方面,在米罗的维纳斯的审美知觉(理解)中,就没有这一类的东西。……在审美态度中失去了手臂并没有干扰我们。……我们首先理解的是维纳斯整个形式的积极审美价值的直观特征,手臂并没有妨碍我们直接看见形体的完美无瑕的线条以及整个形式特有的苗条,当我们从一定的距离以外来看塑像,并且被形体那难以觉察的微妙而又敏捷的动作所打动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英伽登把这样一个审美对象在审美态度和审美经验之中的构成过程看作是一个“审美知觉—审美体验—审美对象”的过程。于是,他指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考虑的是处在哪一种基本情境更好一些,既不是对一块大理石的简单的感性知觉,也不是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知觉,最后也不是艺术史家冰冷的观照,他精确地观察这个从海里打捞出来的‘艺术作品’的细节以便‘科学地’描述它,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的也只是感性知觉。它毋宁是这样一种情境,我们在其中衡量什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更好一些。对这种情况,感性知觉只构成进一步体验的基础,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这种体验从它得到一定的支持,并且最终把米罗的维纳斯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经验的对象。与此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审美经验的对象不等同于任何实在的对象。正是某些以一定方式构成的实在对象(特别是在雕塑中:事物),成为在审美态度中展开的经验过程中的审美对象构成的出发点和基础。这些实在对象(作为出发点和基础)的形式和各种视觉特征都不是不相干的和任意的,如果一个特殊的审美对象在某种经验中构成的话。创造的艺术家力图给予实在对象的正是这种形式,并且使它显出这些特征,它们(连同观者方面适当的态度)就成为构成审美对象(艺术家预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预见到的对象)的指导原则。这就是那些只有在艺术作品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解释的艺术的‘秘密’。”在这个基础上,英伽登认为,我们还要从其他的角度来进行审美对象的构成,“只有在我们成功地把这些价值在直观中具体化,并且综合地获得最后的统一整体时,我们才能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观照中,欣赏到最终构成的审美对象的可见和可感的美的魔力。” 英伽登的这些论述,把审美对象在审美态度和审美经验之中作为意向性构成物的构成分析得非常到位。这种思想,虽然是康德以来先验认识论的一个美学成果,但是,英伽登却把这个过程描绘得合情合理。这应该是审美对象构成论的一个很好的理论表述,对于我们正确地以审美态度和审美经验来构成审美对象,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这对于审美反映论的某些不足之处也是一种补充。 二、审美经验的三阶段 英伽登认为审美经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审美对象构成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原始情感阶段;第二,审美对象构成阶段;第三,审美对象的宁静反思和情感反应阶段。 关于原始情感阶段,英伽登认为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快感”,而是一种对对象的特殊性质的特殊情感,这种原始情感还具有“原始性质的欲求因素”,这种原始情感转化为审美经验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和审美态度,并且在本质还原的直观之中建构起审美对象,实现了审美经验的积极创造性。在英伽登看来,把原始情感视为所谓“快感”是一种“庸俗化”,因为在其中包含着兴奋、惊奇、原始性质的欲求因素等等。他所谓的“原始情感”是一种对特殊性质的特殊情感。他说:“在一个实在事物的知觉中,我们被一种特殊性质或一系列性质,或一种特殊的格式塔性质(例如一种色彩或色彩的和谐,一种旋律或节奏的性质,等等)所打动,它不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且还不让我们无动于衷。它对我们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这种特殊性质——吸引我们的注意并且影响着我们——使我们产生一种特殊情感,按照它在审美经验中的作用,我称之为这种经验的‘原始情感’。因为它是审美经验这一特殊事件的实际起点,尽管决不能忘记它已经是打动我们的性质影响的结果。”在明确了“原始情感”的概念以后,英伽登指出了在原始情感阶段,人们如何从一般日常生活的“正常”过程过渡到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产生审美态度的变化,所以原始情感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这种审美态度的产生。他指出:“原始情感以及从它发展出来的审美经验其后各阶段占据了我们新的目前时刻,所以它和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的过去和未来的任何明确联系都丧失了。于是它构成一个自足的生活单元,它从现实生活中划分出来,并且只是在审美经验过去之后才重新插入生活的过程。”原始情感所促成的这种与日常生活过程的分离又促成了日常生活态度向审美态度的转变。英伽登说:“原始情感使我们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现实生活的自然态度到特殊的审美态度。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它的结果是人们原先注视着现实世界的事实(要么存在着要么将要实现)的态度转移到注视着直观的质的构成的态度,并且同它们建立了直接联系。”也就是说,随着对待对象的态度的改变,人们把握对象的方式也由普通的知觉转变到本质还原的“直观”,这种直观“作为原始情感的结果,我们注视的不是具有这些或那些性质的现实存在的事实,而是注视着这些性质本身,它们的格式塔……仅仅这种性质的出现,就完全足以使我们观照它们的特殊本质并从而产生原始审美情感。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感性知觉,在我们发现具有审美感染力的材料中,以一种本质的方式得到转化。”这样,观赏者就会以现象学还原方法去对待对象,即把对象的现实存在“悬置”起来,把最初“在相关知觉中显现为事物特征的性质”从原有的形式结构中解脱出来,呈现为纯粹意识现象,为构成审美对象做好准备,实现“从实践态度到审美态度的过渡”这种“彻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并不是现实本身的改变,只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细致的、创造性的人类活动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把现实对象还原为审美经验的“现象”——纯粹意识现象。 第二阶段是审美对象构成阶段。对此,英伽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首先,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对产生原始情感的性质的直观理解(知觉)占主导地位。“在理解中设想的那种性质获得了某种新的、第二性的特征:它满足了我们‘看’它的愿望;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这种愿望;与此相关它也变得比以前更‘美’了(用通俗的语言说),它获得了一种活力,一种魅力,一种魔力,对此我们以前从未怀疑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它的渴望。以这种面貌显现并使我们着迷的性质现在对我们变为一种特殊的价值,特别是一种不是冷静地判断而是直接为我们感受的价值。这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情感的高涨,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快感的形式(方式),是对这种性质,它的外观和自我呈现的形式的欣赏。它使我们暂时陶醉和欣喜,就好像美丽的花朵的芬芳令我们陶醉一样。”其次,英伽登指出了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构成审美对象。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构成审美对象,另一种是提供一些细节进一步去构成审美对象。他说:“要么审美理解把握的是一种要求补充的性质,要么在它的理解中,对象呈现出全新的质的细节,在这些细节中第一次出现了某些相关性质;而且这些细节同原来的性质和谐一致,并且丰富了对象的整体。于是,审美经验开始新的发展,它常常可能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它可以发展成为两种不同的情况。或者原始情感和一开始出现的性质促使我们完全自由地构成审美对象,而不与周围的对象保持进一步的联系,或者这种性质是一部艺术作品的一个细节,艺术作品具有这种性质作为艺术家创造的实在事物(一幅画、一座建筑等等)的物理基础,对它的知觉使观察者进入审美态度,使他可以观照一系列审美价值质素,促使他重构相应的艺术作品并且构成一个特殊的审美对象。”再次,英伽登分析了后一种情况。他认为,这是一个由各种审美质素逐步达到和谐的过程,不能一下子完成。“‘审美相关性质’的各种和谐都在这里呈现出来,它们以各种外观为条件和互相补充,要求感知主体采取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以便在其多样性和由此产生的最终和谐中实现其构成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从客体质料(如大理石)创造(建构)出主体对象(人),在其中可能出现“移情现象”;另一是,在一系列性质基础上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质的和谐”。“构成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的)具有最终确定性质的质的和谐是审美经验整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或至少是其最终创造阶段的目标。审美经验的范畴构成从属于它的结构。这意味着:范畴构成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即我们得到一个尽可能丰富和有价值的质的和谐。这种和谐,尤其是其确定性质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审美对象构成和存在的终极原则。艺术作品提供审美对象的最高性质和结构来帮助我们构成审美对象。” 第三阶段是审美对象的宁静反思和情感反应阶段。“审美经验的最后阶段显示出一种宁静。一方面是沉浸于一种更宁静的反思中,在审美对象中对质的和谐进行观照,以及接受各个成为可见的性质。另一方面,与此相一致,开始出现我上面提到的对已构成的质的和谐第二种情感反应形式。就是说,承认审美对象价值的情感以及同它相适应的赞赏方式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英伽登说明了在这个阶段中审美经验的主要表现。其一,这种经验是一种确定的情感行为。他说:“这种经验,就像对某种东西的快感、赞赏、欣喜、热情一样,是由非常明确的情感确定的行为。”英伽登用马克斯·舍勒的“意向性情感”和希尔布兰德的“对价值的反应”来指称它。“在这种意向性情感中,和同某种东西的直接意向性联系同时,表现了对它的某种评价形式。正因为如此,对审美价值的承认发生在一种情感活动中。它构成我们对价值的适当‘反应’。希尔布兰德把它正确地称为‘对价值的反应’。它产生对于直接呈现的价值的观照。”在这里,英伽登明确地揭示了审美经验的意向性情感性和情感价值性。这在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还是一种新鲜观点,因为当时价值哲学才刚刚兴起不久,把价值哲学运用到美学和文学思想之中那就更是凤毛麟角,而且当时流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也阻碍着这种运用,而现象学的文学思想在意向性的观念中实现了这种运用,英伽登是运用得很成功的。其二,审美经验是一种与审美对象直接交流的直观活动。英伽登说:“只有在同审美对象的直接交流中才能对它可能的价值作出独特的和生动的反应。当然,我们可以冷静地‘判断’某种东西的价值,即运用适当的专门标准对它的(审美)价值作出判断,而没有相应的审美经验,也没有在审美对象中构成并观照一种质的和谐。”他指出那种以纯粹理性来判断艺术作品的人,由于他们把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完全和判断一棵树是橡树的判断等同起来,所以“这种对一个对象的审美价值纯粹推论的判断不再属于审美经验”,而职业批评家往往就是这样的情况。“职业批评家经常以高度技巧作出的判断一般只是一些间接判断,不是对审美对象的价值,而是对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手段(工具)的判断,借助于这种手段审美经验可以构成一个具有积极价值的审美对象。职业批评家即使在他们关于艺术作品的判断没有错误时,对有关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的本质也没有说出所以然,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不再能具有完整的审美经验。”这些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职业批评家的弊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原则——美学批评必须以完整的审美经验来构成和观照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而批评家的审美态度和研究态度应该是有机结合的。其三,审美经验还应该与理性概念相结合,才可能得出正确的审美判断。英伽登非常明确地确定,“审美对象的价值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手段(工具)的价值,这个手段具有另外的价值。如果审美价值毕竟存在的话,它就包含在审美对象自身之中,并且以它的性质和由这些性质构成的质的和谐为基础。”这里坚持了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的本体论存在性质,当然这种存在不是与人的情感无关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意向性情感的直接构成物和相关物。不过,在整个审美过程之中,审美经验还应该与理性概念相结合,把审美态度与研究态度结合起来,以达到审美判断的理解性。对此,英伽登说:“在完成了整个审美经验之后,当我们同直观地呈现给我们的审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时,我们可以在一个判断中认为它具有一种价值,我们也可以对这种价值作出判断,或把它同其他价值相比较并在一系列价值中排列具有价值的对象。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再是在审美态度中发生的,当我们力图冷静地意识到在审美经验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并且想从概念上确定这种经验的结果时,我们就又回到研究的认识态度。”也就是说,审美态度只是让人“审美地体验某种东西”“在直观理解中观照质的和谐”,这不同于对某种东西的“研究态度”,研究态度是要“了解(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审美对象是什么,它是如何构成的,它包含哪些性质,它们在其中构成哪种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审美活动不仅仅要以审美态度去形成审美经验,而且还应该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构成审美经验与理性概念相结合的新经验,以认识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图式化外观和形而上的质素。英伽登说:“我们可以试图在已有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经验,我们在这个新的经验中把注意力指向所构成的审美对象,并清晰地理解它的细节特别是它的价值。换言之,我们必须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把审美经验中构成的东西理性化,以便从概念上把握那渗透着情感因素的东西,并且在严格系统地判断中论断性地确定它。”在英伽登看来,审美经验中的审美态度和研究态度是应该相互结合的,他的结论是比较全面的:“所以,任何人以适合于认识实在对象的纯粹研究态度来开始研究艺术作品,而没有首先试图恢复作为基础的有时候相当复杂的艺术作品,同时又没有在审美经验中以艺术作品为基础构成审美对象以便认识它,就决不能获得关于审美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单是审美经验也不能为他提供这种知识。它只能给他一种具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和其他具体经验一样,必须尽可能从概念上理解其结果。”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全面把握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其四,快感是审美经验的附带现象。英伽登在前面分析审美经验时,非常突出了情感因素:在审美经验的第一阶段就是“原始情感”产生,到第二阶段审美对象构成过程中也离不开“意向性情感”,而到了第三阶段还是离不开“情感反应”。但是,他却提醒人们不能耽溺于“快感”之中。他说:“审美经验在其全部过程中,尤其是在积极展开的终极阶段中,无疑包含着某些使经验主体愉快的因素。它还在经验主体身上产生进一步的愉快,甚至快乐状态,或者正相反,产生不愉快的反感状态。和具有高度价值的审美对象进行交流,直接地观照它并赞赏它,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任何专注于这种愉快的人,实际上都把审美对象主要的和本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他所注意的只是审美经验的一种附带现象,顺便说一句,这种现象的产生不限于审美经验。……任何人以这样一种不理解的方式忽略了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他也就不能理解审美经验的本质功能。它一方面在于构成审美对象,并从而‘实现’那些只能以这种方式具体化的非常特殊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于实现一种对于审美价值性质的和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价值的情感——观照经验。发挥这种本质功能就通过一种特殊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价值来丰富了属于人的世界;它也通过一种打开通向那些价值之门的经验而丰富了人类生活,最后还赋予人一种属于他作为人类成员的质素的能力。”换句话说,在审美经验中,我们不能忘记它的主要功能、本质功能——构成审美对象,在具体化中实现审美价值,如果仅仅满足于其中的快感,那就会达不到文学艺术作品的真正审美价值——使人成为人,使人类生活和世界丰富多彩。这对于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商品化、消费化和娱乐化也是一种很好的警示。其五,审美经验最终构成全新的意向性对象。英伽登认为,审美对象的最终构成以及对价值的肯定情感反应在审美经验的终极阶段中导致一种进步的因素出现。这就是说,审美经验最终是要祛除人们的一些把审美对象假定为某种东西存在的“独断的”要素,“审美对象中描绘的事物人物和事件的准实在性构成这些被修正的‘独断的’要素的意向性关联物。”在英伽登看来,审美经验构成的审美对象是一个全新的对象——意向性对象。他说:“尽管审美经验是创造的,但是只要它构成一个全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仅超越了任何实在事物而且超越了作为基础的艺术作品,它就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发现的经验。因为按照从艺术作品的知觉中产生的暗示,它在纯粹性质,尤其是审美价值性质中发现了某些必然的联系。在理解了这些联系之后,它就可以在想象中把握包含在审美对象中的质的和谐。特别是,审美价值格式塔性质在审美经验中借助于艺术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性质铭刻在审美对象上。但是这个过程一旦完全构成这个对象,审美经验主体就在下一个阶段中感知这个对象,在审美经验中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承认要素,它就是确信实际存在着这样一种审美价值性质的和谐。”不过,这种审美价值性质的和谐的“存在”是一种“理念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实在存在;相反它是纯粹性质——这里尤其是纯粹审美价值性质——中一种必然的和本质的互相联系的理念存在。”英伽登指出了“存在承认要素是成功的审美经验的最后阶段,它不同于并且完全独立于我们周围现实世界的存在承认要素,它甚至也不同于对艺术作品中再现客体的得到限定的存在承认要素。这种要素变成(或进入)一种对质的和谐的存在确认或巩固的要素。”这确实是现象学文学艺术作品论的独特之处,它指出了我们最终在审美经验中承认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是一个审美价值的质的和谐的“准实在”或“意向性存在”。不过,他的这种描述倒也符合审美实际的某些方面,尽管在笔者看来它在本体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 [收稿日期]2015-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