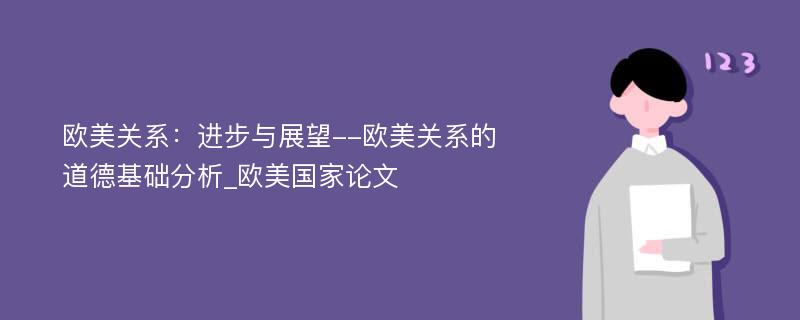
欧美关系:进展与前景——解析欧美关系的道义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欧美论文,道义论文,前景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中不能讳言利益,但也绝不是除去利益别无他物。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双边或多边国际行为体之间达成合作关系的时候,一般都会表述共同利益之外规范性的价值追求,常见的包括“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与繁荣”之类。质疑者或云:这些表态不过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或者增进双方利益自然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毋庸赘言。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国际关系中强化“道义基础”,无疑是增强国际利益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后冷战时代欧美关系的特点是强调双方之间的“认同”(identity)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国际关系中的“认同”,指的是国际行为体(agent)之间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1990年的《跨大西洋欧美关系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双方关系的基础是欧美国家“铭记它们的共同遗产和紧密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这就明确区分了“我们”和“他们”。随后,宣言强调,跨大西洋关系是基于欧美国家“对人的尊严、知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和公民自由,以及对过去几个世纪中大西洋两岸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信仰”而建立的,双方以“支持民主、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和个人权利,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社会进步”为共同目标。①显然,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从认同和价值两个方面赋予欧美关系优于一般国际关系的“紧密度”和“高尚性”。在最近一轮欧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这种黏合剂性质的论调没有丝毫改变,值得进行解析。
(一)欧美关系的“道义基础”是“普世价值”
相比其他国际关系,欧美关系的特点是有着更加明确的“道义基础”,即推广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在它们看来,自己在这些方面堪当世界各国的表率,而且这些规范已经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具有无可争辩的“政治正确性”。从这个视角看,在国际舞台上构筑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就是既正当又合算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尽管上述政治价值观念在原则层面上具有“普世性”,但目前世界上在那些方面“无可指摘”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并不占多数,主要包括美国(3.01亿人,占全人类的4.6%)和欧洲(4.55亿人,占全人类的7%),即使加上日本(1.2亿人,占全人类的2.1%)等“后发民主国”,“我们看到的例外也仍是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②正是由于“接受者”众而“达标者”少,“价值普世主义”在后冷战时代才足以成为欧美国家重要的“国际战略工具”,使它们获得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舞台上对别国实施干预的权力,为其“新干预主义”提供了道德合法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普世主义”是欧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大共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对“1500-1900年主要支配国及其权力资源”进行分析后认为,只有20世纪崛起的美国才以“普世性文化”作为“主要权力资源”。③但事实上,“价值普世主义”在此前欧洲外交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现在以民主、人权和法治为主要内涵的版本称为“政治价值普世主义”的话,那么在1500年后的历史中,至少还曾经出现过以传播基督教福音为内涵的“宗教价值普世主义”和以要求各国“门户开放”为主要内涵的“国际贸易价值普世主义”两个版本。
有学者指出,以不同版本的“普世价值”为基础,19世纪以来欧洲人已经习惯了一种居于世界体系“金字塔”顶端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表现都被确信是以基督教会为媒介、从上帝的意志中得到其至高无上的合法性。”④直到二战之后,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和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增加,多数欧洲政治家才逐渐摈弃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是,在观察当代世界格局或设计未来世界秩序的时候,在他们心目中,维持欧洲的“中心”地位通常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在欧盟的对外政策框架中,欧洲传统的价值普世主义仍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在其成员国看来,欧盟正在成为建立后冷战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按照“新帝国主义”理论家库珀的说法,“后现代的欧盟为合作帝国提供了一个蓝图,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没有以往帝国的种族支配与中央专制,也不存在那种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种族排斥”,而是“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它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新帝国主义,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它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然而如今这些依照自愿的原则”⑤。
对欧美国家而言,建构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价值观共同体”是符合其共同利益的。但是,从文化相对主义视角看,当代“普世主义(典型表现在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和欧盟援助以及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中)否认了被干涉地区的复杂性,结果是构建出了天然具有劣根性的‘他者’”,⑥从而在认同层面上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进而在价值层面上获取了“我们”对“他们”施加干预的“合法性”。那么,对于世界上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而言,无论是否接受欧美国家推行的政治价值,来自欧美共同体的潜在的外部压力却都足以威胁到内部的安全与稳定,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以“排他性”为特征的欧美关系面临挑战
作为欧美关系“道义基础”的价值普世主义在后冷战时代面临多重挑战。这是因为,欧美国家实际上所做的是通过“普适性”的价值来获取“排他性”的权力,延续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地位”,这不符合多极化的历史潮流。
第一,道德的挑战。后冷战时代,欧美国家“价值观外交”的“道义基础”经常沦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使得人们难免怀疑,推广“普世价值”在很多时候不过是欧美国家实施国际干预主义的一种口实。例如,“2003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的官方理由是消灭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并未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战争的理由就转变成了给这个国家和地区带来民主和法治从而铲除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专制”。⑦试想,如果没有价值普世主义的支撑,那么不仅美英等国发动的“倒萨战争”会失去合法性,而且欧美国家对伊禁运造成的灾难也难逃道德谴责。据说,仅因为1991-2001年西方国家对伊禁运造成的缺医少药,就造成50万名伊拉克儿童丧生。⑧欧美价值观外交的工具化,更为常见的表现是依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对相似的国际事态采取大相径庭的对策,采取实际上的“双重标准”。此类案例,在欧美国家处理中东和北非国家关系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实际上,欧美国家的这些做法都是在侵蚀价值观外交的“道义基础”。
第二,世界格局变化的挑战。欧美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发展以“排他性”为特征的合作关系,从根本上说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不过,虽然美国和欧盟在认同方面有天然联系,在价值观方面基本一致,但在利益上却存在冲突。冷战结束后,随着外部威胁的消失,作为防务与安全共同体的美欧同盟趋于松散,欧美关系进入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一直试图建立新型同盟关系,先后提出多项宣言、战略和计划,但实际进展不大。这说明,认同与价值观方面的高度契合并不能弥补美国与欧洲在利益上的差异性,欧美之间在价值观共同体道义基础上建构更紧密利益共同体的尝试面临诸多困难。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给欧美国家发展排他性合作关系带来了重要的限制。2000年后,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贸易占比迅速增大。事实上,2001-2011年,欧盟从美国、日本这两个最重要的“价值观盟友”的进口额不断下降,从中国的进口额则不断上升。2001年,欧盟27国进口额中,美国占27.9%,日本占7.7%,中国占5.3%;到2011年,美国占比下降到16.9%,日本下降到6%,中国则上升到12%。⑨这种变化并非人为决策,而是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将新兴工业化国家排除在外的欧美经济合作关系无疑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第三,欧美差异性的挑战。欧美双方有着不同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模式,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美国和奉行“多边主义”欧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对欧盟国家来说,自认为“山巅之城”的美国是既“不可缺少”(indispensable)又“难以忍受”(intolerable)的伙伴。⑩冷战结束后,欧盟在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积极与外部世界构建全方位的合作关系,试图建立一种世界性的多边主义格局。欧盟所倡导的多边主义是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并不冲突。因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必须与世界各国合作,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武器扩散、毒品走私等问题。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能力以“霸主”身份在安全与繁荣方面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但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多极化世界是由它所主导的,而欧盟则试图建立一种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从此次欧美自贸区的建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别:对美国而言,“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1)是以它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两根支柱;而对欧洲而言,与美国建立自贸区则主要是强化欧美价值观共同体的经济实力,借此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欧美双方战略位势的差异,决定双方合作关系中的冲突性因素会长期存在,从而限制了以排他性为特征的欧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注释:
①"Transatlantic Declaration on EC-US Relations",1990,http://eeas.europa.eu/us/docs/trans_declaration_90_en.pdf.
②[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苟海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③[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⑤[美]罗伯特·库珀:“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OBSERVER,April 7,2002,http://wmdzj.xiloo.com/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Relation-2.htm。
⑥[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第157页,本文对其术语略作修改。
⑦[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第142页。
⑧同上,第158页。
⑨欧盟官方统计网站,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 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t00018&plugin=1.
⑩See Erwan Lagadec,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Europe,America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Routledge,2012,p.5.
(11)"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