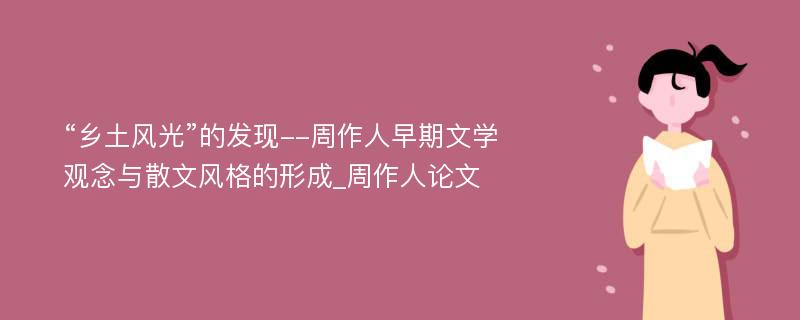
“乡间风景”的发现——周作人早年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间论文,早年论文,文体论文,散文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关注周作人的早年生平时,科举经历作为一条潜在的重要线索,与他的文学活动参照后会照亮后者的意义①。少年周作人的兴趣爱好可谓广泛:他喜爱乡间美景、民间饮食,爱好莳花种草,也着迷于书房清玩,这些在他的日记可以清楚看到。而就在这一系列多姿多彩活动的同时,他也在为科举考试进行着准备。但即便他在举业上再用功,应试也从未成为他真正倾心的生命重点。因此,两种差异明显的叙述色调在他日记中交替出现:一是记录准备科举考试的具体进程,从中不难看到作者正在承受的心理压力;二是对乡居生活细节的生动展现,此部分着墨更多。他不厌其细地描绘令自己兴味盎然的乡居时光,显然这才是他的爱好所在。前往南京求学前的十六七年的生活,对他的漫长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审美模式的定型留下了显明烙印。而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乡间风景的观察鉴赏与诗文吟咏,则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散文文体有着塑造之功。 周作人的风景观念颇为新颖:他认为“吾乡”风景才是天下美景的参照系,他乡的山水佳绝地,不过是与家乡风景略具可比性而已。他少年时即反复称颂故乡风景如画,赞叹“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②,即便是天下闻名的西湖“亦只如吾乡之南镇而已”③。在他的乡居日记里,对于家乡风景的描写相当引人注目:他曾用诗与文两种文体描摹过会稽“揽鉴湖八百里”④的山水之美,而他的观察风景既细心、角度也够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有心栽花的旧诗写作虽未如期结出硕果,却蕴含着日后重要的文学观念——“生活之艺术”的萌芽形态;而他无心插柳的风景片断,又让他的日记成为耐人咀嚼的现代散文“前文本”。本文将从周作人日记中的风景描写入手,探讨他早年的诗文写作与日后的文学观念、文体之间的关联。 一、“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 周作人居杭期间去过西湖,但当天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⑤。后来当他每次再提西湖时,景色本身都不是目的。他要么是由眼前的家乡风景衍生出联想⑥,要么是对与西湖有关的民俗产生再追述的兴趣⑦,或者是从典籍中来想象西子湖的水光潋滟与山色空濛⑧。同样,对于绍兴遐迩闻名的名胜兰亭他也只在日记中一笔带过⑨,日后通过典籍阅读的方式再做精神游历。对待名满天下的胜景,周作人的态度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观照。 相比较而言,绍兴本地的名胜像娱园、赵园、大善寺、开元寺、应天塔、张神殿、曲池等名头远没那么响亮,它们分布在绍兴的大街小巷,是寻常人家的街坊邻居。与其说它们是名胜景点,不如说是与民间生活无法分割的文化与民俗。例如正月去开元寺罗汉堂数罗汉是绍兴人过年的一项习俗,鲁迅和周作人都去那里数过罗汉⑩。由于这类名胜古迹与家乡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周作人无论在当时的日记还是以后的散文中,都对它们投注了特别的重视。由此可见,周作人的风景鉴赏并非从风景本身或是它的名声为出发点,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做出与众人不一样的发现。 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名胜、在寻常中发现风景,使周作人从独特的个人兴味出发,寻找家乡风景的妙绝。而最令其陶醉的,是“景”与“人”紧密无间的形态。游人与在地者因身份不同、与风景的关系也存在着紧张与松弛的差异:游人与风景之间有着无法尽消的隔膜感,在地者才能真正自在地饱览秀色。周作人风景观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以生长于斯的越郡少年身份、同时更用游人的鉴赏目光,寻觅并体悟那些与生活贴合最切的风景,赞叹那些在旁人看来普通到不值一提的日常景象。例如他认为最寻常的田间之景自有一番心旷神怡之妙:他欣赏“稻细如秧”的“翠绿可爱”(11),为“四岸菜花,色黄如金”而“纵观久之,怡然自得”(12),赞叹农人“着蓑笠立岸旁罾鱼”的图景“真是一幅画图”(13)。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风景成为他的乐趣。怀抱着一份对于家乡风景隐藏的自豪,少年周作人延伸着感悟的触角,将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处均变成春醪般可供小口啜饮的美景。对很多人来说因频繁接触而审美疲劳的景象,在他那里则始终保持着持久的新鲜度。如行舟中他能品鉴水乡中人或许早就视而不见的“水天一色,浪纹如谷”(14);“在园中闲玩”时能听见“山蝉鸣丛篠中”、“嘒然幽远”的声响,并由此形成有关“夏日园林景致”的典型体验(15)。甚至一阵小雨后“天色蔚蓝可玩”亦能令其欣然(16),从最常见的天象变幻中细心体悟其间的愉悦之美。当他发出“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17)的赞叹时,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既包含对乡邦故土的特别情感,更有因别具慧眼而另辟一片洞天的喜悦:越郡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使风景的要素咸备目前,生活其间的人无须费力寻访那些与生活隔绝太远的名胜古迹,甚至无须离开当下当地,只需耐心体悟一草一木、一花一虫之妙,便能找到极具亲切感的风景之趣。 需要注意的是,饱览风景的机会往往与绍兴的扫墓习俗息息相关。与人们印象中只有清明扫墓的风俗不同,绍兴民间扫墓活动一年中有三次:分别在正月、清明和十月。其中“越俗正月祭祖,名拜坟岁”(18);清明前后的上坟最为隆重:“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19);十月祭墓也叫“送寒衣”,只“数人而已”(20)。周作人日记中提及的上坟地点有调马场、乌石头、木栅、梅里尖、小皋步、小南山、圭山、了山、秋湖、龙君庄、俞家舍、富盛、鲁圩等多处,遍布绍兴乡间。在跟随族人长辈频繁习演当地民俗的过程中,周作人有了充分观察不同季节乡间美景的机会。拜坟地点乘舟来回要耗费大半天(21),下舟后还要坐轿,但却认为每到扫墓时节,虽“仆仆数日,从事于虚无,然水色山光,足偿劳苦,亦不苦也”(22)。因为一路上如画图般徐徐展开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乡间的清绝山水更使他的景物感兴源源不绝。周作人在日记中频繁记录了从己亥至辛丑两年间的拜坟岁经历,而他日后的文学成绩也证明这一时期的观察与写作训练,对其审美感受与文体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扫墓经历时,周作人频频使用的词汇是“春游”。无论是1940年代在《儿童杂事诗》中所说的“跳山扫墓比春游”(23),还是1950年代在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中谈到周氏兄弟共同的旧家生活时,对形同春游的清明扫墓津津乐道,那种少年“迫切”“盼望清明节的到来”的兴奋心情让周作人一生印象深刻。春暖花开之际,在书房关了整个冬天的少年,一旦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后的“兴会飙举”之情是不难想象的(24)。甚至多年前摄入脑海的山林春色牢牢定格为这位散文家审美图像中“代表的春景”(25)。 出于少年喜好大自然的天性,周作人用一双新鲜的眼睛接触春日山林时,他首先对石、树、花、虫等林间野趣表现出极大兴趣。己亥正月十五的调马场,他发现溪水中有“圆石颗颗,大如鹅卵”,而墓所刺栢子实则“香烈无比”(26);一年后的同时同地,“墓所松楸夹道”的“壮观”(27)景象亦令他印象深刻。到了春光绚烂的季节,他从富盛拜坟后则“折刺栢四株、踯躅三株、牛黄花数枝回”(28)。深秋时节,乌石头的秋日山林景象同样令他陶醉:“桕树经霜”后“叶肥赤可爱”;“老勿大”则“叶如榛栗,子鲜红可爱,至冬不凋”(29),草木的形态始终令他兴趣盎然。联系周作人1930年以后散文中的草木虫鱼主题,会发现这一写作旨趣实则来自于数十年前的熏陶培养。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对吟咏自然风光的诗句心有所好。无论是暖风初拂人面的初春还是春光欲老的清明,目力所及的诗句都被他细心留意。己亥正月十五拜坟岁时所乘小舟“舱颜”所刻的“水月”、“咏而归”;三副船联:“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清风明月添豪兴,镜水嵇山入画图”、“官舍不离青雀舫,人家多在白萍洲”(30)均被他一一抄进日记。他在不自觉间开启了“景”与“诗”的转换历程:在咀嚼风景的同时,更反复品读对象化后的风景。不仅将恰为当日逼真写照的咏景之句一并留存,更在乡间景色的启悟中达到对古诗文境界更澄澈的理解。例如他扫墓归途中见到“炊烟四起”、“霞光映水,暮山更苍紫可爱”的景象后,久久不能忘怀,过了一个多月仍为此天日记加上补叙:“真如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31),诗文中经典名句被他引作对日常风景的注解与意境提升。 这种对诗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族的影响。扫墓既是祭拜先人的家庭活动,也是一个诗礼大族具备文才与应试能力的男性聚合吟诗的场合(32)。同行的周氏族人中不少人具备诗才,不仅墓祭时要作赞(33),而且一路上往往也有即景赋诗,这让周作人受到比书斋中的诗文训练更有成效的实地熏染。如己亥清明龙君庄上坟时前去祭拜的族人曾共作《越城鄙夫扫墓竹枝词》,周作人到晚年仍为未记录下此作而遗憾(34)。某位族人即兴吟诵的优美诗句会成为周作人倾慕的对象,如己亥清明乌石头拜坟岁时夏叔“口占一绝”:“数声箫鼓夕阳斜,记取轻舟泛若耶。双桨点波春水绉,清风送棹好归家”(35);辛丑正月同一地点十八叔祖所吟“日暖风和帆脚稳,山弯水曲橹牙柔”(36)都被周作人录入日记。族人们信手采撷眼前风景化作诗句的自如吟咏为周作人树立了典范,他的审美力也在景与诗的双重熏陶中得到强化。相反,如果某位族兄在墓祭“作礼生”的过程中,表现得少墨无才甚至“屡读白字”,周作人则在日记中为之惋惜叹息(37)、暗自引以为戒。文学功力的深浅与否成为家族诗礼活动中表现与衡量个人才干的重要标准。 而科举考试中诗题考核的要求,更是周作人加强诗歌训练的重要动因。例如己亥诸暨县试诗题“乌桕微赤,丹槲叶黄”(38),约半个月后仍然萦绕在周作人的脑海,以致他在扫墓时面对金秋乌石头的景色,仍化用了考题形容其为“正乌桕微丹、菊渐黄时矣”(39)。 因此,无论出于对自然风景的自发爱好,还是迫于压力在家族活动中展现自我、进而实现应付科举考试的人生目标,周作人都从诗意缭绕的墓祭活动中,重视诗歌鉴赏乃至创作能力的培养。然而,或许因为这一时期科举考题的要求束缚了他的自由驰骋,环境的熏陶却并未让周作人很快就拿出亮眼的诗歌成绩。有趣的是,如追溯他后来重要文学观念“生活之艺术”的提出过程,却需要联系此时打下的诗歌基础。此番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经历,值得我们继续细心辨析。 二、“生活之艺术”的早年滥觞 从周作人日记中保存的诗词习作中,会发现他早年很喜欢制作“集句”。从辛丑年的多首集句习作如《[菩萨蛮]夏日邨居集句》、《[浣溪沙]春日集句,用坡公春情韵》、《[浣溪沙]春日遣怀集句》、《[菩萨蛮]春日天香阁偶成,时辛丑寒食》、《春晚村居即景集句》、《初夏村居即景集句》、《四时村居即景集句》(40)等看来,他在古诗词上是一位博览群书的阅读者。当他观临四季村居景色时,总会很迅捷地联想到前人对此番景色的恰切描摹,对那些相对偏僻的作品亦有涉猎,阅读面可谓宽阔。然而这却也妨碍他成为一位才情丰沛的吟诵者:他从厚实的积累中钩沉出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诗句,然而一旦这个以众人之口来传达自我之慨的过程愈趋熟练后,他的诗化表达便开始陷入寻觅他人诗句以投射自我情感的循环。而脑海积存的诗句越多,独辟蹊径的空间就越少,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独创性渠道一开始便有窄化趋势。到了独立吟咏眼前景致之时,他遂难以抹尽“集凑”的痕迹(41):不仅在赋写家乡名胜时(42)出现集句形式的题咏,而且在书写最私人化的情感时,也有着从集句到创作的过程(43)。 尽管如此,经过这番训练,周作人在诗歌创作局部性技巧的掌握上已经相当熟练。例如这位日后的“苦雨斋”主人,在此时的诗作中便有不少对“雨”意象的经营。水乡多雨多变的气候特征也给予了周作人敏锐感知自然的天生条件,落雨时分往往是感性思维之窗被打开之时,雨窗下的挑灯独坐常是这位聪慧少年思接千载的时刻。“雨”作为自然天象,被他很自然地设置利用作“离别”的背景色调,如他作于辛丑初夏、由鲁迅“删改”的《惜花四律步藏春园主人元韵》(44)将“时至将离倍有情”的伤离别与“四檐疏雨送秋声”的秋景融和无间,显示了周作人在雨景与离情的沟通与转化上已是相当娴熟。 事实上,旧家诗礼生活的涵养使周作人有机会大量阅读诗作、欣赏生活中随处可遇的诗歌,而他在建立日常景象与诗文典故之间的关联上也已表现出相当擅长。一方面,他对“诗”的理解常借助日常之“景”得以印证强化。如面对庚子春季的连日阴雨,他会忆起唐人陆龟蒙“十日滴不歇”的诗句,认为“可为今日咏也”(45);而遇“连日亢旱”、“良久不雨”之景象,他则认为《卫风·伯兮》的“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正是恰切写照(46);望见“暮日如火”时,他模仿李白《古朗月行》中“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形容其“如一轮珊瑚盘”(47),而对诗境的把握也在联想中达到进阶。另一方面,日常之“景”亦在此种反复勾连中得以诗化定型,“诗”常常成为特定“景”的固定化表达。例如苏轼的《书双竹湛师房》中“卧听萧萧雨打窗”一句,周作人便在日记中三次提到,分别是辛丑之秋、庚子春天与壬寅夏末,具体情境是第一次童试落榜之际、第二次童试的准备中与第一次求学异乡时(48),每回均是受夜间“潇潇细雨,淅沥通宵”(49)的檐溜之声感触,东坡佳句也因恰切概括出雨夜情境遂成一种固定化表达。以诗意写真来寄怀遣兴,不尽愉悦的生活体验因逐渐具备的将生活即时随处艺术化的功力而呈现出诗意绵绵。而这种与“雨”相联的诗境,似乎到了周作人久住沙漠样的北京后便从此中断了。直到多年后一个偶遇的多雨之夏重新激活了水乡少年“梦似的诗境”(50),他提起笔来写了书信体美文《苦雨》,以苦雨的外形承载了内心深处从少年起横亘半生的乐雨喜雨之情。 有意思的是,对比周氏兄弟早年的诗作,会发现周作人诗歌在意象与情感的运用与阐发上不及鲁迅特别。以庚子二月周作人收到的鲁迅《别诸弟》三首(51)与辛丑正月周作人的和诗《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52)为例,二人诗中都出现了“雨”的意象。鲁迅有“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周作人则有“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仔细辨析,会发现鲁迅对人在异乡、漫长雨夜独对一盏孤灯的“凄绝”感体会至深,而周作人则对兄弟家居相聚时伴随着窗外雨声潺潺的“联床夜话”、欢欣畅谈别有兴会。鲁迅撷取的是被“雨”唤起的难熬孤独感,周作人则留恋手足情深的相聚之乐。二者对比,一凄一乐:“雨”在鲁迅的诗学世界中成为少年离家、“九万里风鹏正举”豪情背面的一缕黯然诗魂;在周作人那里却被定格为兄弟相知相得的永恒时光的温馨音符。二人分别强调的是以雨为背景的散与聚的不同面向。鲁迅一开始就不惮独对孤独之苦,周作人则早早表现出对寻常乐景的眷念。从诗境的独创性上看,周作人对意象的诠释与情感抒怀方式不如鲁迅奇崛、有魅力。 周作人到了1930年代曾说自己的旧诗写得“不成东西”(53),这是他对早年诗歌习作一种不无“悔少作”意味的说法,实际上,要全面检视他的旧诗成绩,还须待到1937年以后。此时统观他的早年诗作,会发现从思想到语言都显得陈旧。如己亥正月的《题天官风筝》有“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54),完全不像是一位未来新文学大家的手笔(55)。即便在他写得较为清新可观的作品中,也仍有一种难以尽脱前人窠臼的平庸感。例如辛丑二月的《游赵园有感》(56)无法超越怀古之作的平常口吻;而求学金陵大半年后的《暮春客居感怀》(57),尽管在表现客居思乡情感上呈现出一种微醺的轻愁之态,有别于一般的伤感套路,但总体看来仍不过是惜春伤逝的寻常之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风景熏陶下的诗歌习作,意外催生了他日后文学理念的养成。1924年11月《语丝》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为主编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他以现代文明建设者的责任感探讨了“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之具体方法:即以实行“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58),恢复“千年以前文化发达”的“灵肉一致之象”(59);通过调和禁欲与纵欲两种极端复兴中国古来生活的美好形态。“生活之艺术”作为周作人思想的关键命题,折射出五四作家为重建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所做的努力。 而这一成熟期的文学观念,实际上通过他早年日记中的文学表现,已能寻觅具体的实践踪迹。这种由景入诗,从风景(生活)到诗歌(艺术)的穿梭,使周作人很早便将生活实景对象化、拉开一段距离进行观照品读,建立起了用生活中的审美体验来印证书本中的美学典范的审美习惯。或许可以说,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思想命题的“生活之艺术”,是提出者对其自身成长轨迹和生命形态的提升与概括。在五四光辉的照明下,个人精神轨迹的自然延展有可能会被赋予时代思想的丰厚含义,然而一旦还原提出者本身基于生命经验的质朴形态,则会发现文学观念本身实则富含个人化色彩的生长方式。 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中追述旧事时曾写下了“会稽文风世称美,吾家诗句却稀微”(60)的句子,在概括周氏的家学渊源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尽管地处“蓑履名贤传翰墨”(61)的文风鼎盛之乡,但周姓诗人却极少,周家虽然举业传统深厚,但有杰出才华的诗人却没出过。这或许跟周氏文风质实、少浪漫气息的特点有关。其实在周氏族人中,倒是一位玉田叔祖写诗,他著有《鉴湖竹枝词》一百首,鲁迅曾手抄过一遍,周作人也在日记中记录过其中的句子(62),他的学术兴趣对周氏兄弟曾有过不小的影响。但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言:竹枝词“须有岁时及地方作背景”,往往要从“平生最熟习的民俗中取材”(63),而周玉田“竹枝词”的写作其兴味也在于地域民俗而非诗艺本身。周作人的诗歌训练日后也将表明,他所沿袭的也是这种以诗歌外形来关注、承载生活情态的路数。他的诗歌爱好一直未能将诗歌本身发扬光大,却能在合适的机缘中建构起一种将诗意与人生密切关联的理论形态。学界已注意到“生活之艺术”的观念曾汲取了多种资源的营养,而周作人早年生活形态中的趣味与审美模式,昭示出五四以后作家视野开阔的理论汲取,实则呼应了自身渊源深厚的个人趣味。 三、作为现代散文“前文本”的风景小品 虽然周作人此时的诗歌训练,要到五四后提出“生活之艺术”的理念时方才展开枝叶与花朵,而他在诗歌上的表现则要待到更迟才有遥远回响,但这一时段并不特出的诗才或许却从另一方面驱使他拿起了散文之笔。例如,孤立来读周作人作于辛丑二月的诗作,会发现其不过是春雨绵绵之夜的起兴,但这种旧诗嵌入到日记却因为诗与文两种文体的参差而产生意外的情致。这一天周作人在接祖父出狱归家的夜航船上“口占二绝”,并写下了二百来字的日记: 晴。晚下舟放至西郭,已将初鼓,门闭不得出,与以蚨二十翼焉。行里许,余就寝。春雨萧萧,打篷甚厉,且行舟甚多,摩舷作声,久之不能成睡。披衣起,阅危言一篇,口占二绝,稿列如左: 东风送雨夜萧萧,独倚篷窗影寂寥。 惟有愁人长不寐,挑灯危坐读离骚。 风雨暗孤灯,倚篷且曲肱。 扁舟何处泊,今夜宿西兴。 坐少刻即寝,就枕即成睡。少选又为舟触岸惊觉,约四下钟矣,遂不复睡。挑灯伏枕作是日日记。书讫,推窗一望,曙色朗然,见四岸菜花,色黄如金,纵观久之,怡然自得。问舟子已至何处,则已到迎龙牐左近矣。大雨。(64) 不难看出,主人公的情绪如从晴夜转而大雨的春夜一样经历了起承转合。在一条夜航船上,在与众多船只挤蹭摩擦中,作者想到祖父即将归家,有兴奋、也有隐隐的不安。由最初的“久之不能入睡”、“口占二绝”,到“就枕即成睡”,后来“遂不复睡”、观金色菜花“怡然自得”,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两首旧诗成为日记的有机部分,它们既勾勒了一位刻意模仿传统士大夫举止的少年形象,又为文字增添了古雅的味道。旧诗更传达出人物的心声:内心的孤独、苍茫、憧憬等多层次情感均包裹其内;这种古典的抒情方式又不同于平铺直叙的直白叙说,是一种变调为雅音之后既旧且新的表达,后来周作人散文中的抒情方式正延续着这种蕴藉的脉络进行。单独聆听并不出彩的副声部的旧诗,与文章融合后却极有效地提升了文章本身的情韵。 这样直接剪裁旧诗入散文的写作实验,标志着周作人在找到散文写作手感之前,曾经历了不断修正提升的历程。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自己亥秋冬至辛丑初春,周作人从14到16 岁曾在两年间三度描写同一片风景——这就是调马场,周家扫墓的重要地点之一。而对读周作人三次描写,会发现他在散文写作上进步迅速: (一)己亥正月:“坐兜轿行山中过一岭,约五伯级,下山行一二里,过一溪,径丈许,长数丈,舁者赤足而渡,水及骱上,下有圆石颗颗,大如鹅卵,颇觉可观。再行二里始至。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65) (二)己亥十月:“过一岭,约二千余级。又行二里许,过一溪,径二丈,长里许,水没骭至股,舁者赤足而渡。中有石,红绿皆备,大如鹅卵。又行二里许,至墓,拜毕回舟已未初矣……初过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袖间,幸即止。饭毕大雨数阵,归家已五点钟矣。”(66) (三)庚子清明:“乘兜轿行三里许,过一岭,约千百级,山上映山红、牛黄花颇多。又有蕉藤数株,著花蔚蓝色,状如豆花,著实即刀豆也,可入药。又二里许过一溪,迳阔二丈余,水没及骭。舁者赤足而渡。行四里许,至墓所,松楸夹道,颇称壮观;余及方叔作赞。方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晴。下山午飧。下午开船,方将进城,忽天色如墨,大雨如注,列缺数声,电光烂然,至家不歇,檐溜如柝声滴然。”(67) 画线部分的文字多有雷同,而作者对熟悉的风景与相似程序的描绘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不断重复的拜坟岁经验给了周作人思考的余裕:他在纪行的同时,更展开了对旧文本的修改。叙述清晰的文字在此过程中定型积淀,而愈渐精密的观察训练则使他的文字每次均有新突破。一开始,他对正月初春景象的形容还只停留在“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这样既不生动、季节感亦不太明确的套语上,但入冬以后这类对仗工整、带有作诗痕迹的文字便不再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己亥秋冬的风景描写后面出现了一段余韵袅袅的补记: 补:山中杜鹃不多,即有之,亦止二三树,每树花一二朵。惟油蛉甚多,一路草木荆棘中无不有之,可作一部鼓吹。(68) “补”字的加入表明此段为事后补充描写。追述当天行程时,周作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山中杜鹃和油蛉秋鸣上。而正如每树仅著花数朵的杜鹃和毫不起眼的油蛉子一样,这段后加入的寥寥数语表面十分平实、细细品嚼却有一股悠长的趣味。周作人放弃了整体概括风景时不痛不痒的浮面文章,开始择取花、虫之类的生动微物,使原本的静态景物画因一二灵动细节而具有浮雕的立体感。而这种不再从大处着眼而专注于小处落墨的手法,是诗歌的重要技巧,将此手法引入散文时却取得了格外明显的效果。从语言上,周作人也开始化骈入散、不再被固定的四字句格式捆住手脚,使文字具有很大的弹性和余地;而有意识地渗入的四字句式,又为风景小品注入了一种雅驯的味道。实际上后来周作人散文的语言主要是沿着这样一种风格演进的。内含文言因子的散句,成为他的语言特色之一。他后来提出要“将古文请进国语文学”(69),并在评点俞平伯散文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说法:即现代小品文的理想语言是将“古文”即文言的“分子”与“欧化语”、“方言”等“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这“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70)。这一时期的风景小品实际上已为后来的理念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此时的写作训练开始让周作人体会到自由挥写的舒畅,他从结出青涩之果的诗歌写作中调转身来,把文言因子融入小品文语言,为他以后综合调度各种语言的涓涓细流以汇入现代散文这条“古河”(71)积淀了语言试验的前提。 随着审美观察的愈趋熟练,庚子清明时节的调马场第三次为他所描绘时,已是一幅着色自然的风景画与节奏轻快的回旋曲了。或许是庚子清明调马场的山花绽放太过绚烂,周作人在每每相似的行程记述之间,引入对花木形态的细节写真,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牛黄花、蕉藤花遂在他笔下呈现出一幅配色协调的画面。这一表面上的闲笔也标志着他的景物观察另一层境地,因为记叙既出现了微视角的聚焦、又形成了如“小雨簌簌”、“大雨如注”交替进行的节奏。雨声仿佛大弦小弦的嘈嘈切切,使这段出色的风景小品交织成缓急得宜的乐章。而这一节奏感则得益于此前日记的积累。不妨来看己亥年将尽时,周作人对于一次扫墓历程的描写: 至施孝子祠前上岸,祭毕下舟,已午,午飧。下午至白莲墺,拨草而入,拜毕而回,红日已衔山矣。鼓楫速归。而舟夫老罢,船亦甚小,至凌家山已炊烟四起,但见霞光映水,暮山更苍紫可爱。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至渡东桥则已昏黑,幸星斗满天。至家饭已吃过,至地叔处夕飧。(72) 如此短章已然表现出一个好的散文写手极佳掌控节奏的能力。一切活动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绷紧着一股内在的紧张感,而每件事又正好在恰切的鼓点上完成、一丝未乱。画外音(叙述者声音)与画中人有一种默契,二者流露出的陶然感又冲淡着这种紧张的潜流。正是对拜坟岁经历的反复书写,使周作人保持着叙述次序上的绵密,也训练出不徐不疾的节奏感。 有意思的是在庚子清明扫墓调马场拜坟日记后,周作人又在日记上方补入了几个生动的细节,延续己亥十月首次出现“补记”的精彩: 山中竹林甚多,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 山中忽闻有声如鸡,其声咯咯然,山谷皆响,闻之轿夫云系雉雊也。十六日笔。 山中人云:雉性极痴,如见之者微惊之,则匿首丛篁中,捧之可得;如逐之,则飞去矣。 十二日东关马家桥雷震死一蜈公,阔于鞋底,长数尺。路中舁夫说。(73) 前三则记述山竹形状与雉雊性痴,貌似与行程关系不大,实则别具一番清淡韵致。这位15岁少年的精彩手笔即便单独作为散文来读,与其成熟期作品比肩也不逊色(74)。实际上在三十六年后《北平的春天》中,周作人引述了当年的日记并做出了重要修改:这些“补记”被当作重要细节被整合进入日记正文。他显然时隔多年仍然非常欣赏这些“补记”,认为它们有为正文点睛的功能。而从庚子清明日记到成熟期著名散文的修改过程,反映出周作人早年日记作为现代散文“前文本”的重要过渡形态。 最后一则记述舁夫闲谈,更与正文疏离。但这种絮语风格的轶闻琐记,却是周作人自庚子三月以来用“补记”形式着意经营的一种文本形态。与日记正文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琐屑记述不同,这些位于页眉处的补记细细咀嚼很像文学性浓郁的古代笔记。 周作人在古代笔记阅读上下过大功夫,他的阅读面极博,而这一时期“补记”已然能窥见他笔记阅读的兴趣。如前所述,他以书斋阅读来题咏眼前之景的审美转换,使补记中实现着从书斋到现实的诗境穿梭(75)。而日后发生更深远影响的试笔则为对古代笔记的征引:如庚子上巳日日记中提到《西湖游览志》,此日“补记”为:“田叔禾《西湖志余》云:明时杭州妇女,是日咸戴荠花。上巳日记”(76)。像这样引述古文献以印证岁时民俗的形态,反映出周作人自少时即关注民俗的个人兴味。日后周作人分别通过两种途径延伸着当年对笔记的兴趣:一是将其融入美文中,如1924年《故乡的野菜》再次提到《西湖游览志》,却与文本融合无间;二是敷衍成后人评价褒贬不一的“文抄公”文体,将笔记阅读趣味铺陈为书话体散文。此时的“补记”可说是包裹着成熟期散文多元可能的雏形。 实际上周作人不仅在古代笔记中找寻个人趣味与极耐咀嚼的清涩语感,更从鲁迅的早年杂记中获得了强化与肯定。他在辛丑日记中抄录了几则鲁迅早年札记,有意味的是他所选摘的文字无论在情调还是文字风格上都有一种神似:如晚香玉的形态、里低母斯的化学特性、鲈鱼饭的制作、茶的夷语来源、试烧酒法等,均文字极简而意韵悠长。这表明周作人在寻找散文语言的过程中曾转益多师,包括离他最近的兄长。 细辨这类“补记”,会发现它们的功能分别是追忆往事(77)、评点日记正文(78)、抄录与正文无关的材料、解释正文内容等,均与日记文体的原本内涵有所偏离。这正表明周作人在有意识地通过“补记”培养出一种清腴散淡的文字感觉。他已不再用记日记的单纯态度来对待日常写作,而是将它作为文学文本来有意经营。 不难发现,在这类与正文关系相当松散的独立补记中,周作人的写作态度更为自在,个人化趣味也能舒徐展露(79)。他的文字时而仿佛清新可诵的小品,时而又如絮语般讲述着余韵袅袅的奇闻轶事(80)。讲述者的形象虽未正面出现,但不难看出背后站着一位对乡间生活兴味盎然的越郡少年。后来郁达夫认定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81),从这一时期补记中不难看到周作人通过一种古雅的札记形式,凸显出自我个性鲜明的面影,正是现代散文着古裳展新姿的有效实验。 四、结语 面对周作人日记的史料功能与文学特质,研究中往往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而早年日记中叙述者以清新口吻与活泼心情来讲述一段精彩纷呈的少年生活,却使人很难对其间的文学性视而不见。 从周作人日记中颇引人注目的风景描写入手,会发现此类完全可视作散文小品的片断,一开始也许只是偶成的效果。如他这样描述首次院试入场的前夜:“天低欲雨,无星无月,色如墨染”(82),仅十二字的天象描写,仿佛正是对于考前因把握不大而产生的茫然、恐惧心理的极好暗示。而第一次童试落榜后,他形容这样一个雨夜:“夜大雨数阵,北风甚烈,雨点颇大,大似中夏光景。夜半小雨,梁宅园竹被风摩戛作声,颇搅人眠”(83),以错乱奇特的季节感受暗示落第后的烦乱心境。当他即将投入第二次童试的准备时,在十六岁生日当天,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清晨:“晨,越见瓦上雪厚寸许。窗前双木犀,一望皎洁如玉树临风。又见千万楼台,参差可爱,真可谓樨窗雪景也……少顷雪止,映书明甚,此古人之所以映雪读书也,越中俗谓开雪眼”(84)。 联系到日记主人这一时期的科举经历,他无法被取代的个人感受使其目睹独一无二的风景,而将此情此景搬至纸面的过程,则酝酿出主观色彩十分鲜明的景物描绘,制造出一种不明言心境却以风景图解心境的客观效果,可谓情景交融达到圆融无间的典型片断。 这些多年前积淀的观察与描写,数十年后往往稍作铺陈便演变成华彩章节。如1924年《故乡的野菜》中一段既清新又浓丽的描写: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 实际上这一段落却是对二十多年前日记中文言片断的白话翻写: 食草紫,杭呼金花菜。(85) 尝草紫。叶如商陆花,如蚕豆,农人种之以粪田。越人以咸菜卤瀹之,佳美可啖。三月则老,不可食矣。(86) 当周作人以白话为工具后,日记中的文学片断一经改写便使得原本语言和意境不乏贫血之虞的白话散文具备了“艺术之美”。作为现代美文理论提倡者与实践者的周作人,曾以日记形式进行着现代散文“前文本”的写作实践。尚未取得成功的诗歌写作,给予他提出文学观念“生活之艺术”的实践与审美的训练,同时也让他转投散文时,有可能在白话中“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的成分,酿造出“理想的国语”(87)。而浅近文言与有涩味的白话之间界限本不甚明晰的差异,使他无论在意境还是语言上都借力诗歌颇多。 但这样的积累不仅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更有赖于白话文风云际会时代的来临。因此我们在周作人的早年日记中,尚且看不到纯文学散文的成型篇章,而只是在一种极简风格的片断描写逐渐熟练之后,作者将十数字、数十字的片断扩充为几百字的成型段落。如辛丑二月对于游禹陵经历的描述(88),对行程记载甚详,视之为微型游记亦无不可。 总之,早年日记写作孕育着今后周作人散文的多元可能性,而日后散文的诸多特质也多在此时习作中能够找到源头。当我们发现一位14 岁少年面对一片“山环水绕”、“鸟语花香”的山岭幽景时,竟发出了想要“隐居”其间、“终老”于此的慨叹(89),我们会惊奇作者的早熟,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不过是少年人对先贤隐逸志向故作老成的模仿,而周作人思想中的避世隐逸脉络或许从中已可窥见源头。当然越到后来,周作人日记中的风景小品越加自然,如辛丑正月十六日对风景幽绝的东湖之行不仅记叙清晰流畅,在景物鉴赏中也不再出现扮演深沉的简单模仿,而是娴熟掌握了如何寓恬淡抒情于景色白描的手法。或许很多作者要到五四以后方才拿起白话美文之笔,但周作人却在约二十年前便以日记作为风景观察与写作训练,悄然却有效地进行着文章功力上进展迅捷的试验了。 注释: ①笔者曾撰《周作人科举经历考述》(《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期),探讨科举经历在周作人早年生平中的位置。 ②己亥十月二十六日日记,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本文所采用周作人日记材料均出自此本,以下简称《日记》。 ③庚子四月初八日,《日记》第134页。“南镇”即“禹穴”,“立石,署曰‘天南第一镇’,在香炉峰下。春初游人士女如云”,见范寅著、侯友兰等注:《〈越谚〉点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④庚子寒食日记,《日记》第121页。 ⑤戊戌四月初八日:“下午往游西湖左祠、岳坟二处”,《日记》第8页。 ⑥辛丑正月十六日:“武林有西子湖,而此名东湖”,《日记》第195页。 ⑦周作人戊戌四月初八游西湖,“杭俗以初八为大佛诞”,两年后(庚子四月初八日)他忆及那天“西湖放生者甚多,故武林士女倾城出游”,《日记》第134页。 ⑧如庚子三月初三日提到田叔禾《西湖游览志》、《西湖志余》(《日记》第120、121页),此后又在日记中又不止一次提及阅读二书。 ⑨己亥二月初三日“偕叔辈登舟往兰亭”,《日记》第42页。 ⑩周作人日记中曾记载庚子正月初一“大哥往开元寺数罗汉,名曰‘宝涯尊者’”,正月初五周作人“又往开元寺数阿罗汉,名‘光英尊者’”,《日记》第107、108页。 (11)庚子四月十七日,《日记》第138页。 (12)辛丑二月二十日,《日记》第211页。 (13)辛丑五月初九日,《日记》第237页。 (14)辛丑正月初九日,《日记》第192页。 (15)庚子五月二十六日,《日记》第146页。 (16)戊戌闰三月廿三日,《日记》第8页。 (17)己亥十月二十六日,《日记》第83页。 (18)甲辰日记:“三次之扫墓”,《日记》第400页。《越谚》中也有“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果盒谒墓”,名曰“拜坟岁”,《〈越谚〉点注》,第262页。 (19)(20)《〈越谚〉点注》,第262、266页。 (21)周作人1946年在老虎桥监狱中作《往昔三十首·东郭门》,忆及当年行程时有“水程五十里,春游正及辰。待得缓缓归,天色近黄昏”,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22)甲辰日记:“三次之扫墓”,《日记》第400页。 (23)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185页。 (24)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229页。 (25)周作人:《北平的春天》,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26)己亥正月十五日,《日记》第37-38页。 (27)庚子正月十四日,《日记》第110页。 (28)己亥三月初七日,《日记》第48页。 (29)己亥十月十六日,《日记》第78页。 (30)己亥正月十五日,《日记》第37页。 (31)己亥十月二十六日,补叙为己亥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加,《日记》第83页。 (32)据周作人晚年回忆:“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鲁迅的故家》,第223页。 (33)如庚子三月初九日:“余与三十叔作赞,祭文甚短,每首只十数句耳”,《日记》第122页。 (34)“伯撝仲翔诸人共作越城鄙夫扫墓竹枝词,惜诗未记录”,《鲁迅的故家》,第232页。 (35)己亥三月初三日,《日记》第47页。 (36)辛丑正月初十日,《日记》第192-193页。 (37)辛丑二月廿二日,《日记》第211-212页。 (38)己亥十月初二日,《日记》第72页。 (39)己亥十月十六日,《日记》第78页。 (40)辛丑年日记后附“柑酒听鹂笔记”,《日记》第268、285、289-293页。 (41)如己亥正月十二日周作人作《春雨记所见》,在眉批处他对此诗自评说“上六句庸,无甚意义,且多集凑,故易之”,《日记》第35页。 (42)辛丑二月十七日“迂道往戒珠寺一游”,《日记》第208页;作有《[菩萨蛮]辛丑清明游戒珠寺望黄琢山率赋》集句(见“柑酒听鹂笔记”),《日记》第289页。 (43)如辛丑正月周作人送别大哥后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而在此之前他先有《[菩萨蛮]送戛剑生往秣集句》,之后才写下这一唱和之作。 (44)《日记》第294-295页。 (45)庚子三月十七日,《日记》第126页。 (46)庚子七月廿二日,《日记》第157页。 (47)己亥十一月十二日,《日记》第88页。 (48)分别为己亥十月初九日、庚子三月廿四日、辛丑八月廿九日,见《日记》第76、128、252页。 (49)己亥十月初九日,《日记》第76页。 (50)周作人:《苦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451页。 (51)见庚子二月十五日日记,《日记》第124-125页。 (52)辛丑正月廿五日,《日记》第198-199页。 (53)周作人:《北平的春天》,《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142页。 (54)己亥正月十三日,《日记》第36页。 (55)这种思想上的旧痕即便在其赴南京读书后仍可寻到踪迹,如他认为孙君培咏鸦片集句“颇佳”(壬寅正月廿八日),《日记》第316页。 (56)《日记》第286页。 (57)壬寅三月廿二日日记后有“十九日作诗一章附此”,《日记》第330页。 (58)(59)周作人:《生活之艺术》,《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14、513页。 (60)周作人:《老虎桥杂诗补遗·吾家数典诗六首·其四》,《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55页。 (61)庚子三月初五日,《日记》第121页。 (62)庚子三月初九日周作人抄录过《鉴湖竹枝词》中的“露霜展谒先贤兆,诗学开科愧未传”,《日记》第122页。 (63)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甲编附记”,《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198页。 (64)辛丑二月二十日,《日记》第210-211页。 (65)《日记》第37页,“伯”字原文如此。 (66)己亥十月十八日,《日记》第79页。 (67)庚子三月十六日,《日记》第125-126页。以上三处画线均为笔者所加。 (68)己亥十月十八日,《日记》第79页。最初周作人在日记正文之外补充文字极少,自此日开始出现耐人寻味的补记内容。 (69)周作人:《国语文学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485页。 (70)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7页。 (71)周作人:《〈杂拌儿〉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456页。 (72)己亥十月二十六日,日记第82-83页。 (73)庚子三月十六日,《日记》第125-126页。 (74)此则日记连同部分补记被冠以“庚子扫墓日记”之题,收入《周作人散文全编》第1卷。 (75)如辛丑正月廿五日周作人送别鲁迅时“执手言别,中心黯然”的情境,他认为可用李白诗句“去影忽不见,踌躇日将曛”作为恰切形容,《日记》第197-198页。 (76)庚子三月初三日,《日记》第120-121页。 (77)如庚子三月廿四日、庚子四月初八日(《日记》第128、134页)对杭州往事的追忆。 (78)周作人往往于时隔多日对以前日记进行批注自评。如辛丑四月一日评点庚子四月十五日对于四野蛙声的描写“如画”、“回忆其景,尚出目前”(《日记》第137页);辛丑正月廿一日评点庚子四月廿八日有关大风的描写“回忆当时情景宛然”(《日记》第141页)。这样的练习与自评,使他的文字处在不断自我监督的进步过程中。 (79)如辛丑二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补录”道:“下午购得鲜吐銕一盂,瀹食之,味极似螺,不甚佳,予拣得活者数枚养于瓷盆中”,《日记》第205页,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趣。 (80)庚子三月十八日:“连日大雨,畦岭皆成泽国。土人以车戽水使干,而后以网乘之,多有得者,类皆鲚鲤之属也。十八日记”,《日记》第126页。 (81)郁达夫:《良友版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导言》,《郁达夫全集》第六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82)己亥十月初四日,《日记》第73-74页。 (83)己亥十一月十五日,《日记》第90页。 (84)己亥十二月初一日,《日记》第96页。 (85)戊戌二月廿八日,《日记》第5页。 (86)庚子二月三十日,《日记》第119-120页。 (87)周作人:《理想的国语》,《周作人散文全编》第4卷,第288-289页。 (88)辛丑二月初五日,《日记》第202-204页。 (89)己亥正月十五日:“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萝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其间。”《日记》第37-38页。标签:周作人论文; 风景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散文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