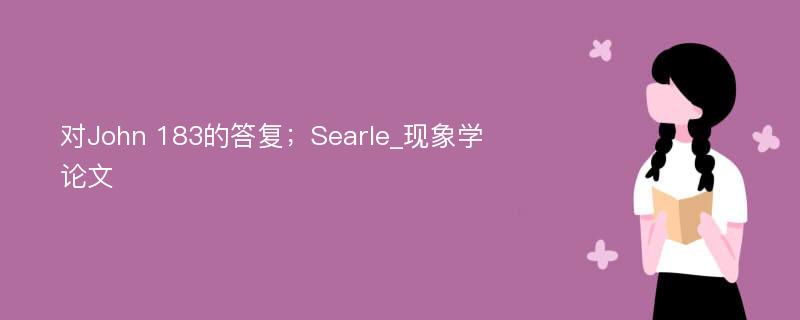
对约翰#183;塞尔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5)05~0020~12 既然我总是把塞尔对意向性和背景的说明看成是当代对这些主题最重要的和最圆满的说明,所以,我对海德格尔的许多解读是在回应这些主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塞尔的诸论证,以使我理解的海德格尔不是在对一个假想的对手提出异议。另外,尽管这对现象学的历史来说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如果塞尔的观点被证明是像胡塞尔的观点,那么,对我来说,这远不如他的观点是不是明确表达了海德格尔所反对的立场的最好版本更重要,因此,我会整理最好的海德格尔学者对它们的反对意见,然后看一下塞尔是否能够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成功的辩护。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论中,这是当前最新阶段的交流。 但在我能够进入使我们产生分歧的深层次问题之前,我必须澄清四个术语要点。 (1)对于我反驳塞尔对意向性说明的论证来说,用主体/客体术语或内在/外在术语陈述他的观点,从来都是不重要的。就我的目标而言,他的心灵/世界二分做得很好。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塞尔认为,所有的意向内容乃至使满足条件成为可能的背景都在心灵/大脑之中,因此,原则上,无论世界是否存在,都能够在梦里或缸里得以维持。如果这使塞尔不高兴地呼吁说,在缸中所保留的是一个自足自立(self-sufficient)的主体,那么,我就放弃这个术语,但事实依然是,他的观点听起来像胡塞尔的笛卡尔主义,而且,塞尔自己说:“许多哲学家试图运用像‘方法论的唯我主义’、‘超验的还原’,或者,只是‘缸中之脑’的幻想之类的概念,得到意向性,我与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① (2)同样,我对塞尔所说明的背景的异议并不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所运用的术语。在我到达伯克利不久,他就与我开始讨论意向性,而且,我很快发现,他的观点是:背景提供了使意向性成为可能的非意向条件,非常接近于海德格尔所谓的“最初熟悉的背景不是故意的,而是以不明显的方式存在的”②观点。1980年,还有1992年,我们联合举办了关于背景的讨论会,我发现这个讨论会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是,我越解读塞尔所说的背景,我就越不理解他的观点。 塞尔说的背景是由技能和能力,还有通常在一种情境中发生的某种准备构成的。我认为,至少有些对构成的背景做出回应的能力、技能和准备是身体的,而不是心理的,的确,塞尔在讨论如何获得技能时说,“重复实践能使身体接手,而使规则不再重要”③。然而,塞尔也想说,背景是心理的,在这里,“心理的”意指,“我的所有背景能力都‘在我的头部’”④。但既然头部和大脑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背景属于哪里。它是内心里的第一人称体验或身体中第三人称机制?我深知,塞尔“对‘心理的’和‘身体的’传统词汇不会感到满意”⑤。他具有的其他本体论词汇是什么呢?梅洛-庞蒂说,鲜活的肉身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身体的,而是“第三种存在”——“运动意向性”(motor intentionality)⑥,或者,他有时称之为“意向的组织”(tissue)。塞尔想说背景也是如此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尽管如果他这么想的话,我会很高兴。 (3)塞尔和我都同意,当人们在获得新技能的过程中遵守规则时,“重复实践能使身体接手,而使规则不再重要”⑦。但我不能接受塞尔的这种观点:当人们变得在行时,规则不再重要,而不是像辅助工具一样就没有用了。就拿他举的靠右开车的例子来说,我同意,如果我遵守“在右边开车”的规则来学习开车,那么,当我学习时,在我的行为中,这个规则就起到了直接原因的作用。我也同意,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能说,现在,这个规则在我的行为中正在起着间接原因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从前没有遵守这个规则,我现在就不是靠右开车。但似乎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当我的技能性行为仍然符合规则时,我不再是以初学者时的样子作为一个步骤来遵守规则。规则曾经一步一步地引导我的行为。在这么做时,它在我的大脑中产生一种结构。现在,正是这种结构,不再是规则本身,在支配我的行为。说我现在是“无意识地遵守规则”⑧,掩盖了这种重要的变化。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这意指我当前的行为,那么,说“我的行为是‘对规则敏感的’”⑨,似乎是一种误导。 因此,我同意,根据科学的断言,我的当前行为是由规则间接地引起的,而根据逻辑的断言,人们要理解的行为,就必须间接提到规则。(这说明了为什么,当要求说明我正在做什么时,我要求助于规则。)但是,在我当前开车时,我“无意识地遵守规则”,或者,我现在对规则是“敏感的”,这些肤浅的现象学的断言,似乎对我来说,或者完全是以误导的方式做出上面的真的断言,或者,只是显然为假。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塞尔既强调他不做现象学,然后又坚持运用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学术语。 (4)我的确说过,塞尔坚持认为,当我们看到一幢房子或听到富有意义的词语时,我们是在“解释”基本的资料。我承认,这是以一种令人误导的方式描述他的观点,而且,我赞同他的这种观点:我们应该以正常的日常方式使用“解释”,在这种方式中,“本义的解释行为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⑩。然而,令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是否需要解释资料,而是塞尔坚持认为,为了看到一个像房子那样的功能客体,我们必须为宇宙的某种物质赋予一种功能。正如他指出的那样: 重要的问题是看到,功能绝不是内在于任何现象的物理成分,而是由有意识的观察者和使用者从外部赋予的。(11) 本义的赋予行为和强迫也是相当少见的,而且,塞尔不可能以日常方式使用这些术语。因此,例如,塞尔坚持认为,为了听到富有意义的语言,我们必须把意向性强加给从人们嘴里发出的响声。这里,需要区分出几种可能的不同问题。对于神经科学来说,说明声波如何在大脑中得到处理,以使得它们对某些动作做出回应,肯定是一个合法的项目。正如塞尔所做的那样,有人也会质问,一连串声音的一种言语行为的逻辑要求是什么。然而,质问“我们具有的从人们嘴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噪音的体验,如何能够变成对言语行为的体验”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执迷不悟;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通常体验过从人们嘴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噪音,但我们却没有。当塞尔说“孩子……学习把从自己和其他人嘴里发出的声音看成是代表了或是有意义的某种东西”(12)时,这充其量是极大的误导,因为,尽管孩子的大脑是逐渐地有条理地处理从人们嘴里发出的响声,以使孩子听到有意义的声音,但是,孩子根本没有学习把这些噪音看成是有意义的声音,由于从孩子的观点来看,工作总是已经完成了。 当我得知,通常描述心理活动的那些术语,比如,“赋予”或“强迫”,被用来说明行家本人如何获得意向性时,我必须认为,塞尔既不是在做脑科学,也不是在做逻辑分析,而是在从事坏的现象学。但在他关于社会实在的著作中,塞尔为他的方法辩护。他说,他不仅质问而且回答逻辑问题,一定不是在做现象学,而且,补充说:“我将用第一人称意向性的词汇试图揭示社会实在的基本特征。”(13)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如果他不是在做现象学,为什么他使用第一人称词汇呢?确实正是这个词汇误导像我这样的某些人假设,既然强迫的活动不是有意识的,那就一定是无意识的。胡塞尔称如此假定的心理活动(即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无意识的)为“超验的”,而且,谈到了把资料本身“看成”是有意义的超验意识。这像是变戏法一样,把意义的赋予描述成第一人称的心理活动,但然后,取消这种心理影响。 现在,我们终于要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塞尔和我在三个基本问题上有意见分歧。(1)什么是意向状态?(2)什么类型的意向状态——命题的或非命题的——引起动作,并把这些动作视为行动?(3)塞尔是进行逻辑分析,还是在做现象学? (1)什么是意向状态?当我一开始写到意向性时,我断言,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把日常持续的应对解释为是对既不需要意识也不需要意向性的情境诱惑做出的回应。(14)塞尔向我指出,即使熟练应对可能会成功或失败,因而有满足条件,同样也一定是一种意向性。在我的早期论文中,尽管我应该有更好的理解,但我还是错过了这一要点,因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确认,他们是在研究一种更基本的意向性,但还是一种意向性。我感谢塞尔呼吁我注意到这种错误。(15) 塞尔认为,所有的意向状态一定有满足条件,我对他的这种最低限度的逻辑条件没有异议,但这证明,塞尔也维护强的实质性断言(substantive claim):这些满足条件一定是“心理表征”。这并不是术语“心理的”或“表征”问题,而是塞尔的这种有争议的断言:满足条件的内容一定是命题的。正如塞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使用的“表征”能够为用来说明表征的所有概念所取代,比如,这样的逻辑要求:行动有满足条件,而且,(我称之为现象学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有“命题内容。”(16)追随海德格尔关于行动的观点和梅洛-庞蒂关于知觉的观点,我坚持认为,满足条件涉及知觉,而且,行动在通常意义上不需要是命题的。(17) (2)什么类型的意向状态——命题的或非命题的——“来说明这些行动?”塞尔和我都同意这种逻辑的必要条件:对于身体动作是一种行动来说,它一定是由其满足条件引起的,在这里,这可能意味着,只是对成功运动的约束是敏感的。然而,对我来说,当塞尔补充说,对于一种意向状态说明了一种行动来说,表征行动的满足条件的命题内容一定伴随和引导适当的身体动作时,他似乎是在做现象学。塞尔看起来像是逻辑分析的东西,我看起来像是现象学,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引起动作。梅洛-庞蒂断言,在持续熟练应对时,人们受到偏离满意形态的紧张感的引导,因此,在人们适应了满意形态之后,他才会在回顾中意识到,接下来做什么。这种最终形态,在人们达到之前乃至之后,都不可能被以命题形式来表征。(18)这种弱逻辑条件,在塞尔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比如,海德格尔与梅-庞蒂)之间,没有争议;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的确对塞尔的强现象学的必要条件表示异议。 我们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没有断言,塞尔的说明是坏的现象学,反而现象学是,只有充满努力的、谨慎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比如,教哲学课或写哲学文章等,才不包括人们体验运动流程或只是寻找人们在世界中的方式这类熟练应对。因此,我同意塞尔的这种观点:做哲学是“意向的心理行为的一个范例”,但这并没有表明我的下列观点完全是“自我反驳”。这种观点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忙于塞尔所谓的心理行为。事实上,我认为,塞尔的现象学对我的观点是支持的。我的断言是,尽管我们通常从事我所谓的慎思的活动,但如此深思熟虑的活动不是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基本的方式。 正如塞尔在体育运动中所要弄清楚的那样,这个问题开始真相大白。在他对一位分数落后且不想失去注意力的疲倦的竞技型网球运动员的描述中,塞尔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描述:迫使去赢球是什么滋味。我承认,这样一个人是在战斗,很难达到某些特殊的目标。我为此接受塞尔的话语,在某类“严肃的竞技型活动”中,努力尝试是比赛最主要的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的体育活动都需要如此有压力,也不是所有的锦标赛都需要二选一。如果添·高威(Timothy Gallway)(我曾听过他的网球课)是那位教练的话,他会劝告塞尔的那位有压力的网球运动员放松下来,只是对情境做出回应,就像禅宗大师那样。(19) 塞尔如此深信,这位行动者总是在尝试,他举了我的拉里·伯德(Larry Bird)的报告的例子,他通常不知道他在球场上正在做什么,直到他在下列情况下把事情搞糟为止,这种情况是:“我们不能得到具体的满足条件;我们不能得到行动者正在试图(原文如此)要做的事情。”(20)塞尔因此认为,我的像禅宗那样流畅的描述恰好是不切题的,因为他得知这些描述,被认为是断言,尝试是无意识的。但我们的断言是,在这些情况下,行动者根本不是在尝试。此外,一位运动员花百分之多少的时间进行轻松自如的应对,花百分之多少的时间进行慎思的尝试,这并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存在着一种前语言的、非命题的应对,即,在体育运动中持续进入最佳时刻。在这些情况下,行动者不是正在有意识地尝试做任何事情,而且也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正在进行无意识的尝试。 海德格尔和我也希望断言,这种回应式的、非命题的持续应对,使塞尔很好地描述的那种慎思的、命题的尝试成为可能。但是,塞尔反对这种举措。他坚持认为,即使存在着我描述的这种回应式的应对,尝试也是更基本的,因为它在支配所有的技能性活动时起到了原因的作用,技能性活动最终完全是“意向行为”(21)。人们不可能只是对一种形态作出回应;人们一定是在他尝试要做的某种服务时做出回应。在许多行动类型的情况下,这是讲得通的。我通常不只是在熟练地活动我的舌头,而且我也在说出词语以使你理解我所说的话时,移动舌头,我通常为了赢球,或玩儿得更好,或得到训练,或其他原因,移动我的胳膊来击中网球。正如塞尔所断言的那样,在这些情况下,意向性总是提升到了技能的层次。 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另外一些活动,比如,当我们离开他人适当的距离而站立时,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这么做,还有,我们无意识地定位自己和寻找我们在世界中的方式,在这些方面,并不是为了达到特殊的目标,比如,赢得一场比赛或赢得一分。在这些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可表征的意向性,而是我们会说,一直存在着背景技能。塞尔无疑回应说,当我站得离我的对话者很远时,即使我在靠近对方时有一种无意识的紧张感,这也只是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正在尝试进行一次会话或实现某种别的目标。我会回答说,即使当我根本没有试图与他人有任何关系时,我通常也会站得离开他们适当的距离来,面对他们,等等。更一般地说,塞尔总是会说,我的所有活动,比如,我寻找我在世界中的方式——我的所有定位和应对实践,比如,我走路、穿衣、坐在椅子上、上下公交车,等等——都只是由我试图在世界中随意走动所引起的。但我不明白,根据这种空洞的断言,能得到什么。对我来说,似乎至少准确地说,如果我没有从事梅洛-庞蒂、海德格尔以及像杜威描述的其他人的那种前语言的、非命题的应对,那么,我就不可能执行任何我的有意识的慎思的活动。我坚持认为,海德格尔的背景不只是一种才能、能力或技能;它只是一种活动,活动的满足条件只是做感到适当的事情,没有详细阐述人们试图达到什么目标的任何命题内容。 总之,塞尔为成为一种行动的活动提出了逻辑的条件和现象学的条件。弱的逻辑条件是,活动是由行动者的满足条件引起的。强的现象学断言是,这种活动一定是由对这些条件的一种命题表征引起的。如果从极个别方面来说,在塞尔和我之间,意向行为表现的逻辑条件没有分歧。即使在我所举的例子中,网球运动员不知道最理想的形态是什么,他也会意识到,他是走向还是远离这种形态,因此,满足条件在指导他的行为时确实起到了原因的作用。如果这就是意向内容的原因作用表示的所有意思,那么,谁会否认这种必要条件呢?但我确实想否认塞尔的强的现象学的必要条件:支配一项行动的意向内容(即,对满足条件的表征)一定是心理的,也就是命题的。我是在断言,网球运动员在持续应对时,没有在命题意义上表征这种最理想的形态,虽然如此,这种最理想的形态也在指导他的身体动作。正如梅洛-庞蒂(我感谢他的这种描述)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种‘我认为’来说,一个运动或知觉力的系统,即我们的身体,是否是一个客体,这是一个经历过向着其平衡状态运动的意义的一种归类。”(22) 我不明白,为什么塞尔根据他的现象学的反诉(counter-claim)来反对这种现象学的断言,特别是,如果他只关注成为一种行动的活动的逻辑条件的话。我猜想,有两种理由让我觉得,他一定否认,存在着一种支配形态的行为方式,而且,这是他描述的如此好的在命题意义上故意受支配的那种当时更基本的行动。第一,我私下以为,他希望在他对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包括这样的断言:构成任何一种行动的动作都一定是由对行动的满足条件的一种命题表征引起的。第二,在塞尔的主体/客体本体论中,没有为身体意向性留下余地。 (3)塞尔是在进行逻辑分析还是在做现象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塞尔以他自己的强现象学立场的名义花费了很多努力对我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提出异议,但是,他的退路是他只进行逻辑分析。为了保护现象学不受塞尔的误导的和肤浅的指控,我需要表明,塞尔把他对现象学的说明偷换成他对逻辑说明的一部分,这种企图是不连贯的。 塞尔根据现象学的描述开始他的说明,这表明,行动的体验包括对行动者的意向和他的动作之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体验。他通过运用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工作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彭菲尔德断言,当他把一个电极放入患者的大脑里时,患者能举起胳膊,但当彭菲尔德“把电极拔出”之后,患者感觉到他不会动了。塞尔认为,所缺乏的是患者的努力感:正是他有意举起胳膊使他的胳膊举了起来的那种体验。塞尔总结说:“现在,这种具有现象的和逻辑属性的体验我称之为行动的体验……这种体验具有一种意向内容。”(23)行动体验具有这样的意向内容:适当的身体动作是由完成一种行动的意向所引起的。塞尔把这种意向称为行动中的意向,而且指出,在通常的日常行动中,“行动的体验只是行动中的意向”(24)。行动中的意向的意向内容、它的满足条件是,我通过履行行动中的这种意向引起了身体的这种动作。因此,塞尔说:“在行动的情况下,我的意向状态引起了我的身体的某种动作。”(25)对于成为一种行动的动作来说,这种动作一定是由一种行动中的意向引起的和不断地引导的。正如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意向性变成了自愿行动的基础,每个动作都是受这种连贯的意向性支配的。”(26) 已知上面的断言,我很自然地把行动中的一种意向认为是这样的体验:我的努力是由我的身体动作引起的。但塞尔说,我通过建议说意向状态或心理状态“是一回事”,歪曲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他明确地同意,在无意识行动的情况下,人们履行某种身体动作的意向能够致使他们完成这一动作,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意向。因此,他坚持认为,“表征……不是本体论的范畴,更不用说是现象学的范畴了,而是一种‘功能的’范畴’”(27)。 我现在认识到,塞尔坚持认为,当人们做出一种身体动作时,这通常是由人们的行为表现的体验引起的,因此,他能够在彭菲尔德让患者举胳膊的例子和使读者能理解成为一种行动的动作的逻辑条件的行动体验之间,运用现象学的对比。他的逻辑分析的结果是,对我正在尝试要做的事情的心理表征一定伴随和引起我的身体动作,不管我是否意识到我正在要做的事情。这种最低限度的逻辑要点是,一种行动的成功条件,一定在导致这种行动的成功条件时,起到一种原因的作用。因此,对于塞尔来说,行动中的意向一定在因果性的意义上是自指称的,而且,他写道,正如他做的那样,谈论因果性的自指称性,就是讨论“意向现象的逻辑结构”。因此,应该明确的是,我的行动体验的现象学只是一个必须被废弃的楔子、一个阶梯。塞尔坚持认为,在最后的分析中,这是意向内容本身,不是引起身体动作的行动体验。 我现在明白,我错误地以为,塞尔把因果力归属于心理条款,即行动体验,但我发现,塞尔对逻辑结构具有因果力的讨论是难以理解的。对于塞尔来说,“基本的因果关系概念是使某事发生的概念”(28)。这样,当我有举起我的胳膊的体验时,正是这种体验使我的胳膊举了起来。因此,只要我完成一次行动,甚至是一次无意识的行动,人们也会认为,一定有某种原因致使我产生了身体动作。的确,当塞尔说“正如我所做的那样,如果我相信,‘原因’确定了真实世界中的真实关系,那么,我们就是因果实在论者”(29)时,他就强调了这一点。而且,他继续说:“根据我的理由,行动……是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因果交易和意向交易。”(30)但是,一种抽象结构如何能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并使某种事情发生呢? 塞尔无疑会答复说,意向内容,即使只是一种逻辑结构,也能够通过被意识到在能够发挥原因作用的大脑状态中,起到原因的作用。(31)但即使我们同意塞尔的心/脑一元论,也没有解释当前的问题。塞尔认为,与意识体验不相符的大脑状态不可能有意向性。因此,即使我们同意一种形式的逻辑结构能够被意识到在大脑中,像在计算机中一样,因而具有因果力,也不能推出,一种意向结构。(比如,一种行动的满足条件)能够被意识到在脱离意识的大脑中。在没有意识的前提下,充其量所能认识到的是,了解意识意向状态的一种倾向性。正如塞尔所说的那样: 无意识的意向状态,例如,无意识的信念,真的只是大脑状态,但它们能够合法地被认为是心理状态,因为它们具有与大脑状态一样的神经结构,如果不以某种方式阻止的话,大脑状态是有意识的。它们没有意向性,只是作为大脑状态,但它们确实有潜在的意向性。(32) 这是对我们如何能谈到无意识信念的一种拟真的说明,但这种观点,当被推广到无意识地激发的行动时,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后果。行动中完全潜在的一种意向如何能够引起成为一种行动的身体动作呢?塞尔明白这个问题并回答说, 在我们当前的非二元论的实在概念中,没有一种感觉能够附属于这样的概念:体形(aspectual shape)能够既明确地被认为是体形,也还是完全无意识的。但既然具有体形的无意识意向状态是在无意识时存在的,并且,在无意识时引起了行为,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把什么样的感觉附加给这种无意识的概念呢?我认为,我们在下列完全适当的意义上能够附加给它:把无意识意向性归因于神经生理学,就是把能力归因于以一种有意识的形式陈述的原因。如果没有引起一件有意识的心理事件,那么,不管这种无意识的意向性是否能引起一种无意识的行动,这种观点都成立。(33) 但这是不可行的。假设在家里吃晚饭时,比尔“意外地”把一杯水泼在他弟弟鲍勃的大腿上,因为正如比尔的治疗医师后来告诉他的那样,他有一种惹怒鲍勃的无意识的愿望。这种行为说明不只要求潜在的信念,比如,比尔的长期信念是:鲍勃窃取了他的母爱,而且还要求实际发生的信念,比如,使鲍勃沮丧的愿望。这也要求塞尔所谓的一种“先验意向”——借助把水泼到他身上使他沮丧——和实际“支配”比尔的身体动作的一种“行动中的意向”,以便这些动作就是泼水的情况,而不是H[,2]O在周围运动。 按照塞尔的观点,无意识的大脑状态不可能决定体形,而且,我举的例子还要求,引起身体适当动作的行动中的意向有一种实际的、不只是潜在的体形。否则,人们不可能说,比尔正在做什么,或者,确实他正在做某一件事。这似乎是,因为构成一种行动的这些动作是由行动中的意向引起的,所以,行动中的意向不只是一种逻辑结构,它一定是一种心理状态。 在不久前发表在《国际哲学评论》(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的《既不是现象学的描述,也不是理性重构:答复德雷福斯》一文中,塞尔说到了他自己的工作:“我试图在不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前提下分析意向性。这项工作没有预料到的一种后果是,我的分析所揭示的因果结构和逻辑结构的结合超越了现象学分析的范围。现象学的传统,不管是胡塞尔的超验形式,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形式,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结果。”但是,对于现象学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回答关于塞尔必须超越逻辑分析的产生身体动作的因果性问题。因此,对我来说,看起来,在塞尔的逻辑分析中,现象学的作用,一定不只是纯粹的教学法。不管他是否喜欢它,塞尔似乎都致力于这样的观点:它是下列行动的动作的逻辑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行动是,人们把他们的意向状态感受为那种动作的原因。至少在行动的情况下,塞尔的最重要的洞见可能是,现象学不是一个肤浅的出发点,而是一个必要的终点;这种必要的逻辑分析导致了现象学。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30年来一起讨论和上课的原因所在。 思考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注意到,塞尔在行动的分析中,在考虑到因果性的重要性方面,超越了胡塞尔。但似乎对我来说,在这么做时,他只是成功地表明,试图通过把知觉与行动的可能性追溯到心灵,来说明知觉和行动,但知觉和行动的固有的意向性是注定要失败的。基本的物理世界和个体心灵的固有意向性的笛卡尔/胡塞尔的本体论恰好没有丰富到足以说明我们如何能够采取行动。我们只是不得不咬紧牙关支持身体意向性和作为第三种存在方式的在世存在。 最后,为了理解塞尔所说的关于我的观点,我必须假设,有两个塞尔,现象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其中每一个都持有一种有力的和一致的立场。现象学家接受的强有力的观点是,存在着被称为意向状态的真正的实体,而且,因为有行动,所以,这些状态一定是引起动作的有效原因,正如,因为在物理世界中存在着意义和功能,所以,人们必须把意义或功能强加于物质本身一样。 这种观点类似于胡塞尔的观点,而且,是对包括语言、尝试成功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在内的某些人类活动的真实描述。但是,作为对全人类的意向的行为表现和世界中所有有功能的东西的说明,它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使意向性的命题形式成为可能的更基本的意向性形式——持续应对,以及能使人们寻找在世界中的方式的一种行为举止——背景应对。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当对于塞尔的胡塞尔来说我扮演了海德格尔时,塞尔明白,他的现象学是无法得到辩护的。然后,他退回到较弱的立场并坚持认为,他只是在进行逻辑分析,因为现象学无论如何都是肤浅的。对于逻辑分析者来说,他指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实体,比如,行动、言语行为和像货币那样的社会实体,而且,每一个实体都有一种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包含着塞尔以巧妙而令人信服的细节所分析的意向内容。只要我批评现象学家,我就发现了逻辑分析家,但我很快找到了我悄然返回来不能接受的现象学断言。这就好像是,中性的逻辑分析家恳求这位分析家充实建立这种分析的因果断言,而且,塞尔无法阻止这种挑战。因此,他引入在因果性的意义上有效的心理表征,然后断言它们只需要逻辑结构。 我知道,塞尔并不欣赏恭维的话,但我发现,他的企图是,公平地对待逻辑的必要条件和现象学的必要条件(他的最显赫的成就),而且,我从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争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有对行动的说明,还有对胡塞尔缺乏的背景重要性的社会意义以及海德格尔意义的说明。而且,与海德格尔不同,他提出了对语言行为和更需要努力的意向状态的命题内容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他也列举了许多始终散见在他的书中的熟练应对现象的事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些,提出他自己对我们日常的非命题的在世存在(nonpropositional being-in-the-world)的看法,以便完善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但当然,这意味着,他必须采纳一种比笛卡尔的客体本身和他捍卫的自足自立的主体(缸中之脑里的心灵)更丰富的本体论。(34) 注释: ①John R.Searle,“Response:The Background of Intentionality and Action”,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eds) Ernest and Robert van Gulick,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1,p.291. ②Martin Heidegger,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Translated by Theodore Kisiel,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2,p.189. ③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0.塞尔在第5页指出:“意愿和意图只是其中的意向性形式之一……[p.50]……为保持明确的区分,我将在专业意义上利用‘意向性的’(Intentional)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 ④John Searle,“Response:The Background of Intentionality and Action”,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Ernest Lepore and Robert van Gulick,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1,p.291. ⑤Ibid. ⑥参见Sean D.Kelly,“Grasping at Straws:Motor Intentionalit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Skilled Behavior”,in Heidegger,Coping,and Cognitive Science: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Dreyfus,Volume 2,edited by Mark Wrathall and Jeff Malpas,Cambridge:The MIT Press,pp.161~177。 ⑦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p.150. ⑧Ibid.,p.87. ⑨Ibid. ⑩Ibid.,p.73. (11)John R.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p.14. (12)John R.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p.73. (13)Ibid.,p.5. (14)很久以前,我的确认为,塞尔正确地把我的观点称为僵尸观点,也就是,当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的事情时,他可能是在熟练地做事。我感谢塞尔说服我远离了这种立场。我现在明白,即使在换档踩离合器时,我也必须有一种最起码的感觉:事物像它们应该是的那样进展顺利。否则,我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如果事情开始出错,我的注意力会立即注意到这个问题。 (15)我高兴纠正的另一个错误是,我对自指称性和自我意识的混淆。我现在认识到,根据塞尔的观点,动物具有自指称性的意向状态,尽管这些意向状态肯定不是反思的。但是,我仍然不太理解,狗,尽管它们没有语言,但怎么也会具有含有命题内容的意向状态。如果人们坚持认为,狗的行动是由梅洛-庞蒂所描述的形态的意向性(gestalt intentionality)所导致的,那么,人们就能避免这种不可靠的陈述。 (16)John R.Searle,“Response:The Background of Intentionaltiy and Action”,p.295. (17)所有的行动都要求对它们的满足条件做出一种命题表征,为了对这种必要条件做出辩护,塞尔需要强意义的“命题内容”和弱意义的“命题内容”。这样的内容,为了说明慎思的行动,必须是抽象的,即非情境的(nonsituational),而为了说明全神贯注的应对,必须是具体的,即,索引式的。参见我的文章“The Primacy of Phenomenology over Logical Analysis”,Philosophical Topics,Vol.27,No.2,1999。从现在开始,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在强的意义上来使用“命题的”这一概念。 (18)参见我的文章“The Primacy of Phenomenology over Logical Analysis”。 (19)参见添·高威对竞争性的网球比赛的批评和他对禅宗网球运动员的心智状态的讨论。W.Timothy Gallwey,Inner Tennis:Playing the Game,New York:Random House,1976;也可参见Mihaly Gsikszentmilalyi,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 (20)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p.85.维特根斯坦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在《蓝皮书和褐皮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一书中说:“我故意举起其中一个稍重的哑铃,做出决定之后,我就竭尽全力举起它……一个人从这种事例中接受了他关于意愿的观念,关于意愿的语言,而且认为,它们一定适用于——如果不是以如此明显的方式——他能恰当地称之为意志的所有情况。”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The Blue and Brown Books,Oxford:Blackwell,p.150。 (21)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p.81. (22)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p.153. (23)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p.90. (24)Ibid.,p.91. (25)Ibid.,p.119. (26)John R.Searle,“Response:the Background of Intentionality and Action”,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eds.) Ernest and Robert van Guliek,Cambridge:Basil BIackwell,1991,p.293.尽管胡塞尔没有更多地说到行动,但似乎他的观点与塞尔的观点十分接近。根据凯文·穆里根(Kevin Mulligan)在《知觉》(“Perceptio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32)一文中的观点,胡塞尔“拒绝接受只是尝试开始和在动作之前的观点。更确切地说,尝试与动作同在并引起这种动作,即,通过下列事实有可能达到的一种成就,这种事实是:知觉与意愿是相互伴随和相互引导的”。参见Husserliana XXVIII,A§§13~16。我当然不想否认,有时情况就是这样。 (27)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p.74. (28)Ibid.,p.123. (29)Ibid.,p.120~121. (30)Ibid.,p.130. (31)参见John R.Searle,Mind,Language,and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98,Chapter 2。 (32)John R.Searle,“Consciousness,Explanatory Inversion,and Cognitive Scienc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Vol.13,No.4,1990,p.603,p.604. (33)Ibid.,p.634. (34)我已经到了允许我做出回应的空间极限,但幸运的是,塞尔提出的其余的大多数问题,通过我以前的学生们以我同意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关于塞尔仍然接受笛卡尔的内在与外在区分的一种感觉,参见大卫·卡布恩(David Cerbone)在第一卷中的文章。关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实在性问题,参见Charles Spinosa,“Heidegger on Living Gods”,in Heidegger,Coping,and Cognitive Science: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Dreyfus,Volume 2,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0,pp.209~228。关于背景不是以命题的(乃至概念的)术语可表征的一种重要的感觉,参见Sean D.Kelly,“Grasping at Straws:Motor Intentionalit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Skilled Behavior”,in Heidegger,Coping,and Cognitive Science: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Dreyfus,Volume 2,pp.161~177。至于我对物理学中的实在论的观点和它如何与关于实在的无因果说明的实在论相融合,参见Hubert L.Dreyfus and Charles Spinosa,“Coping with Things-in-Themselves”,Inquiry,Vol.42,1999,pp.49~78。指出塞尔关于大脑现象只是心理现象的断言所引发的那些问题,参见Corbin Collins,“Searle on Consciousness and Du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Vol.5,No.1,1997,p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