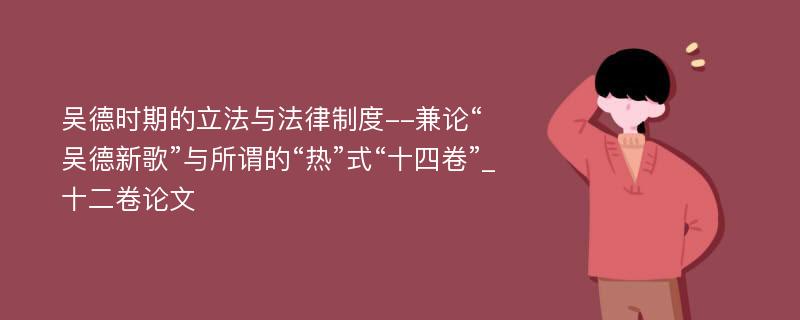
武德时期的立法与法律体系——说“武德新格”及所谓“又《式》十四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德论文,法律体系论文,时期论文,四卷论文,武德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武德年间立法,最为基本的史料,自然是《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和《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参与立法之人,所定法律内容及各次立法时间上小有差异,但在大事节目上是基本相同的。在此姑将《唐会要》所载列出以见其要: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诏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遂制为五十三条。务从宽简,取便于时,其年十一月四日颁下。仍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门郎中沈叔安、内史舍人崔善为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内史令萧瑀、礼部尚书李纲、国子博士丁孝乌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诏颁于天下,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 这段记载年月日分明,当自《实录》等较为原始的记载摘录而来,说明的则是唐高祖李渊禅隋登位以后的两次重要立法:一是武德元年(618)损益开皇《律》、《令》而制行“五十三条”,这显然是一份包括了五十三个条款的条制,故《旧志》述之为“五十三条格”,《新志》述为“新格五十三条”,可见唐初仍沿袭了北魏以来称敕例或条制为“格”的习惯①;二是五十三条格施用后,又诏裴寂等“更撰定《律》、《令》”②,具体则是以开皇《律》、《令》为其蓝本,又“正五十三条”来展开的,至武德七年告成颁行,而并无同时颁行《格》、《式》之事③。所谓“正五十三条”,意即新《律》、《令》的制定,是把五十三条格从条制“正”为《律》文,又据此调整了开皇《律》、《令》的其他相关内容。故《旧志》载此为“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④,其意与《唐会要》所述相同而更加明晰,特别是明确了五十三条格实际上是刑事条法的性质。 据此则武德时期的立法,先是武德元年制定了性质类于东魏《麟趾格》的五十三条新格,行至武德七年(624)本朝新《律》、《令》修订完毕颁于天下,此格内容亦像当年《麟趾格》那样被采入了新《律》而自然停废。由此看来,除非武德七年以后另有不见于史载的集中立法之事,整个武德时期实际上从未形成过《律》、《令》、《格》、《式》并行之制,而只是在武德元年至七年间出现过“五十三条格”部分替代隋法而行的局面。也就是说,武德七年最终确定的法律形式,实际上只有《律》、《令》而无《格》、《式》,这在关于当时立法的记载中本是十分清楚,无庸置疑的⑤。 而其之所以成了问题,首先是因为《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史部刑法类著录了“《武德律》十二卷,又《式》十四卷,《令》三十一卷”。这条著录意味着武德七年曾与《律》、《令》同时制订和颁行了武德《式》十四卷,南宋王应麟编纂《玉海》时,即注意到这条记载,遂在概括武德立法时标出了“律令格式”之目⑥。直到最近,也还有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唐代有《武德式》⑦,此外又有学者将之联系《隋书》提到“律令格式”之文和两《唐书》、《唐会要》中的某些记载,认为武德已承隋而有《律》、《令》、《格》、《式》并行之制⑧。但隋代有无这四部法书并行之制,本就不能直接说明武德时期也是如此。更何况,《隋书》中提到“律令格式”的几处记载,其实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无论开皇还是大业年间,都只有灵活而笼统地以“格”、“式”等词来指称的敕例或条制,却没有编纂过与《律》、《令》并行的《格》、《式》法书⑨。这也就无法再因武德诸制多承隋代而说其已《律》、《令》、《格》、《式》并行了。若再仔细梳理和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德时期的“又《式》十四卷”,乃是一条同期文献仅此一说的孤证⑩,而学者用来证明武德时期已有《格》、《式》的另外一些记载,则要么是原文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要么是今人在理解上存在着问题,不仅不能说明武德七年以后还编纂过“新格”,且亦难以构成“又《式》十四卷”是否存在的佐证。 以下即摭拾有关记载,加以辨析和梳理,以明武德立法及当时尚未形成《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相关史实。 一 武德立法与“五十三条格”的相关问题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载五十三条格颁后: 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 这条记载中的“丽以五十三条”,同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史部刑法类著录武德“《令》三十一卷”的原注,述为“以五十三条附新《律》,余无增改”。两处所述“附”、“丽”,意思都较为含混,似乎五十三条格未被修入新《律》,而是附丽于《律》而行(11)。然则武德七年以来出现的,就会是《律》、《令》与五十三条格和《艺文志》著录的“又《式》十四卷”并行的局面了。不过这样解释显然极不妥当,因为其毫无道理地否定了上面所说《唐会要》和《旧志》关于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的记载。特别是《唐会要》载武德七年诏颁新《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这段文字,实际上不仅体现了《旧志》述当时“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的史源所在;而且也反映了《新志》所述“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一句的史源所在,其显然不过是对《唐会要》或其所据《高祖实录》中“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这一句的改写。至于《艺文志》说当时“以五十三条附新《律》”,更可说是对改写的改写。而改写显然是不能用来否定史源的,故两处所用“丽”字和“附”字都极成问题而不足训,武德七年以来肯定已不再施行五十三条格,也就谈不上有《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了。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云:武德元年五月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六月甲戌,“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十一月乙巳,“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根据这些记载,在武德元年五月壬申“修《律》、《令》”与十一月乙巳“颁五十三条格”之间,又制行过另一个“新格”。给人的印象是:五十三条格固然已随武德七年新《律》的颁行而停废,但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未被废止的《格》。但这个印象还是经不起推敲的,上引文述“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之事,当即《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下列记载之所指: 高祖初入关,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 《旧志》亦载此事,但把“初入关”改成了“既平京城”(12)。两处所谓的“余并蠲除之”,说的也就是上引《旧纪》文中的“废隋大业《律》、《令》”;同时又说明十二条约法中“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等规定,也是像诸处所载五十三条格的制订那样,是“损益”隋《律》、《令》而成。由此可断:《旧纪》所载武德元年六月甲戌颁行的“新格”,其实就是约法十二条,由于其同样是一份条制,故亦可称之为“格”;其既损益和取代了隋代《律》、《令》,故颁行之日自须明令废除正在行用的大业《律》、《令》。而其后颁行的五十三条格,则必然是为解决约法十二条内容过简不敷治理之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增益而成。故其实际上是继十二条而再次“约法”,上引《旧纪》文述其“约法缓刑”,正包含了这层意思。《新唐书·刑法志》曰: 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用刑。(13) 这里概括的,便是五十三条格的内容,但其显然不会只有官吏犯罪不赦和用刑日期的规定,而是必然包括了以往约法十二条中“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等规定,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武德元年的立法进程,大体就是高祖入关以后先约法十二条,登位以后再在此基础上制行五十三条格,再开始正面修订本朝的新《律》、《令》。至于《旧纪》所载武德元年五月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修《律》、《令》”,指的实际上是高祖入关以后约法十二条之事,因为从约法十二条到再定五十三条格,都是损益隋《律》、《令》而成,也都可以视为修订本朝新《律》、《令》的开始(14)。而《旧纪》之所以会把“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放在高祖登位以后的武德元年六月甲戌,一种可能是入关之初只是明确废除了隋法而只作泛泛之约,而内容较为精确的十二条“新格”确是在此时定讫颁行的;另一种可能则是《高祖实录》系年已经淆乱,当时史事在贞观初姚思廉至长寿中牛凤及再到长安中刘知幾、吴兢以来的几次《国史》修撰中,其系年已有所不同的缘故(15)。但尽管如此,武德元年这三次立法的基本内容和先后次序,大体上仍是清楚的。 对于“五十三条格”的行用来说,还有一件事情堪值注意。《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政事·平乱上》收录的武德四年《平王世充赦》有曰: 可大赦天下,自武德四年七月十二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发露、未发露,悉从原放。自武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亡官失爵者,量听叙用。天下民庶给复一年,其陕鼎虢等六州供转输之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给复三年。身死王事,量加褒赠。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法。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武德四年》七月丁卯记事节引其文,其“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法”一句则被改写为“律令格式,且用开皇制”。有些学者是以此来证明隋文帝时已有《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其说妥否别为一问题,因为隋及唐初人所说的“律令格式”,往往只是对各种法律的一种泛称,以此来笼统地指称《律》、《令》及与之并行的各种敕例或条制,是很难证明当时已制行了《律》、《令》、《格》、《式》这四种法律形式的(16)。不过无论如何,这条记载表明的主要史实,是武德四年七月以后,前面所述高祖入关“约法十二条”以来“并蠲除”隋法的局面已被改变。也就是说,此前“五十三条格”实际上完全取代了隋法,而此后隋开皇所行之法至少已部分恢复了效力,直至武德七年新《律》、《令》推出以前,五十三条格实际上已与“开皇旧制”相辅而行。这是切关武德时期法制局面,特别是“五十三条格”效力和地位变迁的一件大事,在此基础上,武德七年颁行的新《律》、《令》之所以要取本开皇《律》、《令》又采纳“五十三条格”而成,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 武德“《式》十四卷”之不存在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辨析,非惟武德七年所颁无《格》的事实可以确定无疑,武德元年以来立法之要亦已可明。由此再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德《律》、《令》外尚有“又《式》十四卷”一句,更可见这条孤证几乎与当时立法的所有史实相悖。以下谨举四点以见其断然不能成立之况: 一是诸处皆载武德七年颁行的新《律》、《令》,是取开皇《律》、《令》为准,又据五十三条格而制定的。这方面说得相对比较准确的,当首推《唐六典》卷六《刑部》原注: 皇朝武德中,命裴寂、殷开山等定《律》、《令》,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唯三流皆加一千里,居作三年、二年半、二年,皆为一年,以此为异。又除苛细五十三条。 这段文字也为《新志》述武德《律》、《令》所据,其中只列举了武德《律》、《令》在“刑名”上与开皇《律》、《令》的不同,但亦可以想见刑名以外的其他变化还有不少。同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和“以此为异”之语,亦体现了变化幅度的有限。因此,诸处所谓“余无所改”,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武德《律》、《令》未对隋代《律》、《令》作全面调整,恐仍是无可置疑的史实(17)。而若当时确实创制了与之并行的《式》十四卷,那就必然会全面涉及《律》、《令》与《式》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内容安排、主从定位和文字表述,也就势不能不对开皇《律》、《令》进行大幅度修改了。然则史官们言之凿凿的“余无所改”等语,也就成了全然不顾史实的荒谬表述了。应当说,在这件事情上显得荒谬的,不是武德《律》、《令》并未大变的史实,而是竟出现了武德七年存在着“又《式》十四卷”的记载。 二是诸处皆载五十三条格的规定被修入了新《律》,前已辨其内容被修入而非附《律》而行,亦应是确凿的史实。不过“入于新《律》”之类的表述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五十三条格的内容显然远较约法十二条细致,上引《唐六典》卷六《刑部》原注甚至称之为“除苛细五十三条”;《新唐书·刑法志》则述其中包括了官吏犯贪赇等罪不赦和正月、五月、九月及断屠日不得用刑的限制,故可推知其不仅关系到《律》,亦必关系到了《令》的制订。其显例如《唐律疏议》卷三○《断狱篇》“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条疏议曰: 依《狱官令》:“从春分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闰者,《令》文但云正月、五月、九月断屠,即有闰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决死刑。 这条疏议十分清楚地表明,正月、五月、九月不得用刑的规定,后来不仅其大意被修入了《律》,其具体规定亦被修入了《狱官令》。因此,较之“入于新《律》”更为准确的表述,是武德七年已把五十三条格修入了新《律》、《令》。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表明,武德君臣实际上并无意在《律》、《令》之外,另再制行与之并行的《格》、《式》法书,“又《式》十四卷”在当时的立法规划中肯定并不存在。 三是武德七年制行新《律》、《令》,要在以此纠正隋法之弊,而隋法之弊,本不在《律》、《令》而在敕例条制的横行和大幅度架空了《律》、《令》的规定(18)。《旧唐书·刑法志》载武德七年颁行新《律》、《令》诏,虽为节文而此要愈显(19)。其中指斥隋法之况并称本朝立法之旨有云: 有隋之世,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深浅;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釐革,卒以无成……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 所谓隋代“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说的正是当时《律》、《令》既定而仍以敕例、条制屡加改作;“品式章程,罕能甄备”,亦主要是说敕例、条制横行,却全无约束而多“差遗”之况;“微文曲致”以下,则是说《律》、《令》成为具文而敕例、条制横行,势必使司法过程失去定准,从而陷入法愈繁而犯愈众的困境。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诏文用“斟酌繁省,取舍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来概括本朝颁行新法的宗旨,显然是要通过制定和颁行新《律》、《令》来抑制敕例、条制的横行,此即其明示“矫正差遗”所务须遵循的“体要”(20)。如果这样解读并无大误的话,那么新《律》、《令》的制订和颁行,也就必然会是武德七年立法的惟一中心;因为当时已认定这才是彻底纠正隋代“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局面的“体要”,而不是要为此而另行制行《格》、《式》之类的法书与《律》、《令》并行。当时新《律》、《令》之所以未对开皇《律》、《令》作重大修改即予颁行,其行用七年的五十三条格之所以要修入新《律》、《令》而随其颁行自然停废,也正是贯彻了这个宗旨。这就是说,武德七年颁行新《律》、《令》诏实际上已经表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同时颁行“又《式》十四卷”。 四是武德七年前后被称为“式”的敕例或条制仍然不少,说明当时“式”还不是特定法律的专有名词(21)。这里无妨来剖析其中典型的一例:《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九年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诏曰: 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依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此诏显然是要求有司制定一份关于僧尼、道人及寺、观管理的单行条制,并且称之为“条式”,从而反映当时“式”作为指称还处于灵活不定的状态。同时,诏文所述“违制之事,悉宜停断”,意谓违反这份“条式”也就是“违制”,适用于《律》中的“被制书施行有违”等条。这不仅再次证明“条式”在当时同于条制或制敕,亦透露了当时《律》中尚无“违《式》”的规定(22),从而反映了武德七年确未颁行“又《式》十四卷”的史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限制和管理佛道的规定,自北魏孝文帝推出“僧制四十七条”直至隋代以来,皆是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加以施用的(23)。武德九年制此条式,便取鉴了以往的这类规定。《续高僧传》卷二六《习禅篇六·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载辅公祏反于丹阳之后的一段史事: 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 此事应发生在武德七年四月新《律》、《令》颁行以后(24),而当时定制所依的“关东旧格”,也就是武德四年平定关东以后下达的一份限制当地寺僧数量的条制。《续高僧传》卷三一《护法下·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载有此事: 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留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 武德七年便是把这个原本行于关东地区每州限置一寺三十僧的规定,推行到了辅公祏作乱的江表地区,而上面所引的武德九年五月诏,则又将之推广到了全国寺观僧道的管理。从这个“关东旧格”效力从局部地区逐步推广至全国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德七年四月庚子新《律》、《令》颁行前后,实际上都未出现过本应统一规定寺观僧道管理事宜的《格》和《式》。直至贞观十一年定《格》,永徽二年(651)以来又以《祠部格》、《祠部式》来统一规范寺观僧道以前(25),朝廷在这方面的有关规定,除散见于《律》、《令》者外,一直都是像北魏孝文帝“僧制四十七条”和隋代以来的相关规定那样,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陆续推出施用的,且其称“格”称“式”仍无定准之可言。这也就彻底否定了武德《律》、《令》之外存在着“又《式》十四卷”的可能。 三 武德时期尚无《律》、《令》、《格》、《式》并行之制 据上所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武德“又《式》十四卷”,可以说是必无其事,必无此书。这应当就是现存唐代记载中绝无此《式》存在的任何踪影的原因,否则的话,武德创《式》十四卷对于当时法制来说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史官们又岂能对此置若罔闻,全不在文献中留其痕迹?故在《新唐书·艺文志》何以在武德《律》、《令》外出现了“又《式》十四卷”这一问题上,有可能是其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这条衍文,更有可能是《新志》在修撰之时已经发生了错误。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的著录,本来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前引滋贺秀三先生之文,即以其中著录的贞观“《留司格》一卷”和“《式》三十三卷”本不存在为例,指出了《新志》常有并未真见其书,而是仅据记载应有之书即加著录的现象。这种类于后世“《补经籍(艺文)志》”的做法,在帮助今人了解一时期著作之况时是有其意义的,却无法说明某个时间断限实际存在之书的状况,同时又极易因为相关记载本身的错误,或对这类记载理解的错误而发生“无中生有”的问题。在武德是否有“又《式》十四卷”的问题上,今存唐代立法史料中有可能被人视为其佐证的惟有两条记载: 一条是《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贞观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韩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并无为诸司寻检《格》、《式》之文。比年诸司,每有与夺,悉出检头,下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轻重。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讹弊日深,事须改正。”敕旨:“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准旧例录在官厅壁。左、右丞勾当,事毕日闻奏。其所诸司于刑部检事,待本司写格令等了日,停。”(26) 这条贞观二年(628)的记载说到了《律》、《令》和《格》、《式》,粗心者或亦以此来说明武德时期已《律》、《令》、《格》、《式》并行,且诸司皆按“旧例”将其常用条文书于厅壁,而未注意到其本是贞元二年(786)之事,“观”字当作“元”字才是。这不仅是因为这条记载在《唐会要》此目之下排在开元十四年(755)和宝历二年(826)之间;也不仅是因为其中提到了“文明敕”,而此敕即为《唐会要》此目前文所载的“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更是因为这个“韩洄”是在德宗贞元二年正月才由京兆尹转刑部侍郎的(27)。故其所证明的,只能是贞元以前的状况。 另一条是《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对仪凤年间高宗说《法例》宜废的下列记载: 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便。因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计此因循,非适今日,速宜改辙,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废不用。 这里高宗既说《律》、《令》、《格》、《式》“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又说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参详裁定而成,遂有学者以此为高祖、太宗时已有《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证据。但在前面对武德“五十三条格”及其是否定《式》已作讨论的基础上,高宗说的“武德之际,贞观已来”在时段上本就涵盖了高祖、太宗至高宗永徽立法的状况,其语是否即可理解为武德已“创制”《格》、《式》与《律》、《令》并行,答案显然应当是否定的。更何况,唐人对《律》、《令》、《格》、《式》由来的叙述,有时甚至还可将之上溯至汉。如《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开成元年(836)三月刑部奏事有曰: 伏以《律》、《令》、《格》、《式》,著自汉初,其后经历代增修,皇朝贞观、开元又重删定,理例精详,难议刊改。 所述“《律》、《令》、《格》、《式》,著自汉初”,大体是据汉初萧何定《九章律》而言,从汉代以来《令》补充和修正《律》,《格》、《式》则在补充或修正《律》、《令》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史实看,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问题。故高宗所谓《律》、《令》、《格》、《式》“非朕庸虚所能创制”本身就表明当时公认其当高宗所创,否则此语岂非可怪;故其继云“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所定,从发生学角度和上面所析当时立法史料提供的情形来看,亦当合理地解释为其中若干为武德或贞观以来所定,而不能一一指认这四部法书的每一部都定于武德以来。 因此,尽管今天很难判断《新志》著录武德“又《式》十四卷”时是否参考了这两条记载,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记载根本无法说明武德制定了《式》,更谈不上其卷数篇帙的多少,也就无法解释《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何以著录武德“又《式》十四卷”的问题,无法改变这一著录乃是一条孤证的性质。至于其是否就是一条衍文,或《新志》作者是否另有今已不见的其他记载为据,自然还可以继续加以研究,但有一点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在今仍信从《新志》著录,认为武德确有“又《式》十四卷”的学者那里,其看法多少都是与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那种认为隋代已有《律》、《令》、《格》、《式》并行之制,而武德则完全继承了此制的先入之见(28)。只要秉承这一歧见,自然就不会再去怀疑《艺文志》著录的“又《式》十四卷”,或将之视为一条孤证,同时也不免会影响其在史料出现种种歧义而需要作出判断之时的倾向。笔者相信,在重新考虑隋代有无《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前提下,只要仔细审视开皇、大业和武德时期的立法史料和立法进程,当时实际上还未形成这种法律体系的史实是不难得到澄清的。 二是武德元年以来五十三条格的制行,毕竟还是构成了当时已继东魏、北齐《麟趾格》、《权格》而再次出现了《格》这样的法书或法律形式的事实,证明了武德时期除制行《律》、《令》之外还制行了《格》的事实。不可否认,这样的事实多少也使“又《式》十四卷”的存在,看起来不是显得那么突兀可怪或出人意料了。只是,对认识武德时期的法律体系来说,在肯定这样的事实时,绝对不能因此而忽略武德七年四月庚子五十三条格已被修入《律》、《令》并已随其颁行而自然停废,以及武德任何时期都未出现过《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事实。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在看到这后一个事实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当时制行五十三条格这一事实背后的历史内涵,特别是其上承东魏、北齐《麟趾格》而下启贞观定《格》之举,而在北朝后期至唐初立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事情很清楚,制行五十三条格的事实,虽然无法证明武德时期存在过《律》、《令》、《格》、《式》并行之制,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或取鉴了北朝后期的相关做法,从而再现了以《格》来删定和归置隋代横行于《律》、《令》之外的大量敕例条制的努力。前已指出,五十三条格的前身是“约法十二条”,且其同样是被称为“新格”的。唐高祖李渊即位前后相继推出而内容累加的这两份“格”,针对的都是隋的苛法;而隋法之苛,又完全是通过《律》、《令》之外纷至叠出的敕例、条制而体现出来的。后来颁行的武德《律》、《令》之所以基本沿袭了开皇《律》、《令》而只作了局部调整,恰好证明了当时立法要在以之清除隋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敕例、条制的重心所在。因而约法十二条和五十三条格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固然也是要以新朝制定的若干新规定来取代隋的《律》、《令》,更重要的却是要以之取代隋代横行于《律》、《令》之外的各种内容苛暴的敕例或条制。武德四年平王世充赦令明定五十三条格与开皇《律》、《令》相辅而行之事,就十分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唐高祖李渊入关之后相继推出十二条“新格”和五十三条格,同时又开始制定本朝新《律》、《令》时,显然不是简单地取鉴汉高帝刘邦约法三章的故智,而是在正面处理北朝后期以来《律》、《令》与各种敕例、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先后约法之所以皆称为“格”,也必是由于北朝后期至隋以来“格”或“格式”的指称习惯薰染所致;而其约法从多达十二条再到五十三条的事实,又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麟趾格》、《大统式》等东、西魏以来出现的新法律形式对之的影响。 因此,尽管武德七年最终仍以五十三条格修入《律》、《令》的方式,继隋以后再次舍弃了北齐和北周以《格》、《式》来删定和归置各种敕例、条制的做法,以此强调了《律》《令》作为基本法无可取代的地位;但十二条新格和五十三条格的制订施用,却还是体现了武德初年以“格”来删定和约束各种敕例、条制的再次尝试和努力,反映了当时对北朝后期至隋代立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证明了《格》、《式》这类新的法律形式,确可以在处理《律》、《令》与各种敕例、条制的关系,删定和约束各种必然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敕例、条制时发挥重要而灵活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武德元年至七年十二条和五十三条格的相继制订施用,特别是五十三条格曾与开皇《律》、《令》相辅而行的经历,为太宗贞观年间的立法提供了弥足重视的前例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发挥的创制空间。这就连接了从东魏《麟趾格》、西魏《大统式》到北齐制订《权令》、《权格》和北周编纂《刑书要制》,到隋代“格”、“式”在整套法律体系中愈受重视,直至唐太宗、高宗相继制订《格》、《式》的演化史;并在北朝后期以来“格”、“式”由泛指某些重要法令,再到隋代“格式”常与《律》、《令》相提并论,直至初唐以后特指与《律》、《令》并行互辅的《格》、《式》这两种法律形式的发展链条中,构成了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楼劲:《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②《唐会要》述命裴寂等人及再命萧瑀等人修订新《律》、《令》,显然都在武德元年。《旧志》述武德立法通篇不出具体年月。《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五十三条格颁行在武德元年十一月乙巳,新《律》、《令》颁行在武德七年四月庚子,虽与《唐会要》时间稍异而仍同在武德元年。但《新志》述“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述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则在武德四年(621)。《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未载武德元年以来制行五十三条格及修《律》、《令》之事,而只记载了武德七年四月庚子“大赦,颁新《律》、《令》”之事。《新志》与《旧唐书》及《唐会要》所载的这些差异,当是《高祖实录》经太宗以来修改,其中与刘文静相关史事包括其主持当时立法的过程已面目皆非,遂致后来几次修撰的《国史》,在武德二年(619)九月刘文静被诛以前史事撰作上并未按《高祖实录》所存时序来系年的结果。对此,当然还可再据《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处所载加以梳理和辨析,但其既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此处自不宜再赘。 ③《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唐历次立法,不像其他记载那样往往只书《律》或《律》、《令》,而是把《格》、《式》也一一记明的,故其记武德七年颁法而不及《格》、《式》,记贞观十一年(637)颁法有《格》而无《式》,应当都不是失载而是史实本来如此。 ④《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所载与同。 ⑤关于武德立法,《旧唐书》卷八○《韩瑷传》载其父仲良“武德初为大理少卿,受诏与郎楚之等掌定《律》、《令》……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时以为便”。同书卷八一《刘祥道传》载其父刘林甫,高祖时“诏与中书令萧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议》万余言”。同书卷一八九下《儒学郎余令传》载其祖楚之,“武德初为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诸处皆只提《律》、《令》而已。 ⑥《玉海》卷六六《诏令·律令下》。《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刑法类亦著录了“《唐武德式》十四卷”,当是照袭《新志》之故。 ⑦如侯雯《唐代格、式的编纂》(《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认为:“《武德式》颁布的时间与《武德律》、《令》颁布的时间一致,由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撰定。”王立民《唐律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四章《唐律与令格式》二《唐律令格式的各自特点》亦说:“唐代先后颁行过武德式、贞观式、永徽式、垂拱式、神龙式、开元格式律令事类等。”李玉生《唐代法律形式综论》(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法律史论丛》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也认为武德式是与律、令一起完成的。 ⑧如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文史》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表列唐代编制的重要法典,前两种依次为武德七年三月裴寂等制定的“武德律、令、式”和武德九年(626)六月刘文静等制定的“武德新格”。这显然是说武德时期已经出现了《律》、《令》、《格》、《式》并行之制,但刘文静被诛于武德二年九月,武德九年六月适值玄武门之变,其时当然没有制定和颁行过“新格”。故后来遂有庄昭《〈武德新格〉并非制作于武德九年》之文(《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认为这个“武德新格”指的或者就是五十三条新格。这似乎表明杨先生当年所据乃是一张讹“元”为“九”的资料卡片,故其后来《唐律初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收此文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其中所列唐代编制的重要法典表上,已把“武德新格”放到了第一栏,制定年代则已改为武德元年十一月,意即此为“新格五十三条”。不过此表仍列有“武德式”,说明杨先生至此仍倾向于武德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了《律》、《令》、《格》、《式》并行之制,这应当是与法史学界长期都认为隋代已“《律》、《令》、《格》、《式》并行”相关的。《唐律初探》收录的《唐律内容评述》一文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唐代的成文法典与隋代相同,分为律、令、格、式四类。”后来的《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隋唐》第六章《唐朝的立法》第三节《唐朝的法律体系及其渊源》一《唐朝的法律体系》,以及最近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第二章《唐代武德到贞观律令的制度》第一节《武德律令格式的编纂》中,都还在因循此说。 ⑨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⑩除那些陈陈相因的目录书以外,《通典》卷一六五《刑四·刑制下》、《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载武德立法,俱只提制行约法十二条、五十三条格和《律》、《令》之事,而全然不及《式》的制行。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四》述唐武德立法只列“约法十二条”、“新格五十三条”和“武德律”,而全然不提《艺文志》著录的“又《式》十四卷”,即是有鉴于此的结果。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东京,创文社,2003年)《考证篇》第六章《汉唐间の法典にっぃての二三の考证》三《贞观留司格一卷の不存在——旧唐书刑法志の衍文、新唐书芸文志の批判》(原载《东方学》第17辑,1958年)中,更指出《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著录的开元以前法书,常取《隋书》、《旧唐书》等处记事折衷而成,认为其中如“《贞观留司格》一卷”其实并不存在,且对武德“又《式》十四卷”及“贞观《式》三十三卷”是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怀疑。 (11)《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刑制下》载“及受禅,又制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武德七年颁行之”。其文意亦有欠明朗。《资治通鉴》卷一九○《唐纪六·武德七年》四月庚子,“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也是一个易致误解的表述。又其前文载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这显然只是《官品令》的内容,亦属不妥的记载。 (12)《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丙辰“克京城”,“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义宁元年》十一月丙辰“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且其后文未载武德元年制行五十三条格之事。 (13)《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武德二年正月,诏自今已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二月。制官人枉法受财及诸犯盗诈请仓库、隐藏官物者,罪无轻重,皆不得赦原。”《新志》显然认为这就是五十三条格中的两条,所以才把五十三条格的颁行时间定在武德二年。若据《唐会要》和《旧纪》五十三条格颁于武德元年十一月,武德二年这两条规定显然不应列于其中。但即便如此,五十三条格仍应是在约法十二条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唐会要》卷四一《断屠钓》则载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两处所载这份诏书的内容,《新纪》与《册府》所载武德二年正月诏略同,《唐会要》则明显与之有异,但其“正月九日”断屠并无典据之可言,且此诏全文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释》所载武德二年正月《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诏》,《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亦载之,校之可知《唐会要》“九日”实是“九月”之误,且其前脱“五月”二字。 (1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正月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这类规定显然都在新《律》、《令》规定之列,而其当时先以敕例、条制形式施用,这也是武德二年正月以前《律》、《令》修订实已开始之证。 (15)《史通·外篇》卷一二《古今正史》。本文开头所述武德立法时间诸处记载有所不同的现象,似亦因此而来。 (16)参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 (17)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均田制研究者对《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载开皇《田令》与《唐六典》卷二《户部》所载武德《田令》相关规定的异同比较,其所示变化大致有五:一是“丁中”年龄段从11-20岁改为16-20岁;二是“露田”改称“口分田”;三是“公廨田”从无到有;四是妇女、奴婢从受田到不受田;五是僧尼道冠从不受田到受田。而第三及第四、五项之变化其实仍发生于隋代,分别是开皇十四年(594)及炀帝时所改。由此可见,武德《令》并非皆取开皇《令》加以损益而成,而是兼取了开皇和大业《令》的相关内容,同时其损益幅度确实有限。参武建国《均田制研究》第七章《北朝隋唐均田制度的演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八《隋律考·序》述隋末“刑罚滥酷,本出于《律》、《令》之外”。其论甚确。 (19)此诏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二《刑法》收录的武德七年四月《颁新律令诏》。 (20)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四》“武德《律》”条即引此诏的这些言论,以之为武德制定《律》、《令》时“颇有所釐正,不全用开皇也”的证据。其实这些言论主要是针对隋时敕例、条制横行之况而发,而不是说的新《律》、《令》具体应该如何修订。 (21)如《唐大诏令集》卷一○八《政事·禁约上》收录武德三年(620)四月《关内诸州断屠杀诏》,其末云:“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赡。详思厥衷,更为条式。”同书卷一○五《政事·崇儒》收录武德七年二月《置学官备释奠礼诏》,末云:“释菜之礼……比多简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所司具为条式,以时宣下。”相应地,当时也还有不少称“格”的例子,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政事·举荐上》收录武德五年(622)三月《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其末有“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下援引,务在奖纳,称朕意焉”之文,意即命所司制行一份赏罚有关官员举人得当与否的“别格”,“别格”自然是单行条制。同书卷一一九《政事·讨伐上》收录武德六年(623)九月《讨辅公祏诏》,其末云:“勋赏之科,具如别格,宜明宣布,咸使闻知。” (22)《唐律疏议》往往规定有关事务须“依《律》、《令》、《格》、《式》”而行,违犯者则正刑定罪。如其卷一○《职制篇》“事应奏不奏条”疏议曰:“应奏而不奏者,谓依《律》、《令》及《式》,事应合奏而不奏;或《格》、《令》、《式》无合奏之文及事理不须闻奏者,是‘不应奏而奏’;并合杖八十。”同时《唐律疏议》又在卷二七《杂律篇》中专设了“违《令》、违《式》”条,用来处理那些《令》、《式》有所禁制而《律》无罪名的行为。 (23)孝文帝制行“僧制四十七条”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隋代这方面的情况,如《续高僧传》卷一四《义解篇八·江都慧日道场释慧觉传》:“隋朝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同书卷二四《习禅篇五·汾州光严寺释志超传》:“大业初岁,政网严明,拥结寺门,不许僧出……(武德初年)时遭严敕,度者极刑。” (24)《释法融传》载此事在武德七年。《资治通鉴》卷一九○《唐纪六·武德七年》三月戊戌,李孝恭克丹阳,公祏授首,“江南悉平”。房玄龄据“关东旧格”奏行州留一寺三十人之制,显然是平定此乱的后续措施。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二《通表上·左右仆射左右丞年表》、卷五《辑考一上·尚书左仆射》述武德六年至九年裴寂为左仆射,其后萧瑀两任此职,而房玄龄则在贞观三年(629)二月方由中书令迁左仆射。 (25)贞观初年以来这方面仍承武德而续有措施,如《续高僧传》卷三一《护法下·京师大总持寺释智实传》:“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书卷二六《习禅篇六·扬州海陵正见寺释法响传》:“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泷川政次郎《〈令集解〉中所见的唐代法制史料》(《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有斐阁,1941年)认为,《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启福篇第八》收录的《度僧于天下诏》,即为太宗贞观十年(636)所下,此诏乃因沙门玄琬上年遗奏请定僧科,而命有司制订了一份规范和管理天下寺观僧道之事的完备条制。劲案:泷川先生钩沉出来的这份贞观十年条制,很可能是贞观十一年定《格》十八卷之前推出的最后一份规范寺观僧道之事的单行条制,永徽以后有关规定就被集中在《祠部格》和《祠部式》中来规范了。参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第六章《律令制下的唐代佛教》第四节《唐代〈道僧格〉及其复原之研究》一《唐代律令、式关于道、佛教的法律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刑制下》原注亦载此为贞观二年七月事。 (27)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四《通表下·兵刑工尚侍表》、卷二○《辑考七下·刑侍》韩洄条。 (28)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一书《考证篇》第六章《汉唐间の法典にっぃての二三の考证》三《贞观留司格一卷の不存在——旧唐书刑法志の衍文、新唐书芸文志の批判》即认为《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著录的武德“又《式》十四卷”,有可能是其撰者认为武德承袭了隋代《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