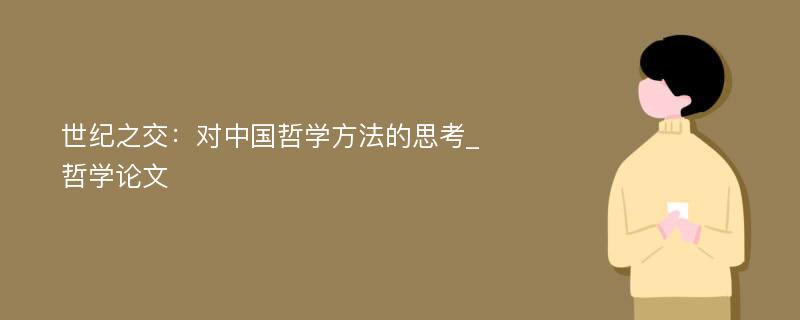
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断想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法论问题的再提出
我们一般把“五四”以后的中国哲学视为现代哲学,其实,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哲学的发展身负着双重的任务,即既要完成她的近代化历程,又开始了她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所说的“近代”一般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已进入了近代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近代哲学却步履蹒跚,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量的西方哲学思潮涌入的情况下,中国许多学人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以及胡适等人通过融会中西,特别是以西方哲学作为新的参照系反观中国哲学并建构其新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向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转化,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才取得了完成的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与中国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与各种外来思潮和流派的激烈较量而在中国得以广泛地传播。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也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主流。
现当代整个中国哲学格局主要表现为三个运思进路: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路;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进路;三是西方哲学的继续传入和中国化阐释的进路。应该说,通过这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着的运作进路,中国哲学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有了较大的推进。但是,毋庸讳言,这几个进路上的努力后来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因而它所力求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能解决得好。概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路上,受到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严重干扰;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上,则出现了明显的简单化、绝对化、模式化的倾向;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或方法。前者离开了毛泽东在30年代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实践论》所指出的方向,而照搬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既定模式,习惯于八股式的语言或经典著作中已被教条化了的语言,既不能以哲学的方式顾及和观照当代社会的巨变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也不注意对它所面对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做深入地了解和分析,拒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某种中国化的合理解释(如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讨论和对杨献珍的批判),甚至无休止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哲学,企图在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情况下来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方法上的教条化导致其内容的直观化和机械论,以至于在“文革”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几乎被“斗争哲学”所取代,矛盾的“同一性”成了阶级调合论的代名词。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理解的方法和模式来简单地套解中国哲学的情况;研究的目的盲然,有时甚至以简单地把历史上的哲学家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完事,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把本来难以分解的混沌一体的中国哲学思想简单地分隔开来;其研究也基本上停留于发掘古代哲学家“本文”的“原意”而弱于理论的创新,更缺乏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出发对三个进路的哲学运思进行整合的力量和进行总体性时代创新的精神等等,从而使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深化步履维艰。虽然在8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已有了十分可喜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醒,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要真正形成适应21世纪世界多元化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中国哲学能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首先要根除以前在哲学运思中造成的痼弊,清除其影响,还需要在哲学方法论上进行深入的反醒。
二、历史的反醒:哲学格局是一元的?
如果对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加以反思,不难找到中国当代哲学进行时代创新的切入点,即首先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哲学、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科学的关系;三是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哲学、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看不清哲学、学术与政治的区别,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或给哲学赋予较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哲学固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确实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且作为反映一定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当代总会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但是,也应看到,在意识形态诸形式中,哲学又是较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式,它须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才能产生,也要通过诸多环节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如果说政治思想因其直接由经济所决定且处于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它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整个社会意识的主导,但哲学则不同,哲学是一种探寻宇宙、人生本源归罕和生存意义的学问,并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来建立人的意义世界,而这种意义世界的建立其进路常常要表现出较强的超越性。由于这种追问总是与思想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根据和个人意识的特殊成因有关,加之世界在多个领域日渐表现出的多元化发展以及认识的多元取向,从而决定了未来的哲学形态可能是多样性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中,可能会形成某种主流哲学,我们也可以提倡某种主流哲学,或表示不赞成某种非主流哲学,但不可以用主流哲学排斥乃至禁绝别的非主流哲学,不能把主流哲学看成是“哲学之哲学”而以此君临一切,更不能以行政的方法强迫人们接受或放弃某种非主流哲学。宣扬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是错误的,用多元并存来否定一方主导也是不对的。但把一个时代的哲学形态一元化,就很容易使哲学特别是主流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人为地强化,甚至把哲学等同于政治。于是,哲学有可能成为注解政策的一种工具,这种哲学就会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其丧失合理性。一方主导和多元并存亦即“一”“多”的对立统一,也许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大体格局。
与上述问题相关,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科学的关系上,也曾出现过在宣传我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拒斥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在一个时期,我们对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其他哲学多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特别是对当代的西方哲学,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予以拒绝,而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将其视为人类认识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必要环节、看成可能带有某种普遍性原理的体系而加以发掘,这就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起来了,使之脱离了哲学发展的当代视野。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上,当代科学虽然在突飞猛进,但由我们所叙述的“哲学”则仍“岿然不动”,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样,对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的发现可能带来的革命性突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喜悦,看不到当代科学的一些最新发现将对原有的哲学体系可能引起的内原性突破,在那里,科学常常不过是哲学外在的注脚。事实上,科学的一些新进步或新发现,已对现行的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此外,在实践上也常表现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适性的同时,又有以此排斥或代替各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我们则常常以静止、孤立、片面的观点和方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看起来是在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度,而实际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弱化了它的价值和作用,其本身也不能在生活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对这种由我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不应局限在个别观点方面,而应该是对既定的理论模式进行解构和重构,并努力在当代哲学视野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做出中国式的、更准确、更具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揭示和把握。虽然这一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但这应是当代哲学工作者的使命。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是19世纪中叶直到80年代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这里且不论争论的各方谁是谁非,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封闭起来孤立地得以发展;历史的发展也总是先进的文化征服落后的文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是连中国古人也懂得的道理。但是我们在处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上,却走上了一条脱离世界哲学发展背景和文化氛围而封闭行进的路向。如果说建国前期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那样做实出于无奈,那么,到“文革”时期我们则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而“自为”地关起门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20多年的世界和平时期的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远远把我们甩到了后面。从哲学的发展状况说,“五四”以后的30到4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挑战曾做出过的被动回应,本该在此一时期转为主动地批判性认知,但遗憾的是,随着哲学政治功能的愈益强化,中西哲学的互融终于由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冲突观念的加强而几乎被中断。此后的结果则是不堪回首的但又不能不引起深刻思考和须加反醒的。当然,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80年代的改革开放已使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要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回荡在中国的大地。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中国哲学的发展应该是世界性的,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哲学的发展既不能割断与传统的关系,也不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隔绝。因此,主张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特点是正确的,但固守中国文化本位则是不合时宜的。在中国走向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过程中,当代学人应自觉担负起把中国现代哲学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任务。
关于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世界文化的关系,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关系问题。就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又承认,马克思主义可以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有一定地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于是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单一的或唯一的,因而在世界上可能形成诸多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否则我们就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研究层面上说,我们则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发展路向,研究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同时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即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因为,从文化的发展来说,任何一种学说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在解释时可能受到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它可能会发生某种分休,例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离为三”就是明证。所以,在今天世界复杂的、多样的、有多种矛盾交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也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能采取历史上孔墨分化之后都自认为是“真孔墨”的那种唯我为是的态度,而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要尊重、研究其他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丰富自身。因此,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时,也不要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这一文化背景,处理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三、中国哲学如何走向未来?
中国哲学在21世纪要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哲学,就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有根本的改观。除了上面提到的要注意弱化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解决好哲学、学术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等方法论问题之外,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哲学既要反映当前总的时代精神,也要注意到世界的多极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取向。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理解“时代精神”?什么是我们当代的“时代精神”?对此人们往往把它仅局限在中国社会当代的狭小范围。在中国尚未融入世界史之前,这样理解不是不可以。但当中国已越来越世界化,中国文化也越来越需要世界化的今天,这样理解就很不恰当了。随着世界现代发展的逐渐一体化,世人关注的问题也愈来愈趋于同一和全球化。因此,今天要在世界的大范围内煅铸时代精神,中国哲学也要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探寻自身发展的道路,确定发展的方向,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平和发展是今天世界的主流,人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人际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等都是世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哲学必须同世人一起共同研讨这些关注人类命运的世界性难题,并在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中提炼富有时代性的哲学课题,升华具有时代性的哲学意识。不过也要看到,世界发展中利益的一体化与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两种趋向是并存的,这种矛盾悖论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伦理方面到21世纪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提升或煅铸,就既要关注世人的共识,也要注意到多元化存在的差异。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现代化进程统一起来,也许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可行的进路。
其次,哲学要“忠于职守”,坚守人文阵地,努力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建国以来,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哲学已从哲学家的书斋走出来,成为广大群众手里的有力武器,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哲学的通俗化是必要的,但把哲学泛化乃至使之与一般的工作方法、研究方法相混同,则可能使哲学非哲学化。诚然,哲学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方法论,但这种方法论是根本的、普遍性的,它可以给人一种高瞻远瞩的视野,但不可能代替各种具体的方法。在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探寻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具体方法方面,还需要进行开发,但哲学依其形上学的本性,其旨趣不在于“对象化”的“求真”和认知,而在于内向化的建构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在于净化和充实人的心灵和构筑人的精神家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即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它显然和科学认知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现代西方哲学由科学世界向人文世界、从自然——知识世界向文化——价值世界转变的动向。这种动向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向人的回归是当今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趋向,而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中国哲学在吸收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时,要努力不失中国哲学这种“超前”的人文取向和价值关切。
与此相联系,传统的哲学本体论也面临着从外在宇宙本体论向人的本体回归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曾引进了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来探讨中国哲学。这种方法在深化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弱点也暴露出来,即它没有充分顾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特征和整体的、综合的直觉思维这一致思趋向,忽视了中国哲学与政治伦理、道德修养、理性认知混然一体的进路。事实上,中国哲学常常是从宇宙论来说明人生论的,其真理论也从属于价值论,整个哲学不过是在为人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理念确立宇宙论的根据。哲学史上即使最具玄想意味的魏晋玄学也不过是要证明“名教本于自然”。朱熹那个至高无上的“理”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佛禅的“不离世间觉”、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形上本体与人的道德“体用不二”,其中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种进路,把人放到了宇宙中心的位置上,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依归的价值转向,可以匡正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对建立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一对世界本始的追问本应属于科学的任务,在科学尚未被分化出来的过去曾由哲学来担当,但在今天则应当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中国哲学要忠于人文的职守,在对象上就要从外在的宇宙转向人自身,转向“自我”。在方法上也要努力找回“自我”,既要不失其对天人、物我、人己和谐关系和价值境界的传统追求取向,同时又要以人文领域的这种天人和谐以弥补科学领域无法超越的天人对立所可能出现的偏差。
再次,要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法论问题。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严重挑战是,社会愈益现代化,人们的观念愈益远离传统,同时,世俗的生活也在不断消解着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哲学要在日渐技术化、商业化和文化愈益世俗化的下一世纪得以存在和发展,就既要找到自身获得生命力的新的根基,也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提炼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并能通过新的形式切入其中的主体内容。亦即在其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现实性等方面都要有所超越。中国哲学必须保持本有的实践性品格,努力从生活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出发,提升哲学精神,并通过对其精华体系的现代阐释以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也就是说,要从社会生活的迫切问题出发对内容进行取舍、发掘和给予新的诠释。例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现代阐释并加以运用,也许可以缓解日渐技术化所带来的世界性的天人失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球性问题。中国传统的心性论和道德理性论也许可以对商业化和文化的世俗化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信仰淡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人生意义的消解起一定的遏制作用等等。同时要在诠释中赋予传统以新的形式,使之能为当代人所接受。未来中国哲学注重的应是义理的现代阐释和富于时代性的创造。没有创造,中国哲学将失去活力,从而与时代发生隔膜。这里有一个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汉学”与“宋学”亦即训诂、考据与义理之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曾外在化为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立。强调史料考据者不屑于义理的探究,而注重义理者又略于史料的挖掘,多年来二者此消彼长,相互磨擦,例如对“新国学”就曾引起过诸多的议论。其实把二者分割开来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其统一起来,建立二者的联盟。事实上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就不可能有坚实可靠的义理分析;而没有深层的义理分析、现代阐释和高度的哲学升华,史料的梳理考究也就会失去其生命和意义。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诠释,多年的实践表明,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引入西方哲学范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来诠释中国哲学,如何使传统范畴的理解和运用准确化、规范化和现代化。虽然人们近年来对中国哲学范畴史做了较深入地研究,但问题还是不少,其中主要存在着生硬地照搬西方哲学范畴来套解中国哲学的观念,或以西方哲学的既定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等有关中西哲学融通的方法问题。有了新的参照系,我们可能做到高屋建瓴地把握中国哲学,但又不能脱离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和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这就要求从史料本身引出结论,而不要先入为主,从既定的模式出发套解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史上确实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也有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古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刘禹锡曾分析过的“自然之说”和“阴骘之说”就接近这种看法,否认这一事实是不合实际的。但如果以此为模式来套解每一思想体系,或对某一哲学家做两极对立的分析从而得出一些绝对的结论,则是不正确的,例如,把老子非要说成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把张载的“气论”一定要与二程的“理论”做唯物与唯心的绝对对立等等,就表现出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退一步说,即使对某一哲学家的思想性质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也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探寻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总结人类思维的一些经验教训;同时更要追寻人生的理想境界,按冯友兰所说,即是要建立不同于存在世界的与人的觉解相联系的意义世界。
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规律性的探寻历来是当代中国学人致力的重要方面。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原理,我们确实可以比较明晰地看出某一思想体系或思潮形成的历史根据和内在动因,从而使我们从迷离混沌的社会思想之网中超拔出来,看清思想或思潮的主脉和线索。但是,一个思想家其思想的形成既有必然的因素,也不乏偶然的因素。就某一位思想家来说,除了社会大背景之外,思想家其特殊的家庭环境、独特的经历和家学素养、个人的特有的人格气质和交往关系以及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阶级状况等等,对他的个人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无疑会构成影响。如果对此不做具体地考究,而只注意历史大背景的分析,也很可能会出现偏差。这些恰是以往所忽视的。人们注重其中的必然因素是对的,但忽视其中的偶然因素就可能导致一般化的研究或得出一般性的乃至错误的结论。把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起来,对历史上的思想或思想体系做进一步深入细密地全面分析,并着重于对其偶然性成因的考察,也是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研究应注意的方面。
收稿日期:1997—04—30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