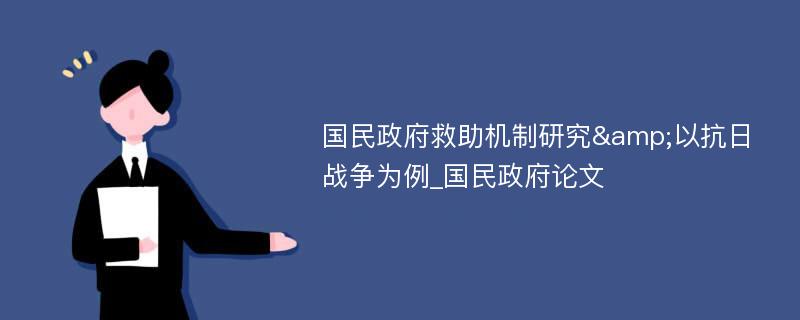
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政府论文,为例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3)04-0146-04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战不断,外患尤重。每次战争都造成大批难民,难民潮在近代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难民潮是八年抗战时期。有学者估计此次难民潮至少有6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4%略弱。[1](p63)面对如此庞大的难民潮,国民政府原有的救济机制不堪重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救济机制来削弱这种灾难,减轻由此带来的对抗战的不利影响,就成为国民政府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救难目标与原则
抗战烽火燃遍全国后,难民潮也随之汹涌而至。国民政府从有利抗战的目标出发,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救济运动。
1、救济目标
与常时救济弱势群体不同,国民政府认为要增加抗战胜利的筹码,必须把庞大的难民群体整合起来,加以组织训练,使潜在的战争资源和抗战力量转化成现实的资源和力量。为此,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与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2](p50)将难民救济与抗战事业联系起来,说明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国民政府已经不再把难民问题视为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将其视为能否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政治问题。根据国民政府纲领,相应地把难民救济分为两层目标来实施。基本目标是解决难民的食宿问题,“不令难民失所,……使其居有处,食有所,得免冻馁之忧”;较高目标是增强难民的民族意识,坚定其抗战信念,为此,对难民“施以组织训练,参加各项工作,以加强抗战力量”。[3l(p430-431)难民救济目标的明确,为建立救难机制指明了方向。
2、救济原则
难民人数庞大,救济工作繁重,难民救济原则直接关系救济行动及成效。国民政府依据以往的救济经验和近代社会救济思想的要求,采取了三项原则:
第一,积极救济原则。传统救济偏重消极施与,长期以往,使被救济者养成一种依赖心理。抗战时期难民救济采取“寓赈济于生产”,使“壮有所用,如为农夫可资助其垦殖,如为工人可介绍其工作,俾能发挥生产能力,以维持国民经济繁荣”[3](p430-431)。1941年制定的《社会救济法》更将这一原则法定化,如规定对贫穷者给以“资金粮食之无息或低息贷与”;对不良者“实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训练”;对失业者施以“职业介绍或指导”、“实施技能训练”等,即是这种积极救济原则体现。
第二,国家与社会协作进行原则。难民人数众多,单靠政府一支力量,难免顾此失彼,因而需要“发动社会团体的救济力量,使广大的社会救济工作,与政府的赈济政令,紧密协调,互相呼应,群策群力,以求战时救济政策之表里贯彻,扩大救济工作的效果”[3](p430-431)。在国家危难之际,国民政府主动弱化“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表达了国民政府企图发挥国家与社会两种资源,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救济。因为难民救济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涉及阶层广泛,人数繁多,只有将各种社会资源调动起来,才有可能将这次亘古未有的救济事业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
第三,政府责任原则。此次难民救济,不同于传统的慈善之举。传统的慈善行为,是执政者出于怜悯的目的,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仁政之举。而难民救济,国民政府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义务体现,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如法规规定:对于“无工作能力者,应指定地点收容”;“有工作能力者,应参酌人数多寡、工作类别及当地环境,妥为分配,……给予相当工作”;“难民之失学儿童及青年,得按其程度分别插入相当学校借读或施以临时教育”。[3]“应受救济人得向主管官署或有救济设施之处所,请求予以适当之救济”;“法院或警察机关,得将受救济人送交救济处所,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受”;“救济事业经费,应列入中央及地方预算”;“县市依本法举办之救济事业,得由中央政府予以补助”。凡此种种,都是政府救济责任观念与原则的体现。
简言之,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树立起了一应现代社会救济思想的目标原则,这反映了经过近代化的洗礼,中国社会在思想观念层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由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带有不平衡性,但它毕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救难机构
救难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一套救难应急机构。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难机构的变革大致经历了三次:先是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一应急机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专门用于救济难民。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由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署、赈务委员会各派高级职员一人为委员,以行政院所派之委员为主任委员,在省及院辖市一级设立分会,在县一级设立支会,从而建立起一套分级负责的难民救济体制,专办难民收容、运输、给养、救护、管理等事项。不过,随着抗战区域的扩大,难民数目成倍增加,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缺陷也显露出来:一是协调各部、委、署力量有余而事权不专不大,无法确实负责,增高效率;二是在职守上与战前已有的以救灾济难为职志的赈务委员会有许多重复之处。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将难民救济机构进行整合,以提高救济效率。经国防最高会议交办和行政院审议,1938年4月成立赈济委员会,将赈务委员会、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合并改组,并将内政部民政司所职掌的救济行政,亦划归赈济委员会掌管。
赈济委员会的成立是战时救难机构的第二次变革。赈济委员会虽为一临时性机构,但其权高位重,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为特任,并得出席行政院会议。此职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原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代理委员长。赈济委员会也采用科层制式治理结构,将各省、县赈务会、难民救济分会等即行改组,成立省赈济会、县赈济会,以资调整而一事权外,还在全国设立6个救济区,在难民转徙路线上,设立26个难民运送总站和132个分站、166个招待所,建立起覆盖主要难民区和难民线的救济网络,随时对难民进行接济、运送。赈济委员会具体职掌是:救济灾难机关及团体之指导监督;赈款之募集、保管、分配;灾民难民之救护、运送、收容、给养;灾民难民之组织训练、移植配置及职业介绍;灾民难民生产事业之举办及补助;急赈工赈子粜之举办或补助;勘报灾歉之审核;捐款助赈及办赈出力之奖励;慈善团体之指导监督;残废老弱之救济;孤苦及被灾儿童之教养;贫民生活之扶助;游民技能之训练;贫病医疗之补助等等。[3](p439-440)
到抗战后期,难民遣返、战毁重建等复员事宜成为当务之急,以救难为职责的赈济委员会使命宣告结束。1945年1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成立。行总实行署长负责制。行总在承继赈济委员会工作同时,将善后救济作为工作重心。具体而言是:难民输送及复业;难民福利;难民工业;流离人民之调查;工商业损害调查;泛滥区域之灾情调查;其他有关善后救济之调查。行总根据收复区特点和被难情况,在全国设立东北分署、冀热平津分署、晋绥察分署、鲁青分署、河南分署、苏宁分署、安徽分署、湖北分署、湖南分署、广西分署、广东分署、江西分署、浙闽分署、台湾分署、上海分署等15个分署和滇西、福建和中共抗日根据地共5个直辖办事处。为了接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中国的物资,还在上海、天津、青岛、九龙、广州、大连设储运局。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一级专职救难应急机构,明确了救济工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民国社会救济行动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表明民国社会事业在曲折前行。
三、救难措施
抗战难民潮呈现出人数多、规模大、成分复杂的特点。将这些潜在的战争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战争资源,就必须根据战时环境与难民群体特点,采取适宜的措施,予以救济和组训,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1、紧急救济
战争初始,难民每日都在大量产生,不少社会团体设所收容。但随着难民人数增多,已有的收容所不堪重负,导致难民露宿街头,饥寒交迫。社会部紧急制定《各级党部难民救济工作实施办法》,规定:
(1)在战区或临近战区之各级党部应协助当地军政机关,并指导各级慈善团体办理难民登记、疏散及放赈等事宜。
(2)各级党部应将所在地所有难民、难童之人数、姓名、年龄、籍贯、性别、职业,调查清楚,呈报上级考核。
(3)在后方或边区各级党部应详细调查当地可能各项工业或垦殖事业,协同政府纠集民力规划举办之,务使难民从事生产,以谋根本之救济。
(4)各级党部应协同政府调查当地祠堂、庙宇及公益场所,借作难民收容所、难童教养院之用,其各祠堂、庙宇、公益场所原有之经费,亦应劝其捐助百分之十,以作难民救济、难童教养以开办难民生产事业之经费。[3](p283-285)
同时赈济委员会紧急拨助十数万元,分令地方政府或救济团体,速施救济。[4](p505)此外,日军对我不设防城市狂轰滥炸,惨重情形,目不忍睹。国民政府乃订颁《空袭紧急救济办法》十条,规定空袭灾害发生后,主管救济机关应立即派员会同有关各机关团体弛赴被炸地救护,并详查死伤人数状况及房屋因炸受损情形,分别予以登记、抚恤。赈济委员会先后督导各地成立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预拨救济准备金,办理紧急救济。其余紧急救济事宜,在赈济委员会负责筹办下,均依令办理,对抗战民心的安定,深具重要意义。
2、难民组训
难民组训战是难民救济最具特色的一项内容。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例如交通、运输、担架、救护、慰劳等,都迫切需要人们努力去做。如何将难民中众多的有用之才组织起来,有力出力,有才出才,以增加抗战的力量,化消极救济为积极救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938年,赈济委员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会同组织难民组训委员会,开始共同领导难民组织训练工作。
难民组训目的和方式在1939年8月赈济委员会呈报行政院的《难民组训计划大纲》中,规定得很清楚:
(1)使战区及接近战区之难民,人人不离乡土,并能切实做到自卫自养,以增加抗战力量而减少政府对难民之负担。
(2)使移居后方难民,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安定日常生活,充实抗战力量,巩固后方秩序。
(3)使后方回籍难民,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不作顺民,不为敌用,并能发挥各个人或集体之力量,摧毁敌人一切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侵略设施。
(4)难民组训之实施,应依其职业、性别、年龄、体力、环境之不同,适应实际需要分别进行。
(5)难民组训工作务须与难民救济设施取得密切联系与配合。[3](p471-472)
难民组训内容因难民所处战区不同而有别:处于战区及临近战区的难民,“其训练以军事与政治并重”;处于逃难到后方的难民,“其训练以生产技术与政治并重”;对于返回原籍的难民,“其训练除注重军事与政治外,并应授以必须的特种技术”。[3](p472-473)总之,通过组训得到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一种抗战的合力。
随着抗战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更多的平民被卷进难民潮。同时,抗战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日益增加,国民政府对难民的组训工作愈加重视,进—步制定了《加强难民组训实施方案》,其组训方针是:“精神训练:难民组训以精神训练为主,务期提高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技能训练:同时注意各种专门技能训练,使受训之后获得各项简易生产技能,自立生活。”
难民组训对于持久抗战有着极为重要作用,故各省对此非常重视,抗战期间各地历年成立的难民组训委员会有21个,每次组训40000人,以3个月为一期,受训难民人数仅1938~1941年就达147,079人。[3](p10)难民经过训练,在军事、生产等方面的技能得以提高,在政治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抗战胜利的信心,并成为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3、以工代赈
难民群体中有相当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人,据对湖南赈济委员会遣送湘西入川难民年龄构成分析,16岁至60岁的青壮年人口占总数的63.2%弱,此中又以16岁至40岁的壮劳力居多,占难民群体总人数的46.1%以上。[1](p66)如果将这些青壮年难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生产,寓救济于生产,无疑对于稳定后方、促进抗战是十分有益的。赈济委员会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通过兴办工厂、移民垦荒、修渠筑坝、开矿铺路等“以工代赈”措施,安置了大批难民。
“入厂做工”是赈济委员会规划实施的解决难民谋生办法之一。赈济委员会自1939-1941年,先后组设赈济工厂20个,连同赈济女子工艺社和赈济实验农场达22个,吸收难民14551人就业。[3](p13)此外,还补助各地难民工厂91家[3](p13),帮助它们克服困难,度过资金缺乏难关。
移民垦荒是“寓救济于生产”的又一举措。战初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最早提出移民垦荒的设想。该方案指出:“抗战以来,凡战区民众之避至后方者,政府当妥为抚辑,不令失所,更当使彼等从事于生产工作,以增加抗战力量。彼等对于生产工作可以用力之处甚多,其最要者,厥为垦荒……难民中能从事此种工作者,自应协助迁徙,俾有以自效。”[5]为促使这项工作有序开展,1939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规定:难民移垦事宜由经济部会同内政部、财政部、赈济委员会管理统筹,并督促各省政府办理之;各省得于一定期限内,设立垦务委员会,办理难民移垦事宜;中央主管垦务机关,应自行或限令各省政府,于短时间内完成下列事务:(一)调查并确定垦荒区;(二)确定能容纳垦民人数;(三)拟定各项移垦详细实施办法或计划;(四)办理移垦难民登记。此外,为确实照顾移垦难民,该条例还规定:
(1)移垦难民到达垦区后,在尚未收获以前之生活,由赈济机关及垦务机关维持之。
(2)垦民第一年所需食粮、农具、耕牛、种籽、肥料、饲料、种畜,由垦区管理机关采购贷之。
(3)垦民所需其他生产资金及必需费用,由垦区管理机关介绍贷款,或会同工作主管机关指导组织合作社,介绍金融机关贷予之。[3](p6-471)
移民垦荒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江西等省区。抗战期间各垦区中,陕西黄龙山垦区成绩较为显著。该垦区成立于1938年3月,1941年9月时全垦区共收容难民26537人。[6]就垦区经营方式来看,有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就垦区实际开发数统计,大约有1,444,209亩[7](p185)。如以每人10亩计,共吸收难民14万多人。
兴修水利、铺路建桥也是工赈的基本方式。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组织实施了百余项水利工赈项目,既有复堤堵口,也有象绥远省的大黑河、红河、昆独仑河及民生渠和官厅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修复,还有诸如筑堤、疏浚、凿井、灌溉等小型地方水利。据统计,水利工赈共用工数59,133,766人次[8](p94),数千万难民的生计得以一定的解决。交通工赈仅次于水利工赈,占整个工赈总量的五分之一。按类型分,交通工赈可分为修复破坏的公路、修复县乡道路、修复铁路和修复重要桥梁四部分。交通工赈共用工数33,643,105。[8](p95)除此之外,尚有房屋工赈、市政工赈等。据有关数据统计,行总主持工赈共供给粮食30万吨,工赈总工数1.8亿,解决了1000万难民的生计问题。其成绩不可忽视。
4、职业介绍与小本借贷
抗战初期,全国工人失业人数至少有350万人[9]。抗战结束前后,民营工厂或因缩小范围而裁减工人,或因打算迁返原地而解散工人,全国因受失业与半失业影响,受到饥寒威胁的劳苦市民,当在160万至200万人之间[10](p188)。为救济失业难民,社会部在重庆、内江、遵义、贵阳、桂林、衡阳、兰州等市的部属社会服务处内设置职业介绍组,开展求业登记、求才登记、职业调查及职业介绍等业务。赈济委员会于1941年度开始分令各救济区、站、会,根据当地难民情形,分别设立难民职业介绍所,1941年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91个,1942年发展到168个。各职业介绍所介绍难民人数,1941年为101444人,1942年为645403人。[3](p56-57)另外,为救济难民中的工商业者,国民政府还设立“小本借贷处”,借贷给贫苦无资营业者。借贷数额自10元-500元不等。赈济委员会先后在重庆、西安、西康等地设立小本贷款处及分处数千个。其中,重庆小本借贷处自1939年6月1日开业至10月14日的短短四个半月时间里,共向638户工商业经营者贷款46721.6元,平均贷款每人70多元,借款人来自15个省市,经营小工商业30余种。[1](p397)就全国而言,截至1944年3月,共为2414人办理了贷款,间接受惠者仅万人。[11](p449)
上述措施,是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的组成部分。从其内容来分析,可以认为国民政府愈来愈抛弃传统的“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方法,而重视“以教代养”的积极救济方法。这是近代工业化发展和社会救济思想变化的结果。
四、救难效应
救难原则的确定、救难机构的设立及救难措施的采行,是国民政府救济的三部曲。从救济效果来看,1938-1944年各级赈济委员会共救济难民19,563,362人,占同期难民救济人次的40%,其他则由各慈善机关和社会团体来完成。[3](pp9-10)行总办理急赈和特赈受惠人数3700余万人,协助返乡难民及侨民逾160万人,医药救济1170万人,工赈800万人。剔除重复计算人数,实际受惠者估计4600多万。[8](p246)由此可以认为在抗战及善后难民救济中,国民政府承担着主要作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仅有的一次政府投入相当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从事社会救济事业,它使成千上万的难民免于死亡,这对于保持民族有生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如此,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的建立,对于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也有积极意义,对于后人也有借鉴作用。
在肯定国民政府救难举措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救难机制的运作尚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救济经费十分有限,限制了工作的开展。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为例,实拨救济粮仅占申请的30%,衣着仅占20%,而善后物资配拨数量尤少,致使其他救济措施无法展开。二是救济行政官僚化、腐败化严重。救济官员对难民的疾苦冷漠敷衍,较远地区难民难被注意,个别贪官,贪污、克扣救济粮、款,散赈时不能在时间和地点上作有计划的安排,使—些无法久储物品变质。三是救济政策不能如数兑现,如移民垦荒的优惠条件不予兑现,使不少移垦难民生存难保;救济设施数量过少,许多难民无法得到安置,变成游民。上述弊端既有客观方面因素制约,又有主观原因导致。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管理上的不力和玩忽职守,是不能开脱罪责的。
收稿日期:2003-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