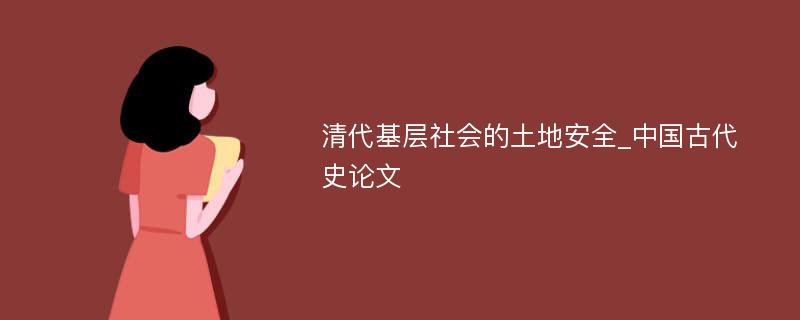
清代基层社会的地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保论文,清代论文,基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9)02-0089-12
揆诸清代文书档案以及各种笔记、方志、政书等文献记载,地保之称频繁出现,广为使用。地保是清代以及民国时期重要的基层管理人员之一,其普遍存在于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地方社会。
关于地保,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萧公权和瞿同祖认为,地保是州县政府为控制乡村而委任的行政代理人,其社会地位非常低。①[日]佐伯富从探讨清代基层社会自治组织角度,对乡保(乡约、地保)作了考察② 而斯威特、黄宗智、王福明等认为,乡保(乡约、地保)不代表乡村社会,而是县衙之下由知县任命、并向知县负责的下层吏役,属最基层的半官职人员,是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是地方领导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缓冲人物。③ 杜赞奇则从“乡村社会的经纪统治”角度,对“地方”(即地保)作了考察,认为“地方”通过垄断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联系而获得了某种权力,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身份较低。④ 戴炎辉对清代台湾的基层乡治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地保本质上系驻乡的差役,属于“在官人役”,其在身份上系贱役。⑤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清代华北的基层管理制度中,对地保亦有述及。如魏光奇认为,由于保甲组织在清代始终未能成为经常性的编民组织,直隶各州县在雍乾以后陆续出现了另外一种职役系统——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⑥ 李怀印根据直隶获鹿县晚清地方档案,指出获鹿县的地保等乡地人员,由村民根据村规轮任,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⑦ 而孙海泉则认为,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乡地组织,其实就是保甲组织。地方、地保等职役的存在是保甲制度演变的结果,是清代保甲组织承担各种地方公务造成的。⑧ 另外,日本学者山本进在研究清代财政史中,分析了清代赋役制度改革与江南地保产生之间的关系。⑨ 概括来说,以上研究多认为地保是清代州县政府为控制乡村而委任的行政代理人,充当政府的最下层吏役,其社会地位很低。但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华北地区,且附于其他论著之中,并非专题性研究。迄今为止,有关地保的系统性考察尚属空白。
那么,清代地保之称是何时出现的?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设置的?地保的主要职能及其变化怎样?地保的身份和地位如何?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颇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拟在广泛搜集史料基础上,对清代地保试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论述。
一、地保与保甲
自明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清代,保甲重新兴起。在清代,当提及保甲时一个新的名称出现了,这就是“地保”。地保之称早在康熙年间即已出现,其时地保之称当与民间俗称保甲之役有关,并开始被一些地方官员和幕僚载入政书之中。如康熙年间任山东蒙阴县令的陈朝君,为防止逃人和匪类入境而申饬保甲,要求“乡耆、地保务必小心稽察”,并严禁“地保人等,指称造册名色,摊派纸张,科敛牌甲。”⑩ 又,康熙间,钱塘幕僚潘月山在其所撰的《未信编》中亦载:对于“决过犯尸枭首者,示挂通衢,取地保收管。”(11) 另外,清初与地保相类的职役多被称作“地方”。“地方”频繁见称于康熙年间的相关文献中。如康熙间,陈朝君所撰《蒞蒙平政录》中有:“时将荒欠,米价腾贵,有地方之责者,即将捐纳银两,转粜于他省外郡丰熟之处,归而减价平籴于民”,并要求“委用老成殷实者分头往粜”,为了盘诘匪类,稽查流民,要求“各该管地方,务要小心稽查”。(12) 又,康熙间,潘月山的《未信编》中亦载:“遇有人死,地方不许不报,不报则地方宜责”,且“令尸亲与地方守尸,候官看验”。对于盗犯,“必令亲属、近邻识认,不可只凭地方呈词”。(13) 又,康熙间,黄六鸿所撰《福惠全书》中,亦多次提及“地方”之役。从中可以看出“地方”的主要职能有:(1)配合捕役巡缉逃人。(14)(2)禀报地方命案,看守和掩埋尸体。(15)(3)接应上司:“上司所临之处,预饬地方等巡逻。”(16)(4)配合编审:“今既编审,著里书、户长等,并乡约、地方俱具并无受贿隐漏及偏累孤贫等弊。”(17)(5)巡查地方:对于地方游惰匪类,“有司捕获渠首,余党自散,严饬地方倍加巡警。”(18)再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苏州府“长、吴二县奉宪永禁向玄妙观勒索陋规碑”中有:“如敢故违,该地方即同住持控禀府县衙门。”(19) 以上很多场合所称“地方”,其职能和性质与地保基本类同。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地方”之称,即指地保而言。(20) 然清代“地方”所指较为宽泛,实际上图正、书役等亦包括在“地方”之内。又,总体来看,康熙年间地保之称尚不普遍。
到了雍正年间,地保已较多地出现在官府的文件中,在正式场合已被承认。如雍正二年(1724)七月,总督河道齐苏勒关于施救盐城县水灾的奏折中报称:
二十日辰刻,潮头汹涌,直撼城脚。巳时,水势始觉稍平。除一面行查各里各场,责令城内城外地保人等,各择寺庙,安插被淹人民,并亲赴新兴场等处,一体安辑捞救。(21)
又如,雍正六年(1728)正月,浙闽总督高其倬为开洋事所呈奏折中言:
臣随行令凡飘洋船只,务令将船上人数据实造报,先取族邻地保不敢稽留外地甘结,地方官加具印结,并填左右箕斗,再令海口文武各员查验明白,方准放行。(22)
再如,雍正七年(1729)十月十四日雍正皇帝的上谕中说:
据署总督唐执玉奏称,磁州民人杨进朝在路拾银四十两,钱三千文,即告知地保,仍至原处寻觅本人,如数交还,丝毫不昧等语。(23)
乾隆以降,“地保”一语则常见于各种记载。一般文献已不必说,即使在官方颁布的典志之中,“地保”之称亦屡见不鲜,而成为被官府正式认可的一种基层管理人员的专称。乾隆《钦定大清会典》载:
凡安置军犯,畿辅、盛京不得编发罪人。苗夷杂处之地,令该督抚酌移别属军犯到配,年六十以上及有废疾者,入养济院,年力强壮者,充驿站及各衙门夫役,有艺业能自谋生者,交地保收管,仍于月朔,按名点验。(24)
乾隆《大清律例》条例中载:
凡窃盗等事,责令该地保、营汛兵丁分报各衙门,文武员弁协力追拿。如地保、汛兵通同隐匿不报,及地保已报文职而汛兵不报武弁、或汛兵已报武弁而地保不报文职者,均照强盗窝主之邻佑知而不首例,杖一百。若首报迟延,应照牌头曾首告而甲长不行转告例,杖八十。(25)
《皇朝通志》载乾隆皇帝为官营社仓事所发上谕亦言及地保:
(乾隆)四十三年,山东巡抚国泰请社仓春借时,地方呈报州县,批交社长支发,秋还时由州县开单,交地方按户催完,每岁杪责令州县亲赴四乡盘查。上谕:“此是在官又添一常平仓矣。社长侵渔原不能免,然因此而官为经营,则书役、地保之藉端勒索更甚,惟仍旧令督抚饬州县,实心稽核,期得实济无事。”(26)
在这则史料中,“地方”、“书役”、“地保”三者同时出现,可以看出,所谓“地方”之称是包括“书役”、“地保”等在内的。
综上,地保乃清代保甲组织负责人之俗称,有的场合即指原来的保正或保长,有的场合亦包括甲长、牌头在内。在清代康熙年间,地保作为一种俗称开始出现于一些地方官员和幕僚的政书中。雍正年间,地保已较多地出现在官府的文件中,且正式场合已被承认。乾隆以降,保甲负责人之地保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不少地方,地保或地方之称逐渐代替原来保甲组织中的保正、保长、甲长、牌头等。特别是地保与明末清初的保正相比,其设置、职能、地位均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地保普遍出现的背景
清代地保的普遍出现,究其原因,乃与雍乾以降里甲向保甲嬗递所带来的乡里职役变化有关。
如众所知,清初基层社会组织的设置承袭明制,既沿用里甲,又设置保甲,二者共存构成地方管理之基本格局。一方面,国家基于编审赋役、催征税粮之需要,继续推行明代的里甲制度,并着力于对里甲组织的恢复和完善。另一方面,为了“弭盗安民”,清初以后还特别加强推行明代以来的保甲制度。本来,明末至清初里甲和保甲所发挥的社会职能各有所侧重,所谓“里甲主于役,保甲主于卫”。(27)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与赋役制度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明末万历以后一条鞭法开始推行,至清初即正式废除了黄册制度而实行编审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正式实行“摊丁入地”。乾隆五年(1740)户部题准朝廷不再依编审照报人丁,而按“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的“原有册籍”,“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28) 这样,就停止了人丁编审制度,户口统计的依据遂从编审册转到了保甲册。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编审制度。(29) 上述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最终导致赋役编审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里甲组织本来是在赋役编审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于是,随着编审制度的废除,清代里甲组织的功能日趋削弱乃至崩溃。钱粮催征事务的大大简化也为保甲取代里甲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保甲逐渐取代了里甲,而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主要作用。(30) 在里甲向保甲嬗递过程中,清政府不断赋予保甲组织更多的职能,保甲除了承当原来“弭盗安民”职役外,还取代了里甲催征钱粮和查编户口等役。并随着清代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其所承值的地方事务越来越繁杂。保甲组织转变成为集弭盗安民、催征赋税、编查烟户、赈济救灾、缉捕逃亡、稽查命案、应官差遣、调处词讼等职能于一身的地方基层组织。清政府还大力倡导“以乡人治其乡事”,于是各地因地制宜,主要是发挥某些既有的基层人员如乡约、地保、图正等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能。(31) 清代地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而普遍出现的地方重要职役之一。
如上所述,地保与保甲本来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地保的设置应建立在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的保甲编制的基础之上。然而,雍乾以后地保和保甲的设置,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官方推行的这种保甲编制的基础上,而多是以自然乡村聚落为基础而设置的。如《学治一得录》载:
卑县四乡村镇向皆各有乡约、地保,原为稽查弹压而设。职到任之初,逐一点查。间有日久裁撤,未经补报者,殊为漫无约束;又有数村公共一人者,亦恐鞭长莫及。职当即出示晓谕:着各村镇认真选举公正殷实之人充当乡约、地保,每村二人,不许一村不设。(32)
又,《沧县志》载:
原夫里甲之制,期在野无旷土,人无游民,举凡田赋户役之数,保受比伍之法,靡不条贯其中。自后地乏常姓,民鲜恒居,或此里之地,属之别里之人,或此里之人,迁居别里之地。故里仅能制其田赋,不能限其居民。所有征发、勾摄,保甲不得不以现在之村庄为断。(33)
这种以自然乡村为基础而设置地保和保甲,乃与雍乾以降里甲崩溃、保甲代兴所带来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相关。具体地说,清代前期为配合钱粮的滚单催征、作为整顿里甲组织之一的重要措施,是各地先后实施的顺庄法。其做法是“以地从人,先归村庄,后编里甲。将本人所有各都之产,尽数收归一户,即在所住之都立户完粮”。(34) 可见,顺庄法的核心是将田产和人户按现居村庄来编造册籍,旨在理顺地产与业主间的关系,以避免赋税征收中诡寄隐漏等弊端。雍正间,实行摊丁入亩,顺庄法得以广泛推行。此乃赋税征派在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直接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为的里甲行政编制陷于崩溃。于是在里图之下,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地位上升。尽管清政府不断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度,但很多地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实际上并未按照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的统一规制进行实践。各地推行保甲的力度和具体做法差别很大,“南北异趣,新旧杂陈”。(35) 或彻底打破里甲系统,严格编制保甲;或在原有里甲(图甲)基础上加以整顿;甚或有保甲之名,而实际上推行乡地组织等等,不一而足。结果是在雍乾以后,很多地方都是“以现在之村庄为断”来推行保甲法的。这种寓保甲于自然村落之中的做法,导致清代地方事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自然村落及其乡村性组织所制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自然性的“庄”、“村”、“图”等为基础设置“地保”一役,成为相当普遍的做法。如清代德清县“每庄由地保一名,所以稽户口,便征收也”;(36) 乾隆间,山东淄川县“责令各庄地方代为催科”;(37) 乾隆间,永清县“以村落大小而置地保焉”,如该县东乡有村庄70个,按10户一牌凡编牌785个,共设地保66人。其中“横上村”编制37牌,而“东贾家务村”仅编制2牌,二者人口数量悬殊,但均各设地保一人。显然,该县是按照自然村庄为单位而设置地保的。(38) 昌黎县亦“按地保所管村落联为一保”;(39) 清代宝应县共辖45个铺,依据铺所辖村庄数量多少,小铺设地保1名,大铺设4-5名,共设地保85名。(40) 江西新喻县“附城为五坊,坊有坊长;乡为五十七图,图有地保。”(41) 在太仓,“地保,每图一人……有领催条漕及巡查协捕之责。”(42) 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尤其在南方,其里甲在清代多称“图甲”。随着顺庄法的实施,这种“图”经过“活图法”的改制,其区划已彻底打破了原来里甲编户形式。保甲制度推行后,又经历了“通县民图拆散甲分,查照烟户住址编为庄村”的变化。(43) 因此,图下所辖的亦主要为村庄。(44) 所谓“图有地保”中的“地保”,亦当是按自然村庄为基础而设置的。
由上可见,雍乾以降,保甲职役的日益繁杂及国家对自然乡村控制的加强,是清代普遍设置“地保”的主要动因。随着清中期自然村庄成为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基本单位,“地保”的设置亦主要体现为以自然乡村为基础,并成为基层社会“以乡人治其乡事”的重要基层管理人员之一。
三、地保的职能
清代“地保”所管理的事务十分繁杂,总体上可以从民事和刑事两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考察。
首先,从“地保”管理民事事务方面看,其主要职能涉及钱粮催征、支应官差、治安管理、田土勘丈、民间调处、救灾赈济等。
第一,钱粮催征。清代前期,赋税征收仍以里甲组织为主导。雍乾以后,随着摊丁入亩的实施,里甲编审的废止,里甲组织衰退。在赋税征收上,清政府不得不实行顺庄滚催,于是,钱粮催征成为地保的一个重要职责。关于保甲催征,在乾隆间即规定:“一切户婚田土、催粮拘犯等事,另设地方一名承值。”(45) 从很多地方的具体实践看,多通过设置地方、地保之役,以责“按庄开载,开单确查,有地必有粮”。(46) 如广宗县规定:“死亡逃户应征粮银由各村地保赔缴”;(47) 乾隆间,淄川县也是“以地方代催科之役,民颇便焉”;(48) 乾隆间,四川巴县亦推行乡保督办钱粮。(49) 直隶大名县的钱粮催征“不责之里甲”,而“改按村庄,分为五路……或有玩户则惟乡地是问”。(50) 山东章邱县在革除里长后,赋税“惟有用乡保按庄传催,以本庄之人催本庄之赋,事易不劳,绅民称便”。(51) 嘉道间,曾历任地方官的王凤生在其《保甲事宜》中亦强调:“一切催征钱粮、命盗词讼等事,仍归地保办理。”(52) 丁日昌《抚吴公牍》亦云:“武阳二县,各图地保,无论士农,逐年逐庄,按亩轮充,收缴钱漕。”(53) 可见,在钱粮征收上,保甲与原来里甲的征派形式和内容颇有差异。在人丁税尚未摊入田亩前,里甲组织原则上是一个既承值赋役又催征赋役的赋役单位,其赋役承值和征派应是统一的。摊丁入亩后,保甲组织对于赋役征收,侧重于应官催征和直接支应官差。这种催征和支应官差,很多地方均落到了乡村地保(地方)身上。
第二,支应官差和治安管理。如上所述,支应官差是清代地保重要职役之一,具体体现为:(1)上报地方情况。如地方治安“谕饬乡长、地保随时妥查密报”。(54) 在广东,遇有地方械斗,“或责成族长、地保飞报。”(55) 另外,举凡地方册籍,亦往往“交该管地保进城之便,投县备查”。(56) (2)执行官府禁令。如金溪县对于地方“溺女”恶俗“专责于地保”。(57) 宁波府为禁止演出淫戏,要求地保督同地方宗族“随时随地互为查禁”。(58) 乾隆四十六年(1781),祁门县一份告示中亦明确宣示,“如敢抗违,许该地地保人等指名赴县具禀”。(59)(3)张贴告示。地方官颁发告示,一般“交地保实贴,无论村僻处所,不许遗漏,并令收管,不得风雨损坏”(60)(4)地方接应。地方官员下乡,往往“先期传集地保伺候”。(61)(5)治安管理。清代地保具有监守和维护辖区内地方治安的职责,主要体现为对乞丐等流动人口的监管。如在浙江,为了防止流动乞丐结伙为匪,官府采取“交地保收管,记档备查”。并予以集中管理,“责成地保稽查,(夜宿间)不许外出”。(62) 另外,浙江还规定:对于沿海流动水手、纤夫等,如无当地居民保结,“即行驱逐,并选派兵役协同地保严行稽查,以杜为匪之渐”。(63) 从地保管理地方治安职能看,其具有地方保甲组织的性质,并在清代中期以后,治安稽查成为各地地保的主要职责。
第三,田土勘丈。清代一些地方的地保往往参与民间土地管理。如《牧令书》中有:民间土地纠纷“先令地保于两家管业四至处所插签标记,并密吊该业之四邻契据,令其勘日当面呈阅,然后履勘。”(64) 又如,近代上海开埠后,为了适应外国人租借土地,上海道台与各国领事联合成立了专门性机构——会丈局。至今遗存的大量“道契”,很多是会丈局管理土地申领和勘丈的相关文书。从这些文书记载看,近代上海民间土地的租佃和买卖,必先经各图地保勘验和盖戳方能生效。(65) 因此,在近代上海,管理土地的地保又称“盖戳地保”。(66)
第四,民间调处。明清时期,地方纠纷和诉讼多于民间范围内得以调处。民间调处的途径灵活多样。里甲、里老、乡约、保甲等基层组织,宗族、文会等社会团体,中人等民间群体,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清代,地保作为官方基层代言人,往往亦参与“户婚田土”等民间细故的调处,这从一些地方官所撰的各种政书中可见一斑。所谓“无关紧要之事,或批族老调处,或令地保查覆,酌量办理”;对于“一堂不结”的民间案件,“或添传人证覆讯,或交族人、地保调处”。(67) 光绪间莱阳县孙兰馨府控张尚谟案,最终“仰地保协同首事人等调处”而息讼。(68)《办案要略》中亦云:“讼之起也,未必尽皆不法之事。乡愚器量褊浅,一草一木辄争竞。彼此角胜负气,构怨始而投知族邻、地保,尚冀排解”。(69) 道光间,黟县程嘉栋因纠纷而投族邻以及“地保胡吉”理处,胡吉随即“往验属实,邀同族邻劝谕息事”。(70) 当然,一旦所调处的纠纷被“讦告官府”成为诉讼,地保又必须配合官府履行相关勘验、取证职责。如乾隆间,休宁县首村朱氏与黄姓发生产业纠纷,并讦告于县,县主即批复“地保查复”,地保黄时英随向官府出具了禀呈。(71)
第五,救灾赈荒。清代官府对地方的救灾赈济,亦多赖地保一役。地保在这方面的职能有:(1)上报灾情。如河南永城县对于蝗灾,“责成地保随时禀报”,捕蝗时,地方官“督率地保查察”。(72)(2)参与救灾。雍正二年(1724),黄河入海口发生泛滥,地方官责令“地保人等各择寺庙安插被淹人民”。(73) 雍正四年,福建省罗源县因水灾山崖塌方,对压死之人“量给银两,令地保买棺埋葬”。(74) (3)参与赈荒。如《牧令书》载:官府勘灾赈荒由“地保协同业户逐段挨查入册”,(75) 在赈荒中须“取有地保并邻佑保结,给予(救济)”。(76)(4)协助掩埋无殓尸体。如《得一录》中有:“向来流丐病毙,该图地保、丐头以篇草包裹掩埋”;(77)“偶遇(乞丐)身故,经同事看明,地保收殓”。(78)(5)收管流丐。如在南方一些州县,对于流丐采取集中安置,“每冬于城外空旷处,搭盖席屋数间……或地保、甲头,令其掌管”。(79) 又如,在上海,曾设立抚教局收留乞丐,并规定:“如尚见有此辈沿街乞食,惟丐头、地保是问”。(80) (6)协助慈善机构收养病茕。所谓“填单收敛,来去俱凭地保……如无地保送局,概不收养”。(81)
其次,从地保管理刑事事务看,其主要职责涉及案情查验,案件报官、传拘罪犯、充当质证、查盗起赃、“另户”监管等。
第一,案情查验。凡地方发生人命、强盗、窃盗等刑事案件,“地保宜立刻究问衅由及斗殴之状,受伤之处,细细诘问察看”。(82) 尤其是命案发生后,多责令“地保勘验”。(83)
第二,案件报官。地保查验后,须及时闻官。所谓地方命案“地保及尸亲、邻证不分雨夜,立即赴县报名”(84) 在清代相关法律文书中,“事据地保呈明”,“据地保禀称”是十分常见的用语。
第三,传拘罪犯。刑事案件闻官后,地保须直接或协助官差缉传罪犯。如《庐乡公牍》案例中有:“谕饬地保居腾和严拿展洛四等(犯)”。(85) 又如,清代莱阳县“传拘人犯,向系差协地保到庄传拘。盖非地保无人指户”。(86)
第四,案件干证。由于“地保系其土著,耳目难瞒”。(87) 因此,地方官在调查和审理案件中,地保呈词成为侦办和处理案件的关键。所谓“闾阎巨细争斗事件,无不投知地保。地保既经查验,则两造之曲折周知,虚实轻重自有公论……是地保之报词乃案中之纲领也。”(88)“命案取尸亲或地保报呈。”(89) 甚至一些地方幕僚处理命案,直接“先传地保严讯确情,再行按名查拘凶徒”。(90) 在刑事案件判决中,地保作为不可或缺的干证方,其叙供至关重要。“凡看案须先分层次,命案先叙地保原禀。”(91)“叙次先地保而后邻证,及轻罪人犯,末则最重人犯,即常格也……此即案中前后层次之法也。”(92)
第五,查盗起赃。缉捕盗贼是州县官的重要职责,在清代,重大窃盗案要求地方官限期审结,举凡州县长官对于弭盗和捕盗均不遗余力。(93) 因此,熟悉地方原委的地保往往被赋予查盗、捕盗任务。一遇窃盗发生,即“发内票着地保查起”。(94) 地保还负有起赃职责,所谓“地保起赃到案,将物件点明封寄内署,立传事主到案逐一供明”。(95) 另外,审理盗案,亦须“取地保甘结,加印钤报”。(96)
第六,“另户”监管。所谓“另户”主要指游惰、惯盗、匪犯等素行不法之人户。由于“各居民不屑为伍,即行摘出,别立一册”,这种册籍被称作“另户册”、“弃民簿”等,其有别于保甲所编制的良民“烟户册”。(97) 在清代,“另户”多由各地地保收管,“凡差使往来罚充供役,该地但有失事即于此辈根求”。地保并定期“降该户等有无改悔情事,赍册送县,以凭稽察示惩。”“如实系改悔”,经保结方准入甲为良。(98)从相关资料看,清代地保监管“另户”在不少地方均被付诸实践。如乾隆《永清县志》将地保视为“稽其宵小为非法者”,所谓“宵小”当为被监管的“另户”人员。(99) 《刑幕要略》云:“凡窃贼详立册籍,发交地保人等领回,照例使其充警缉盗”,“能悔过自新并缉获盗贼,例准起除刺字,可复为良民。”(100) 乾隆间,浙江省曾推行“以贼捕贼”之法,凡盗贼“另交该地地保管束,毋致走脱”,并令其“挂铃带枷,充警巡缉”。(101)“如有改正自新者,许本犯自向地保说明,取地保甘结禀明开除。”(102) 甚至官府为了防止窃贼重操旧业,对于开释窃贼“苦无生计,即当堂酌给每名钱一二千文交与地保,作为肩挑买卖资本。仍按卯带县查点,察看两年。心果坚定,准其亲属、地保切实保结,令其安业”。(103)
综上所述,清代地保之役十分繁杂。总体而言,雍正、乾隆间,随着里甲的崩溃,地保在清初弭盗安民职能基础上,又被赋予催征钱粮、支应官差等民事事务,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是一种“以乡人治其乡事”的民间职役。乾隆以降,地保逐步向全面承值乡里差役演变,并随着清代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地保既治其乡,又役于官。其性质亦日趋从乡里职役向官府吏役转化,成为官府的“驻乡代理人”。(104)
四、地保的地位
清代地保的社会地位低下。如嘉道间,历任地方长官的王凤生曾强调:地方自治性的乡长等“不得视同地保,令其点卯接官及催粮派夫”。(105) 晚清冯桂芬亦视地保为贱役,流品在平民之下。(106)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地保在职能上日趋侧重于协助官府,履行对地方刑事和治安的管理,因此,清代一些幕僚往往将地保、衙役等合称为“在官人等”,(107) 视其“与在县之皂隶、民壮等役无二”。(108) 显然,将地保与官府胥吏同列。而明清时期,大凡为胥吏者,其社会地位难以受到民众肯认。如在明清徽州,人们对基层胥吏的社会评价亦很低。《茗州吴氏家典》中即规定“子孙毋习吏胥”。(109) 不但一些宗族蔑视吏胥之职,在整个徽州,地方社会习惯将胥吏与“狡狯”并称,甚至否定其社会地位。所谓“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流辈”。(110) 与胥吏情形颇为相似的是,在徽州,民间亦视地保为贱差。如《南屏叶氏家谱》有:“族内不收义子;婚嫁不结细民;子弟不为优隶;不充当地保,违者斥逐”。(111) 可见,南屏叶氏将充当地保,与收继异姓、联姻小户、卖身为仆等为传统族规家法所不齿的低贱行为相提并论。显然,民间视地保同于胥吏,自好者多不屑为之。
其次,清代地保的社会地位低下,当与充任者的身份有关。如上所述,清代地保主要是按自然村庄为单位而设置的,那么,在基层乡村,地保一役是如何选任的呢?起初,由于地保职能侧重于催征赋役和官差支应,为确保催征和应官的顺利实现,不少州县仍采取过去佥选里长的方式,或要求地方殷实之户承充此役,或经由地方佥选,轮流充任。如乾隆间,“浙西杭嘉湖三府属州县,将地保一役不许乡中无业之人充当。每岁底择图中田多殷实之良民,号曰‘殷户’,押令充保。”(112) 另据《庐乡公牍》载:该地如“平蘭社”、“西馆社”、“店上社”等村社的地保,采取按族姓(如“平蘭社”按潘、于二姓)或房派(如“西馆社”系赵姓村,地保“向归老三支充差”)轮流充任。每年系经地方公议并上报,嗣经县刑房书吏禀复认可后方能赴任。(113) 然而,随着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丁役甚轻,且可因当差而得到官府不少便宜。故愿充役者甚众。”“自书吏以下,诸役既庇官事,亦养身家。在民每愿为承差。”(114) 因此,随着地保在职能上由职役向官差的转变,一些地方任者“恋差不舍”,(115) 地保之差日益成为“乡中无业之民愿充此役者”的专利。(116) 他们熟悉地方原委,仰承官府鼻息,仆仆奔走于民间。加上官府依赖地保对地方游惰、惯盗、匪犯等素行不法之“另户”的监管,使其长期与“另户”为伍,这一切,难免不被“良民”视之为不齿的“另类”,从而,对地保的充任出现了“贤者不为,为者不贤”的局面。
再次,清代地保地位低下,亦与其劣行有关。地保之充任者,多以欺瞒贪索而混迹民间。地保作为清代地方的一种差役,官府不负担工食。其收入来源大致有:(1)官府酬劳。如乾隆十四年(1749),浙江省“酌定缉捕事宜”规定:“地保人等首报(罪犯)得实,同(捕役)一体给赏”。(117) 嘉善县亦规定:“地保等分段巡查居民,挨户支更……视其所管区内有无失窃之案,分别功过。如功至三次者,赏给银牌。过至三次者,提案重比。浮于三次之外者革役另募,准其功过相抵”。(118)(2)欺瞒贪索,私敛钱财。《庐乡公牍》中有不少案例与地保贪索有关。如“地保赵仁山名为慎重差务,其实觊觎地产”而致业主讦告官府。(119) 地保勾结胥吏讹索“宫焕文银十两有奇”。(120) 又如,休宁县“陈九春等开场聚赌,既经该县亲拿,地保竟敢得贿纵逃”。(121) 《牧令书》载:在地方官府“平粜官米”中,地保为骗取官米,卖钱渔利,其所报户口“率多捏冒”。(122) 地方赌博,地保“明知不问,抑且与为朋伙”,并在地方演戏中,“地保、棍徒动辄敛钱”(123)《得一录》中亦载:嘉庆十九年,苏州“放生官河,永禁采捕”,而该处“地保人等,得其规利,代为包庇”。(124) 凡此种种,有关清代地保假公济私的相关记载十分常见,其地位自然难以得到地方民众的肯认。
五、结语
综上考述,关于清代地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地保的起源,与清代里甲的衰退,保甲的代兴紧密相关。有清一代,尽管国家不断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度,但实际上,许多地方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正如晚清冯桂芬所云:清代除了皇帝和地方官员发布的一大堆强调保甲制的命令外,保甲很少实行过,在实行了保甲制的那少得可怜的场合,也没有产生什么实效。(125) 瞿同祖亦认为:清代除了王凤生、叶佩荪、刘蘅等少数官员因力行保甲而闻名外,清朝历代帝王不断要求整顿保甲组织,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各地推行保甲不力的现实。(126) 因此,里甲崩溃后,不少地方的保甲因推行不力而徒有其名,正所谓:官方以保甲行乡治,而民间以乡治代保甲,此种情形相当普遍。从而在基层社会出现名目繁多的乡地职役,其中,尤以地保(地方)设置最为常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保的普遍设置乃是清代保甲制度流变的产物,不过是保甲制度推行不力之次生形态而已。
第二,地保的设置既有普遍性,又有区域性特征。在北方(如华北),普遍存在乡地组织。(127) 其管理人员名目繁多,地保仅是乡地管理人员之一。地保在北方更多地被称作“地方”,所谓的“乡保”、“乡地”,均包括地保或地方。在南方一些地方(如上海、江浙、徽州、江西、广东等地),乡(都)—图—村构成基层的区划形式,按图设置地保颇为常见,因此,地保多被称为“图保”、“图正”。另外,对于宗法制度强固的地区,地方宗族往往以组织化的形式应对官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保的职能。如在“最重宗法”的明清徽州,宗族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地保乃至胥吏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功能远不及宗族组织。史载:“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巨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128) 关于地保设置的区域差异,笔者将撰文另作讨论。
第三,地保的普遍设置,加强了清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代叶佩荪在《饬行保甲》中曾云:“夫州县所领一邑人户不下百十万计,若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四境之奸良,虽有长材,势难尽悉。”(129) 可见,清代推行保甲的目的是为了深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很多地方在保甲推行不力的情势下,按自然乡村聚落为基础而设置地保等役是各地普遍的做法。地保的设置,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里甲或保甲那种理想化的行政编制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代政府面对人口快速增长和频繁流动的现实,而有效转变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方式,反映了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第四,清代地保的产生是以里甲向保甲嬗递为背景的,其职能既有继承性的一面,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变迁的一面。清初地保继承了明代以来保甲组织的“弭盗”职能。雍乾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和里甲组织的彻底崩溃,地保又被赋予催征钱粮、支应官差等民事事务。这一时期,地保作为一种正式职役名称出现于“谕旨”等官府文件,且不少方志关于这一时期地保的记载,更多地被放在“赋役”条目中,即是证明。总体来看,清代地保的职能大体经历了从弭盗安民到全面承值乡里差役的演变,而从乡里职役向官府吏役转化。
[收稿日期]2009-01-08
注释:
① 参见萧公权(Kung- chuan Hsiao):《乡土中国:十九世纪的帝国统治》,西雅图,1960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② 佐伯富:《清代の乡约·地保につぃて——清代地方行政の一出》,《东方学》第28辑,1964年。
③ 斯威特:《从福建教案中来看地保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清史问题》1976第6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234~241页;王福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载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41页。
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45页。
⑤ 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⑥ 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历史研究》2001第6期。
⑧ 孙海泉:《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⑨ 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第七章,汲古书院2002年3月发行。
⑩ 陈朝君:《蒞蒙平政录·为特设牌坊以靖疆界等事·为严格保甲册费以恤穷民事》,康熙二十八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701、780页,黄山书社1997年版(下同)。
(11) 潘月山:《未信编》卷4《刑名下·发落》,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93页。
(12) 陈朝君:《范蒙平政录·为通饬详陈预筹积储悉心条议以备采择事·为盘诘匪类稽查流民以靖地方事》,康熙二十八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726、780页。
(13) 潘月山:《未信编》卷4《刑名下·理人命·理盗案》,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98、117页。
(14)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9《缉逃》,《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422页。
(15)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看须知》;卷14,《检验》,《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241、373页。
(16)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4《承事上司》,《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262页。
(17)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9《立局亲审》,《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320页。
(18)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2《问拟余论》,《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346页。
(19)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7页。按:又见同书第629页。
(20) 瞿同祖先生即认为,清代“地方”即“地保”。参见瞿氏的《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从相关材料来看确有此种情况。至清代中期,“地方”之役的名称仍然存在,其职役性质和“地保”亦基本相同,甚至存在二者叠相为称之情形。如在清代天津相关土地买卖契约的署押中,“地方”、“地保”的称谓颇为常见,并可见同一人氏如“邵永祥”,既称其“地方”,亦称之“地保”。见刘海岩主编:《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9、56页。
(21)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2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下同),第416册,第92页。
(22) 《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176之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23册,第821页。
(23) 《畿辅通志》卷6《诏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04册,第106页。
(24)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67《兵部·发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19册,第624页。
(25) 《大清律例》卷23《盗贼上·强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72册,第722页。
(26) 《皇朝通志》卷88《食货略八·平粜·常平仓》,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5册,第275页。
(27) 徐栋:《保甲书辑要》卷3《广存》。
(28)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户口·编审》。
(29) 《清高宗实录》卷911,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壬午条。
(30) 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1) 以上各种职役的称谓名目繁杂,究其原因,与各地推行保甲制度力度和具体做法的差异有关。
(32) 何耿绳:《学治一得录·整饬捕务并拟弭盗清盗禀》,《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685页。笔者按:这里所谓的“乡约”是一种职役,与讲约制度的“乡约”不同,讲约“乡约”是一种组织和制度之称,该组织中力宣教化的人通常被称作“约正”、“约副”。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页。
(33) 民国《仓县志》卷11《方舆志,疆域》。
(34)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5《告示·一件晓谕业主速行赴局推收毋得观望自误事》,《官箴书集成》第4册,第142页。
(3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编·乡治与保甲》),中华书局,1986年。
(36) 民国《德清县志》卷1《舆地志·区分》。
(37) 乾隆《淄川县志》卷3《赋役》。
(38) 《重刊永清县志·刑书第五》,民国重刊本。
(39) 张谐之:《办理乡甲禀》,《碣阳乡甲小试录》卷首,光绪刊本。
(40) 民国《宝应县志》卷2《铺庄》。
(41) 恽敬:《新喻东门漕仓记》,《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3。另据《上海道契》可以看出,近代上海为管理土地事务,亦普遍于图中设置“地保”。
(42) 宣统《太仓州志》卷7《赋役·徭役》。
(43) 同治《湖州府志》卷4《疆域》。
(44) 如清代徽州府所辖六县之下,其行政区划即为以都辖图,以图辖村。参见道光《徽州府志》卷2《舆地志·乡都》。
(45) 《清文献通考》卷24《职役考四》。
(46) 徐栋:《牧令书》卷11《赋役·催科》,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211页。
(47) 民国《广宗县志》卷7《财政略》。
(48) 乾隆《淄川县志》,《建置志·乡村》。
(49) 乾隆《巴县志》卷3《赋役志》。笔者按:在清代一些地方,“地保”、“地方”仅是乡地组织职役之一。参见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另外,乡地组织中的其它职役的名目繁多,各地不一。所谓的“乡保”、“乡地”,均包括“地保”、“地方”之役。
(50) 乾隆《大名县志》卷9《赋役志》。
(51) 运泰:《临析归并大粮总征分解详稿》,康熙《章邱县志》卷10。
(52) 王凤生:《保甲事宜》,见徐栋:《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上》。
(53)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13《札饬武阳通图合办地保案由》。
(54) 庄纶裔:《庐乡公牍》卷1《上抚宪袁请禁止平度州教民冷受谦越境敛钱禀》,《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38页。
(55) 徐栋:《牧令书》卷20《缉暴·粤东风俗之坏莫过于械斗》,《官箴书集成》第7册。
(56) 徐栋:《牧令书》卷16《教化·义学条规》,《官箴书集成》第7册。
(57) 余治:《得一录》卷2《保婴会规条》,《官箴书集成》第8册。
(58) 余治:《得一录》卷十一,《禁串客淫戏告示》,《官箴书集成》第8册。
(59)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2),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第22页。
(60) 王凤生:《保甲事宜》,《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上》。
(61) 徐栋:《牧令书》卷13《畴荒中·浙江湖郡酌办赈务事宜》,《官箴书集成》第7册。
(62) 《治浙成规》卷5《臬政》,《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522页。
(63) 《治浙成规》卷8《臬政》,《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669页。
(64) 徐栋:《牧令书》卷19《刑名下·勘丈》,《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453页。
(65) 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卷30,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119页、378页、385页、410页。
(66) 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卷30,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
(67) 褚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上,《批阅呈词》,《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742页,第751页。
(68) 庄纶裔:《庐乡公牍》卷2《详县民孙兰馨府控张尚谟案详文》,《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64页。
(69) 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官箴书集成》第4册,第769页。
(70) 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9页。
(71) 《休宁首村朱氏文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72) 徐栋:《牧令书》卷22《事汇·河南永城县捕蝗》,《官箴书集成》第7册。
(73)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2(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92页。
(74)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176之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739页。
(75) 徐栋:《牧令书》卷13《畴荒中·赈恤》,《官箴书集成》第7册。
(76) 徐栋:《牧令书》卷13《畴荒中·赈荒简要》,《官箴书集成》第7册。
(77) 余治:《得一录》卷8《施棺代赊条约》,《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597页。
(78) 余治:《得一录》卷4《冬月恤丐条约》,《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517页。
(79) 余治:《得一录》卷16《每冬栖恤老病元依说》,《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722页。
(80) 余治:《得一录》卷13《沪城抚教局条规》,《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679页。
(81) 余治:《得一录》卷4《楼流公局规条》,《官箴书集成》第8册。
(82) 徐栋:《牧令书》卷19《刑名下·论命案》,《官箴书集成》第7册。
(83) 褚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上《假命讹索》,《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746页。
(84) 刘衡:《庸吏庸言》卷上《嚴禁藉命擾害及賞格告示》,《官箴书集成》第6册。
(85) 《庐乡公牍》卷3《居腾和等具保展正仁呈批》,《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95页。
(86) 《庐乡公牍》卷2《移即墨县程商订缉票办法移文》,《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67页。
(87) 徐栋:《牧令书》卷19《刑名下·命案相验》,《官箴书集成》第7册。
(88) 王又槐:《办案要略·论详案》,《官箴书集成》第4册。
(89) 《刑幕要略·人命》,《官箴书集成》第5册。
(90) 徐栋:《牧令书》卷18《刑名中·访案》,《官箴书集成》第7册。
(91) 徐栋:《牧令书》卷17《刑名上·窨断》,《官箴书集成》第7册。
(92) 王又槐:《办案要略·叙供》,《官箴书集成》第4册。
(93)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94) 《幕学举要·盗案》,《官箴书集成》第4册。
(95) 《刑幕要略·盗贼》,《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3页。
(96) 徐栋:《牧令书》卷19《刑名下·害理盗案》,《官箴书集成》第7册。
(97) 笔者按:据叶世倬云:“另户”源于明代王阳明所倡导的“弃旧图新簿”。参见叶世倬:《为编审保甲示》,徐栋:《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上》。
(98) 参见王凤生:《保甲事宜》、《弭盗条约》,徐栋:《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上》、《成规下》。
(99) 《重刊永清县志·刑书第五》,民国重刊本。
(100) 《刑幕要略·盗贼》,《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3~14页。
(101) 《治浙成规》卷6《臬政》,《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548~549页、591页、661页。
(102) 徐栋:《牧令书》卷20《缉暴·弭盗详议》,《官箴书集成》第7册。
(103) 徐栋:《牧令书》卷20《缉暴·清贼源》,《官箴书集成》第7册。
(104)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05) 王凤生:《约正劝惩条约》,徐栋:《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下》。
(10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复乡职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
(107) 《刑幕要略·断狱》,《官箴书集成》第5册。
(108) 《治浙成规》卷2《藩政二》,《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87页。
(109) 《茗州吴氏家典》卷1《家规》。
(110) 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111) 《南屏叶氏家谱·祖训家风》,清刊本。
(112) 《治浙成规》卷2《藩政二·禁止勒派殷实农民生监充当地保庄长》,《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87页。
(113) 《庐乡公牍》卷3《潘茂具控于振忠案堂判》、《宋裕谦控林升案堂判》;卷4《赵乃春控赵乃榛案堂判》。《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634页、第608页、634页。按:《赵乃春控赵乃榛案堂判》中“地保”被误作“地方”,参见第648页勘误。
(114) 江士杰:《里甲制度考略》,载《民国丛书》第4辑,第23册,第60页。
(115) 《庐乡公牍》卷4《潘茂兴起控于振忠案堂判》,《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634页。
(116) 《治浙成规》卷2《藩政二》,《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87页。
(117) 《治浙成规》卷6《臬政·酌定缉捕事宜》,《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548~549页。
(118) 《治浙成规》卷8《臬政》,《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661页。
(119) 《庐乡公牍》卷3《刘杨氏控赵仁山案堂判》,《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605页。
(120) 《庐乡公牍》卷3《宫焕文控宋廷栋案堂判》,《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610页。
(121) 刘汝老骥:《陶甓公牘》卷7《祁门县监生胡舜传呈批》,《官箴书集成》第10册。
(122) 徐栋:《牧令书》卷13《畴荒中·平耀事宜》,《官箴书集成》第7册。
(123) 徐栋:《牧令书》卷16《教化·敝俗》,《官箴书集成》第7册。
(124) 余治:《得一录》卷7《放生官河條约》,《官箴书集成》第8册。
(12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
(126)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5页。
(127) 参见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孙海泉:《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等等。
(128)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
(129) 叶佩荪:《饬行保甲》,徐栋:《保甲书辑要》卷2《成规上》。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乾隆论文; 组织职能论文; 雍正论文; 康熙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