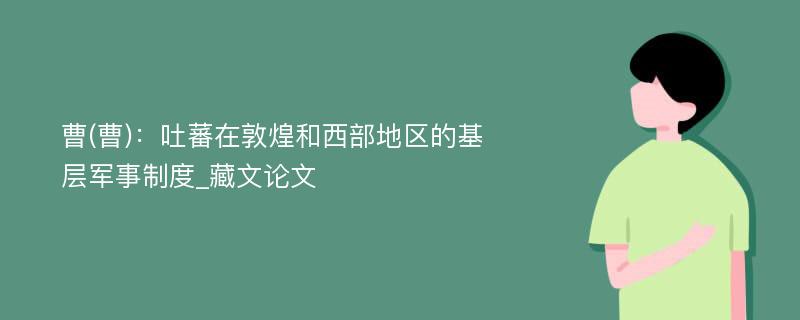
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西域论文,敦煌论文,兵制论文,基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兴起于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曾一度攻占和统治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达百年之久。本世纪初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就反映了唐代吐蕃统治上述地区的军政机构、部落名称、经济制度等情况。其中,藏文术语Tsh ar反映的是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笔者初步认为此术语来源于汉文的“曹”。以下试证之,供治敦煌学与新疆史的同行参考。
一、记载Tshar的藏文文书
就笔者目前的统计,本世纪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三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中,共有17件文书记有Tshar这个术语。其中,敦煌莫高窟1件,若羌米兰遗址1件,和田北面的麻扎塔克15件。
因敦煌出土的这一件,反映Tshar的情况比较完整和典型, 故先引出如下:
编号:Ch.73,XV,10(fr.12,vol.69,foll.62—3),写卷;规格:76×15厘米;首残,存文字53行;汉译文如下:
曷骨萨部落中翼、孙补勒支主从四十人,一曹(Tshar)之本籍表。
曷骨萨部落安则亨,主;与右小翼张卡佐之旗手汜崑哲相衔接。
曷骨萨部落,僧董侗侗,主;曷骨萨部落张华华,从。
曷骨萨部落,僧钟忱忱,主;曷骨萨部落张崑哲,从。
曷骨萨部落张淑淑,主;曷骨萨部落张白娣,从。
曷骨萨部落段客四,主;曷骨萨部落韦空空,从。
曷骨萨部落,僧董卜蛮,主;曷骨萨部落金礼客,从。
曷骨萨部落,僧张禄勤,主;曷骨萨部落金崑英,从。
曷骨萨部落,僧张皮皮,主;普光寺寺户曹泽泽,从。
曷骨萨部落段亨谷,主;曷骨萨部落辛节节,从。
曷骨萨部落薛空,主;曷骨萨部落薛崑崑,从,持手。
曷骨萨部落折逋勒,主;曷骨萨部落张忱忱,从,煖员。
曷骨萨部落王可勒,主;曷骨萨部落张相泽,从。
曷骨萨部落,僧张拉启,主;曷骨萨部落金亨泽,从。
曷骨萨部落,僧曹逵逵,主;曷骨萨部落张娣成,从。
普光寺寺户郝朝春,主;曷骨萨部落王忱新,从;灵图寺(?)寺户王崑泽,从。
曷骨萨部落王勤新,主;曷骨萨部落董旺多,从。
曷骨萨部落,僧李金昂,主;曷骨萨部落薛忱因,从。
曷骨萨部落张泽泽,主;曷骨萨部落张更子,从。
曷骨萨部落,僧空泽,主;曷骨萨部落钟子成,从。
曷骨萨部落钟子新,主;……〔1〕。
以上从“安则亨”始,至“钟子新”止,共计40人,为一“曹”(Tshar)之人数。
米兰遗址出土的载有Tshar一词的木简,编号为:M.I.Xii,3;规格:9.5×2厘米,右边有一系孔,文字一行:
曹长(Tshar dpon):潘库将头(Pang kuv tshan)〔2〕。
此件反映出Tshar的官吏称为“曹长”, 且与吐蕃的另一基层组织“将”有交错任命的情况〔3〕。
和田麻扎塔克出土的这一部分,有写卷10件,木简5枚, 共记载有46个地名后缀有Tshar这个术语。因篇幅限制, 以下仅举出两件较典型的写卷进行介绍:
写卷M.tāgh.b,i,0095,对开本第36号;285×8厘米;常见草书体,反面5行,正面5行,字迹不同:
在……克则,两个吐蕃人,两个于阗人。
在达则元弃古觉,三个吐蕃人,[即]仲巴(Grom pa)部落的男子则孔,娘若(Myangro)部落的洛郎墨穷,蔡莫巴(Rtsal mo pag)部落的纳雪塔桑。
在叶玛朵克则, 两个吐蕃人, 一个于阗人, [即]雅藏(Yangrtsang)部落的普米克通,俄卓巴(Vo tso pag)部落的索迪科,坚列曹(jam nya tshar)的于阗人则多。
在于阗玉姆(Ho tong Gyu mo),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即波噶(phod kar)部落的……〔4〕。
写卷M.tāgh.a,i,0031号,残,形制稀见;对开本第3号;最长与最宽为16×21厘米;常见草书体16行,字残:
哈班曹(Ha ban tshar)……。
……部落,拉桑,于阗人……。
……卓特曹(Dro tir tshar)的于阗人仆蔡……。
……布[赞]部落的洛萨密……。
……在突厥州(Dru gu cor),桑(Shang)部落之吐谷浑(Va zha)……。
……部落之于阗人叶耶……;……罗噶列曹(Nos go nya tshar)之于阗人楚[穆]……;……巴麻诺列曹(Bar mo ro nya tshar)之于阗人比得;……曹(Tshar)……。
……在贝玛,仲(Vbrom)部落之卓塞塔……;卓特曹(Dro tirtshar)的于阗人库苏;……依隆街区之……;拉若列曹(Las ro nya tshar)的于阗人琛格;……之于阗人……;……达孜曹(Dar ci tshar)之……;……哈罗列曹(Has ro nya tshar)之于阗人贝……;……曹(tshar)之于阗人希尼……〔5〕。
在这里,前面缀有于阗小地名的“曹”(Tshar), 是与“仲巴”、“雅藏”等吐蕃部落名称相间在一起的〔6〕, 从前者派出的于阗人,与从后者派出的吐蕃人同在一处巡逻、守卫。而且,与“曹”有关的均是于阗人。
二、国外藏学家对Tshar一词的考释
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学者F.W.托马斯、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日本敦煌学学者藤枝晃三人,对Tshar 一词的含义及其所指的组织的性质进行过探讨。
在译注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时,托马斯对于Tshar 这个术语并没有作出考释,他只是照搬了这个词的转写体。但当他稍后在译注于阗地区的藏文文书时,就不得不对大量遇到的地名后缀有Tshar 的情况进行解释。他提到:术语Tshar出现在一些残破和难以辨读的文书中, 这些文书看来是驻扎在各地的兵士或官吏的名单。这个词或许可以被解释为部落的下属组织;但是就在同一件文书中,有一个词yul yig(地区名册),因此由吐蕃军队的分布地域看来,可能是有部落的情况下,tshar的区域含义就是“教区”。这个词好像不是出自藏语,而是于阗语,因为凡与tshar有关的人都是于阗人。也许最古老的于阗圣地赞摩(Tsarma)寺,其寺名的含义就是“下教区”〔7〕。
托马斯把Tshar一词看作是藏文拼写的于阗语, 这种观点并没有多少依据,只要看一看在米兰和莫高窟的藏文文书中同样出现了Tshar 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所以,在1955年出版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三卷中,托马斯对自己以前的看法作了一些修改。他说:Tshar一词看来是出自某地方土语, 这个词或许就是梵文的simā,后者曾出现在佉卢文书中。但由于tshar这个词又出现在于阗以外的罗布泊和敦煌地区,已经超出了于阗的地区范围;那么,只能就于阗地区来说,tshar可能相当于于阗文的sārstai。当然,即使这种 联系能够成立,藏文tshar也只是一种不完整的拼写形式〔8〕。
确实,于阗塞语专家贝利和恩默瑞克,均未提到sārstai相当于藏文tshar,或说tshar一词借自于阗文〔9〕。根据贝利的观点, 于阗文sarstai一词可释为“神龛”、“圣祠”或“遗殿”。显然,托马斯在 藏文tshar与于阗文sārstai之间所作的联系,是建立在《于阗国授记》用tshar一词称小规模宗教场所的基础上的〔10〕。因而,他自己也感觉到如果超出了于阗塞语使用的范围,譬如像在敦煌和罗布泊地区,就只好另当别论了。
第二个注意到Tshar这个术语及其所指代的组织的性质的, 是匈牙利有名的藏学家G.乌瑞。他在《关于敦煌的一份军事文书的注释》一文中,重新注释和详尽地讨论了本文前揭Ch.73,XV,10号藏文写卷。 关于Tshar一词,他没有理会托马斯将其译作“教区”的观点, 而尝试把它译为“队”。他提出,Tshar所代表的组织是一种领地防卫部队, 它具有半军事化半行政化的特点。由于这份像是征兵表的文书上竟然还提到了寺户,可知他们也要被迫服兵役的。而且名册中还包括佛教僧侣。这件不仅包括有曷骨萨部落管辖下的各阶层的人物,而且还包括该部落中所有寺庙的僧侣和寺户在内的Ch.73,XV.10号文书,无疑是一份具有军事性质的士兵注册名单〔11〕。
也就在乌瑞发表上述文章的同一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他发表的《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一文中,用日文全译了Ch.73,XV.10号文书。他为此文书取名为《编成表》,认为是军队或者力役的编成表一类,其中每队由40人组成,每二人以主、从相组合。而且,从僧人的前面仍冠有“曷骨萨部落”的字样,与吐蕃统治初期置有僧尼部落比较来看,这件《编成表》的写成时间当在吐蕃统治中期,即公元9 世纪初的一二十年内〔12〕。
三、Tshar相当于“曹”
上述三位外国学者并没有解决Tshar一词的语源问题。 托马斯将其译作“教区”的观点,超出于阗塞语使用的范围就不再适用;乌瑞释为“队”,也仅仅是参考了现代藏语中这个词的含义,而未探究其由来与演变。藤枝晃则干脆就撇开这个词的含义本身,去探讨它的人员组成情况和组织的性质。
笔者认为,由于藏文Tshar这个词在同一时期出现于敦煌、鄯善、于阗这三个地方的文书中,它就不大可能是从于阗塞语或是从佉卢文中借来的。其所出自的语言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这种语言能够在上述三个地区流行,是一种官方语言或是一种交际用语。在唐朝中后期,能够满足这种条件的只有汉语和藏语,由于我们在同一时期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唐蕃会盟碑》等文献金石中没有找到Tshar这个词, 因而就只好认为它是一个汉文借词“曹”。Tshar 与“曹”不仅在音韵对勘上比较完整,而且前者所代表的军事组织性质也与后者相当,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因为前者正是吐蕃受唐朝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影响的结果之一。
首先来看“曹”的中古音,根据《广韵》,它是从声豪韵,拟定出来就是Tshau〔13〕。但由于藏语没有复韵母, 要把“曹”这个音拼写成藏文,就只能把-u这个复韵母变化为-r。关于汉字复韵母-au、-uo拟为-ar、-ur的例子,在古藏语中还能找得到。如汉语“樱桃”,在《华夷译语》中,藏文音译转写为’an-dur,“桃”的韵母与曹相同为“豪”(-au),这里却被变化为-ur。另一个例子是藏文的gur(朝代), 有学者认为它是从汉语的“国”字来的,“国”的中古韵为-uk、今韵为-uo,在藏文中被音译转写成了-ur〔14〕。因此, 从音韵上看, 藏文Tshar来自汉语的“曹”是没有障碍的。
从唐朝在敦煌及西域东南部各地的兵制设置来看,是有“曹”这一级组织的。而且,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吐蕃时期汉文文书中,可看出当时还沿用了“曹”这一称谓。如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就有“弟嘉珍,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之文;P.2763背《吐蕃已年(789)七月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吐蕃午年(790)三月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中, 有“仓曹汜”、“仓曹杨[恒谦]”的具名〔15〕。
鄯善在唐以前是有“曹”这一基层组织的,如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就有“仓曹”、“兵曹”、“水曹”的记载〔16〕。稍晚一些的佉卢文书中,有apsu一词,被研究者译为“曹长”〔17〕。入唐以后,曾于上元二年(675),改隋之鄯善镇为石城镇,隶沙州〔18〕。按照唐朝的兵制,镇有镇将、镇副、录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等职官〔19〕。石城镇既隶属沙州,其镇将及下属官吏的设置应同于后者,有仓曹、兵曹之设是当然的。
唐代于阗的情况类似于鄯善。同样是在上元二年,唐朝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属州先是5个,后改为10个。 史籍中虽不见这些州的名称,但其城镇的名称和所在却是清楚的。如《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下:“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东有且末镇。西南有皮山镇”。这里的镇、守捉均是一级军事机构所在地,有从内地征发的精兵和土著民兵驻守〔20〕。镇有镇将及仓曹、兵曹等,这已见上述。
唐朝于鄯善、于阗地区设镇,以镇将领仓曹、兵曹等诸将吏,这就为吐蕃在占据这些地区后,仍仿照唐制组建基层兵制“曹”(Tshar)准备了条件。根据已有的研究得知,唐代吐蕃在统治河西、陇右及西域东南地区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机构来取代或模仿唐朝的州县制度,如以将军充任节度使,以节儿论为刺史,千户长约相当于县令,小千户长相当于乡长,百户长相当于里正〔21〕。 基于此, 吐蕃又以曹(Tshar)来组建和称呼统治区内的准军事组织,这是十分自然的。
另一方面,不仅是Tshar与曹在音韵上相近,唐朝曾在敦煌、 于阗等地设立过曹这种组织,就是藏文文书反映出Tshar的性质, 也与曹(尤其是兵曹)的组织特征、任务是相同的。《唐六典》说得很明白:“兵曹掌防人名帐,戎器、管钥,差点及土木兴造之事”,对照于此,前文所引敦煌、于阗的藏文文书,不正好是“防人名帐”或差点用的名册么?再说,将米兰出土的那枚藏文木简上的Tshar dpon译为“曹长”也十分贴切。前文说过,佉卢文书中有“曹长”之称,而这一称呼在唐代还十分流行,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22〕。这里虽然记载的是朝官们相互之间的谦称,但它却真实反映了下层官吏的情况。吐蕃既已沿袭唐朝基层兵制“曹”这一建制,一曹之长自然也要依汉制称为“曹长”了。
至于《于阗国授记》中提到的三千余处小规模的宗教场所称作Tshar的问题,也当是与“曹”这个基层建制的分布广、数量大有关的。因为不管《于阗国授记》记载的是9世纪以后的或者是9世纪以前的于阗王统,当时的大、小寺庙和小龛均应是佛教徒活动的场所,而以数十人为一曹的居住点或驻守地中设有一龛,作为礼佛的场所是十分自然的。如要统计这种非正式庙宇的场所,唯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将于阗地区当时分置的“曹”的数量合计起来,于是便得到了这种小规模宗教场所的数量,进而出于统计和称呼的方便,就以“曹”(Tshar)来指代这样的小规模的礼佛场所了。
注释:
〔1〕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Ⅱ,London,1951,PP.67—69;G.Uray,Notes on a Tibetan military documen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Hung,vol.XII.nos.1—3,1961,PP.227—228;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第三一册,1961年,第229—231页。
〔2〕〔4〕〔5〕〔7〕F.W.Thomas上引书,第338页;第173— 174页,第174—175页,第二卷,第169页。
〔3〕有关“将”与“将头”, 参见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二期。
〔6〕关于仲巴、雅藏、波噶部落, 参见杨铭:《唐代西北吐蕃部落述略》,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
〔8〕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Ⅲ,London,1955,P.60.
〔9〕H.W.Railey,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Asia Major,new series vol.Ⅱ part Ⅰ,1951,PP.4、27.恩默瑞克撰、荣新江译:《于阗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61页。
〔10〕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Ⅰ,London,1935,P.135。
〔11〕G.Uray,Notes on a Tibetan Military Document fromTun-Huang,Acta Orient.Hung,vol.XII,nos,1—3,1961,PP.223—230。
〔12〕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第三一册,1961年,第229—231页。
〔13〕丁声树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5页;陈复华编:《汉语音韵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43、180页。
〔14〕劳费尔著、赵衍荪译:《藏语中的借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印,1981年,第48、51页。
〔15〕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507—508页。
〔16〕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1、53页。
〔17〕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38页。
〔18〕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19〕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5—756页。
〔20〕详见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6页。
〔21〕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39页。
〔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