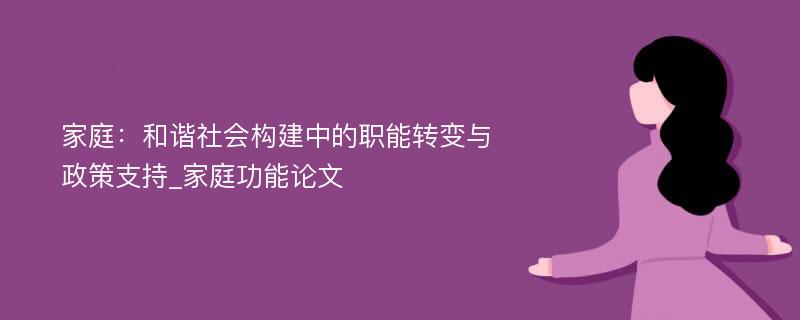
家庭: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变迁和政策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功能论文,家庭论文,和政策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4-0031-08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推助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家庭功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不少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或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策略、积极有效地迎接社会转型期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是众多家庭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而给予家庭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改善家庭的生态环境,也是公共政策和服务的一个新课题。
一、家庭在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变迁
1.经济保障作用增强
尽管政府采取了最低生活保障、廉租住房、奖学/助学/贷学金等经济救助措施,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险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但众多下岗、失业、投资经营失败、低收入、病残者仍主要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扶持,从而减少了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研究表明,城市家庭养老除了依靠制度性保障如离、退休金和社会救济外,主要由子女、亲属负担,农村更是主要依赖子女、亲属的经济支持;而生活照料在城乡都极少获得外部支持,主要由家人承担,其中儿媳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①。上海失业群体求职社会网络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大多数被访利用家人亲属强关系网找到工作②。我们日前对上海920个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家里经济拮据或需要调剂,老弱病残生活困难,或下岗、待业想找工作时,求助并获得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等亲属支持的比重和频率为最高。
由此可见,家庭的生活保障已成为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补充,在单位保障全面减弱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转型期,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在众多家庭尤其在一些处于市场竞争弱势的家庭显著增强,乃至成为抵御生活风险的“救生筏”。
2.养育功能的结构优化
家庭是目前社会所认可的生育子女、繁衍后代的合法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人口再生产的唯一社会单位③。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出生率持续下降,从数量上看,家庭的生育功能显著弱化。然而,人口再生产不仅要控制数量,更关注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生育数量的减少对优生优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所付出的经济、心理和机会成本比以往更高,家庭养育功能面临结构优化的转折。
3.儿童社会化功能削弱
家庭是人之初的社会化场所,与学校、社会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和终身性的特点。父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人、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与态度,家庭教育对子女是非、善恶、美丑观念形成的影响更直接、更大。然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父母外出工作的时间和双重负荷,以致不少儿童接受幼托机构和大众媒体教育的时间比与父母共处的时间还多,电视、电脑等传媒以其生动形象的视觉效果、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和新奇刺激的感官体验,日益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大众媒体对孩子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以及社会期待和适应的实际影响已不亚于父母。在现代信息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父母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往往失去资源优势和传承价值,他们的话语权地位下降,家庭在教化角色规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的作用显著削弱。
与此同时,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模糊甚至颠倒的“反向社会化”现象。年轻人凭借对新事物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以自己的信息量、知识面和社会适应能力优势获得了对日渐力不从心的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的话语权,在消费意向、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长辈④。
4.情感支持功用趋强
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的强化,首先在于物质生活质量提高后,家庭不再仅仅是经济共同体,而更多地满足成员随之提升的对感情生活、心理支持的需求,其次,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紧张、焦虑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理重负,当人们在职业舞台竭力拼搏、疲惫不堪、压力重重乃至伤痕累累之际,家庭无疑成为他们暂时远离尘嚣、逃避世俗的宁静港湾,是他们卸去双重面具而回归自然、享受轻松的温馨暖巢,再次,居住条件的改善使封闭型的独门独户住宅成为主流,邻里相见不相识,而社会竞争使亲戚朋友也多陷入紧张、繁忙之中,人际互动减少、关系疏离,家庭成员更多地期待私密空间的情感支持和相互陪伴,依赖家人的相互理解和关爱而减少生活压力。
5.性规范作用弱化
从婚姻制度的起源看,婚姻从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和规范人们性行为的功能。在一夫一妻制的背景下,婚姻是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⑤。随着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性观念趋向开放,性与婚姻分离的现象增多。一项对城市30岁以下未婚青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半数被访者有条件地赞成婚前同居⑥;对大学生所作的多次抽样调查也发现,有过性行为的在9%~11%之间⑦。最新一项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指出, 已婚男女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分别为21.2%和5.1%(其中经理、厂长、老板高达56.3%),20~64岁的男性承认有过性交易的占7.6%⑧。
然而,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性自主的意识有所增强,社会对非婚性行为的宽容度也有所提高,但仍有90%以上的人持有性忠诚的期望⑨,多数人仍认可婚姻是性行为的合理保障。况且,婚姻不仅规范人们的性行为,同时还是已婚者享受性快乐的温馨暖巢。随着性科学的普及和性文化环境趋向现代、开化,性在个人身心和夫妻生活中的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男女所肯定,性快乐和幸福主义的原则正日渐被认同⑩。
二、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所突显的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和社会分化,物质至上、消费主义以及高科技、信息化等所引发的各种困扰和压力都会延伸到家庭中来,使家庭面临巨大挑战。
1.社会竞争和分化递增,家庭关系调适难度加大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职业竞争激烈、工作节奏加快,不少人的就业和工作压力显著增大,投入家庭生活的时间和精力日渐减少。而职业流动的递增、终身教育的普及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一些夫妻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发生明显的分化,双方的价值目标、兴趣爱好、婚姻需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一致趋增甚至难以协调适应。加上因职业和地域流动导致的跨国、异地婚姻比重的上升,如全国涉外婚姻从1979年的8460对上升到2003年的78285对,上海的异地联姻比重已占结婚登记总数的近1/3(11)(这还没有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已取得本地户籍的外省市男女与上海人的联姻数)。而异质夫妻的婚姻幸福感明显低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或在各方面同质较强者,他们中离婚者更多,这一点也为不少研究所证实(12)。
由于市场经济更青睐青年人,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呈现未婚者明显高于已婚者,子女明显高于父母的新倾向(13)。而在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数字化的鸿沟也横亘在代际之间。父母与子女在价值目标、兴趣爱好、消费意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将不断加剧代际冲突。
2.物质至上主义流行,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加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物质和商品空前丰富,媒体和商业炒作不断地催化人们对物质追求和功成名就的欲望。消费文化的流行,使许多人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个人是否成功或家庭是否美满,将物质追求视为第一生活准则。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推销,那么任何东西都需要更新:我们要新车、新房子、新衣服,也许还有新的鼻子(14)。加上职业流动和不稳定的普遍性,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弱势家庭因其成员歇业/失业或重病等致贫,由经济压力引发的焦虑和困扰随之加剧。
3.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加重了家庭的赡养负担
2004年末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5%(15),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19.3%(16),到2010年将达22.7%,2040年更将占到40%以上(17)。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家庭规模日渐缩小,目前全国户均人口3.38人,上海仅2.81人(18);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则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程度还将加深。据我们对上海920个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56~65岁年龄段被访男女独居或空巢的比重分别为5%和31%,合计达36%,表明空巢家庭的生命周期已提前,数量明显增多。在独生子女家庭为主流的上海,不少子女为了学业/事业发展需要,短期或长期离沪外出学习或工作的比重趋升,加上众多年轻人婚后独立门户,父母独居速增也是必然的。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人口高龄化,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未来家庭的中青年夫妇将面临照料护理父母乃至祖父母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独居和空巢家庭的递增也使中、老年人的心理孤独和精神抚慰问题凸现。
4.离婚率上升使面临福利水平下降的单亲家庭递增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2000年的粗离婚率是1980年的近3倍,上海的离婚率20年间增幅达7倍(19),2004年全国共有166.5万对夫妻离婚(20)。尽管众多的离异男女将再婚,但每年100多万对夫妻离异以及因一方丧偶形成的单亲家庭无疑仍然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离婚、单亲依然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中国,承载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单亲男女将面临福利水平下降、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等问题,并不同程度地殃及孩子。已有的研究显示,单亲男女的在职状况、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等明显低于双亲家庭(21)。对上海和南京单亲家庭的调查显示,约5成不同居父母未承担子女抚养费,相当一部分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22)。另外,随着职业流动的频繁和单位保障制的弱化,作为家庭唯一劳动力的单亲父母的工作不稳定乃至无业,也将加剧一部分单亲家庭的困境或弱势。
三、创建和谐家庭,有效迎接挑战
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或不断继替的家庭成员始终生活在和谐、幸福的氛围中并非易事。在当前社会变迁加速的时代,家庭及其成员尤其要注重开发如下品质或作出如下努力,才能有效地迎接各种挑战。
1.多点时间与家人共处
按照美国家庭学者的观点,许多美国家庭最难开发的品质就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能力。技术和物质至上主义、消费主义使人们被迫去做更多的事、去拥有更多的物——为了抓住一切疲于奔命,个人幸福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这种环境的牺牲品,人际间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成为—下一个牺牲品(23)。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使人们少放些时间在工作上,而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多投入些时间(24)。
2.学习增进互动沟通的艺术
相互沟通是每个家庭成员每天都要面对的不可或缺的能力。奥尔森提出家庭成员间的沟通需要积极的倾听(包括移情和反馈)、语言技巧(包括谈自己和使用“我”开头的叙述而不是说别人)、澄清(包括交换清晰明白的讯息)、说话切题等技巧(25)。拉曼纳等认为婚姻冲突不应是破坏性的而应试图维护彼此的自尊,也称为聚合的冲突(bonding fight),诸如彼此真诚坦白,给予适当的回馈,将恼怒集中在特定的争端上而不要翻老帐,愿意改变自己,不争胜好强等(26)。无论是夫妻还是亲子,或是婆媳、翁婿、祖孙之间,都要增进相互沟通,多倾听对方的想法,多关注他人的需求。尤其要提倡父母耐心地聆听和理解孩子的心声甚至是离奇的想法,把孩子视作可信任的伙伴,了解他们的独特需求,平等地与他们一起讨论、说理和协商。有调查显示,翻看孩子私人物品、训斥打骂子女、过分干涉子女行为成了孩子“不喜欢父母”的三大缘由,尊重子女、平等地和孩子交流沟通、言行一致的父母最受欢迎(27)。
3.增加角色的弹性
在职业流动频繁、社会变动剧烈的今天,社会更推崇角色的独立和弹性。
首先,两性角色不宜定型化。当今社会女性跻身政界和管理层、男性乐于育儿持家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相当普遍、蔚然成风,性别角色的双性化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潮流。男女只有不拘泥于传统、不为刻板固化的性别角色规范所束缚,在顺应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性别角色,增加独立自主性和角色的弹性,才能真正实现夫妻的平等伙伴关系,实现两性的全面发展。
其次,角色的弹性还表现在及时转换社会和家庭的角色身份,既不要将王作中的紧张性压力或职位上的领导面孔和行为模式带回家,也不要让家庭压力或冲突的负面情绪蔓延到职业岗位。而应适时调整自己在家庭内外的不同角色,尤其在丈夫/妻子面前,应根据不同情景,经常转换角色身份,扮演或客串妻子/丈夫、妹妹/弟弟、母亲/父亲甚至女儿/儿子等角色,以满足配偶的不同心理需求,增进婚姻生活的新鲜感、情趣和满意度。
4.平衡代际互动的重心
祖辈和父辈对孩子的“众星捧月”和子代体抚、回馈亲代的疏略,儿童节的“热”和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的“冷”,折射出家庭中爱的天平向子女倾斜以及中国传统反哺模式的式微。
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以及高科技、信息化时代教育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父母对子女的过高期望和过度付出。随着抚育成本的攀升、社会保障的弱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双职工夫妇既要在孩子身上投入极大的经济、时间和心理成本(即使是成年子女的就业、继续教育、结婚乃至孙辈抚育也要依赖父母),还要不断适应紧张、快节奏的社会竞争,往往难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孝敬老人。而平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使社会日益面临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位以上老人的重负。因此,“重小轻老”现象的出现难以避免。现代社会应倡导成年子女的自立和家庭断乳,同时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的同时,鼓励中老年夫妻拓展自己的活动天地和需求目标,而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仅建立在子女的幸福上,以减少对子女的无限付出和过度依赖。
但在目前养老、医疗等保障、保险尚未全覆盖,一些老人尤其是农村众多老人的生活条件仍难以获得基本保障的情况下,中青年夫妇宜适当调整重小轻老的家庭投入和忽视父母需求、过于溺爱孩子的失衡策略,给予父母更多的嘘寒问暖、聊天陪伴和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支持或生活料理,使倾斜的爱的天平有所平衡。
5.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挫折和压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变迁,使不确定因素大为增加。而众多不确定因素、风险和变化,在激发现代人潜在的欲望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常诱发其紧张、焦虑和各种压力。
面对挫折和压力,一些家庭成员或怨天尤人、消极等待,或依然如计划经济年代那样奢望依赖单位和政府的包揽。其实,否认压力存在、消极等待、不作为只会使压力积聚甚至转化为危机。只有改变对挫折和压力的负性认知,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才能:(1)视危机为转机——因为挫折和压力在家庭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都是负面的,调适得当可将压力变为动力,并成为新的转机和起点,家庭成员也可在挫折中学习、成长;(2)增进成员间的沟通——家庭成员要在压力事件中,彼此交流个人内在的不安、焦虑、愤怒或各种矛盾的感受,而不是把家庭成员当作发泄的对象,藉以隐藏真实的感受;(3)对压力重新命名——通过对压力源的重新认识、澄清事件的本质与难度,对挫折和压力取正向定义,由此降低因事件带来的情绪紧张,鼓励家庭履行对成员提供社会与情绪成长的承诺,增加对压力的管理能力(28);(4)资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开发自身的优势,寻求、发展有效的亲属和社会网络的支持资源,通过提升家庭凝聚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相濡以沫地渡过难关,同时也使家庭在积极改变中减缓压力,复原和提升功能。
四、优化家庭系统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
尽管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之一,但家庭作为一个次级系统,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深受超系统亦称作生态系统所涵盖的历史脉动、经济环境、家庭发展阶段和传承环境、文化规范和习俗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29)。因此,改善外在的社会生态环境,给予家庭必要和有效的社会政策、人文关怀和服务支持,将有助于家庭系统的良性运转。
1.社会政策保障家庭功能的发挥
(1)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导向。尽管社会转型期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增强,家庭已成抵御各种风险的救生筏,但由于社会保险尚未全覆盖,相关政策尚不到位,家庭的承受能力仍十分有限。报载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已有意扩大城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如以家庭为单位纳入医保,将医保受益面扩大到家属(30)。这种改革思路值得倡导。除了城市医保,其他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等不妨也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需扶养的人数不同,经济负担各异,因此,适值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之际,我们建议在税收上对抚养、扶养和赡养负担较重者试行减免政策,以减轻那些供养责任过于沉重家庭的经济压力。
此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和服务也应考虑家庭人口数。比如,独居、老弱病残、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成员少,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要的人均费用相对较多,对其应享受的救助标准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体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2)弱势家庭及其成员的特殊关怀。第一,高龄、特困老人和空巢家庭的特殊关怀。为解决独居高龄老人生活照料的后顾之忧,一些地方政府推进、实施了养老服务实事项目,同时采取购买公益性劳动岗位即家政服务的形式。然而,由于高龄老人退休金低而照料强度和难度则较高,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全天陪护,即使有政府补助也难以留住家政服务员,因此,还应倡导不同居子女主动分担部分服务费用,给予父母更多的嘘寒问暖、聊天陪伴和体恤关爱。
第二,单亲家庭的人文关怀应引起关注。由于单亲家庭的父母独自抚育子女须付出双倍的经济、时间和精力,不少人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接受终身教育,或为了照顾子女往往放弃某些高薪职业或减少了升迁机会,在社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不仅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税制减免应考虑单亲家庭的抚养负担,而且享受再就业扶持(包括职业培训、优先上岗)政策的对象也应涵盖单亲弱势群体。此外,婚姻法的立法和司法也应保障单亲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将子女抚养费给付标准的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使之公开、透明和便于操作,以切实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扭转单亲家庭的贫困化趋向。
第三,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和保险覆盖。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关职能部门要规范单位用工行为,对于侵害外来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强化监察和查处。同时,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使外来从业人员在就业、培训、居住、子女教育等方面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机会和待遇,使他们也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推进中国特色的家庭支持网络
(1)社会应鼓励亲属支持网络。如鼓励城市房产开发商多建小房型的经济适用房,既满足众多工薪阶层和下岗、退休的中老年家庭的需求,又便于老少家庭有分有合的代际互动。而在税收上对抚养、扶养和赡养负担较重者试行减免政策,也可鼓励家庭支持网络。
(2)整合非正式的社区服务资源。发掘分散、潜在、非正式的社会资源,通过组织、培训形成一支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单位队伍,开拓社区服务新领域,使更多家庭共享社区的教育和服务资源。
(3)推进专业性的家庭心理咨询和治疗。有关部门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以促进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速变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系统。
3.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家庭新文化
(1)幸福主义为导向的家庭价值观。现代社会应更关注婚姻家庭的内在质量、个人的幸福感而并非只是其完整的外壳,应把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增进婚姻主体的福利和满足、提高他们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上,而不应让婚姻当事人肩负起不该由个人承载的过重的社会压力。
(2) 多元、开放的生活方式和关系模式。公众态度趋向宽容、开放和理性,道德也不再是评判个人私生活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无疑是社会文化开明、进步的折射。而解构传统定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为女性参与社会、择业升职创造更公平合理的机制,倡导男子多参与家务、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对于弘扬性别平等的先进文化,改善和优化两性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双向社会化的代际互动新文化。“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既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决策权,同时使中年父母提高了对速变社会的适应能力,亲子间也减少了对立而增加了理解、宽容和取长补短的融合。尽管在双方社会化的代际主动中仍有冲突,但毕竟是一种社会进步,“向孩子学习”将掀起亲子关系的深刻革命,21世纪的家庭代际互动将在撞击、磨合中更加民主、平等和融洽。
4.普及家庭科学教育和训练
(1)将婚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一是列入中学性教育体系,也就是在性教育中增加有关择偶、恋爱及家庭人际关系调适等方面的课程内容;二是在大专院校开设婚姻家庭讲座,并在有条件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系中,将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课程逐步纳入选修或必修课程;三是一些区、县的民政、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也需对婚前教育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2)把家庭科学知识普及到社区。由于大多数市民未经婚前指导或学校教育,因此,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在社区普及家庭科学的相关知识通常更具广泛受惠性也更见成效。
收稿日期:2006-02-24
注释:
①张友琴:《老年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②桂勇、张广利:《求职网络的性别差异:以失业群体为例——兼论社会资本的中西差异》,《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③参见朱力、肖萍、翟进《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应用心理研究》1999年第4期。
⑤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⑥参见李煜、徐安琪《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潘绥铭、曾静:《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胡珍、史春琳:《2000年中国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1年第12期。
⑧参见潘绥铭、白维德、王爱丽、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⑨Thornton,A.and Young-DeMarco,L.,"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63(4),2001,pp.1009-1038; Treas,J.& Girsrn,D.,"Sexual Infidelity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ing American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2(1),2000,pp.48-60.
⑩徐安琪、叶文振:《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原因》,《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王婧《上海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异地联姻的新人接近1/3》http://scvnet,news.sohu.com/news/20050429/n225389093,shtml.
(12)Bitter,R.G.,"Late Marriage and Marital Instability:the Effects of Heterogeneity and Inflexibilit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6,48,pp.631-640,Amato,P.R.,Johnson,D.R.,Booth,A.& Rogers,S.J.,"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ital Quality Between 1980 and 2000",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2003,65(1),pp.1-21,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郑晨:《家庭变迁对新时期家庭伦理道德构建的挑战》,载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编:《中国婚姻家庭历程·前瞻》,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年:徐安琪:《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以上海为例的实证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4)约翰·德弗雷、大卫·H·奥尔森:《美国婚姻和家庭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家的对策》,《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5)根据新华社2005年2月28日提供的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资料计算。
(16)参见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17)参见周海旺、沈安安等《2004年上海人口发展报告》,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所2005年内部资料。
(18)参见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19)徐安琪、叶文振:《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
(20)参见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21)杨建军、徐燕萍、李晓东:《单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研究》,《中国妇运》2004年第10期;徐安琪:《单亲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2)徐安琪、叶文振:《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王世军:《坚强与无奈单亲家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3)约翰·德弗雷,大卫·H·奥尔森:《美国婚姻和家庭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家的对策》,《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4)Hochschild,A.,The Time Bind: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1997.
(25)Olson,D.H.& Olson,A.K.,Empowering Couples:Building on Your Strengths (2nd ed.),Published by Life Innovations Inc.,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Copyright,2000.
(26)M.A.拉曼纳、A.里德曼:《婚姻与家庭》,李绍嵘、蔡文辉译,巨流图书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版。
(27)张颖:《学生告家长的三大“罪状”》,《中国妇女报》2003年7月30日。
(28)(29)Boss,P.,1988,转引自波玲·布思《家庭压力管理》,周月清等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McCubbin,H.I.& Patterson,J.M.,"Adolescent Stress,Coping,and Adaptation:A Normative Family Perspective",in Leigh,G.K.& Peterson,G.W.(eds.),Adolescents in Farmilies,pp.256-276,Cincinnati,OH:Southwestem。
(30)《卫生部官员称城市医保将扩大,有望以家庭为单位》,《新京报》2005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