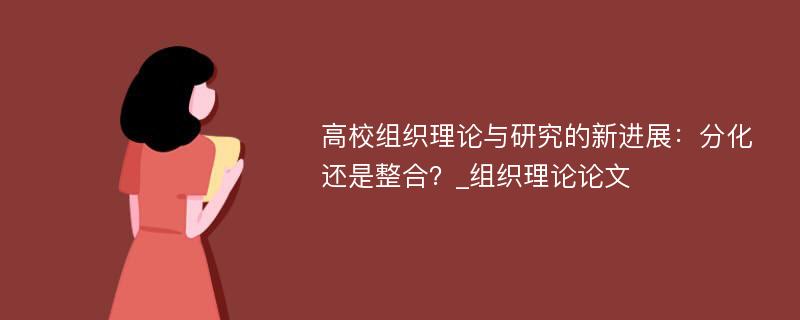
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的新进展:分化还是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高校论文,组织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23-09
回顾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近年来高校组织行为领域的相关知识不断增加,分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而知识整合的需要与上述趋势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提及这个问题,请回顾一些对学院和大学具有敏锐眼光的观察家曾经向我们提出的忠告。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大学的评论是:“事情的核心超出了规则所限。”[1]
鲁道夫(Frederick Rudolph)在《美国学院和大学》(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一书的结尾部分写道,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特征在于:“放任自流,不情愿地做出调整,事后才意识到变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而没有人注意这个过程”。[2]
布如斯特(Kingman Brewster)指出:“大学试图制定一种战略(更不用说规划了)的真正困难在于,我们(教员)基本上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普遍认为,重要的思想、技艺和行动必须具有创新性。而创新本身就蔑视任何预先制定的计划。”[3]
如果我们中还有人认为,高校组织行为的研究切实有效,那么这些观察和评论就有理由要求他们正视现实。确切地说,正是学生、学习和研究风格、教员和管理行为、学术和行政结构、外部需求和压力,以及学校的角色、使命、结构、过程和特征这些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我们理解具有很强分化趋势的组织行为模式提出了挑战。组织方面的挑战在于,我们既要保留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积极方面,又要确保高校更有效地实现教育和学术的双重目的。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不在于要不要组织起来,而在于如何去组织,组织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组织。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正是致力于理解这些奇妙的机构如何联系起来成为组织,以及它们怎样才更有效率。
青春期的特征
在考察近期的发展和提出问题之前,记住高校组织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很有裨益。例如,组织行为研究领域几乎是在二战结束后才出现的。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发展迅速,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研究生项目、系、学院以及由研究者和实践者组成的专业协会。同时在组织理论、研究以及应用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学术刊物。梵佛(Pfeffer)把目前的发展状况比作“丛林”。[4]
尽管理论和研究的发展速度还谈不上“丛林”,但是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的文献仍然增长很快。用人的成长过程来代替“丛林”比喻更为恰当。1963年,我们开始对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产生了兴趣,可以把这个时期比做该领域成长的“婴儿期”。该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麦康奈尔(McConnell)[5]和密歇根大学的亨德森(Henderson)[6]分别撰文,描述了当时高校组织管理文献和研究的匮乏状况。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出版了无数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研究方面进行了一些严肃的探索。
在1974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这个领域可以被看作是从“少年”向“青春早期”的过渡。同年,我在《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第二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的文章。这篇评论性文章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对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并且试图找出存在的主要分歧。[7]在最初文献清单上有500篇文章,但是称得上研究的文献只有不到200篇。这篇评论文章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数量大大增加,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被吸引了过来,他们工作得十分出色。60年代末、70年代初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大多数主要问题,均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领域的理论模式或者概念的有限发展和应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
2.研究通常采取的是探索性的个案分析或者描述性的问卷调查。纵向的、前后对照的、实验及比较研究都还是空白。以探索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阻碍了概念化的进程,量化研究也实施得较少。即使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量化的问卷调查也很少采用双变量、多变量或者因果路径统计分析方法。因此,还需要更先进的研究策略、设计和方法。
3.很少在不同的组织种群中采用高信度的研究工具进行重复性的研究,以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推广度,然而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4.由于最高深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都来自于具有学科背景的学者,因此需要在他们中间形成一个专业网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关于高校组织行为的研究在数量上和水平上都有了发展,这些研究在个人、团体或过程、组织以及组织间的关系等层次进行。与10年前那篇评论文章相比,本文涵盖的内容要丰富得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从该领域选取一些要点,对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的主要发展以及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做一个概述。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可以被视为“青春成熟期”——成长迅速,在有些方面已经非常成熟,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显得比较幼稚,有时表现得很自信,有时又表现得忐忑不安。目前,在相关理论、方法以及应用方面产生了一种张力,可能会使该领域知识激增并且分化,也可能会促使该领域走向新的综合。
进入“青年”期后,这个研究领域正在为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而奋斗一该领域的本质是什么?理论和研究方法何去何从?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它还在为研究的实际意义而奋斗——是否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去解决重要的问题,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者是促进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呢?它还在努力寻求合法性——什么样的专业合作伙伴能够为该领域的发展提出具有明智性的指导意见呢?总结这五个方面的发展——理论、研究、内容、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合作伙伴——给“我们应该往哪里去”的讨论提出了有意义的概念和问题。
考虑到组织行为很少有明确的边界,本文关注的是在组织层次上的现象,即从整体上把高校(或者高校的重要部分)看作是一个组织。同时,由于研究文献增长迅速,本文也不打算总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而只是围绕一个问题来进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领域应如何发展?
理论发展
我在1974年撰写的评论性文章中指出,理论概念和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只得到了有限的使用,之后,这个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有三种基本的组织模式(如果包括衍生模式,共有六种):科层模式(或正规一理性模式)和目标模式;学院模式和专业团体模式;政治模式和公共科层模式。这些模式基本上都是从组织内部着眼来分析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高等教育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开放系统、环境权变、组织生命周期和战略模式,它们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影响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任务一技术以及信息/资源模式,反映了我们日益重视这些外部变化对组织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这张理论清单上还包括了各种各样新兴的社会系统模式。暂时适应、松散连接’、有组织的无政府和社会网络模式,这些模式基本上属于内部模式,它们试图解释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在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8]的推动下,文化模式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再次成为一个热点。早在1970年,克拉克(Clark)[9]的《特色学院》(Distinctive Colleges),瑞斯曼、古斯菲尔德和甘姆森(Riesman,Gusfeld and Gamson)[10]的《学术价值和大众教育》(Acndemic Values and Mass Education)就曾经引起我们对组织文化的关注。迪尔(Dill)[11]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评述了不断变化的组织价值体系,而贝斯(Bess)等研究者,也提出高校和学者应该关注价值观。与组织文化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是对组织现象的自然研究——一种反模式(anti-model)的研究视角。最后,还有组织间的模式:组织系统、组织网络、组织生态学和产业模式,都被用来考察高校之间更宏观的关系模式(见表1)。
表1高等教育的组织模式
内部目的明确
正规-理性/目标
学院/专业团体
政治/公共科层
环境
开放系统
权变
战略性
生命周期
技术
任务/技术-结构
信息系统/资源模式
新兴的社会系统 暂时适应
有组织的无政府
松散连接
社会网络
组织文化/价值
组织学习
自然/反模式
组织间 组织系统
组织网络
生态学模式
产业模式
这张理论模式清单并非包罗万象,它只包括了在组织层次上的模式。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考察每一种模式的具体内容,而是从这张清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一些观察和思考:在理论模式和理论框架的扩展过程中,我们在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974年以前提出的模式,正如1982年梵佛分类中指出的那样,是“内部的、目的明确的”模式;它们关注影响组织运作的可管理的活动——组织被看作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机构[4]。而近期出现的理论模式更多地把技术、环境以及新兴的社会结构看作是决定行动的主要因素。(关于“内部的、目的明确的”和“新兴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将在本文的后面谈到)
第二,70年代中期以前,高等教育理论模式清单基本上是由“借来的”模式组成。无可否认,很多模式都被扭曲或者加以修改来适应高校的情境,只有两个模式——1974年科恩和马奇(Cohen and March)[12]的“有组织的无政府”以及1976年韦克(Weiek)的“松散连接”[13]概念——在最初产生时就反映了高校的情况。即使如此,这两种模式也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植根于其他的组织背景,可以说它们都不是新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认为具有独特性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却很少有理论创新,而较多借用从其他组织背景下诞生的理论分析模式。很明显,我们特别需要重视理论创新。
第三,这些模式之间具有分化性,理论建构采用的是演绎的方法。(注:关于组织理论发展更详细的讨论,参见莫尔(Larry Mohr)1982年的《解释组织行为》[39]一书及梵佛的《组织和组织理论》一书。)借来的不同理论模式关注着不同的组织现象。大量的模式在规范、分析和预测目的上有所差异,对于解释因素也有不同的假设(比如,是关于组织内部的还是关于组织外部的,是定向的还是自发的)。很少有人勾画被这些借来的理论模式有效解释的组织现象,也很少有人比较每一个模式的特性。1983年,贝斯(Bess)在他主编的《高等教育评论》(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撰文指出,需要把理论模式和组织现象(即组织域)联系起来寻找研究中存在的差距。[14]
对分析类似组织现象的几个模式之间的直接比较,有利于突出每一种模式的独特视角和内容。1971年,鲍德里奇(Baldridge)比较了当时流行的科层、学院和政治模式。[15]最近,对模式(子模式)或者概念之间进行的比较分析非常有限,都是集中于某一水平或者某一种类型的组织现象——例如,1984年卡梅隆(Cameron)在《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比较了四种组织适应模式(种群生态学、生命周期、战略选择以及符号作用)。[16]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如何比较松散连接模式与社会网络模式?前者的连接(coupling)跟后者的连接(linkage)有什么区别?绘制地图以弄清理论与现象的联系并且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减少分化以及(或者)发现彼此间重迭的地方;然而,建立一个对所有模式进行比较的综合体系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努力。
最后,我们未能考察每一个借来的模式或建构的“适切性”和“充分性”,显然这是因为它们从表面看起来自成体系、合乎情理。在很多理论文献和研究中,作者都倾向于赞成自己所使用的那种模式。他们很少提出分析方面的关键问题。这种模式是一种分析框架、规范性理论、解释性理论还是预测性理论?这种模式满足一个好理论的简单标准吗?要记住1982年梵佛提出的好理论有五条标准:第一,要考察的现象、关键概念和变量的界定是否“清楚”?变量的理论和操作定义是否清楚?例如,有人从不同方面对“影响”加以界定和测量,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却混为一谈。第二,在变量的数目方面是否过于“精炼”(或者充满了不可解释的偶然因素)?第三,理论是否具有“逻辑连贯性”?例如,1976年韦克(Weiek)建议把“松散连接”作为一个分析视角,但他认为还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分析和发展。然而,1982年,卢兹(Lutz)在讨论这种模式的时候,已经把它作为不再质疑的理论[1]。第四,呈现出来的模式跟真实数据是否“一致”?具体情况或者“偶然性”是否被考虑在内?例如,现在流行用有组织的无政府模式来解释一些难以预测的行为,但是当它的一个重要前设“组织冗余”(organization slack)不明显或者不成立时,我们就要质疑这种模式的有效性。1984年特罗(Trow)在对伯克利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重组进行评论和分析时就提出一个较为理性的范式。[18]
第五条标准是理论的“可反驳性”。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模式进行反驳或者反证的尝试?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随着这些模式或者关键概念应用程度的推广,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对这些在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特定理论模式方面达成一致或者存在分歧的根据,没能进行一次归纳性、权衡性和系统性的考察。因为众多的高等教育组织研究都以问题为导向,所以,研究评论集中围绕问题对研究进行分类,描述研究发现的模式,被研究的机构类型,运用的方法等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对一个模式以及它的预测达成一致或者存在分歧的事实上。学术上很少有反映评论这些方面内容的途径,而对结果进行评论性的比较研究也不被高校组织理论研究人员所重视,至少不是他们优先研究的部分。很多评论文章甚至整部书都在报告一些结果和启示来支持他们采用的模式,并没有系统地权衡一些相反的证据。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外是关于失学(attrition)的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位学者以系统和比较的方法围绕理论框架仔细考察了一些定量研究(Pascarella & Terenzini[19];Tinto[20]),即便是这些人也没有用源分析方法来检验不同研究中理论和预测在统计意义上的一致性。
关于研究模式反驳和反证的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是,尽管组织研究现在看来多以理论或概念为导向提出假设,但是这些努力都还局限在单一模式上,即进行研究设计,支持或反对一种模式。我们很少使用1964年普拉特(Platt)在《科学》(Science)上提倡的“强推论”——在同一研究里检验不同的模式或者相互竞争的假设。[21]卡费(Chaffee)1984年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22]尽管没有采用统计检验,但是她对为改变机构衰退而采取的适应性和解释性策略进行了比较。
上面对组织理论和模式的简略评述勾勒出了一个混乱的局面,同时也突出了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选择困境。高校组织研究应该致力于理论创新,以充分反映高等教育的独特性呢?还是应该集中于对众多理论模型和研究的系统综合,以增加一致性,减少分歧呢?是否应该注意对模式进行系统的检验,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虽然这样做耗时、昂贵、实用价值也很有限?这些困境将会在下面段落中详细谈到。
研究发展
1974年,高校组织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描述性的问卷调查或探索性的个案分析阶段。目前,尽管这些情况仍然存在,但是研究策略、方法和技术都有所扩展,变得更为成熟。在分析变化之前,首先要注意没有发生变化的方面。实验的方法仍然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被运用。研究重心还是基本放在实地调查上,很少有纵向的、前后对照的或者准实验的研究设计。模拟的方法有所运用,但是大多限于定量的计算机模拟。1972年,科恩、马奇和欧尔森(Cohen,March and Olsen)对有组织的无政府这一模式的检验[23],以及其他在7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资源流和行为模拟都非常引人注意。有趣的是,曾经在其他专业背景下用来模仿组织行为的行为模拟在这个领域却运用得并不多。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变化很有意义,它们是反映理论模式转变、环境影响高等教育以及研究工作日益成熟的产物。
首先,同时运用结构化的量的和质的方法的比较个案研究变得越来越多。这就增加了变量和因果模式的效度,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有时还可以进行高级统计比较和多变量分析。莫提梅尔(Mortimer)1979年在对资源减少过程的研究中,着重对几所学校的文件和访谈进行了内容分析[24]。鲍德里奇1979年在分析几所文理学院管理系统的影响时,同时用了量的和质的研究方法,并在两者之间进行了对比。[25]
其次,更多的大型调查研究把学校的特点和对个体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因此可以对组织和个体变量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鲍德里奇在70年代中后期对管理进行的广泛研究就是一个例子[26],它引发了对各种管理问题的研究,在比较个案和大规模研究中,有时会使用到复杂指标建构和因果路径模型。
第三,在大规模研究中,更多地对表明学校特点的标准化数据库进行二次分析。1983年波恩保姆(Birnbaum)关于学校多元化的变化模式[27]和1984年赞姆托(Zammuto)关于文理学院及其招生的转换模式[28]都运用了HEGIS(注:美国高等教育综合信息系统。——译校者注)数据库,对高校进行了生态学的分析。
第四,由于对组织文化以及反映非正式突发现象的模式(松散连接,有组织的无政府,自然模式,等等)的重新关注,半结构的质的研究方法受到更多关注。对文件和访谈的内容分析、隐蔽的测量、人类学和现象学的方法,被更频繁地运用。
满足下列条件的大规模研究仍然为数不多:高度综合研究,仔细地改进模式和变量,在对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使用比较个案研究,同时运用量的和质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例子有:1983年卡梅隆对组织效益的系列研究[29],1984年卡费进行的战略管理研究[22],以及我本人1978年对黑人学生在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院里产生影响的研究[30]。这些研究费用高,耗时长,而且要求研究人员有一种长期的使命感。不幸的是,这种支持大规模研究的经费在不断缩减。
以上对研究策略和方法的观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高等教育的组织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方法迷宫”。研究在日益成熟的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困境:我们要加强大规模的量的研究,还是集中开展质的研究?前者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有可能得出统计模型,但是需要较多的经费,而且结果也不确定;后者可能会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组织行为:情境化讨论
前面谈到的理论和方法上所处的困境,反映了过去五年在组织行为这个更广阔的领域里的争论。因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总是沿袭并且落后于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争论很有意义。夸张一点说,这种争论集中表现为两种极端的观点或者范式,它们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和抽象的前设上:什么构成了现实的组织?(本体论)?我们如何获得这方面的知识(认识论)?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前设是什么(目的论)?(详见表2)
简单地说:第一种被称为“传统”、“保守”和“社会事实”范式(Cummings,1981[31];March,1982[32];Meryl,1981[33])。这种范式把组织要素看作客观事实,具有实证性,可用来进行预测,把注意力放在了组织结构上,看得见的行为,组织要素,研究对象的态度和自我报告。理论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看一组变量如何随其他变量的改变而改变。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简化法和量化法。
第二种被称为“文化”、“激进”和“社会定义”范式。它将组织要素视为主观的,必须由组织角色自己来进行解释。这种范式更关注诊断性或者事实的最终原因,把注意力放在了组织的自然过程和动态过程上。分析理论是过程性的,主要关注理论的发展。然而,这种范式的一些支持者摒弃所有理论模式,认为研究只在于观察和描述一些现象。在研究方法上,这种范式倾向于整体论,注意考察组织行为的整体情境,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暂且不管前面提到的以外部为导向和技术组织模式,我们的高校模式已经呈现出了差异性,尽管这种差异还不够明显。例如,在1974年以前提出的正式一理性、政治、学院模式更符合传统范式。它们都认为客观现象可用于说明事件的发生,在理解了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可以对组织有目的地加以管理或指导。以这些模式为基础的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和其他客观分析方法,如关于态度和看法的问卷数据,对个人和组织特点的测量,以及分析文件和结构化访谈内容。
表2组织理论和研究的两种文化
范式
传统 文化
保守 激进
社会事实 社会定义
事实要素
客观 主观
知识观 实证 解释
因果关系
预测 诊断
最终原因
内容焦点
结构,模式
自然过程
动力
理论应用
变差检验 过程或
发展性的
研究设计
计划 旁听
研究方法论 简化主义 整体主义
测量方式
量的 质的
另一方面,最近出现的理论模式,如社会网络、松散连接、组织学习以及组织文化,都拒绝传统模式的目的或者理性前设,批评这些传统模式未能解释很多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事情。它们把注意力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他们如何受环境和事件内容的影响,他们如何给这些内容赋予意义。研究重点在于对行为的考察和诊断,在于了解这个过程如何出现并且成型的。研究方法更倾向于人种志(深入的人类学个案研究)、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现象学研究。
自然,这两种立场比较极端,高等教育领域很多关于理论、研究和方法的讨论,都同时包含或者承认这两种观点。讨论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了前文提到的两个困境,并且反映了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发展中可能面临的第三个困境:这些辩证的观点将来会继续保持二元对立呢?还是会达成一致呢?
从理论到实践
在我们的议程上,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实际意义”,即理论和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高校组织研究主要以实践为导向这个基本特点。然而,很多变化都在改变着这种关系。
第一,对现状作出反应的趋势仍然存在,并且有可能导致极端描述性研究的流行。幸运的是,最近关于学生规模缩减(或者衰退)或组织效益的研究(如,Cameron,1983[29];Mortimer,1979[24])通过考察一些非暂时性的问题以及把这些问题置于一个扎实的理论框架内,避免了这样的批评。考虑到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的压力,既要重视那些显而易见的描述性研究,又要对那些重要的长期问题给以同样的关注。
第二,高校从事管理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要求学者从事直接应用研究的压力也随之减轻。教师队伍里热心于组织管理问题的成员,也有机会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把结果报告给能够理解理论含义的管理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有发展潜力,而且已经反映在日益增多的系列研究专著上面,比如ASHE/ERIC出版的各种《研究报告》,琼瑟。巴斯(Jossey-Bass)出版公司的《院校研究新趋势》(New Directions)系列专著,以及其他各种协会对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出版物。
第三,前面提到过的、反复强调的概念模式和日益复杂的研究策略方法,使高校组织研究的实用性降低,较难被管理者所理解。这就使得将研究结果传达给行动者的过程比以往更为重要。我观察到,这种需要在增加,但是高校组织研究者却不太重视这种研究的应用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出版的《院校研究新趋势》就涉及到了这个主题(Lindquist)。[34]
最后,与前面几点密切相关,目前组织研究的趋势是研究者保持中立或者采取价值无涉的态度。在我所作的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设计的文献综述里,与研究实践、政策分析、评估有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大部分是从一个研究者的中立角度出发进行的,很少有研究者跟其他角色一起参与的策略或者行动研究。几乎没有为政策辩护的研究,尽管很多高等教育方向的研究生毕业后很多将从事管理工作,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技能。学者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改进。例如,《文理教育的多样性》(Variety of Liberal Education)一书就是甘姆森(Gamson)1984年根据她做FIPSE(注:美国中学后教育质量改进基金会。——译校者注)协调员的经历写出来的。[35]鲍德里奇最近领导了几所学校减少失学率(attrition)研究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评估活动,并在其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康拉德(Conrad)、布兰克波恩(Blackbum)、伯达尔(Berdahl)和其他人参与了美国司法部在路易斯安纳州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辩护研究。问题的核心在于把研究的设计和传播策略引入理论应用方面。
这些观察指出了第四个困境:研究者是应该更加独立呢,还是应该更深地参与实践活动呢?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对理论或现实问题的兴趣不同,更在于高校组织研究者应该做价值无涉的专家,进行翻译和传播,还是行动型的研究—参与者或者拥护者。
专业伙伴
最后一个内容涉及谁是能够为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提供合法性批评和指导的专业伙伴或者顾问。很容易辨认从事理论研究的个体,但是,还有一些致力于高校组织领域的研究项目或者机构。在AERA和ASHE(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和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译校者注)这样的协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正规的团队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一家高等教育期刊或者系列专著单独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很多刊物都用专门的篇幅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由于理论和研究的分化趋势和缺少专业发展重点,所以对专业伙伴送行一些简短评论是适当的。
首先,前面关于理论应用的讨论已经指出合作者身份不易认定。他们是研究者呢,还是管理者呢?显然,研究者应该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来源,那么管理者呢?正如前面理论—应用的困境所指明的那样,我们是同类人呢,还是异类人呢?在校外,一些高校组织研究者在参加院校会员协会(如AGB和ACE等(注:美国高等学校董事会联合会和美国教育理事会。——译校者注等)和其他管理协会(如AIR和AAUA等(注:美国院校研究协会和美国大学行政人员协会。——译校者洼))中找到了合作伙伴,并获得了研究资助。在校内,管理者发现问题,提供一些实用性的研究项目、数据、校内资源、研究成果传播机会,也能够产生影响力。我们发现,具有组织理论和研究专门知识的高级管理人员变得越来越多。很多学校里从事应用研究的院校研究和计划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多。不幸的是,预算上的压力经常使管理者不愿意学校的研究人员探讨一些敏感的冲突事件和问题。
其次,在学者队伍中,研究人员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网络还处在萌芽阶段,联系不够密切。在校内,有教育学院的其他学者,但是他们在组织概念和研究问题上的兴趣有限,而且很多人具有很强的行动导向特点。教育统计和实证研究学者常常关注的是个人或者小团体,而不是将整个组织作为分析单位。
在教育领域之外,有很多校内外的学者在研究组织行为,但是他们缺乏对高等教育的特别兴趣。在所有跨学科领域里,我们都可以选择加入一个以协会为基础的跨学科团队(如,ASA(注:美国社会学协会。——译校者注)的组织研究分部),一个专业学院中的单位(如,商学院里的组织行为学系),或者一个没有清楚边界的跨学科网络。密歇根大学的“组织行为专题讨论会”就是这种网络的一个例子,它由来自于法律、商业管理、教育、社会工作、工程、公共政策、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健康、政治科学等各个学科的25名教授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会面,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与外来的访问学者进行交流。有趣的是,很多校内成员彼此相识多年,但是平时各忙各的,直到一个外来的访问学者邀请大家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聚在一起。
这一部分讨论的要点在于专业伙伴的资源是无穷的,但是他们通过批评、指导和合作来推动研究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促进这种合作网络的建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活动,但是这涉及到定位和成员选择问题:行动者还是研究者?教育学家、专业人士还是各学科专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会影响到对前面几个困难的解决。
重温困境
这篇文章阐明,在迅速发展的高校组织理论和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分化,其中有比较突出的五个困境。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这五个方面都做出肯定性的回答。
混乱的理论模式仍然存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理论,以找到更好的途径来理解高等教育领域的独特性。最新出现的模式提供了有用的例证。但是,需要花力量进行理论和研究的“综合”,弄清楚每一个理论和建构,更关键的是,要考察借来的理论模式的可应用性以及高等教育组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收获。要对个别理论模式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对不同的解释要进行对比验证,从而证实或者推翻这些模式,而不是一味地维护这些模式。
方法迷宫会继续呈现出多面性,这对于我们认识组织行为在不同背景下的复杂性是有所帮助的。要继续重视大规模的比较和调查研究,运用“量的”研究以及多变量和因果分析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并且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检验。同时,也需要运用更深入的“质的”研究方法(注:关于非量化的研究方法有两个比较好的资源,它们分别是1982年第27期《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面专门讨论质的研究的文章,以及最近由库恩斯和马托瑞那[40](Kuhns and Martorana)撰写的关于院校研究中的质的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in lnstitutional Research,1984),后者为《院校研究新趋势》系列中的专著。)来考察变量的结构效度,检验理论的前设,从广泛的调查中找到新的理论启示或者模式。
不仅要重视两种范式的区别,、还要寻求两者的整合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哲学二元对立关系上纠缠不清。每一种不同的模式、理论、研究策略和方法,都需要用相关标准进行检验,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目的、问题和背景加以运用。对量的方法和因果模式保持敏感,进行开放性的解释,将有助于推翻现有模式,这里还会提出适合用质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将两种范式结合起来的例子,是在大规模比较研究中同时运用量的和质的两种方法,比如NCHEMS(注: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心。——译校者注)对组织效益和衰退的研究,以及1983年理查森、费斯克和欧康(Richardson,Fisk and Okun,1983)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的关于读写能力的研究。(注:康拉德[41](Conrad,1982)在《高等教育评论》(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上撰文讨论了扎根理论。)
显然,理论一实践或者实际意义这一困境,是理论和研究的不断扩展与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解决问题之间矛盾的产物。我们需要好的“理论家和设计者”把实践中的发现放在广义的情境中加以考虑,发展出一个解释性的框架。我们也需要“翻译者”有效地传播大量的理论和研究文献,需要“行动研究者”参与到关于研究过程的题目中来,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理论发展和批评的角度来关注研究方法,关注研究策略和对研究成果的传播,关注参与式的研究方法。
罗杰斯和甘姆森(Rogers and Gamson)198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评估》的文章。[37]在1978年出版的《白人校园里的黑人学生》(Black Students on White Campuses)(Blackburn.Gamson,& Peterson)[44]中的一章里,作者讨论了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中白人黑人混合团队的作用。我们需要分析和分享有用的看法,提高高等教育组织研究的水平。在这些例子和关于理论一实践和专业角色的讨论中,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建立由伙伴和顾问组成的“合作”团队完成下列的功能——围绕高等教育组织理论和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及时地把合作者团结在一起。
在上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将决定着高等教育组织理论和研究能否克服目前青春期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健康地成长,提高整体水平,避免出现过度分化。
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了作者的授权。原文发表于《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1985年,第14卷,第3期。该文被收录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ASHZ)2000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Organization and C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ASHE Reader Series)一书中。虽然该文发表的时间较早,但是仍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经典的研究评述性论文,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首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