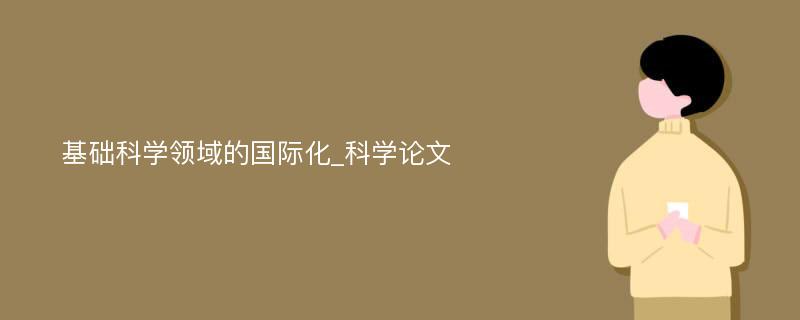
基础科学领域的国际化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科学论文,课题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前言
在世界快速发展的激烈变化中,涌向日本的国际化浪潮势不可挡。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但是在科学领域的国际化方面,正像目前存在的就业问题、未来管理问题一样,由于日本制度不完备以及适应国际的发展趋势滞后,因而面临着很多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使日本的基础科学真正达到国际水平,还必须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2.“国际化时代的科学”学术讨论会
1992年6月,由日本学术会议天文学研究联络委员会建议、天文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制定计划,加上物理学研究联络委员会的支援以及丰田财团的赞助,日本学术会议天文学研究联络委员会主办的“国际化时代的科学”学术讨论会在东京青山的学术会议演讲厅召开。
本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以推进基础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中心,从科学、文化等多角度看日本的科学制度、科学发展体制、基础科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
日本的科学研究人员本身要多方面了解日本科学的现状,扩宽与社会对话的渠道,努力改变基础科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号召包括政界及新闻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参加讨论,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活动。
学术讨论会进行了两天,以天文、物理学领域为中心,大学、研究所的与会研究人员约80名,文部省、外务省、科技厅等官方代表十几名,新闻、科学杂志等新闻界人士十几名,企业界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约十几名以及其它各界人士,共计120名学者参加。
下面简要介绍本次学术讨论会的要点。
3.国际联合研究的现状
学术讨论会首先就天文学、地球物理学、高能物理、宇宙科学、核聚变等几个领域的国际联合研究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进行了讨论。
(1)天文学 目前,日本国家天文台正在夏威夷建设口径8米的可见光、红外线的“昂宿星团”望远镜。国家天文台的安藤裕康氏就这座望远镜当前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所作的报告指出:
昂宿星团望远镜是日本第一次建在国外的永久性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日本科学史上的一次尝试。正如宇宙科学和高能物理学所评价的那样,日本的物理学早已进入了高水平的国际化研究阶段。昂宿星团望远镜就是日本独自在国外建设的第一台大型装置。
海拨4200米的冒纳凯亚山顶具备宇宙观测的优越条件。世界各国在这里建造了可见光、红外线、电波等第一线望远镜群,发展成最大规模的国家观测站。目前除昂宿星团望远镜外,还有口径为10米的合成望远镜KECK两台,密执安大学的亚毫米波阵,美国、英国、加拿大的8米望远镜GEMINI(1台在夏威夷、1台在智利)等。下一代望远镜群预计在本世纪完成。
经过长期的实践,这些国家的国际天文台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研究活动经验。但对日本来说,预计1999年建成的国家天文台夏威夷观测站(暂名)如何进行研究及运营,取得赶超其它诸国的优异成绩呢?需要解决的难题比预想到的要大得多。例如,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像国家天文台教师那样的公务员不允许在国外工作,虽然允许临时性出差,但仍然存在着国外出差开支数额大、在当地的活动受限制以及责任范畴、家属安排等很多实际问题。例如从日本派遣60多名职员以及在当地雇用职员就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从日本调派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雇用当地职员又受到夏威夷法律的限制。即便是灵活地运用现行的法规,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天文学能否带头解决这些困难呢?
(2)地球物理学 今天,地球物理学已成为阐明行星和地球的一门学科。整个地球已进入综合化(地球系统科学)的时代。京都大学超高层电波研究中心的山中大学氏作了报告。报告指出:
目前覆盖全球的数据网络系统无论在大气圈、生物圈还是地壳研究方面为全面阐明地球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它打破了以往一些大国的探险调查及设置观测设备收集情报的模式,与世界各国的研究、观测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多元化的国际合作,使集世界性的观测、研究、教育为一体的中心机构应运而生。
山中氏特别强调了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及亚洲诸国对日本的期望。为了实施综合判断大气立体结构的“赤道雷达计划”,在雅加达的大气观测中心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在位于赤道上的印尼原始森林设置大规模的气象观测雷达(直径300米),开展新水平的国际合作。
(3)高能物理学 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并不像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那样需要选择场所,而是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装置的大型化、高技术化,因此,它是一个需要发达国家紧密推进合作研究的领域。
通过国际间的相互合作开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国际性的开发计划均由多国间的对等组织实施,但由于日本的预算体制及人员出国限制等一些未成熟的制度随时会碰到障碍。但是进行一项新事业必然要遇到困难,只要有信心去战胜困难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举动。
(4)宇宙学 宇宙科学是应用宇宙空间这种特殊状况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它被列入国家级宇宙开放的框架中。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的西田笃弘氏在报告中谈了巨大科学的典型——日本宇宙科学的现状。
宇宙科学具有基础科学及作为国策的宇宙开发的二重性。国际合作也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为基础科学,其根本的动机就是要体现科学需要这一“基础”,但另一方面,又具有基于政治、政策及经济的需要而开展国际合作的条件。二者若达到一致则圆满无缺,但现实中二者很难达到一致。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必须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其政治因素。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宇宙空间站应该是无人式的,但美国的航空宇宙产业为保其自身的未来,强行推行有人宇宙空间站计划,实在令人担忧。由于科学理论概念上的差异,使发射卫星的国际合作进展艰难。但又不能对此一概加以否认,而应以另一种立场来考虑这一问题。因此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发展全世界的科学。
(5)核聚变 能源政策是每个国家政策的基础。核能源作为一项国策来说,这比宇宙科学发展更强劲。但其装置的巨大化,正以无法预见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人类共同的能源问题”的旗帜下,发达的四个集团(美国、欧洲、原苏联、日本)共同开发的组织化不断深入。虽然一些国际合作项目脱离了基础科学这一范畴,但作为巨大技术开发的国际间合作代表实例,日本学术会议核聚变研究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关口忠氏仍在报告中概括说明了它的现状。
日本(JT-60)、欧洲(JET),美国(TFTR)“三大托卡马克”(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一类装置)以临界等离子体为基础的研究,正在按照大规模国际共同开发计划(ITER),联合兴建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这项工程是以自行点火、获取能源为目的的综合开发系统。
ITER是核聚变发达国家之间的史无前例的大型合作项目,与各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自1988年开始,花费二年半的时间进行了“概念性设计”,四个阶段的研究开发经费总额高达1.2亿美元。在第二阶段的光学设计活动中,围绕着中央设计小组办公地点设在何处一直争论不休,最后决定分别设在日本、美国、德国。现在预定2020年前拿出实验结果。但对不能分割的大型装置的安装地点仍是争议的焦点。
4、关于日本科学的思考
由于与会者来自各个领域,讨论的内容也涉及到多方面,现仅就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
有三个人提出了关于“国际联合研究的各种课题”。
日本国家天文台的小平桂一氏指出:目前与物理学有关的国际合作计划有二十多项(根据二年的问卷调查)。对日本来说,要求现实制度要先走一步,要加强国内的科学基础,尽快建立不仅是“官”还包括“民”在内的支援国际合作项目的系统。
东京大学理学部的釜江常好氏以日本、印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详细分析了追赶欧美的日本基础科学的科研经费。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国家拨给基础科学的科研经费为2万亿日元。但是除去研究人员的工资、建筑经费、维修费等项开支,纯科研经费只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1/2到1/3,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樱美林大学的光田明正氏曾担任过文部省审议官。他根据从政的经验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提出远离大会议题的问题。指出曾深受韩国文明影响又要保持自我独立的日本如今是否已溶入标榜科学的欧洲文明圈呢?对于只知努力奋斗而不顾追求合理性、不想搞清事物本质的日本的这种强烈的心理状态来说,它能成为西欧流派的科学吗?实质贫乏的日本,尽管国际性气氛很稀薄,我们总在这样的国情下发展科学。当然,日本的科学迄今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能得到日本全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上述发言的提示下,与会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将讨论范围归纳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关于科学文化论,除上述光田氏的发言外,还有美国公共广播东京特派员关于“追求秩序、安定的日本社会能出现科学所必需的异端分子吗?”的发言以及日本文部省高教局草原克豪氏的“有没有适应日本组织社会的日本科学?”的发言,他们围绕着历史的观点、“西欧”本身的多样性、日本组织社会的优势、研究人员的流动、组织与创造性等有趣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这些讨论中可看出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及其它职业人员所持的观点与立场是不同的。不过,与其一味地将西欧和东洋加以区分,倒不如去探求和重新认识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探索理解新自然”这一科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关于研究经费,这是援助科学的问题。釜江氏再次提出,如果有1000亿日元,日本的好多科研课题2-3年内都能解决。丰田财团理事长、原名古屋大学校长饭岛宗一氏指出:援助科学的财团只能按照日本的法律和行政规定对一些困难的项目给予援助,但是对非政府间的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的援助确实微乎其微。日本在文化、学术、福利等方面约有400个公共财团,但到目前为止,民间资助在学术基础学科方面没起什么作用。与会人员还指出:文部省制定的科研相关经费预算要在以大学的收入为基底的“国立学校特别会计”的框架内进行。这样就必然出现很多矛盾。为使所有人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必须从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改变思想认识两方面着手。
第三,关于推进科学体制、行政制度。草原氏提出“如何与科学大型化相对应的问题”,海部提出“日本是否有科学政策存在?科学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程度如何?日本负责推进的科学政策体制至少从国际性角度看不到”等问题。大阪大学理学部的伊达宗行氏提出,“日本虽然提出一百年内赶上西欧的科学文明,但实际情况是不仅体力上(经济),而且智能方面也远远不及西欧。例如供给恶化、大型化不足等,日本学术结构的缺陷等问题应在学术会议上进行探讨。”从日本目前的状况看,需要组织一个具有行政官员与研究人员中间特性的群体,各省厅机关也应全力以赴为科学开绿灯,改变旧的习惯势力,冲破行政制度羁绊,团结那些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当前的现状取得共识。
此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见:
·科学家的努力是否还有不足之处?是否应该更广泛地宣传科学,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科学家们是否仍关闭在偏离社会常识的世界里?应拼命地争夺生存之地。
·科学应该公开化,但日本的科学家是否开诚布公地议论过这一类问题?只有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方能涉足,但要在科学杂志上进行公开讨论则非常困难。
最后海部氏进行总结说,要认识新的大世界,发挥科学作用,通过实践扩展共同理解的视野。
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说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研究人员的意识与社会的差距,是一次发挥集体创造性思想的大会,在探索未来世界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5、东亚地区的天文学交流
国际化本来是从物质、金钱、人的来往中自然膨胀发展起来的,欧洲如此,岛国日本也不例外。目前我们处在科技交流历史时刻,课题之一就是与韩国、中国天文学的交流。
1992年10月,我们参加了日本、韩国、中国联合在韩国召开的“关于毫米波、红外线天文学的东北亚地区会议”,这是韩国天文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日本包括大学生院研究生在内有十几人参加,中国也派了十几名代表参加,是一次热情洋溢的盛会。其中印象最深的议题是:
一、日本与韩国之间相互并不了解各自天文学的发展状况,韩国基本不了解日本的“昂宿星团”计划。而日本对在美国深造的韩国天文学家大批归国,带来韩国天文学的大发展这一情况也一无所知。通过交流对双方都是一个触动。日本与韩国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相互之间的了解要比了解遥远的美国少得多。
二、韩国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大部分是大学生院研究生,他们的报告非常精彩。两国与会的年轻代表都很意气相投,往往饮酒论争通宵达旦。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韩国大学研究生中近一半是女性。在热烈的讨论中,日本青年提出举办大学研究生天文学交流会的计划,受到韩国大学研究生们的赞同,并提议联合举办,结果一拍即合。
由于日本过去对邻国韩国的侵略,一度造成政治上的封闭,这次的交流一举冲破了闸门。青年一代竭尽全力地推进两国科技交流的举动,令人感到日本新国际化时代的到来。
1992年在韩国的研讨会上,日、韩、中三国达成的共同意向是:今后,日本、韩国、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要更紧密地交流信息,推动交流,为实现作为东北亚天文学研究和观测中心的东北亚天文台的早日建成而努力。今年9月在中国内地黄山进行了天文观测装置安装现场的实地调查。当时韩国和台湾也参加了此项调查活动。如果时机成熟还将邀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天文学家一起参加安装小型红外线望远镜共同观测的事业。
日本的国际合作并非只着眼于对自己有利的欧美诸国,如果能在亚洲寻找到合作伙伴,将是令人鼓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