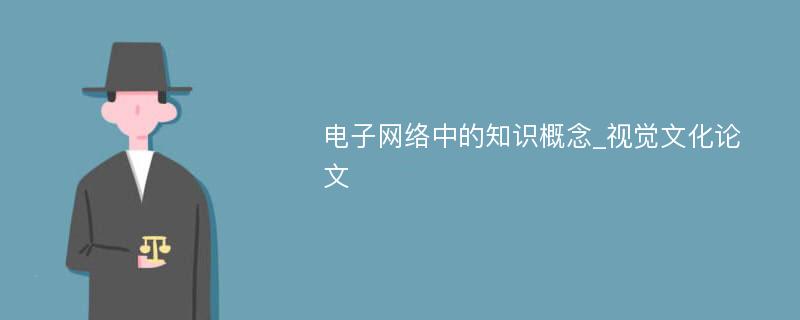
电子网络中的知识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知识论文,电子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写作现在这一总结时(1997年1月), 我们对网络认识论的了解比两年前这一合作主题确定下来时多得多了。这种增长部分地是由于网络本身的巨大发展;然而,部分地是我们自己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流所造成的。因此,我宁愿说这一课题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但是这可能会产生误导。
首先,因为在概念用语上我们的结果主要是否定的,因而容易产生误导。关于如何不在网上强调知识问题,以及关于这一难题不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成功地发现新的肯定性概念。而且我认为我现在知道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其次,从电子讨论尚未真正出现的意义上讲,这种结果是消极的。这就是我使用“一系列交流”这一迂回说法的理由。当然,我们使用了电子邮件和邮件表;当然,其中的文本是数字化形式,并可在同时获得。但是,我起初提出的讨论话题(一个传统的哲学话题)根本不适合在网络环境中讨论。无疑,哲学在网上具有自己存在的空间——或者我们应当称之为时间(?)。网络确实需要它的哲学家。但是这些哲学家以及他们的问题所属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哲学世界。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从这一课题中所得到的主要教训。
下面是它如何开始的,即在1996 年1 月, 我用电子邮件给“ mii—cken”目录发去一个文本:
亲爱的网友:
我们的讨论(像“一元论者人机对话问题”所面临的所有其他讨论一样)应当以主持人邮出通常称为“目标论文”的活动开始,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主持人(即我)早在很久以前就应当完成这一点——事实上是在去年十月底完成的。如今我担心,现在这一文本仍然不是你们所期望的论文。或许根本没有这一论文——或许这一讨论从一开始就必须出现。其理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越来越难于坚持我在过去几年间所坚持的观点——然而,却没有达到某种确定的、可选择的立场。尤其是我在1994年所撰写的《电子网络和知识的统一》一文中所捍卫的观点,已经不再令我满意了。我逐渐感到那些观点的印刷偏见对我有干扰——尤其是在阅读了塔尔博特(Talbott)的《未来不能计算》以后,更是如此。塔尔博特对于有意义的知识意味着什么具有某种陈腐观念;他的哲学人类学完全是非历史的;这种非历史性使得我在自己先前的研究中,以我现在认为是潜在的非历史态度看待问题。我并不是说《电子网络和知识的统一》中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其实,如果你们中有人在某些阶段想看上它一眼,我将感到欣慰——我将把这一论文与这一文本一起用电子邮件给诸位寄去);但是它的论证预先假定了某些观念具有永恒的有效性,而事实上,据我现在所知,这些观念是受印刷书籍的年限所制约的。
因此,如果说我自己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我宁愿说传达它们的合适方式,根本不是对它们作出陈述,而是对问题作出详细阐述。因而下面提出一些问题——我邀请诸位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
1.假定“知识”概念具有一堆意义,其中大部分是含糊不清的,那么,当人们探讨电子网络中的知识概念具有何种意义时,应该如何进行呢?譬如说,人们是否应当使用那些非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即把那些特殊的认知态度描述为显示在特殊的网络居民语言习惯中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应当描述某些新出现的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描述新的概念类型,而对旧的概念类型不予理睬?抑或相反,人们应当严格地以对那些旧的类型进行表达与分析的方式开始,并在前者的框架中检验这些新用法?我自己的选择仍然是后者。
2.假定你们接受了这一选择,那么,迄今已经确立的“知识”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区别或许是“知道什么”和“知道如何”之间的区别:即一方面是言辞或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实践知识(各种技能和技术)。但是,这时人们会马上追问:这一区别是如何作出来的?譬如,由图画(图像、表格、图表、地图)所传达的知识是什么呢?第二个(与之有关但不大相同的)区别是操作性知识和思辨性知识之间的区别。第三个区别是私人知识(在某些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意义上)与集体知识(某种共同体或文化所拥有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第四种区别是私人知识(在评价的、规范的意义上)与客观知识(在纯描述的、事实的知识的意义上)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分是有用的吗?其他何种区分是恰当的?知识与“信息”之间也能作出区分吗?知识完全不同于信息,或者前者是后者的一种特殊情况吗?
3.当我相信知识的性质,或者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说不同的知识概念得以出现、繁荣和衰落的方式,并非独立于知识得以传播和保存的各种技术时,我是正确的吗?这里包含着哪些联系?
4.因此,电子网络技术对知识的性质具有哪些影响?当计算机网络代替孓印刷文本时(在这里,哪个是合适的表达:是“代替”还是“补充”?),在知识的传播和保存方面发生了哪些相关的变化?
5.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相关的变化之一涉及到我们关于时间的经验和概念;涉及到我们在其中感知现存传播内容的暂时背景,尤其涉及到我们体验和处理过去事物的模式。例如,关于不断变化的存档观念,人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观察(Hedstrom;Bearman)。在我读到伯克茨(Birkerts)的著作《古腾堡的悲歌》时,我为之深深地打动,为我们“分散的时间感觉”和我们“与过去的分离、与作为累积的或有机的过程至关重要的历史感分离”而悲伤。我现在仍然很感动,但不再信以为真了。
6.伯克茨所要论述的中心思想是,我们正在失去数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思维之特征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们真的失去了某些东西吗?在我写作《计算机时代的历史意识》(1990年)一文时,我确实认为我们是在失去某些东西。今天我认为,我们失去的或许正是某种过时的理想物。或许正如尼采曾经设想的那样,我们正在获得以一种实践精神去解决现实的新自由。
7.当然,历史意识只是许多有争议的理想物中的一员,即创新性、个性、不受干扰的自由、知识的统一、客观性和绝对真理中的一员。我认为,对这些理想物的解释和评价不应脱离它们出现于其中、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受之约束的社会组织。对电子网络背景中知识概念的讨论,在任何时候都还应当是对电子网络使得我们能够(或不能够)建造的那种社会的讨论;是对它促进或排斥的那种生活的讨论。
期望我们均获得富有成果的交流。
——J.C.尼弗里
如今,“mii—cken”目录在网上已经广泛地公开化了, 那里有各种询问,人们在那里注了册——上述文本必定出现在许多电脑屏幕上。但是它没有引起任何回应。因此在1996年4月14日,我决定重新开始。 我再次把那篇目标论文,连同我的《知识的统一》一文,发给大约20个网友。他们之中有两位是我通过电子邮件而熟识的;其他人则是我的老相识——同事和学生,有匈牙利的,也有外国的。我请求他们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意指mii—ckcn目录已暂时冻结。
在随后四个星期里,有两个地址作了回答。一个是英国哈福德郡大学艺术与设计学校的麦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博士。 麦克尔事实上是对《知识的统一》中的一段话作了评论;所以让我首先把《人文科学中的网络》卷中的那段话(第261页以下)引述如下:
在印刷时代以前,图画和图表仅仅发挥着有限的作用。……罗马人使用简单的图画(称为寓意画)帮助他们克服其文字描述方面固有的视觉缺陷:(注:萨恩格《默读:它对中世纪晚期的手稿和社会的影响》,载《旅行者》13、37页。)他们通过记忆页边上的特殊图画而回想文本中的特殊部分。在中世纪早期的手稿中,那些插图有助于读者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文本中的相应部分。以这种方式应用的图画,仅仅具有辅助功能;并且即使这种功能,也随着引入文字间隔而丧失了。正如萨恩格(Saenger)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发明赋予书面拉丁语以某种表意文字的研究价值,同时没有牺牲音形统一的阿拉伯字母在教育学上的固有优势。(注:萨恩格《默读:它对中世纪晚期的手稿和社会的影响》,载《旅行者》37页。)此时,图画已不再是视觉所必需的辅助物。并且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它们也不能成为知识传播的辅助物。由于它们在复制过程中必然要受到歪曲,因而它们也不能保存信息。随着印刷的出现,这种情况改变了。但即使那样,同图画相比,文本仍然可由作者、尤其是印刷者以更为方便得多的方式进行巧妙处理……从整体上说,插图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图画作为思维的载体几乎未起任何作用。偶尔有人感觉到这可能是某种损失。因此培根写道:“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词语是思想的图像,而字母是词语的图像。’然而思想由词语媒介表达并没有必然性。因为无论何种能够足以区别开来的东西和那些能由感觉来感知的东西,从本质上说都能表达思想。”(注:F.培根《学术的进展》,1974年英文版,第131页。)
这就是当里查德·拉纳姆(Richard Lanham)说学者的论证应当使用图像“去思考和概括问题,而不只是通过其他手段对所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进行说明”时所面临的问题,(注:R.A.拉纳姆《电子信息对知识社会学的意义》,载《技术、学者和人文科学:电子信息的意义》。)或者是当麦克尔·埃斯特(Michacl Ester )谈到“根据某种思维方式去安排图像”时所强调的问题。(注:M.埃斯特《艺术和人文科学中学者使用电子图像的问题》,载肯纳·和罗斯编:《人文科学中的网络》,第120页。 )拉纳姆所指的是由在屏幕上处理图像的可能性所开启的图景。但是在印刷时代晚期,把文本与图像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的计划,已经作为一种〔譬如说对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 )来说〕可感知的目标而出现。他写道:“人们经常很难用词语表达在眼睛看来是非常清楚的东西。某种东西能用图画说清楚,就不必用语言去说。”(注:O.纽拉特《国际图画语言》(阅读大学印刷与图解系),第26页。)纽拉特致力于研究一种“国际印刷图画教育系统”,简称为“Isotypo ”,这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图像系统,可与由词语构成的语言一起使用,但是它却具有其自身的视觉逻辑。Isotypo将是二维的, 使用那些具有明显特征的约定、形状、颜色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纽拉特特别强调,这种图画与语言的结合意在达到某种更加广泛的目标,即建立一种关于日常统一知识的国际百科全书——他说,这是“我们的时代巨著”——在此他是特指法国百科全书,该书“提供了大量材料和大量图画,但是它们之间只有某种松散联系。”(注:O.纽拉特《国际图画语言》(阅读大学印刷与图解系),第65页和第109页。)
下面是麦克尔·比格斯所写的话:
为了在思维中重现想像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几种不同层次的做法。最积极的做法是使用不完善的插图,它们只是重复文本中已讲过的东西。这正是狄德罗(Diderot)和法国百科全书中的情形。 其次纽拉特也是如此,他出于效率的缘故,不希望使用语言去表达图画能更好地、更有说服力或更容易表达的东西。(注:还要参考L.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I—50。 )当然这里并非必然说有些事物“只能”由插图来表现。因此,拉纳姆和埃斯特(注:我(即麦克尔·比格斯)是指拉纳姆和埃斯特根据尼弗里的引文所作的论证。)提出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论证,其大意是说,视觉思维提供了一些文本思维所不能提供的工具。这种观察不仅仅是一种效率论证。以同样方式,维特根斯坦把被词语所说服的情形同我们用图像所不能论证的相反情形作比较。(注: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I—34。)这不是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注:L.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1212)中关于“言说”和“显示”之间的区别相混淆。在《逻辑哲学论》中,这种区别是结构性的,其中“被显示的”东西隐藏在“被言说的”东西之中。被显示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注:J.辛提卡《维特根斯坦研究》,1986年英文版,第 6页以下。)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指视觉实践,例如,用例证表明的定义。那种不可言说性属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它强调了实践(注: 例如“拿六个苹果来”,见L.维特根斯坦《蓝皮书》第16页。),并且在其中“精神图画”成为不必要的构造物。视觉推理新出现的这种优势导致了诸如“证明”这样的词语可被描述为“一幅单独图画”的观念。(注:L.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I—28。)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并非由于图画和证明是同义词,而是因为这种观念使得我们的思维摆脱情绪的干扰,从而考虑到证明是要告诉我们某些与图画性的图表所不同的某种本质,而图画性的图表只是一种范型,不一定是某种本质。(注:L.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I—74、75。)
因此,电子文本的问题在于,概念是由非语言实践所支撑的。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文本传播优势的影响,并且有可能被因特网上便利的视觉形式所克服,这些便利的视觉形式比直接的文本和文本字符串(电子邮件)传播更有优势。其局限性表现在概念上,因而,我们没有一组关于书写法的分析工具能与文本的书写法相媲美。譬如,我们能以基于实践的传统方式组织和建构文本,但却没有任何实践的并且因而是分析的相应统一性可应用于图像。因此,维特根斯坦对某种相似性的认知可能会表示惊奇。(注: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I—xi,第210 页。)对图像表达意向时所发生的变化表示惊奇。(注: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I—683。)这种一致性通过与我们在文本中获得的那些分析二具相比较可以弄清楚。我们不能分析图画的外貌。(注:L.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I—78。 )所以,视觉知识与文本或语言知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一致性。
书写文本的逻辑与图画逻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关于网络知识难题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里,只要这些探究仅仅以所涉及的这两种范畴之一即言词来进行,哲学的进步无疑就很难出现。我们将通过参照菲尔·马林斯(Phil Mullins)的论文,在本文总结的末尾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这一轮的第二个评论是由维也纳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技术设计与评估学会社会控制论组的马吉·波尔(Margit Pohl)博士作出的。 (马吉给我发邮件用的地址是“Kristof”,这是“Christoph”的匈牙利译文。亲爱的读者,请容忍一下我的絮叨:我出生在匈牙利,并且在那里长大,但我家是讲德语的家庭,因此尤其在我用英语或德语写作时,我通常把我的名字写成“Christoph”——因而在“J.C.”中用了“C.”。)下面是马吉特的(稍作编辑了的)文本:
克里斯托夫·尼弗里传给我们两篇作为讨论起点的论文。关于这些论文,我想做两点评论。第一个评论论述写作技巧与一般的知识表达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评论专门讨论超文本(作为写作技巧的一个样板)。
1.目标论文。在此我将对论点(3)和(4)作出评论。
我认为写作技巧会影响人类的知识表达形式,这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这种关系似乎是相当复杂的。被认为是电子时代典型的知识表达的许多特征,在计算机技术引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克里斯托夫本人就常常引用马齐尔(Musil )或维特根斯坦作为网络化的离散思维和写作的早期样板。显然,技巧对写作过程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和一维的。有可能存在着既影响写作技巧也影响知识表达形式的网络哲学之类的东西。超文本社区中著名的科学家兰德·斯拜罗(Rand Spiro)论证说,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复制现代生活复杂性的方法。在他的理论中,正是复杂性而不是诸如此类的技术是知识表达中各种变化的原因。因此,复杂性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哲学观念,它在同时带来了技术和智力上的变化。
2.在其论文《电子网络和知识的统一》中,克里斯托夫写道:“把所有可恢复的信息都仅仅看作原材料,使用者可以从中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超文本结构——这种当今非常时髦的观念,是把知识视为零散状态,而不是视为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
就超文本的一种特征,即它能使读者找到他们自己穿越知识丛林的道路而言,我赞同克里斯托夫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非常混乱的。尽管如此,超文本还不仅限于此。超文本还能使它的作者更清晰地呈现文本的结构。印刷形式的概述卡片具有这一功能。如果作者使用打印链,他们就不得不仔细地考虑他们想创造的这些链的性质。如果超文本文件得以很好地建构,这种表达方式能给读者提供该材料的概观,那么这比传统的书籍所能提供的要好得多。此外,这种方法还迫使作者以比传统的线性文本(这种文本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含蓄地表现出来)更高的程度考虑他们的文本的整体结构。
超文本仍然是很“年轻的”媒介,因此,如果未来的超文本文件是离散的和无序的混乱状态,或者是结构合理但却灵活多变的客体,那么它就会依然存在。这两种发展每一种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人类的理性,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我认为,当谈论电子网络对知识表达的影响时,这表明了另一种主要问题——使用计算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
1996年5月14日,我再次按照上述20个地址, 给他们发去了麦克尔和马吉的评论。
在我发去的内容中, 还有赫尔伯特 · 赫拉科维克 ( Herbert Hrachovec)最近撰写的一篇论文(大概用的是德语写的)我发现这篇文章非常切题。它的标题是:《二乘五预示了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有关研究》。该文章的内容直接参考了“《一元论者》相互作用问题课题”。我在最近几天前于明斯特所作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那种参考;并且通过引用该谈话结束了我的5月14日的讯息:
赫拉科维克所说的是他和我仍然在进行的某种共同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令人不快的体验。“《一元论者》相互作用问题课题”是试图通过利用因特网上发起和进行的讨论而收集这一值得尊敬的美国哲学期刊中的特殊问题。我本人计划主持一个讨论,题目是“电子网络背景中的知识概念”,并且在最近几个月中,向那个广阔世界发去一个内容广泛的问题表以供思考,与那张表一起还发去一个长文件。我还没有接到任何回答。起初,我有些困惑不解;今天我认为我明白了。在电子网络背景中根本没有像知识的概念之类的东西。那里的全部东西就是人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程序,或者没有告知的程序;或者是人们已发现或没有发现的全球性超文本的位置。未来的人文科学将不会有柏拉图式的观点;相反,可能会坚持某种维持根斯坦式的观点,即不问意义,只问用途;或者甚至会坚持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非常热衷于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多媒体传播的流变需要未来的人文科学竭尽全力去理解——并且我相信,如果传统文本仍然保持某种程度的功能的话,就必须去理解,或许这会导致停滞不前。(注:这个谈话现在由J.C.尼弗里以《后文学时代的人文科学》为题,发表在《布达佩斯图书评论》6/3(1996)。 其概要见http: //www.hungary.com/books。)
我的赫拉克利特幻想并非没有效果。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拉兹洛·图里(Laszlo Turi, 我正好也在那个研究所工作)受到它们的激励,因而他也决定参加这个讨论。图里当然是一篇介绍《一元论者》现在的这一论题的文章的作者,因而读者至此会有机会熟悉他的某些观点;下面是他对我的目标论文所作的(稍作删节的)评论。我是在1996年5月20日收到它们的。
我评论的是数字技术和网络中涉及的具有三重性的知识范畴:(1)如何获得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2)关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 (3)知识的使用,即对知识的存取和传播。
1.如今司空见惯的是,自认为属于“老一代”的人们发现,他们比“年轻人”更难于学习使用新技术。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个体的差异比那些与年龄组有关的差异更有意义:有些老年人比其他人更为成功地学习和使用了新技术。我认为,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年龄的意义,而应集中注意于类比:那些能够较容易发现类比的人,很快就能掌握新技术;那些与他们的前辈提供类比的技术,同那些宣称是全新的技术相比,更容易被人们掌握。换言之,在数字技术时代最迫切要求获得的知识,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事实上它是类比的——对设计者和使用者都是如此。
2.我承认关于过去的经验如今正在发生变化。我也能理解当案卷保管员发现数字化文件中根本不再有“这里和现在”的感情时所具有的恐惧心理:比特和字节是永恒的,它们几乎不需要保存。但是我们要记住,这种经历并不是全新的:至少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它就已为人们所知晓了:“传统的”手稿文本的印刷版同“原稿”“存档”所产生的感情已经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把口头传统凝结为永久存在的技术——换言之,我们在此所面对的东西或许是这种传播技术中所固有的影响。
然而,数字化文本确实具有某种以前从未有过而且我有所担忧的特征:现在的数字化文本是建立在默读和写作时代之前所发展起来的同一准音位学写作体系基础之上的。该体系因为引进了其他标记如词语单位之间的空隙、停顿符号等来帮助眼睛,因而在对符号的解释不再借助于耳朵的时代里成功地幸存下来。然而,在数字时代,当对符号的解释既不借助于耳朵,也不借助于眼睛,而是设计成仅仅在线性符号序列上工作的自动过程时,它几乎就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人类语言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们不能在一个层次的线性结构中再现:人类读者运用他们的三维视觉和极为丰富的私人“词汇”去理解简单的写作系统背后的复杂语言系统,但是,按程序运转的机器对此无能为力。由于现在的文本检索工具几乎不能可靠地在巨大的数字化文本档案中航行,我们所失去的可能不是关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关于过去的知识。
3.根据我对机器可读的准音位学文本的存取性的看法,可得出如下结论:写作技术在如今面临着严重问题;甚至或许可以说,书写沟通或传播技术遇到了危机。然而同时,视听传播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贮存和传递系统,通过更好的分割而提供了质量更高、相互作用更大和更为精确的存取方法。仅举一些著名例子来看:交互式压缩盘(CD—I)、 高容量数字光盘(DVD)、网络实时数字化声音(Real Audio)和CD —ROMs或万维网上的超链接图像和影像。换言之,当传统的书写传播技术似乎处于危机之时,视听传播的发展则显出无限的前景。无疑,视听传播也能像书写传播一样精确而复杂,并且它也能是一种叙述媒介(试分别比较:交通信号、名画和电影):然而,它不适合传递那种我们通常称之为欧洲科学的抽象理论知识。
如果要对拉希·图里的评论(“拉希”是匈牙利语“拉兹洛”的口语形式)作出评论,首先,我将评论说,我发现关于类比知识的概念在此得到相当好的说明。要知道,这一概念在欧洲中世纪哲学〔一种关于手稿文化和交互文本(intertextuality )的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印刷时代的哲学中它有可能再次发挥这种作用。
其次,我认为拉希关于在存档方面的新情况并不是真正全新的见解,
仅仅是部分可信的。
在此我仍然赞同马格丽特·赫兹特罗姆(Magaret Hedstrom)的观点。正如她以非常赞赏的口吻所说的那样:“许多现行制度的实践活动都在破坏着对电子记录的保存、保护和二次使用……甚至存档一词也失去了它许多传统的意义和联想。在数据处理专业的行话中,‘存档’是指脱机贮存数据。‘永久性媒介’是指那种不能被抹去或改变的媒介,即使它只能持续几年时间。这些新定义没有体现档案保存者通常与‘存档’一词相联系的任何概念,没有在其背景中理解信息,确认什么是有价值的,或保存记录和只要有价值就使它们成为可接受的……有些档案保存者已开始对这些基本的存档活动(譬如出处和发生顺序)是否适合于电子记录管理产生疑问。关于发生顺序和出处的概念是从基本的档案原理中所产生的……记录的许多意义和价值起源于该记录由以产生的背景知识。关于这种产生的背景知识反过来又可通过检验它们的产生顺序,通过研究管理史、组织机构、组织的功能和……个体的生活史而得以确认”。然而,“除最简单的数据文件结构以外,数据的物理顺序是由软件所控制的,并且与其逻辑顺序相区别”。(注:M.赫茨特罗姆《理解电子文本或初期版本》,第336—349页。)
第三,我承认,并非只有历史意识,而且还有历史知识,能够部分地在数字化文本海洋中被淹没。正如我在我的目标论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历史意识的缺失可能最终根本不是损失。但是无疑我们不想失去对相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在第一层面上,我们已经明白数字化图书馆对传统人文科学的学习确实具有不良影响。在线公共存取目录倾向于关注专题论文和系列论文的最新材料。然而,正如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在人文科学中,新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文献总体的自由研究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所选择的新近出现的一小部分内容之上。(注:参见D.克雷因《无形学院:科学共同体中的知识混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94页。 同样还有莱恩·伯林德雷的文章, 见她最近的研究《90年代的图书馆指南研究》,载S.罗斯和E.黑格斯《电子信息资源与历史学家:欧洲人的观点》,第178 页:“对人文科学的引证研究……表明,所引用的50%以上图书的出版日期是35年以前或更早。”)在第二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下述危险:实际上起作用的图书馆藏书,由于磁盘和光盘贮存媒介的相对非持久性以及硬件与软件迅速成为废品,可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成为不可复制的,或者要付出过分昂贵的保存费用。(注:参见罗斯《引论:历史学家、机器可读的信息和过去的未来》,载S.罗斯和E·黑格斯《电子信息资源与历史学家:欧洲人的观点》。)在这方面,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规划确实值得注意。1998年全部开业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试图既成为巨大的物质性图书馆,也成为数字在线图书馆。正如它的两个神奇的设计者所指出的那样,它旨在“使古腾堡的宇宙与麦克鲁汉的联姻更加完美……它将是开放的、民主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但是,所有这些事物在某种限度内会保证对过去的最大尊敬。”(注:D.詹米特和H.威斯巴德《历史、哲学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抱负》,载《表象》42。特殊问题:《未来图书馆》,R.霍沃德·布洛赫和卡拉·赫斯编。关于知识和数字图书馆的话题,还可参见彼特·莱曼的优秀文章:《何谓数字图书馆:技术、
智力特性和公众的兴趣》,
载Daedalus 125 (1996)(《图书、砖块和比特》:第125卷,《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的活动IV》。)正如莱曼所说:“知识人产品鲜明的真实性”——即知识的物质载体的真实性——“造成了观念的连续性和结构性,使得作者的权威声音、文献结构和连续性以及最终的公共机构生活本身成为可能。……印刷物和计算机屏幕由于都包含着字母数字的符号而似乎是相似的,但是,文本和信息却构成了种类极不相同的公共知识。”(同上第6页以下)。)在第三层面上, 还存在着由拉希所指出的那种危险:即使通过数字化所保存的知识,如果所用的电子搜索机制碰巧不合适的话,也会丢失,并有可能永远丢失。最后,我赞同在新的传播媒介中,西方科学必然会失去其抽象性。未来的人文科学将不会有柏拉图式的观点——并且我认为,对未来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1996年5月20日以后,该讨论趋于静止。我只好等待,直到11月7日才收到另一条信息。它是由我在布达佩斯大学的一位攻读心理学和数字专业的学生格治利·科维斯德(Gergely Kovesd)发来的。在这里,我把他对人机对话和万维网的评论复述如下:
我们可以根据电子邮件与原始的口语之相似性观点而对它进行研究,从而对它进行适当的分析。然而,随着万维网的广泛扩展,已经发生了许多剧烈变化。为了检验这些变化,运用连续统研究方法去研究人机对话是比较方便的。仅仅考虑这种传播是否是双向的,这还不够;我们还可以谈论某种较低或较高层次的人机对话。双向传播或多或少是平衡和对称的。万维网的作用介于面对面的相互交流和电子邮件为一方,印刷图书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虽然用电子邮件确实能够把文件送回超文本文件的制作者那里,但大多数使用者只是阅读这些文件,很少对它们作出评论,并且仅仅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对它们有影响。
万维网带回了面对面交流的那种生动性,但是其背景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面对面交谈中,直接的交流背景是由物理环境构成的。而在万维网中,它是由设计者的理性计划所造成的。由于这种计划要耗费时间和能量,因而必然会尽可能把交流者的网页建构成普遍地可接受的。除非具有相当可编辑的原材料,该网页通常不能加以改变。结果,人机对话减少了,并且该文本的稳定性比电子邮件形式要大得多。
在我收到格治利的评论几天以后,菲尔·马林斯加入了这个讨论。我感觉这几乎是以一种旧式的方法发生的。赫尔伯特·赫拉科维克提醒我注意艾斯卷(参见马林斯《文本海洋中的圣本:北美电子文化中的圣经》,载埃斯《关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的哲学观点》,1996年英文版,第284页。),因而我开始阅读马林斯那篇论文。我认为它很精彩;并且我发现其中有一段尤其切中要害:
“信息”一词及其情侣“数据”是相当中性的技术用语,在当代它们常常代替“知识”一词来指示我们保存下来的文化知识。这些术语还暗示了我们对二十世纪后期所产生的许多符号性人工制品所持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信息”和“数据”意味着不固定的人工制品;这种非背景化材料似乎漂浮着和积累着,并且对电子文化中各个存在者来说还起着某种积累作用(很大部分未利用)。当然,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认识者,其方式同他们在以前的时代一样。成为认识者,这是一种社会努力,它涉及到这样的背景化程度,以致于人成为某种有效的媒介。认识者是在信息领域中认识有意义的关系的。尽管如此,电子文化中的个体可以感知到个人生活和更大的环境之间存在的距离;他们感觉到了信息扩张的大框架内部存在的某种分离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不过是说,在书本文化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理性和知识大厦的推测似乎正在崩溃。我们至少想像出存在着无数合适的分类方案,其中可确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验的位置;但是如今我们似乎至少在地图上正在放弃这一希望。信息世界似乎失去了它的人类尺度;即使我们仍然对它的前景感兴趣,它的广大无垠性已使我们感到惴惴不安了。(注:马林斯《文本海洋中的圣本:北美电子文化中的圣经》,载埃斯《关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的哲学观点》,1996年英文版,第284页。)
在该文中,马林斯提到了他的一篇早期论文:《作为理论工具的多媒体》。论文是提交给1993年11月23日举行的华盛顿特区圣经文献交流年会的。〔其电子文件可在下述地址中找到:mullins@griffon.mwsc.edu〕因此,我给这个地址发了电子邮件,要求得到那个文件。活生生的反应开始了(也收到那个文件),并且我迅速把我在《一元论者》上的讨论通知了菲尔。我把这个材料发给了他(在下列段落中,《知识的统一》一文称作“论文”,目标论文称为“片段2”)。在11月19日, 他对它们评论道:
克利斯托夫——我决定一晚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而阅读和思考你的论文和你发送给我的其他材料。我非常欣赏你的论文。我也能理解你现在关于该论文对知识的预先假设的不安。我的一般观念是,可称为“知识”的东西和我们如何思考“统一的知识”,相当决定性地是由我们发展起来并用来获得和传播知识的技术所形成的。显然,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位置,因为我们正迅速地转向某种更加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我们先前关于知识的图像或理解以及“知识的统一”(它的构成和可能性)正在我们面前发生转变。我猜想,这也正是你在片断2 第三个观点中所提出的。
你提到了关于“历史意识”的数字文化的某些关注。我怀疑印刷文化的历史意识部分地是从文本的增殖和文本与社会背景之间似乎是天然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从历史性上看,数字文化对文本不会如此关心。我不能肯定这种发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可能这两者兼而有之。我已经证明,对圣经的许多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就这些神圣文本在文化中的功能而言,它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朴素或天真(naivete )。
我对“知识”与“信息”之间的联系也感到困惑。我认为,漂浮在全球网络中的信息图像是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图像。网络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人的尺度。
最近,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设法纠正数字文化中的真理观念。我喜欢罗伊斯的“是真”观念或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值得探索的合适观念的忠诚观念。我也越来越被C.S.皮尔斯的符号观点所吸引。他是个实在论者,因而我想知道在数字世界中是否有可能做一个实在论者。我认为,当皮尔斯说自从中世纪以来的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名论的特点时,他或许是正确的。换言之,我想知道的是,数字的多元论能否通过某种形式的实在论而复活虚无主义。
最后,你关于数字文化中的知识反应诱使我进一步思考数字文化中“意义”的性质问题。当我发出我最新撰写的论文时,你将会看到关于“意义”问题我变得有点迷惑不解了。在我看来,在印刷文化中有可能对“包含”意义的文本进行思考,而在数字文化中可能性则不大。“意义”是电子文本永远可望而不及的。一件事情必然会导致电子网络中的文本。那就是,只有相当严格的实用主义“意义”观点才是貌似真实的:用皮尔斯的语言来说,符号的意义是其本身立刻成为新符号的那种解释性反应(interpretant)。
菲尔所说的“最新撰写的文章”,是指他于1996年3月24 日在美国铁路协会中西部年会上的谈话:“创造电子文化中的宗教意义”在我看来,根据现在的分析,该谈话的核心段落如下:
……在电子环境中,有意义的是由它的流动性所清楚地标志出来的东西;有意义的事物出现、消失和流动。在人机对话的数字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那些由计算机使之社会化的东西把可见的符号视为短暂的和不稳定的(正如在转化过程中一样)而不是固定的。因此,在电子环境中,认为意义是对之有兴趣的团体在特殊时间把它们带到一起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最自然的。
然而,我最迫切地引用的段落来自我首先询问的菲尔的那篇论文——他的论文《作为理论工具的多媒体》,是1993年11月23日在AAR/ SBL会议上所宣读的。该段文章如下:
我们现在开始理解你能用任何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写作。语言符号在交流方面不再有任何优势了。如今,你可以通过把激发感情的图像、声音和传统的书写语言串在一起而写作。每一种媒介或许都有其特殊的语法和修辞方法,但是如今混合的语法和修辞法是可想像的。当然,你不能必然地在音频或视频或它们的混合中编造出三段论(或演绎)。但是,你能制作或设计出已呈现的意义。
我们现在通过言词的逻辑又回到了图画逻辑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要在这些交流过程中获得其基本意义。
我认为,其他主要问题是:人机对话性和同时性。从哲学上说,一般而言受电子传播、特殊而言受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兴起之制约的三种最重要的现象,事实上是下列现象:与图画和声音相区别的文本之逐渐变小的重要性——柏拉图意义的丧失;作者与读者相区别的丧失;以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丧失。
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家的工作就在于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把提示物收集起来。”(注: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27。)我在这里收集了关于我们都要进入的计算机网络世界的提示物——是为某种特定目的而收集的。我相信这种特定目的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这一系列交流所表明的是,哲学事业的性质已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我撰写《电子网络和知识的统一》一文时,我还没有明白这一点。那时我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所分析的现象已相当难。如今我认为这一任务本身是一项全新的任务。
(J.C.NYIRI ed.,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NETWORKING,原载THE MONIST 1997(80)3:405—422 杨富斌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