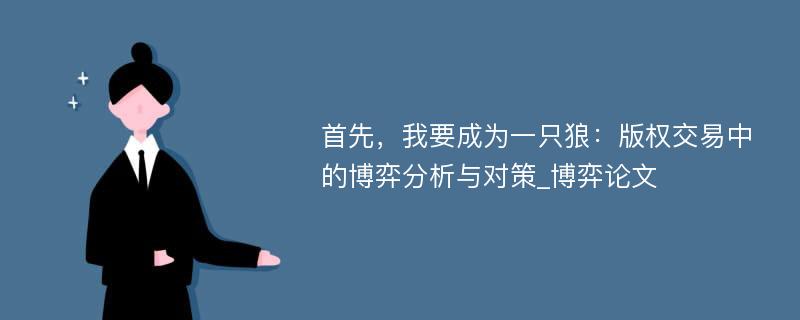
自己首先得成为狼——版权贸易中的博弈竞局及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版权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要躲避锋芒,也不要坐等中国加入WTO将带来的机会,主动、正面地与中国政策对接”——这是全球传媒巨人默多克在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论调,也是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渗透的典型言论。
WTO就像是一双神奇的巨手,把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带到中国面前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大门轰然打开。近年来,我国的版权贸易呈现出明显的“一边倒”趋势,在拥有成熟规范的运营经验、实力雄厚的资金技术的国外大型出版集团面前,我国出版界无论从规模、运营策略、技术与人才优势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被动防守、疲于应付的境地。进口版权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销售业绩、利润额等各方面较之出口版权都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给中国的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哈利·波特》系列、《卡耐基成功之道全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系列、《我的野蛮女友》、《菊花香》、《失乐园》等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售奇迹。面对引进版图书和国外大型出版集团的强烈冲击,业内有识之士惊呼:“狼来了!”
一、当前对外版权贸易中的博弈竞局
“博弈理论”(game theroy)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博弈论来源于且适用于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活动和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论,博弈即一些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按照一定的规则,从各自循序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如果以博弈论的视点来观察,当今中国的对外版权贸易堪称一场“境外出版商——本土出版商——政府管理机构”三边参与、按照本土化制度、同时参照日益国际化的规则争夺世界范围内图书市场份额的超级博弈竞局。境外图书业如何谋求市场准入?管理机构如何掌控全局?本土出版如何以弱制强等等问题日益成为热点。从目前来看,各主要博弈方的具体情况及各自的博弈策略有以下几种模式:
1、境外出版商。作为博弈三方中的“外来户”,境外出版商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扮演了“主动进攻”式角色。其主要优势体现在资金、内容与人才三大方面。就资金而言,由于实现了集团化发展、产业化运营,且融资、投资、风险退出等渠道十分畅通,因此,依靠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占领国内市场,就成了外方出版巨头的第一大“撒手锏”。相比而言,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有限,本地出版商在外方的资金战面前显得抗御乏术;就内容而言,外方巨型出版集团由于有产业运营的成熟经验和社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的“先发”积淀,因而具有异常庞大的产品库和多样化的系列产品构成。例如在电影《哈利·波特》全国热映之际,《哈利·波特》系列图书、音碟、游戏等产品也呈铺天盖地之势蜂拥而来,一时几乎占据了中国所有的媒介形式,那个骑着扫帚的魔法少年也成了无人不知的“世界级偶像”;就人才而言,国际出版巨头本身拥有的巨额资金、高薪待遇和更加成熟完善的人事制度、更大的发展空间等都对出版界精英人才构成了强大的诱惑力,他们还特别注重对所在国本土人才的吸收。如贝塔斯曼集团就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公开招聘编辑、文案人员,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们对本土化人才的高度重视,也对国内出版界构成了强大的挑战。
然而,境外出版商在中国也并非畅行无阻,政策与文化壁垒仍然对其谋求市场准入造成一定的障碍。为了在这场博弈竞局中保持和扩大自身优势,外方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博弈策略:
首先,在面对政府管理机构这一主要博弈对手时,外方主要是谋求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多边利益平衡,特别是充分利用WTO的规则一致性所造成的“国内政策国际化、国际政策本土化”格局并辅之以某些涉外条约的政策优惠来作为交换条件,摸准我国目前政府管理机构急于广泛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的内在需求,因势利导,通过改变博弈竞局中可利用的“变数”来构建更有利于自身产品输出的新型动态博弈格局。
其次,在面对国内文化壁垒时,则采取“顺应”与“引领”并行的方针。诚如默多克所说:“如果你忘记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想观看的基本上是地方节目、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顺应”,主要是指顺应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需求和阅读习惯,使外来文化尽可能本土化。例如:大量招聘本土人员进行译介工作以避免“硬译”的出现,使外来作品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语言文化习惯;充分利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进行二度创作(例如迪斯尼的动画巨片《花木兰》)消除受众的文化、心理隔阂;充分利用中国出版界现有的人才和渠道进行营销等等。所谓“引领”,是指境外出版集团通过种种经济、政治上的优势来维护其话语强权,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使得他国受众逐渐认同其所宣传的文化的优越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文化产品的输出大国,其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灌输着一种“现代性”假相,在其输出的文化产品中,美国人极力鼓吹美国文化的先进性,以此来诱惑接受者最大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害怕自己被戴上“反现代”的帽子,从而竭力去认同美国形象。在这种引诱与迎合之间,美国以“现代性”扩散的名义实施着操纵第三世界文化之实。
2、政府管理机构。如果说,境外出版集团的种种博弈策略,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产品输出过程以攫取海外市场的超额利润的话,那么,政府管理机构在这一博弈竞局中的核心目标却是如何保护本国出版企业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对外宣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政府机构虽然可以通过制定“倾斜性”甚至“不对称性”的政策帮扶本国媒介获取优势以保证和保护本国利益,但又需考虑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多边利益平衡,政府在谋求融入全球政治经济新环境时必然会以文化产品的开放准入作为“机会成本”之一。由于中国入世,当保护性时间表到了倒计时的执行期,政策壁垒对合法化、市场化竞争特别是不抵触政府宣传权的理性竞争的制约会逐渐弱化,以此来换取我国的经济、文化产品进入世界大市场的机会。
3、本土出版商。作为版权贸易博弈竞局的“第三方”——本土出版商,则常常处于酷似博弈案例中著名的“囚徒困境”——一种“左顾右盼看政策,前思后想找资金”的两难境地。与分别拥有政策资源强势和产业资源强势的政府管理机构和境外传媒相比,本土媒介均处于弱势地位。主要原因是政府管理机构、外资媒介的主要诉求目标都近于“一维”,而需要不断寻求政治、经济“二维”利益平衡点的本土媒介将遭遇更加复杂、艰难的竞争环境和博弈选择。特别是在双重博弈(政府管理机构的“游戏规则化博弈”和海外出版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博弈”)的“内控外压”之下,本土出版商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博弈关系——一方面要服从服务于本国政府的舆论宣控引导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在许可的范围内、在与境外出版集团的竞争合作中寻觅产业化发展的机会。虽然在大多数时候处于相对弱势的本土出版业会尽力走好“钢索”,但也难免出现失衡乃至摩擦、矛盾。这样的两难境地显然不适于本土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在这场博弈竞局中,处于弱势的本土出版业究竟如何才能摆脱困境,更好地打入国际市场,与海外强势出版集团展开竞争?
二、本土出版业的对策
博弈理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指出了在动态博弈环境中,任何博弈方都不可能无视其他各方的存在,各方作出策略选择时都会相互制衡,以及充分考量其他博弈方的可能性决策,变数颇多。那么,我国出版界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博弈竞局中一切利己的变数,以改变博弈方的力量对比,建立更有利于我方的全新博弈竞局。
1、改变观念,赢得地位,转“守”为“攻”。
我国出版界长期以来在版权贸易竞局中一直处于守势,除了资金、规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思想上的谨小慎微、固步自封也有很大关系。记得一位编辑在参加完法兰克福书展之后,盛赞其规模巨大、设施完备、参展图书精美、摊位布置新颖,谈及收获,则以此次中国各出版社共引进了多少版权,学习了何种先进经验为荣。没错,国外具有价值的好书应该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经验是值得好好学习,但不可以此为终极目的。现在,从政府部门到各出版社似乎都形成了一个误区:我们参加国际书展是去参观、学习的——不要忘了,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出版社参展的最终目的是出售产品(图书或版权),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产品建立充分的自信,不能在世界图书市场上主动出击,那我们就永远无法抢得先机。
2、适当利用“制度成本”,善用“规则致胜”。
如果说,外方出版集团的优势在于资金、内容等硬件设施,那么,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本土管理机构的政策杠杆调节。这是博弈竞局中于我们有利的又一变数条件。政府管理机构应当利用现有政策杠杆抢先“将管理政策法制化,将政策管理法制化”。这并非同语反复,而是说既要把原则、精神、意见等“软要求”尽可能地转化成“硬法律”,又要把问题、争议、分歧等“行政性处理”转换成“法制化管辖”。比如说默多克新闻集团为打入英国电视体育传播市场曾雄心勃勃欲收购英超巨无霸曼联队,虽然商业谈判一帆风顺但却遭到英国政府及议会以反垄断等为由的投票否决。这可谓政府机构以“规则”博弈的典型案例。
3、确立国际出版的观念,注重文化产品输出的对口性、适应性。
我国出版界对外版权贸易的又一重要误区就是产品输出的对口性、适应性差。事先不充分研究了解目标销售国的文化传统、阅读心理,使得参展图书缺乏市场,自然难以输出版权。就选题内容而言,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医、武术、儒学道学、历史等为主。也许,我们参展者的本意是要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但这类书籍在海外毕竟缺乏广泛的受众群,且年复一年,书籍选题差别不大,自然难引起外国出版商的兴趣。就装帧而言,我国的参展图书在制作上普遍采用纸皮书装订,色彩变化丰富,定价低廉,这可能适应了国内购买者的口味,但却与国际惯例背道而驰。例如美国出版界就对纸皮书和精装书的区分严格,硬壳精装书大多开本较大,选料考究,装帧精美,多数采用小牛皮封面,烫金字,定价在大众纸皮书的10倍以上。而纸皮书通常被认为是大众的、廉价的娱乐消费品,至今美国许多严肃的书评杂志拒绝评论纸皮书。如此一来,自然给外国出版商留下了缺乏吸引力的整体印象。就受众而言,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出版社编辑的做法,把作品类型分得很细,如小说就分为罗曼史小说、冒险小说、西部小说等等。罗曼史小说又分为“冒险——浪漫”型、“穿越时空”型、“国际婚恋”型、“灰姑娘”型等等,每类都由专门作家撰写,基本上做到了“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书”。而在这一点上,我国出版界做得还很不够。
4、充分利用多种融资渠道,积极筹措资金,改变本土出版业规模小、资金少、被动防守的局面。
众所周知,我国出版界难以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资金匮乏。这也是我们与兰登书屋、贝塔斯曼、朗文等超级出版集团难以抗争的根本。因为,外方出版商的种种优势,归根结底来自于资金优势。资金充足了,自然容易做大做强,自然能以充分的先期投入打开市场,自然可以大规模吸收、雇用我国和贸易所在国的优秀人才。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潮下,“资本意志”正逐渐成为版权贸易竞局的决定意志。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方出版业界必须及早转变观念,大力吸引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然后以全新的面貌、雄厚的资本、磅礴的气势,重新投入到这场博弈竞局中来;以充分的自信,彰显文化大国的气魄与风范。否则就只能落入资金不足——宣传营销无力——外界(外国)知之甚少——缺乏国际影响力——无法达成版权输出——资金无法回笼的怪圈。
5、大力培养我国优秀的双语创作、翻译型人才。
翻译质量是影响图书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就认为中国作家不能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是翻译质量不高。翻译不仅要有过硬的外文功底,更要有良好的中外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的综合素养。如此才能使译文“信、达、雅”,同时又充分尊重各国语言习惯和风俗、宗教信仰的要求。举例而言,中国传说中龙是吉祥的尊神,而在西方传说中,“dragon”(龙)却是凶残的喷火怪兽。所以,英美人对我们自称“the son of dragon”(龙的传人)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硬译”尚如此误事,更遑论错译!此外,有时“美文难译”,作品文笔之美是很难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我们应大力培养本土的双语作家,提倡作家用外语创作。中国在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中有不少人具有很高的英文水平,如林语堂(《京华烟云》)、梁实秋(《槐园梦忆》)等,这应是今后中国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
6、充分利用外方现有的引进、销售渠道,同外方版权经自己人积极展开合作。
正如外方出版界极力吸引本土人才一样,我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大力启用西方出版经纪人,凭借其对图书市场的了解和熟悉迅速打开市场,这样也有利于节约资金。如阿来的《尘埃落定》通过经纪人桑蒂与美国著名的纯文学出版公司米费林出版公司达成版权输出协议,就是一次成功的运作样本。
7、积极融合、溶入到国际出版竞局新秩序中去,在国际大竞局中打上“中国制造”。
中国经济界有这样一句应对WTO竞争压力的名言——“狼来了”,要想战胜狼,自己首先得成为狼。换言之,中国出版业界只有先具备了足以和国际出版巨头一争高下的实力,才能真正在这场国际版权贸易的大竞局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出版界综合实力的体现,并不仅仅是上文论述到的资金、人才、行销渠道之类,我国出版界的自身形象与品牌价值更是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制造”的物质商品已经走向国际市场,但是如何让特殊的精神产品——图书在国际国内市场中更多地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这将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经济安全和利益的长远之需。
标签:博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