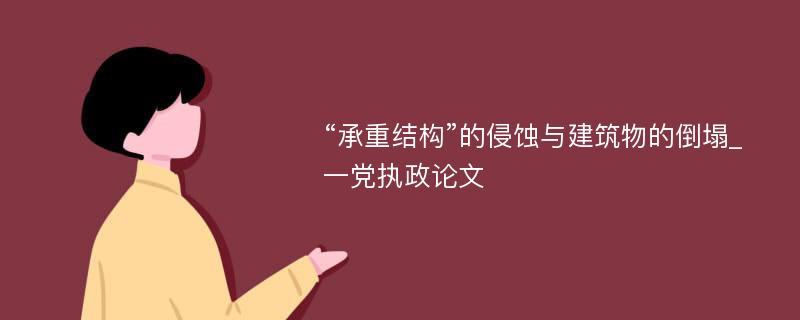
“承重结构”的销蚀与大厦的倒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厦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新年钟声敲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按惯例发表的新年献辞中说:“最困难的一年已经被我们送走,我们国家挺过了这一年,也作了不少斗争,未来一年对我们不同寻常,解决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就落到未来这一年。”谁都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这句话竟在新的一年里成为谶语:一个多民族的超级大国在一夕之间轰然倒塌,举世震惊。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大国衰落的事件发生,可是不论从衰败的原因或者衰败的进程来看,人们很难找到与苏联的败亡大致相类似的案例。这一事件发生如此之快,如此出人意料,连早在20世代70年代就预言苏联将“分崩离析”,而被西方学界称作“苏联问题的诺斯特拉达穆斯”① 的法国学者爱连娜·唐斯科,后来在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诚实地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1]
苏联解体的几种解说
15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本文在这里略加解说和评述。
其一,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其二,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2],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3]。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其三,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其四,腐败导致党衰国亡。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5]。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6]。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苏共:大厦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在关于苏联解体的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值得关注苏共的强弱、兴衰这个重要因素。苏联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都实行着“共产党的垄断”[7]。共产党不但执掌着政权,领导和确立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而且掌控了国家的所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70多年来,苏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有一个由盛及衰、最后丧失执政地位的跌宕起伏的过程。
苏共是列宁亲自参与缔造的党,依靠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支持,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发扬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一举夺得了政权,成为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盟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是苏联这座大厦的“承重结构”。毫无疑问,承重结构的牢固还是脆弱,对一个建筑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掌政权后,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党执政”的局面。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带领俄国走上国家振兴、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之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陌生的,无前例可循。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列宁和俄共(布)保持着强烈的“革命党”意识,主张建立“绝对强硬的政权”,以对付十分猖獗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并试图用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执政党面临的种种问题。列宁时期,国内外局势非常严峻,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依靠共产主义理想焕发起来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新国家的坚强决心,使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终于站稳了脚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执政的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认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正如当年亲临其境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说:“据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8]
但是,列宁的早逝使新经济政策的前途未卜,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苏共又未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变,致使确立斯大林在全党最高领袖地位以后,一方面,由于五年计划的实行,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依靠意识形态宣传的强大功能,社会主义信念开始深入人心,加上对领袖个人崇拜风气的蔓延,使苏共的执政地位空前巩固,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的执政模式,也留下很多隐患。人们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已有很多评述,本文着重对苏共执政模式进行一些剖析。苏共执政模式从初期一直延续到晚期,戈尔巴乔夫试图对其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使苏共走向衰败,苏联走上不归之路。
苏共执政模式的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执政理念陈旧僵化。苏共曾经是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岁月,在新旧阶级的无情搏斗中,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发挥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是苏共克敌制胜的武器和法宝。然而,随着时间和条件的转移,国内阶级斗争逐渐淡出,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和主题。斯大林一面重视抓工业化建设,另一面仍严密注视党内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强化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功能,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他在给列宁主义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中,强调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样,就把执政党的功能依然定位在抓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之上,以“巩固和扩大专政”。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必须保持强烈的“革命党”意识,始终把“斗争”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
与此同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苏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它把经典著作的思想“教科书化”,抽去其活的灵魂,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禁锢了众多党员干部、大学生和学者的头脑。即使到了后斯大林年代,斯大林的肖像和语录虽然销声匿迹,但思维方式依旧,在时代变迁和具体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还要到经典作家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语录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发展平稳,思想界也死水一潭,一场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大讨论,变成了引经据典、空洞抽象的概念游戏,对实际生活不起什么作用,这是进入停滞时期的标记之一。苏共执政理念,看似十分正统、正规、无处不在,又与外部世界隔绝,似乎筑起了一座牢固的意识形态堤坝,可是经不起风浪的冲击,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一打开“闸门”,整个堤坝就坍塌了。
执政体制弊端显露。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搬用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这是无疑的。苏联建立的一党执政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政党制度,本来没有什么好与坏的绝对标准。政党政治的内在要求是推行现代民主社会的构建,进而推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列宁曾经反复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可否认,对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党体制,列宁的思想是有变化的:从原先倾向于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方向下多党合作、联合执政,到认同一党执政,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晚年对执政体制没有作出明确的表示,但倾向于在苏联建立一党执政的模式,这是可以肯定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局势过于严峻,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纷争又过于复杂,以致执政党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妨碍了苏维埃政权的正常运行,而一党执政比起多党联合执政要简约、省力、安全得多,办事效率也可能高一些,这也许是列宁改变初衷的缘由。
在苏联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时候,列宁已身患重病,他对这一体制的是非优劣,已不可能作深入的考察,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发。从理论上对苏联的一党制加以论证的是斯大林。他认为,在苏联,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是国家、社会、各群众团体唯一的领导党,1927年9月,斯大林在接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时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9] 斯大林不仅把一党执政提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几乎把它提到规律的高度,显然是十分片面的。
一党执政的体制在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及各种政治运动中,起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去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的作用。当然,一党执政往往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民主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因此,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要求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制定和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以使国家公共权力合理配置,权力运作能置于法律、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并使各种社会力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这也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求党的干部忠实地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苏联后来的发展,却是使一党执政弊端不但不能克服,反而恶性膨胀,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公共权力被滥用,民主空气被窒息。以苏共干部制度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就实行一种官职等级名录制(Номеиклатура),按此名录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由于可以不经过民主选举程序,执政党干部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官职,助长了一些人追求职位,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以权谋私,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赫鲁晓夫试图对干部制度进行若干改革,推行任期制和轮换制,却因为与既得利益相关,遭到许多干部的反对,成为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所以当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
执政能力的衰竭。执政能力是指一个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它包括执政党在驾驭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及抵御各种风险等诸方面的能力。可是,在苏共长达74年的执政进程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历届领导人几乎越来越平庸,党的整体执政能力也越来越走下坡路。
执政初期,俄共(布)面临的局势十分险恶,紧急突发事件接连发生,解散立宪会议、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分裂、列宁遇刺、战乱与饥荒,国内战争结束后仍不平静,不少地方农民因不满粮食征集制而蜂起暴动,工人士兵也对新政权不满,直至发生喀琅施塔得兵变,党内又出现工会问题的大争论,在这样极端复杂危难的条件下,列宁和俄共〔布〕表现了坚强的毅力和应对各种危机的本领,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个“婴儿”,显示了高超的执政能力。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苏联主政近30年,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突出成就使苏联在不长时期内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这一时期给劳动者带来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福利保障曾使东西方人士惊羡不已;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已经永远镌刻在史册上。斯大林及联共(布)尽管在这一时期犯了个人崇拜及大清洗等错误,但它的执政业绩是不可磨灭的。不管人们对斯大林作什么样的评价,他坚强的意志和处理国内外事变中机敏的应变能力,却是公认的。
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党的执政水平每况愈下。马林科夫承认自己因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辞去领导人的职位。赫鲁晓夫在一些领域里有开创性,但他缺乏理论修养和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应有的风度,决策主观随意,朝令夕改,在处理外交风波中更显得捉襟见肘,经常陷于被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主政18年,史称“停滞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暮气沉沉,鲜见活力,究其根源在于执政党已经褪色,逐渐丧失了先进性。勃列日涅夫晚年体衰多病,基本上丧失治国能力,但由于他是党的总书记,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苏共又没有相应的领袖任期和更替的机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领袖集团年龄老化,思想保守,拒绝革新,终于把党和国家拖入危险的深渊。
执政方法简单粗暴。苏共长期以“革命党”的观念治国理政,与此相适应,在执政方法上也袭用革命风暴年代的许多做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过度使用专政手段,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苏维埃政权初期,针对敌对分子疯狂的破坏活动,俄共(布)不得不建立铁的政权,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然而,当新政权得到巩固,尤其是当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日程,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时候,20世纪20年代末叶,苏联在工业领域以破获“沙赫特案件”为由,大肆清查和镇压工厂企业里“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活动;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极为严酷的“消灭富农”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出现的一系列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政见的争论。党内出现反对派是常见的现象,可是,苏共不但把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党,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几次“大审判”中,无视共产党执政同样需要依法治国,大肆践踏民主和法制,在大清洗的名义下将一大批反对派分子作为外国间谍、杀人凶手、人类渣滓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和忠诚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那种明显践踏法制的事件,但强力部门的目无法纪,将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集中营的消息仍时有所闻。
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持续不断的批判,是苏共执政的重要方法。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确立共产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苏共先后发动对德波林、波克罗夫斯基在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很快波及所有学科领域,严重压抑了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精神和创新意识,意识形态控制也筑起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壁垒,极大地滋长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
政治动员是苏共常用的一种治国方式。依靠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依靠各级党组织的保证作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头作用,去完成某项重大工程,去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有时是适用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厂、农村开展的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垦荒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卫国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这种形式毕竟不符合科学执政的要求,且不能常规使用,因此它的作用有很大局限性。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动员,则常常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二次大战前期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迫使一些少数民族大迁移,埋下了日后联盟国家瓦解的祸根。
思想教育工作的疏失,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失落。长期以来,不能说苏共不重视这方面工作,1934年苏共中央曾作出决议,统一编纂5本历史教科书,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3位党的领导人还亲自过问,提出纲要“意见书”,指导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提出要“不惜钱财”,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可是,苏共中央将思想教育理解为一味简单化、教条化的强行灌输,全然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青少年思想的实际状况,不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这一切表明,苏共作为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承重结构”,未能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而且任凭体制内外各种消极因素的侵蚀,到了晚期,支撑这个超级大国的承重结构已经相当脆弱了。
苏联剧变的理论思考:历史合力的结果
苏联解体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之一。这一罕见的历史事件在引发人们的感慨之余,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乃至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研究。
就苏联解体的原因而言,可以也应该有多种视角进行研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外部的、内部的、主观的、客观的……等等,在一部著作(哪怕是所谓“巨著”)中,要想穷尽所有的原因,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得出一个公认的权威的结论,恐怕也是徒劳的。这使我们想起经典作家的“历史合力”说,这一学说准确地说明历史的发展、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不能以某种“因素”来裁断一切、决定一切,哪怕这是极其重要的关键的“因素”。在人类思想史上,历来都有人认定社会是由某种“因素”决定的,于是,100多年前,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出现过用“经济因素决定论”等观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对此,恩格斯晚年作了不少评论,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综合的”而不是“分解的”观点去看待历史的,“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确不爱到处乱引经济因素。不但如此,就是问哪一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在他们看来,这也是毫无根据的问题”。[10] 本文着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也只是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个视角,把它融入到发生这一事件的“历史合力”中去。
人们通常认为,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高度统制的思想文化体制。然而,苏联模式恰恰是从苏共模式的母体里带来的,并在苏共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执政者和领导者,因此,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组织制度、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就往往与国家的体制结构、发展战略、运作机制、干部制度、施政方式等融为一体,而“革命党”观念的长期没有转变,致使在执政时期仍运用革命时期的许多原则和方法去看待和处理面临的新问题,其制度设计(诸如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又存在许多重大缺陷,因此,当这种原则和方法固化为体制以后,就以其惯性和刚性牵引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蹒跚前行。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体制可以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其内部结构却是有严重缺陷的、僵硬的、不合理的,因而是相当脆弱的。
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新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执政的苏共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掌控着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11] 这是相当形象而又准确的描述。笔者赞成俄罗斯学者的这个观点,并借用这一观点阐释自己的看法。
承重结构对一座建筑物的质量和牢固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吸取苏共这样一个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加强执政党建设,不断加固我们党作为承重结构的内在质量,以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①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年),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占星家,曾经预言欧洲及世界500年后历史的发展。
标签:一党执政论文; 斯大林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论文; 巴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