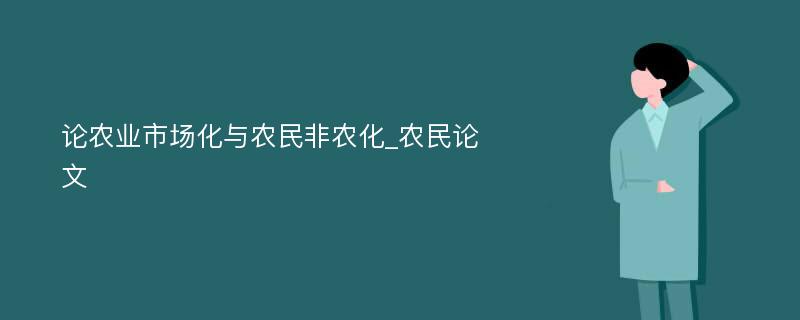
论农业市场化与农民的非农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农民论文,农业论文,市场论文,非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以联产承包制为基本标志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释放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连续出现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也得到了改善。但是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工业经济的转移,农业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没能深入下去,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没有继续提高,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和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城市倾向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及随其伴生的体制政策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等等,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所谓“三农问题”。实践证明: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首先,只有根本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才能真正使有限的土地资源真正实现市场化配置,从而提高其配置效率。土地是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资源。只有它实现了真正的市场化配置,农业的市场化才能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和企业化才能成为现实,才能使农业大国拥有真正的农业产业优势,“三农问题”才能真正的彻底解决。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改革只是一种“半截子”产权改革,农民相对完整的土地财产权至今不能确立,我认为这是农业经济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根源之一。现阶段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真正的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保障。同城市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一样,农村中乡、村干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表,随时干预农民的自主经营。在广大农村,土地权利的含金量越高,土地的所谓集体所有权就越在实际上转化为干部的支配权。由于农户的土地产权不完整,土地使用的预期收益不确定,从而对土地的使用和开发的长期激励严重不足导致土地摞荒现象严重。二是农民只有对土地的有限使用权。农民只能以农业方式利用地表资源,如有地下资源,不仅承包户没权开采,即使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乡、村权利机构也无权开采。也就是说,农村不完全是农民的农村,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如能源、矿山、森林等,农民不能拥有平等的开采权,也不能正常地享有这些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一切主要资源的开采权,而农村和农民不能对自己家门口的资源进行开采,或者分享开采这些资源所取得的收益。三是农村土地资源不能根据市场原则流转,从而提高土地的边际收益由于农民本身不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且农户不能自主地配置土地的有限权利,土地也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配置。正是由于土地的配置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造成了农业的小规模、高成本经营,从而成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和规模化的最大障碍,使我国农业的特质没有根本改变,迟迟没有培育出农业大国的农业产业优势。其次,只有农民拥有了自主择业、自主迁徙、自主经营的权利,农业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和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隔离政策,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土地上,才导致了农土流转、土地市场化配置难以实现的局面。只有充分尊重农民自主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让其按市场原则来选择就业领域和居住地,才能减少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只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放弃承包的土地,才能将有限的耕地集中开发,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取得农业生产的规模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由此可见,农业的市场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而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又依赖于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的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仅仅立足于农村、农民和农业。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是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其真正根源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根源在20世纪的延续。因此,农业市场化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农业市场化必须以城市化的发展为条件。更进一步讲,农业的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整体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条件的。而且,城市化不仅是指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或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它本质上是指农民社会角色的现代转型,即市民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就是农民的非农化解放,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的平等发展,共同向现代市民转化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时,人口规模大,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现代部门相对较小,且比早期发达国家的相应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在整个就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小,甚至不能满足城镇自身的就业需求。传统部门不仅规模大就业人口多,而且生产率低下,并因此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工业自身积累能力弱,外资输入有限,从而不得不由农业来为工业积累。这一方面延缓了农业的改造和社会的转型步伐,使农业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支持力减弱,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传统的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人口结构被强化,加大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难度。更严重的是,这一过程使城市居民的创新动力和压力不足,养成惰性和依赖心理,从而使其转变为现代市民的过程被延长,不利于城市社会的根本转型。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和早期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起点和外部条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结合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而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很容易跌入“城市化陷阱”。
中国不仅面临着与发展中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城市化初始条件和可能的城市化问题,而且还有自己更为特殊的国情,那就是历史更为悠久的传统农业,规模庞大的农业人口,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乡体制隔离等。由此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也不能抄袭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的城市化经验。诚然,我们也面临着城市失业和待业的巨大压力以及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严重短缺等问题。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跌入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的“城市化陷阱”。但是,就城市化而言,我们还有着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沉重的任务,那就是加快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和农民的非农化解放步伐,同时尽快消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体制隔离,使城市和乡村尽快地向现代开放型社会转变,城市居民和农民在公平的竞争中共同向现代市民转变。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城市化不仅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迁入人口如何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与原有居民间实现真正的融合。即使城市拥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以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使原有的城市居民和迁入人口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权利,而对新入人口采取歧视态度,会加剧城乡利益分化,引发城市内部对立,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城市病变,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陷阱”。
在我国,由于农业社会发展的历程非常漫长,加之历代各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致使城市主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经济贸易功能没有得到应有加强,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尽管经历了近现代的发展,城市居民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城市社会也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前,可以说中国的所有居民都是农民,而并没有peasenty与citixen之分,有的只是社会等级阶梯之别,即有权的农民和无权的农民,城市农民与乡居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保障并受到严格约束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从而约束也不太严格的农民之分,正如发达国家有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市民与从事农业的市民,有住在城市的市民与乡居市民之分一样(秦晖1998)。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化就是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就是所有居民从传统农民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它包括:农业的市场化改造和乡居农民的非农化解放;城市社会共同体的现代化改造和居民的现代转型两个方面,其中农业的改造和农民的非农化解放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中国的城乡人口结构中,农村的居民占有绝对的比重,故而他们的现代化对于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与市场化改革相联系的:是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以及从传统的“习俗——指令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等三个过程的统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角色转换与农村农民的非农化解放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从而构成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的一个基本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以城市权利为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和劳务,城市权利中心向农村辐射的依附性共同体制度。其实质就是城乡之间的隔离和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与统治。这种依附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强化也形成了城市人对农民的相对优越感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制度和观念的相互强化又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更深隔离。解放后,在农村重新强化共同体——人民公社实际上抵消了近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农民个性的逐步独立化发展成果,加深了农民的依附性,在此基础上实际的城乡分离的两套体制割裂了城乡之间的正常交流,弱化了社会的开放性发展,从而不利于城乡居民的个性解放,即向现代市民转变。同时,城市工业通过“剪刀差”等政策和体制从农业取得资本积累延缓了农业的自身改造,而且政府给予城市居民高于农村人的社会福利保障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心理失衡:养成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和惰性。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不应再坚持所谓城市改造农村和城市人改造农村人的传统观念,而应该让农村居民的非农化解放以向现代市民过渡和城市居民的市民化过程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其中,城市原居民和新迁入者之间平等相处,共同竞争,共同发展和进步是实现城市社会开放性发展的基本内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隔离的旧体制和工农之间的“剪刀差”政策虽然都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由于旧体制仍未能实现根本性突破,特别是城乡隔离基本标志的户籍管理制度,仍然从根本上阻止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体制。同时,由于相对于农村居民的优越感在城市人口中(也包括部分领导干部)根深蒂固,即使进入城市的原农村居民(其中分为已入城市户籍的人和虽已入城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原籍的人,后者在整个迁入者中占大部分),也很难在制度和文化心理上与城市居民实现真正的融合,即进城者虽然人入了城,但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体制和城市社会,原有居民和新迁入者仍然生活在两个体系之中,如当城市出现失业或者再就业压力增大时,城市当局几乎本能地选择了清退“农民工”(从这一名称上就能直观地体会出城市人对农民的优越感)和限制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规模等保护城市人既得利益的作法。如果不打破城市在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封闭性,使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全方位地向农村居民开放,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不能使城市社会尽快地向现代社会转型,从而也不能使我国的市场化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等发展和共同发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