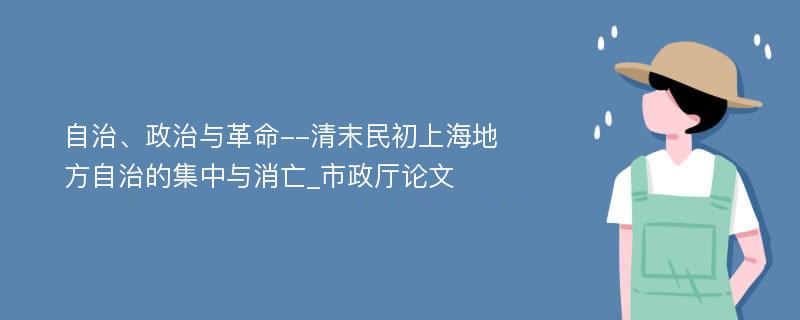
自治、政治与革命——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中心化及其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上海论文,政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9-0135-09
1860年以降,上海的地位迅速崛起,使它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中担负起了社会中心的角色。姚公鹤认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① 这一格局,使得京、沪在自治和一体化民族国家双重路径下暗流涌动。拨开浮于表面的以各自利益为基础的话语言说,可以发现,一方所要表达的是对上海地方自治的固守,另一方则是对一体化民族国家整合式目标的追求。两者之不能调和,决定了上海地方自治的命运。
一、“拆城案”变化轨迹揭示上海自治政治化历程
了解上海自治政治化过程,“拆城案”是一把钥匙。它清晰地表达了上海社会的权力结构、分裂和融合,以及如何在拆城主题下将帝国官僚体系拉入到上海权力结构中。
上海的城墙历史悠久,在上海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自治机构成立后,多次提出拆城,但由于受到各方掣肘,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才完成拆城工作。这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市政工程机构:总工程局的拆城案及其折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元月十六日,上海自治领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等三十一人联名上书上海道台袁树勋,拉开了“拆城案”的漫长序幕。
总工程局提出拆城议案的书面理由是,为了改善城厢交通,繁荣商业,防止租界向华界扩张。拆城对社会、心理、文化造成的冲击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然而,让人费思的是,上海自治领导阶层何以提出一个貌似激进主义的议题,而将自己投入舆论的旋涡之中?在笔者看来,拆城议案之所以提出,可以看作是上海地方自治的高调登场。它揭示了地方自治领袖没有言明的对地方自治的认知、定位、抱负和雄心。当拆城工程把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权力主张纳入进来后,它本身已隐含着政治化转型的潜在机遇。
“拆城案”将整个上海士绅阶层划分成了三个阵营:一是以总工程局李平书为首的拆城派,主张拆除城垣,一劳永逸地解决上海交通问题,达到兴市目的。二是以曹骧为首的保城派,认为城垣一拆,上海屏障尽失,盗匪、西方势力乘虚而入,上海有可能被蚕食。三是以孙文诒、郁颐培等为代表的驰城派,主张城门二十四小时开放,以满足城内通行需要。各派观点经过三年多的反复讨论,以及官方内部的反复协商,决定在原有城门的基础上新辟四门。在这场争执中,地方公益研究会喧宾夺主,几乎主导“拆城案”的进程。反对拆城的曹骧和地方公益研究会有很深的渊源,城门马路的绘筑、新辟城门的选址,在初期都由这个机构完成。② 从其积极性来看,是想造成辟城的既成事实,以降低拆城之议的声音。
总工程局虽在拆城上影响力不足,但对拆城的初衷十分坚持。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皇帝朱批核准上海辟城,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八月间,总工程局仍然坚持拆城念头。后来,因遭到督宪的明令禁止,拆城议案才真正走上辟城之路。③
然而,提出拆城议案并非毫无收益。总工程局在成立之初几乎悄无声息,无人重视。自治领袖将拆城这样一个全屙眭、历史性宏大议题提上桌面,迫使上海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人物都卷入进来。这个议案也使上海社会上至士绅下至普通市民都知道总工程局不是可以忽视的存在。甚至自治领袖在拆城议案上的坚韧意志力,迫使督抚和光绪皇帝也卷入进来,就拆城议案发表意见。拆城议案虽然受阻,但一个僻处江南的地方性工程机构引起皇帝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1909年,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几乎就是以上海总工程局的规章为模版,可以说是为拆城议案打下了基础。
(二)寻求自主化声言:自治公所城濠公地争执案
自治公所是根据清政府《城镇乡自治章程》于宣统元年(1909年)由原来的总工程局改组而来。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在完成辟城后,又提出了收回对城门的管辖权和城濠公地的处量权。作为“拆城案”的延续,自治公所在城濠公地争执案中面临两个对手:一方是以提督为代表的公地实际控制者绿营,另一方是以何琛、唐锡瑞等为代表的公地租户。
针对绿营,自治公所认为,军政与民事不应混淆,地可出租即与防守无关;④ 地方卫生事宜,应由公所负责,不能为了绿营利益损害主权。⑤ 提右营则认为,军用重地不能由局外人干预。根据江苏会议厅第三次议决清查荒地案声明,土地为国有产业,地方自治若以团体名义据为公产,是国有与公有界限相混。⑥
针对公地业户指责自治公所自命为公法团,实为逐利放利,⑦ 自治公所进行了驳斥,认为“自治团体为国家特定之公法人,整理道路河渠均在自治范围内”⑧。请求两江总督严惩唐锡瑞等人,以挽回声誉。
自治公所在与绿营争夺城濠公地及派警接替绿营驻守城门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硬立场;在与地方利益团体争夺公产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个自主化机构的面目。虽然在以官权力为核心的中国政治体系中,仍然不能争得城濠公地和城门的管辖权,但它寻求自主化的立场已表露无遗。
然而,自治公所在强硬的立场和表达背后有一个软肋,即自治公所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个软肋既被提督抓住,也受到公地租户的攻击。从前者来说,自治公所体现在一个“公”字,官权力体现在一个“国”字,公权和国权之间有一道鸿沟,难以跨越,所以,提督对国有和公有的解释使自治公所回应乏力。从后者来看,唐锡瑞等公地租户也抓住一个“公”字,试图将自治公所矮化为与其他普通公共团体类似的机构,是一个自私的利益团体。针对提督的批评,自治公所只能用军民两分的立场来回应,实际上是将自己限定在民的地位上,成为提督“公”“国”鸿沟的注脚;对于公地租户的批评,自治公所除了援引法律条文外,主要强调自己是一个为全上海谋福祉的团体,通过宣扬道德正当性来说明自己的地位,仍然不能超越“公”团体的地位,无法跨越“公”“国”鸿沟。
(三)政治化和自主化的确立:市政厅拆城案和城濠公地案的立决
市政厅是在辛亥革命所昭示的一个新时代背景下对自治公所的改组与延续。它与自治公所相比有更强烈的自主化利益诉求,并借助辛亥革命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取得了只有一个地方政权才具有的权力。市政厅在实施拆城的过程中,有意回避了讨论过程,通过快速拆城⑨ 使反对声音无效,并在“武力看守拆城”这一符号化场景中表达了市政厅的“强权”特性。⑩
上海市政厅汲取了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时期拆城的教训,拆城的动议和完成几乎在瞬间实现。民国元年(1912年)1月,“辛亥光复之后,县议会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决议拆城……不一月而东北西三面均已拆毁一空”(11)。
市政厅对拆城议案的解决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有一个大的转变,即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是在帝国体系下依循体制内规则寻求解决方案,帝国体系是仲裁者,自治机构与上海其他利益团体不过是利益主张的平衡的一部分;市政厅则打破了帝国体系在上海社会的存在,以议事会为支撑的市政厅取代帝国体系,成为仲裁者,市政厅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团体之上,这使拆城案的解决成为市政厅体系内的一部分。
借助上海光复的契机,上海市政厅完成了政治化和自主化蜕变。但这一变化对于地方自治的前途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以上海市政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北洋政府就地方政治化和自主化展开了持续博弈,整个博弈过程始终没有点明“政治化和自主化”问题,但各方势力无论是提出“安定”口号还是“反袁”口号,都围绕着对上海的控制展开,上海市政厅也在各方势力博弈场中、在经历初期的短暂兴盛之后,迅速走向衰亡。
(四)“拆城案”揭示自治机构“强权”本质
从辛亥光复前后在拆城案和城濠公地案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自治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总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再由自治公所到市政厅。这一变化,表现出了鲜明自主化特征和“强权”色彩。
首先,自治机构和上级权力机构合二为一,演变成政治化和自主化地方政权机关。1912年以后,市政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政自主统系。李平书对此曾有过一段评论,“论地方办事机关,惟民政长、市政长为一切政令所出,而民政长直隶都督,并无别项长官可以管辖。市长直隶于民政长,亦无庸加以长官”(12)。
其次,“拆城案”在光复前后的逆转,说明了市政厅摒弃和平自治方式,而以武力为基础实现对城墙的拆除。即以地方政权机构的身份发布行政命令,放弃了常规的商议和表决,表现出一个政治主体才具有的特征。
“拆城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寻求拆除城墙的过程,实质上却是一个抗争的过程。上海城墙的最后拆除与自治领袖的个性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拆除城墙一直很坚持,也有一举拆之的决心和勇气,但之所以在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时期都没有办法完成拆城,是因为个性的坚强、勇敢都被程序化的制度扼制了。这个程序化的制度是凌驾于自治机构之上的帝国体系,议事会通过的决议在帝国体系面前是无效的。而当辛亥之役使帝国体系下程序化的制度被打破之后,长达六年的郁积的愤懑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饱受争议修修补补的城墙在一夜之间被拆除了。与其说现在对城墙的拆除是为了畅通城厢内外的交通,不如说是对凌驾于自治机构之上的帝国体系颠覆的象征。随着上海城墙的轰然倒塌,上海自冶机构的政治主体性地位亦随之建立。
二、自主与统一:一对结构性矛盾
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普通民众的心理受到了猛烈冲击,社会变化之速、景象之混乱让人难以适应。新秩序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但没有真正成型,社会处于一种兴奋的骚乱情绪中。以前存在的惯习仿佛一夜之间被扫除了,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些可以跨越的边界,而另一种使生活回到常轨的边界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出现了许多可以被评定为怪异的景象。(13) 评论认为,“自辛亥武昌起义,未及半年,而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共和进步之速,实古今中外所罕有。然政制易改,人心则不易改”(14)。
(一)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充满风险的上海政治形象
上海借助辛亥革命的契机,跨越了社会中心的边界,成为了临时性的政治中心。上海自开埠以来取得江南重心的地位之后,还从未获得过政治中心的地位,其政治形象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边”、“野”、“影”。“边”是指边陲,在帝国体系中是末梢之地。“野”是指在野,旅居上海的最高级别的官吏是道台;另有其他一些退任官员闲居,高级别的官员由于坚守“华夷”大防,在潜意识中将上海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污点,不肯轻易涉足。“影”是影子、幕后,高级别的官员来到上海也是偷偷地来、偷偷地走,不肯声张;“影”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上海不是正统政治的焦点,但它是幕后政治的策源地,反政府的中心。
上海市政厅成为政治化自主机构,正是“影子政治”的胜利。而“影子政治”的胜利带动了边陲向核心的进发、在野向在朝的转换。但是,上海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结构使边陲和核心之间的相对关系很难长久维系。上海临江、临海及租界文化带来了高度的市场繁荣,也成为上海政治形象的致命伤。西方势力在上海化外而居,使上海成为“他们”和“异类”,与正统政治中的“我们”和“我族”对立;上海可以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城市,但不能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的中心。上海可以成为光复华夏的大本营(15),但它不能成为华夏的大本营。对于光复华夏而言,上海与清王朝相比是正统;相比于光复后的华夏而言,上海只能是一个异类。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可以选在武汉,也可以选在北京、南京,但就是不能立足上海的原因。
这种在特殊状态下形成的权力格局和光环效应是异常而非常态。上海可以凭借先于南京独立取得暂时政治地位,但上海自治领袖在潜意识中缺乏领导全国的精神气质和愿望,在本质上他们是事务性官员而非感召型领袖。他们可以把上海的市政、教育、慈善做得井井有条堪称全国模范,也可以深挖财库筹集资金为辛亥革命输纳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但他们很难走到聚集的人群前振臂高呼成为宏大变革的倡导者。他们是自治领袖而非政治领袖,他们更擅长在一个微观的领域做一些常规性事务,而在一个宏大的场景中则会感到惴惴不安。
然而,辛亥革命的机缘将自治领袖推向了一个历史变革的宏大场景,帝国体系中位于官僚体系上端的庇护者和控制者消失了,自治机构驾轻就熟的一套操作模式瓦解了,现在议事会的表决是最后决定,民政总长的命令是最高命令。对于事务型自治领袖而言,这套体系该走向哪里?无论上端是帝国体系还是共和国体系,上海都应该成为归属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没有依归的孤岛。
归根结底,上海自治是有限自治,它习惯了来自官僚体系上端的庇护和控制,当遭遇困难和障碍时,这个体系能够有效地帮助解决。但辛亥革命将来自上端的庇护体系切除了,自治领袖突然面临自己解决高度分化上海社会中的复杂问题,以及由于巨大社会变动带来的超出上海范围的混乱和纷争,这是辛亥革命带给上海自治的第一个风险。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风险是,上海“影子政治”的胜利强化了上海在正统政治格局中的动乱策源地的形象。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终究要复归常规政治,袁世凯北洋政府是常规政治的代表。在任何一种常规政治模式下,革除“影子政治”策源地的弊端是常规政治主导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市政厅作为光复华夏的影子中心,它势必会威胁到光复后的华夏常规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而受到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的高度戒备和特殊关照。这一风险,在辛亥革命的局势稍稍平定下来之后,就日益逼近了。
(二)自主与统一:促使上海回归江苏省厅统辖的结构性矛盾
上海的特殊地位对全国的政治版图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北京为起点的权力中心建构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上海因素。上海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实质独立地位对全国的统一进程是一个障碍,加上上海是南方独立的策源地、全国社会势力的中心以及借助革命进一步坐大的上海市政厅,诸多要素集合在一起,使上海成为南方与北方、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势力和社会势力盘根错节、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博弈场。在这种背景下,自主与统一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上海迈出了回归江苏省管辖的步伐。1912年4月5日,上海市政厅议长呈请江苏临时省议会,请求“直隶于省会官厅”(16),表达了回归江苏省管辖的意愿。
然而,回归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上海市政厅自主意志所能决定的。清廷覆亡之后,上海社会的政治势力是以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为框架建立的,上海市政厅向江苏省厅的回归取决于两大势力之间的博弈。
两大势力在决裂之前的博弈策略更多地是以非政治性事件展开的,而这一策略给上海市政厅带来了沉重压力。1912年6月,上海发生的军警冲突便是这样一起非政治性事件。6月1日晚,一名由沪防“福字营”刘司令包租的车夫拉客进入上海城内四区,因忘带执照,被站岗巡士查出,双方发生冲突,致巡警伤者十一人。(17) 警察厅与“福字营”刘司令交涉,遭到刘司令否认,认为是“流氓借名而为”。(18) 警员呼吁工商各界联合起来,“设法芟除去此污点”。(19) 后经警界与军界之间多次交涉,双方达成和解协议。(20)
军警冲突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军队代表统一的外来政治势力,警察代表自主的上海本土势力。两者内在的使命担当使一起很小的纠葛演变成一起很大的风潮——明确自己目标和任务的军队借题发挥,摆开了破裂的架势;对政治形势浑然不知的警察兢兢业业于自己的分内事务,而不知自己陷入一场暗藏玄机的事件中。然而,自治领袖对这起偶然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有着敏锐的察知。上海警察厅长穆湘瑶(21)、市政厅长莫子经、副厅长顾馨一先后提出辞职,(22) 可见军警冲突的政治效果。时评认为,“中国今日如在汪洋大海之中”,呼吁政府实行稳健主义。(23) 到1912年7—8月间,江苏省成功取得对上海的管辖权。(24) 与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相配合,言论界一再呼吁实现国家统一。(25)
上海市政厅对于回归省辖很不适应。8月27日的秋季会由于议员多半不到会而流产。(26) 从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权力实体在其地位不定时,常常会陷于瘫痪状态。而在其权力的履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在上海回归江苏省之前,发生军队与巡警冲突,在表面上看是由一件小事所引起,是军警之间的偶然性事件,但在实质上却体现了上海独立与政治统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上海回归江苏省厅,都督府和民政总长被取消后,上海即回到安堵无惊、一派和平景象,揭示了偶然性军警冲突的必然本质。上海市政厅作为自治载体,也面临着深刻危机,自主和政治统一的纠结在潜隐的结构中渐渐浮出水面。
三、“门禁交涉案”:政治杯葛自治的风向标
李平书是上海地方自治的标志、象征和缔造者,是上海地方自治中心化和政治化的主要推手,他也是上海自治领导群体中不多见的兼具事务型和感召型双重特质的领袖。江苏省在收复市政厅的过程中,对李平书所采取的不着痕迹的外科手术具有较深的政治意涵。这种虚置、架空李平书,让李平书从自治和社会事务中退休的策略,所要表达的显然不是让市政厅回归江苏省厅管辖统系那样简单。作为市政厅政治化和中心化的代表,清除李平书可以理解为当局的市政厅去政治化愿望。但后面的事态表明,市政厅去政治化并不是当局政治谋略的底线,其底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自治不休,动作不止。
(一)宋教仁被刺与“门禁交涉案”
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在一些热点地区始终未曾建立常规化的和平统一局面。上海作为热点中的热点,更为各派势力所觊觎。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宋教仁在上海被刺一点也不让人奇怪,而宋教仁被刺与上海地方自治扯上莫大干系则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地方自治被先入为主地打上了党派政治的烙印,并被划入国民党阵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电召赴北京参加总统选举,当晚“十一点四十分,宋君被人枪击”(27),于第二天凌晨死亡。袁世凯下令,“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28)。租界捕房先后逮捕武士英、应夔丞和朱荫榛(29),武士英在狱中自杀。后经政府和租界当局商定,宋案转为普通刑事犯罪,应桂馨、朱荫榛押解归上海审检厅审判。
5月3日,淞沪警察厅决定将市政厅大门关闭,将两人作为普通人犯关押在与市政厅共用大门的巡警第一区,引起门禁交涉案的发生。市议会高调反弹,议决以二十四小时为限,要求警察厅交出大门钥匙。警察厅长穆湘瑶以需等省长和都督批准婉拒。(30)
5月8日和9日,市议会和董事会以警察厅关闭市政大门妨碍办公和主权(31),相继全体辞职(32)。市议会决定起诉穆湘瑶(33),县议会函请县知事调解(34)。
宋教仁被刺已使国民党遭受重创,又因关押人犯而使在辛亥之后具有党人色彩的市政厅闭门,无疑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关闭市政厅大门后来被证明不是一个轻率的举动,而是经过精心谋划的策略之举。
北洋政府对上海地方自治的意图犹如藏在幕布后的牌局,幕布是慢慢揭开的。随着幕布完全揭开,一些似乎比较突兀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才能显示出精妙之处。一年之前,由黄包车夫引起的军警冲突差点让警察厅长穆湘瑶辞职,而穆的欲辞未辞恰似一个洗礼仪式,仪式完成后穆也成了北洋政府在上海的“自己人”。一年之后,借宋教仁被刺案的契机,这个举足轻重的“自己人”突然冲上前台对市政厅发难,而市政厅除了感到惊异和愤怒外,对其深意浑然不知。军警冲突是外(军队)对内(上海)的压制和打击,闭门案是内(警察厅)对内(市政厅)的打击,是地方自治的内在分裂和冲突,而这场角力的设计者是场外的北洋政府。
(二)“门禁交涉案”反响揭示自治成色
“门禁交涉案”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阵阵涟漪。“门禁交涉案”之前,市政厅在上海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人调查,也无统计数据发布。“门禁交涉案”的发生,为上海自治机构的合法性及在上海社会受拥戴的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检验机会。它能证明,上海自治机构到底是一小撮士绅群体的攘利工具,还是上海市民社会的利益诉求载体。
警察厅关闭大门激起上海市民社会的强烈反应,他们通过三种手段向穆湘瑶施压,试图促使穆软化立场,早日解决危机。一是借助《申报》等公共媒体,对穆本人展开猛烈批判,同时详细跟踪报道事态进展,以媒体的发酵效应将穆置于压力的漩涡之中。《申报》两次发表攻击穆本人的文章(35),这对于持论平和的《申报》较为少见,并在半个多月时间中,发表了“九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将“门禁交涉案”不断推向高潮。二是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寻求法律诉讼,并恳请省长出面调停,试图向穆实施法律和行政双重压力。(36) 三是动员与穆私交甚笃又曾长期共事的县议长和县知事出面,以公共威权和私人情谊化解危机。5月17日,县议长莫锡纶(37) 和县知事吴馨从中斡旋,市政厅与警察厅达成谅解,嫌犯迁移关押,门禁危机初步化解。(38)
“门禁交涉案”引起官绅商学、社会团体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弹,从侧面反映了市政厅在上海社会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自治在上海之深入人心。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武力与民意之间的一次冲撞,武力的坚韧性和耐受力是检验自治自主性的一个标杆,而武力闭门背后的政治意图揭示了政治对自治的敌意。
北洋政府借力打力的柔软的推手也探测到了上海自治的群众基础和民气之可畏,认识到了上海自治作为“影子政治”的中心不可不除,但也不能以蛮力铲除,而应以更为含蓄的策略不着痕迹地消除自治的活力,直至取消自治。
(三)自治“强项”揭秘“门禁交涉案”幕后政治黑手
警察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关闭市政厅大门,其幕后的秘密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秉承“长官意志”是一项基本规则,也是官场生存之道。闭门警员自是秉承警察厅长穆湘瑶的意旨,和自治关系如此密切的穆湘瑶又秉何人旨意?闭门是为了关闭嫌犯还是另有所指?
警察厅长穆湘瑶与自治有深厚的渊源,几乎参与自治全过程,历任议事会议员(39)、南区区董(40) 和警务长等职(41);民国成立后,警察从自治机构中分离出来,穆出任警察厅长。穆湘瑶言公言私与自治机构之间有融洽的关系,“门禁交涉案”因私人恩怨发生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门禁交涉案”从5月3日发生到5月18日开禁,共有十六天时间,市议会作出激烈反应是5月8日(42),当市议会和董事会要求开门时,穆湘瑶的最初说辞是“我一日为警长,此大门一日不能开”(43),颇有意气的味道。之后,在压力之下(44),穆湘瑶强硬立场有所松动,向外界表示,在市政厅关押嫌犯是奉都督和省长之命,若要启门需奉省长批准。(45) 至此,才使问题的症结显露出来。穆湘瑶之所以能抵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是有江苏省厅最高层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发出并不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省厅闭门命令的背后,如果没有更深层的考虑,那么作为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命令是不可能发出的,答案是在江苏省厅乃至中央政府内部,有取消自治的考虑,“闭门案”是一个信号气球,以观风向。
在闭门案发生之前,江苏省长有一道通令发出,对自治的一个重要权限进行解释。这个通令发出时间比门禁案早三天,正好形成呼应。通令指出,近来在江苏太仓厅属各乡不断发生自治团体违法侵权、武断乡曲、勒罚款项事件,“官治自治不相越俎……前清地方公事往往由豪绅劣董相与把持,擅作威福。”民国肇兴,“此风未革,异地同然”。(46)
从这个通令来看,中央和省政府对自治已有很强的不满情绪,列举了发生于自治过程中的种种污迹,将前清时期的自治领袖定义为“豪绅劣董”,辛亥革命以来领导自治的仍是这一批人,从身份和道德两方面都给予负面评价。这个通令也采取了以偏概全的手法,将发生于某个地方的自治污迹当作是全国所有自治的总体形象,从而形成了自治的“污名化”迹象。此外,这个通令将自治和官治作了分割,将自治定位于“第三人”,即强调自治的“私人性”。这无疑是在前清自治解释立场上的一大倒退,前清颁行的市乡制强调自治的公法人性质,拥有对公产的处分权。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北洋政府绕路攻远、借力打力的策略是成功的。它在上海自治机构的核心处插入一个楔子,促使上海自治出现结构性裂痕。这起事件是直接关闭市政厅大门,已在民众中形成了市政厅存在关门可能的印象。而且,民众在这起事件中心理应急水平已达到一个高峰,对于市政厅突然闭门的惊异、愤怒、焦虑的情绪已得到有效释放。如果在将来某一天,北洋政府真的宣布取消自治,民众的心理应急将很难达到以前的水平,从而大大降低了北洋政府作出决策的压力。
四、“革命”话语的介入:上海自治政治化的最后声言
“门禁交涉案”是中央与地方两套话语体系一次隐晦的、检验双方影响力的间接交锋,警察闭门带有武力成分,但与“革命”无关。国民党与北洋政府矛盾激化引发的“二次革命”将局势导入了“革命”话语体系中,中央与上海自治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随之也被带入“革命”话语的阴影中,上海地方自治势力试图借助“革命”话语挽回地方与中央话语权争夺中的弱势。但是,随着“革命”话语被北洋政府扫除荡尽,上海自治势力所追求的地方话语体系也随之失语。
(一)“革命”话语的凸起
自从1912年7月上海民政总长和沪军都督府被取消后,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便面临窘迫的境地。“门禁交涉案”虽然揭示上海自治深得人心,但不能改变自治机构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无所作为。在这种背景下,上海自治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利用“二次革命”爆发的契机,试图以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调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两大政治集团的争执,从而维护自治机构的自主化地位。
“二次革命”之由来,约言之,即为袁世凯与国民党之冲突。郭斌佳认为,“谋革命者,最初集于沪。因不得遂其志,乃转而往鄂,又为黎元洪所遏,乃再返沪,而北军开至,防范甚严”(47)。上海市政厅很快作出反应,县知事吴馨、警察厅长穆湘瑶、总董陆崧侯开会讨论局势,“以保护商业,维持治安为唯一目的”。(48) 同时,组织单一上海保卫团,推举李平书为团长,在市政厅内设事务所。(49)
李平书于一年前从民政总长的职位上退隐之后,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上海作为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争夺的主战场,以保境安民为职任的上海市政厅需要作出自己的选择。而李平书作为感召型特质的政治领袖,是不多的可以整合上海各方力量以应对当下重大危机的合适人选。
警察厅长穆湘瑶首先退缩,于7月18日宣布辞去警察厅长职务,在沪各团体遂推举李平书为代理厅长,宣布上海独立,自治机构主要领导人追随李平书(50)。至此,上海市政厅公开走向了北洋政府的对立面。
市政厅追随李平书宣布上海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怪的抉择,是对两大政治势力斗争前景的形势错估?还是“不自治勿宁死亡”的坚定表达?现在都不得而知。但至少李平书在上海社会强大的感召力,以及对1912年黯然退隐郁郁不得志的坚定反击,导致上海自治走上了一条没有归途的叛乱道路。
(二)两套话语体系矛盾和上海自治的终结
在各方势力汇聚的上海这样一个复杂的时空环境中,北洋政府、国民党和上海自治机构在所关涉的题域中是三种主要势力。国民党因为缺乏根基,被北洋政府风卷残云般的迅速击败,在“二次革命”后退出上海,销声匿迹,而剩下北洋政府和上海自治机构两大势力。北洋政府主要借用了国民党留下的政治遗产——上海自治机构在“二次革命”中支持国民党——打击上海自治机构,侵削之,灭亡之。但是,在北洋政府与上海自治机构之间的博弈中,“革命”话语并非起到关键作用。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自有其一套话语体系,而上海自治机构作为一地方性自治机构也有其自身的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是上海自治终结的根本原因。这两套话语体系一方是中央政府在全国政治格局中加强中央集权维持对地方控制的诉求,另一方是上海自治机构在地方视野中追求本地利益和自治机构自主化诉求。
在戒严令之外,中央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侵削和取缔上海地方自治势力:
其一,以柔软的手段迫使复职的穆湘瑶辞职,控制上海警察机构。1913年9月1日,上海设立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任命萨镇冰为督办。(51) 萨镇冰将上海和吴淞巡警划为四大区域,城厢内外一区仍归穆湘瑶继续办理,(52) 以削弱穆湘瑶为首的上海本地人的警察权力。对警察管理权限的变更,给穆湘瑶以暗示,穆在第二天提出辞职(53),获批准(54)。
其二,中央政府规定不允许官员在本乡任职。这条命令直接针对上海县知事吴馨。在这条命令下,吴馨与崇明县令洪锡范对调(55)。吴馨是上海自治的主要发起者,清末民初近十年来上海自治的主要领导者和支持者。上海自治的四根台柱中,李平书以赣宁之役获罪流亡日本,穆湘瑶赋野,吴馨离乡履新,四去其三。另外一根台柱,市政厅现任董参两会受到助逆的指控,自治被钝刀慢慢肢解。
其三,以董事会总董、董事及乡董、乡佐领取薪水,性质与地方官吏相同为由,免除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6) 随后,以国家财政面临困难及自治职员是义务职为由,停给自治职员薪水。(57)
在侵削、打击、抑制上海自治的各项措施全面布局完成后,1914年2月3日,袁世凯终于颁布停办各省自治令。2月18日,上海正式发布停办自治布告。(58) 3月1日,工巡捐局取代市政厅开始办公。(59) 同日,上海戒严令取消。(60) 3月23日,市政厅董事会移交,标志以市政厅为主导的上海自治退出历史舞台。
上海地方自治机构对“二次革命”的深度卷入是中央与地方两套话语体系无法有效对接的必然后果。上海自治机构试图借助“革命”话语实现自己的话语理想,抵制中央话语体系的侵削和控制。当两套话语体系矛盾只能用“革命”加以解决时,两大机构之间的互搏和存亡便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由之,上海自治之终结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上海自治的结束与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因上海而兴,也因上海而亡,上海地方自治是“漩涡”的制造者而非仅随“漩涡”而亡者。上海自治领导阶层以李平书为代表,不甘于平庸,将上海自治机构培养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自治团体,也凭借辛亥革命的机缘完成政治化和中心化转型,这一特征决定了上海自治与一体化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不可调和。在上海这样一个独特的场域中,执政的北洋政府、在野的国民党、完成政治化和中心化的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三股势力互相纠结。夹峙于两大势力之间的上海地方自治势力试图以中立立场维系政治化和中心化地位,但在北洋政府一体化民族国家进程下不可得,转而与国民党结盟以抗衡北洋政府,然而随着无根的国民党被迅速击败,经营近十年之久的上海自治也随之结束。中央政府对上海地方自治的叛乱式定性,拖累了地方自治在其他地区的后果,促使全国地方自治程序性死亡。在这起地方与国家关系悲剧中,上海地方自治的中心化和政治化乃是一个重要的症结。
注释: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50—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 《苏松太道蔡照会将拆城辟门两事孰权利害重加妥议再行核办文》,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八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议请拆城及改办辟门筑路案》。
③ 《苏松太道蔡照会奉督抚院批准道详上海拆城事遵批停议辟门事俟款足勘办文》,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议请拆城及改办辟门筑路案》。
④ 《禀苏松太道蔡遵饬议复城根公地事宜录送议案文》,宣统二年三月初八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乙编《城濠公地争议案》。
⑤ 《禀苏松太道蔡陈复整理城根公地案议事会议决遵奉宪批仍照春季议决案决定目前折衷办法先行整理恳请转核文》,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乙编《城濠公地争议案》。
⑥ 《上海县田录札照会城濠公地仍归营管由营照议酌拨切实整顿改良不必再行照会核议文》,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乙编《城濠公地争议案》。
⑦ 《苏松太道蔡录札照会上海城濠公地争执案非折衷至当难期妥洽饬集议见复文》,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乙编《城濠公地争议案》。
⑧ 《禀苏松太道刘上海城濠公地案提台咨文自治团体不能承认请予详复立案文》,宣统三年二月初六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乙编《城濠公地争议案》。
⑨ 《实行拆除上海城》,载《申报》,1912-01-19。
⑩ 《拆除城垣之防备》,载《申报》,1912-01-20。
(11)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65—66页。
(12)《补录李总长辞职呈文》,载《申报》,1912-09-05。
(13) 《上海时事谣》,载《申报》,1912-01-14。
(14) 郭斌佳:《民国二次革命史》,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261页,武汉出版社,1990。
(15) 《为请取消沪军都督事呈孙中山文》,载《申报》,1912-02-11。
(16) 《咨商市政厅之统系》,载《申报》,1912-04-05。
(17) 《巡警与营兵冲突》,载《申报》,1912-06-03。
(18) 《三志营兵与巡警冲突》,载《申报》,1912-06-05。
(19) 《巡警被欺之愤懑》,载《申报》,1912-06-06。
(20) 《关于兵警龃龉之文告》,载《申报》,1912-06-07。
(21) 《李总长挽留警务长》,载《申报》,1912-06-20。
(22) 《市长又欲辞职》,载《申报》,1912-06-22。
(23) 《论中国今日宜取稳健主义》,载《申报》,1912-06-23。
(24) 《沪军都督将实行取消矣》、《上海财政之结束》,载《申报》,1912-07-10、1912-08-02。
(25) 《论内治之亟宜统一》,载《申报》,1912-07-27。
(26) 《市议事会之冷落》,载《申报》,1912-09-01。
(27) 《宋教仁被刺详记》,载《申报》,1913-03-22。
(28) 《大总统令南京程都督等电》,载《政府公报》,1913-03-23。
(29) 《不测之事变》,载《申报》,1913-03-23。
(30) 《议员不甘进后门》,载《申报》,1913-05-09。
(31) 《市议会要求开门》,载《申报》,1913-05-08。
(32) 《呈县知事吴议事会因警厅押犯闭门交涉公议辞职文》,民国二年五月九日;《呈县知事吴议事会辞职机关停滞董事会并应辞职文》及批文,民国二年五月十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编《门禁交涉案》。
(33) 《市政厅与巡警长激战》,载《申报》,1913-05-10。
(34) 《再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载《申报》,1913-05-11。
(35) 参见《穆湘瑶之专横》,《穆警长之强项》,载《申报》,1913-05-09、14。
(36) 《三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载《申报》,1913-05-12。
(37) 《九志市政厅与警务长之激战》。载《申报》,1913-05-18。
(38) 《县知事吴令奉省电转知自治会职员照常任职文》,民国二年五月十一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编《门禁交涉案》。
(39) 《上海市自治志议事会职员表》。第3页,见《上海自治志·图表》。
(40) 《上海县续志》卷十二《兵防》。
(41) 《上海市巡警职员表》,第1页,见《上海市自治志·图表》。
(42) 《呈县知事吴议事会因警厅押犯闭门交涉公议辞职文》,民国二年五月九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编《门禁交涉案》。另见《议员不甘进后门》,载《申报》,1913-05-09。
(43) 《穆湘瑶之专横》,载《申报》,1913-05-09。
(44) 参见《市政厅与巡警长激战》,《再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三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载《申报》,1913-05-10-12。
(45) 《五志市政厅与巡警长之激战》,载《申报》,1913-05-14。
(46) 《市乡公所职员失势》,载《申报》,1913-05-01。
(47) 郭斌佳:《民国二次革命史》,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261、264页。
(48) 《上海方面之维持》,载《申报》,1913-07-17。
(49) 《上海方面之维持(二)》,载《申报》,1913-07-18。
(50) 《上海方面之维持(三)》,载《申报》,1913-07-19。
(51) 《萨督办开始办公》,载《申报》,1913-09-06。
(52) 《淞沪警察区域之分划》,载《申报》,1913-09-07。
(53) 《穆湘瑶电请辞职》,载《申报》,1913-09-08。
(54) 《穆警长预备交卸》,载《申报》,1913-12-28。
(55) 《本地人对于本地事之感情》、《新知事接任》,载《申报》,1913-12-13、1914-01-03。
(56) 《县知事吴令奉文行知市董事会及乡董乡佐停止选举权文》,民国二年十二月九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编《奉文停办自治案》。
(57) 《呈县知事洪遵文开送市董事会职员薪水数目文》,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见《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编《奉文停办自治案》。
(58) 《停办自治机关之布告》,载《申报》,1914-02-19。
(59) 《改组工巡捐局之手续》、《工巡捐局之开始》,载《申报》,1914-03-01、1914-03-02。
(60) 《淞沪宣告解严》,载《申报》,1914-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