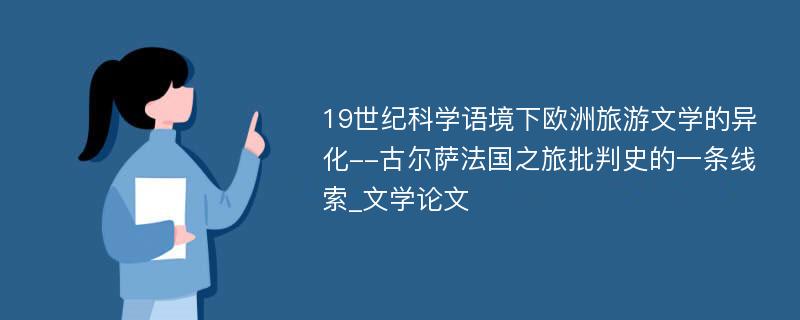
欧洲游记文学在19世纪科学境遇中的“异化”——以法国人古伯察游记的批评史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记论文,欧洲论文,境遇论文,法国人论文,线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055-06
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方向之一,游记文学在19世纪的存在状态这一问题也属于这一范畴,同时它也是文类与时代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思考:一、19世纪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世纪,与此相伴随的异质文化交往活动亦很频繁,游记文学作为其天然产物之一,成果相当丰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现象。二、在以科学为主导特征的19世纪,作为跨文化交流产物的游记文学在欧洲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起了相当的奠基作用。三、从文类研究来看,游记作为副文学(paralittérature)处于同纯文学 (“vraie”littérature)相对的位置,(Chevrel,1989:76;1992:85)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孔布(Dominique Combe)在其《文学类型》中将游记同哲学讲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归在“论”(essai)一类。他即指出这类文体“可能是被思考得最不清楚的一类,意识常常通过排除法来识别它”。(Combe:16)结合国内学界的研究,关于19世纪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它们均围绕以小说、诗歌、戏剧为主体的纯文学作品,对游记一类关注较少;同时国别文学的研究视野决定了游记文学在研究中所处的边缘地位,而后者在跨文化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在形象学研究领域,如孟华教授所说,是一片急待开拓的土地。基于以上各个层面的问题,笔者力图以19世纪中期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以下简作《旅行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的批评史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为线索,对19世纪游记文学在科学规约下的“尴尬”处境进行论述,并主要从欧洲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类属性两方面剖析其原因,试在文类与时代的关系研究方面作一个个案浅析。
《旅行记》于185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主要记述了古伯察同其上司秦神甫(Joseph Gabet)于1844-1846年间在中国蒙古和藏族地区的游历情况。游记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通过各种语言的译本和再版本向欧洲世界传播它的影响。就其影响来讲,首先在于两人的行动对当时的法国及欧洲都有重要意义,他们穿越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到达拉萨,这一经历在西方人的人藏史上写下了新的一笔,在法国同中国藏族地区交往的历史上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其次,古伯察的游记为时代传达了关于藏族文化的丰富内容,被中国学者戴裔煊视为19世纪中期西方民族学的重要著作。同时它也成为后世入藏旅行者的基本读物,关于藏族地区地理、气候、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多由此游记的叙述引发,在欧洲关于藏族文化的记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它的多重历史和时代意义,巴尔贝·多列维利(Barbey d'Aurevilly)指出了其所将经历的批评历程,这是一部将会传世的作品……此著作并非是我们有关亚洲知识的里程碑,而是其总结。那些新的概述和由其他人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会围绕本书而聚集起来,如同一座丰碑一般长存。这或是为了证实或驳斥他的说法,或是为了从中增补风俗、法制和各种事态可能遭受的变化。(古伯察:13-14)
关于《旅行记》的批评首先引发的问题是《旅行记》是“回忆录”还是小说?在实际的阅读中,它多是因为其想像性质赢得称誉的。1876年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i Yule)在关于普热瓦尔斯基(N.Preievalsky)《蒙古、唐古特地区和北部西藏》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普氏很朴实,他所见的是很精确的照片似的东西,而古伯察更是一个聪明的艺术家,相比之下他更为后者活泼的笔触所吸引。(Prejevalsky:xiv)时隔四十年后,法国著名探险家、语言史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为《旅行记》英文版作的序言中指出,此游记的持续成功在于作者的文学天赋,它使其作品富于想像力。(Huc:v)游记的可读性毋庸置疑,但也正是这种文学笔触使游记在当时多被当作小说性质的作品来接受,并遭致贬斥。玉尔除了提到一些法国人将其作品看作是半小说性质外,还以其朋友朱尔·莫勒(Jules Mohl)的经历做补充。后者谈到他在古伯察出书的年代拜访东方传教会(Estern Missions)宗座代牧主教巴勒耶瓦(Mgr Pallegoix,玉尔认为他来自暹罗)的情景。当时古伯察的书摆在桌上,主教抱歉说他应该将其放在卧室,认为一个主教不应该被人看见在读小说。而1893年奥尔良王子(Henri d'Orléans)在其《古伯察神甫及其批评者》(Le père Huc et ses critiques)中为他正名时,也间接地表露了游记的社会接受效果。“(它)成为儿童们的读物,如同今天的儒勒·凡尔纳的著作一样……有些人认为它完全是由错误编织而成,其他人又认为它仅仅是一部普通的传奇故事或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内容似乎都不值得过分重视。”(D'Orlé ans:3)可见,《旅行记》中作为游记这种叙述性文本基本要素之一的主体对客体的描绘和陈述在相当大程度上因为作者文学性很强的叙述手法被掩盖。但值得注意的是,阅读行为所引发的“新奇”感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同游记所描述的对象——藏族文化自身的特质有关,直到今天后者还是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旅行记》“不真实”的另一种反应通过学者的考据工作表现出来。玉尔曾对谁是游记的真正作者一点提出疑问。他一方面通过一些传闻判断《旅行记》是古伯察以秦神甫的书稿为基础写成,同时他又研究了《传信年鉴》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第十九一二十二卷(1847-1850)所刊登的两位神甫的书信,从两人的写作风格上看出秦神甫的报告模糊而无生气,与古伯察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秦神甫关于其在拉萨居住的全部描写中没有如同游记中所描写的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这一点也引起了对古伯察“编造”工作的怀疑。此外,他还结合了普氏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后者在中亚地区游历途中寄回俄国的信中表露出对古伯察记述的“真实性”的怀疑。他对神甫在库库诺尔一带没人怀疑他们的身份感到惊奇,同时他所询问的在塔尔寺居住了三四十年的喇嘛没人说见过一个外国人。而在阿拉善(Ala-shan)地区却有人能记住二十五年前有两个法国人来过。针对这一点,玉尔提示说他们扮作喇嘛可能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普氏同时也提到他见过的古伯察两人的侍从桑丹金巴 (Samdadchiemba),后者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但并没有与古伯察相矛盾之处。玉尔最终认为《旅行记》是由古伯察基于两人的书信而做。此外,伯希和也做了相似的考证工作。他在1925-1926年《通报》上发表了《秦神甫和古伯察的旅行》一文,同时参考未刊布的一些文献如遣使会档案馆材料、英国人为其写传记所利用的资料等,尤其是桑德伯格(Graham Sandberg)的《西藏探险》 (The Exploration of Tibet)一书再次进行考证,认为两位神甫确实到过拉萨,但古伯察文中记述的日期都有错误。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被广泛运用,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威(Paul Demieville)在其《法国汉学研究史》一文中谈到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研究历程时就指出,“当时法国最时髦的是唯科学主义和唯历史主义”。(戴密威:45)
从普通读者到学者,《旅行记》“真实性”的不足最终被导向对其有无“科学性”的判断。玉尔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古伯察能画出神奇的景致,但他不仅缺乏科学性思维,也不具备地理学意识,因为有时候即使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这样的旅行者也能对地理学知识有所贡献。那个时代欧洲地理学的发展印记被刻画出来。同样,伯希和虽然认为古伯察做了一次精彩的旅行,且其记述中相关的许多事都是重要的,但最后还是从“科学”的观点进行考量,认为其叙述不精确,历史性弱化,其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不能为历史学家所用。这样两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古伯察提出了要求,即作为传教士的古伯察应该同时成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时代的局限决定了无人能像当代德国萨尔大学的学者施米令(Manfred Schmeling)一样,在关于游记文学的思考中提出想像与客观记录的界限问题。(Schmeling:59)。
针对学者的诸多批评,不少游历者都为古伯察辩护,双方在很长时间内展开了关于其游记记述真实与虚假的论战。1891年法国旅行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在其《勇闯无人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Tibet inconnu)中为古伯察两人正名:
有人尖刻地批评他们,甚至指摘他们把好几条山脉忽略过去了。在两位神甫的记录中曾有大河的地方,三十年后经过那里的人却只见到一条小河,因此有人嘲笑他们,其实这些地区的河流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那些批评的人完全忘了,这两位神甫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旅行的,当时没有足够的仪器进行周密的考察,人数又少,又在未知国度旅行,如何能进行详细的勘察呢?……我们应该对两位神甫抱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才对。(邦瓦洛特:378)
同年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在其《喇嘛之国》(Land of the Lamas: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Mongolia and Tibet)中也希望重版古伯察游记并加一些注释(1924年该游记的包士杰[J.M.Planchet]版本就是应北京的传教士要求,在增加历史和地理考释及一些汉字专用名词的基础上再版的),以增强人们对普氏关于神甫两人指责的判断力。同时,他在1910年的《通报》上发表文章,就梅尔思所认为的古伯察关于诺们罕噶尔丹·锡图生平等的记述是臆想出来的一点进行批驳,“梅尔思肯定完全错了。正如1877年向理藩院呈奏皇帝的表章所证明的那样,该文已由9月7日北京《邸报》发表。”(古伯察:524)从某种意义上讲,柔克义的辩护向那些对游记一概否定的史学家过于决然的判断提出了警示。同样,1893年奥尔良王子在其《古伯察神甫及其批评者》中坚持了游记描述的确实性。他指出,“尽管诸如爱莲斯(Ney-Elias)、玉尔等英国人和其他人或在地理学会的报告中,或在序言中回答了普氏,但这位俄国旅行家对古伯察游记的批评依然被许多地理学家们所接受。” (D'Orléans:4-5)他对游记的这种接受效果并不满足(包士杰也有同感,并将其与斯文·赫定[Svin Hetin]赢得的荣誉相比),认为那只是限于“有趣”,而他更想强调的是其在地理学上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认为当时对地理发现不太重视的态度是许多思想家不读古伯察游记的原因。事实上,身处19世纪末的奥尔良所要强调的是19世纪中期古伯察的入藏行为及其对藏族地区的各种描述在地理学等方面的重要性,游记的意义亦表现在此。同奥尔良自己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Du Tonkin aux Indes,Janvier 1895-janvier 1896)所宣扬的思想相互联系,他认为这一地区正是处于扩张中的法国殖民势力可以延伸的广阔领域。到了1932年,弗尔涅(P.Fournier)在其著作《15-20世纪法国自然学家传教士的旅行和科学发现》中作了总结性发言。他将古伯察和秦神甫视为19世纪上半期中国部分的代表。关于对他们的批评,他提到普氏的指责,指出爱莲斯、玉尔等人对古伯察游记的同情,还认为奥尔良、邦瓦洛特、柔克义、兰斯(Dutreuil de Rhins)、斯文·赫定等人都肯定了古伯察记述的精确性,还有考狄(Henri Cordier)的文献作为支持。他最终认为古伯察两人首先是传教士,他们不是学者,也不是地理学家,尽管他们没有经受过科学训练,但已经是很优秀的观察者,对气候、植被、河流等的记述实有其价值。他还认为从科学和文学的角度,古伯察的游记都被低估了,他的语言优美而有趣味,符合最纯正的法国传统。(Fournier:24-25)
基于以上考察,在关于古伯察游记“文学性”、“真实性”和“科学性”的论战中,不管批评者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科学性”都成为评判的最终标准,它主要包含地理学的精确和历史学的“真实”,这些内容成为时代赋予游记的社会角色和任务,远远超出了它原本具有的娱乐性质。联系19世纪法国及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状况,我们不难理解游记文学所处的这种状态。
英国人梅尔茨(J.T.Merz)在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中宣称,“本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梅尔茨:79)这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游记文学命运的基调。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国家向外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它直接带来了诸多领域的副产品:各类商品的输入、考古活动的开展、地图绘制等实用工具的发展、基督教文化的传播等,其中游历者的旅行记录成为数量众多的文化产品之一。这种对“域外”民族地区见闻的记述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各社会科学的发展。学者们依据游历者的旅行记录对原始初民的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信仰等进行研究,扩大了原有的认知范畴,发掘了新的研究视角,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在逐渐膨胀的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纷纷得以建立,它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学术的、无偏见的“科学性”。麦克斯·缪勒(Max Mueller)于1870年在其《宗教学导论》中就将宗教学定义为“一门关于宗教的科学,以不带偏见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比较人类的一切宗教,或至少是以比较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为基础”。(夏普:1)此外,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业已发现游记作者记述的不确切性,被人称为对这种不确定性很有直觉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Tylor)就提醒学者们在做评断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到了20世纪 30年代,更有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 (Lucien Lévy-Brühl)对游记作者满怀怨气,
“最先看见这些不发达民族的人们,即使他们要在这些民族中间逗留很久,也往往忙于研究另一些事物,不会去对他们所接触到的制度和风俗作精确、细致和尽可能充分的观察。他们只是记上他们认为最突出、最奇怪、最强烈地打动他们的好奇心的东西。这一切他们描写起来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这样搜集来的观察,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附带的东西,进行这种观察,从来就不是他们要在这些民族中间逗留的主要原因。此外,这些观察者从来就是在描写事实的同时不客气地给事实以解释。批判审核的观念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岂能想到,他们那一切对事实的解释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和曲解,而‘原始人’和‘野蛮人’几乎永远是十分谨慎地隐藏着他们的制度和信仰中那些最重要最神圣的东西呢!”(布留尔:23)
“19世纪在这两个方向——积累知识的方向和凝缩知识并使之理想化的方向—一都作了大量令人瞩目的努力。就前一方向而言,19世纪是史无前例的,而在后一方向上……本世纪已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它制定了关于扩展知识的正确方法的较明确观点,以及关于知识可能统一的独特概念,并用专门语言把它们积淀下来。”(梅尔茨:26)而游记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各种知识学科的规约:地理学家要求数据的精确,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要求资料的翔实和确定,历史学家要求事件记述的确切。这就使原本相对松散的、自由的作为文学的游记在19世纪各学科研究者的规约下几乎要变成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它在各学科间被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致达到相当的“异化”。
针对游记文本在19世纪被赋予的特殊的历史命运,对这种介乎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游离”状态,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游记作者来看,19世纪的游历者多是普通人,他们主要为了探险、游历或传教等目的到欧洲之外的世界,这种身份决定了其对对象国文化的接触方式、观察视角、记述程式都具有个人化色彩。而研究者们多偏爱书斋,固守书本。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说,“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不是一个亲赴实地的人,而我却通过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了实地人种学。” (埃里蓬:25)这部分反映了当时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对文本的依赖。相反,他们却要对游记作者提出“科学性”的要求,并对其进行责难。
其次,从游记的文类性质来看,内容的纪实性和按照物理时间流程进行记述的单一形式是其最主要也是最稳固的特点,这相反也形成了它的保守性。在同科学的关系上,与纯文学作品相比较,后者具有更大的可融合性。它因其虚构的特质、形式的灵活可以吸收并借用各种新兴的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以实现某种新的发展。在19世纪的法国,我们可以看到圣伯夫、泰纳、勒南和贝尔纳等人均受到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分别在文学批评、艺术、宗教及医学研究中有所突破。从文学创作来看,科学向文学的渗透除了在巴尔扎克及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外,主要表现在以左拉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创生和发展上。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发展的这种新方向是创作者们基于时代思想的影响自主选择的结果。对游记而言,从作者、内容到形式都难以接受“科学性”的改造。旅行记述以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其中又难免夹杂道听途说和个人观感,这种“不确定性”是其固有的特点。如果按照德昆西关于重教化的“知识文学”和重感化的“权利文学”的划分,则原本属于后者的游记文本却因为学术的需要被挤为前者,这一外在的、非内在发展需要产生的推动在各学科起步的19世纪终究难以改变游记写作的整体状态。同游记文本相似,马德(Roger Mathé)关于异国情调文学(la littérature éxotique)在19世纪发展状况的研究向我们提示了那个时代与跨文化主题相关的文学形式的最终走向。这种文学“为了寻求生存之路,采用了更精确和更细致的形式。异国情调从而丧失了它的纯粹性和色彩,开始服务于社会学、民族学和哲学的目的”。(Mathé:125)
最后,从游记的对象和功能来看,它终究是面向大众的,是“文学”的、娱乐性的。但在欧洲对外扩张、科学进步、现代文明发展的 19世纪,它以其对域外民族社会、宗教、语言、风俗等的描述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从而在加入到欧洲各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同时,必然受到其外加的强制性的规范。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也许是19世纪学者们期待的那种游记,但作者已然是经验丰富的专业研究者。所以,从游记文学在19世纪遭到“异化”的历史境遇中可以看到,一定的历史时代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思想的规约和影响,但文学因为其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又能维持自己独立的发展轨道,这种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