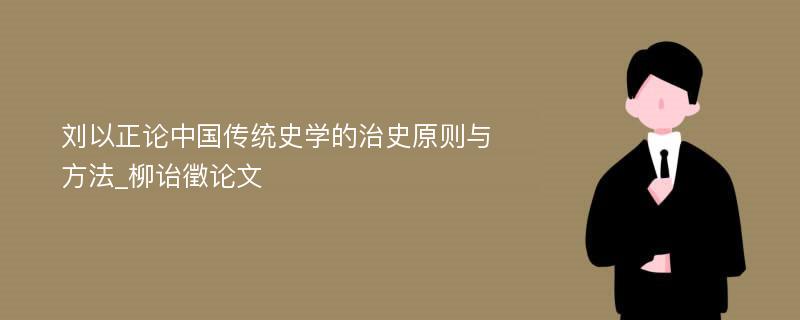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原则论文,方法论文,柳诒徵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5-0101-07 柳诒徵(1880-1956)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民国时期史学界有“南柳北陈”①之称。在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力挑战,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盖晚清以来,积腐襮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著无文化可言”②。柳诒徵对此予以批评,主张全面和客观认识中国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价值。这就要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为此,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抗战后期所写《国史要义》一书。学术界对柳诒徵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缺乏这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③。故,本文拟对柳诒徵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加以梳理和评析,以丰富和推进柳诒徵学术思想的研究。 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 “治史必本于德”是柳诒徵最强调的治史原则。他深入阐述了中国传统史德论的内涵和要求,指出治史与修德是相互促进的,史德表现在史尚忠实和存疑、强调实录的笔法和精神、历史记载要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等;近代“疑古”之风妄疑和菲薄中国古史记载和历史文化是有悖史德的;传统史学重史德是中国文化以德为本在治史上的反映和体现。 柳诒徵比较了刘知畿与章学诚的史德论,批评刘知畿因郁郁不得志,故“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肯定章学诚从“敬恕”的角度将史德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④。他认同梁启超治史应心术端正的主张,即“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故史家应摒除夸大、附会、武断诸病,对过去事实取存疑态度,“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⑤。但梁氏的主张并未穷尽史德之义。他对三位史家的史德论予以评判,称章氏论德仅强调“临文必敬”,未言及“修德”的重要性,易使学者误认为平时不必修德;而刘、梁仅“就史言德”,没有彰显“修德”的普适性。为此,他提出“治史”与“修德”相互促进的新见解,“则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⑥。而且,这种思想和做法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言德不专为治史,而治史之必本于德,则自古已然”⑦。 中国史学讲求史德,一是表现为史尚忠实。柳诒徵说:“至于史尚忠实,尤必推原古史。饰伪萌生,伊古已然。积其经验,则政教必重信,信者忠实之征也。……故治吾国史书,必先知吾自古史官之重信而不敢为非,而后世史家之重视心术,实其源远流长之验也。”⑧二是表现为实录的笔法和存疑的态度。后世史官与古之史职虽有不同,“而自史迁以降,史家所重,尤在实录”⑨。史实会有可疑之处,故要真正做到实录,就要秉承《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而史家秉笔,又必慎重考订。存信阙疑,乃得勒成一代之史”⑩。三是表现为集史家群体之力修史,使历史记载能囊括历史的方方面面。他说:“史之信也,基于群德,百为之征。匪第关于君主之记注。故吾先民之为史,必大集全体之所为书。三皇五帝之书,与四方之志并重。人民财用九谷六畜数要利害,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之阻,咸有专官,详为记录。”(11)可见,中国史籍,“自古相承,昭信核实,以示群德。……治史者正不可以偏概全也。”(12) 他抨击近代的“疑古”之风是尤令人痛心的“附会之病”,“以他族古初之蒙昧,遂不信吾国圣哲之文明,举凡步天治地、经国临民宏纲巨领、良法美意,历代相承之信史,皆属可疑。……复以挽近之诈欺,推想前人之假托。……至其卑葸已甚,遂若吾族无一而可,凡史迹之殊尤卓绝者,匪藉外力或其人之出于异族,必无若斯成绩。”(13)在他看来,这种全盘否认中国史学“存信阙疑”精神和中国古史真实性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是最有悖于史德的。 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德是中国以德立国及中国史学以德为本思想的产物。柳诒徵说,中国古代将伦理道德视为立国之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良传统所在,“然人类皆具兽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国民也。”(14)由此,中国传统史学有了“以道德观念为主”的精神,“治历史者各有其主观,吾国之群经诸史,皆以道德观念为主。……实则《易》、《书》、《诗》、《礼》亦无非以正伦纪明礼义,后世史书高下得失虽不齐,其根本亦不外是。”(15)儒学真义即在于主张人格修养,孔子所学首重者曰成己、成人、克己、修身和尽己,“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儒教真义,惟此而已。”(16) 柳诒徵主张“治史必本于德”,将史德放在史家四长之首,强调了史德在治史中的决定作用。他对传统史德论内涵的概括和阐述极大丰富了史德论。他认为治史以德为本是中国以德治世思想的体现,是将史德论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高度来认识,突出了传统史德论及其对治史的指导意义,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史德论作了重要的发展。 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 柳诒徵十分重视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称:“史之所重在持正义。”(17)他通过辨析中国史学的各种正统论,批驳了对正统论的诸多曲解,指出传统史学实际是以史之正义为统来书写国史的,对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提出了崭新的见解。 正统或闰统,是中国古代史家和统治者对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或中央与地方政权统治合法性的评判。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正统论本质上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18)。柳诒徵却对正统论予以新阐释,称其并非是强调“一家传统”,而是持义之正。他说,梁、隋提出“正史”说以后历代相延,然而对“正史”却缺乏准确界定或合理解释,章学诚辨《四库提要》的正史类例“亦未陈正史之定义”,梁启超视官书为正史,“义亦未谛”(19)。他认为,随着清帝制被推翻和民主共和制的建立,正、伪、杂、霸之辨可存而不论,但正统论仍有合理性,“然民族主义及政权统一,皆今之所最重,亦即吾史相承之义有以启之。故由正史之名,推其义之从来,则三统五德及后世正统之辨,固今日所当理董,不必为清人隐讳之辞及前哲辨析未精者所囿矣。”(20)《公羊传》以大一统释“正”是合理的,“一统与居正,实贯上下千古而言,故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炎黄以来,吾史虽有封建郡县之殊,禅让世及之制,而群经诸子以迨秦汉记载,述吾政教所及之区域,赢缩不同,地望互异,要必骈举东西南朔所届,以示政权之早归于一。”(21) 柳诒徵从儒家天下观出发探讨了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赋予正统论新的内涵,“由天下之观念,而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观念;又有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之观念。故曰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断。三统五德,不必拘于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22)可见,正统论本质上是要求以统治者的道德作为衡量标准。汉代以来的史书就有判断政权是否合法的“正闰之辨”;秦、新失德,故史家不认其为正统;曹魏篡逆失德于天下,故史书皆斥魏而正蜀;宋代以来,更有持正统论和不持正统论的此消彼长。然而,究其实质并无区别,“而传授之正,疆域之正,种族之正,道义之正,诸观念恒似凿枘而不能相通。使四者皆备,则固人无异词,而史实所限,则必一一精析而后得当。骤视之似持论不同,切究之则固皆以正义为鹄也。”(23)通过对历史上正统论与非正统论的辨析,他得出这一结论:“既知不持正统论者之同一尚统一、尚正义,其所持之正义,同一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是实吾国传统之史义。即亦可以明于持正统论者之基本观念,亦无异于不持正统论者也。”(24)总之,书写国史时不论对正统论持何种看法,本质上都要以持正义为史统。 以正义为史统是中国史学得以发展和具生命力的体现。他说:“华夏之人,服习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而必思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缘此而强暴者虽专恃力征经营,而欲其服吾民族之心,则虽据有其实,犹必力争于名。”(25)又说:“吾族由大一统而后有所谓正史,由正史而后有所谓通史、集史。而编年与纪传之体虽分,要皆必按年纪录。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是即梁氏所谓统在国在众人也。明于三统五德之义,则天下为公,不私一姓,而前史之断断于一家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营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因。”(26)强调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是柳诒徵视道德与礼为国家本质的思想决定的。他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有精言曰: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又曰: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故千古共同之鹄的,惟此道德之团体。”(27) 柳诒徵对正统论的新解释未必符合历史上正统论的原义,但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指出史统包括三方面内涵: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历史上能得疆域和民族之正者,即能“持义之正”,才符合“史统”。可见,所谓义正,是指疆域之正、民族之正,即是说,没有丧失领土,同时国内各民族是平等的,汉民族也未受外来奴役。这种思想是对传统史统论的新发展,体现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学者说,在抗日民族危难之际,“柳诒征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发挥,强调持义之正,强调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自在情理之中。”(28) 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 柳诒徵认为求取史识是治史的目的。他通过对刘知畿、章学诚、梁启超和刘咸炘史识论的评析,阐述了史识的内涵及与治史的关系,指出史德出于史识,史识与史法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强调治史重在求取史识。这些思想深化了对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认识。 柳诒徵对四位史家的史识论做了评述。他说,刘知畿首倡史有三长说,而尤重识,“刘氏所谓史识,在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29)章学诚对刘氏史识有误解,“误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能贸化……而以有学无才之弊,属之有学无识”;不过,“实斋虽误解刘氏之语,而谓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所以补充刘氏之说者,要自有见,第未推原道德观念实出于史耳。”(30)认同史德出于史识,表明柳诒徵把史识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不治史和读史便无以求取史识,进而养成国民和史家之道德。梁启超将史识理解为观察力,即要关注到全部与局部、勿为传统思想和成见所蔽,“盖示人读史而创新史”;然而,这种要人摒弃古代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学者识力,大都出于读史。苟屏前史,一切不信,妄谓吾之识力能破传统观念之藩,则事实所不可能也。”(31)这实际是驳斥了梁启超《新史学》一文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做法。 柳诒徵充分肯定近代史家刘咸炘的史识观,深入阐述了史识与史法的辩证关系。他说:“刘咸炘则以观史迹之风势为史识,又曰:作者有识,乃成其法,读者因法而生其识,虽二而实一。又曰:读史本为求识,所以必读纪传书。又曰:吾辈非有作史之责,而必斤斤讲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识乃生也。”(32)在他看来,刘氏所言史识的获取要有正确的史法,史法的养成又要依靠史识的观点相当正确。他批评近人视史书为史料的观点,说,刘咸炘所谓作者有识乃成其法,使人们知道了中国史书有别于史料,“近人恒谓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者,坐不知吾史相传之义法也。”(33)只有研读中国历代史书来领会其中的义法以获取史识,方为治史正道,“凡为良史,经纬万端,闳识眇旨,非仅举一二语所能罄也”,“读史不窥此秘,惟务辑逸钩沉,则正刘氏所谓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及吐果弃核,捃拾登荐之类耳”(34)。柳诒徵既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史书为培养史识之要道,反对将中国古代史书视为没有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死史料,又指明了人们治史和读史的正确立场和途径。 柳诒徵进而提出“史为识之钥”的重要观点,说:“识生于心,而史为之钥。积若干年祀之纪述,与若干方面之事迹,乃有圣哲启示观察研究及撰著之津涂。后贤承之,益穷其变,综合推求,而饷遗吾人以此知识之宝库。”(35)主张识生于心,是肯定了史家的精神思维在历史认识中的主体作用;以史为识之钥,则阐明了研读历史是人们获取史识的惟一途径。史识的最高形态即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故吾人治中国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36)可见,史识即是对历史规律和原理的认识,即历史哲学。如果人们掌握了阐明历史发展和原理的历史哲学,便能“知几”,而这正是治史的目的和任务所在。他说:“观风之变,于其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于其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故治史所得,在能知几,非惟就已往之事,陈述其变已也。”(37) 柳诒徵主张史德由史识而来,说明了人的道德来自于经验性的历史认识,是经验主义道德观,表明他反对抽象地谈论史德。他对史识与史法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正确阐明了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史识与史法是相辅相成和不断提升的。史识本质上是对历史规律和原理的认识,最高形态即历史哲学,则指出了史识对治史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源所在。可见,史识既是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又是研读历史后所形成理论和思想的升华,这无疑拓展了中国传统史学史识论的内涵,对治史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 柳诒徵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制度记事皆有“联”的制度和特点,决定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尤其是纪传体注重和善于载述史事间的联系,使之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风貌,这便驳斥了近代以来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记载和表述优越性的观点。 在柳诒徵看来,中国史书编纂注重载述各类史事及相互间的联系,源于上古史官制度载事方法和制度化的要求。《周官》曰:“小宰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凡小事皆有联”;《周官》联六事之事不仅在六职,从中还可见合天下为一家之气象,“故在《周官》之书,有分有联,已具史法,交互错综,各视其性质之特重者分之,又视其平衡或主从者著之。”(38)这种制度所体现的“联事”方法被纪传表志体史书加以综合发展,“史之所纪,则若干时间,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联带关系,非具有区分联贯之妙用,不足以胪举全国之多方面,而又各显其特质。故纪传表志之体之纵横经纬者,乃吾大国积年各方发展各方联贯之特征,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39)可见,中国史学早已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性,故载述时特别注重反映史事间的联系。其次,中国古代史职所统的广博又决定了史书记载内容浩博、规模宏大,这是西方史学难以媲美的,“故周之史官,为最高之档案库,为实施之礼制馆,为美备之图书府,冢宰之僚属不之逮也。由是论之,后世史籍所以广志礼乐、兵刑、职官、选举、食货、艺文、河渠、地理,以及诸侯世家、列国载记、四裔藩封,非好为浩博无涯涘矣。自古史职所统,不备不足以明吾史之体系。……他族之国,无此规模,文人学者,自为诗文,或述宗教,或颂英雄,或但矜武力而为相斫书,或杂记民俗而为社会志,其体系本与吾史异趣。或且病吾史之方板简略,不能如其活动周详。是则政宗史体,各有渊源,必知吾国政治之纲维,始能明吾史之系统也。”(40) 柳诒徵称,中国的正史体裁纪传(表志)体尤善于记载和表述史事间的各种联系,历代史家、特别是刘知畿和章学诚对此却缺乏正确认识。刘知畿在批评纪传体时说:“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41)章学诚虽没有贬低纪传体,但其《史篇别录例议》也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42)。可见,刘、章都没有看到纪传体的特质和优点,“而不知表志即所以联合,纪传即所以分著。又其分合均所以为联,乃纪传体之特色。徒曰纪传区之以类,事有适从,寻求便易,故相沿不废。盖犹未能深求史之起源,乃吾族立国行政与史义、史法一贯之故也。”(43)此言不仅批评了刘、章对纪传体的错误认识,指出了纪传体的根本优点在于能将史事及相关方面都能联成一体,还回答了史联的内在依据是“官联”,即政治和管理之职相联。总之,上述观点深刻阐明了纪传体具有史联特点的历史依据和文化根源。 柳诒徵称纪传体是一种完美的体裁,起源于《世本》,史事分载于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等史体中,“而人事之有联属者,必各就其特质分著于某篇某体之中。纵横交错,乃有以观其全,而又有以显其别。……《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史体之区分综合,即由先哲类族辨物之精心也。”(44)纪传体史书妙在纵横贯通,表、志、纪、传相互关联,相得益彰,“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表志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45)此言既分析了史联的内涵,即史迹之联系,又阐明分类相联,即相联的史迹并非杂乱和缺乏内在关系的,必须是同类相联。在他看来,中国史书体裁的形成是为了更好记载历史,纪传体能够成为正史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中国传统史学创造了纪传体这种综合性叙事体裁,通过多样化的叙述手法来揭示史事间的关联和演进原委。柳诒徵对“史联”的阐述体现出对中国史学编纂体例和方法深刻而独到的思考。这不仅驳斥了近代以来新史学指责传统史学不能全面记录社会历史的错误观点,也驳斥了近代以来片面推崇西方章节体,否定中国史学体裁及其表述的极端化思想。 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考据。中国史学有重考据的传统,两汉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考据甚至使经史考据成为主导时代风气的学术范式。柳诒徵自小受乾嘉风气熏陶和考据方法训练,重视考据的作用,亦不乏考据杰作。不过,他认为考据只是一种方法,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精神和目标是重义和讲求修身经世。 他指出,考据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但需要正确运用,须谨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46)他反对“为学问而学问”的考据学风,认为这有悖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史学精神。首先,中国学术传统重修身立德和经世致用,“文、周、孔、孟皆是在身上做工夫者。自汉以来,惟解释其文学,考订其制度,转忽略其根本,其高者亦不过谨于言行,自勉为善,于原理无大发明。至宋儒始相率从身上做工夫,实证出一种道理。不知者则以是为虚诞空疏之学,反以考据训诂为实学。不知腹中虽贮书万卷,而不能实行一句,仍是虚而不实也。”(47)其次,传统史学主张事、文、义三要素的合一,宗旨则是“明史学所重者在义也。(近世有所谓考据、辞章、义理之学。考据者事也,辞章者文也。以孔孟论史之义绳之,考据、辞章,必归宿于义理,始得为学。且可悟是三者之学,皆出于史。)徒骛事迹,或精究文辞,皆未得治史之究竟。”(48)他称,阳明学“知行合一”论“最有益于世道者”,“盖吾国自古相传之法,惟注重于实行,苟不实行,即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亦不过贩卖衒鬻之徒,于己于人,毫无实益,即不得谓之学问。”(49)然而,近代以来片面讲求考据则背离了中国学术的致用精神,“所以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就是说讲学问不要有用的。”(50)他称这种风气有害于国家和民族,“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51)。 中国现代实证派史学推崇清代乾嘉考据,故亦称“新考据派”。柳诒徵对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称赞清初诸儒的治学精神和方法远非乾嘉间人所可比,“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其风气实截然为二,不可并为一谈也”。清初诸儒功夫皆在博学,而学必见之躬行,“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52)。他对乾嘉考据的本质、源起和利弊等做了如此分析:“要其人所自称许者,无过于征实。近人尤盛称其治学之法,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实则搜集证佐,定为条例,明代学者已开其端,非清人所得专美。虽科条精密,后胜于前,然其能成为科学者,自文字、音韵外,初不多觏也。”“盖汉学家所考证者,局部之考证,于唐以下之书率不屑读,尤鄙夷宋人,好事诋斥,此皆其所短也。”(53)乾嘉考据之风盛行,是因文人志士迫于文字狱“不敢讲有用的学问”,现在清朝已被推翻,“应该将历史和政治连合起来,发见史学的功效了”(54)。另一方面,他对清代史学考据的成就也予以充分肯定,“有清一代,考史之书,校正讹脱,辑补逸文,钩稽表志,厘析疆域,皆以补前人之未备,供末学之研求”(55)。对晚清以来的史学考据,他评价说:“矧以近世,新得滋多。流沙竹简,高昌壁画,河洛新碑,洹水甲骨,古城逸器,往往而出。旧史所无,宜增图录。域外文件,参稽亦多。粟特之文,匈奴之字,契丹石刻,西夏遗书,东西学人,竞事考证,逐译最录,责在吾辈。”(56)柳诒徵高度赞许晚清以来新史料的考据成就,并视之为现代史家的职责,这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家的认识相近,亦可见现代史学重视考据方法对他的影响。 柳诒徵治史亦始终重视考据。其1910年所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教育史,书中特别重视史料考证,有学者称述此书编纂特点是:“其一,史料翔实。作者广泛征引先秦经书、子书及汉魏唐宋学者注疏和《史记》、两《汉书》、《竹书记年》等史书,尤其是清人如戴震、阮元、汪中、焦循、章学诚、段玉裁、孙诒让等的考据之作,兼及大量国外理论著作,做到了无一说无出处。其二,长于考证训诂。作者习惯于从字词训诂入手,广征博引,论述一事一物,无不考其本原。”(57)其史学考据代表作有《宋太宗实录》和《明史稿》校证。这两部著作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考据水平,“从考校文章看,他考据时态度审慎,凡有异同,必定排比原文,以事实为据,不杂己意;而查校推断,逻辑严密,层层推导,尤如抽茧剥蕉,胜似老吏断狱,其学术功力确然不凡。”(58)孙永如还概括了柳氏史学考据的特点,“柳治征是受过严格而系统的旧学训练的学者,虽然他反对乾嘉学派孜孜以求于考据,脱离社会的学风,但他对乾嘉学者搜集佐证,重视史料,讲求‘无一字无来历’的治学方法深为赞同。他的研究,力求凭证据说话,断语总是从排比、综合大量史料后,提炼而出。”(59) 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是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其史学思想的宗旨和特色——以继承和发扬具有儒家精神的中国传统史学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及其史学思想,进而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 柳诒徵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推崇孔子在中国文化和史学中的中心地位。他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60)无孔子则无中国史学,故,“青年学者读中国史,首宜认识孔子”,“吾人今日能知孔子以前之史,实赖孔子之传。……一玩史目,即可知论中国史而欲撇去儒家别开生面,犹之论西洋史,欲撇开耶教,为不可能之事”(61)。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和史学。《国史要义》的“题辞”言及此书撰述宗旨时说:“钩稽群言,穿穴二民,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下逮明清,旁览域外。抉擿政术,评骘学林,返溯古初,推暨来叶。”其中,“旁览域外”既指对西方史学和文化的介绍,也指以之评骘中国史学。现代国学大师吴宓称柳诒徵是堪与梁启超并立的学术大师,“近今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诒徵先生翼谋。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鹄的”(62)。质言之,柳诒徵史学思想的特征可概括为:“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 由于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儒学精神和特质,故柳诒徵在论述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时,着力对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价值做出符合现代史学要求的阐释。他提出“治史必本于德”,把史德放在治史的中心地位,将史尚忠实和存疑、主张实录的笔法和精神、历史记载要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等传统治史方法和要求都概括为史德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站在这个立场上,他对国史(正史)书写的道德合法性予以新解释,称史之正统的本质在于“持正义”,其内涵即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这种观点既吸收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和道德观,又显示出以现代话语表达传统史学重历史道德评判的特征。他指出治史旨在求取史识,因为要培养和树立正确的史德观必须求之史识;史识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原理的认识,此即历史哲学,故,求取史识不仅有益史德的培养,还能通过历史发展规律彰往知来。这是对中国传统史识论的现代诠释,赋予了史识以历史哲学的地位和功用。他一反近现代史学界视传统史学为记述帝王将相之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片面看法,指出中国传统史书、特别是纪传体事实上特别强调史事记载的全面性和普遍联系性,从而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编纂体例和方法的现代价值。他秉承中国史学重修身经世的宗旨,辩证分析了考据的史学地位和作用,指出考据是极好的治史方法,肯定乾嘉考据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又脱离了中国学术精神和史学传统。 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体现出较浓厚的文化保守色彩。他虽然力求会通古今和兼融中西,实际上却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方法及文化传统继承得多,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发掘和阐扬的多;对西方新史学的科学治史精神和方法吸收得少,对如何运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方法治史阐发和运用的不够。质言之,可谓“据旧”有余,“开新”不够,这是柳诒徵学术和思想的局限和不足所在。 ①卞孝萱说:“解放前,我国北方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号称‘二陈’。南方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柳诒征先生,有‘南柳北陈’之称。”(卞孝萱:《柳诒征评传序》,孙永如:《柳诒征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按,柳诒徵的“徵”,多数用繁体,也有一些著述和学者用简化字“征”,本文引用这些学者著述的内容或题名时用“柳诒征”,其它处则用繁体。 ②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1页。 ③如,张文建的《传统史学的反思——柳诒徵和〈国史要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4期)初步探讨了柳诒徵《国史要义》反思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王家范的《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史林》2006年第6期)从人本主义立场来发掘此书的文化观及其史学思想。向燕南的《关于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对此书的史学思想和特征做了分析。此外,孙永如的《柳诒征评传》、郑先兴《论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也有所涉及。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126、131、132—133、134、142、136、148、161页。. (14)(1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35、234—235页。 (15)柳诒徵:《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01页。 (17)(19)(20)(21)(22)(23)(24)(25)(26)(27)柳诒徵:《国史要义》,第73、73、76、76、78、82、88、95、96—97、340—341页。 (18)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17页。 (28)孙永如:《柳诒征评传》,第177页。 (29)(30)(31)(32)(33)(34)(35)(36)(37)(38)(39)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63,163、165,164、165,164,166,179、187,193,193—194,197,101—102,102页。 (40)(43)(44)(45)(48)柳诒徵:《国史要义》,第36—37、101、103、113、616页。 (41)(唐)刘知畿:《史通·六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4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317页。 (46)柳诒徵:《历史之知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83页。 (47)(4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508、616页。 (50)(51)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502、501页。 (52)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58页。 (53)(5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715、720,745、746页。 (55)柳诒徵:《修史私议》,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32页。 (56)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95页。 (57)杜成宪:《中国学者的第一部教育史——柳诒徵〈中国教育史〉》,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页。 (58)(59)孙永如:《柳诒征评传》,第92、208页。 (60)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31页。 (61)柳诒徵:《与青年论读史》,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549、553页。 (62)吴宓:《论柳诒徵诗》,镇江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印,第234页。标签:柳诒徵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周官论文; 纪传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