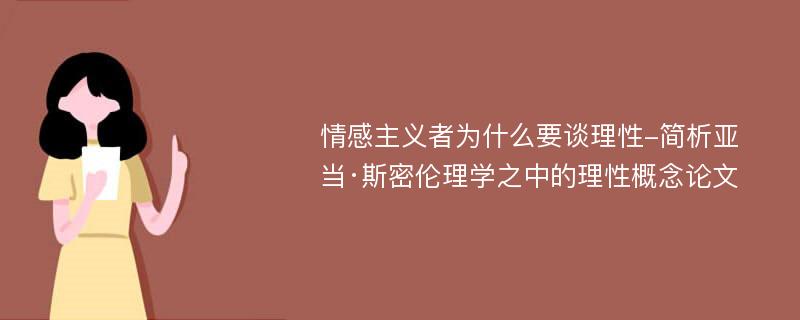
情感主义者为什么要谈理性
——简析亚当·斯密伦理学之中的理性概念
贾 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100086)
摘 要: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然而,他在其第六版的《道德情操论》中却着重强调了“理性”的作用,并且还将“理性”置于其学说的关键位置。文章试图结合斯密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深入考察并解析斯密诸版本的《道德情操论》在论述主题上的变迁情况,进而说明斯密虽并未抛弃情感主义的立场,但理性概念对其的伦理学是必须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理性观念可以为当代情感主义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某种历史启示。
关键词: 理性; 情感主义; 斯密; 道德情感败坏
理性(reason)在哲学中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它在狭义上是指一种区别于经验归纳的演绎推理能力,在广义上则是指包含归纳和演绎在内的认识事物和获得知识的能力。第二个含义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它特指理性主义伦理学体系中的实践理性(practical-reason),这是一种先验道德律,一方面它是规则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反思、认识和履行规则的能力。与理性主义伦理学相对的是情感主义伦理学,后者认为提供规则和道德行为动机的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情感,而理性仅仅是一种作为“情感的仆从”的工具性能力。情感主义伦理学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是该体系的集大成者,但他在第六版《道德情操论》中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既然我们消极的情感通常是这样卑劣和自私,积极的道义(principle)怎会如此高尚和崇高呢……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它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它是理性(reason)、道义(principle)、良心(conscience)、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1]
综上所述,经过TBL、CBL、PBL融合教学法在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病理实习课中实践提高临床思维综合能力,为打造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医学专门人才奠定基础,对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通常我们认为斯密是一位持情感主义立场的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思想直接受到了他的好友休谟和他的老师哈奇逊的影响,而这两人也都是18世纪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将他的伦理学代表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冠以“道德情感”之名,也很明显地摆明了情感主义的立场。最后,就内容而言,在该书的第七卷,斯密也很明确地驳斥了理性主义伦理学并坦白了自己的伦理学立场,他说:“虽然理性无疑是道德判断的根源,但是认为有关正确和错误的最初感觉可能来自理性,甚至在那些特殊情况下会来自形成一般准则的经验,则是十分可笑和费解的……理性不可能使任何特殊对象因为自身的缘故而为内心所赞同或反对……最初区别美德和邪恶的不可能是理性,而是感官和感觉。”[1]377
然而,在上面那段话中斯密却似乎是忘掉了他之前的立场,反而主张人性之中存在一个足以抵消自私自利,足以促使人做出高尚行为,并且不会出错的、统领和抑制激情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哈奇逊讲的仁爱或休谟讲的正义而是“理性”。一个情感主义伦理学家为什么要谈理性,并且还将理性、道义和良心这三个具有浓厚理性主义伦理学色彩的概念置于自己学说的关键位置?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饲喂试验表明,本次试验所生产山羊颗粒TMR具有很好的适口性,羊爱吃,每次采食时间约1 h,日喂2次,日采食量为0.833~0.889 kg/只,观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854±0.031)kg/只。日喂3次,日采食量为0.944~1.0 kg/只,观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978±0.031)kg/只。日喂2次,补料2次,采食量为0.944~1 kg/只,观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976±0.029)kg/只。
一、 理性概念的提出
上述理论本无太大问题,但斯密并不满足于仅给出道德的定义,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往往更注重道德教化以及道德准则该如何实现。因此斯密接着给出了现实生活中道德情感的形成过程和德性的端绪,而这一点恰恰成了李德的靶子。斯密认为,同情(sympathy)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并且它总能使人们感到快乐。同情带来的快乐不是被同情对象的原始激情在当事人身上的投射②,而是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的一致时或看到他人赞同自己的情绪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快乐,而这种特殊类型的快乐是“所有事情中人们最希望获得”的。于是为了获得这种快乐,人们就会主动调整自己的情感使之与旁观者的情感相符,这也就是李德说的“诱因”。
1. 李德的批判
托马斯·李德(Thomas Reid)是与斯密同时代的道德哲学家,并且还从斯密那里接手了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尽管他不是第一个意识到斯密伦理学中存在某种分裂的人,但他的批判无疑对斯密造成了很大影响。当代研究者如Norton[2]认为,李德的刺激是《道德情操论》第5次修订的直接原因。
李德在1788年出版的《人类的能动的力量》(Essays on the Active Powers of Man )一书中写道:“某位非常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把有关自我控制的德性的道德判断还原为了对世俗舆论的考虑,他过于重视了对好评的爱,于是创作出了一个幻影替代了德性的实体。”[2]557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李德说的这位独创性的作家无疑就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义中,他把话说得更清楚:“我以为,这个体系(斯密的伦理学体系)与其说是有关真正有德者的理论,不如说是有关如何装出德性的外表的理论。通过这个体系,社会性的德性被还原为了努力同情他人的苦乐,但促进人们做出这种努力的诱因是什么呢?按作者的意思,我们要把公正旁观者嵌入到我们行动的原理中去,要带有同情地行为。但对于目的来说,有必要的仅仅是装作同情他人的外表。并且,对于能引发称赞和喝彩的东西来说,有必要的也仅仅是德性的外表,这样解释的话,社会性的德性就被还原为虚荣心或利己了。”[3]
2.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前,山东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教育机构,学校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山东沦陷以后,这些教育机构遭到日本的严重破坏,“各校或被焚烧或被拆坏的约计十之七八”,学校的校舍、图书和器材多数毁于战火。据统计,全省约283所学校毁于日本炮火,财产损失达到4000多万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日军铁蹄践踏之下,山东较为完备的教育机构基本毁之殆尽,学校被迫内迁或停办,教师和学生被迫流亡或辍学。
斯密认为,人们评判某人行为正确或错误的根据就是他们自己抱有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而在情感主义伦理学体系下,赞同或不赞同实质上直接等同于旁观者和当事人二者情感上的一致与否。因此,在任何人看来都值得赞同的情感,或者说与一个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情感趋于合宜的情感便是普遍意义上正确的情感,由此便可以被称为道德情感。而人们为了使自身的自然情感具有合宜性而做出的努力便是德性。至于德性的内容,根据人类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他人的天性可以推理出两条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德性,它们分别为努力同情体谅他人的仁爱和努力抑制自身激情的自制,这也就是李德所说斯密伦理学中的“真正的德性”。
周岱翰说,不同人有不同口味,如有人偏爱咸,太淡了他一点也不想吃。如果他患高血压,为身体着想他应该吃淡,但太淡了,他可能什么都吃不下去,没了胃口,营养跟不上,身体更差。还不如让他吃点咸,只要总量控制,不会有大问题。很多癌症患者家属认为鱼、鸡、鸭皆属“发物”,不让他们吃,这也是不对的。其实鱼类不仅能提供人体所需又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质,还能养阴补血,完全可以作为癌症患者常用的滋补佳肴。忌口,根据情况遵医嘱即可,享受美食也应是癌症患者高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这段话出自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第三卷第三章“论良心的权威”,这是《道德情操论》到第六版时新增的一章,因此第六版的成书背景和修订原因便是解读斯密的理性概念的关键。《道德情操论》一书一共出过六版,分别出版于1759、1761、1767、1774、1781、1790年,其中第二版到第五版的区别不大,与第一版相比只是在注释里加入了一些对当时学术界批评意见的回应并调整了各章段落顺序。而第六版则修订篇幅最大(新增了第三卷第三篇良心论和第六卷德性论)耗时也最长(这次修订占据了斯密生命的最后三年),斯密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本书的大约三分之一是新写的”。斯密做出这些重大修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同时代道德哲学家托马斯·李德的批判和早期道德情感败坏问题的深刻化。
李德的批判不是空穴来风。在初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说:“共同生活的人们投来的赞同和尊重,对我们的幸福来说非常重要。而只有通过使我们自身成为这样的情感的正当和合宜的对象,并且通过自然赋予的尊重和赞同的尺度和规则来调整我们自身的性格和行动,我们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③既然完全的满足全部或者相当大部分来自于他人赞同,那么培养仁爱和自制的德性就不会是获得满足的唯一途径了。这是因为,人们所赞同的必然仅限于他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而这个能观察到的东西就只能是德性的外表了。别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知道我的动机和我真实的品性。而装出有德的外表显然比真正地培养德性更简单省力,于是假仁假义和隐瞒罪恶的伪君子便出现了。李德的批判正是要揭示这一点:获得他人赞同的愿望不足以构成道德的端绪,不仅如此,这种愿望反倒会造就伪君子。这是斯密在初版《道德情操论》中未曾考虑到的。
2. “道德情感败坏”认识的深刻化
初版《道德情操论》的另一个缺陷同样与“赞同”有关:人们不只会赞同和钦佩有德性的人,还会赞同和钦佩富贵的人,对后者的赞同有导致“道德情感败坏”的危险。
斯密认为,除了同情的天性,人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天性,那就是对痛苦的切身感受比对快乐的切身感受更激烈。例如,损失和获得一笔相同数量的财富,导致的痛苦和快乐却不是同等程度的,损失导致的痛苦总要更激烈一些。再如,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很轻易做到克制自己的喜悦,但悲伤的情绪则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掩饰。这样一来,在一个旁观者那里,同情痛苦就要难于同情快乐,用斯密的话说:“对快乐表示同情是令人愉快的;无论哪里嫉妒都不会同它对抗,我们心满意足地沉湎于那极度的快乐之中。但是,同情悲伤却是令人痛苦的,因此我们作此表示总是很勉强。”[1]56而在人们眼里穷人一般总是愁苦的,富贵的人一般总是喜乐的,因此,人们为了获得他人认可便倾向于夸耀自己的财富和隐瞒自己的贫穷,评价他人时则倾向于钦佩富贵和轻蔑贫贱,由这种天性衍生出的野心、促发的追名逐利的行为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便统称为“道德情感败坏”。
生性好强的他不甘心安贫守旧,通过培训学习,眼界开阔了,思路也宽了,他想自己创业,他根据团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创业思路和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他的农资店在团部开张了。
奈斯的生态自我实现需要人类的精神有种进一步的成熟成长和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世界的确证,这种思想深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甘地的影响,甘地认为当一个人寻求神的真理时,惟一必要的手段就是爱,即非暴力,神就是爱。人们可以通过爱来感化别人。[9]33
然而,现实中人们的道德情感并没有按照斯密在初版《道德情操论》中的乐观预期走上正轨。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贸易的扩大④和制造业的发展⑤使国内财富得到了迅速增加,但中下层民众的道德品质却并未有所提升。商人群体作为曾被斯密一度视为勤勉、正直的中下层民众的代表,在他们获得了支配社会进程的能力后便变得狡诈和贪婪起来,《国富论》(1776年)中斯密相当冷淡地描述他们为:“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5];而中产阶层也步了商人们的后尘,将大量财富和空闲用在了后来经济学家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上,迪克(Dicky)指出,中产阶层“被18世纪50年代以后污染英国的显著的消费‘恶习’所玷污了”[6];至于下层民众,则因整日从事机械性劳动而日益愚笨,又因劳动的异化而日益贫困,他们无力改善自身状况,以至于后来的经济学家穆勒都感叹“工人阶级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总体来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变化,18世纪的人们获得了改变自身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则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已不再适用,人们的野心被解放了出来,它固然显著地促进了物质财富增长但它给人们的道德情感带来的危害同样严重:人们不再重视谨慎、自制的德性而转去崇拜和追求奢侈,甚至于“富人和权贵们身上的罪恶和愚蠢也成了时髦的东西,大部分人以模仿这种品质和具有类似的品质为荣”[1]75。更为糟糕的后果则是斯密时代的商业社会似乎正向着卢梭批判的那个商业社会的方向演化:社会整体的最低生活水平固然因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开展而获得了提高,但人们却并没有利用从中获得的闲暇来追求真正的幸福,反倒是把虚荣、奢侈和高人一等当作了人生的唯一目标。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社会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高人一等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零和博弈,人人都沉迷于炫耀和嫉妒,并且人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焦虑和不安,道德情感败坏对个人的最大危害正在于此。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克服道德情感败坏成了斯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事实上在《国富论》里斯密就曾尝试通过分析雇佣“非生产性劳动”和购买奢侈品可能给经济体和当事人造成的不良后果来规劝人们停止炫耀性的消费,但伦理学领域的问题终究难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他的这一理论很不完善,以至于当以盈利为目的的服务业出现后就不再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提起了。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时隔20年后的第六版《道德情操论》里,斯密正式以伦理学家的身份来直面这一问题。
第二件事是此前媒体盛传的银隆收购天津一汽夏利事件。最初董明珠持支持态度,但在股东会上,卢春泉对此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银隆的技术优势并不在乘用车市场,不宜过早进入这个高投入的市场。
二、 理性的内涵
(1)天性的欺骗和真正的幸福。第一个论证是一个快乐主义的论证,这个论证由《道德情操论》第四卷中所讲的一个穷人的孩子的故事开始。穷人的孩子不幸被“上天发怒时赋予了野心”,他羡慕富人车马成群、锦衣豪宅、前呼后拥的生活,并认为在那种处境中才能品味到幸福与宁静带来的快乐;对他而言,幸福仿佛就是某种高人一等的生活。为了获得这种幸福他甘愿忍受足以毁坏健康的艰苦劳动;为了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不惜巴结所有人,不惜为他憎恨的人服务,不惜阿谀逢迎他本来鄙视的人;在奋斗的途中,朋友的背叛和敌人的不义也是常有之事。在经历了这些磨难之后,他终于如愿凭借自己的勤奋和磨练出的才能获得了财富和地位,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权贵们“见到他,先是轻视,继而妒忌,最后以卑贱地表示屈服为满足,这种态度本来是他们希望别人向自己表露的。”[1]68《道德情操论》此处描述的穷人的孩子正是《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原型。斯密指出,吸引人们奔波忙碌和培养自身才能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1]61而商业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恰恰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中下层民众钦佩富人和权贵这种不道德的动机之上的。
1. 对李德批判的回应:理性是正确地认识自身处境
第六版《道德情操论》新增的第三卷第二篇中,斯密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视为他对李德批判的回应:“造物主不仅赋予了人某种被人赞同的愿望,而且赋予了他某种成为值得被赞同的人的愿望,或者说,成为在别人看来值得自我赞同的人。前一种愿望,只能够使他希望从表面上去适应社会;后一种愿望对于使他渴望真正地适合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一种愿望,只能够使他假仁假义和隐瞒罪恶;后一种愿望,对于唤起他真正地热爱德性和痛恨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斯密区分了两种愿望并指出,只有“成为值得被赞同的人的愿望”才是德性的真正端绪。那么何谓“成为值得被赞同的人的愿望”呢?按照斯密的解释,这其实也是一种被赞同的愿望,只不过这里给出赞成的不是旁人而是当事人自己,更确切地说就是上文提到的“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人”,也就是内心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在不考虑道德情感败坏的情况下和现实中的他人有着同样的赞同的标准和原则,但不同的却是他能够知晓当事人的真实动机和本来面目,当事人的一切伪装都不能瞒过他。若想获得他的赞同,除了成为真的有德的人之外,便再无他法。当人们考虑到这个内心的旁观者的意见时,李德说的徒具德性外表的伪君子就不会存在了。然而作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家的斯密还必须回答公正旁观者在经验中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人们才能够设想出这样一个内心的旁观者并且愿意重视他的评价胜过重视现实中他人的评价?斯密认为促使人们这样做的动机正是理性。
斯密据此指出,道德情感败坏起因于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因此它不是不可克服的;并且一个真诚地追求个人幸福的人应当主动去克服它。而克服它的工具恰恰就是理性——这里的理性依旧仅仅是一种认知能力。它的作用是教我们识破天性的欺骗并认识到真正的幸福。
事实上斯密之所以遭受李德批判,正是因为他在第一版《道德情操论》和之后的《国富论》里把人们自发地运用理性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人性预设:“酿酒师、屠户、面包匠自私自利的算计”不可能不依赖他们各自的理性。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家们虽然贬斥理性在道德哲学领域的地位,认为它不足以作为道德和德性的动机和端绪,但他们并不贬斥理性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能起到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启蒙主义者们还坚信,人类能够并且必然会在理性的照耀下获得幸福。李德的批判固然一矢中的,但若非经验中有例证存在,虚荣伪善的行为在斯密看来反倒是难以理解的:对于一个徒有德性外表的伪君子来说,旁人和社会舆论虽然投来了赞同,但这赞同却不是投给他本人,而是投给他装扮成的那个人的。伪君子内心的那个人或者说他的理性时时都会提醒和否定“由于你知道自己不应该得到这种称赞,所以接受它们就会使你变成可卑的人”[1]150。这样一个费尽心思伪装自己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人,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愚蠢的了。但是无论如何,有伪君子存在这个经验现象是斯密必定承认的。因此在第一版里,作为默认预设的理性才在第六版里降格为一个要求或补充条件。一言以蔽之,斯密所言的“理性”并未逾越情感主义伦理学的范畴,它终究是一种认识和推理的能力而非某种先验的道德律,它自身只有工具价值。但在它的协助下人性中的某些天然倾向会成为德性的端绪,就道德判断的过程这一层面来说,理性就是真诚和正确地认识自身的处境。
2. 抑制道德情感败坏:理性是审慎地认识幸福与获得幸福的手段
斯密的理性不仅涉及道德判断的过程,同样也关系到了道德判断本身的判断标准,并在抑制道德情感败坏这一主题上凸显了其在后一层面上的作用。在第六版《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援引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学说,提出了两套不同主旨的论证,以对抗和抑制道德情感败坏。这两个论证的主题分别是真正的幸福和德性的唯一合理性。
道德情感败坏不是第六版中的新发现,早在第一版中斯密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所论述了。关于道德情感败坏成因,第一版和第六版的论述没有太大出入;但关于它可能导致的后果,第一版和第六版的态度截然相反。在第一版中,斯密认为道德情感败坏只发生在一个社会的上层人士、即富人和权贵身上,而中下层民众若想获得他人的赞同和尊敬便只有通过“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1]74才能获得成功,对中下层民众而言,追求财富和地位的道路与追求德性的道路是重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中崇拜财富和地位的倾向反倒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使中下层民众有德,因此道德情感败坏纵然“是对高尚的道德甚至是对美好的语言的一种亵渎”[1]73但考虑到它所能够带来的社会效用,道德哲学家们却尚可把这个问题放置不论[4]。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斯密在第六版《道德情操论》中增添了很多新命题,如内心的旁观者、自我认可、审慎之德等。以往学者对这些命题已有单独评述,在此不表。笔者认为,隐藏在这些新命题背后、并贯穿起它们的东西正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句话中的“理性”概念。在斯密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体系下,这个理性不是也无需是某种先验道德律;同时也并非休谟说的那种完全服务于情感的认知工具,它的具体定义还要结合斯密对初版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的回应来分析。
语篇的结尾部分“In short,we are seeing cyber flexing and,cyber exercises,in some cases,but not cyber war.”是对“网络战争说”的总结和评价,是从整个语篇中浓缩出来的宏观新信息,与该语篇的题目、宏观主位“Cyber war,this is not”及“要闻”遥相呼应,它们属同一语义关联层级,用不同的语言反复强调着该语篇的中心思想。
斯密借着这个故事指出“所有人都必然会或迟早会适应自己的长期处境,真正的幸福只存在在平静和享受之中”[1]172,“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一个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1]216。钦佩富人和权贵固然是一个天然的心理倾向,但这个倾向却是“天性对我们的欺骗”[1]214,它起因于人们在同情富人和权贵时自然而然地犯下的一个认知上的错误:人们永远不能直接感受他人的情绪,同情本质上只是当事人通过想象把自己置身在他人所处的环境时所产生的情绪。在同情富人和权贵时,人们仅仅看到了富人和权贵拥有更多获得幸福的手段,便因此认为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值得被追求,而这是错误的。完美的幸福的关键要素之一正如伊壁鸠鲁学派主张的那样,“存在于肉体所感到的舒适和内心所感到的安宁之中”[1]350,财富和权力本身是为了肉体上微不足道的便利被设计出来的“庞大而费力的机器”[1]213,当它们带来的便利超出了当事人所能享受到的程度时,它们不仅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便利反而会给他带来维持上的麻烦和失去它时的危险。
然而,穷人的孩子的故事还有后半部分:穷人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劳苦拖垮,他的心灵已经因遭受了成千上万次挫折和不义而充满羞辱和恼怒。回首往事时他突然发现,“财富和地位仅仅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它们同玩物爱好者的百宝箱一样,给带着它们的人带来的麻烦多于它们所能向他提供的各种便利”[1]232,而它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业已放弃的那种微末的安定和满足好多少”,他穷其一生不辞劳苦追求到手的生活居然并不比他本来的生活好上多少。钦佩富人和权贵的心理倾向固然促进了商业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但从个人幸福角度来看这种心理倾向却摧毁了穷人的孩子们的安逸和宁静。
上海市近期将进一步深化完善共有产权保障房申请供应政策,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规定标准分值(120分)、已婚、在本市无住房、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5年、符合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收入和财产准入标准的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保障范围。
同样在第六版新增的这一章中,斯密把这两种不同来源的评价比喻为法律裁判中的二审和一审,并且认为:“虽然人以这种方式变为人类的直接审判员,但这只是在第一审时才如此;最终的判决还要求助于高级法庭,求助于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求助于那个假设的公正的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法庭,求助于人们心中的那个人。”[1]150内心或良心的法庭之所以有更高效力是因为内心的旁观者掌握了更完整的情报,所以他给的评价必定比现实中他人给的评价更准确。而理性则要求当事人认可和重视正确的评价,忽视错误的评价。在这个层面上,斯密的理性一方面不是先验道德律而仅仅关乎对事实的推理、归纳和认知;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要求,它要求当事人正确地认识自身处境。
(2)德性的唯一合理性。第二个论证是一个怀疑论和演绎法的论证。通过这个论证斯密试图证明唯有同情别人和抑制自己的激情的两个德性才是唯一合理的、值得赞同的事情。在上一个论证中,斯密肯定并采纳了伊壁鸠鲁学派的一些主张。但他并不赞同伊壁鸠鲁学派将所有快乐都归结于肉体舒适的观点。正如上文介绍斯密的德性论时所述的,斯密认为,来自肉体感官的快乐只是某种“原始激情”,它固然是真实的但不是所有快乐的源头。除了这种快乐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快乐:例如受人尊重、成为尊重的合宜对象以及与亲人朋友相处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合宜的情绪。与前一种快乐相比,这种相互同情和被赞同的快乐才是“每一个善良的心灵更为重视的事情”[1]351。缺少或忽视了诸如亲情、友情的社会性情感的生活,即便再舒适、再优越,也显然不能被看作是幸福的。如此,阻碍我们获得这种快乐的直接原因则是同情的局限性:同情发生于对某个境遇的观察,它的强弱程度一定与观察的真切程度有关。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自己所处的境遇,他对自己所处境遇的观察便必定非常细致和真切,所以他对自己的同情、或者说自爱的程度必定非常强烈;相反,人们对别人所处境遇的观察便不会像对自己那样真切,因此人们对他人的同情必定不比他人的自爱那样激烈。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过多地关心自己,而过少地关心他人。过强的自爱和过弱的同情就会导致社会交往中人们情感上的不合宜。斯密据此推理出,克服这个缺陷使自身的情感获得合宜性的方法,也就是同情别人和抑制自己的激情的仁爱和自制这两种德性。
但是,在道德情感败坏的情形下人们不再关注一个人是否具有这两种德性,转而以是否拥有财富和地位来判断他是否值得尊敬。实际生活中富人和权贵们若想获得他人的尊敬便必须彰显他们优于常人的财富和地位。于是类似奢侈、时髦这样炫耀性的消费便成了道德情感败坏的社会中评价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的指标。而在斯密看来,这些指标是不自然和荒谬的:它们仅仅来源于个别富人和权贵们恣意的偏好和愚昧民众的盲从。如果我们问一个爱好虚荣奢华的人那些他所痴迷的东西究竟有何可赞同之处,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理性中找出一个根据来说服我们的。这是因为理性正像休谟说的那样,仅仅能够描述和推理事实而断然无法赋予它所描述的某件事情或某种状况以好或坏、值得尊敬或应当谴责的价值。斯密与伊壁鸠鲁不同,他认为追求精神上的快乐或者说交往时情感上合宜的快乐是自然赋予人的天性,人们愿意这样做也必然会这样做。凭借自身所具的理性,人们基于同情皆有远近之分和赞同即是情感上的一致这两个事实可以推理出同情别人和抑制自己的激情这两种德性必然可以受到赞同,这种必然性是由推理保证的。但某种理智上趋于怠惰和盲目的倾向却使人把评定赞同和尊敬标准的权力交给了社会舆论,交给了那些炫目、浅薄和反理性的风气。于是,斯密借斯多葛派学者之口道出了他的主张:“据斯多葛派学者说,因为我们按照每个事物在天下万事万物中所占的席位,运用这种正确和精确的识别能力去做出选择和抛弃,从而对每个事物给予应有的恰如其分的重视,所以,我们保持着那种构成美德实体的行为的完全正确。这就是斯多葛派学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生活,即按照天性、按照自然或造物主给我们的行为规定的那些法则和指令去生活。”[1]322斯密笔下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即便生活在一个道德情感败坏的社会中也依旧能够维持自己的德性,因为他的理性使他推理出了什么是真正和必然值得赞同的事情。在斯密的语境下,德性或者“自然给我们的行为规定的法则”不是某种先验的道德义务,而是人们依据理性基于人性事实推得的道理。一个人越是重视理性,便越是免于受到道德情感败坏的影响,并越是有德性。
道德情感败坏使人们混淆了对德性和对财富地位的尊敬乃至于将后者当作了评价幸福和荣誉的唯一指标。斯密这两个论证之目的都在于对抗和抑制这种倾向。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论证在较低的层面上要求人们认清和舍弃那些与真正幸福无关的东西,而第二个论证则要求人们用正确的方式把握真正的幸福,或者说在较高的、道德修养层面上要求人们真正地认可并具有德性。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动机不可能是理性而只能是情感,这是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张之一,斯密的伦理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否接受理性的指导,是否采取合理的手段来获得幸福,却决定了情感动机的进路是德性还是伪善或虚荣。与回应李德批判部分相同的是,斯密在抑制和克服道德情感败坏的问题上所用的理性仍是一种工具性的认识能力,而就认识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一层面来说,理性就是识破天性对我们的欺骗以及采取合理的方式追求幸福。
三、 理性的意义
综上,无论在回应李德批判的主题上还是在抑制道德情感败坏的主题上,斯密所讲的理性都是情感主义或英国经验主义体系下的理性。它终究是一种认识能力,即一种推理的工具而非义务论或理性主义体系下的某种先验道德律[7]。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本不是认识或推理,但这种工具性的理性对于斯密的伦理学来说却极其必要以至于不得不谈。斯密谈理性的原因表面上来看是为了解决初版《道德情操论》面临的两个问题。但从《道德情操论》版本演变方面来看,第六版新增的理性概念最终促使了斯密的伦理学完成了由描述性的道德心理学向规范性伦理学的转变。我们认为,这就是理性之于斯密伦理学的最大意义。
当代研究斯密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道德情操论》一书较多对心理和社会事实的描述而较少规范性要求[8]。比如,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的主编拉斐尔曾明言,《道德情操论》是一部描述性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著作而非规范伦理学著作[9]。但笔者认为,斯密并非没有规范道德理论,或如学者们所说的,无心建构规范道德理论[10];他的这一理论隐含在初版的自然秩序之中,直到第六版理性概念的出现才由一种被动的秩序或规律显现为了一种主动的规范要求。在初版中,斯密用一种陈述性的语言阐述了一种自然秩序[1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性善论”。即,人人皆有同情心和某种希望被赞同的愿望,这些能力和愿望会在自然秩序的安排下最终转化为德性。然而,如前所述,真正到了现实生活中,自然秩序不是放任不管就能自然运行的,人们只有遵循理性的指导方能使自己的本性贴合自然秩序从而有德和幸福。斯密虽然尊重人们自由的自然情感,但不是所有自然情感都是道德情感,他认为只有遵从理性指导,符合了自然秩序的才是。理性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认知和推理能力,其本身固然不足以提供某种主动性的道德规范,但却起到了保证自然秩序得以正常运行的作用。斯密伦理学的目的在于人性自然的实现,这一点从初版到第六版都没有变。而其规范性要求则是重视理性的指导,用正确的方式真诚地追求真正的幸福,这一规范道德理论只有靠第六版的理性概念的补充才能够完全成立。
(2)报名结束,整理所有参赛者的信息,召集参赛者开赛前会议,介绍比赛的具体内容以及流程,解答参赛者的疑问,发布第一环节的比赛试题;
以上所说的还仅仅是理性概念对于构造规范性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体系的意义。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七章中还曾说过,一个伦理学思想属于情感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以及它是否具有规范伦理学的要件,这只是引起哲学家好奇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思辨中非常重要,但在实践上并不重要”。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特殊身份,并把他晚年的理性概念代入到他早年的《国富论》中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理性概念不仅是对他早年伦理思想,也是对他早年经济思想的修正[12]。
众所周知,在《国富论》中斯密借经济人假设和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论证了,自由放任政策下各个经济人的自由活动将会使当事人和整个社会双双受益[13]。然而,在道德情感败坏的情况下,这个理论却不能完全成立[14]。因为正如斯密在初版中所说,促使人们去追求财富的,不是获得安全和维持生存的愿望,而是引人注目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分工和自由贸易确实可以带来物质资料的增长和基础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使人们的前一种愿望获得普遍的满足,但它对于后一种愿望却无能为力:一个社会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人上人,物质财富无论怎样增长都无法使每个人都在财富和地位的序位上凌驾于其他人。于是为了把别人踩在脚下,人们便要追求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而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以至于即使某一天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足以轻易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物质资源已经丰富到如同休谟假想的“黄金时代”的水平,即“每一单个人都发现不论他最贪婪的嗜欲能够要求什么或最奢豪的想象力能够希望或欲求什么都会得到充分的满足”[15]的程度,这些“穷人的孩子们”也不能“沉醉于音乐、诗歌、欢笑和友情”[15]35而仍旧要为生计和闻名欲无尽地操劳。如若不然,他们便要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过上真正唯有汗流浃背方能勉强糊口的日子。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本应是更少、更轻的劳动和更多、更高品质的闲暇,但是在道德情感败坏和竞争的双重影响下,人们却比以往更加劳累。更加糟糕的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基础需求的满足,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更具破坏性地危害人们的生活。斯密固然不是凯恩斯或马克思,他所处的时代无法让他亲身感受经济自由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所隐含的危机。但他在晚年时却隐约预感到了这些[16],并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提示了解决之道。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像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一样能够凭借理性区分真正的幸福与财富带来的幻象,那么他们又怎么会牺牲自己已有的安宁生活去追求那些实际上自己无法享受到的财富,进而导致生产过剩呢?如果人人都像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一样仅仅把具有仁爱和自制这两种德性作为唯一能被接受的赞同,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为了财富和地位这种在理性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用不正义的手段去剥削别人,进而导致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呢?斯密预见到了这些理论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像后来经济学家一样为自由主义增添政府干预的对策,反而是给这个理论中的人加上了一个伦理学意义上的限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理性,即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和真正幸福的理性能力。斯密的理性概念之于其经济学的意义亦正在于此: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好的体系,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由一群遵循理性的人组成才可能带来理想的结果。
注 释:
①已有观点指出,将斯密的sympathy一词译为同情并不妥当(罗卫东.老调重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 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说起[J].博览群书,2005(3):34-42.),这是因为sympathy一词在斯密原著中是指一种情感上换位思考的能力,并没有什么心肠好坏的含义;相对的,同情一词在汉语中则可以引申出好心肠、善良等带有价值判断意味的概念,因此准确的译法应是“共感”,但在汉语中“共感”是一个生僻词汇,并且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本文依旧采用同情一词。
②事实上,同情对象的原始激情既可能使当事人感到快乐也可能使当事人感到痛苦,比如当我们同情一个痛苦的人时,我们也切身实感了他身上的痛苦。第一版《道德情操论》问世后休谟就曾拿这一点反驳过斯密“不管怎样,同情及增加快乐也减轻痛苦”的观点。斯密回应是,“我的答复是,在有关赞同的情感中,存在着两种引人注目的东西;第一,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激情;第二,由于他看到自己的表示同情的激情同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完全一致而产生的情绪。后一种情绪——其中当然存在有关赞同的情感——总是令人愉快和高兴的。前一种激情既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也可能是令人不快的,这要视原始激情的性质而定,它的特征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
③这一段话在第六版中被删去了,可见斯密意识到了初版中的这个问题。
④七年战争(1756—1763)胜利,将法国势力从北美和印度殖民地驱逐了出去,由此建立起了势力遍及全世界的庞大帝国。
⑤自30年代起纺织业机器不断改良,棉纺业产量大幅提升,1764年珍妮纺纱机问世。
参考文献:
[1]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M].Camibridge:Cami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 Thomas Reid.Essays on the Active Powers of Man [M].London:Thoemmes Press,1994.
[3] Norton D F,Stewart-robertson J C.Thomas Reid on Adam Smith ’s Theory of Morals [M].Philadelphi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84.
[4] 张翼飞.文明社会的伦理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主题[J].求是学刊,2017,44(6):25-30.
[5] 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 Dicky L.Historicizing the Adam Smith problem:Conceptual,historiographical and textual issues[J].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86,58(3):579-609.
[7] 徐向东.康德论道德情感和道德选择[J].伦理学研究,2014,69(1):59-66.
[8] 李家莲.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J].道德与文明,2018(4):124-129.
[9] Raphael D D.The Impartial Spectator [M].Oxford:Clarendon Press,2007.
[10] 李家莲.论斯密伦理思想对哈奇森仁爱观的背离[J].世界哲学,2018(4):66-72.
[11] 罗卫东,王长刚.亚当·斯密的知识论及其意义[J].世界哲学,2018(1):78-86.
[12] 柘植尚則.良心の興亡[M].东京:山川出版社,2016.
[13] 张江伟.亚当·斯密重商主义批判的政治学维度[J].政治思想史,2018(4):101-118.
[14] 张江伟.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斯密论商业社会对个人道德的要求[J].道德与文明,2017(3):124-132.
[15] 大卫·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6] 李宏图.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J].世界历史,2017(4):4-17.
Why does a Sentimentalist Talk about Rationality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Adam Smith’s Ethics Theory
Jia 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 Adam Smith was a great master of English emotionalist ethics during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eriod.In the sixth edition of his book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however, Smith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and put it in the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his doctrine.This article tries to combine Smith’s thoughts with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s, and then goes to great lengths to examine and interpret the changes of themes discuss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his book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By th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w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Smith’s ethics theory, though he did not give up his standpoint of emotionalist ethics.In a sense,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could be able to provide some historical inspiration and illumination for contemporary sentimentalism moral theories and economic theories.
Keywords : rationality; emotionalist ethics; Adam Smith; the corruption of moral sentiments
中图分类号: B8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 2019) 06-513-08
收稿日期: 2019-04-17.
作者简介: 贾 谋(1989— ),男,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贾 谋,13642059896@163.com.
标签:理性论文; 情感主义论文; 斯密论文; 道德情感败坏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