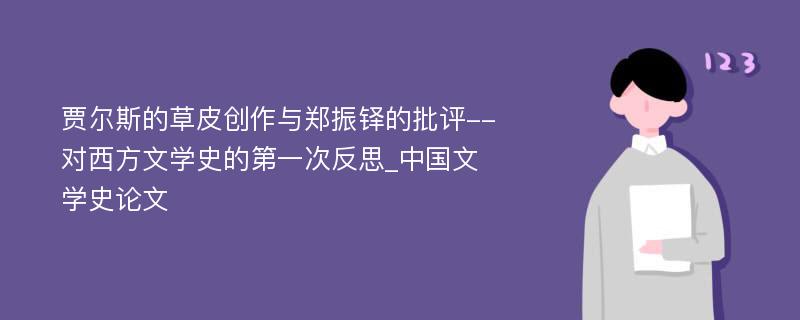
Giles的草创与郑振铎的批评——西方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部论文,批评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郑振铎论文,Gile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I206.09
近些年来,从“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到《文学史》辑刊的出版,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已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史学,以及中国文学史学史,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些早被淘汰的著作,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等重新被提起、被讨论。但是,作为这些早期中国文学史范本的日文中国文学史,还有英文、德文中国文学史,却未能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史发生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的发韧之作,只有追溯到它真正的源头,才能了解其范式的初始状态及演变过程。此外,将国外中国文学史写作纳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的个案予以考察,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的需要。本文探讨英国汉学家Helert Allen Gi-les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ture(《中国文学史》1901),以及中国文学史家郑振铎对该书的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一
Giles中文名翟理思(士、斯),1845年出生,1867年到中国任使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1891年离华时为宁波领事。1897年继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28年退休。1935年去世。Giles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出版有关著作和译作六十余种。经其修订的汉语罗马字拼音系统,即威妥玛——翟理思音标,仍是目前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七十年代,新中国编纂第一部汉英字典时,Giles的《汉英字典》(1892)仍是主要的参考书之一。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全译本。他的几个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Bertram Giles翟比南和lance Gilesa翟兰思曾分别担任过南京和天津的总领事,Lionel Giles翟林奈于1900——1940年间在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东方(主要是中国)书籍。
Giles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之际,Wade已去世两年,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James Legge理雅各也于当年去世,英国的汉学研究正处低谷时期。由于当时英国上下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无知,汉学尚未形成气候,Giles在剑桥既没有专业上的同事,也没有助手,30年间跟他读中文学位的学生也只有寥寥数人。另外一些大学也有几位汉学教授,Giles对他们似乎颇为不屑。例如,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职的Edward Harper Paiker庄延龄常有著译出版,Giles总是要指出其中的错误或不妥的地方,两人笔战频频;伦敦皇家学院任职的Water Caine Hillier禧在明出版了两卷本的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中文学习指南》1907),立刻遭到他的猛烈抨击;牛津大学接替Legge的Thomas Lowndes Bullock布勒克,除了在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及编过一册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1902)外,只是埋头教学,不愿著书立说,据说就是畏惧Giles的批评。这些不能仅仅看成是同行相轻,Giles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同行还是十分敬重的,如Legge及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Friedrich Hirth夏德。对自己的作品Giles也要求甚严,所满意的只是两三种而已,1901年作为伦敦出版的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tures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恰好在其中。
二
Giles的《中国文学史》原书32开本,448页,按朝代分八卷,每卷又分数章,分别介绍那个时期的经典、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杂著等。第一卷封建时代,从公元前600年到前200年,主要介绍五经、四书、诸子和楚辞;第二卷汉代,从公元前200年,主要介绍秦汉时期的诗文、历史著作及佛教经典的翻译;第三卷小朝代(即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00年到600年,主要介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潜、鲍照等人及一些研究典籍的学者;第四卷唐代,从公元600年到900年,介绍了从王勃到司空图之间的主要诗人,以及儒家经典研究、古文运动等;第五卷宋代,从公元900年到1200年,主要介绍历史学家、理学家、诗人,以及《广韵》、《集韵》、《太平御览》、《文献通考》,还有星象、植物、医药方面所谓的“百科全书”;第六卷蒙古朝代(即元代),从公元1200年到1368年,主要介绍文天祥及其后的一些诗人,《赵氏孤儿》、《西厢记》等戏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第七卷明代,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主要介绍宋濂之后的一些诗人,《金瓶梅》、《今古奇观》等小说,《琵琶记》等戏剧,以及《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第八卷满族朝代(即清代)从1644年到1900年,主要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还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工具书,《日知录》、《皇清经解》等学术书,《小仓山房尺牍》、《花镜》、《感应篇》、《玉历钞传》等杂书,以及晚清的《申报》和翻译的《天路历程》、《教育论》、《基督山伯爵》、《伊索寓言》,最后还谈到中国传统中的幽默问题。
这是一部读物型的文学史,而非讲义型或论著型。全书以内容概述和作品译介为主,偶尔引用一点前人的评论,很少发挥什么高见,只是尽可能地引导读者去亲近原作。书中选录的各类作品,除四书五经用了Legge的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中的译文外,都是出自Giles本人的手笔。
用今天的学术水准来估量,这部文学史体制简陋、选材不当、判断有误的地方一定有不少,可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进程看,对中国文学有如此全面、系统的知识,并以当时刚刚盛行的文学史形成予以介绍,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只是个别人物对偶尔接能的个别作品感兴趣而已。那些诗、戏剧或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都不清楚,赞美也好,批评也好,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好恶,误读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状况即使在汉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也普遍存在,或许是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错位吧?而Giles当年以一己之力,本着求真的态度,完成了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全景描绘,仅凭这一点也可谓功不可没。
从中国文学史范式的形成看,Giles以朝代分期,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类,已是初具规模,早期同类著作少有能及。日本古城贞吉和笹川种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分别出版于1897年和1898年,较Giles之作早,但都因篇幅较小,内容过于单薄,影响不大。中国人自己最早的本国文学史,一般认为是林传甲1904年印行的《中国文学史》,时间较迟不说,全书仅七万字,观念陈旧不堪,未能统一按时代分章节,且只写到宋代就中断了。这样看来,无论从文化交流的意义,还是从文体草创的立场看,Giles的著作都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
然而,Giles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本土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不久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文学史写作时,目光都集中在日本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上。林传甲自称师法笹川种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书名中的“大”字显然是日语用法,写《中古文学史》的刘师培,写《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都与日本学界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最早关注Giles的是郑振铎,那已经是三十年代的事了。郑振铎写过一篇短文《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另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和《我的一个要求》中也曾提及。
郑振铎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又以这方面藏书丰富而著称,加上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不能满足Giles已有的成绩。他以“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的标准来衡量Giles的《中国文学史》,自然发现了许多错误。《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一文,对原书作了毫不含糊的批评。该文主要部分分四节:甲,疏漏;乙,滥收;丙,编次非法;丁,详略不当。关于原书的优点,只是在结尾部分一笔带过:“总之,Giles这本中国文学史,百孔千疮,可谈处极少。全书中最可注意处:一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二能注意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除了这两种好处以外,Giles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郑振铎的批评无疑是言之有理的,至少是言之有据的,那么,Giles的《中国文学史》真的只有那一点点价值了?我们并不这么看。郑振铎的判断自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判断的标准上,他不是将Giles之作当作中国文学史草创之作,从发生学的立场探讨其历史价值,而是将其与后三十余年中国文学史已有的成绩作比较,用共时的目光追问其学术价值。
文学史的研究在不断发展,文学的观念和学术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郑振铎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可以批评Giles的不足;不用理想的文学史作参照,换一种眼光重审Giles的《中国文学史》,对于郑振铎的一些批评,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例一:郑振铎批评Giles之作“滥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的东西”,所举例为《花镜》一类园艺书籍、《感应篇》一类道教读本。郑振铎说“文学作品的范围本来不易严密的划定”,可又要以“文学元素”来作取舍的标准。什么是“文学元素”呢?郑振铎所取的是所谓“纯文学”的概念。而“纯文学”只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文心雕龙》,我们不是也可以说刘勰滥评了许多“非文学作品”吗?翻一翻今天流行的英国文学史,无论是牛津版还是剑桥版,其Essay散文部分不也是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吗?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逐渐趋向文化研究的今天,清楚的界分纯与不纯的文学已经毫无意义了。例二:郑振铎说Giles之作“详略极不均”,“李白不过四页,杜甫不过二页,司空图则反占了九页”。这种指责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各人心中自有尺度,详略取舍不一定要意见一致。想一想我们古代一些唐诗选本,独尊王维,而不看好李白或杜甫,《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不选李贺,我们可曾因此否定其价值?郑振铎接着又说:“《红楼梦》则几占有三十页,尤其奇怪的是蒲留仙之《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而Giles则推崇甚至,叙之至占二十页之多,且冠之于清代之始,引例至五六则以之。“在《我的一个要求》中,他又说:“此书误解之处极多,如以《聊斋》与《红楼梦》并举,及给《笑林广记》以重要的位置等,都是极可笑的。”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过不了几年郑振铎本人也会觉得不妥。《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代表着清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笔记小说和章回小说的最高成就,在今天已得到世人的公认,用醒目的位置和大量的篇幅予以介绍,不仅不是失察,而且正是表现了Giles慧眼独具的超前意识。例三、郑振铎说:“又于叙清代文学之末,忽叙淳于髠及汉唐宫庭弄人之语,这都是编次极不对的地方。”既然是断代分卷,在清代部分叙述汉唐内容,的确是不少的错话。然而对于这部书的目标读者来说,已经习惯于英语文学的幽默传统,而在中国文学中见不到幽默的成份,自然会有疑惑,Giles正是为这部分读者写下这段追溯到汉唐的文字。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谈密尔顿悼亡诗时,引述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与时间和国别的体例都不符,我们不仅没有指责他,反而称赞他的比较文学视野。Giles难道不也是试图打通两种文化的隔阂,何况他还在替中国说话呢,郑振铎的批评是否有点是非不辨?
郑振铎提到Giles注意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有眼光的,这里补充一点,Giles不仅谈到佛经翻译,在介绍晚清文学时,他还谈到西方著作的翻译。中国文化有过两次大的一放时期,一是中古时期对佛学的接纳,一是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大量的翻译作品对其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些年,国内出版大型丛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就特设了“翻译卷”,把翻译作品也看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有人还认为这代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其实,Giles早就注意到前后两次文化对话的意义,并记录下文化交流的最初成果,虽然远不够全面,其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治史者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四
我们针对郑振铎的批评,替Giles作了一些解释,并非要说明他的《中国文学史》有多么杰出。事实上,任何一部草创之作都不可能杰出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是想将Giles之作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在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之下,它做出了哪些成绩,对于我们今天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哪些有认识价值,哪些有参考价值。抛开一些意气之争,减少一些认知的盲目,看清楚中国文学第一次被纳入西方视野,被纳入世界文学系统中的形态,无疑是有益的。当然,我们只是初步涉及了这一问题,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