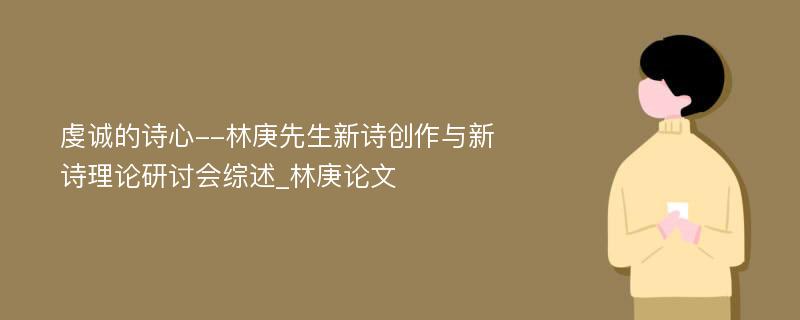
一颗虔诚的诗心——林庚先生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一颗论文,的诗论文,虔诚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4月15日,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林庚先生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这是继2月22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林庚先生90寿辰举办的祝寿会之后,针对林庚先生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方面的贡献而举办的学术研讨活动。三十余位诗人、诗评家对林庚先生的新诗创作、新诗理论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及不灭的诗歌精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吴思敬和孙玉石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
林庚先生的诗歌精神:建安风骨,布衣怀抱
吴思敬在主持发言中,代为宣读了因故未能到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的来信。温儒敏在信中说,林庚先生是现代最关注新诗命运,又对新诗的得失最有真知的诗人,开这么一个主题的研讨会不只是对林先生个人的评价,也是对新诗理论资源的发掘,可以引发对新诗前景的思考。孙玉石向大家介绍了林庚先生的近况,刚满90岁的林庚先生精神很好,还在坚持写作,最近刚出了两本书:一本诗集《空间的驰想》,一本诗论《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孙玉石动情地称林庚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系宝”,他一生对诗的追求,对学术的探究,孜孜不倦、不断创造,永远保持着年轻的精神,是北大中文系的灵魂和“系格”的代表。林先生将一生的热情倾注在学术和创作的园地中黾勉耕耘,他对名利一向淡泊,开研讨会不是他的初衷,但对于新诗创作和理论的发展而言,研究林庚却有着重要意义。感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为筹办这次研讨会所做的努力,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对林庚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深入下去。
老诗人牛汉说林庚决不同于其他带着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诗人,他对新诗有着独立的认识和执著的探索。林庚最初写自由诗,1935年以后转入对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尝试。唐弢曾把林庚的诗批得一塌糊涂,血淋淋的,语言很粗暴;以后又有各种各样的讽刺和批判袭来,但他直到现在还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新诗创作和新诗格律的建构。先不说他的创作和理论本身的价值,就看他这种诗歌精神,给中国新诗带来了多少生气、多少启示!牛汉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几位毫不知名但都曾为中国新诗默默奉献的诗人的交往,认为林庚恰恰也是这样一位中国新诗默默的、清醒的开拓者。牛汉对林庚甘于寂寞的精神表示由衷的钦敬和欣赏。他说,在林庚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暗淡的,似乎显得灰暗冷清,但却很静、很美,这是一种艺术、一种人生的境界。牛汉说,中国新诗史上为诗奉献了一生的人们,有的黯淡、有的明亮,但都是恒星,都具有永恒的亮度;诗坛上有的人哗众取宠,虽然亮得刺眼,我却闭上眼,不看他们;但对这些默默奉献的诗人们,我永远都凝视他们。应该有一部更详细的新诗史,给大家提供一些被掩盖的内容、被埋没的诗人。林庚以及其他为新诗默默奉献了一生的诗人,不要忘记他们,他们在历史上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却仍然保持着对新诗的虔诚和热情。
谢冕认为林庚是一位始终如一的、真真切切的现代诗人,深厚的古典诗歌造诣与真切的现代诗实践构成了林庚先生的特殊魅力,他的诗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谢冕说,作为听过他课的学生,我始终在他的旁边注视他,学习他的治学、做人。林庚先生乐观超脱、清淡高雅、与世无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名士风度。看到邵燕祥先生在《九言诗的一次小试验》中说他在1950年或1951年才接触到林庚关于九言诗的主张。我很骄傲,我是1947年读到林庚先生的诗的,十五六岁还曾模仿林先生的九言体写诗,虽然当时没有机会向林庚先生求教,但九言诗给了我少年的启示。林先生一生都浸泡在古典中,却永远是年轻的、青春的、现代的。最后从未写过旧诗的谢冕还为林庚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建安风骨、布衣怀抱;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曾直接受到林庚先生教益的洪子诚、费振刚、吴福辉等也都对林庚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歌精神敬仰有加。洪子诚说,林庚先生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都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容易就是不平常”的境界。他是一个葆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不发宣言、不打旗号、不拉帮结派、不党同伐异、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保持着思想、人格、学术和诗艺的“独立”。这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他和新诗、和诗歌研究所建立的关系,使我们理解了他所推重的古代“寒士”、“布衣”的内涵。费振刚说林庚先生是为人为学的典范,越到晚年越平淡,“繁华落尽见真淳”是林庚先生的写照。他不赶世俗的热闹,少有出席会议,从不四处剪彩,也不忙着当顾问、做主编,而是甘于平淡,潜心学术。吴福辉回忆了“文革”期间听林庚先生在课堂上讲课和在宿舍高声唱歌的情景,高度赞扬了林庚先生在衰落的、废都一样的北平,还在思考民族、现代的问题的精神,他将林庚先生的诗歌精神归纳为四点:一是最现代地融化了古诗和西洋诗;二是在中国把一种人文精神和时代节奏融为一体;三是于格律中追寻一种自由的表达,是自由的格律诗;四是一种精英文化对市民文化的靠近。
林庚先生的新诗创作:现代精神,古典韵致
林庚先生诗歌的生命之树长青,他的新诗创作从193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问路集》、《林庚诗选》及《空间的驰想》等诗集。他曾经写过不少旧诗,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赏,但他开始新诗创作之后便不再写旧诗,而将激情全部倾注在了新诗上。他的新诗创作包括自由诗、新格律诗,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孙玉石对林庚30年代的新诗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林庚的新诗创作最重要的成就在30年代,那时林庚抱着通过诗歌使人生获得解放的理想放弃了旧诗,开始新诗创作。1933年他以诗集《夜》获得清华大学毕业文凭,成为清华大学教学史上第一个用诗集代替毕业论文的学生。俞平伯在为《夜》所作的序言中称林庚的新诗是“异军突起”。林庚的才华在新诗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孙玉石认为林庚30年代的诗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完成了边城知识分子心态的雕塑,如《空心的城》、《北平自由诗》、《黄影》、《朦胧》、《沉默》等,从各个角度展现了边城人在痛苦和孤寂中的徘徊,对古城的眷恋、对现实的抗争、对未来的凝望……二、他是生命、自然、青春和童心的赞美者。林庚即使在压抑的环境里也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相信诗可以解放人生,因为那里蕴涵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冲动、爱与美的渴慕和追求;林庚对自然的描写和生命的赞美是融合在一起的;林庚在诗中将诗人与孩子的对话变成自己在内心世界、诗意天地中创造的一个葆有童心的形象,林庚的超越在于他所创造的境界不属于孩子,而属于成人的开朗、豪放、快乐和天真。林庚的诗中有若即若离的人间味,有孩子般的喜悦,即林庚所称的“少年精神”。
牛汉则称自己年轻时狂傲激烈,不容易接受一些宁静美丽的诗,第一次认真读林庚的诗是在1960年前后,但对林庚的诗有较冷静的看法是近二十年的事。牛汉说,林庚从汉语传统、人文精神出发探索新诗,对外国诗的借鉴我认为没有。林庚的诗有音韵的诱惑,逼着你去念读、去研究。林庚的诗像流水似的,清新流畅,读起来很舒服;不像有人写的诗,一句里面就有三个句号,我不喜欢。林庚不写旧诗,但因为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的新诗有古典诗词的意境、韵味。同时,林庚的诗又有一种先锋精神,总在不懈地追求、默默地变化。
张玲霞专门收集了林庚1931年到1933年间在清华园发表的新诗,其中很多是后来很少被人提起,连林庚先生自己也说“记不得了”的诗。张玲霞拂去了岁月的尘埃,将它们晶莹润泽的光芒重新展现出来。她认为林庚先生在清华时期创作的诗是古典意象与现代精神的融合,他诗歌的意象大致上没有突破古典诗歌的框架,但传统的意象经过诗人的思想印照,被赋予了强烈的主观情绪和崭新的时代精神。林庚的诗歌大致不脱婉约一类,他独有的只是理性和风骨。总的来说林庚的诗情是忧郁的,但有青春和暖意荡漾其间,给人感觉不是忧伤,而是清纯和静穆,是美的流溢。
王晓生以林庚的三本自由诗集《夜》、《春野与窗》和《空间的驰想》为例,探讨了林庚诗歌穿行在现代与古典之间的特征与意义。王晓生认为,林庚的诗歌并不像废名在40年代所言“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因为林庚没有完全避免3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冲击,而是受到其影响的,表现在林庚诗中是:意象之间突兀与暧昧的关系、象征的多层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传达的深度暗示性与中国古典诗歌明显不同,具有现代主义美学色彩;但废名所言林庚的诗“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也启示我们林庚的诗继承了丰富的古典传统,突出表现在意境和禅意两个方面。王晓生认为林庚的诗充满了多维意境空间的追求,多以优美、娴静为意境旨归,且林庚诗中时见“无我”和“空”的禅意。林庚诗中古典与现代的张力体现了一部新诗史的丰富性,谈论林庚对21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林庚先生的新诗理论:典型诗行,独树一帜
林庚是新诗格律理论最勤勉的探索者,从3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末,林庚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新诗格律的建构问题。与会者围绕他所提出的“半逗律”、“新音组”、“典型诗行”、“九言诗”等新格律诗的范畴和形式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从各自的角度评价了林庚新诗格律理论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其在指导新诗创作方面的局限性。
谢冕将这种以九言为基本调式的诗体称为“林庚体”,认为林先生格律诗的主张积极地推动着新诗的建设,因为他一方面立足于现代汉语写作、立足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是对“五四”新诗传统的坚定维护;另一方面,他又得古典诗的神启获得了“林庚体”构想的资源,对新格律诗的坚定态度是针对早期新诗的“散漫无章”弊端的反驳。
王光明说,林庚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的诗歌形式理论是建立在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语言的基础上的。林庚先生认为,形式不是由内容决定的,而是由语言决定的。这一认识非同小可,能够澄清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而对林庚本人,也由于这一重要理论前提的自明,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第一,既然诗歌形式是由语言决定的,那么,汉语诗歌就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建构自己的诗歌形式,林庚追索了先秦以来语言与形式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诗必须根据变化了的语言考虑形式问题,同时认为面对更加逻辑化的现代汉语,必须依靠诗歌的力量使之得到解放和新生。第二,作为新诗形式的具体构建,林庚对关键的建行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发现了汉语诗歌以“半逗律”组织节奏的特点,并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实践与构想了新的建行方案。王光明认为林庚先生是对新诗内心经验形式化作过最深探索的学者之一。
龙清涛对林庚的新诗格律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析,认为林庚在进行新诗“节奏单元”和“诗行”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最能结合汉诗的传统,也最能体现汉语的特点。龙清涛细致地分析了林庚关于汉语诗歌“诗行的节奏是掌握在行的下半段”的理论,以“顿说”为参照,肯定了“半逗律”能较好地解决节奏中声音和意义的矛盾的优越之处;并认为,林庚以其理论洞察力把定型诗行从直觉认同的层面提升到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问题来论述,并建设性地为新诗提出了“建行”和“典型诗行”两个重要命题,这确实是林庚超出于旁人之上的对于新诗格律探索的杰出贡献。龙清涛同时也分析了林庚新诗格律理论一些不能自洽之处和局限性。
徐秀认为“典型诗行”、“半逗律”、“节奏音组”构成了林庚诗歌格律理论的支柱,是林庚对汉语诗歌建行规律相当富有创见的发现,林庚先生的新诗格律理论对规范新诗、繁荣创作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具体方案;但对于新诗格律建构而言,则过多地倾向于对旧体诗建行规律的继承,将诗句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半的“半逗律”、固定在行尾的“节奏音组”在旧体诗中是规律和基本因素,但在新诗行中只是偶然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新诗建行的依据;并且九言诗并不能容纳繁复多变的现代情绪,对于创作实践而言也会造成束缚。
西渡则侧重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对林庚的新诗格律理论提出了批评。西渡说,新诗形式一直是被关注然而未被解决的问题,林庚先生的新诗格律理论有一个成型的理论体系,我是在北大上学时接触到的,当时也曾想按照林庚先生提供的范式写诗,但并没有进行下去。林庚先生所建的新诗形式是由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形式引申出来的,符合民族欣赏习惯,但还不是普遍通行的形式。其一,由于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适合于古代汉语的声音模式能否在新诗中套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节奏对诗歌的声音起主要的控制作用,规定一种声音模式会限制对诗歌声音、节奏更为丰富的形式的探索。其二,在写作实践上,只要按半逗律去组织诗行,就会产生文言腔的问题,即使用大白话写,也仍然能从声音中听出旧诗的音响。其三,“半逗律”限制了诗句的标点和跨行,而跨行能给声音提供无穷的可能性,形成诗歌织锦般的整体感。其四,从现实中的新诗创作来看,格律诗从来不是主流,自由诗才是主流,自由诗为诗人传达自己独特的声音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每个诗人都可以通过它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声音、语调和节奏。西渡认为,新诗形式理论的探讨是必要的,但更需要实践。林庚先生希望新诗赶快成熟起来的迫切愿望感动着我,但这仅靠理论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近年在年轻诗人中可看出较有规律的诗体,就是臧棣在评论戈麦的时候所指认的无韵体诗,诗节整齐、节奏和谐、结构匀称。此外,北大年轻的一批诗人也较重视诗的形式,也在探讨。
郭小聪在发言中则认为,作为诗人和学者,林庚先生善于将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结合起来。特别是他对《楚辞》“兮”的研究,见出古典诗歌从“散文化”到“诗化”的历史性变化,并进而指出了现代新诗正面临着类似的历史进程。郭小聪还认为,九言诗应者寥寥,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九言诗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尝试存在着反差。林先生一个人的尝试使人们只看到一种风格,显得很单一;人们在偶尔尝试时,生疏之感也会使写出来的东西像是凑字数的文字游戏,这造成了人们对九言诗的半信半疑的态度,但一种诗体的成熟需要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不能因某种诗体尝试的现状而忽略了林庚先生理论眼光的长远性和深刻性。郭小聪还提出林庚先生以统计的方法总结上口的优秀诗行的规律,是很好的思路,但除了中国新诗外,还可以扩大统计范围,从优秀的外国汉译诗获得启示。
参加会议的诗人、诗评家还有杨匡汉、刘士杰、程光炜、王家新、钱志熙、陶东风、肖鹰、杨克、林莽、刘福春、陈旭光、马相武、徐伟锋、陆健、荒林、王家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