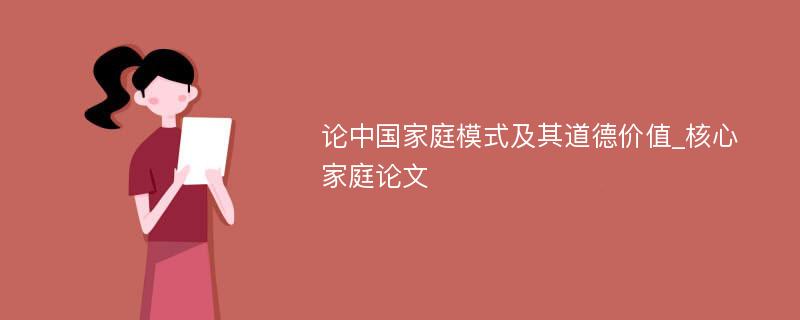
论中国家庭模式及其道德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德论文,模式论文,价值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不同意“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看法,认为其典型结构模式是三世同堂,它以分而不离的形式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一般模式。双向扶养功能是中国家庭模式的独特优势,它密切了家庭关系,减轻了社会负担,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造成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道德风尚。随着中国以及全世界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家庭模式将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老年人问题的极为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家庭模式 三世同堂 双向扶养 道德价值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传统家庭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出现了所谓“家庭危机”,造成西方传统家庭的动荡与解体。不少学者提出要以东方药治西方病,中国模式的家庭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什么是中国模式?其道德价值如何?这并非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中国传统家庭究竟是什么模式,由于史料缺乏现已难作确切的回答。几千年来,宗法道德和传统家庭观念深植于人们头脑之中,古人特别重视家庭继宗室、睦亲友的功能,强调多子多福、孝慈友悌。兄弟不分家,三世乃至更多世代的同堂共居,被视为幸福和睦的理想家庭。政府对此类家庭予以各种形式的表彰,文人墨客着意渲染,史不绝书。于是在外人眼中甚至在国人的观念中,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便成了“大家庭”,即由几个世代兄弟的数对夫妻所组成的联合大家庭。这实际上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史籍中大量的户与口的统计资料、推测出传统家庭的规模与结构。下面是从正史中撷取的几个主要统计数字:年代
公元
户数
口数
户均人口西汉平常元始二年
2年
12233026
59594978
4.87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年
2459840
16162865
6.57隋炀帝大业二年
606年
8907536
46019956
5.17唐玄宗天宝十三年
754年
9069154
52880488
5.83宗徽宗崇宁元年
1102年
20264307
45324154
2.23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
13430322
59848976
4.46明成祖永乐十年
1412年
10992436
65377633
5.95清红宗嘉庆七年
1812年
49589715
264278228
5.33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西汉以来史籍中较为可信的户口统计数共71个,家庭人口平均值为4.95人。秦汉以前,中国还很少有后世的大家庭,孟子说的“八口之家”只是他的理想。秦用商鞅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①。强令民人分家,不许组成大家庭。汉承秦制,其规模亦不大。“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②从上面的统计材料可见,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传统家庭规模无实质性变化,民国时期,家庭规模与古代相差不远。据官方统计,家庭户均人口1911年为5.17人,1912年为5.31人,1928年为5.27人,1933年为5.29人,1947年为5.35人。这些数据与该时期学者们的调查大致相符。建国以来,中国户均人口从未超过5人。1979年最高,为4.81人。1990年最低,为3.96人。6人以下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90%以上,在城市中已超过95%。
已有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家庭规模绝大部分在6人以下。在此规模中,要成立联合的大家庭是很困难的。古人初婚年龄小,生育子女多,以最保守的计算,一家三代,第一代2人,有2个儿子均已婚未分家,即第二代4人假设,第三代2人,则全家共有8人。易言之,在一般情况下,至少须8人才构成联合大家庭,而资料证明,8人以上家庭在古代只是极少数。
为什么家庭的实际状况与人们的观念不一致?这须得从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原因。首先,以家庭能够承受人口多少的经济能力而言,绝大部分家庭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孟子设计的井口制,每家耕作百亩,租税徭役不在其内,才能使八口之家无饥。在古代能够拥有百亩土地的家庭并不多,大部分家庭很少甚至没有土地。客观经济规律必然调节、控制着家庭的规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次,古人虽不控制生育,但由于生活、保健条件差,预期寿命很短,加上战争、灾荒、瘟疫的影响,很多人难以自然终老,而生命力弱的一般是老人和儿童。儿童的死亡减缓着家庭人口的自然增长,老人的死亡不仅是家庭人口的自然减少,而且直接导致它的社会性衰减——分家。再次,家庭人口多尤其夫妻关系多,相互间的矛盾也越多。一个家庭中夫妻对数愈多便愈不稳定。
因此,理想只是一种向往,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在上述经济能力、寿命期限和利益冲突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联合的大家庭必然不断瓦解,不可能成为传统家庭主要的普遍模式。上述家庭规模表明,中国模式的家庭大部分具有父母子女三级结构,这一结构仍是当代中国家庭的普遍模式,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家庭的瓦解并未在中国出现,据调查统计,一对夫妻和其子女及其他亲属同居的家庭占全部家庭总数的90.85%,残缺家庭只是极少数。③而西方家庭危机现象则十分严重。1966年,美国户均人口尚有4.2人,与中国大致相当。到1989年,其户均人口降至2.6人,表明当前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不是由夫妻子女三级组成。这种结构反映了家庭的不稳定。现在,美国已有近1/4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模式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
联合的大家庭虽不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典型模式,但却是它的理想模式;虽不是普遍形式,却也是实际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受到社会的褒奖和人们的向往。古代张公艺九世同居,隋朝、唐朝的统治者均旌表其门,号称义门之最。象这种名副其实的“大家”,史书上还有记载。实际上,此类大家并没有道德家歌颂的那样美好。严格说来,它已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甚至也不是古代意义的家庭,而是家族,至少家与族不分了,其存在不能当作传统家庭的典型模式。
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是三世同堂。它既非现代的核心家庭,也不是主干或联合家庭,而是后二种家庭的混合形式。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划分方法,它注重夫妻对数,与注重代数的中国传统家庭并不相合,对数标准着重强调个人利益,代数标准则把家庭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这是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重要区别。
传统家庭模式的结构依据如下原则:以家中最年长的人为起点,其所有男性后代及其配偶、未出嫁的女性后代必须在一个家庭中生活,父祖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是三世同堂家庭的法律和伦理保证。活着的最高男性尊长是家庭的核心和最高权威,这个家庭是他的家庭。这种模式把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连接为一个整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高度的稳定性,强化了代际感情和认同。然而,由于它实行父家长制,所有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其权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以家长为代表的家庭的整体利益,所以,又造成家庭的不平等和否定个性存在。
古代社会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家庭的稳定。按礼法,子妇不许有个人财产,不能私自积蓄,家庭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家长手中,分家便意味着财产的减少和权利的缩小,故他一般不容许分家。他的这种权利得到法律的支持,唐以后历代法律都把父母在子女别籍异财视不孝之罪。于是,已婚的男性子嗣仍旧生活在父祖的家中,如果他们企图分家,将受到舆论和法律的强制干涉,从而出现了普遍的三世同堂的现象。
三世同堂与家庭自然经济密切相关,维系着家庭生产的稳定与发展。随着家庭自然经济的瓦解,旧的行为规范已失去约束力,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个人利益的觉醒,人们更多地注重个人生活,从而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在本世纪30年代,三世同堂的家庭还占全部家庭总数的40%以上,而现代则主要是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据一些学者80年代初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报告,核心家庭已达66.41%,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只占24.79%和2.30%④。可见,二代人的家庭已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而三代同堂的家庭虽不再是主要形式,但仍是其重要的形式,在农村,它所占的比例肯定还要大得多。
建国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卫生保健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平均寿命延长,世系中的三个世代的关系无疑比建国前和古代有很大增加,但家庭中的世代结构和人口规模反而减少,反映了中国现代家庭小型化的趋势。这种变化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生产不利于家庭的内部分割,加上在传统父家长制的管理下,家长不同意分家,子女不敢也很难独立,三世同堂必然是普遍模式。现代社会中,家庭已由生产单位变成了主要是生活的单位,家庭中的成年成员在经济上具有平等地位,特别是在城市还有各自的独立收入,从而产生了古代不可比拟的独立的能力与愿望,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二代人的家庭便取代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而成为现代家庭的主要模式。
但是,现代中国人并未抛弃传统。在许多人的观念中,父母仍是家庭的主要成员,而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凡有子女的老人,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是和自己的某一个或几个子女生活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尊老爱幼是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老年人希望也需要获得子女的关心与照顾,子女也需要退出生产领域的父母帮助料理家务和照看自己的孩子,在经济上和生活上仍然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关系。故三世同堂仍然是现代中国家庭的重要模式。然而,现代三世同堂的家庭与传统家庭相比有质的变化,即子女在家庭中有了独立的地位,父母越来越不干涉子女的家庭生活,且不再单以男性子嗣维系其结构。实际上是两个家庭的共存,而不是父母家庭的存在形式。笔者把这种新的模式称之为“分而不离”的三世同堂,它不仅包括三世实际同居的家庭,还包括虽然分居,但仍有广泛经济、生活联系的不同代际家庭在内。现代中国家庭的小型化、二世化并没有割断与上一代父母的联系,这是中国核心家庭与西方核心家庭的典型区别。中国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家庭模式不但仍实际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且以分而不离的形式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新的形式正在家庭变革的过程中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
家庭本质上是以男女婚姻结成的社会人的存在形式,是夫妻共同社会人格的表现。因而,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最能反映家庭的本质。一对夫妻便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子女在未成家以前包括在父母家庭中,处于社会人的孕育时期,一旦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便应脱胎而出。但是,脱胎只是独立,而不是割断与母体的联系。西方模式忽略了这种联系,造成代际感情淡薄和晚景凄凉。下面两组数据反映了中西模式的差异。据上海市两次不同的调查,老年人(60岁以上者)与已婚子女和未婚子女同居的比例分别为:57.93%和27.59%;上海市老人生活抽样调查为54.31%和23.45%,绝大部分老人与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⑤上海是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其他城镇的比例更高。在广大农村,只有极少数老人(大部分是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没有和其子女生活在一起。可在当代英国,老人与已婚女儿同住的只有4%左右,与已婚儿子同住的仅0.7%。⑥,西方绝大部分老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这种状况表明,西方现代家庭模式强调个人的独立利益,使每个家庭成为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封闭单元,形成一种自发的自我隔离(self-initiated isolation)机制,从而忽略代际的联系,把老人排斥在家庭之外。西方社会学家指出:“个体化核心家庭权利的扩大,是老年人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⑦许多老年人处于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照顾与保护。“因此老人无意之中成为犯罪的牺牲品,他们遭抢劫、殴打、强奸,乃至被凶杀。……很明显,当社区和家庭都遗弃了这些老人时,这些灾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⑧
而中国传统的三世同堂及由此演变出来的分而不离的模式,使老年人生活在子女的家庭之中,或在家庭生活上受到子女的直接照顾。中国家庭的衍生是连续的,西方家庭的衍生则属于断裂型。家庭的连续沟通着代际亲情,使人终生领略天伦之乐,有助于家庭的和睦、巩固,并引申出良好的社会道德关系,尊老爱幼。而家庭的断裂则反映代际关系的疏远,使老人处于被遗弃境地,正是由于中国模式的这一优势,西方把老年人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家庭的发展。
三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以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要形式,但是,它与西方“核心家庭私有化”不同,而是以分而不离的形式对传统三世同堂家庭模式的改造与发展。这种模式与传统家庭模式相比,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
首先,家庭的核心由第一代转移到第二代(一个家庭有三代人),它不再是第一代人的家庭,而是第二代人的家庭。这一变化标志着父家长制的瓦解,二代人有了较多的平等和独立。家庭至上的观念让位给个人的独立自主,有利于个性的自由发展。
其次,依男性世系构建家庭转变为男女世系均可构建家庭,标志着家庭宗法性质的消亡。古代家庭的一个重要职能即传宗接代,故家庭以男性子嗣的繁衍来维系。而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在古代女子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只有男子才能承担养老抚幼的责任。现代男女经济上获得了平等,都有能力与义务承担上述责任,传宗接代已失去了实际的社会意义。
再次,家庭关系中心发生偏移。传统家庭关系的核心是父子,家庭的统系和事业父子相承,各种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依次为父子、兄弟、夫妻。血缘重于姻缘,没有父子关系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被称之为“绝户”。现代家庭关系的中心是夫妻。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基础,有了夫妻关系才派生出其他家庭关系。因此,这种偏移是对家庭本质的回归,标志着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
中国家庭模式最值得肯定的道德价值就是它继承了传统家庭双向扶养的传统,浓化了代际亲情,促进了家庭的和睦、巩固与发展。
人类生命有两个阶段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他人的扶养和照顾:即儿童期和老年期。在古代社会、在自然经济体系之中,社会无力为儿童和老人提供必需要的福利,故无论中外,绝大部分社会的家庭都采取双向扶养模式。那时,“三个世代的人幸福地生活于同一个家庭,曾经是家庭关系的黄金时代。……这一黄金时代的消失导致了现代的萧条和家庭的破裂。”⑨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传统家庭日趋瓦解,便逐渐采取了只抚育后代,不赡养老人的单向扶养模式。
现代西方家庭的扶养模式把对老年人赡养的责任移交给社会,它的长处在于减轻了中年人的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建设自己的生活。同时,子女一旦能够自立,就基本上脱离了与父母的联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具有较多的个性自由。然而,它的弊病也同样明显。首先,它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淡薄。过于强调独立,必然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用此原则处理家庭关系,感情因素便退居次要位置,父母兄弟子女关系异化为利益关系。其次,它造成人的晚年的孤独与寂寞。人的晚境凄凉,正是这种扶养模式的最大弊病。美国社会学家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强调家庭(按,此处家庭指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引者)内部感情和亲密的中产阶级的私有化,阻止了扩大亲属,包括老年父母的参与。现代家庭同时也从社区事务中抽身出来,这样更加强化了家庭和社区内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隔离,并且把老年人排除在可行的家庭角色之外。”⑩在以个人利益和竞争为最高原则的西方社会,老年人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也受到极大冲击。但是,工业化的魔力并未在中国唤出以利己主义为最高原则的家庭模式作为一般范型。大多数家庭继承发展了古代家庭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父慈子孝,采取了双向扶养的模式。这种扶养模式与西方模式相比有其不足,它使家庭成员之间过多的相互依赖,独立意识不强烈。它把三代人联系在一起,使家庭关系变得较为复杂,如中国传统婆媳矛盾仍然是导致家庭冲突的重要因素。另外,双向扶养加重了中年人物质和精神的负担,束缚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建设自己的生活。但是,与西方模式相比,它的优势更加明显。第一,它密切了家庭关系。经济上生活上的联系与依赖,促进了代际间的相互关心,加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第二,减轻了社会的负担。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将越来越多,赡养这批老人是社会的沉重负担,当家庭与社会分担这一重任时,将有利于社会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发展生产。第三,家庭赡养有着社会赡养所缺乏的优点,它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心、和睦的生活环境,享受独特的天伦之乐,丰富和充实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第四,它造成了尊重老人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老年人曾经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有深厚的人生阅历,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它们对于下一代的工作和生活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在谈到西方家庭扶养模式的转变时说:“以前,子女有义务赡养他们年老的父母。自从19世纪核心家庭私有化和独立的新观念出现以后,这种义务就丧失了其重要性。结果使政府日益忙于为老年人提供财政资助和保健的便利条件。不幸的是,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尚不能满足退休老人的要求。此外,政府建立的福利计划无法证明自己有能力与前工业时期老年人从由他们子女和其他亲属所构成的亲属网络中获得的义务感、满足感相抗衡。”(11)所谓“核心家庭私有化”,指一个家庭以夫妻为核心,只容纳未成年子女,形成独立、封闭的结构。西方家庭的这种模式,突出强调了家庭作为社会人形式的独立性私有观念,与这个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相适应,而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成了“最不幸的牺牲品”。就一般情形而言,西方家庭扶养模式的单向性,并未使老年人断绝生活来源,只是赡养老人的责任由家庭移交给社会。退休金制度及其他福利保健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的需要。然而,强烈的竞争把老人抛离于社会,严重的利己主义又使老人与子女隔绝开来。弗·斯卡皮蒂说:“在美国,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他们孤立于家庭和社区以外的情形也相应地增多。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不是被当作社会上起作用的成员,而是当作包袱对待。为他们提供的必需品与病人和精神错乱者一样,他们的生活依靠社会福利机构而不是家庭。”这种双重的失落使得“老人可能陷入孤独与绝望,没有家庭快乐,也没有令人愉快的环境。”(12)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老年人问题将是我国今后可能要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据有关统计和预测,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2.8亿,占当时人口的20%,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65个百分点,如果采取西方的扶养模式,将会成为社会不堪承受的负担,出现西方社会早已出现并力图消除的种种弊病。
中国有几千年尊敬老人的传统,我们不能重蹈西方人的覆辙。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双向扶养功能的继承与发展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重要途径。当然,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赡养老年人的责任也不能完全沿袭传统,让家庭独自承担。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水平正在迅速提高,社会已经分担了一部分老年人的赡养,形成社会与家庭共同赡养并以家庭赡养为主的形式。在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赡养模式将发生由以物质赡养为主、精神赡养为辅转向以精神赡养为主、物质赡养为辅,由以家庭赡养为主、社会赡养为辅转向家庭赡养和社会赡养并重的变化。精神赡养的主要内容是在家庭中给老人以更多的关心和温暖,为其晚年创造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环境。子女尊重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让他们参预家庭事务,同时留给他们足够的文化娱乐时空。孔子以“敬”释孝,认为犬马皆能有养,惟敬方别于禽兽。今天,我们继承改造孝道,更要灌注一个“敬”字,并把它化为高度的尊重、主动的关心和细心的照料。老年人往往把自己的家庭和子女看作是一生中的重要成就,是一生的理想和感情的寄托。如果晚年能得到子女的关心和照料,这对他们的精神是极大的安慰,也是感情上的极大满足。家庭赡养的这一特性,社会赡养永远也取代不了。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即具有上述优良传统,我们应当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传统,使老人们在中国现代及未来的家庭中生活得更加幸福,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注释: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
③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公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一对夫妻也没有的家庭(包括单身户,与总户数之比为127291:2483831,只占5.56%。
④参见《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刘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⑥参见杨遂全:《现代家庭的源与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⑦⑧⑩(11)[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320页、319页、318-319页。
⑨[美]Arlene S.Skolnick,JeromeH.Skolnick,Family in Transiti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86,P41.
(12)[美]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刘泰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20-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