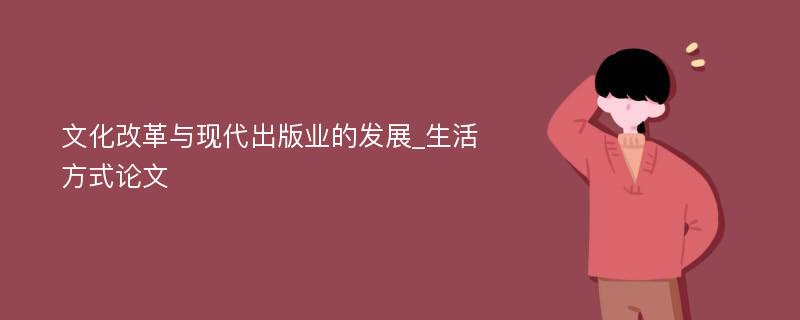
文化变革与现代出版产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产业是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供应为主体的产业,它本身就是文化性和经济性的统一。出版物是记录、传播、积累、发展人类文化知识的载体,形象地说是文明人类自身的阶梯,归根结底是建筑人类文明大厦的脚手架。一方面进入工艺—社会结构,推动物质文明前进,另一方面进入文化—心理结构,丰富精神文明的积淀。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文化的模式和结构也产生重大的调整和变革。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对宇宙、地球、生命、时间、空间乃至人类社会及人类文化的理解,人类自身也不得不调整乃至改变自身生存的、曾引以自豪的文化结构。知识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性质。这也是“第三世界”即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全部知识在内的称谓,在上世纪经波普尔提出后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缘由所在。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已发生了冰河的时代末期、河谷文明时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三次大的文化变革。目前,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正发生着一场新的文化变革。这场文化变革以现代科技革命为依托,以信息革命为核心,把人类从20世纪的机器工业化时代带入21世纪的知识信息时代。这次文化变革在文化观念上的表现是:西方人开始着手对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展开批评,如萨特用生来自由,哈贝马斯用交往合理,批判学派以家庭、劳动性等方面的变革来抵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种种异化;而对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保存完整并还继续发挥活力的中华文化,如汤因比乐观预言的那样,是21世纪人类的希望。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我们自己谨慎扬起的“民族复兴”风帆。在实践层面上,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冷战格局的结束,人类的交往真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全球化是指现代人类的生产、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不断超越国界而面向全球发展的趋势。除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形式外,文化交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而现代出版产业适逢今日文化交往对流盛世,必然会通过自身的出版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现代出版物为当今人类文化的大交流、大传播、大融合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活力。人类的出版活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具有国际性和全人类意义。
一、生活方式的变革引起现代出版文化的全面革新
生活方式作为人类文化总体结构的一个最基础的层面对出版文化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与远古文明相对应的原始生活方式向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传统生活方式转变时,记载原始人生活方式的巫术、神话、图腾以及种种具有原始意象性符号的原始形态的“出版”活动,便让位于记录传统生活方式的具有某种约定的风俗、习惯、常识、经验、戒律、规则以及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纽带、自发地进行个体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日常生活内容。当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传统生活方式向以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时候,现代出版形态便抛弃了那封闭的、慢节奏的出版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快节奏、大规模的出版生产方式。
从哲学的层面讲,现代生活方式在20世纪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人类对自身生活的世界不间断地进行审视和反思。一方面,人们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日常生活世界(以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行交往为主要内涵)和非日常生活世界(以专门性的学科建设如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为内涵)的统一。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出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充满竞争和创造机遇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另一方面,理性和人文精神重新纳入现代生活的序列中,人们不再囿于传统的经验、常识及习俗,而是以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参与到改变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单调性上,从而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协调起来、共同发展的理想模式。它的基本精神是:同日常生活分离已久的科学、艺术、哲学、文学等精神生产应“重归故里”,向日常生活领域渗透,为人们提供自由创造和竞争的空间;而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应该为一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创造相适应的条件,为人类提供安全的家园。但西方已走出“现代”的那些发达国家,则告别“短暂、飞逝、偶然”而走向“后现代”,而中国正大步迈向“现代化”。因此,这“回归”的内容和形式便是很不相同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二者有一种互补张力。
从现实层面上看,由于科技革命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封闭性、单一性走向现代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在劳动生活方式上,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原来繁重的体力劳动已不复存在,劳动者由从追求单纯的实惠的物质生活的充裕转向了追求带有浓郁文化色彩、充满丰富精神特质的新的劳动工艺及新的生活价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由于高科技的加盟,越来越多的家庭走进了“电子化”的生活方式,家用电子计算机及联网系统使得家庭的文化氛围出现了现代化的特征;在日常交往方式上,由于现代通讯条件的改善,人类的交往方式正由劳动型交往方式向知识型交往方式转变,信息交往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人们交往所要处理的信息,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个体生活方式上,由于受市场经济法则的制约,“个人性”愈来愈突出,传统的“群体”概念正在被“全球”概念所取代。
二、新的教育模式给现代出版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教育和出版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教育是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出版是通过不同的复制手段将各种形式的出版物提供给读者进行阅读的一系列活动。出版物是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它为教育提供必需的资料与信息。受教育的人多了,教育发达了,对出版物的需求量就大了,对出版业的要求也就更高了,如不仅是抽象的符号—文字,而且是生动的图像、画页,不仅是视觉的延伸,而且是听觉的扩大(电视教育),从而促进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发展了,会为教育的普及提供“物质形式”的保障,从而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及生理—心灵—精神都得到更大的提高和培育。这种天然的联系形成了二者之间互生互动的关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出版业的繁荣和发达总是带动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教育的内部要求使然。而每当教育模式向前推进和更新时,出版业较之以往则会更加繁荣和发达。而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出版业的持续繁荣。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在《现代出版学》中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球“出版爆炸”现象时说,“出版爆炸”是和“教育爆炸”现象同时出现的,并且“直接影响出版的量和质的,只能是教育”。他还引用了美国学者R.E.沃尔斯利的《理解杂志》一书中有关美国出版业和教育有关的数据,结果表明,二战后美国杂志出版总数的增长率与中、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人数的增长率基本上是一致的。1940年美国国民的平均就学年数只有8.4年,而到1956年,就学年数延长为11.2年;而美国1956年杂志的出版总数也增加了2.2倍。这些资料说明了日、美两国二战后由于教育的广泛普及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出版业呈现出繁荣的态势。
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在一个由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教育模式演变的时期。传统教育模式从总体上是和农业文明及机器时代(前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它具有教育地点的集中性、教育标准的统一性、教育空间的封闭性、教育时间的阶段性、教育形式的单一性、教育内容的滞后性、教育手段的传授性等特点,许多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说是缺点。因此,也越来越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在当今世界,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知识经济)的主要动力,并逐渐成为人们新的消费基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教育必须走出传统教育模式,而勇敢地面向21世纪的“大教育”模式。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总量正在迅猛增加。现代科技知识不仅呈指数规律增长,而且科技知识的物化期即从发明、发现到应用的时间段也在迅速缩短,科技知识的更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如本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发明和创造,就比以往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据国外学者估计,全世界一年新出现的“知识流”(指新名词、新术语等)约有70亿到80亿个;而学校教育提供给一个专门人才的知识却只占他一生所用知识总量的20%。20世纪50年代,激光从发现到应用的时间是两个月;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更新的时间是5至10年。这些数据表明,传统的教育模式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一种“启蒙式”教育,已不适应今天科技快速发展的需要。从“大教育”的模式出发,传统的封闭的学校教育理应转变为开放的社会教育,单一的阶段性教育理应转变为终身教育。在当今乃至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活到老,学到老”将成为人们极为现实的生存原则。这种“大教育”模式的建立将直接影响到出版观念的更新。
第二,由于知识和信息带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人们对自身提出了重新学习的要求。当代经济产业结构的基本趋势是第三产业比重在迅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第三产业。据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统计,1950年美国只有17%的人从事信息工作,目前则已超过60%。劳动者从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自身提出了重新学习的要求,或是为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或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势必打破学校教育的狭隘圈子,而不断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第三,由于高新科技及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出现了“智能化”的趋向。这就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为其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了时间保障。同时,城乡差别也在进一步缩小,教育的层面在不断扩大。出版产业及现代出版人的出版活动理应顺从教育深入发展的每一动向,不断对其加以研究和分析,以确定出版的思路和方向。
上述三个方面即科技发展,“三产”繁荣、“智能”趋向对教育的挑战及对印刷出版业的呼唤已经开始。对发达国家似乎不成问题,但对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则是难题。但教育必须面向未来,出版也不能按兵不动。可能的答案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1.承认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研究差距的具体情况;2.提出初步改革措施,研究具体途径方法,制订可行性方案;3.协调出版与教育,沟通交换意见,达成共识,然后付诸实施,分工合作,齐头并进。
三、价值观念的更新对出版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价值观念是对总体的人而言的。它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功利观、审美观等等涉及到价值判断的综合体。其本质在于是否能满足人的求真、向善、爱美的价值需求,达到“自由向全面的发展”。出版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活动,它直接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是需要,当人们的价值观念决定需要某一类出版物时,出版活动就会满足这一需要。同时,出版所具有的前瞻性、能动性也是出版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何把握价值观念与出版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积极因素成为关键。这就是说,它肩负着选择、传递、保存人类优秀文化的功能,如果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占上风时,人类的出版观也会产生自觉的抵制作用,从而使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出现新的面目。
从史学的角度讲,因社会变革而导致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对人类出版活动的影响是主要的。如果说原始人的价值观还处于开化时代的低级状态,那么“开始于铁器的制造,终止于音标字母的发明及用文字于文学作品的写作”(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卷),这一时期则是开化时代的高级形态。铁器的使用使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成了传统的重血缘、人伦关系及人的地位的新的价值体系。如西方古希腊时代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价值观、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崭新的人学观以及东方中国商周以降就萌芽的以重血亲,重仁爱,重天时、地利、人和为主体的价值观等。这些价值观对人类出版活动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但这种“根本性”是历史而具体的从而是相对的。夸大了这种相对性便走向“自我中心”论,如中国的“华夏本位”、西方的“欧洲中心”等。
但随着历史逐步打破民族界限,这个“中心”就保不住了,而要吸取别的文明的长处发展自己。如佛教从汉朝就传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古代出版活动中就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典籍;直至唐玄奘印度取经,更是人类史上空前的文化交流盛事,这一盛事以出版形式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载。
人类文明进入机器时代时,人类近代价值观才开始形成。人类可以用机器来延伸自己的肢体,借助机器来完成自身体力所达不到的某些劳作。这时,人对自然的认识更加深刻,于是就产生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面向现实、积极投入、提倡创造、鼓励自我实现的新的价值观。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时期人类价值观念的总体走向。人类的出版活动在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一扫传统价值观的那种闭塞性、滞后性,使这一时期的出版物无论是文学如但丁的《神曲》、哲学如培根的《新工具》,还是科学与自然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都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冲破“神”的藩篱,打碎封建枷锁,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征服自然,证实自己的存在,这一价值观在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上留下了众多可资凭依的记录,成为人类启蒙时代宝贵的文化遗产。
越过近代,就迈入了现当代人的历史。但是近代竭泽而渔的“透支”活动,带来了震惊人类的“生态失衡”,由是引发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的强力呼吁。“人类中心论”于是悄然兴起,也成为出版业的热点,大批的科学考察、文学诉说、伦理斥责及审美重估兴盛一时。更由于现代化在全球发展的极端的不平衡,从而使现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各种观念、思潮此起彼伏。于是,新旧价值观的碰撞更加剧烈。这在出版业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尤其是文学上“现代派”的崛起,可谓“一叶知秋”。现代艺术,包括兴盛一时的“立体主义”、“抽象派”的现代艺术主流作品,以看不出具体意义的丑陋的、扭曲的、骚乱的形象情景的场面引起复杂的心理感受。由“美”走向“丑”。至于“黑色幽默,《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多有介绍,不再多谈,因为太荒诞,离奇。但是,由于自我调节机制的牵制和校正,从内而起的反对力量则从理论上的“智商第一”走向“情商为首”,例如《廊桥遗梦》、《雨中人》等走向了田园牧歌、世俗人情。
面向未来的当代价值观给现代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如上所述,这良机不仅在于物质发达、信息快速、交流频繁,而且在于价值观中的对流与对抗、互补中的个性差异。竞争里的各领千秋,会衍化为出版物的百舸争流、气象万千、各展风采、蔚为大观的风云际会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