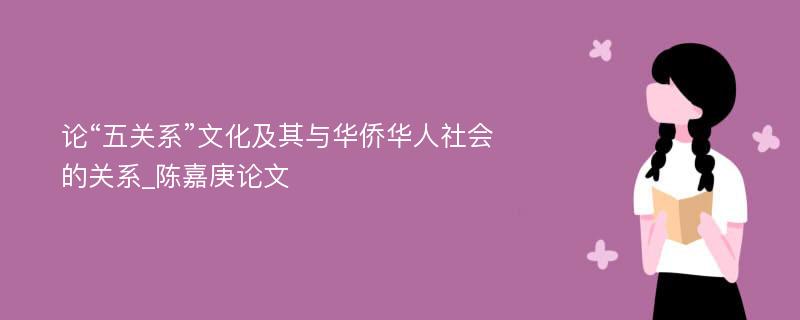
试论“五缘”文化及其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侨论文,试论论文,海外论文,华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苏东水教授在“关于发展泉(州)台(湾)经济关系的设想”一文中,曾提出过六缘(地缘、血缘、人缘、文缘、商缘、神缘)文化理论,在泉州市的学术界中,曾就此举行过四次研讨会[1]。自1990年春,由林其锬教授提出的“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文化论[2]。最近李定国研究员又发表“关于开展‘五缘’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思考”一文,提出许多颇有启发的理论[3],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对活跃社科领域特别是边缘学科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笔者拟就“五缘”文化及其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 关于“五缘”文化理论的想法
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是个复杂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报导,世界上学者们对文化的定义,有二百六十种的不同说法[4],截至目前为止,国际上学者们对此仍众说纷纭,无公认的定义。就目前我国而言,关于文化的定义,比较通行的说法,“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5]。”关于“五缘”文化,笔者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以群体文化为特征,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文化史领域一个综合性概念。就辞类而言,它是一个集合性名词。
文化是人类社会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五缘”文化,来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影响人类社会生活。就文化形态而言,“五缘”文化是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群体文化。从总体上观察,人类社会历史上进行群体的结合有多种的方式,笔者认为其中以血缘、地缘、神缘(宗教信仰)、业缘四种方式结合,为最主要的方式。这四缘群体的结合,其产生有先有后,并非人类社会同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的属性各有其内涵互相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别,欲对其进行界定下一个定义,确实比较困难。血缘即是家族、宗教亲戚间的血统关系,地缘则是乡里邻党地域关系,神缘即是宗教信仰或民间信仰,业缘则是同业结合如行会、同业公会、商会等。
血缘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最自然的结合方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血缘纽带都普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的血缘意识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旧石器晚期的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君览》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与生母的血统关系。进入父系氏族时代,由对偶婚建立的对偶家庭,使父亲已确知自己的子女,从此人类血统世系开始按父系计算,财产也按父系继承。神缘意识起源于原始宗教,萌芽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万物有灵观念,它本是原始人在和自然斗争时软弱无力,把自然力和自然物加以神化的结果。随后又经历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了阶级社会便出现地区性和全国性崇拜的神,进而出现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如三大宗教等),统治阶级便利用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地缘意识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的出现。那些个体家庭的人们,为了相同经济利益需要,居住在同一个地域里,形成以地域为联系纽带的统一体--村落。到了阶级社会,地域单位便扩大为乡、镇、县、州(郡)、省等建制单位,县、州、郡地域单位往往又与共同方言连结在一起,增添了一层亲切感。同一地域出生的人们便互称为同乡,形成地缘观念。至于业缘组织的出现则比前三缘为迟,它产生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但在奴隶制社会手工业劳动者属于奴隶范畴,没有人格自由,不允许成立自身组织。因此,业缘组织它产生于中古封建社会。在中国,学者们主张产生于唐宋时期[6]。唐代城市中同业的店铺有“行”的组织。北宋时期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也有称为“作”,例如制鞋业的称为“双线行”,木制品业的称为“木作”。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一书中,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一书,对当时都城杭州的行会组织皆有祥载[7]。欧洲的行会出现比中国稍晚一些。在意大利出现于10世纪[8],并于10至12世纪相继出现于法国、英国和德国[9]。历史上手工业行会是小商品生产者的团体,是为了与封建主斗争和防止竞争需要而成立的,但其内部的严格等级制和剥削关系,所以当时它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组织[10]。至于物缘,按林其锬教授的解释,主要指出土、特、名、优产品为媒介从事联络的人际关系。它的出现当然只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人阶层出现)之后的阶级社会。以上事实雄辩证明,“五缘”文化就世界全局而言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所独有,尤其是民族血缘寻根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它根植于人类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物质生产、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而且表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特征。例如,就亲缘文化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深受宗法制度的羁绊,而在古代希腊、罗马国家就与中国迥然不同;神缘文化方面除世界三大宗教外,各国地区性的宗教仰和民间信仰更是异彩纷呈;物缘文化方面,例如中国山东维坊的“风筝”文化,与荷兰人的“风车”文化,何尝不是迥异其趣,各国饮食文化的差异更是尽人皆知的。
无论是地缘、神缘、业缘群体,它们都是基于共同的心理需要而自发结合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聚合力。血缘群体则是基于血统传承关系本能自发地结合的,不仅凝聚力强而且笼罩着更亲密一层的血浓于水天然的亲情关系。加之血缘(亲缘)群体--家族、宗族以及地缘群体的村、乡、县、州(郡)省等地域性组织,又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基本社会结构坚韧牢固地连结在一起,因而使中国人的亲缘、地缘意识这条联系纽带特别根深蒂固。
在中国,自春秋战国和汉代以后,历代思想家们对社会上业已形成的亲缘、地缘等社会群体以及人伦之间关系,不遗余力地注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例如,儒家大师们在家庭、宗教、宗亲关系方面,竭力倡导“仁爱”[11]、“孝悌”[12]和“仁、义、礼、智、信”[13]。在人际之间关系方面,提倡“人和为贵[14]”、“与人为善[15]”、“诚信守约[16]”、“以德报德[17]”,以及“见利思义”、“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等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力求使社会上人与人这间维持和谐的关系。尽管这些道德信条,在当时剥削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对后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则是及其深远的,成为公认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清初以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大量移民的悌航海外谋生,不仅把国内宗亲、宗族、同乡、同业群体组织,以及宗教和民间信仰及其庙宇,传播到海外居住国,而且把国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处理人际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也远播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但因“世异则事异”,海外这些群体组织已不具封建的性质,其功能旨在团结互助和联谊自治。
二 “五缘”文化与早期海外华侨社会
1.地缘、亲缘、神缘认同,促进早期华侨聚落和社区的形成。
早期华侨,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移居南洋及世界各地谋生。到达目的地后,面对人地两生的复杂环境,寄人篱下,受人支配,尝尽人间辛酸苦辣。既得不到祖籍国政府的保护,更无法获得侨居地政府的支持。他们深切感到,为图生存须和衷共济,求发展须团结互助。基于此,他们便以相同的出生地或共同方言以及姓氏等为联系纽带,进行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自发地建立起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再往后便创立同业公会和商会等。例如,1819年在新加坡开埠不久,广东台山县籍华侨曹亚志,便创建曹氏宗亲会馆,称为曹家馆。1848年又成立广东四邑陈氏会馆[18]。根据吴华先生统计,新加坡共成立102个华侨姓氏宗亲团体。在地缘团体方面,新加坡华侨移民先后建有以省、州、县、乡为单位的各类同乡会馆。其中以广东宁阳会馆创立于1822年为最早,接着应和会馆(1823年)、1845年义安公司(潮洲八邑会馆前身),琼州会馆(1857年)、福建会馆(1860年)等相继建立。截至1974年,新加坡共建有地缘同乡会馆133个[19]。在日本,移居长崎的早期华侨,则以佛教信仰认同为纽带,以地缘乡帮为单位,先后于1623、1628、1629、1678年建立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作为团结、联谊、自治的群体,成为同乡会馆的雏型[20]。宗亲会馆和地缘会馆,以团结互助、联络感情为宗旨,对安置和收容初来乍到的同乡同宗,提供住宿,介绍职业,资助贫病,购置墓地,调解内部纠纷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初来刚到的同乡、同宗侨胞,得以在异国他乡平安落脚、获得生存,使“散者聚,疏者亲”[21],凝聚成群体,从而有力地促早期华侨众多聚落点和社区的形成。
2.由乡情、亲情和神缘等联系纽带,进而形成华侨群体(同乡、宗亲会馆、庙宇)关系网络。使刚移居异国他乡的华侨“新客”,由个体结为群体,由举目无亲,变成同乡同宗视已为亲。获得同乡、同宗会馆协助安排食宿,推荐工作,为他们提供最初的生存和谋生条件。有助于华侨“新客”打消对前途的恐惧感,增强了华侨新移民在海外生存的信心。
3.地缘、宗亲社团、庙宇、业缘公会、商会、扮演了早期华侨自治群体的功能。海外早期华侨是自发性移民,得不到政府支持,政府也不护侨。因此,他们唯有靠自身组织的同乡、同宗会馆、同业公(商)会,实行自治和自我保护。对外充当华侨社区的发言人,为华侨争取正当权益,对内调解仲裁华侨纠纷,协调华侨各帮各派利益,组织华侨公共活动,组织筹建华侨社区的公共设施,以至负责华侨婚姻注册登记等。例如,19世纪新加坡华侨福建同乡会馆[22],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华侨的菲华商联总会等,就曾出色地起到上述的作用[23]。
4.海外华侨地缘及宗亲会馆,积极举办文教和公共慈善福利事业,对弘扬中华文化贡献卓著。早期海外华侨建立的同乡、宗亲会馆,均把对会员的团结互助、共谋福利,作为宗旨,把恤贫济急、资助老病回乡、为会员及先人举办丧葬礼仪及庆吊、春秋两祭,为会员子女举办华文教育学校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自身的社会功能。如1823年新加坡广东应和同乡会馆成立时,就规定促进客家五属人士之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作为该馆的宗旨。新加坡福建会馆1937年注册时,也将促进教育事业、捐助公共慈善事业作为该馆的宗旨[24]。马来西亚琼州会馆1933年成立时宣布: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团结,共谋会员福利以及赞助同乡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25]。截至1941年日本入侵前,新加坡华侨同乡会馆,创办的各类华文学校共达370间之多[26]。
5.海外华侨地缘、业缘、宗亲社团,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树辉煌。
如1928年日寇出兵侵占山东济南,阻挠北伐军北上,并杀害我外交官蔡公时,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当时任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总理,他以新加坡树胶公会为依托,发起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二、三月间筹募捐款国币130余万元,汇交南京政府施赈[27]。1935年福建闽南泉、漳等地水灾严重,陈嘉庚遂以福建会馆名义,发起募捐救灾,共募捐国币8万余元,汇回施赈[28]。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威胁。海外侨胞义愤填膺,纷纷以同乡会馆、同业公会和中华商会、宗亲会馆等名义,组织筹赈会,发动会员捐款、捐物、出钱、出力,赈济国难,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嘉庚就是以新加坡福建会馆为基地,才敢于“放胆发动星华筹赈会(1937年)与南侨筹赈总会(1938年)[29]”,担任南侨总会主席,挑起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重担。
菲律宾著名侨领、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他不仅发起成立南侨总会并出任副主席,带病领导全菲律宾华侨,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战募捐筹款运动。在临终弥留之际还嘱咐妻子将遗产中10万美元捐献祖国救济难童。著名侨领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蚊光炎,抗战爆发后亲自兼任全国公债劝募总会暹罗分会付会长,领导侨胞踊跃捐款认购公债,为祖国捐款达600万元以上[30]。
三 地缘、亲缘、业缘关系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
1.扶掖早期华侨创业起步
华侨移民在海外居住国落脚后,开始谋生,有的当矿工、有的当割胶工人、有的当工匠、店员、学徒等。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赚取工资,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积累了少量资本,拟开一间小店铺。经筹措仍感资本不足,于是便借助亲缘、地缘关系,向亲友或向乡朋友融资,得以成全开业支撑门面。有的开小杂货店、有的开小餐馆、有的开理发店、有的开洗衣铺等。例如祖籍南安县的华侨企业家黄奕住,家境贫寒,1884年16岁时随乡亲到新加坡及印尼三宝垄谋生。初到三宝垄时,人地两生、语言又不通,幸得同乡资助。在街头巷尾设一摊点替人理发,夜间则借宿庙宇,过着半饥半饱的辛酸生活。数年后积蓄一点钱,又得到老华侨魏嘉寿(曾任当地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借到一笔钱,开始改业从商。每日肩挑日用杂货及食品,走衔串巷或沿村镇叫卖,至1890年才熬到一间正式商店。1895年以后改专营糖业为主,成立日兴行,获得可观利润。至1920年便发迹成与黄仲涵等齐名的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这一[31]。
早期华侨初创的商店企业,多数是家庭式企业。其特点之一是资本少、规模小、从业人员不多。借助同乡及宗亲友人帮助融资,得以迈出创业第一步难关;特点之二是这种家族式企业其老板和员工大多是同宗家人、同乡或亲友。五缘文化的群体意识,同宗同乡之间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信任感,以及亲情关系笼罩着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
2.有利于华侨企业编织商业网络
借助地缘、亲缘、业缘群体意识,拓展人际网络关系,发展商务和供销往来,这是海外华侨华人企业家建立商业网络,常用和有效的经营策略。凭借这张关系网络,以取得对方的信任感。有时虽互相间彼此并非老相识,但只要是同乡或同宗,便表示互相信任、给予某种方便。这种群体意识,在海外华侨华人企业和商务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时这种群体网络关系,简直成了一种商业关系网和信贷网。利用它甚至“无形可以变有形”,“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可以得到对方的赊购商品或借款、贷款等。因此,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常流行一句话:看在同乡、宗亲或同行面上三分情,生意便好谈、好作得多。
3.业缘团体,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工商界,维护和争取合法权益,调解内外纷争,发挥出色作用。
成立于1904年的马尼拉中华商会,在本世纪50年代,确定其宗旨为:“奉行中菲国策,发展菲华工商业,团结菲华工商界,谋求合法权益,增进当地社会建设,赞助慈善福利、文教事业,敦睦中菲友谊[32]”。二十世纪上半叶,菲律宾排华法案叠起,严重威胁华商利益。例如,1921年菲律宾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菲全国商店必须以英文、西班牙文或菲文任一种文字建立账簿,引起菲华商界的恐慌。面对此严峻形势,中华商会奋起抗争,推选代表多方与美菲当局交涉,终于在1926年促使美国大理院判决该簿记案无效[33]。又如,1924年马尼拉市一华侨商人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一时谣言四起,结果酿成排华风潮,许多华人商店无幸遭袭击、抢劫。马尼拉中华商会立即出面联合善举公所,召集菲华各社团紧急会议磋商,派代表与菲政府交涉,终于平息了此次风潮[34]。
4.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网络,为海外华人企业家发展成企业集团提供条件。
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华绝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其经济已融入当地民族经济。特别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实行政策调整,采取放宽限制,鼓励华人资本投入国内工业建设。例如,印尼苏哈托总统于1967年和1968年先后颂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令》和《国内资本法令》,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华人资本采取利用其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鼓励华人资本由商转工。至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印尼华人企业基本上完成由专门经营商业向经营工业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许多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华人企业集团脱颖而出。除上述政策性的决定性因素外,华人原有的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网络,也为华人企业集团的产生提供有利条件。例如,印尼华人林绍良企业集团,主要由“三林集团”和“林氏集团”两个部分组成。而“三林集团”是由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兄弟合创的。其由亲缘关系结合的鲜明特色自不待言。再如,在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中,“就多数而言,仍以家族统治和管理为主。”“郭兄弟集团在国内外创办的重要企业,由郭鹤年、郭鹤举、郭鹤尧兄弟及其子侄……分任领导,而集团首脑一向由郭鹤年担任。云顶集团及其所属主要企业,由林梧桐、林国泰、林其华父子分任主要领导职务[35]。”这些都是由家族亲缘关系的资本构成企业集团的主体,而且又主宰了企业集团决策大权的典型例证。
5.地缘、亲缘、业缘团体,为华人经济步入国际提供条件
自60年代末70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一些华人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世界许多集团性、区域性、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也纷纷出笼。如欧洲共同体、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77国集团、东盟组织、石油输出国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阻挡的潮流,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增进各国华人之间的联谊和信息交流,维护各国华人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基于此,自70年代以来,各国许多原有华人宗亲社团、地缘性同乡社团及业缘性社团等,便通过联络,由国别进而地区性,再发展为国际性的联谊组织。
例如,1971年世界首届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举行,它是客家人世界性的联谊组织,截至1994年已举行过12届。为加强世界潮州人同乡的联系,促进经贸活动,1981年11月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在香港举行,至1993年已举办过7届。1986年12月,第一届世界林氏恳亲大会在曼谷举行,至1993年已开过6届。1988年10月,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新加坡举行。1990年5月,第一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新加坡举行,至1994年已开过3届。1991年8月,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其宗旨是发扬华人勤俭苦干,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增进彼此的了解,交换经验和讯息,共同探讨关心的问题,以便为其所居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36]。
当然还应当指出,“五缘”群体是历史的产物,渊源悠久,受旧时代,旧意识的影响,因而具有两重性。除了其团结互助、和衷共济、崇尚正义、扶贫济困、助人为乐、诚信守约、对文教公益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等积极主导面外,也存在一些诸如小团体意识、排他性、地方帮派、搞酬神迷信等负面意识。因此,必须因势利导,既发扬其长处,积极主导的一面,又要注意抑制和防止其负面意识表现。
在这方面,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早在1929年,陈嘉庚就主张废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实行分帮选举的制度,指出分帮选举“不惟选不择材,且地方主义、封建色彩浓厚至极[37]。”1945年12月,陈嘉庚在《我之华侨团结观》一文中,提醒当时在华人社会中存在一些不利团结的现象,呼吁新加坡华侨各帮促进团结,倡议裁并大小林立的会馆,各帮的华文学校应统一办理[38]。“这些划时代言论,可惜都未能为当地政府与当时商会会董所接受。[39]”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地华侨宗乡社团携手合作投入民族救亡运动,使存在于宗乡社团之间的一些负面意识,消声匿迹,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
四 展望
二战以来,就东南亚而言,约90%以上的华侨已入籍所在国,政治上已认同所在国,经济上已融入所在国民族经济组成部分。原来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已当地化,宗乡、业缘等群体,已失去其自治性功能,其性质已变成文化和慈善福利的团体,不仅面向华人会员也面向当地社会服务。当今东南亚国家除印尼外,多数采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政策。使华人(华族)的中华文化名正言顺继续扮演为当地社会服务的使命,且与其他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成为居住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马来西亚自1983年以后每年均举办“华族社团文化节”,颇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因此,“五缘”文化只需加以当代转换和诠释,便可继续发扬。既为当地主流社会服务,又为当地华族会员服务。它仍然是华族之间开展联谊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根天然联系纽带。
至于日本,则与东南亚国家不同。截至目前,日本华侨人数远比华人多,华侨社会尚未当地化。传统的地缘、业缘社团仍然发挥着自治的主导作用。日本华侨特别重视寻根问祖活动,使年轻华侨不忘却自己的祖根。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曾先后于1984、1991、1995年,组织旅日福建籍华侨两次回故乡福州、一次回祖国首都北京(1995年)进行寻根问祖恳亲活动。并且在1996年11月10日至14日,第四次组织旅日福建华侨回故乡福清市,举行第36届恳亲大会,通过寻根访祖增强对祖国和故乡的感情。当然,日本华侨社会的日益当地化,也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西欧、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和日本则有很大差异。战后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数目增加很快,其中绝大多数是近20多年的新移民,他们年纪轻(多数在20-40岁之间),文化素质较高(平均在中学以上,其中大学以上占比例不小)。由于他们多是新移民,所以他们创办的同乡社团或联谊群体,历史短浅。基于这些国家都实行宽松的多元文化政策,加之他们多数是从祖籍地来的第一代新移民,与祖籍地亲友仍保持千丝万缕联系,因而对祖籍地和中华文化怀有浓厚的感情,而“五缘”文化则是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今后与祖籍地长久保持联络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根坚韧纽带。
以上粗浅看法,就教于诸同仁,旨在抛砖引玉。
注释:
[1]国内缘文化研究动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P.63、66。
[2]林其锬:“五缘”文化的承传与变异见《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一书P.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国内缘文化研究动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P.63、66。
[4](马)谢爱萍:族群关系与文化因素,(马)《星洲日报》1995.1.1
[5]《辞海》(下)P.3510,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P.24,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京出版。
[7]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团行”。
[8](意)马基雅维里(李活译):《佛罗伦萨史》P.63,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9](比)亨利·皮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P.160-165,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7,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孔子:《论语·颜渊》、《论语·子路》。孟子:《孟子离娄下》。
[12]孔子:《论语·为政》。
[13]《汉书·董仲舒传》。
[14]孔子:《论语·学而》。
[15]《孟子·公孙丑上》。
[16]孔子:《论语·为政》。
[17]孔子:《论语·宪问》。
[18](新)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二册)1974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19](新)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P.194-198、23,1974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20]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1](新)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P.72、58。
[22](新)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P.72、58。
[23]宋平:《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P.136-143、3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24](新)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P.194-198、23,1974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25]转引自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P.211。1995年1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26]林远辉、张应龙:《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史》P.496,1991年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
[2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P.22、31,1946年新加坡出版。
[2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P.22、31,1946年新加坡出版。
[29](澳)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P.129,198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30]黄小坚等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P.262,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31]蔡仁龙等:《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第一集)P.116-119,1989年海洋出版社出版。
[32]宋平:《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P.117、117、118
[33]宋平:《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P.117、117、118
[34]宋平:《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P.117、117、118
[35]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P.108,1995年5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36]方雄普、许振礼编著:《海外侨团寻踪》P.321,1995年10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37](澳)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P.201,198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3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39]同上注第[37]P.201。
